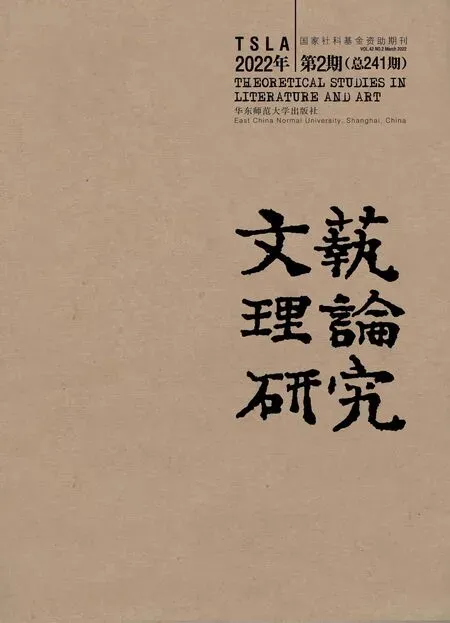符號結構與感覺重構
馬大康 王正中
一、 行為、語言、符號及其文化慣例
在《符號建模與審美創造》中,我們曾專門闡述了符號建模的三個序列: 行為建模、語言建模,以及其他符號建模。行為建模是在生物體與世界打交道過程中形成的,是生物體關聯世界所構建的“關系模式”。這種關系模式將生物體與世界融為一體,相互適應,既賦予世界以生命結構,又積淀為生物體自身的無意識經驗,形成生物體的本能。人類就繼承了生物體這一珍貴饋贈。語言建模則建立在行為建模的基礎上,是對無意識經驗的歸類、凝聚和抽象,由此形成具有外延和內涵的“概念”,形成“概念/音響形象”的語言。這是一個巨大的飛躍。語言建模享有相對獨立性,這使得人與世界之關系模式發生了實質性變化。它在建立人與世界聯系的同時,又將人與世界相區分,將萬物相區分,進而構建了人類意識與意識對象,于是,一個澄明的世界誕生了(馬大康178—190)。從語言與意識同步形成而言,語言建模本身就已經是皮爾斯意義上的符號活動,也即言語行為。
語言具有對象化能力,并因此具有符號化能力。語言可以將行為(姿態、動作、表情)從人的身體上強行剝離開來,作為“對象”來看待和解釋,于是,行為也就成為表征無意識經驗的符號。可以說,正是由于語言和意識的誕生,行為建模才轉化為皮爾斯所說的“符號”,我們稱之為“行為語言”。自此,語言建模攜手行為建模共同構建了所有其他符號。
三種不同類型的符號具有不同的施行方式和特性: 言語行為構建了人與世界的“對象性關系”,這種二元關系可以通過觀察、分析、認識來把握世界,人類意識及精神和理性就建基其上;行為語言則構建“非對象性關系”,這種一元關系只能借助于體驗、直覺、悟解來把握世界,構建無意識經驗,塑造身體,且直接體現著情感形式和生命形式;由于其他符號是由行為建模與語言建模共同構建的,因此兼有兩種迥然不同又相反相成的性質,并且最終可以用言語行為與行為語言的張力關系予以解釋。人的感覺、感受背后就潛藏著符號建模過程,并運用所有各種類型的符號來把握世界,以及構建文學藝術的可能世界。
所有符號活動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賴文化慣例(社會規約),否則,符號就喪失了社會交流功能。這種慣例并非有明確條文規定的規則,而是在符號實踐過程中形成的范例。在文學藝術活動中,符號慣例雖然在源頭上與生活實踐分不開,卻直接借鑒自藝術圈公認的文學藝術典范構成的范例。每個文學家、藝術家都以自己的方式來理解典范,擇取和分享慣例,并使典范與慣例構成張力關系,由此來繼承文學藝術傳統。當文學家、藝術家以獨特的方式來挑戰既成慣例,改造慣例,以致造成某種斷裂,進而獲得部分文學家、藝術家的承認,形成新的文學藝術共同體,逐步更新了符號慣例時,一種新的文學藝術風格和流派就誕生了。但是,當文化慣例的更新不僅涉及作品風格,而是針對文學藝術的基本觀念和制度,也就是說,這種改變不是停留于符號慣例層面,而且深入符號背后的言語行為,通過宣示行為來再造文學藝術觀念和制度,變更言語行為范式,調整言語行為與行為語言的張力結構,改變感覺、感受背后的“建模”方式,它將轉移人的注意力,重構人的感覺配置,重塑人的感官,制造文學藝術發展過程中的重大事件。
二、 符號·儀式·文學藝術
在《古代藝術與儀式》中,哈里森追溯了藝術與儀式的共同根源,認為它們都源自渴盼生命死而復生的強烈愿望,兩者有一種“渾然不分”的共生關系。她指出:“藝術并非直接源于生活本身,而是源于人類群體對于生活需求和欲望的集體訴求活動,即所謂儀式。”(哈里森134)
《呂氏春秋·古樂》記載:“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蓄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為五弦瑟,以來陰氣,以定眾生。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 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呂氏春秋》101)古代的詩、樂、歌、舞是用于儀式活動的,以此來溝通神人,調和天地陰陽,而且它們可以統稱為“樂”。《禮記·樂記》說:“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胡平生 張萌758)所謂“樂”并非僅指現代意義的“音樂”,而是同時包含著詩歌樂舞,并含有“使天地相和”“使人(神)愉悅而有所得(德)”之義。至于精致的紋飾圖像則主要出現在儀式所用的禮器上。因此,我們今天所謂的文學藝術原本就圍繞著儀式活動緊密結合在一起,是多模態共存的,與人類生存活動密切相關,有著明確的功利目的性。“共情”“移情”則是其主要特征,也即行為語言占據著主導地位,致使儀式參與者全身心投入其中,融合為一。
如果我們進一步追問,儀式又是如何建構的,其根據何在,那么,就不得不回到人類符號建模活動。人類文化活動本身就是象征符號活動,而所有的符號都建立在行為建模與語言建模的基礎上,是雙方相互協作的成果,因此,最終都可以用這兩者間的張力關系加以說明。一方面,行為建模強勢貫通并融合了人與世界,把人的生命結構賦予世界;另一方面,語言建模卻將人與世界相區分,把世界設立為人之意識對象。由于雙重建模的協同作用,對象世界已然成為擬人化、生命化的世界,對象也因享有生命性且具有神秘力量而轉化為至高無上的“神靈”。這就是萬物為神的泛神論世界。儀式就是人類為了自身生存,祈求和利用神靈而建立的特定行為程式,吟誦歌舞則是對神靈的敬獻和企盼,是不同類型的符號建構,只不過它們還是原始儀式的有機構成部分,是全體成員共同參與體驗的集體活動,并沒有從中分化出“觀賞者”而成為現代意義的文學藝術。
在《藝術社會史》中,豪澤爾又進一步對巫術與禮儀作出區分,對舊石器時代的自然主義映像與新石器時代幾何圖形風格作了比較分析。他認為,舊石器時代還處于巫術觀念籠罩之下,人們尚未萌生神的觀念,藝術與現實的界限是模糊的,映像就是現實對象,是施展魔術的手段,巫術對映像的操控,就是運用魔力對現實對象本身的操控,兩者是同一的。這也要求藝術風格是自然主義的,需要有熟練技巧的巫師來制作,模仿過程本身就具有巫術功能。新石器時代,農耕和畜牧替代了狩獵,分散的人群改變了群龍無首的狀態,集聚為更加集中的、受統一領導的社群,泛靈論成為主導性世界觀,禮拜和祭祀取代了巫術和魔術,映像逐漸演變為象征圖像,風格則趨向于形式化、抽象化。“巫術的世界觀是一元的,在它看來,現實世界的萬事萬物全都密切相連,是一個無間隙、無跳躍的連續體;泛靈論是一種二元世界觀,它把知識和信仰納入一個由兩個世界構成的體系。巫術具有感覺論傾向,著眼于具體事物;泛靈論具有二元論傾向,喜歡抽象思維。前者關注此岸,后者關注彼岸。正因如此,舊石器時代的藝術模仿生活和現實,新石器時代的藝術則塑造出一個經過風格化和理想化并且和經驗現實相對立的超驗世界。”(豪澤爾11)
豪澤爾很好地從人類生存狀態變化的角度來闡釋原始藝術的演變,但是,假如結合符號系統二維張力結構的變化,便可以更明晰地看到背后隱含的要素。巫術是人類早期的智慧。語言的產生才剛剛破除了混沌蒙昧,開啟了人類意識。但是,在符號活動整體結構中,由于行為建模仍然占據著壓倒性地位,人也就難以從一元論中擺脫出來,他尚未從混沌的世界中完全超越出來,更未享有由語言構建的形而上世界,未能真正享有精神生活,萬事萬物依舊是相連相纏、相互感應的。這還只是個巫術世界。只有當社群擴大越來越強調語言交流的重要性,語言愈加增強其規約性及相對獨立性,這才逐步奪取了應有的權力。語言的相對獨立性,使其具備了超越現實、構建形而上世界的能力。于是,不僅人與物、物與物被明晰區分,經驗世界與超驗世界、看得見的世界與看不見的精靈世界、肉體與靈魂也發生了分裂。前者是身體可直接經驗的,后者則主要是語言對經驗的重構,只能通過想象來體驗。盡管行為建模將人自身的影像投射給了現實對象,并賦予對象生命性,卻已經無力徹底彌合雙方的間距,只能由語言建模把它設立為藏匿在現實對象身后、高高在上的神靈。這就是泛神論的世界,一個既具有神秘力量又朝夕相處、近在咫尺的神靈的世界,一個需要祭拜儀式才能支撐生存信心的世界。與此同時,語言還將具體映像加以概括、抽象,使“藝術”趨向于觀念化、風格化、普遍化。
語言是區分,是抽象。自從人類享有了語言,就再也無法停止自身的理性化腳步。言語行為在符號系統張力結構中日趨強勢,也就勢必推動人類不斷地區分世界和認識世界,使原本渾融的世界日漸澄明,人類理性日益健全,物我一體的融貫狀態遭逢徹底瓦解。人與世界的分裂、人對世界的認知又漸次破解了神秘,驅逐了神靈。神靈開始從物的世界中撤離,遁入一個遙不可及、不可知的世界。這就是“世界的祛魅”,也是原始儀式消亡的根本原因。于是,儀式中的吟誦歌舞因其激發情感的娛人作用而流落民間,它們不再僅僅被奉獻給神靈,而主要成為人類自身觀賞、享樂的藝術。失去儀式的支撐,也就注定各種藝術類型間的維系紐帶斷裂了,文學藝術相互交融的關系也分崩離析。紋飾圖像由于依附在獨立的物質載體上,勢必最容易從儀式中分離出來。
柏拉圖對待文學藝術的矛盾態度,就緣于他處身儀式逐步解體的理性化時期。對于文學藝術作為儀式的有機部分,柏拉圖十分推崇文學藝術,認為詩人可以借此進入迷狂狀態而與神靈相溝通,并因此把握真理。可是,對于淪為娛樂觀眾的東西,他又認為文學藝術是蹩腳的模仿,應該將其驅逐出理想國。柏拉圖自相矛盾的二元態度,正顯現了文學藝術脫離儀式而進入民間娛樂的漫長的過渡性階段。
在《日知錄》中,顧炎武說:“歌者為詩,擊者,拊者,吹者為器,合而言之謂之樂。對詩而言,則所謂樂者,八音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是也,分詩與樂言之也。專舉樂則詩在其中,‘吾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合詩與樂言之也。”(顧炎武228)又說:“《詩》三百篇,皆可以被之音而為樂。自漢以下,乃以其所賦五言之屬為徒詩,而其協于音者則謂之樂府。宋以下,則其所謂樂府者,亦但擬其辭,而與徒詩無別,于是乎詩之與樂判然為二,不特樂亡,而詩亦亡。”(226—227)
孔子正處在“禮崩樂壞”的年代,周王權衰落,王綱解紐,儀式式微,采詩制度失去了重要性,詩歌樂舞也就散逸了,所以孟子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所謂孔子“刪詩”,一方面收集、保存了散逸的詩歌;另一方面又為詩與歌的分裂埋下了伏筆。盡管詩經仍然被人傳唱,可以被之以音樂,而歷時久遠的書面化流傳卻不能不令詩歌逐漸遺忘音樂。“詩亡然后春秋作”(楊伯峻177)正意味著: 詩歌隨儀式廢弛而衰落,于是,記載并規范行為的歷史著作也就竊取了詩的重要位置。書面文化的興起,更貶低依賴口頭傳唱的詩歌的地位,導致散文化的《春秋》誕生。及至漢代發明紙張,唐代以詩取仕和宋代出現印刷術,書寫文化、印刷文化日益蔓延、流行,物質化的文字成為一種重要的、間接的交流媒介,詩才終于從詩歌樂舞一體中漸次獨立出來而成為“徒詩”,一種特殊的藝術接受方式“閱—讀”,也從文字的實用性中超越出來,在藝術感知中日益突顯其重要性。最初,詩作為儀式敬獻辭,是詩樂歌舞的核心和靈魂,詩的離去,也就導致了歌、樂、舞相互分裂。雖然在民間,各類藝術仍然相互糾纏,這種分離狀況主要局限于雅文化中,因為文字僅為少數文士所占有,但是,對文學藝術的走向卻產生了巨大影響。在這一文化變遷背后,又潛隱著文字對人類理性的助長。書寫文化的繁榮加速了人的理性化進程。
在討論人類理性發展過程的問題時,韋爾南指出語言從口頭向書寫轉變的重要性。他認為,在口頭文明中,詩歌作為一種有節奏、能伴舞的歌唱,占據著智力舞臺的前臺。“這一口頭體系建立在某一種同情活動的基礎上,它使聽眾像中魔一樣被詩行流露出的激情所打動。”散文的出現是一個重大的改變,它意味著從口頭歌唱到文字作品的轉化。這是個根本性轉變。文字書寫不僅開創了話語邏輯的一種新方式,而且開創了作者與公眾交流的新方式。文字作品是可以反復閱讀的,在某種程度上會激發批判性思索。“由此,人們不是把純粹的混沌放在起源,不是讓一個強加秩序的至高無上者在這一混沌中誕生,而是探索事物的本原都是些什么,或者作為一切之基礎的那個本原(Principe)是什么。”(韋爾南240—241)文字以其物質性、經久性、間接性,改變了口頭語言的直接性、現場性和倏忽即逝的特征,強化了語言的獨立性,有效拉開了人與語言的間距、人與自我思想的間距、人與語言所構建的世界的間距,以使批判性反思有了可能。在此過程中,以共情為基礎的神話敘述日漸衰微,一種趨向于客觀化的全新的陳述誕生了,人類理性成長了,敘事也因往昔神圣性的消退而蒙上人世塵埃。理性化過程勢必導致人類活動領域的細分,導致學科畛域的界定,也導致不同藝術類型的劃分和感官感覺的分工。
人類理性的誕生扼殺了種種神靈,卻無法抹去人類自身的無意識經驗,無法抹去行為語言記憶,無法祛除貫通、融合人與世界的凝聚力量。只不過它們不再作為儀式活動的基礎,而成為文學藝術活動的必要條件,并在理性的照耀下日漸喪失了神圣性。恰恰是潛藏在無意識深處的行為語言記憶,蓄積著最為深刻的生存經驗;也正是行為語言所具有的融貫人與世界的聚合力,賦予文學藝術如癡如醉的無限魅力,以及無法言說的深長韻味。言語行為與行為語言深度協作,開創了一個想象的世界,在這里蓬勃著人類最為深沉、古老而又鮮活的經驗。
在文學藝術活動中,言語行為與行為語言的深度融合所形成的張力關系,使創作者或欣賞者與審美世界之關系總是處于或二元或一元的張力關系和過渡狀態中。在對藝術活動的分析中,梅洛-龐蒂曾力圖彌合觀看與被觀看、把握與被把握、記載與被記載、主體與客體的分裂狀態,他將主動性與被動性視為渾然一體、無法區分的共在,把創作視為“任由存在”,或者是“空竅”自行敞開,是我們與世界的肉身相遇,突出藝術的肉身性,以此克服二元對立。究其實,梅洛-龐蒂始終沒有真正跳出主客二元論的陷阱。人與藝術世界之關系是極其復雜多變的,雙方既是二元的,又是一元的,時時刻刻處于張力關系和過渡狀態中。
三、 語言、符號的虛擬意指與審美隔離機制
在萬物為神的世界中,言語意指指向了神、物合一之對象,而在神、物關系解體之后,言語意指則發生了分裂: 其一,指向現實的物質世界;其二,指向不可知之神靈,并且由于吟誦歌舞最終與儀式相分離而失卻神靈的依托,言語意指也就不得不指向虛無。這就是文學藝術活動中具有獨特意指的言語行為。言語的意指意向終于發生了分化。因此,文學藝術并非“說假話”,它并沒有作真假判斷,只不過其言語意指不再指涉現實對象,而是指向虛無,指向一個虛擬世界,由此誕生了言語的虛擬意指,一如瑞恰慈所說的“非指稱性偽陳述”。語言的這一向度為人類構建了一個非現實的生存維度,一個精神得以安頓、靈魂受到庇佑的家園。
在日常活動中,人們運用語言與他人、他物打交道,言語意指也就必然糾纏于人和物,這勢必難以避免功利目的性。特別是語言在構建人際關系時,總是自覺不自覺地將權力帶入其中,以命令、祈求、告誡、規勸、承諾等語力來構建利害關系。可是,一旦言語意指虛無,其功利性就失去效用,失去目的,無所附麗,不能不注銷言語意指本身的功利性。因此,在人與作品世界之間,言語的虛擬意指行為本身就是無關功利性。
約翰·塞爾對虛構話語的邏輯狀態作了很好的分析。他認為,日常話語中的斷言,需要符合語義學和語用學規則,即遵循真實性和真誠性規則,這些規則構成話語與現實世界的縱向關聯。虛構話語則不同。虛構話語雖然需要遵循橫向慣例,即語言內部的組織慣例,卻中止了話語與現實相關聯的縱向規則,即真實性和真誠性,解除了話語與客觀世界的直接關聯。“虛構話語構建一部虛構作品是由于存在一套慣例而成為可能,這些慣例懸置了聯系言外行為與客觀世界關系的規則的正常運作。”(Searle67)言語的意指性也即語言使用者(創作者或欣賞者)的意識意向性。從言語的虛擬意指來看,由于它放棄了人與現實世界的關聯,又遺失了人與神靈世界的關聯,重建了人與虛構世界的聯系,其現實的功利性、目的性也因此喪失殆盡。可是,從虛構話語構建一個虛構世界來看,它又必須遵從既成的橫向慣例,否則,話語就會失去結構功能和交流功能,喪失可理解性。而這些慣例本身是在漫長的社會交流過程中塑造成形的,不能不反映著現實社會的權力關系。因而,虛構話語本身就體現著雙重性: 對于語言使用者來說,它指涉一個非現實的虛構世界,也因此失去了功利目的性;而話語自身的慣例卻早已被權力所玷污,沾染了功利色彩,展示了話語背后的利害關系。虛構話語的雙重性也決定著文學藝術與現實的雙重關系: 文學藝術本身并沒有直接的功利性,但是,構成它的話語慣例卻折射出現實的權力關系,折射出現實社會的不平等,因此,又隱含著對現實的間接評判。
當語言發展出虛擬意指行為,也就為人構建了一個虛構世界,一如馬爾庫塞所說的“異在世界”,一個現實壓抑被撤銷、無意識經驗得以充分涌現的世界,一個深層次行為語言記憶復蘇的世界。于是,言語行為與行為語言深度融合,自由想象的審美世界誕生了。一方面,言語行為以其意指區分了現實世界與虛構世界,展開了一個形而上的精神空間;另一方面,深層次的行為語言記憶因獲得釋放而融貫了人與虛構世界,令人不能不陶醉于這個虛構世界。這是人的無意識經驗充分敞開的境界,是滲透著最原初、最深刻的生存經驗的境界,是人體驗自身解放和自由的境界,是人的肉身親臨其境的狀態,也是莊子之所謂“游心于淡”的精神狀態。這不僅是人類感覺的重大更新,也是心靈的重大提升。
符號的意指是與其背后的言語意指密切相關的。正是語言的區分功能,語言意指的分化及虛擬意向的產生,致使審美無功利性、文學藝術獨立性成為可能。當言語虛擬意指解除了人與現實的關聯而指向一個虛構世界,功利目的性也就無所附麗,審美隔離機制就形成了。在現代化的進程中,當社會分工和商品交換成為一種最為普遍的生活形態,強調審美無功利性和文學藝術獨立性,也就不僅成為文學家、藝術家擺脫宗教和貴族附庸地位的一個有力口號,而且為他們提供了一種謀求自保自重的生存策略。言語虛擬意指的無功利特征也得到了片面強調。于是,文學藝術趁機謀取了獨立身份,審美與日常態度終于發生了分裂,審美世界成為一塊獨立的精神飛地。直至后現代思想來臨,學者們將目光轉向語言的具體用法,轉向語言所遵循的慣例,虛構話語與權力的復雜關聯才重新顯露出來。新歷史主義、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和文化批評就抓住文化慣例來展開批判,從中揭示出篡改、扭曲、操縱慣例的隱蔽權力。
席勒十分推崇審美教育。他痛心于社會等級和分工所帶來的人性分裂: 人被束縛于整體中一個孤零零的斷片上,自己也成為斷片了,并因此造成感性與理性、自然與自由、多樣性與普遍性之間的分裂。席勒認為,唯有借助于文學藝術的審美教育,人才能重新彌合種種分裂,恢復人性的完整性。對席勒的美學觀,韋爾施提出嚴厲批判。他將席勒的美學思想指斥為“反感性的獨斷主義”“剔除了世界的獨斷主義”和“審美獨斷主義”,并認為,其背后的系統錯誤是對審美需要的誤解。這種美學“沒有發展認識和解放感覺的策略,而是發展了控制感覺、消滅感覺和嚴格管理感覺的策略。這是傳統美學最內在的悖論”(韋爾施90)。其實,是韋爾施誤讀了席勒。在席勒美學思想中,人類感性被放在極其重要的地位。席勒認為,對于人類總體而言,感性是“先于”理性而存在的,我們應該“給予自然以決定性的最后發言權”(席勒47)。然而,在現實社會中,理性對人的企望過高,它褫奪了人身上的動物性,這等于在法則之前撤掉了人腳下自然的階梯。因此,藝術作為自由的女兒,就必須擺脫現實,越出需要,在“游戲沖動”中,將“感性沖動”與“形式沖動”結合在一起,席勒稱此為審美心境的“零狀態”,同時又是“最高的實在狀態”。席勒所謂的“零狀態”,即感性與理性尚未分裂的原初狀態,也即“感性在先”的狀態。在此狀態中,理性不再是凌駕于感性之上的權威力量,而成為服務于自然感性的理性智慧。“只有當他的形式活在我們的感覺里,他的生命在我們的知性中取得形式時,他才是活的形象。”(席勒87)因而審美心境的“零狀態”,又必定是“最高的實在狀態”。
在日常生活中,人是不可能處身“零狀態”的,他必須“擺脫現實”,進入彼岸的虛構世界。這是一個“無規定性”的世界,又是“無限規定可能性”的世界。在這里,虛構話語構建著一個虛構的可能世界,描述著虛構人物,賦予這個世界某種形式,而行為語言記憶卻因此獲得了釋放,它將豐沛的無意識經驗投注于這個虛構世界,投注入虛構人物,使形象成為凝聚著濕漉漉的生存經驗、洋溢著自然的生命感的“活的形象”。這是感覺的解放和生命的敞開,也是在一個嶄新層次上實現感性與理性的自由合作。
生命總是行動著的身體,正是行為語言充分體現著生命自身的自然特征。而行為語言與言語行為的深度協作,則維護了身體與精神、感性與理性、自然與自由的統一。一方面,人通過言語行為來構造一個形式世界,理解和解釋這個世界,他無法背棄邏輯和理性;另一方面,人又充分調動了行為語言投身這個世界,體驗這個世界,他回歸于自然的存在狀態,回歸于身體,回歸于生命本身,并且這種回歸又賦予他一個區別于日常狀態的嶄新立足點,一個充分享受生命自由的立足點。當他從生命本身出發來解釋世界時,一種深刻的人性批判就生成了,理性也不得不服從于生命而作出自我修正。文學藝術活動體現著席勒所說的“審美教育”,體現著馬爾庫塞所說的“審美解放”和“新感性”,促進著人性的完整完善。
在人類發展過程中,不僅物質世界被不斷認識、開發和擴展,人的想象力更使得虛擬世界具有無比強大的擴張力,它一邊在現實世界之外開疆拓土,另一邊又不斷侵入物質世界的領地,賦予物質世界虛幻的光環。
當我們將注意力聚焦于某個現實對象時,這一對象也就可以從具體環境中突出來,甚至剝離開來。認知科學稱此為“注意瞬脫與心理不應期”。迪昂說:“一旦注意首先集中在前一項信息上,我們便對其他信息視而不見了。”(迪昂196)注意力的這種特點,與言語意指意向是分不開的,它使得意識所聚焦的對象與所處現實的功能性環境相脫離,凸顯出來,形成叔本華所說的“孤立”狀態。這就促成我們去營造一個虛擬語境來彌補空缺,使對象陷入“互文性”之中,縈繞著虛幻、迷蒙的光暈。我們的無意識潛能因此得以解放,行為語言記憶得以復活,它們既成為展開想象的推動力,又直接參與想象的構建。就如克拉里所說:“當注意力把一個特定的內容從一個更大范圍的認知中隔離出來時,這種分離的活動能夠成為一種生產性活動的開端。”(克拉里107)因此,在伍爾夫凝視墻上的“斑點”之際,她也就敞開了自由舒展的意識流,聯想不由自主地聯翩而至,將她帶入想象的虛擬世界。在此狀態中,個體并沒有與外界失去聯系,而是改變了關聯方式,改變了感受方式: 符號系統的二維張力結構發生了改變和倒轉,行為語言重新占據了主導性地位,凝視轉換為想象及體驗。
虛擬世界的擴展力致使人的審美能力得到了極大開掘。在日常生活與審美活動之間、日常用品與文學藝術作品之間不必再劃出明確的界限,也不必跨越物質界限,只需要改變人的態度,改變語言和符號的意指方式,改變人與對象世界的關聯方式和感受方式,就可以在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之間實現自由轉換,把日常的觀看轉變為自由的藝術觀賞。這正是杜尚創造“現成品”《泉》的奧秘,也是行為藝術的奧秘。同時,這預示著“日常生活的審美化”和“審美的日常生活化”。“非藝術的事物可以被人自由看待,這才是藝術的生命所在。”(朗西埃51)
因此,審美能力既是一種區隔能力,又是一種轉換能力,是兩者的協同作用,并且只有經過必要的審美訓練,才具備這種可能性。在《論悲劇》中,韋爾南列舉了一個驚人的事例: 公元前5世紀,一出講述米利都陷落的悲劇初次上演,竟引發了一場騷亂。韋爾南指出,正是缺乏時間間距導致了這場騷亂:“悲劇方式是一種悲愴的方式,它提出關于人的問題,它自我詢問——而不是詢問當代的事件。”(韋爾南434—435)韋爾南正確地強調藝術欣賞與現實之間的間距,其中,最簡便有效的途徑是設置時間間距,它為觀眾提供一個自由想象的空間,迫使觀眾不得不運用自己的想象力來進入藝術世界,并與現實世界相分離。特別是對于尚未將審美與現實生活作出明確區隔的古代希臘人來說,這種時間間距就更為重要,可以避免因混淆兩個不同的世界而引發騷亂。這種區隔能力是需要通過審美實踐來培養的。“作為取消日常急需且擱置實踐目的的普遍化了的能力,作為無實踐功能的一種持久的實踐傾向和才能,審美配置只有在一種脫離迫切需要的對于世界的體驗中,且在本身就有其目的的活動如學校訓練或對藝術作品的靜觀中,才能形成。換句話說,審美配置意味著與世界的距離(戈夫曼提出的‘與角色的距離’是這種距離的一個特定維度),這種距離是資產階級對于世界的體驗的根源。”(布爾迪厄89—90)因此,具備審美能力的感官只有在審美實踐中才能塑造成形,并且與言語意指意向的分化密不可分。
審美活動中的區隔能力根源于言語行為對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的區分,是語言意指方式的分化,而轉換能力則來自語言意指方式的自由轉換,及其與行為語言二維張力結構的變化。在日常活動中,人總是啟動現實行為來應對具體處境,盡管這種行為受到無意識經驗和意識的雙重掌控,但是,行為畢竟是真實行為。而在虛構話語的虛擬指涉中,潛意識經驗得以復蘇,行為語言記憶獲得充分激發,并協同言語行為共同構建一個想象的虛構世界。從這里就可以看到審美活動與日常活動間的差異: 日常活動所啟動的是現實世界的真實行為,它受制于現實活動的目的性及規約性;審美活動所激發的則是虛構世界的行為語言記憶,它復現了深層無意識經驗,讓欣賞者充分體驗審美情境,產生一種身臨其境的感受和共鳴,體悟了深刻、純凈的生命感,卻并非啟動真實行為本身。當人們放棄了日常的目的性行為,而轉變為對深層的行為語言記憶的召喚,也就必然擺脫了社會規約的束縛,使行為變身為虛構世界中的想象的自由行為。這就是所謂的“審美抑制”和“審美自由”。因此,唯有語言的意指發生了明晰的分化,虛構世界(虛擬語境)與現實世界之間建立了邊界,人類審美能力得到了顯著提高之后,審美活動與日常活動之間的自由轉換才成為可能。自此,文學藝術創造者和觀賞者都能夠自由穿行于審美與日常兩個世界,而不至于造成淆亂。“注意力不是某個早已成形的主體的一項官能,而是一個符號,與其說是主體的消失的符號,還不如說是主體的不穩定性、偶然性和非實體性的符號。”(克拉里35)在文學藝術活動中,作為“解釋的共同體”實質上就體現于藝術符號上,它同時隱含著兩個對立共存的要素,即行為語言與言語行為及其慣例,它們是人類感覺、感受世界的共同尺度,規定著感覺、感受的方式和秩序。正是符號及慣例的共享性,為“解釋的共同體”提供了基礎。
因此,在語言意指尚未發生明晰分化,虛構世界與現實世界之間尚未形成邊界,審美教育尚不普及之際,人為地設立藝術與非藝術的邊界是文學藝術欣賞的必要條件。特別是戲劇往往需要“第四堵墻”協助造成區隔,因為戲劇直接以人體作為表演符號,所以更容易與現實情境相混淆。隨著觀眾審美能力的提升,導演們也就可以不斷嘗試拆除這堵墻。
四、 語言、符號的自我指涉與感覺配置及重構
語言所具有的相對獨立性,使它獲得了對象化能力,這不僅可以將世界設立為對象,而且可以將語言自身設立為對象,致力于將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語言本身,讓語言重新煥發生機。此際,語言所指涉的對象不再是語言之外的世界,這是語言的自我指涉,甚至指涉語言的形式、語言的組織結構方式。就如穆卡洛夫斯基談到詩歌語言時所提出的“前推”:“在詩歌語言中,前推的強度達到了這樣的程度: 傳達作為表達目的的交流被后推,而前推則似乎以它本身為目的;它不服務于傳達,而是為了把表達和語言行為本身置于前景。”(穆卡洛夫斯基19)在文學藝術活動中,當語言和符號本身成為關注的焦點,文學藝術所傳達的內容已不再具有分量,處于前景位置的是文學藝術的形式、它的符號結構方式或組織法則,也即慣例,文學藝術于是成為“純詩”,成為“純形式”。
在古代中國,無論詩歌作為儀式的組成部分,還是察知民風民情的詩史,或是熏陶品性的詩教,其所指內容都具有非同凡常的重要性,而聲律形式則并不是關注的重點,所以,沈約解釋說:“若斯之妙,而圣人不尚,何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于訓義,非圣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云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為’。”(沈約137)
一方面,魏晉以降,權力更替頻仍,儒家獨尊的地位受到沖擊,儒、道、釋同時并存,玄談之風和山水詩流行,都顯示了文士逃避現實社會的心理狀態,這同時令詩人逐漸厭倦對現實的關懷,轉而以賞玩的心態競逐詩歌形式,特別是聲韻之美。另一方面,在詩樂一體的狀態下,詩歌語言本身所具有的音樂性往往湮沒于樂音之中,并沒有顯示自身的獨立價值,雖然在實際創作中語言聲韻一直被廣泛采用,卻并非作者刻意而為。而當詩歌與音樂逐步分離而成為徒詩,為了吟誦之暢、之美,語言自身音樂性的價值也就凸顯出來了。詩歌語言的指涉從所指轉向能指自身,語言能指的聲律開始成為詩人目光審視的焦點和特意修飾的鵠的。于是,佛經的模擬轉讀之聲適巧為詩歌語言提供了啟示和借鑒。
甄琛曾批評沈約“不依古典,妄自穿鑿。”沈約則答復說:“經典史籍,唯有五聲,而無四聲。然則四聲之用,何傷五聲也。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上下相應,則樂聲和矣;君臣民事物,五者相得,則國家治矣。作五言詩者,善用四聲,則諷詠而流靡;能達八體,則陸離而華潔。明各有所施,不相妨廢。”(沈約468—469)這一段辯駁,很清楚地顯示詩歌與音樂逐漸分離的途程中,詩歌、音樂兩種不同的聲律要求在當時仍然有所混淆。甄琛所言“不依古典”強調的是音樂的宮商角徵羽五音,而沈約提出的四聲則明確指語言的平上去入。前者指音樂的音階,后者指語詞的調值。沈約明了這一區分,所以他說“各有所施,不相妨廢”。由于文士常常借用音樂用語來比喻語言聲韻,也就延續了這種誤解。
語言的自我指涉,凸顯了詩歌語言聲韻的重要性,塑造了感性對形式的敏銳性。在《謝靈運傳論》中,沈約提出:“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后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沈約484)這種過分強調語言聲韻的做法,雖然是對文學語言的自覺,卻不免墮入形式主義的泥淖。
朗西埃對黑格爾關于“理想對自然的關系”的論述作了進一步闡發。他指出,在藝術轉向非功利的過程中,藝術題材的變化產生了重要的過渡性作用。弗萊芒、荷蘭畫派的題材不再是宏大事件和尊貴人物,而轉向了日常生活和普通人。一旦任何現象都可以進入作品題材,題材的重要性就喪失了。于是,繪畫不再包含某種深刻寓意,不再頌揚某個威嚴的人物,不再是一種道德示范和勸誡,作品好像只能展示畫面的造型和光亮、畫線和上色,只是供人欣賞表面的游戲,供人享受純粹的樂趣,因此趨向于“無關用途”,趨向于“自治”。如果說,語言和符號虛擬意指從根本上為文學藝術的獨立提供了可能性條件,那么,語言和符號的所指從尊貴、威嚴的題材轉向日常普通題材恰恰起到了過渡性作用。作品題材涵義的貶損自然使自身流失了受關注度,它與現實相關聯的紐帶松懈了,作品逐漸走向“自治”了。當語言、符號的所指內容不再重要,并解除了所指與現實的聯姻,一個脫離現實語境的能指就占據了前景位置,非現實的虛擬意指也借機凸顯了出來,這就為文學藝術活動帶來了更大的精神自由,也使注意力發生了遷移。從史詩到小說,再到先鋒小說、后現代元小說的變化軌跡也展示了這一漫長的蛻變過程。
西方現代主義文學藝術就朝著自我指涉這一方向演變,由此造成人的注意力從作品所描述的內容向形式轉移,造成感覺的重新配置和重構。這種對文學藝術符號本身的關注,強化了藝術形式及其肌理的重要性。“正是這種肌理,讓一個形式、一抹色彩、一段激情、一處留白、一發動作、一層平面上的一點閃光,給人帶來了感動,讓其成為事件,然后才聯系到藝術創作的理念。”(朗西埃2)這一轉向使得文學藝術脫離了普通大眾的生活經驗,脫離了日常的行為語言記憶,脫離了他們所熟悉的日常感受和情感,成為那些精通藝術符號的專家的專利品,成為文學家、藝術家小圈子內部“自戀式”的自我欣賞。凡是沒有經受過專門訓練,缺乏對藝術符號及慣例的熟悉和理解的人們,就被拒斥于文學藝術殿堂門外,失去欣賞文學藝術的資格。
在《藝術的去人性化》中,加塞特指出: 對于大多數人來說,美學享受與日常生活中通常的好惡態度沒有本質區別。當人們對一部戲劇中的人物命運產生興趣,他們就喜歡上了這部作品。人物的愛恨情仇打動觀眾的心靈,他們與人物同悲共喜。在詩歌中,讀者感興趣于詩人的內心生活。在繪畫中,人們尋找自己熟悉的人物和景象。加塞特認為,這些都并非審美感受。真正的審美感受存在于新藝術中,這些藝術趨向于“純藝術”。“在這個過程中,最后總會有那么一刻,作品中的人性化成分會減少到幾乎看不出來,而這樣的作品,便只有具有那種特殊藝術感的人才能有所理解了。這種藝術只屬于藝術家,而不屬于人民大眾;它將是小眾藝術,并不通俗[……]新藝術是藝術化的藝術。”(加塞特10—11)加塞特所說的“新藝術”抽空了藝術所要敘述的日常內容,以形式創新迫使欣賞者的注意力不得不轉向藝術的形式因素,符號的意指意向不得不轉向符號形式自身。這些失卻所指內容、抹除人物的作品不再引起人們所熟悉的情感,不再具有熟悉的人性。但是,這并非說藝術從此成為單純的藝術形式,恰恰因為它已經從日常生活語境中超脫出來,所以能夠更深入地激發行為語言記憶,釋放無意識經驗。只不過這種經驗不是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習得的經驗,不是那種淺表層次的無意識經驗,而是更深層次的無意識經驗。由于這種深層次的無意識經驗來自生物體,歷時久遠,對于人類來說已經顯得意義模糊、無法解釋,它們從熟悉的日常生活和具體物象中抽離出來,只留存著生命體對光、線、色、聲音、運動、節奏、形式肌理的生物、生理反應,這些反應已經被“去人性化”了。
以加塞特的角度來看,音樂是藝術中最先“去人性化”的門類。特別是無標題音樂,符號的所指內容被徹底淡化,涵義已經漫漶不清而只剩余樂音的符號形式,只剩余音素、音響、節奏、旋律及和聲,成為藝術“去人性化”的范例。現代抽象畫則追隨著音樂去尋求自己的獨立性,與現實物象解除聯姻而專注于繪畫符號自身。它們所熱衷的“格子”就顯示了反自然、反模仿、反實在的藝術主張,致使符號所指意義遭到貶值,由此迫使注意力轉向能指本身,強調了符號能指的獨立性。在抽象畫的背后,言語行為發揮了一種特殊作用: 既強勢地迫使意指意向轉向能指自身,又弱化和模糊了繪畫符號的概念意義。
一旦繪畫轉向符號結構,立體主義就進而將物體視為可以拆卸的結構零件,加以重新組裝和構建,打破視覺習慣和理性觀念,將物體的不同側面恣意拼合在同一個平面上。“立體主義拼貼畫把自然的物的視覺世界換成人造的法典化的符號語法。”(克勞斯25)舞蹈的身體動作也逐漸擺脫描摹生活、敘述情節、塑造人物、抒發情感這些目標,轉向探索身體運動本身的可能性,不斷挑戰動作極限,展現力的多樣形式。就如朗西埃所說: 在這種舞蹈中,身體抽離了肉身,消融在形式之中,轉化為一種力量的回旋。它描摹飛翔而不畫鳥,描繪漩渦而不畫浪,描述綻放而不畫花。“這種新藝術,是新身體的藝術,它除去了肉身的重負,簡化至線條和色調的游戲,在空中旋回。”(朗西埃109)凡此種種,都促成人的注意力的轉移,特別是無意識經驗從個人轉向深層次的原初經驗,造成對感性的重新發掘,構造了一種嶄新的觀看方式。
比較而言,文學則步履維艱。語言幾乎難以洗清所指內容,即便將能指形式推向前景,也無法徹底清除概念意義,難以抹去語言所指所表述的人或物或事,難以徹底地去人性化。瓦萊里就深切體會到了這種艱難。一方面,他提倡“純詩”,致力于改造作為“實踐工具”的語言,賦予它虛構的理想秩序,將音樂“純粹的音素”和“純粹的組合”視作詩歌的目標;另一方面,他清楚地知道,語言本身是一個五光十色的“大雜燴”,只能把“純詩”視為一種努力的趨勢和希望的境界,一個不可思議的典范思想。艾略特也將語言“意義”比喻作“小偷”為“看門狗”準備的“肥肉”,是詩人為實現創作目的而隨時可以丟棄的手段。與此不同,沃倫則明確批評“純詩論”,他指出:“那種企圖從詩中排除概念的努力破壞了我們的存在的統一和我們的經驗的統一。”(沃淪202—203)盡管如此,文學仍然義無反顧地匯入了這個注重形式的總趨勢,語言張力、象征、隱喻、含混、悖論、反諷……都備受關注地登上前臺,并培養了欣賞者的“細讀”習慣。
這種新藝術運動,“首先是對各種藝術不作分別的藝術,也可以說,是融合它們的藝術。但這種藝術不是把詩歌、交響樂、造型藝術、舞蹈編排的資源組合起來。這種藝術,可以呈現一個‘同質和完整的場所’,反而是因為它否定了材質和手法所謂的特性,因為它呈現的是先于這些特性的力量和形式的展開: 舞蹈之前,先有運動;繪畫之前,先有姿態和光線;詩之前,先有各種記號和形式的形跡: 即世界的姿態,世界的構圖”(朗西埃,120)。歸根結底,各種不同的藝術符號都有著共同的源頭: 行為建模。正是深層次的無意識經驗,那種生命體行為的共同積淀,使得不同藝術類型趨向于同一個方向: 一種展現生命形式的純粹力量。事實上,當藝術符號指涉符號自身之際,它已經向最深層的行為語言記憶發出熱切召喚了。這也正是艾略特主張“非個性”和加塞特指出“去人性化”的根源。
當藝術符號本身占據前景位置,藝術家不再醉心于表現現實生活,而是熱衷于嘗試藝術形式本身,熱衷于玩弄藝術符號,符號指涉不再是現實物象,而是藝術符號自身。于是,符號慣例就成為藝術家有意識地違犯、挑戰和革新的對象。以勃勃雄心來篡改和廢除既成慣例,謀求建立新慣例的合法性,不斷地進行形式創新,以及向人的感覺、感受挑戰,成為文學藝術自身的歷史使命。意識形態也趁機借道于改變慣例來夾帶私貨。
只有經過特殊訓練,熟悉藝術符號慣例的專家才能專注于藝術符號本身,并且仔細琢磨特定藝術品與符號慣例的關系,體驗藝術符號的意味。就如布迪厄所說: 藝術作品只對懂得它的編碼的人產生意義并引起興趣。“這種能力往往是無意圖訓練的產物,經由家庭或學校獲得合法文化而獲得的一種配置,使得這種無意圖訓練成為可能。這種可移植的配置配備著一整套可普遍應用的認識和評價模式,它是傾向于其他文化經驗的東西并允許以其他方式認識、劃分和記錄這些經驗。”(布爾迪厄40—41)布爾迪厄所說的“一整套可普遍應用的認識和評價模式”是藝術訓練的成果,其中,符號慣例起著核心作用。慣例是藝術圈協商所形成的“公約”,普遍的認識和評價模式就是適應藝術符號慣例而建立起來的。符號慣例的穩定性保證了認識和評價模式的普遍有效性;慣例的變革則導致藝術風格、流派的演變,藝術認識和評價模式的更新。
對傳統藝術作品的解讀,自然也不能脫離對藝術符號及慣例的了解。藝術“有屬于自己的‘語言’,人們需要努力了解隱含的復雜意圖、慣例、風格、技巧,才能真正理解它”(Haskell10)。即便如此,在傳統繪畫中,符號知識對欣賞者的影響并非決定性的,作品所表達的重點還是人們熟悉的日常情感和日常經驗,因此,對作品的解讀并不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難。但是,隨著現代藝術轉型,藝術符號及其慣例已經占據前景位置,藝術本身成為欣賞和評價的核心,并且慣例也已經發生了重要變化,假如缺乏對符號及其慣例的掌握,也就完全失去了藝術欣賞和評價的可能性。
當語言、符號的自我指涉愈加凸顯符號慣例,當符號慣例的變革不僅僅涉及藝術風格、流派的革新和嬗變,而是直接指向藝術觀念、藝術制度,并對藝術觀念和制度提出尖銳質疑,甚至對藝術“定義”作出重新闡釋時,“元藝術”就誕生了。藝術家更為大膽地顛覆傳統藝術,打破藝術與非藝術的邊界,向藝術觀念和制度發起突擊。觀念創新則成為藝術家的癖好。杜尚的《泉》、曼·雷伊的《禮物》、馬格利特的《這不是煙斗》、沃霍爾的《布里洛盒子》、勞森伯格的《共鳴版》、莫里斯的《自發聲響的盒子》,以及種種行為藝術等,都意圖動搖、解構,乃至拋棄“什么是藝術”這一基本信念,對藝術觀念和制度造成了巨大沖擊。然而,無論觀念或制度的變化,都主要是言語行為建構的成果,這種轉向充分顯示出言語行為在藝術活動中的強勢地位。
“藝術不擇手段地采取各種偽裝以避免貌似藝術”(萊文152)。關于《泉》,杜尚所重視的已經不再是藝術符號自身的“語法”,而是“語境”,他從符號“語法學”轉向了“語用學”,借用現成品《泉》完成了一次“宣示性行為”,以此宣告: 拆除原有藝術與非藝術間的藩籬,讓現成品成為新的藝術品,并且讓任何東西不經改變就可以成為藝術品,進而與藝術界,乃至公眾達成了新契約。杜尚以選擇性的態度來對待藝術慣例,他利用藝術外部(即展覽廳空間)的制度性慣例來廢除藝術符號自身的慣例,以此凸顯原本隱身于藝術符號慣例陰影下的制度性慣例,造成藝術觀念和感知配置的改變,終于讓《泉》成為20世紀新藝術的標志性事件。
在文學領域,元小說、歷史元小說則成為時髦。庫切的小說《福》以《羅賓遜漂流記》的成書過程作為反思對象,揭示隱藏于敘述話語中的殖民主義思想傾向。朱利安·巴恩斯的《福樓拜的鸚鵡》則抓住一個細節來顛覆福樓拜傳記的歷史敘事,重新審視歷史敘事與現實的關系: 究竟是歷史敘事描述了現實,還是現實模仿了歷史敘事?作家和讀者的注意力作了重新配置,“敘述話語”則從隱蔽走向前臺,成為新歷史主義、新殖民主義、女性主義、文化批評挖掘各種隱形權力的焦點。
當符號指涉的是藝術觀念和藝術制度,藝術就回到了概念本身,藝術成為關于藝術的“理論”,成為一種觀念化的哲學,成為不斷受到藝術自身攻擊和解構的事物。創新則成為針對一切創新觀念的不間斷反對。藝術與非藝術之間的物理界限被拆除,藝術自我防護的甲胄被撕爛,堅固的圍墻土崩瓦解了。“藝術家不再是創造者,他們變成了批評家,評論家和缺席的表演者,恰似一個受著無形力量控制的木偶。”(萊文160)對這種藝術狀況,丹托作了這樣的概括:“我們所看到的卻是某種越來越依賴理論才能作為藝術存在的事物”,這些作品顯示了另一種特色,“那就是對象接近于零,而其理論卻接近于無限,因此一切實際上最終只是理論,藝術終于在對自身純粹思考的耀眼光芒中蒸發掉了,留存下來的,仿佛只是作為它自身理論意識對象的東西”(丹托101—102)。藝術本身成為理論,成為對藝術觀念和制度的反思、商討和論辯,成為黑格爾所說的精神發展的終極階段:“哲學”。隱藏于藝術符號陰影下的言語行為急欲直接現身,以非凡膽識和囂張氣勢來宣示己見。因此,丹托仿照黑格爾的說法,稱藝術的這種狀態為“藝術的終結”。
① 在此,我們所說的虛構話語不同于假話。虛構話語只是放棄了現實維度,不指涉現實世界,而假話卻仍然指涉現實,它有意識地以扭曲的方式來指涉現實、構建現實,以此達到欺騙他人的目的。
② 符號意指與言語意指密切相關,但又有其復雜性。正如我們所說,任何符號都由行為建模與語言建模協同建構,因此,其意指意向與兩者相關。行為語言的趨向性隨外來刺激的變化而改變,與刺激的新穎性、陌生化(即新刺激)密切關聯,可是,一旦它貫通雙方,融合一體,也就取消了趨向性。行為語言的趨向性也必然影響著言語行為的意指意向。但是,從符號意指來說,最終取決于言語意指。因為言語意指即語言使用者的意識意向,而人的意識意向又與符號意指相統一,所以,言語意指、意識意向、符號意指有著內在統一性。為表述方便,我們省略了行為語言的相關性。
③ “慣例”不同于“語法”,它沒有明確的規則,無法如語法那樣作出明確的歸納,而是范例性的。因此,我們所說的“語法學”和“語用學”只是一種譬喻性表述。
皮埃爾·布爾迪厄: 《區分: 判斷力的社會批判》,劉暉譯。北京: 商務印書館,2015年。
[Bourdieu, Pierre.:. Trans. Liu Hu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
莫羅·卡波內: 《圖像的肉身: 在繪畫與電影之間》,曲曉蕊譯。上海: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
[Carbone, Mauro.:-. Trans. Qu Xiaorui.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6.]
喬納森·克拉里: 《知覺的懸置: 注意力、景觀與現代文化》,沈語冰、賀玉高譯。南京: 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2017年。
[Crary, Jonathan.:,,. Trans. Shen Yubing and He Yugao. Nanjing: Jiangsu Phoenix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17.]
阿瑟·丹托: 《藝術的終結》,歐陽英譯。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
[Danto, Arthur C.. Trans. Ouyang Ying.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1.]
斯坦尼斯拉斯·迪昂: 《腦與意識》,章熠譯。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年。
[Dehaene, Stanislas.. Trans. Zhang Yi. Hangzhou: Zhe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8.]
高誘注,畢沅校,徐小蠻標點: 《呂氏春秋》。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Gao, You, Bi Yuan, and Xu Xiaoman, eds.ü’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4.]
奧爾特加·伊·加塞特: 《藝術的去人性化》,莫婭妮譯。南京: 譯林出版社,2010年。
[Gasset, Ortega y.. Trans. Mo Yani. Nanjing: Yilin Press, 2010.]
顧炎武: 《日知錄集釋》,黃汝成集釋。石家莊: 花山文藝出版社,1990年。
[Gu, Yanwu.Daily Understanding. Ed. Huang Rucheng. Shijiazhuang: Huash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0.]
簡·艾倫·哈里森: 《古代藝術與儀式》,劉宗迪譯。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
[Harrison, Jane Ellen.. Trans. Liu Zongdi.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Haskell, Franci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阿諾爾德·豪澤爾: 《藝術社會學》,黃燎宇譯。北京: 商務印書館,2020年。
[Hauser, Arnold.. Trans. Huang Liaoyu.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20.]
胡平生 張萌譯注: 《禮記》。北京: 中華書局,2017年。
[Hu, Pingsheng, and Zhang Meng, ed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7.]
羅莎琳·克勞斯: 《前衛的原創性及其他現代主義神話》,周文姬、路玨譯。南京: 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2015年。
[Krauss, Rosalind E.-. Trans. Zhou Wenji and Lu Jue. Nanjing: Jiangsu Phoenix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15.]
吉姆·萊文: 《超越現代主義: 70年代和80年代藝術論文集》,常寧生等譯。南京: 江蘇美術出版社,1995年。
[Levin, Kim.:. Trans. Chang Ningsheng, et al. Nanjing: Jiangsu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1995.]
馬大康: 《符號建模與審美創造——兼對“總體符號學”的質疑》,《浙江學刊》1(2021): 178—190。
[Ma, Dakang. “Semiotic Modeling and Aesthetic Creation: Querying ‘Global Semiotics’.”1(2021): 178-190.]
揚·穆卡洛夫斯基: 《標準語言與詩歌語言》,竺稼譯,《符號學文學論文集》,趙毅衡編選。天津: 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15—32。
[Mukalovsky, Jan. “Standard Language and Poetic Language.” Trans. Zhu Jia.Ed. Zhao Yiheng. Tianjin: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4.15-32.]
雅克·朗西埃: 《美感論: 藝術審美體制的世紀場景》,趙子龍譯。北京: 商務印書館,2016年。
[Rancière, Jacques.:. Trans. Zhao Zilo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
弗里德里希·席勒: 《美育書簡》,徐恒醇譯。北京: 中國文聯出版社,1984年。
[Schiller, Friedrich.. Trans. Xu Hengchun. Beijing: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Publishing House, 1984.]
Searle, John 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沈約: 《沈約集校箋》,陳慶元校箋。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
[Shen, Yue.Collected Works of Shen Yue. Ed. Chen Qingyuan. Hangzhou: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5.]
讓-皮埃爾·韋爾南: 《神話與政治之間》,余中先譯。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
[Vernant, Jean-Pierre.. Trans. Yu Zhongxia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羅伯特·潘·沃倫: 《純詩與非純詩》,蔣一颿、蔣平譯,《“新批評”文集》,趙毅衡編選。天津: 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176—208。
[Warren, Robert Penn. “Pure and Impure Poetry.” Trans. Jiang Yifan and Jiang Ping.Ed. Zhao Yiheng. Tianjin: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1.176-208.]
沃爾夫岡·韋爾施: 《重構美學》,陸楊、張巖冰譯。上海: 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
[Welsch, Wolfgang.. Trans. Lu Yang and Zhang Yanbi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2.]
楊伯峻譯注: 《孟子譯注》。北京: 中華書局,2010年。
[Yang, Bojun, ed. Menciu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