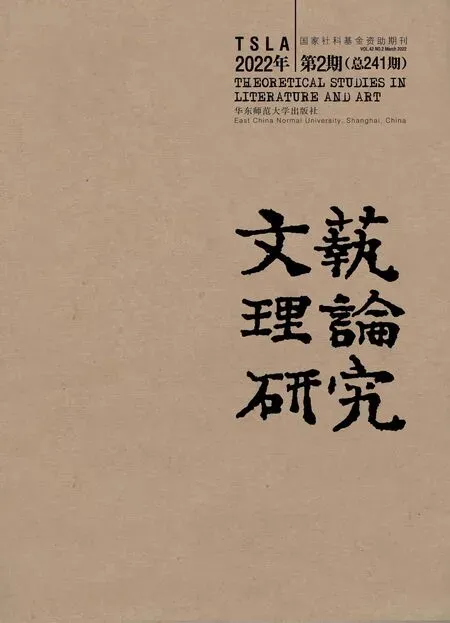五言排律在詩學理論上的闡述過程及命名原理探析
鄭佳琳
五言排律的創作興于唐代,但“排律”一詞在詩學上被公認為是指代這一詩體的通用名目,卻是后世才形成的傳統。唐人往往將近體無論長短統稱“律詩”,是廣義的說法。唐宋以來,“長篇”“長韻”等名目紛雜,有時專指長篇近體,有時則不區分古近,泛指長篇幅的詩作。“排律”之名在唐宋亦已出現,但尚未從諸多說法中脫穎而出。到了以《唐音評注》《唐詩品匯》為代表的元明詩歌選本中,“排律”作為篇幅長于四韻、符合近體聲律規則、除首尾外中間各詩聯對仗的這種特定詩體的標準名稱,被普遍而固定地使用。又因七言排律歷來作者甚少,故而后世對排律體的臻選和討論,更主要集中在五言。另一方面,五言排律的詩體理論也經歷了從隱而未發逐漸走向成熟的過程。排律創作形成后的很長一段時間,詩家對其體裁形式的理論認知往往蘊藏在創作實踐之中,間或有所闡發卻比較零散模糊。到元明之后,五言排律詩體理論才趨于深細。關于五言排律詩學理論的闡述過程,學界尚缺少系統研究;而關于以“排律”作為該詩體通用名目的合理性,也值得從原理上進行辨析。
一
詩歌創作中的辨體意識,與詩學理論上對詩體問題的闡述,是兩個層面的問題。在創作層面,唐詩古近體分流完成時,中國古典詩歌各體裁形式業已定型。在理論闡述層面,唐人主要圍繞著“古近對立”構建理論,分有格式和復古兩派,對于近體詩聲律、對仗兩個要素亦討論頗多。相比之下,唐人論篇幅長度對體裁的影響,則遠不如論聲律、對仗那樣充分。然而,律詩與排律之間的辨體,最直觀的表現便是在律詩是固定的四韻篇體而排律須長于四韻這一篇幅形式上。因此,研究五言排律的詩體理論的發展歷史,要重視“篇幅因素與近體詩內部分體之關系”這一問題的理論闡述過程。對某一特定詩體的理論闡釋,絕不僅停留在對古近聲律、長短篇幅等表征的描述,更多是對該詩體豐富的藝術內涵、審美格調等的深入探索。
在以篇幅維度探討近體詩內長篇、短章體制風格之差異這一問題上,元稹有著超前于其他唐人的詳細論述。在《上令狐相公詩啟》中,元稹將近體詩分長篇與短章各自闡發:
唯杯酒光景間,屢為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為律體卑痹,格力不揚,茍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自遠,然而病未能也。江湘間多有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仿效,而又從而失之,遂至于支離褊淺之詞,皆目為元和詩體。某又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為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為千言,或為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為次韻相酬,藎欲以難相挑耳,江湘間為詩者復相仿效,力或不足,則至于顛倒語言,重復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目為元和詩體。(元稹,卷六十727)
元稹對律體創作的分析,分“小碎篇章”及“窮極聲韻,或為千言,或為五百言律詩”兩部分進行。在創作動機上,作小碎篇章是為杯酒光景間吟詠情性,而作長篇律體則是與白居易次韻相酬,具有文人之間驅駕文字的競賽性質。在藝術缺點上,小詩因體格卑下而缺少“姿態”,流于凡俗;長篇則文字難以駕馭,只充當“戲排舊韻,別創新詞”的游戲之作。后輩詩人在短章和長篇上皆效仿元白,導致小詩流于支離褊淺,長篇語言顛倒而首尾重復,給詩壇帶來不良影響。元稹亦指出造成這樣后果的原因,在于短章無法達到“語近思深”的藝術高度,作長篇者又“力或不足”。總之,元稹的近體詩論完全分兩路展開,對小碎篇章和長篇律體在創作動機、藝術缺陷、詩壇現狀等方面,各自條分縷析。
元稹對長篇律詩藝術理想的表述,則集中體現在他對杜甫長篇律體的評價上。元稹推崇杜甫,主要因其眾體皆備,“盡得古今之體勢”(元稹,卷五十六691),于眾體之中,格外標舉老杜的長篇律體。他認為李白在“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等方面可與杜甫比肩,但在長篇律體創作上,李白則“尚不能歷其藩翰”(691)。這是給予杜甫長篇律詩極高的評價: 以杜詩論,此類詩超拔于眾體之上;以李杜優劣論,杜之高妙在于長篇律體。
元稹樹少陵為長篇律體之典范,因而對其藝術造詣的總結,即代表了元稹對長篇律體最高藝術目標的追求:“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元稹,卷五十六691)。“詞氣豪邁”是長篇詩作區別于短篇的藝術特征,但如前所述,長篇在缺乏強健筆力的情況下容易語言重復堆砌、晦澀平庸。而杜甫避免了這一弊病,能于長篇恣肆鋪張中具有清峻深切的風骨體調。而“屬對律切”是近體詩作的形式特征,但律體常流于凡俗淺白,杜甫卻能在格律對仗精切的同時脫棄凡近、別具一格。因此,元稹對老杜長篇律體的概括,是其將長篇、律體兩個形式要素的創作優勢發揮到極致,同時又規避了二者易導致的藝術缺陷。這正是元稹對于長篇律體創作的藝術理想。“鋪陳始終,排比聲韻”八個字,則抓住了長篇律體最為關鍵的鋪陳排比特征,而這也正是后人論排律藝術的核心所在。
但是,元稹沒有論述清楚五排區別于五律的固定篇幅要求,對排律藝術規則的認知也局限于以杜甫為發軔、以元白為主體的鴻篇巨制一類,而忽略初盛唐流行的篇幅較小的一類。因而只能說是后世排律理論的先聲,距離排律詩體理論的全面成熟還要經歷漫長發展。
二
宋人諸詩話中,不乏對于長篇幅詩歌創作的理論探討。這些探討往往建立在詩論家所倡的各種重要詩學范疇之下,對長篇詩歌的題材風格、藝術體制、生成機制等問題進行論述。其所謂“長篇”多數情況下是一個古近體通用的概念,并不局限于近體詩內部。即便如此,由于篇幅形式與體裁的關系問題是構建排律詩體理論的要點,故而宋人這部分對長篇詩歌創作理論的深化,也是排律詩體理論闡述史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階段。
兩宋之際,葉夢得發揚王安石、魏泰一脈反對蘇黃“以才學為詩”的理論,主張氣格超勝、言不盡意,以氣格韻味矯正江西偃蹇狹陋的死板詩風。在此詩學主張下,葉夢得注意到長篇詩歌“傷于多”的問題:“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之不敢議,此乃揣骨聽聲耳,其病盡傷于多也。如李邕、蘇源明詩中極多累句,余嘗痛刊去,僅各取其半,方為盡善,然此語不可為不知者言也”(葉夢得,《石林詩話》;何文煥411)。長篇傾盡敘事的語言特征,與石林追求言不盡意、氣格韻味的審美觀念產生較大沖突,從這個矛盾角度出發,他提出了“長篇最難”的看法,認為即使是成就最高的杜甫長篇,亦難免會有傷于累句的弊病。
這一觀點在張戒《歲寒堂詩話》中有進一步闡發。他指出元白長篇之弊在于“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為工,本不應格卑,但其詞傷于太煩,其意傷于太盡,遂成冗長卑陋爾。[……]若收斂其詞,而少加含蓄,其意味豈復可及也”(張戒,《歲寒堂詩話》;丁福保459)。在張戒看來,長篇“詞煩”有兩個表現,一是語言淺露少含蓄,一是語言繁復冗長。詞煩則導致意盡,缺少“不盡之意”則導致意味不足、格調卑下。
南宋前期,楊萬里出自江西而力求革新。《誠齋詩話》羅列出“五言長韻律詩”“七言長韻古詩”“唐律七言八句”“五言長韻古詩”“五七字絕句”等詩體。“五言長韻古詩”與“五言長韻律詩”的分體命名,將對五言長韻律詩的論述從五言長篇的泛泛理論中分離出來。同時,誠齋對不同詩體的風格特征進行了總結,對五言長韻律詩則著重論述其頌美功能:“褒頌功德五言長韻律詩,最要典雅重大”(楊萬里,《誠齋詩話》,丁福保138)。“褒頌功德”被明代詩論家看作是五言排律體最主要的一項題材功能,而誠齋于南宋前期就已經用“典雅重大”準確概括了褒頌功德之五言長韻律詩的氣象。且誠齋詩學本倡“韻味”,對其他幾種詩體譬如七言長韻古體、五言長韻古體、唐律七言八句等的論述皆落腳于“意味”“無窮之味”“句淡雅而味深長”。但對五言長韻律體卻不提“味”之范疇,反而論其頌美之作的典雅重大。可見,誠齋對不同詩體的認識,不拘于他總的詩學主張,而是從各自創作事實出發,捻出其獨特的藝術風貌。
南宋中晚期,四靈、江湖詩派為反對江西末流在南宋的僵化詩風,推崇賈島、姚合之苦吟,重視近體短章。周弼《箋注唐賢三體詩法》輯錄唐人七言絕句、五言律體(四韻)、七言律體(四韻)共五百余首,合稱“三體”,其中,周弼稱五言律體“足見四十字字字不可放過也”(轉引自陳伯海 李定廣《唐詩總集纂要》180)。可見此時期以周弼為代表的一部分詩論家所言“五言律詩”已指代狹義的四韻五律,而非唐時無論短長的廣義“五律”了。
“三體”盛行的時俗,反過來促使一部分有識詩論家推崇與“三體”相對的其他“古之所謂詩”,劉克莊是其中代表。劉克莊詩學的核心概念,在于詩有“大家數”與“小家數”之分。他晚年對時下詩風極為不滿:“近時詩人竭心思搜索,極筆力雕鐫,不離唐律,少者二韻或四十字,增至五十六字而止[……]雖窮搜索之功,而不能掩其寒儉刻削之態”(劉克莊4082)。以反對四靈、江湖詩派推晚唐苦吟冥搜為師、專工二韻四韻短篇律體為出發點,劉克莊將此類短章近體的創作歸為“小家數”。
與“小家數”相對的“大家數”,不僅指與近體相對的古體,亦指與短章相對的長篇。對此,劉克莊在《瓜圃集序》中自述了其探索過程,大意為本計劃從古近體的維度入手改變“小家數”,棄唐學古,后吸取旁人意見,認為唐律近體中亦有“黃鐘大呂”,所謂“余謂詩之體格,有古律之變,久之情性無今昔之異,選詩有蕪拙于唐音者,唐詩有佳于選者”(3975)。故而,劉克莊也從篇體維度入手改變“小家數”,推崇與短章相對的大篇:“短章稀句,賢于他人;鉅篇累韻,其尤高者”(4063)。從其“于古體寓其高遠,于大篇發其精博”(4054)的論述邏輯看,“唐律中的黃鐘大呂”在形式上很大程度指向長篇近體詩。因此,劉克莊“大家數”詩學理論絕不限于談五排,卻同樣適用于五排。長篇幅詩歌創作理論在其間被深化,影響著五言排律的理論闡述歷史。
“小家數”和“大家數”所蘊含的詩學范疇,不止于外在形式,還關乎詩歌主題之深淺、氣象之大小、格局之寬窄、境界之高低、筆力之強弱等。對于“大家數”創作的藝術原理,劉克莊有著更為深刻的探索。《晚覺稿》云:
卷中二韻者、四十字者、五十六字者,尚可以心思筆力為也。至其大篇險韻[……]非心思筆力為也。夫子曰辭達而已矣。翁其辭達者歟?韓子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翁其氣盛者歟?翁博極群書,有易學,秋賦危中鵠者屢矣,而輒失之,遂棄場屋,以琴詩自娛。(4082)
這段話論述了從“小家數”到“大家數”創作對詩人內在需求的不同: 小家數寒儉刻削,首先以“心思筆力”為之;然而隨著篇幅增大,心思筆力不足以為之,于是提出辭達倚賴氣盛、氣盛需要學力的邏輯關系。“氣”與“學力”,是劉克莊追求“大家數”的深層藝術范疇。
“氣”是指詩人之精神力量、道德境界、學問修養等。“養氣”之源泉在于道德學問,所謂“胸中萬卷,融化為詩”(劉克莊《聽蛙詩》4095)。劉克莊以闡述詩之“大家數”“小家數”為核心,構建起一套內外互通的詩學理論體系。學力深厚方能氣盛,然后筆力豪邁、氣象磅礴,作如黃鐘大呂的鴻篇巨制,方可成詩之大家數。劉克莊對長篇律體詩歌藝術特征與創作法度的探討,深入到創作者養氣與增強學力的層面,將長篇律體詩體理論的內在原理,闡述得更為完整深刻。
三
元代李存《唐人五言排律選》是最早以“排律”名目命名的五言排律專體選本,對該詩體理論體系的發展有重要推動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將排律的創作開端追溯到唐玄宗的偏好與試帖詩的制度,且將“御制”“試帖”視為排律體之正態,其余初、盛、中、晚唐詩家創作視為排律體之變態。這與此前對唐人長篇律體的描述有很大區別。從元白至宋人,“長篇”說法多指幾十韻至于百韻的鴻篇巨制。而在創作事實上,唐代六、八、十韻等律體數目非常龐大。五排詩體理論欲臻于完備,不僅要涵蓋千言百韻的鴻篇律體之理論,也要涵蓋六、八、十韻一類稍短篇五排之理論,樹立具有共性的排律理論體系。
從元稹開始,論鴻篇律體皆以杜甫為開山典范。而李存因要重視六、八、十韻等五排理論,故而其源頭不能只上溯到杜甫而止。他認為五排在唐時的興盛根由在“上有好者,下必甚”(李存,《唐人五言排律選序》;陳伯海 李定廣,《唐詩總集纂要》239),是唐玄宗的審美愛好自上而下影響了創作風尚。李存高度評價唐玄宗自己的五排藝術成就,認為“明皇五律,亦一代之雄乎?[……]雖使王楊草創,燕許潤筆,亦不能過”,所列舉皆玄宗六韻、十韻五排。同時,他還關注到“省試諸首,則上以是取士,下以為先資,揣摩合度,不失分寸”(李存,《唐人五言排律選序》,轉引自陳伯海、李定廣,《唐詩總集纂要》,239),認為唐代詩賦取士中按規定創作的六韻五排“試帖詩”,也是五排詩體的重要形態。李存先以此兩類為排律之正態,“繼以初盛中晚諸名作,而后排律之變態悉備”(李存,《唐人五言排律選序》,轉引自陳伯海、李定廣,《唐詩總集纂要》239)。一方面,李存這些觀點對十韻及以下排律的形成過程作出了重要補充,從而使得“排律”詩體理論更加完整。另一方面,以“正變”論排律詩體的意識萌生。御制、試帖兩類排律列于首卷和次卷,意味著在對五排詩體理論的整合過程中,李存將盛唐自上而下的應制風尚和詩賦取士的制度規定下創作的以六、八、十韻為主的作品,上升為詩體正宗。“御制”“試帖”以外,在對初、盛、中、晚唐詩家五排進行分卷和甄選的過程中,《唐人五言排律選》也比較準確地呈現出了唐代五排詩史的面貌,對各時段五排創作主要特點的把握是比較符合詩史事實的。
《唐人五言排律選》雖通過選詩標準透露出“五排”就是指長于四韻的五言律體,但在自序中仍稱其為“五律”。到楊士弘的《唐音》,則將五律、五排以分體條目區別,并各自撰寫小序。楊士弘對五言排律詩體理論的認知,相比唐宋時期發生了較大變化,對明清五排詩體理論的構建具有重要影響。
后人往往用近體聲律完全定型后的標準去衡量初唐詩體,是有失偏頗的。楊士弘《唐音》注意到此問題并加以處理,故而“始音”錄四杰詩不分體,“以其四家制作初變六朝,雖有五七之殊,然其音聲則一致故也”(楊士弘編選,《凡例》)。許學夷稱贊楊士弘“首以初唐四子為始音,而不名古、律,最當”(許學夷363)。不過,楊士弘只認可了四杰詩古律混淆的狀態,對四杰之后的初盛唐詩則改以嚴格近體聲律衡量。“正音”五排小序云:“唐初作五言排律者非少,然首尾音律往往不純。今通得八人,共詩十五首”(楊士弘編選70)。“正音”所錄五排詩俱較為嚴格地符合近體格律,“遺響”中則收錄了一些不符合近體格律的詩作。可見,“正音”將“音律不純”作為不入選的理由之一。其實所謂“音律純否”使用的是格律固定以后的概念,將其作為審識初唐五排藝術價值的形式要素進而決定是否入選,顯然不夠客觀,且容易遺漏佳作。這個問題在明清時期唐詩批評中亦經常發生。
其次,《唐音》所錄五排句數均在十韻及以下,以六、八、十韻為主,不錄十韻以上的長篇。“始音”和“正音”所錄題材多為應制、臺閣、游覽及邊塞,風格上皆是高華典正之作。受到《唐音》的影響,明清詩論中初盛唐“平正典重,贍麗精嚴”的臺閣體被論定為五排正聲。但是,楊士弘完全忽略了五排中長于十韻的作品,這樣的選擇不僅在篇幅形式上有所缺失,更遺失了長篇五排的詩史發展線索。李存以前,詩學理論上對五言長韻律體的討論大多側重在鴻篇巨制。從元白到劉克莊,詩體理論中對于“力”強調,顯然更多是在針對尺幅浩蕩的長篇,至于六韻、八韻等句數的五言律體,與四韻短章在筆力上的需求差別并不明顯。然而,楊士弘吸取李存對御制、試帖等盛唐主流五排的新探索,將五排正音選詩時段局限在初盛唐、篇幅局限在十韻及以下、風格局限在高華典正、題材集中在應制臺閣,這其實是轉移了五排詩體理論史的研究重心。從以筆力、學力談五排,變為以音律、氣象談五排。當然這種情況與此書不錄李白、杜甫、韓愈三大家詩亦有關。
到楊士弘《唐音》,對五言排律的理論闡述著重發展出兩個核心。一是從元稹到宋人重視其藝術之鋪陳始終、筆力雄肆,一是在元代選本中突出體現的評定正變、關注功能和氣象。這兩個理論核心,前者側重于考察區別于短章的鴻篇巨制,多以老杜為尊;后者側重于以略微長于四韻的初盛唐臺閣創作為正音。就楊士弘本身的五排詩體理論而言,對后者的高度關注彌補了此前理論體系的不足之處,但對前者的忽視也導致對五排詩體的整體把握不夠完整。就對唐代五排詩史脈絡的構建來說,《唐音》并不如《唐人五言排律選》客觀。
四
明初高棅的《唐詩品匯》是明清詩學中最重要的選本之一,其中“五排”單列一體,而不像《唐音》附于五律之后,意味著詩體理論上已將五排論定為與五律、五古、五絕等同一級別的詩歌體裁大類之一。《唐詩品匯》的論述和編選,可以代表五言排律詩體理論闡述的成熟。
首先,《唐詩品匯》探索了五言排律詩體的唐前淵源,這在此前詩論中不曾涉及,而一種詩體理論想要成熟,追本溯源必不可少。《唐詩品匯》五言排律敘目之“正始”敘目:“排律之作,其源自顏謝諸人,古詩之變,首尾排句,聯對精密,梁陳以還,儷句尤切,唐興始專此體,與古詩差別”(高棅618)。高棅指出五排之濫觴應追溯到顏謝古詩,因為排律體兩個重要的形式在顏謝古詩中就已具備,一是“首尾排句”,即詩聯之間的排比;一是“聯對精密”,即一聯之內的對仗。同時,高棅還敘述了從顏謝古詩發展到齊梁體后“儷句尤切”的情況,認為首尾排句和聯對精密的特點在梁陳得以加強。之后,高棅又指出這一脈詩歌隨著唐代古近體的分離而形成了排律一體,成為近體詩的一種,從而“與古詩差別”。因此,高棅已將排律體鋪陳排比、對仗精工、符合近體格律三個形式要素的形成變化過程大體勾勒出來。作為對比,《唐詩品匯》五言律詩“正始”敘目中對四韻五律淵源的敘述為:“律體之興,雖自唐始,蓋由梁陳以來,儷句之漸也。梁元帝五言八句已近律體,庾肩吾除夕律體工密,徐陵庾信對偶精切,律調尤近,唐初工之者眾”(506)。高棅認為四韻五律的雛形產生于永明新體之后。其對仗藝術來自梁陳儷句,篇幅規則來自梁陳五言八句之體,加之唐代近體聲律的定型,五言律詩由此形成。那么,源自顏謝古詩的排律和源自梁陳五言八句的五律,從源頭上就是兩種不同的詩體。高棅對五排唐前淵源的這種論述是比較實事求是的。
其次,關于唐代五言排律的發展流變和藝術特色等問題,高棅采納楊士弘尊盛唐的主張并修正其選詩不夠精當的弊端,發揚李存、楊士弘重視體制正變的觀念,于各詩體內論定品目。“因目別其上下、始終、正變,各立序論”,以期“使吟詠性情之士,觀詩以求其人,因人以知其時,因時以辯其文章之高下,詞氣之盛衰,本乎始以達其終,審其變而歸于正”(10)。在《品匯》的五排分目中,初唐五排被歸于“正始”,且詳細劃分了三個時段描述初唐內部五排藝術之變化。李存認為玄宗時期五排方盛,而高棅將初唐視為“正始”,盛唐視為“正宗”,“其文辭之美,篇什之盛,蓋由四海晏安,萬機多暇,君臣游豫賡歌而得之者”則是高氏對初盛唐五排興盛外因的概括。同時,高棅還敘述了五排“正體”的藝術特征:“文體精麗,風容色澤,以詞氣相高為止”(618)。文體精麗、風容色澤是五排的修辭藝術和語言風格,這種風格多指向初盛唐時期應制臺閣的五排創作,其審美傾向與《唐音》選錄高華典則的五排相同。但高棅還指出五排之高妙者還應重視“詞氣”,包含對長篇文勢、筆力的要求。因而,區別于五律追求“興象高遠”,高棅對五排藝術的概括重在精麗、詞氣這兩個層次。此外,《唐詩品匯》五排“大家”敘目云:“排律之盛,至少陵極矣。諸家皆不及。諸家得其一概,少陵獨得其兼善者,如上韋左相、贈哥舒翰、謁先主廟等篇,其出入始終,排比聲韻,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所施而不可也”。(618)五排“長篇”敘目云:
長篇排律唐初作者絕少,開元后,杜少陵獨步當世,渾涵汪洋,千匯萬狀,至百韻千言,力不少衰,及觀杜審言《和李大夫嗣真之作》,乃知少陵出自其祖,益以信詩是吾家事矣。次則高達夫數首可法。元和后,張籍、楊巨源各一首,格律亦可取[……]若韓柳雖肆才縱力,工巧相矜,往往不愜人意,皆置而不錄。(621)
高棅對五排藝術“出入始終,排比聲韻”“至百韻千言,力不少衰”的總結,與元稹對杜甫長篇“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的評價一脈相承,皆強調鋪陳排比的藝術手法和雄健豪邁的筆力特征。總之,高棅兼取前人理論,既強調鋪陳始終、筆力雄肆之章法修辭,亦重視詩體風格、氣象、題材、功能之正變,是傳統詩學中較為成熟的五排理論批評。
此后,明清五言排律詩體理論的闡述進入到持續深細發展的階段,不過整體上都是承接高棅之說,圍繞詩體淵源和詩體藝術流變兩方面展開。在溯源方面,胡應麟意識到在近體格律定型之前,已經出現幾乎符合排律篇制的長詩:“薛道衡《昔昔鹽》等篇,大是唐人排律,時有失粘耳”;“孔德紹《洪水》一章,則字句無不合矣”(胡應麟61)。用“失粘”的說法去衡量六朝詩,這是后人不妥的觀念,薛、孔之詩更并非刻意遵循格律。不過,胡氏之說也已開始關注前朝長詩與排律體制間的關系。周敘《詩學梯航》對排律源自長篇古詩的問題也有論及:“五言長篇,漢已有《焦仲卿妻》等詩,至唐始盛,于李、杜少不下二三十韻,多至百韻。其后詞人踵作,遂成一體。五七言既著,于是有律詩焉。有律詩,遂有排律。排律,即律詩排敘者也”(周敘,《詩學梯航》;周維德集校《全明詩話》97)。周氏的說法中,包含了對唐代五言古詩和五言排律兩種詩體的討論,篇幅上的共性使二者皆可溯源到漢代五言長詩,而相比于五言古詩,排律是經過律化的五言長篇詩體。不過周敘不僅沒有論及漢唐之間魏晉南北朝詩體的變遷,且關于排律究竟是長篇五言的律化還是律詩的加長排敘,周敘的表述亦是模棱兩可,“有律詩,遂有排律”容易給人造成排律形成于律詩之后的誤判。王世貞《全唐詩說》則云:“謝氏,排之始也;陳及初唐,排之盛也;盛唐,排之極也。”(王世貞,《全唐詩說》;周維德集校2048)這里排律雖然溯源于顏謝,但唐前的五言長詩與排律還是有本質區別,王氏將“排之始”“排之盛”定于謝、陳及初唐,如果說“排”是指排律詩體,顯然是不妥的;如果“排”是指鋪陳排比之藝術而非詩體,那么對這三個階段的描述也不準確,譬如盛唐排律中鋪陳排比的密度其實是低于前代的。不過王世貞的表述雖不準確,但他摘出大謝、梁陳、初唐、盛唐幾個時間點,其初衷應與高棅類似。許學夷的觀點也存在問題:“初唐五言,古、律混淆,古詩既多用律體,而排律又多失粘,中或有散句不對者,此承六朝余弊,蓋變而未定之體也。”(許學夷153)一方面,許氏對于初唐古律混淆、詩體“變而未定”的總結是非常有意義的,可以作為對初唐排律乃至初唐各詩體創作狀態的定性。但另一面,許氏用后世成型的近體聲律去對比初唐詩,認為失粘等是“六朝余弊”,這本身就是“后之視今”的視角。并且“中有散句或不對者”更非初唐排律對齊梁陳隋長詩的承繼,事實上梁陳“儷句尤切”,入唐后反而散句有所增加。許學夷會這樣認為,也是被定型后古近分明的詩體思維所限制,將出現散句理解為近體詩不成熟的表現。這種有失偏頗的觀點同樣出現在清代錢木菴《唐音審體》中:“初唐諸家長律詩,對偶或不甚整齊,第二字或不相粘綴。如胡、鐘正書猶略帶八分體,至右軍而楷法大備,遂為千古立極。詩家之少陵,猶書家之右軍也。少陵作而沈宋諸家可祧矣”(錢木菴,《唐音審體》;王夫之等《清詩話》782)。
而在五言排律的藝術流變方面,明清詩論家則繼承高棅兼重正變與鋪陳的觀點,對不同詩人的五排成就、風格及關系展開描述。其中胡應麟的描述比較到位。胡應麟認為沈宋五排“藻贍精工”,而“宋精碩過沈”,“初盛唐間排律宋之問為冠”,因為“宋則遍集中無不工者,篇篇平正典重,贍麗精嚴”,并提倡“作排律先熟讀宋、駱、沈、杜諸篇,仿其布格措詞,則體裁平整,句調精嚴”(胡應麟76),從而將高棅初唐五排作為“正始”的論斷具體到以宋之問為中心、以“藻贍精工”“平正典重”為風格特征。初唐除了沈宋之外,胡應麟還格外關注駱賓王與杜審言的五排:“杜審言排律‘六位乾坤動’‘北地寒應苦’等,極高華雄整”(67)“沈宋之前,排律殊寡,惟駱賓王篇什獨盛。佳者,‘二庭歸望斷’,‘蓬轉俱行役’;‘彭山折坂外’,‘蜀地開天府’,皆流麗雄渾,獨步一時”,“賓王《幽縶書情》十八韻,精工儷密,極用事之妙。老杜多由此”,“初唐四十韻惟杜審言,如《送李大夫作》,實自少陵家法,杜《八哀·李北海》云‘次及吾家詩,慷慨嗣真作’是也”(75)。可見,與沈宋作為初唐正格五排代表不同,胡氏對駱、杜五排的關注主要在于其對杜甫在雄渾高華風格、精工儷密且用事極妙的句法、長詩章法篇制等方面的影響上。對于盛唐詩人排律藝術的高低,胡應麟亦有評點:“太白、右丞,明秀高爽”、“盛唐排律,杜外,右丞為冠,太白次之”、“常侍篇什空澹,不及王李之秀麗豪爽,而《信安王幕府》三十韻,典重整齊,精工贍逸,特為高作,王李所無也”(77)。對于杜甫五排的理解亦較為深入:“杜排律五十百韻,極意鋪陳,頗傷蕪碎。蓋大篇冗長,不得不爾。唯贈李白、汝陽、哥舒、見素諸作,格調精嚴,體骨勻稱,[……]然后究極杜陵,擴之以閎大,濬之以沉深,鼓之以變化,排律之能事盡矣”,“惟老杜大篇,時作蒼古,然其材力異常,學問淵博,述情陳事,錯綜變化,轉自不窮”(72)。其中,除了前人已經提及的氣象閎大沉深、章法錯綜變化外,胡氏還強調了杜甫五排對學問、材力的內在要求。另外,《詩藪》對中唐以后五排的流弊亦有討論。總體而言,胡應麟在高棅以初唐為正始、盛唐為正宗、杜甫為大家的基礎上,突出論述了宋之問、沈佺期、駱賓王、杜審言、王維、李白、高適和杜甫等詩人五排風貌、地位之異同。
以沈宋為五排正格,以杜甫為五排之最,成為明清五排批評中的普遍認知。如王世貞《藝苑卮言》云沈宋排律“用韻穩妥,事不傍引,情無牽合,當為最勝”,而少陵排律“強力宏蓄,開闔排蕩,然不無利鈍。余子紛紛,未易悉數也”(王世貞,《藝苑卮言》;《全明詩話》1918),馮復京《說詩補遺》云宋之問排律“格正詞華,壯嚴典贍,[……]少陵而外,固當推宋第一”(馮復京,《說詩補遺》;周維德集校3913)等。
同時,明清詩論還對五言排律常用的創作法度、題材功能等進行過一些探討。關于五排篇制的問題,許學夷認為只有雙韻五排才是符合法度的,“初唐沈宋雖為律祖,然尚不循此法,張說、蘇颋、李嶠、張九齡諸公皆然”(許學夷152),“盛唐惟李、杜、高、岑、孟浩然,極守其法,而浩然實不嚴整”(168)。這種觀點當然也是建立在以杜甫之后五排皆雙韻的標準之上去衡量初盛唐五排。施閏章意識到這個問題,指出:
有謂排律無單韻,如老杜集中止有十、十二、十四、二十、二十四、三十、四十、五十韻之類,并無十一、十三、十五韻者。考之杜集,良然。按此體唐人以沈宋為宗,及考盛唐諸家,沈佺期諸君用五、七韻者頗多[……]大抵以對仗精嚴、聲格流麗為長,未嘗數韻限字,勒定雙韻。杜審言排律皆雙韻,《和李大夫嗣真》四十韻,沉雄老健,開闔排蕩,壁壘與諸家不同;子美承之,遂爾旌旗整肅,開疆拓土,故是家法。(施閏章,《蠖齋詩話》;王夫之等387)
二者對創作情況的考察其實是相同的,只不過施閏章以沈宋為宗,認為五排雙韻、單韻皆可,只不過杜審言、杜甫一脈是嚴格使用雙韻。這種說法比許學夷以雙韻為五排法度而否定初盛唐大量的單韻作品要更符合事實。此外,周敘《詩學梯航》對五排創作要點的概述是比較精準的:“須先將己之胸次放闊,以次取詩之指意展開,鋪陳錯綜,有條不紊。天昊紫鳳,粲然盈幅,及其冠冕佩玉,球琳鏗鏘,擲地當金石聲”(周敘,《詩學梯航》;周維德集校97)。這里將五排鋪陳排比、冠冕高華這兩個最主要的特色突顯出來。五排應制游宴、酬贈唱和的功能最受關注,如《漫堂說詩》贊同高棅的觀點,認為初唐五排“大約侍從游宴應制之篇居多,所稱‘臺閣體’也”(宋犖,《漫堂說詩》;王夫之等418)。除此,胡應麟還專門稱贊了宋之問寫景狀物類游覽五排,認為其“登粵王臺、虛氏村、禹穴、韶州清遠峽、法華寺等篇,敘狀景物,皆極天下之工。且繁而不亂,綺而不冗,可與謝靈運游覽諸作并馳,古今排律絕唱也”(胡應麟76)。詩論家們也意識到排律表現功能的最難處在于抒情陳意:“大抵排律句煉字鍛,工巧易能,唯抒情陳意,全篇貫徹而不失倫次者為難”(費經虞,《類編》;周維德集校4712),因而對杜甫五排中的述情陳事功能十分重視。五排抒情功能的薄弱,使得一些尊古體薄近體的詩論家從性情詩學的角度對其大加批判。《藝圃傖談》云:“近體之敗興,無如俳律。使有情不得展措,滯鈍者托以藏拙。唐人編類書,染著人,如疊板砌甓,含氐吞針,性情之道,溫柔之意盡矣”(郝敬,《藝圃傖談》;周維德集校2885)。
五
以上探討了五言排律體詩學理論的闡發歷史。關于“排律”這一名目,錢木菴曾云:“棅又創排律之名,益為不典。古人所謂排比聲律者,俳偶櫛比、聲和律整也,乃于四字中摘取二字,呼為排律,于義何居?古人初無此名,今人竟以為定格而不知怪,可嘆也!”(錢木菴,《唐音審體》;王夫之等782)此論注意到“排律”之名是后世所加的事實,并否定了這個名稱的詩學意義。那么,“排律”這個名稱何以會被詩家廣泛采用并固定下來?以“排律”命名這種詩體的原理何在,又是否真正合理?這需要通過考察詩體理論的藝術內核,來判斷“排律”二字究竟是否做到了名副其實。
唐人廣義的“五律”說法,本身已經包含了“五言”與“律體”兩方面的含義。所以,欲命名篇幅長于四韻的五律,重點是如何在名目中體現“篇幅”這一形式要素。除“排律”以外,“長律”的說法也比較常見。楊載《詩法家數》總論云:“長律妙在鋪敘,時將一聯挑轉,又平平說去,如此轉換數匝,卻將數語收拾,妙矣。”(楊載,《詩法家數》;何文煥736)以“長”字直接說明篇幅之長,與“律”字的近體含義結合,再與“五言”搭配,通過詩名將該詩體的外在形式要素都反映出來。因而,用“五言長律”命名詩體本身也是妥當的。
相比之下,“排律”之“排”字并非直接描述外在形式。排者,元稹及高棅所謂“鋪陳終始,排比聲韻”也。“排律”即是指在廣義五言律體之中具有“鋪陳排比”特點的詩歌。
葛曉音先生認為,漢代五言詩成熟的過程,也就是五言體雛形將排比對偶修辭的重復連綴和連貫的敘述語脈兩個詩化途徑相融合以創造多種詩行呼應方式的過程。到秦嘉時代,“五言體排偶已經由修辭的重疊發展到層意的重疊,往往形成兩句一層或四句六句乃至八句一層的排比。”(葛曉音,《先秦漢魏六朝詩歌體式研究》296)西晉以來,五言詩駢儷漸開,鋪陳特色變得尤為明顯,“為突破漢魏五言場景描寫的單一性和敘述的連續性,圍繞單個場景的描寫轉為拓展時空的全方位鋪寫”(330),劉宋后則從“體俳語不俳”發展為“體語皆俳”。齊梁以來,受到永明新體的影響,長篇齊梁詩鋪陳排偶出現過縮減的傾向,但在梁大同以后復又“儷句尤切”。如前所析,唐代五排正是來自顏謝古詩至齊梁長篇。從淵源上講,這一脈長篇創作始終圍繞鋪陳排比的表現手法展開。
而從原理上講,“鋪陳排比”的表現手法對于詩歌篇幅大小具有決定性作用。詩歌篇幅取決于篇章之結構,進而取決于詩行之間意脈承續的方式。排比既包括一聯兩句之間的對仗,亦包括每層詩意的幾行詩聯內展開的對稱性鋪陳描寫,以及多層層意之間的排比串聯。在每行詩字數確定的情況下,詩歌篇幅的長短,從本質上講正是由一層詩意之內橫向鋪寫的規模與幾層詩意之間縱向連結的層次所決定的。永明新體所采用的五言八句篇制,恰恰首起尾結,一韻一轉,四韻四層,無需鋪排。因此,以四韻為句數界限的五言排律與五言律詩,不僅僅是外在形式和創作淵源不同,其內在篇制體式也截然不同。五律以四韻之間的起、承、轉、合為章法,每對詩聯的容量恰好承載每層詩意;五排則以鋪陳排比為構建詩歌建筑美及詩歌意脈連貫性的基本方式。由此可知,鋪陳排比是五排區別于五律的藝術核心。
這也解釋了五言排律的創作倚賴詩人的學力的原因,本質在于鋪陳排比這種藝術手法倚賴詩人的學力。劉熙載《藝概·賦概》云:“賦起于情事雜沓,詩不能馭,故為賦以鋪陳之。斯于千態萬狀,層見疊出者,吐無不暢,暢無或竭”(86)。漢賦欲達到“鋪采摛文,體物寫志”(黃叔琳 李詳補注95)的效果,需對空間、時間、物色、情景等展開縱橫層疊的鋪敘。王世貞《藝苑卮言》云:“《子虛》、《上林》,材極富,辭極麗”(周維德集校1902),欲極盡鋪張揚厲之能事,則需羅列磅礴奇崛的意象并渲染以繁麗豐富的辭藻,而這樣的藝術特點,尤其考驗作者的學力底蘊。同樣,詩歌創作大量使用鋪排手法時,對詩人學識、工力的要求較高。學力不足,依憑苦思,難以展開多層詩意連綴且每層鋪張排比的長篇創作。相反,四韻律詩因兩句一轉、一韻一層的結構特點,其詩聯之間不使用鋪陳排比的修辭,故可憑才思為之,對雄贍學力的要求相對寬松。
因此,從外在形式看,“排”字代表的鋪陳排比之義,象征著每層詩意之內的多詩聯排比及多層詩意之間的排比,這種排比決定了該詩體在篇幅形式上區別于由起承轉合四聯詩行構成的狹義五律。所以,“排律”名目既能體現長篇幅要素背后的內在藝術原則,又可揭示以四韻這一句數劃分五排和五律的本質原因。從內在機制看,“五言排律”之“排”不僅可突顯鋪陳排比的藝術核心,還隱含著該詩體創作對學力的內在需求。這些皆是“長律”之“長”字不能涵蓋的意義。由此看來,“排律”一詞雖為后世所用,卻是符合該詩體淵源與原理的合理名目。
① 錢志熙先生在《元白詩體理論探析》一文中提出“詩體理論”的定義,即“以詩歌的體裁問題為核心的、圍繞此一問題而展開的一種詩歌理論”,包括“詩歌的體裁分類、詩體藝術特征與功能、特定體裁的創作法則、各類體裁的源流演變等內容”(《元白詩體理論探析》33)。
② 參見錢志熙: 《論唐代格式、復古兩派詩論的形成及其淵源流變》,《中國高校社會科學》5(2018): 90—102,159。
③ 此處“律詩”指篇體固定為四韻的狹義律詩,與“排律”并列為兩種詩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