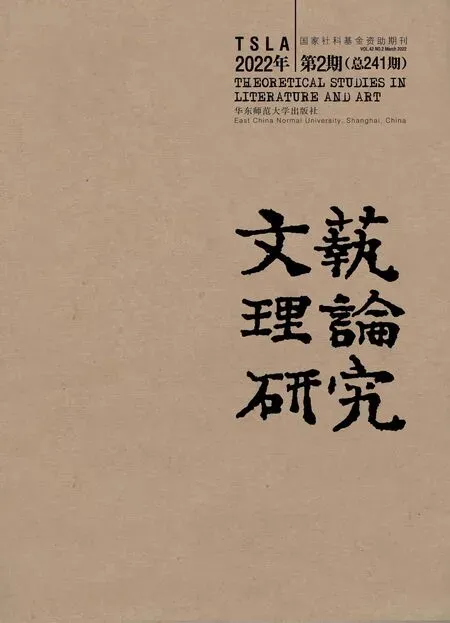反藝術還原論: 論保羅·克勞瑟的后分析現象學美學及其延伸
李 牧
藝術研究大體有兩種互相對立(當然,它們在實質上也是相互聯系的)的趨勢,一是所謂的還原主義(reductionism),二是所謂的形式主義(formalism)。在本文中,所謂還原主義,是指將藝術研究引向與藝術相關的種種外部關系(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文化的),把諸如藝術生產、藝術消費以及藝術歷史進程等事件或者現象,主要歸因于非藝術性因素和條件的刺激和驅動,把后者視為藝術緣起和發展的根源(為人生而藝術)(Crowther,11-24)。藝術社會史、藝術社會學、藝術人類學以及后現代主義的藝術分析(如福柯等人的研究)等,是還原主義的主要范式,目前在藝術研究中居于主導性的地位。與還原主義的藝術研究不同,形式主義取向的藝術研究專注于藝術本體自身,將藝術作品內部所呈現出來的各種形式細節(而非與其相關的外部關系)視為認識、感知、經驗、理解和闡釋的核心,探尋藝術內部自為的運作原則、機制和規律,認為藝術具有自身的獨立性(為藝術而藝術)。唯美主義、維也納美術史派的形式主義藝術史分析等,都是形式主義藝術研究的突出示例。但是,近年來,有關藝術的形式主義分析逐漸式微,在一些藝術研究者看來,這一趨勢使得藝術“淪落”為各種政治、經濟、文化等其他社會性范疇的“附庸”而失去了自身存在的獨特性和價值(9—34)。為了平衡還原主義與形式主義方法在藝術研究中的失衡現象,在還原主義主導的情勢下,當代西方形式主義美學的重要代表人物克勞瑟(Paul Crowther)以康德的美學思想為起點,結合分析哲學與現象學的方法,對傳統藝術以及現代和后現代藝術進行了長期、廣泛和深入的形式主義分析。本文即是以克勞瑟的形式主義美學思想為主要考察對象,梳理其學術源流,通過闡述其對于藝術本質的思考和所使用的后分析現象學方法,展現形式主義藝術研究的重要價值和當代意義。
縱觀克勞瑟的學術作品,可以總結出以下幾個關鍵詞: 康德美學、崇高、現象學、非古典藝術[包括現代藝術、先鋒派藝術、后現代藝術、數字藝術等(當然也有重疊的部分)]。乍看之下,這些關鍵詞雖然都具有不盡相同的指涉,涵蓋不同的人文領域,但是,它們之間其實是緊密相關的,如雷蒙·威廉斯在《關鍵詞》(:)中所表達的,關鍵詞不是單個獨立出現的,在一定的社會文化語境中,它們往往成組地進入我們的視野。因此,本文所要進行的最重要工作,便是厘清原作者的整個思想世界,并揭示其與相關理論之間的同異。接下來的文字將依托上述關鍵詞,闡述克勞瑟的基本研究理路和表述邏輯,展開有關其理論的全景世界。
一、 反還原主義的理論基礎: 康德美學與藝術的形式本質
在克勞瑟看來,雖然許多藝術問題與其外部世界之間存在諸多緊密的關聯,但是前者的存在有其自在的特點和性質,不可與后者等同,或者為后者所替代,即是說,藝術有其特殊的本質或內在意涵。因此,與許多美學研究者相類,認識、尋找和理解藝術獨有的內在意涵,是克勞瑟的研究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也是他對抗單純的藝術還原主義的基礎和出發點。其實,不單是美學研究者,所有的藝術活動參與者,包括藝術家、研究者、批評家和欣賞者等,都在追尋以下問題的答案,即藝術究竟是什么?為什么在人類發展的各個階段,人們在不同的地理和文化空間中,都創造了藝術或者我們可以用“藝術”進行指稱的對象?藝術在人類的精神生活中為什么如此重要,究竟是什么使得它們的形式意味深長?
對此,克勞瑟的思考大體是從兩方面展開的,一是直接探尋藝術的本質,二是通過探究審美經驗的內在邏輯與結構而達到對于藝術本質的認知。在克勞瑟看來,此二者之間具有著相互聯結、不可分割的關系。具體說來,藝術的本質來自個體最真切的審美感知經驗,而非具有普遍性的理論與觀念表述。而關于藝術本質的認識也可以引導主體如何認識、感知和理解作為物、事件和經驗的審美對象。克勞瑟十分強調,我們對于藝術的認識,無論是現成品藝術、觀念藝術或者任何其他類型的藝術形式,都應該建基于對象本身所具有的知覺特征,這些知覺特征就是藝術家的創造性通過具體的身體活動而留下來的經驗痕跡。因此,出于對知覺經驗重要性的關注,克勞瑟的討論最終指向的,其實是人在生活世界之中的主體性及其作為主體的意識活動,這是一種強調個體感知經驗、反抗異化、并在藝術原創性中可以追求到的主體性。在這個意義上說,克勞瑟從具有形而上意味地叩問藝術的本質這一問題,轉向現象學意義上的主客體經驗和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克勞瑟介入于此的方式,是借助康德美學和梅洛-龐蒂的知覺現象學對于審美與生命經驗的把握(具有基礎主義性質的),這與后現代理論家如德里達和巴特所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方式(反基礎主義的或者解構的)。即是說,他所關注的是實在的、可觸的“經驗”(來自本雅明的術語,特別是一種個體的且不可約和還原的經驗),而非以語言為基礎的言說的文本性和社會建構性(Crowther,25-39)。克勞瑟的這一傾向所表現出來的對于藝術本質的強烈追求和反還原主義意味,開始于其學術生活的早期階段。
1983年,克勞瑟在一篇題名為《藝術經驗: 闡釋學分析存在的問題與可能性》的文章的導言中提到,至該文發表之時,二十世紀有關審美經驗的討論,主要是以形式主義分析為主導的(Crowther, “The Experience”347-362)。在這一理路的觀照下,審美經驗被認為是對于線條和色彩及其相互關系的某種感性或知性回應,而非來自于對線條和色彩所再現的主題內容和意義的把握。在這個意義上說,由于忽略了作品主題和內容所可能引起的外部勾連(功能性的),審美體驗是“無功利的”和非還原性的。雖然此文主要討論了伽達默爾的闡釋學對于內容性要素的關注,并將之作為傳統形式主義方法的有效補充,但是,克勞瑟認同形式主義的話語主導(這一點在其后諸多反還原主義的論述中已經清晰可見),并由此而引入康德關于審美經驗的討論。
康德關于藝術與審美經驗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其《判斷力批判》里。此書的第一部分為“審美判斷力批判”,康德在此提出了有關審美對象的兩個類別: 一是“優美”(beauty),二是“崇高”(sublime);以及與之相伴隨的兩種不同的審美經驗,即“優美感”和“崇高感”。在西方美學史中,有關“美”(或者“優美”)的討論自古希臘時期開始便蔚為大觀(如柏拉圖等),在此不再贅述。而出于后文論述的需要,此處重點提及“崇高”的相關論述。有關“崇高”這一概念的發展歷史,可以追溯到古羅馬時期朗吉努斯(Longinus)所著《論崇高》一文。隨后,通過17世紀后期新古典主義理論家布瓦洛(Nicolas Boileau)的推動,崇高逐漸從一個修辭學概念(關注文本效果)轉變成為了歐洲學術史中重要的理論概念。不過,直到這時,崇高的內涵與外延并未完全固化,更未完全成為與優美對立的美學范疇。而基于經驗主義哲學背景,特別是對人的情感(或情緒活動)及其生理機制的關注(神性的祛魅并脫離理性的束縛),在博克(Edmund Burke)于1757年發表的《關于崇高與美的觀念的哲學探討》()一書中,崇高的意涵在與優美的對立性表述中得以固定,二者成為了既相互對立,又互有聯系的審美范疇。博克并未將崇高與理性觀念進行關聯(相反還有否定的意味),而堅持崇高具有理性內涵的康德無疑受到了他的影響(以及來自盧梭、萊辛和巴托等人的影響)。康德在1763年寫就出版的《對美與崇高感受的觀察》()以及更晚完成的《判斷力批判》(1790年)中,繼承了博克將“優美”與“藝術”相聯和將“崇高”與“自然”相聯的基本觀點,并更為深入地從哲學上辨析了優美和崇高的異同。另外,在后書中,康德進一步將“崇高”進行了區分,即所謂數字的崇高(即絕對的大)和力量的崇高(即壓倒性的力量和壓迫感)。
本文在此將重點關注康德關于“優美”和“崇高”的差異。在康德的討論中,“優美”與“崇高”雖然具有一致性,即“二者都自身就讓人喜歡”,而且“二者都既不以感官判斷也不以邏輯的規定性判斷,而是以反思判斷為前提條件”,但是,二者同樣存在非常顯著的區別,“愉悅在前者是與質的表象相結合,在后者則與量的表象相結合”(康德72—73)。對于兩者之間的差異,康德進一步解釋到:“美的就是在純然的評判中(因而不是憑借感官的感覺按照知性的一個概念)令人喜歡的東西。由此自行得出,它必須是令人不帶任何興趣而喜歡的。崇高的就是通過其對感官興趣的阻抗而直接令人喜歡的東西。”(94)可以這樣推論,無論是對于“優美”或者“崇高”的判斷,康德提出的“無功利”的審美活動,是一種主體內在的有關純粹形式的主觀感受和經驗,主題、意義、興趣、價值等超乎對象本體之外的存在目的都在此被超越了。與“優美”一樣,“崇高”作為一個極其重要的審美范疇的地位似乎是無可置疑和否認的。然而,學界對于優美與崇高這兩類審美經驗的探討是較不平衡的。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至少到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學界對于康德《判斷力批判》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中有關“優美”的討論,而有關“崇高”的部分(特別是崇高作為一個美學范疇與藝術之間的關聯)相對而言則較少被學界關注(當然,自席勒開始,黑格爾、叔本華、德里達、德勒茲、齊澤克、利奧塔、南希等都討論過康德關于“崇高”的思考)。
但是,這一主題卻成為了克勞瑟形式主義研究的重點以及對傳統康德美學思想研究的突破。正如羅杰森(Kenneth F. Rogerson)在評論克氏《康德理論中的崇高: 從道德邁向藝術》(:, 1989年)一書時所說的,在當時,克勞瑟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彌補這一缺憾的意義和價值(Rogerson379-381)。其實,康德關于“崇高”的討論被后世學者的相對忽略,是一系列非常復雜的原因導致的。首先,康德對于“崇高”的書寫被視為一種無奈之舉,是對更早期的將“優美”與“崇高”相結合的論說傳統的妥協,因此,在具體的討論中,與有關“優美”的深入探討不同,康德并未給予關于“崇高”的判斷非常精準嚴格的論證和說明,而認為討論“崇高”無需非常完整細致的推導(379)。這使得在克勞瑟看來,康德關于“崇高”的討論非常晦澀,而且他的討論似乎將“崇高”與這個詞在日常和批評用語中的不同用法糾纏在一起,并未對之進行非常明確的、哲學意義上的準確定義(Crowther,1-2)。另外,學界對于崇高的相對忽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西方傳統(特別是藝術傳統以及與此相關的思考)中對于“優美”(特別是古典美)的追求。在此,可以很明顯地看到,自古希臘以來,“優美”便被確立為傳統上西方藝術的核心價值,而“崇高”在某種意義上,則更多地將人們指向自然、道德與宗教,如康德所言,“人們可以這樣來描述崇高者: 它是一個(自然的)對象,其表象規定著心靈去設想作為理念之展示的自然的不可及”(康德94)。在康德看來,“藝術”是與“自然”相分離的。在這里,克勞瑟的問題是,如果藝術僅是“審美的藝術”(無論是“適宜的藝術”或者“美的藝術”(129—131)),引起參與者的“崇高感”的經驗對象(即如有學者所認為的“丑”或者“痛感”等),是否可以被看作藝術?或者說,在更廣泛的意義上,“不優美”的經驗對象,是否可以被納入藝術的范疇?是否可以引發主體真切的審美經驗呢?這便關涉著藝術本質的問題。
其實,在克勞瑟看來,依據其所理解的康德有關審美經驗的思考,這本不應成為一個令人困擾的問題,評判一件作品或者任意經驗對象是否是藝術的標準,并不在于其本身是否“優美”,而在于是否能引起觀照主體的審美經驗。如前所述,康德所認為的審美經驗,并不僅僅包含“優美”,還包括“崇高”。可見,康德在其思想體系內部,已經為我們準備好了正確答案,而非僅僅拋出問題,而克勞瑟正是致力于在康德美學內部尋找解決問題的線索和方法,而并非像許多現代康德研究者那樣,將康德的美學理論視為需要克服和超越的問題與障礙(Crowther,1)。由于克勞瑟將康德美學作為解決問題的基礎,他希望通過對于康德美學的再闡釋,重新建立康德美學與當代美學與藝術之間的聯系。在克勞瑟看來,康德美學揭示了“審美現象更為廣闊的經驗基礎”(199),即一種基于純粹形式的感知經驗,它的目的在于追求一種對于人類普遍審美經驗的思索,具有著跨越地理邊界和歷史時間的超驗維度,是一種對于紛繁復雜的現象的理性重構和邏輯重建。
依托康德美學,特別是其關于“崇高”的討論,克勞瑟開始將并不“優美”的對象納入其考量范圍,并以此重新思考有關藝術本質的問題,在此,他關于“藝術”的認知已經逐漸不同于西方傳統的藝術界定。例如,克勞瑟在1984年發表了一篇名為《巴尼特·紐曼與崇高》(“Barnett Newman and the Sublime”)的論文。其中,克勞瑟批評了紐曼對于“崇高”的認識與實踐,認為后者在畫作中表現出來的,是一種描述性的(descriptive)崇高感,即通過一些顯而易見的形式風格的呈現(如描繪“空”等)來表現所謂的“崇高”(Crowther, “Barnett Newman”52-59)。但是,在克勞瑟看來,這不是康德意義上真正的“崇高”,所謂真正的崇高并不是這種表面上對于刻意營造的震撼感的表現,而是要通過作品引發觀者最深層次的內心情感與反思,如同華托和梵高的作品那樣(52—59)。另外,克勞瑟認為,紐曼在技法和風格上也并沒有獨到之處,也并未引起觀者從形式上“敬畏”這樣的作品(52—59)。總體而言,紐曼所展現的“崇高”是浮于表面的。
當然,在康德有關“崇高”的論述中,他并未指明如克勞瑟所明確闡釋的概念和觀點。因此,一方面,可以看到,克勞瑟并非機械地完全照搬和套用康德的理論,而是對其進行了重新闡釋、結構和整合,使之成為能夠有效解決問題的工具。但是,另一方面,這種看起來脫離康德文本和思想的闡釋,似乎并不為當代康德研究者所完全贊同。例如,麥奎蘭(J. Colin Mcquilian)在對《康德美學: 從知識到先鋒藝術》(:-)一書的評論中,雖然贊賞克勞瑟將康德的美學思想視為一種非常有效地理解當代藝術歷史發展的工具,但通篇都流露出對于克氏闡釋的強烈批評(Mcquilian1075-1078)。甚至,在該評論文章的最后,麥奎蘭毫不客氣地說道:“我不可能會推薦大家閱讀這本《康德美學》。這根本就不是一本能夠有效引導我們走向康德的文本及其觀點的書。”(1078)
雖然來自當代康德學界的異議不少,但是,在筆者看來,克勞瑟仍舊把握了康德思想的核心和主旨,即追求一種非還原主義論調的、趨向于形式主義的人類審美經驗的普遍性以及客觀統一的藝術標準(即形式以及由此引起的審美經驗的普遍性)。在《康德美學: 從知識到先鋒藝術》的第四章中,克勞瑟明確表示他從康德的美學理論(特別是《判斷力批判》中有關審美判斷力的討論)中認識到了審美觀念的普遍性和藝術標準的統一性。對這種普遍性的認識,使得克勞瑟能夠沖破西方中心主義的牢籠和以既定的“優美”為核心的西方藝術審美傳統,而重新認識、理解和定義藝術及其本質。在其2003年發表的論文《文化排他主義、規范性與藝術的定義》中,克勞瑟首先討論的是形式主義對于藝術的定義,指出其所設定的形式標準所蘊含的排他主義傾向(Crowther, “Cultural Exclusion”121-131)。隨后,克勞瑟又討論了藝術冠名(designation of art)(即將某物認定為“藝術”的一系列準則、事件過程等)所隱藏的更為深刻的排他主義。由此,克勞瑟明確反對文化排他主義,反對以某些文化傳統為尊,或以某一社會內部的某一群體的傳統或者風格為尊,而排斥和否定文化他者存在的積極意義和價值,同時,他還指出,要在一種非歐洲中心主義的視角下重新認識和理解藝術及其本質。于是乎,克勞瑟概括出了一個非排他主義的藝術定義,提出了“人為造象”(artifactual imaging)的概念(126)。在克勞瑟看來,“被制作出來的物品”(made artifact)或者說“物品的制造”,是非西方藝術制作的核心,直接指向了具有人類普遍性的藝術本質——形式。
關于藝術的定義和本質的討論,在克勞瑟2007年出版的專著《界定藝術,創造標準: 懷疑時代的藝術價值》(,:,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中得到了進一步深化。克勞瑟認為,要使一件人工造物成為藝術或者一件藝術作品成為經典的東西,是其自身的審美屬性。其中的重要屬性之一便是原創性。一件藝術作品的價值在于兩個方面: 一是,就個人而言,提升了個體的認知能力;二是,在文化層面上,它發展了我們用以表達自身思想、情感和其他各種觀念與意識的媒介。在此書中,克勞瑟反對“反基礎主義”(anti-foundationalist)和文化相對主義(cultural relativism)的觀點,依托康德的美學理論,認為存在著一種普遍性的(即并非西方中心主義的、男權視角或者以種族主義為基礎的)、客觀的關于藝術的定義與有關藝術價值的認知。同時,他也并不贊同傳統形式主義對于作品內容和主題的過分忽略,以及那些從西方批評視角出發對于非西方藝術的專斷評述。另外,克勞瑟對藝術生產在西方世界淪為一種以利潤為目的的商品生產的現狀很不滿意,故而在康德美學思想的指引下,他開始尋求一種通過審美(感性知覺)的方式去定義藝術以及從哲學(美學)上確立統一藝術標準的可能。克勞瑟在此重新強調“人為造象”這一概念,認為藝術就是一種(以人的感性知覺為基礎來)制造圖像(視覺形式)和確立標準的活動。在這一還未最終設定的普適性標準中,克勞瑟希望能更多地囊括非西方的藝術形式,以便有可能建設一個更為客觀的系統來辨識藝術。對于克勞瑟而言,這種客觀性是通過對“創造性差異”的深刻認識和尊重而實現的,在他看來,這種創造性差異是形式主義意義上的,可以使得一件藝術作品或者藝術家的創造性以及由此產生的獨特價值得到承認,從而“開啟審美經驗新的可能性”,并且可以提供“呈現世界的新路徑”(Crowther,56)。克勞瑟極力提倡創造一種具有普世意義的藝術經典以及評價標準,使得非西方藝術有可能參與漢斯·貝爾廷(Hans Belting)所謂的“全球藝術”(global art)(Belting178-185)的建構。當然,必須明確的是,我們不可由此而將克勞瑟劃歸為具有后殖民主義傾向的理論家,其關涉的并非藝術作品的外在社會歷史現實和政治語境化的主題,而是主要從形式主義的角度、以一種內向性的視角對經驗對象進行理解和探討。
其實,克勞瑟重新討論藝術本質和定義藝術的根本目的,是為那些不符合以“優美”為核心的西方藝術傳統之外的人工造物的藝術性正名(Crowther, “Performing Live”909-912)。這便為他后續對于20世紀和21世紀藝術(特別是其中的抽象藝術、觀念藝術、數字藝術)的討論,奠定了理論探討的邏輯和方法論基礎。例如,在《20世紀藝術的語言: 一部觀念史》(:, 1997年)一書中,克勞瑟旗幟鮮明地反對以藝術的外部研究為中心的還原主義傾向,強調一種內向主義(internalism)。他認為,藝術的意義深藏于藝術作品的內部,我們并不需要通過對藝術家的意圖和藝術作品創制與接受的語境的認知,來把握這些作品的內在意涵,或者更明確地說,沒有什么意義是在作品本身之外的,藝術參與者最真實的審美經驗只來自可感知的形式化的線條和色彩等(Crowther,16)。對此,丹托(Arthur Danto)在關于此書的評論中表示,他承認克勞瑟提倡的內向主義的價值,但更主張一種內向主義與外向主義的平衡(Danto41)。
其后,克勞瑟在其多部論著,如《數字藝術的存在論與美學》(“Ontology and Aesthetics of Digital Art”, 2008年)、《現代藝術的現象學: 思考德勒茲,彰顯形式風格》(,, 2012年)、《抽象藝術的意涵: 在自然與理論之間》(:, 2012年)、《數字藝術,審美創造: 媒介的誕生》、《后現代藝術的緣起: 作為圖像學的技術》等,都旨在叩問藝術本質的問題。在克勞瑟看來,非具象的抽象藝術、以理論為核心的觀念藝術,以及用電腦創作的數字藝術等(當然也包括非西方藝術),都是真正的藝術,這些不同于傳統的表達形式,都創造了具有獨特審美效果和價值的藝術作品,形成了新的審美經驗。克勞瑟最新的著作《藝術品的理論》可被視為其對于藝術形式本質的最新思考以及對其過去觀點的總結和反思。在《視覺藝術的現象學》等對不同藝術門類的研究的基礎上,《藝術品的理論》通過對傳統具象藝術、抽象藝術、雕塑及裝置作品、大地藝術、建筑、攝影和種類各異的數字藝術的考察,試圖在形式主義的意義上尋找藝術品作為藝術的本質和基礎以及不同門類藝術之間的共性——即在審美的意義上表現(或者再現)作為個體的我們如何具體地經驗時空以及我們與他人和世界之間的關系。
二、 反還原主義方法論: 后分析現象學方法
在認識和理解藝術的形式本質之后,克勞瑟的主要任務便轉向如何具體地把握和揭示這一本質,也就是說,在具體實踐中,主體如何可以接觸和經驗這一本質,使后者成為對于前者而言具有實際意義或者無功利的審美意味的具體形式。為了有效地達到這一目的,克勞瑟引入了現象學的方法。毋庸置疑,現象學對于藝術對象和審美經驗的考察(或者我們可以稱之為“現象學美學”的東西),已經有了一個長期的發展歷程,其中較為重要的思想家包括維塔塞克(Witasek)、韋貝爾(Franc Veber)、蓋格爾、海德格爾、薩特、梅洛-龐蒂、杜夫海納、英伽登、伽達默爾,以及更晚近一些的諸如愛德華·凱西(Edward S. Casey)等(Crowther,2)。然而,克勞瑟十分清醒地意識到,如此厚重的現象學傳統并未在藝術研究領域產生其本應發揮的更大影響;究其原因,其一是由于藝術并非現象學研究者討論的核心問題,而僅是被作為討論現象學的一個案例,其二,現象學并未發展出一套有關藝術的獨特且綜合的理論(Crowther,2)。因此,我們在此必須認識到的是,出于對過往傳統的深刻反思,克勞瑟的現象學與他前代或者同時代的其他現象學者的理路存在較大的差異。換句話說,他的思想并非完全來自胡塞爾、海德格爾等學者的經典現象學理論,而是更多地源自自身作為經驗主體對于藝術作品(形式)的體察,以及梅洛-龐蒂的知覺現象學方法(這是克勞瑟除了康德美學之外的另一重要起點,但他對此也不是全盤地照搬運用)。因此,克勞瑟在其論著中所討論的并不完全是純粹的理論,而是以經驗事實和具身化主體的生命體驗為中心展開的描述和闡釋。換句話說,其所實踐的并不是理論先行的論說,而是基于具體藝術案例的深入分析,是對于生活世界中的經驗現象的直觀把握和闡釋。其實,克勞瑟的現象學方法,有著深刻的康德美學根源。
在前文已經提到的《巴尼特·紐曼和崇高》一文中,克勞瑟就已經非常清晰地認識到,審美經驗是與主體的感知和自我意識緊密相關的。依據康德的理論,“崇高”成為了審美經驗中不同于“優美”的另一取向。崇高感的基礎是人類以自身的身體為尺度對周遭事物的外在形式進行度量,從而感知到自然的偉大和自身的渺小,也就是說,崇高建基于最直接的身體經驗和由此而產生的各種意識和情感(如恐懼、敬畏等)(康德72—105)。克勞瑟認為,藝術就是具身化的個人意識。這一點應是他從康德關于想象的理論中(并融合了現象學視角)發展而來的。根據克勞瑟的理解,在康德看來,由于人類的有限性,我們對于無限廣闊的世界(崇高感產生的客觀基礎)的認識,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想象而實現的,但是,這種想象性的認識并不是被動的,而是主體主動觀照的行為(Crowther,1,30)。克勞瑟由此而得出審美經驗是與自我意識的緣起相互指涉的結論。同時,他進一步強調,藝術具有一種形象化本質(image character),我們的形象化過程,并不是對于外在客觀世界的簡單再現,而是對之的一種解釋,這便將客觀知識與自我意識和生命體驗進行了勾連。正是由于自我意識與生命經驗對于藝術感知和審美經驗的介入,克勞瑟逐漸從作為起點的、對于普遍經驗進行追思的康德美學走向了以具體身體經驗為中心的現象學,特別是梅洛-龐蒂的知覺現象學。
在此,需要提及的是,克勞瑟有關康德的闡釋,與德勒茲有很多相似之處。在德勒茲看來,主體關于崇高的主觀感受,并不是作為一種抽象的觀念而意指所謂的“真理”(truth),而是與作為有道德之存在的我們的官能的實際指向相關的。與克勞瑟一樣,德勒茲對于崇高的理解,并沒有趨向康德最終對于經驗的超越,而是將在“前真實”的自然中的最原初的感知(一種在知性進入之前的感知)置于討論的核心(Deleuze46-67)。其實,關于這一點,同樣關注康德崇高理論的齊澤克,也曾表達了相似的觀點。在齊澤克看來,“崇高”的悖論在于,從理論上來說,它一方面將經驗(experience)中現象性和感知性的物體與物自體(Thing-in-itself)相分離,而二者之間的鴻溝是難以克服和超越的;而另一方面,崇高是一個物(Object),它使得我們可以經驗這一不可能性(?i?ek229)。齊澤克進一步說到:“沒有什么東西是非現象性的(nothing beyond phenomenality)。”(232)雖然齊澤克最終將討論引向了一種后宗教的神性,但是,在其看來,實在的經驗和感知仍然是審美體驗和獲得精神超越的基礎:“我們對于現象性的克服并不是通過對之的超越而實現的,而是通過經驗它是如何不可被超越而達到的。”(233)
克勞瑟在其《現代藝術的現象學: 重讀德勒茲,彰顯形式風格》一書中,便以自身與德勒茲在有關康德思想闡釋以及分析藝術作品等方面的相似點為起始(即克勞瑟所認為的德勒茲所顯現的現象學洞見——從具體的感知經驗維度探究藝術風格,而非將之還原為審美體系或者更為宏大的社會文化的話語體系中的抽象概念和認知),通過進一步引入尼采與梅洛-龐蒂,基于形式風格(而非藝術作品的外部關系——社會的、政治的,等)的深入分析,對現代藝術的本質內涵以及功能屬性進行了深入討論。可見,康德哲學(克勞瑟主要討論的是康氏對于崇高的理解)是克勞瑟美學研究道路的起點、及其與其他理論家進行對話的支點,最重要的,也是克氏不斷回溯的理論刺點。
在同為1993年出版的兩本著作《藝術與具身化: 從美學走向自我意識》(:-)和《批判美學和后現代主義》中,克勞瑟以康德美學為基礎和起點,討論了藝術與具身化主體的自我意識之間的關聯,并將討論引向了由杜尚開啟的后現代藝術的洪流。其中,克勞瑟將討論的中心聚焦于審美經驗,以及主體的審美經驗是如何得以實現的問題。在其看來,這一審美經驗的實現,是具身化的主體(藝術家)與對象客體(世界)之間的交互性關系(reciprocity)而形成的現象學深度(phenomenological depth)所建構的,是主體通過其身體實踐和感知而達到的內趨性的自我審美意識。與克勞瑟的其他著作一樣,作者在這兩本書中都表現了其對于所討論的藝術作品的熟悉程度。不過,與傳統的作品分析不同的是,克勞瑟在此將其進入方式由描述(description)作品的細節轉向了呈現主體對于作品的感知和經驗(perception and experience)。可見,克勞瑟在此已經顯現出了與后現代主義理論家,如德里達、福柯等完全不同的思考路徑。在后現代理論家看來,主體有關世界的想象和自我的認識,并不存在一種堅實的存在本質和基礎,而是通過權力關系、話語結構以及“語言”所建構出來的,其真實性是虛妄的,對于它的追求將一無所獲。然而,在以直觀經驗為基礎的現象學(特別是知覺現象學)理論的影響下,克勞瑟肯定現象本身(形式)作為物或者事件的真實性以及探究現象背后的本質的可能性,但是,克勞瑟同時強調,要達到這些,需要一種非常獨到和特殊的方法。這一方法便是分析哲學與現象學的結合,克勞瑟稱之為“后分析現象學”(post-analytic phenomenology)。
依據博爾珊(Ludmila Birsan)的說法,這一所謂的“后分析現象學”方法,是在其三本重要著作中奠基的,即《視覺藝術的現象學》《現代藝術的現象學: 重讀德勒茲,彰顯形式風格》《藝術與視覺的現象學: 后分析轉向》(:-, 2013年)(Birsan233-238)。在《視覺藝術的現象學》中,克勞瑟首先提出了所謂“現象學深度”這一概念,用以標注主體的審美經驗。一般意義上而言,現象學考量的是主體如何去經驗現象,或者現象被經驗的方式和結構,而現象學深度所指涉的,是主客體經驗之間的存在性(本體性)互動,或者說,現象學的深度,就是主體的主觀經驗與其所經驗的客體以及有關客體的知識之間的“距離”,正是這一“距離”決定了主體經驗客體的方式。關于“現象學深度”,克勞瑟有如下說明:“現象學深度以主客體經驗的存在性交互(ontological reciprocity)為中心。具身化的主體沉浸于一個不以他/她(甚至它)的存在為前提的客觀世界,而這一客觀世界實際上決定了主體的特性(這種決定性在于規定了主體的物質構成,以及主體為求生存而必須參與的各項行動)。然而,與此同時,物質世界的性質,如其被感知的,是通過一系列由主體帶入并施于其上的認知力和機動力作用而形成的特定形質。因此,主體的本體論結構和其所經驗的客體,在很多重要方面,均是互相交織聯結的。在經驗層面,任意一方事實上都是另一方構筑完整自我存在的一部分。”(Crowther,3)。“現象學深度”雖是克勞瑟所創造的語匯,從本質上而言與杜夫海納在其《審美經驗的現象學》(, Evanston, 1989年)中所使用的“審美深度”(depth of the aesthetic)和“存在深度”(depth of the existence)旨趣相同,均指向主客體之間的“爭執”。
在《藝術與視覺的現象學: 后分析轉向》中,正如克勞瑟在稍后出版的《后現代主義之后的哲學: 文明價值與知識的廣度》(:e, 2014年)中明確指出的,后現代主義思潮往往持一種反基礎主義的態度,在吸取后現代主義的某些批判性思想的同時,由于受到卡西爾的影響,他將引入一種新的分析哲學的方法(并不是以語言為中心的,但是注重“分析”和語言表達的準確性與邏輯性),以走出后現代主義否定一切“本質”和“真實性”的局限。在克勞瑟看來,分析哲學傳統的要義在于清晰且連貫地呈現哲學家的哲思,這一方法可以被運用于他所關注的圖像再現問題,它將有利于我們在視覺藝術紛繁蕪雜、絢麗繽紛的表象之下,認識和理解其深層次的內在形式邏輯和知覺結構。在此,克勞瑟還提到所謂“后分析視野”(post-analytic vision),即主體應當對其所使用的分析框架有所認知,而不是將對象直接投入該框架中進行闡釋。它因而具有一種文化多元主義的意味: 當我們將一種文化放入另外一種文化系統中進行考察時,它的文化優勢在新的文化環境中并不一定繼續保持領先地位,但是,如果我們以一種文化多元的姿態對所有的傳統優勢進行聯合比較時,克勞瑟的題中之義(這聯系到我們之前提到的有關藝術的定義以及藝術本質的認知)便由此顯現了。當然,克勞瑟同樣清晰地意識到,分析哲學的傳統方法傾向于從形式構成上介入對象,并將這些純粹形式上的分析結論用于理解作為知性和感性整體的現象性對象(經驗的、“活的”),但是,無疑,這樣的分析忽略了這一整體是建基于具身化的主客體經驗之間的關聯性存在。因此,唯有引入現象學,才有可能解決傳統分析哲學的困境。
總的說來,克勞瑟的藝術分析方法是分析哲學與現象學的結合,分析哲學提供了認識和理解對象的邏輯和內在結構框架,而現象學則可以非常深入和詳盡地描述(感知)對象。這便是克勞瑟的“后分析現象學”(在《視覺藝術的現象學》中,克勞瑟一開始將其方法稱為“分析現象學”),它通過感知對象最基本的形式要素,如形狀和顏色等,對該對象的風格(或者說是慣例或者程式)進行探討,以追索經驗對象的獨特審美意涵。近年來,克勞瑟的多部著作,如《圖像是如何讓我們成圣的: 美、崇高與神圣》(:,, 2016年)、《素描與繪畫的意義究竟是什么: 圖像與姿勢的現象學》(:, 2017年)、《自我成就的美學: 藝術形式是如何被賦權的?》(:, 2019年),以及《藝術品的理論》等,都利用了“后分析現象學”的方法。他通過對于具體藝術作品及其所呈現的“現象學深度”的分析,探究了主體最真切的審美經驗的形成過程和呈現方式等不同面向,展現了有關客觀世界的知識(knowledge of an objective world)與主體自我意識的統一性(the unity of self-consciousness)之間的緊密關聯。
三、 形式的延伸與后分析現象學的新可能
克勞瑟的理論與方法指明了兩點: 第一,從形式主義的角度而言,藝術的邊界并不局限于西方傳統藝術門類和風格,定義與評價藝術的標準也不應依照歐洲中心主義所設立的具有明顯價值偏向的制度與規范,而應指向一種更具普適性的、以人類共有的審美經驗為基礎的價值體系;第二,后分析現象學方法是一種非常行之有效的藝術分析方法,它強調最為基礎的、以純粹形式為對象的人類感知,是對于還原主義方法的有力補充。從《視覺藝術的現象學》開始,克勞瑟的論著基本上都在深化上述兩個維度。正如克勞瑟在其不同著作中反復提及的,如丹托所言,傳統藝術已經喪失了其明顯的創造力而走向形式的“終結”,在歷史上,唯有不斷引入新的藝術形式風格和媒介,如觀念藝術、數字藝術等,才有可能促進藝術的向前推進和發展。而這些新進引入的、以新形式風格表現并以新的技術手段和材料為媒介的新“藝術”,在一開始并不被視為“藝術”而遭到不同程度的質疑甚至否定。在此,筆者亦希望能以克勞瑟關于藝術本質的討論為起點進行延伸與拓展,通過運用其后分析現象學方法,進一步探討其尚未關注的領域和藝術實踐活動。
在有關藝術界定的討論中,克勞瑟雖然擴大了傳統藝術的視閾,將非西方藝術、后現代藝術等原先并未被承認為藝術的對象納入考量的范圍,但是,他對某些“新”的藝術形式卻并未關注(當然,這關乎個人的學術興趣,此處并無褒貶之意),其中的一個類別,便是所謂的“局外人藝術”(outsider art),這是筆者所關注的領域。局外人藝術是羅杰·卡迪納爾(Roger Cardinal)于1972年通過其著作《局外人藝術》提出的概念,目的是與現代派畫家讓·杜布菲(Jean Dubuffet)所發明的“原生藝術”概念(art brut/raw art)相對應。一般而言,在形式上,這些藝術作品趨向于遠離社區傳統的制作方式以及大眾審美,顯示出一種極為濃烈的個人和亞群體風格,而在形式觀念上,它們不以主流意識形態(特別是歐洲中心主義影響下的西方藝術傳統)為轉移,也不遵從藝術品市場的運作規律。與此相應,所謂“局外人藝術家”指的是那些沒有經過正統藝術訓練的人(包括精神病患者和兒童),他們以及承載其觀念的藝術形式游離于主流文化以及藝術界的大傳統之外,這些藝術作品形質怪異且沒有先例(Wojcik179)。局外人藝術家的創造力以及他們所創作的作品形式,反映了他們與他人以及更為廣闊的外部世界在情感、精神(宗教)、文化與審美觀照上的聯結與互動。這些藝術家往往由于自身的身份而被社會邊緣化或者為他人所排斥,抑或處于較低的政治經濟地位,但是他們渴望表達自己的聲音,與外部世界進行深層交流,抒發自我的情感,并應對生命中的各種不幸和艱難。然而,如果借助克勞瑟關于藝術本質的形式主義界定,加上日益深化的“人類學轉向”和“全球藝術”觀念的推動下,“局外人藝術家”及其作品(尤其是作品的形式風格),顯然已經被納入到全球藝術發展和追求“文化民主”的歷史進程之中。
目前,有關局外人藝術的探討已經不少,但是基本上都聚焦于研究對象的外部世界。例如,邁克爾·歐文·瓊斯(Michael Owen Jones)指出,研究者在探討“局外人藝術”時,除關注物質文化(即物品本身)(material culture),更應該關注其物質行為(material behavior),藝術家的實踐行動中隱藏著可以幫助認知和理解物質對象的各種社會關系,而正是這些社會關系催生了藝術作品的意義與價值(Jones59-60)。在這個意義上,尼古拉斯·博瑞奧德(Nicolas Bourriaud)否認藝術具有一種從形式上而言不變的內在屬性(an immutable essence)(Bourriaud11),提出所謂“關系美學”的概念(relational aesthetics),強調參與性與協作性的藝術實踐(Bourriaud16)。博瑞奧德認為,通過所有實踐者共同協作與參與,可以促成民主且開放的審美意識交流與交換的空間(space of aesthetic exchange)的形成。在博瑞奧德觀念的基礎之上,藝術史家和策展人尼娜·門特曼(Nina M?ntmann)在其《作為社會空間的藝術》(, 2002年)中將藝術看作一種具有能動性的社會空間,在這一社會空間中,各方的互動以及各種社會關系得以開展和聯結。而這些社會關系能夠制造和賦予后者意義和價值的原因,正是由于在后殖民的話語體系中,藝術家和人類學家等文化工作者均將藝術的本質看作是“再現的政治學”(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而非康德所謂“無功利的審美”(disinterested aesthetic judgment)。因此,韋斯·希爾有言:“二十一世紀藝術所再現的眾多對象,均被賦予了各種文化的、制度性的、宗教的和個人的意義。這些指向不同的意義系統同時存在,膠著在一起,互相競爭。”(Hill65)然而,希爾認為,各意義系統之間的競爭并非完全無序,且完全受制于話語體系中的不平等的權力關系,相反,基于各意義系統本身的獨特性,它們之間存在著潛在的平等性和交互性(175)。斯芬·呂提肯(Sven Lütticken)故而將意義與價值系統看作是超越藝術作品本身而存在的、由藝術家、批評家以及所有觀者在不同情境中創作、觀看和使用該對象時,通過某種協作式的“共謀”而重塑的文化身份的標記和屬性(Lütticken124-125)。
非常明顯的是,以上還原主義色彩明顯的討論與克勞瑟所關注的形式主義角度全然相異,上述研究者似乎已經對“局外人藝術”作為藝術的一部分這一事實深信不疑,然而,后者則仍在對這一問題進行思考。在筆者看來,就目前而言,有關“局外人藝術”的研究,其實一直缺乏對于研究對象的本體研究,而過分強調與之相關的外部社會文化語境,這是人類學與民俗學一直以來的具有深刻還原論性質的研究傳統。由于較少關注經驗對象本身所蘊含的形式特征和具體表現形態,它們作為藝術品的特質或者說其藝術特性時常為研究者所忽略,審美經驗似乎是一件令人感到非常私密、不適于分享和用作研究材料的微不足道的細節。但是,正如克勞瑟所言,“找到并呈現有關一件作品如何創作的信仰和社會語境,并不能解釋為什么經過特定方式處理的材料,能夠被用來表現宇宙的力量,或者承載某種魔法或其它類似之物。[……]能使得信仰觀念發生作用的因素,并不能通過還原論的方法清晰地表述出來。有一種積極的審美情愫深藏于創造圖像的那種創造力的內在,而這種情愫并不能被消費主義的還原論調所解釋。雖然‘審美’這個概念作為現代西方的創造,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即使它源于‘美’這個被廣泛傳播和使用的概念,審美本身所指涉的乃是基于特定對象的視覺呈現方式自身所散發的獨特魅力。”(Crowther,16)其實,筆者在拙文《民俗、藝術及審美經驗》(《民族文學研究》2017年第4期)一文中已經提到,有關包括民間藝術在內的“局外人藝術”的研究,應該分為兩個層次,一是從民俗學和人類學的角度進行的語境分析,另外一個便是從藝術學的角度進行的形式分析和審美經驗探究。在第二個層次中,克勞瑟的后分析現象學方法將會非常有助于研究者對民俗材料,特別是其中的視覺材料,進行認知、理解和分析。這應該符合克勞瑟的題中之義。
結 語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克勞瑟的形式主義美學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康德理論中關于“崇高”的表述,但是,他并未完全照搬康德的觀點,而是以其為基礎和起點進行了有效的重讀和闡釋,并賦予了古典哲學文本以新知新意,使之不再成為解決當下問題的阻礙,而轉變為促進其解決的不竭推動力。由于重新確立了“崇高”作為重要審美經驗的地位,原先強調“優美”的藝術傳統(特別是西方藝術傳統)便逐漸發生改變,使得重新定義藝術及其本質成為了可能。在這一進程中,原先并不作為藝術的“類別”開始得到重新審視和理解,它們逐漸被歸入“藝術”的范疇,成為可以進行審美觀照的經驗對象,從而最終擴大了藝術的邊界,并更加增進了我們對于藝術內在意涵的認知和理解。在這一前提下,在觀照經驗對象時,克勞瑟所采取的并非占據主導地位的還原主義方法,將目光投向藝術現象的外部關系,而是結合了分析哲學和現象學,創造了一種所謂的“后分析現象學”方法。這一方法使得我們可以在主客觀經驗的膠著、纏繞與“爭執”中,逐漸獲得關于對象的審美經驗,實現對其的充分且清晰的認知和理解。克勞瑟的理論和方法,可以平衡當代的藝術研究領域中廣泛存在的還原主義居于絕對主導地位的失衡現狀,使得藝術研究不脫離藝術存在的基本形式及其所呈現出來的主客體交互的姿勢與痕跡。可見,唯有重新界定藝術,并有效平衡內外部研究之間的關系,才有可能達到如康德所言最普遍的藝術本質的認識。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諸多現代與后現代藝術才有可能被冠以藝術之名而得以存在和被理解。在當代眾多的藝術存在形式中,“局外人藝術”是一種非常有意味的形式,應通過克勞瑟的分析方法對其進一步地探討、分析和感性把握,從而才能從對象內部理解其作為藝術的本體價值和存在意義。
① 當然,目前很多研究趨向于將還原主義與形式主義方法相結合。
② 本文討論的重要學者保羅·克勞瑟1953年8月24日出生于英格蘭的利茲(Leeds),曾就讀于曼徹斯特大學(后轉學)、利茲大學(獲哲學和藝術史雙學位)、約克大學(哲學碩士),最后在牛津大學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他現在擔任位于斯洛文尼亞首都盧布爾雅那(Ljubljana)的歐羅巴大學人文學院(Alma Mater Europaea-Institutm Studiorum Humanitatis)的哲學教授。克勞瑟教授是愛爾蘭皇家科學院(the Royal Irish Academy)院士,曾為牛津大學藝術史講師,并為該校基督圣體學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成員。他任教于多所歐洲大學,并在其中的四所獲得了正教授的職位(其中包括德國不來梅雅格布大學(Jacobs University Bremen)和愛爾蘭國立大學高威分校(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 Galway)等)。到目前為止,克勞瑟教授共出版了17部涉及美學、20世紀藝術與當代藝術領域的專著,其中包括其最近出版的《藝術品的理論》(, 2019年),以及兩卷有關后現代藝術的研究《數字藝術,審美創造: 媒介的誕生》(,:, 2018年)和《后現代藝術的緣起: 作為圖像學的技術》(:, 2018年)。
③ 然而,在《視覺藝術的現象學》(2009年)一書的第一章中,克勞瑟似乎修正了自己的這個觀點,而認為有關藝術與審美經驗的研究在當時出現了非常明顯的還原主義研究傾向,即將研究的重點從對象的形式和內在結構(內部研究),轉向了藝術的外部研究(如藝術社會學、藝術社會史等)。
④ 例如,保羅·蓋耶(Paul Guyer)在關于康德《判斷力批判》的討論中,大量篇幅都在論述和分析康德對于“優美”及相關問題的表述,而僅有第七章的第三部分涉及“崇高”(Guyer235-238)。
⑤ 羅杰森的原話為:“Paul Crowther’s book on the sublime helps to fill a significant gap in Kant scholarship. While recently there has been considerable attention paid to Kant’s Critique of Aesthetic Judgment (the first half of the Critique of Judgment) the focus has been on the account of beauty.”。
⑥ 當然,席勒已經開始提出崇高源自一種內在力量,而非外部自然的威權,因此,他試圖用崇高來理解和闡釋悲劇。
⑦ 原文為“Art is a class of artifacts that centers upon the making of images, or as I prefer to describe it, artifactual imaging.”
⑧ 當然,必須強調的是,雖然有關趣味(taste)的審美判斷本應是主觀的且無疑是基于感知的,康德自身并未把“經驗”(如物質的、身體的和情感等面向)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相反,他的哲學是有意回避這一點的。在康德看來,經驗是一種被動的主體經驗,并非主體主動進行的認知活動。關于這一點,可以參見其《純粹理性批判》中有關“經驗”(empirical)、“經驗自我”(empirical)和“經驗意識”(empirical consciousness)的討論。
⑨ 關于克勞瑟對德勒茲“現象學”洞見的解讀,可參見(Crowther,1-56)。
⑩ 此處的“美”并不是我們之前所謂的“優美”。
Belting, Hans. “From World Art to Global Art: View on a New Panorama.”Eds. Hans Belting, Andrea Buddensieg and Peter Weibel.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3.178-85.
Birsan, Ludmila. “Art, Vision, and the Necessity of a Post-Analytic Phenomenology.”:,,5.1(2013): 233-38.
Bourriaud, Nicolas.. Dijon: Les Presses du Réel, 2002.
Crowther, Paul. “The Experience of Art: Some 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of Hermeneutical Analysis.”43.3(1983): 347-62.
- - -. “Barnett Newman and the Sublime.”7.2(1984): 52-59.
- -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 -.-:.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 -. “Performing Live: Aesthetic Alternatives for the Ends of Art.”111.444(2002): 909-12.
- - -. “Cultural Exclusion, Normativity, and the Definition of Art.”61.2(2003): 121-31.
- -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10.
- - -.:,.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12.
Danto, Arthur. “Book Review::”.141.1150(1999): 41.
Deleuze, Gilles.’:.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84.
Guyer, Paul.London an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Hill, W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Jones, Michael Owen.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 Ed. Charles Russell.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1.47-60.
伊曼努爾·康德: 《判斷力批判(注釋本)》,李秋零譯注。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
[Kant, Immanuel.. Trans and ed. Li Qiuling.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1.]
Lütticken, Sven. “The Father of the Eagle.”36(2005): 109-25.
Mcquilian, J. Colin. “Book Review::-”122.488(2013): 1075-78.
Rogerson, Kenneth F. “Book Review::by Paul Crowther.”49.4(1991): 379-81.
Wojcik, Daniel. “Outsider Art, Vernacular Traditions, Trauma, and Creativity.”67.2/3(2008): 179-98.
?i?ek, Slavoj.. London: Verso,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