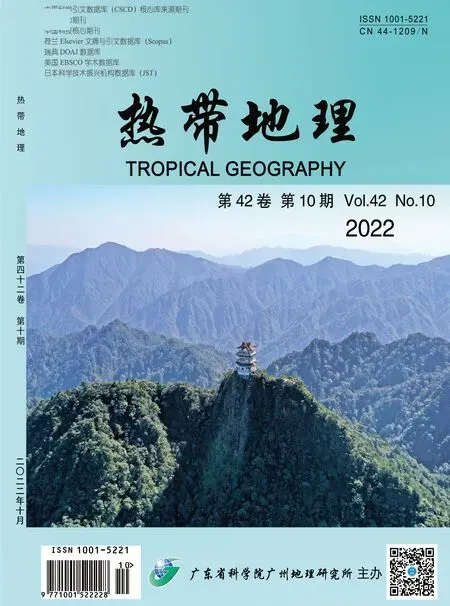中國沿海港口物流網絡空間結構演化及其影響因素
郭建科,喻鑠琪
(1.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遼寧師范大學海洋經濟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遼寧 大連 116029;2. 遼寧省“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高校協同創新中心,遼寧 大連 116029)
近年來,隨著經濟全球化與各國生產貿易的網絡化發展,沿海港口作為海陸間連接點,在物流功能上正不斷拓展與創新,這為沿海港口物流業的快速發展奠定了基礎(Hesse et al., 2006;王成金,2006)。港口物流逐漸由傳統的裝卸服務轉向綜合物流服務,并在全球貨物貿易網絡中承擔著重要作用(葉士琳等,2017a)。而作為港口物流活動的重要載體,港口物流企業主要進行跨區域組織物流活動。隨著城市內港口物流企業的集聚與城市間港口物流企業的擴散,港口物流網絡雛形初步顯現。港口物流網絡化發展是現代港口物流業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通過有效結合各類生產要素,形成高效運作體系與專業化分工,可推動港口物流企業協同合作,提升整體運輸效率,最終實現網絡化配置資源。因此對港口物流網絡開展研究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近年來,國內外關于港口物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物流網絡、港口物流企業空間布局以及港口物流行業3個方面。1)物流網絡方面。國外對物流網絡研究始于20 世紀90 年代,已有研究側重于物流合作網絡與配送網絡(Fleming et al.,1994;Robinson,1998;Lin et al.,2003)。隨著物流企業在歐美的快速發展,國外學者進一步探究物流企業網絡樞紐的影響機制(Carbone et al.,2005;Kim et al.,2005;Rimmer et al.,2005;Ko et al.,2006),并借助軸輻理論刻畫物流網絡。但有關物流網絡的研究還處于初步探索階段,缺乏系統性。而國內港口物流網絡化發展起步相對較晚,國內學者早先更多從區域視角探究港口物流網絡,如王健(2005)采用模糊聚類方法對福建省主要沿海港口進行宏觀規劃層次分析。而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專業化程度與社會分工正不斷加深,物流活動布局在地理范圍上逐步擴展,更多學者將研究范圍放眼于全國,如魏雯青等(2015)針對性地從物流網絡視角提出提升港口物流競爭力的策略。胡榮等(2022)指出可通過建立海鐵聯運、疏港鐵路等相結合的交通網絡以提升物流網絡水平。2)港口物流企業空間布局方面。國內相關研究多側重于單個區域范圍內港口物流企業空間格局及區位選擇,如梁雙波(2013)、朱慧(2017)、王瑞(2018)等基于港口物流企業空間數據,運用GIS空間分析、數理統計等方法,研究單個區域內港口物流企業空間分布特征及影響因素,針對性地提出優化企業空間格局的相關對策建議。港口物流企業作為港口物流網絡的重要單元,其空間布局對網絡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合理規劃企業布局不僅有利于各企業自身發展,而且也有助于推動港口物流網絡的整體發展。3)港口物流行業方面。國內學者針對中國港口物流業發展現狀,借鑒先進港口城市發展經驗,有的放矢地提出推進中國港口物流業發展的相關對策建議,如吳磊等(2016)借鑒鹿特丹和新加坡港口物流轉型升級的經驗,提出解決中國港口物流業轉型升級的關鍵舉措;黃仁剛(2020)指出粵港澳大灣區的物流發展存在資源配置優化不足、同質化競爭、人才匱乏與機制創新不足等問題。
綜上,已有關于港口物流的研究較為豐富,但在港口物流網絡這一細分領域上較少涉及港口節點與航線。面對港口物流綜合服務化發展趨勢,港口物流企業作為沿海城市間重要的物流業務聯系紐帶,正成為網絡研究的切入點。基于企業這一微觀視角的港口物流網絡研究不僅有助于掌握中國沿海港口物流網絡的空間結構特征,同時可揭示網絡發展的影響因素,對于合理規劃沿海港口物流空間布局具有一定指導意義。基于此,本文基于中國沿海城市港口物流企業數據,分析2009—2019年港口物流網絡空間結構演化特征,并運用QAP分析法探究網絡空間結構演化的影響因素,以期為中國沿海港口物流空間布局與網絡結構優化提供參考。
1 數據來源與方法
1.1 數據來源
以中國大陸地區沿海港口物流上市公司和貨代物流企業為研究對象。參照中國國際物流與貨代網①http://www.cifa-china.com/cn/index.html發布的2019年度中國貨代物流企業百強名單與中國物流上市公司名單,基于企業官網信息篩選出主營業務與港口物流服務相關的企業,結合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平臺②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選取在中國沿海城市設立分支機構且信息完備的港口物流企業。最終選定59家港口物流企業,其總部分布于全國21個主要沿海城市,分支機構分布于44 個沿海城市。以2009、2014、2019 年為時間節點,采集企業的辦公地址、注冊地址、注冊日期等數據。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選取的港口物流企業在中國沿海港口物流市場占具較大規模且擁有較高影響力,代表性較強,可有效體現中國沿海港口物流網絡空間結構。進一步,依照港口物流企業在各市的分支機構(總部、區域分公司、地方分公司和辦事處)等級規模依序賦值為4、3、2、1分,從而構建出總部—分支機構聯系矩陣(葉士琳等,2017b)。影響因素分析所涉及的國民生產總值、萬噸級以上泊位數等數據來源于2010、2015、2020 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國家統計局城市社會經濟調查司,2010;2015;2020)《中國港口年鑒》(中國港口年鑒編輯部,2010;2015;2020),部分缺失數據補充自各城市統計年鑒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1.2 研究方法
1.2.1 網絡聯系測度方法 借鑒世界城市網絡方法(Taylor, 2001),對沿海港口物流網絡聯系進行量化。以港口物流企業q所在城市i和城市j的得分表示企業q分布于城市i和城市j的分支機構在其港口物流網絡中的重要程度,分別用viq和vjq表示。在此基礎上,城市i和城市j間的組織聯系度為rij,表達式為:
式中:rijq表示企業q所在城市i與城市j之間的基本組織聯系量;m表示企業總數。城市i在港口物流網絡中聯系強度為Ri,表達式為:
式中:n表示城市總數,每個城市至多存在(n-1)個聯系。
1.2.2 社會網絡基本指標 1)平均度。該指標用以測算沿海港口物流網絡中與城市i直接相連城市的個數,反映該城市中心性高低(Duncan et al.,1998)。
2)加權平均度。該指標是平均度的一般形式,對取得的每個點,將其邊的權重進行求和,計算與節點數的比值即為加權平均度,數值越高,表示城市在沿海港口物流網絡中的中心性越高。
3)網絡密度。用于測度沿海港口物流網絡聯系的密集程度,取值范圍處于[0,1],數值越高表示沿海港口物流網絡中城市間聯系越緊密,具體表達式為:
式中:D表示沿海港口物流網絡密度;n表示沿海港口物流網絡中節點數量;L表示沿海港口物流網絡實際的聯系數。
4)平均路徑長度(Average Path Length)。該指標是體現沿海港口物流網絡中任意兩城市間的最短路徑邊數平均值的重要依據,公式為:
式中:L表示平均路徑長度;n表示沿海港口物流網絡節點數;dij表示城市i、j之間的最短路徑的條數;L值越小,反映沿海港口物流網絡連通性與空間組織效能越高(Newman,2003)。
5)聚類系數(Clustering Coefficient),該指標是表示沿海港口物流網絡集團化水平的重要指標,體現鄰接城市間聯系密切程度,公式為:
式中:Ci表示城市i的聚類系數;Ei表示城市i與鄰接城市間存在的實際邊數;ki表示城市i的度數;Ci介于[0,1]區間,Ci的數值越高,表示城市i與其鄰接城市之間的相互聯系越密切。而整體沿海港口物流網絡聚類系數C則為網絡中全部城市聚類系數的平均值,公式為:
式中:C表示沿海港口物流網絡中全部城市的平均聚類系數;n表示該網絡中全部城市數量;C值越高,則整個網絡局部聯系程度越為密切。
1.2.3 二次指派程序 QAP (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是一種對兩個(或多個)方陣中對應各元素值進行比較的方法,用以研究關系網絡的影響因素(王圣云等,2020)。通過比較各方陣對應的格值,給出2個矩陣之間的相關系數,同時對系數進行非參數檢驗。該分析方法可有效回避多重共線性問題,適用于港口物流網絡分析研究。
2 中國沿海港口物流網絡結構特征演變分析
2.1 沿海港口物流網絡聯系的整體特征
1)網絡整體覆蓋范圍逐步擴大
2009—2019年,中國沿海港口物流網絡覆蓋城市與企業的數量不斷增加,城市間聯系強度持續提升。從網絡節點與邊數看,2009—2019年港口物流網絡覆蓋節點增加7 個,邊數較2009 年同比增長20.56%,網絡空間覆蓋范圍顯著擴大;2014—2019年,節點數保持不變,邊數同比增長9.26%,增幅明顯下降,網絡空間覆蓋范圍波動趨于平緩。從企業數量看,2009、2014、2019年物流網絡覆蓋港口物流企業數量同比增幅分別為30.88%、32.72%,企業數量增幅較大且增長態勢穩定。其中,上海、青島、寧波、大連、天津、廣州6個城市的企業增加總數占總體的40%。作為國際貿易的重要口岸城市與國內核心物流樞紐城市,這些城市正成為港口物流網絡發展的主要支撐力。
2)網絡拓撲特征與動態變化趨于穩定
2009—2019年,中國沿海港口物流網絡平均度增幅為10.77%,表明城市節點整體的重要程度正不斷提高(表1)。每個城市平均可獲得港口物流運輸路線從21 條增至23 條,輻射范圍擴大,連接度和可達性提高,與其他城市聯系也更加便利。同時,沿海港口物流網絡集聚程度不斷提高,平均聚類系數增至0.887,表現出較強的集聚性;平均路徑長度降至1.437,表明網絡中城市節點間港口物流運輸所需經過的中轉點數量減少,可選擇的運輸路線增多,貨物運輸的效率有所提高;網絡密度上升至0.592,表明整體網絡結構更加緊密,節點間聯系穩步增強。其中,2009—2014年各項指標的增幅遠低于2014—2019年,這與網絡空間覆蓋范圍的變化有直接關系。2009—2014年,網絡覆蓋節點增長率與邊數增長率較為接近,導致網絡中所有節點度值的平均值等指標波動平緩;而2014—2019年,網絡覆蓋節點未發生變化,但邊數有所增加,導致平均度等指標增幅更為明顯。由此可見,新城市節點的加入使得中國沿海港口物流網絡整體空間結構逐漸趨于成熟,網絡關聯程度顯著提升,網絡地理空間要素聯系的廣度與深度也有所增強。

表1 2009—2019年中國沿海港口物流網絡整體結構特征Table 1 The overall topologic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coastal port logistics network from 2009 to 2019
2.2 沿海港口物流網絡的空間分異結構演變特征
為進一步探究中國沿海港口物流網絡空間結構演化特征,將2009、2014、2019年所有城市間的聯系強度進行降序排列,分別提取前1%、1%~5%、5%~30%主要網絡聯系城市對,將其分劃為核心網絡、骨架網絡與區域聯系網絡3種類型,以簡化復雜聯系網絡便于分析。同時,運用ArcGIS 10.8 分類繪圖進行可視化分析(圖1)。
2009—2019年,中國沿海港口物流的核心網絡由以上海為核心增長極,輻射天津、寧波、廈門和大連的一核四副結構轉變為一核六副結構,新增青島、深圳2個副中心城市,核心網絡規模略有擴大。隨著青島與深圳被列入港口型國家物流樞紐承載城市,這2個城市積極開拓布局國內外航線,優化航線布局,大力發展港口物流業務。其規模以上港口物流企業增幅分別為64.44%和78.26%,極大增強與其他沿海城市物流業務上的互動;核心網絡組織聯系度從[257,329]上升至[399,626],城市對間聯系強度顯著提升,其中聯系強度最高城市對由上海—天津(329)變為上海—寧波(626)。這是由于建成寧波集裝箱干線樞紐港為長三角地區的遠洋集裝箱船提供了中轉站,極大地節約短途運輸費用;同時,建設“一環六射”高速公路主架可實現與上海等城市的2 h 經濟圈;此外,寧波交通基礎設施的優化布局也為其發展港口物流提供交通優勢,增強了與其他沿海城市的業務聯系,尤其是與上海的網絡聯系。但各副中心城市除與上海相聯系外,其相互間均無直接聯系。這表明在核心網絡中,上海起到決定性支撐作用,因此,增強其他城市相互間的業務聯系對強化核心網絡具有關鍵性作用。
2009—2019年,中國沿海港口物流的骨架網絡保持“多三角”結構,且新增天津—青島—大連“三角區”,網絡結構更加豐富。隨著環渤海港口統籌整合持續發展規劃布局的實施,天津—青島—大連3個核心城市間的港口物流聯系進一步加強,區域港口分工也更加明確。骨架網絡中城市節點從11個增至17 個,相互聯系城市對從16 組增至21 組,相較核心網絡,其網絡結構更加穩定與緊密;同時,骨架網絡聯系強度顯著增強,網絡組織聯系度從[96, 234]上升至[156, 365]。其中,上海—廈門城市對的聯系強度穩居首位,從234 增至391,增長67.09%;而上海、寧波、舟山、天津、大連、青島等城市節點聯系強度也顯著增強,助推骨架網絡形成以主要城市為聯系中心向東西南北方向輻射的“多三角”結構。
2009—2019年,在骨架網絡的基礎上,區域網絡向西南沿海城市擴張,共涵蓋全國44個主要沿海城市。大部分邊緣城市以聯系中心城市的途徑融入中國沿海港口物流網絡,但在組織聯系程度上仍與中心城市存在明顯差距,港口物流業務聯系仍以中心城市為主要發力點。其中,處于5%~10%聯系網絡的城市對從19 組增加至25 組,且組織聯系度介于[46,96]。以天津、大連、寧波、廈門、廣州為頂點的近似“三棱柱”網絡結構中,大連被煙臺所替代,形成新“三棱柱”網絡結構。在省港口集團整合的未來趨勢下,煙臺積極參與環渤海灣港口建設及“集散雙向”等業務合作,極大地促進了其與天津港口物流業務聯系,進而成為“三棱柱”網絡結構的重要頂點。處于10%~30%聯系網絡的城市對從79組增加至104組,網絡規模顯著擴大且結構更為完整。同前兩類聯系網絡相比,區域網絡的整體聯系度水平相對較低,但網絡聯系空間結構更加復雜與稠密。
2.3 沿海港口物流網絡的層級結構演變特征
借助Gephi-0.9.2 對2009、2014、2019 年中國沿海港口物流網絡空間結構進行可視化,并依據各節點城市加權平均度將港口物流網絡劃分為核心城市圈層(>6 001)、次核心城市圈層(2 001~6 001)、一般城市圈層(501~2 000)以及邊緣城市圈層(<501)4種層級排列(圖2)。2009年,中國沿海港口物流網絡形成以上海為核心城市節點,青島、廈門、天津、大連、寧波、深圳6個城市節點為次核心城市圈層,福州、廣州等12個城市節點為一般城市圈層,威海等18個城市節點為邊緣城市圈層的四層級圈環網狀結構(圖2-a);2014年,上海保持核心城市節點地位不變,次核心圈層中新增福州節點,滄州、杭州、威海3個城市節點躋身一般城市圈層,邊緣城市圈層對比2009 年新增了防城港、欽州等8個城市節點,港口物流網絡節點數量呈現增長趨勢,節點間關聯程度顯著增強(圖2-b);2019年,寧波升級為核心城市節點,與上海共同構成了核心城市圈層,次核心城市圈層中增加舟山、廣州2個城市節點,唐山、欽州從邊緣城市節點轉為一般城市節點,港口物流網絡節點數量與2014 年保持一致,但圈層間聯系強度較2014 年明顯增強(圖2-c)。
從2009-2019 年,上海的加權平均度穩居第一。作為沿海港口物流網絡的核心城市節點,上海對沿海港口資源要素具有核心配置能力。而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和上海自貿區的加速推進,寧波的經濟水平與港口物流實現縱深向發展,對港口物流網絡資源的控制能力顯著增強,2019年躋身為核心城市,與上海共同形成雙核核心城市圈層。青島、廈門、天津、大連、深圳穩定處于次核心城市圈層;同時,2019年廣州、舟山升級為次核心城市節點,這些城市在經濟水平、港口基礎設施與環境上具有相對優勢與發展潛力。而其余大部分城市節點長期處于一般與邊緣城市等級上,可能是由于這些城市的港口基礎設施、港口物流市場環境與信息化水平整體相對落后,因而其港口物流市場規模較小,導致其與核心城市節點間的港口物流業務聯系較少,較難實現城市層級的升級。
3 中國沿海港口物流網絡影響因素分析
3.1 變量選取與模型構建
2009—2019年,中國沿海港口物流網絡整體性與關聯性呈現增強態勢,主要沿海城市在網絡中的地位發生顯著變化。為進一步探究沿海港口物流網絡的影響因素,借鑒已有研究(產志勇等,2012;黃晗,2013;宗會明等,2020;王介勇等,2021;尹宗明等,2021),以中國沿海港口物流網絡聯系度為被解釋變量,表示各樣本城市在沿海港口物流網絡中的地位;從經濟發展水平、沿海港口物流市場規模、對外貿易環境、物流人力資源、港口基礎設施、產業結構、信息化水平、港口物流企業總部規模8個層面的城市屬性因素綜合分析港口物流網絡形成的影響因素。
選取解釋變量依據:1)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的發展有利于港口物流業的進一步優化升級,是港口物流業發展的基礎,故采用國內生產總值(XGDP)衡量經濟發展水平。2)沿海港口物流市場規模:市場規模的擴大有助于物流要素在空間上自由流動與配置,推動物流產業發展,縮小物流業發展差距,故選取沿海港口貨運吞吐量(XGKTT)量化沿海港口物流市場規模,考察市場規模對空間聯系的驅動作用。3)對外貿易環境:港口物流作為全球性的經濟活動,廣泛的對外貿易決定了港口物流的發展潛能,故采用進出口總額(XJCZE)衡量對外貿易環境。4)物流人力資源:人力資源作為港口物流業基礎運營與宏觀布局的核心要素,決定港口物流網絡未來發展方向,故以港口物流從業人數(XCYRS)量化物流人力資源。5)港口基礎設施:基礎設施條件是港口進行物流作業的物質基礎,完善的港口設施不僅可以提升物流工作效率,而且影響港口物流發展規模,故選用萬噸級以上泊位數(XWDBW)量化港口基礎設施。6)產業結構:產業結構的優化對要素流在地理空間上的轉移與整合具有推動作用,以物流貢獻率即物流業產值占GDP比值(XWLGX)衡量產業結構變化,分析其對港口物流網絡的影響。7)信息化水平:網絡信息化時代下,智慧化港口物流勢在必行,完善成熟的港口物流信息平臺對提供港口物流流通效率具有重要作用,為此采用郵電業務總量(XYDZL)量化信息化水平。8)港口物流企業總部規模:企業總部對于分支機構及同類企業集聚與擴散具有導向作用,影響港口物流網絡的形成,故以港口物流企業總部數量(XQYZB)衡量港口物流企業總部規模。
根據上述指標,在選取樣本時間點利用各沿海城市對應指標的絕對差異建立差異矩陣,構建沿海港口物流網絡影響因素模型:
3.2 實證結果
3.2.1 相關分析 借助UCINET 軟件進行QAP 相關性分析,選擇5 000 次隨機置換,結果如表2 所示。2009、2014、2019 年,8 個指標都對港口物流網絡聯系度具有一定相關性,其中沿海港口貨物吞吐量在3 個年份均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其余解釋變量通過10%的顯著性檢驗。國內生產總值(XGDP)、沿海港口貨物吞吐量(XGKTT)、進出口總額(XJCZE)、港口物流企業總部數量(XQYZB)的差異對港口物流網絡聯系度具有顯著的正影響,而港口物流從業人數(XCYRS)、萬噸級以上泊位數(XWDBW)、物流貢獻率(XWLGX)、郵電業務總量(XYDZL)的差異對港口物流網絡聯系度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2009—2019年,沿海港口貨物吞吐量、萬噸級以上泊位數與港口物流網絡聯系度的相關程度呈現上升趨勢,而國內生產總值、進出口總額、港口物流從業人數、物流貢獻率、郵電業務總量、港口物流企業總部數量的相關程度呈現下降趨勢,即這些影響因素對港口物流網絡聯系度的影響程度有所減弱。

表2 沿海港口物流網絡QAP相關性分析和回歸分析結果Table 2 QAP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coastal port logistics networks
3.2.2 回歸分析 在影響因素均滿足相關檢驗的基礎上,進一步進行QAP 回歸分析,結果如表2 所示。2009—2019年,R2在港口物流網絡中呈現增長態勢,均通過10%統計顯著性檢驗,較高程度上可解釋各因素差異對港口物流網絡聯系度的影響。基于回歸分析結果可得:1)國內生產總值在2009、2014、2019年均通過統計顯著性檢驗,回歸系數為正,表明經濟水平差異越大,城市間港口物流聯系越緊密。但從2009-2019年,國內生產總值的回歸系數呈現遞減態勢,說明其對港口物流網絡的影響程度有所減弱。隨著區域經濟合作與協調工作的推進,區域合作機制不斷完善,城市間經濟發展不平衡現象有所減弱,城市間經濟水平差異縮小導致其對港口物流網絡的影響程度減弱。2)沿海港口貨物吞吐量在3個年份均通過統計顯著性檢驗,回歸系數為正且有所回落,表明沿海港口貨物吞吐量的差異化發展有助于港口物流網絡空間格局的形成。隨著各港口發展水平的逐步提高,各沿海城市港口物流市場需求的擴張降低了其差異程度,降低了該變量對港口物流網絡發展所產生的影響。3)進出口總額與港口物流網絡聯系度在3個年份中均顯著正相關,但有所降低,表明城市經濟與外貿環境差異化發展推動了港口物流網絡的形成。城市經濟發展與外貿環境對港口物流發展起到支撐作用,直接影響港口物流發展的規模與結構,但隨著區域經濟聯動發展與經濟全球化的影響,其差異化發展對港口物流網絡的促進作用有所降低。4)萬噸級以上泊位數在3個年份中的回歸系數均為負且絕對值有所增加,表明港口物流基礎設均衡化發展有助于港口物流網絡的形成。基礎設施均衡化發展對于降低城市間港口同質競爭與合理分工具有重要作用,深刻影響港口集疏運網絡的發展,進而形成更加龐大的港口物流網絡。5)港口物流企業總部數量與港口物流網絡聯系度顯著正相關,但稍有降低。港口物流企業總部分布廣泛的城市往往是經濟較為發達且地理位置具有優勢的城市,因而港口物流企業總部分布的差異化發展有助于各城市節點在網絡中的分工合作與協調發展。但隨著物流協同化發展的推進,港口企業總部分布差異化發展會導致資源分配不平衡,進而降低對港口物流網絡的促進作用。6)郵電業務總量與港口物流網絡聯系度顯著負相關,但絕對值呈現降低趨勢,表明信息水平的差異化發展不利于城市信息網絡的構建,在一定程度上阻礙各市港口物流業務的溝通與合作。但隨著通信網絡技術的發展,各城市信息水平較2009 年有很大提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信息水平差異化,從而降低了其產生的不利影響。而港口物流從業人數、物流貢獻率與港口物流網絡聯系度的回歸分析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物流從業人員與產業結構對港口物流網絡的作用不明顯。
3.3 影響因素分析
城市經濟發展水平與對外貿易環境是港口物流發展的重要基石。經濟發達、對外開放程度高的腹地城市為港口物流發展提供先進便利的軟硬件條件與較大的港口物流市場體量,同時經濟發達城市的發展實力較強與規模較大,能夠充分利用政府政策實現港口自身發展。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地區港口群經濟實力發達且外貿環境優越,為其港口物流發展奠定良好的物質、制度基礎與提供廣闊的海外市場;而西南沿海地區由于經濟實力的限制與國際市場的開發不足,其港口物流發展水平較低。但由于經濟發展兩極化,長三角、珠三角區域內的港口物流差異化較西南沿海地區與環渤海地區也較大,進而導致整體網絡空間結構呈現差異化特征。
港口物流市場規模是物流網絡發展的重要引擎,是決定港口物流企業布局的關鍵因素。大連、天津、青島,上海、寧波,廈門、福州,廣州、深圳分別作為環渤海港口群、長三角港口群、東南沿海港口群、珠三角港口群的發展主體,擁有較大港口物流市場份額與自然資源優勢,在港口物流網絡中起重要的中介作用;而西南沿海港口群整體發展水平較低,在網絡中的地位處于劣勢。
完善的港口基礎設施促進了物流網絡的業務與地理空間延伸。港口基礎設施是反映一個城市港口物流運輸能力的核心指標,良好的港口基礎設施不僅可為拓寬海外市場提供貿易硬件支撐,同時也有助于吸引港口物流企業的集聚,進而提升腹地城市吸引能力與網絡地位,加強與其他沿海城市間的物流網絡聯系。從核心網絡中7個城市的港口基礎設施條件看,上海、天津、寧波、大連和青島的港口基礎設施條件在中國沿海城市中名列前茅,深圳、廣州也處于偏上游水平,得天獨厚的基礎設施優勢推動這些城市港口物流業高質量發展。
信息化水平反映城市港口物流發展潛力。智慧化與自動化是港口物流未來的發展方向,而信息水平作為其發展的基礎,決定港口物流未來發展空間。同時,當今世界正處在信息化網絡時代,信息化水平影響城市與外部物流網絡聯系的緊密程度。相較而言,環渤海地區、長三角地區、東南沿海地區主要沿海城市的信息化發展水平更具有優勢,這為港口物流跨時空聯系提供了更有力的網絡支撐,進而推動城市間港口物流業務聯系。
港口物流企業總部分布對港口物流企業集聚與擴散發揮引力作用。物流企業總部通過輻射其他城市建立分支機構,成立其他地區的市場營銷和物流組織,促進其與總部城市進行業務往來;同時物流企業總部集聚程度較高的城市,其物流市場規模一般較為龐大,可吸引其他城市物流企業總部到當地發展分支機構,進而不斷壯大其物流企業整體規模實力。物流企業的大量聚集會促進城市物流的規模化、專業化、個性化,進一步擴大物流市場需求,進而反作用于城市企業總部的增設,形成良性循環。中國規模以上港口物流企業總部多集中在上海、深圳、天津、大連、青島、寧波6個城市,占據整體的65%,企業總部規模化發展帶動城市物流網絡的不斷壯大。
4 結論與討論
基于中國沿海港口物流企業總部—分支機構的相關數據,借鑒世界城市網絡方法與社會網絡理論,刻畫中國沿海港口物流網絡結構演化特征,并進一步分析其演化機制。得到的主要研究結論有:
1)2009—2019 年,中國沿海港口物流網絡結構趨于成熟,新城市節點的加入擴展了網絡地理空間,且縮短了城市間的平均距離,提升網絡城市間可達性;同時,網絡整體平均度值與集聚系數均有所提升,各城市間聯系程度顯著增強。但就整體網絡發育程度而言,整體網絡密度偏低,大多數城市仍處于弱連接狀態。
2)網絡聯系空間保持核心—邊緣結構,其中上海穩定保持核心聯系城市,輻射天津、大連、青島、寧波、深圳、廈門構成核心網絡,而邊緣城市主要通過連接核心城市加入網絡,且邊緣城市間互動性較弱;沿海港口物流網絡層級結構明顯,依據網絡中城市地位差異,呈現出核心—次核心—一般—邊緣4級圈層網狀聯系結構,且圈層間聯系強度隨圈層等級降低而逐漸減弱。其中,核心圈層由單核心(上海)向雙核心(上海、寧波)發展。
3)沿海港口物流網絡的發展受多種因素共同作用。其中,受沿海港口物流市場規模與港口物流企業總部規模的正向影響作用最大,這2個變量反映城市港口物流的市場發展空間與供給能力,且其差異化發展有助于港口物流網絡分工格局的形成,促進港口物流網絡協調發展;城市經濟發展水平與對外貿易環境的正向作用次之,城市經濟發展水平與外貿環境水平越高,城市的港口物流市場需求越大,這為其物流發展提供有力經濟發展環境;物流人力資源與產業結構對港口物流網絡的作用不明顯;港口基礎設施差異化發展不利于港口物流網絡的形成,推動基礎設施均衡化發展將是降低城市間港口同質競爭與合理分工的重要舉措;信息化水平的差異化發展不利于城市信息網絡的構建,在一定程度上阻礙各市港口物流業務的溝通與合作。
本文將網絡分析法和經濟學方法相融合,結合企業組織網絡理論、城市網絡理論,采用關系數據研究沿海港口物流組織網絡,相比較于單一方法、單一學科和屬性數據下的研究更能夠反映沿海港口物流組織網絡聯系的現實意義。但由于數據獲取困難,且港口物流企業沒有明確的定義與分類,本文并未將港口物流企業進行分類研究;同時,定性影響指標較少可能會導致對演化機制分析不全面。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可對港口物流企業進行分類研究,探究不同類型港口物流企業組織網絡演化過程,使研究結果更具有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