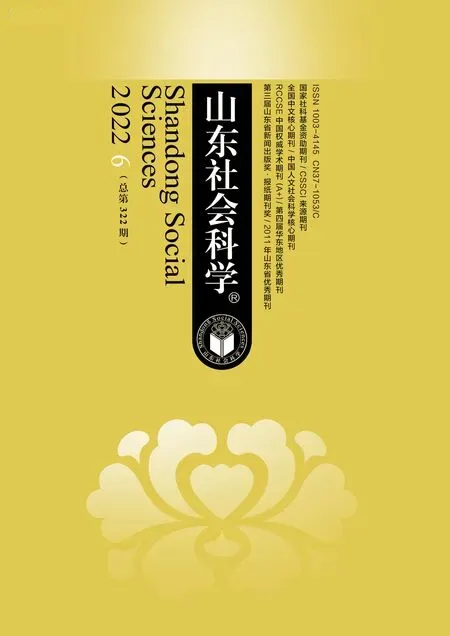元宇宙的時間政治
——生死之間的共在與共情
姜宇輝
(華東師范大學 哲學系,上海 200062)
未老先衰,這句話似乎特別適用于元宇宙這股熱潮如今面臨的困境和僵局。一個看似帶著靈感和期待的思潮卻在如此短暫的時間之內迅速從熱議熱炒的主題蛻變為談資和笑柄,確實令人大跌眼鏡。細數晚近以來的各種思潮,從后人類、思辨實在論,再到人類世和加速主義,幾乎沒有哪個如元宇宙這般曇花一現,倉促收場。即使如此,元宇宙也至少體現出壓過前浪的一個鮮明優勢,那就是它所具有的無可比擬的實操性。即使沒有人真的知道元宇宙到底是什么,但幾乎每個人都在煞有介事地談論元宇宙;而且更重要的是,人人都在鉚足勁頭制定著元宇宙的各種“實現方案”,很短的時間內出現了各種冠以元宇宙之名的虛虛實實的產業和“事業”。思想和觀念直接轉化為產能和產值,這確實是之前的任何一種思潮都從未做到的。人類世的幻想和加速主義的狂想自然不足以展現多少介入現實的力量,就拿與技術發展頗為切近的后人類主義來說,也多少或主動或被動地與現實保持著一個“間距”,既是反思的間距,又是行動的間距。
相比之下,元宇宙的迅速降溫乃至“退場”的一個關鍵的原因或許恰恰正在于間距的缺失,即太過貼近現實反而看不清現實,太過臨近未來反而被未來的不可測、不可控的力量裹挾而去。一種冷靜的反思,似乎總要在流變的現實之中找到一個相對穩定獨立的判斷的立場,或至少是一個足以進行清晰審視的觀測點。這正是我們這些以反思和判斷為業的哲學研究者理應進行的工作。單純地貶斥元宇宙的空洞和盲目并非明智之舉,目前更應該首先進行“回顧”,從元宇宙的泡沫甚至廢墟之中挽回一絲尚有價值的啟示和洞見。如何進行這樣的重審工作呢?比較與權衡仍然是一個基本的方法。元宇宙雖然像宇宙大爆炸一般驟然間降臨,但作為一股有內涵有特色的思潮,它必定、注定與后人類等之前的思潮存在著密切的關系,這個關系才是反思的起點。一方面,前面的各種思潮已然為元宇宙的出現做好了鋪墊;另一方面,元宇宙的誕生和降臨又確實展現出十足的斷裂和變革的極端形態。審視這些密切的關系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入手,但彼得·奧斯本所謂的“時間的政治(politics of time)”似乎最具有穿透力。“時間的政治是這樣的政治,它把社會實踐的各種時間結構當作它的變革性(或者維持性)意圖的特定對象。”實際上,無論“社會實踐”還是“社會思潮”皆是如此。要理解它們的廣泛深遠的影響力,時間性顯然是一個要點。是“維持現狀”、按部就班或者步步為營地向前行進,還是實施“變革”,更為激烈地在過去和未來之間制造斷裂,這顯然是甄別區分不同思潮的關鍵。那么,從時間政治的角度來看,元宇宙到底又展現出何種獨特而迥異的形態呢?
一、時間、精神與死亡
關于元宇宙的時間政治,初看起來幾乎極為明顯直白,那就是義無反顧地奔向未來。“元-(meta-)”這個前綴在古希臘語里有兩個密切相關的基本含義,即“之后(after)”與“超越(beyond)”。把這兩個意思合在一起用在元宇宙上真是頗為恰切:之前的各種潮流退卻、沒落“之后”,讓我們“超越”現有的世界,從零開始規劃暢想全新的宇宙。但若僅從這個未來性的角度看,元宇宙跟同樣以極端的姿態標榜未來性的加速主義又有何差異呢?至少有一個,那就是“超越性(beyond)”與“內在性(immanence)”之別。僅就羅賓·麥凱(Robin Mackay)和阿爾曼·阿瓦內森(Armen Avanessian)這兩位加速主義主將的宣言來看,加速主義的未來指向體現出兩個鮮明特征:首先是對現實持激烈批判的立場,試圖徹底顛覆資本主義秩序,將其“連根拔起(uprooting)”。但其次,他們的此種批判和顛覆又并非基于一個外部的視角,而是要更為徹底深入地回歸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加速其內在的種種錯綜復雜的力量,進而將其推向崩潰乃至毀滅的邊緣。元宇宙則恰恰相反,它雖然也強調加速發展現有的各種(尤其是)技術的力量,但并不認為此種加速最終會導向解體和毀滅,正相反,元宇宙是加速所實現的終極完美的境界。加速不是破壞而是完滿,未來不是黑洞和深淵而是天國和樂土。就未來性這個時間政治而言,元宇宙不僅與加速主義針鋒相對,而且更是對后者之噩夢和噩運的終極救贖。元宇宙既在加速主義“之后”,又從根本上“超越”了加速主義。它絕對夠資格被喚作“元-”的起點。
從這個角度來看,元宇宙似乎更為切近從后人類到人類世的時間性轉向。后人類思潮興起之初,“后-”這個前綴確實還充斥著各種復雜矛盾的含義,連續、發展、超越、斷裂等等時間樣態都悖論性地糾纏在一起。但到了接近尾聲的時候,其時間性的含義就更為明晰和精確了。羅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在《后人類》中有一個經典概括:“我認為,后人類境況的公分母就是承認生命物質本身是有活力的、自創性的而又非自然主義的結構。自然—文化的這種連續統一性是我研究后人類理論的出發點。”可見,至少在人類的未來命運與歸宿這個要點上,后人類與元宇宙是頗為契合的。它們都沒有像加速主義那樣將未來構想為失控的深淵,而是將未來暢想為萬物融合的“完滿”境地。當然,這里的完滿打了引號,強調其并非意味著存在等級的巔峰,而是趨向于萬物密切互聯所構成的那種終極的“共同體”。這樣的共同體當然也隱藏著(或昭示著)巨大的危險,比如它極有可能墮入無序的熵增甚至熱寂式的毀滅,同樣,它亦有可能以同質化的網絡抹殺了不同個體之間的差異性。或許正因為如此,布拉伊多蒂才會將后人類所暢想的“連續統一性”的基本紐帶和介質設定為“生命”,這里的“生命”不是人類特有的生命,而是萬物共有的生命。充滿生命的共同體網絡才能真正有效激活每個動元(actant)的個性和活力,而不至于最終陷入熱寂甚至死寂。作為后人類發展的最有創意和代表性的后續形態,哈拉維的“克蘇魯紀(Chthulucene)”亦是沿著相近的方向進行了更為徹底而極端的推進。在《生于憂患》()一書的開篇,哈拉維就明確指出,所謂的克蘇魯紀不僅是萬物之間的共生、共在、共創(co-becoming),而且是各種時空維度之間的交織互滲。這個古希臘語詞根早已明示了此點,它不僅意味著從過去綿延至未來的生命創造,更有另外一個頗為關鍵的時間性維度,那就是“有厚度的,生生不息的當下/在場(thick, ongoing presence)”。當下是有厚度的,因為它是連接著過去和未來的中間環節,而不是斷裂的鴻溝和深淵;當下是生生不息的,因為它的連接和創造時刻都在進行,不可遏制,變化不已。
但正是在連續性和當下性這兩個要點上,元宇宙體現出與后人類和人類紀的根本差異。元宇宙雖然也是萬物的徹底連接和終極融合,但它用以實現此種連接和融合的基本介質并非生命——無論是人類的生命還是萬物的“普遍生命()”,而是數據(data)。說到底,離元宇宙最近的一次技術變革正是大數據,因此我們有理由將其視作引燃元宇宙構想、玄想和狂想的最直接的導火索。畢竟虛擬現實、電子游戲、VR等都已然經歷了不短的發展歷程,但為何元宇宙偏偏在2021年這個時間節點上驟然出現呢?首先當然是各種前沿技術越來越成熟,而且逐步匯合在一起形成勾連的合力。其次更重要的是,幾乎唯有大數據這個晚近以來最炙手可熱的技術形態才能為人類提供一個后克蘇魯紀的“超越”動力和前提,那正是“世間萬物的數據化”。從生命向數據的轉化正是元宇宙得以超越后人類的關鍵契機,也正是憑著“讓數據主宰一切”這個終極法器,元宇宙才真正史無前例地徹底改變了人類歷史的時間性模式。克蘇魯紀所暢想和憧憬的“過去、當下、未來”的“完全交織”,在大數據時代早已一步步變成現實。更為致命的是,從這個前提出發,元宇宙堪稱有史以來第一次近乎完美地實現了對未來的“預制(preemption)”。不是預測,而是預制。預測還是向著多種可能性敞開,但預制就根本不同了,預制是通過先行“制定”未來而實現對于過去和當下的越來越深廣和牢固的掌控:“對于善于運用科技解讀未來的人來說,我們的未來不再是只字未書的畫布,而是似乎已經著上了淡淡的墨痕。”這樣的說法實在太過謙遜了!元宇宙遠不只是滿足于勾勒隱約模糊的墨痕,正相反,它是極為清晰的未來圖景,清晰到可以按部就班地制定前進的規劃,清晰到足以有滿滿的自信和底氣說上一句:未來已來!
由此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元宇宙確實是連接和融合,甚至是終極的“連續統一性”,當然那只是在至大無外的元宇宙的內部。對于之前的人類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來說,它就是最為深刻和截然的斷裂。《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全書的結語援引了莎翁的名言對大數據時代本質特征的揭示實在是入木三分:“凡是過去,皆為序曲(What's past is prologue)。” (《暴風雨》)從智人到后人類,人類的歷史始終以生命為基質展開演化的歷程,但如今則“俱往矣”,因為元宇宙就是一個全新的數據宇宙的真正起點。元宇宙和人類/后人類之間就是徹底的、終極的斷裂,是新舊世界間的更迭,是兩個宇宙間的變革。由此看來,如果說元宇宙的時間政治是以當下性為關鍵的,那么它與克蘇魯紀的當下性至少存在著以下兩個根本差異:一方面,它不是充實的、有厚度的,而恰恰是空洞的、斷裂的;另一方面,在元宇宙的那個“未來正在發生”的當下之中,充溢的并非生生不息的生命創造,而是一次次預制的數據循環的空洞回聲。在元宇宙預制的未來面前,一切皆已老去,甚至尚未發生之事亦已然化作歷史。當下只是從未來返歸過去的一次次空洞循環之中的那個無比空洞的點而已,它既沒有厚度,也沒有廣度;既沒有內容,更沒有意義。
這樣看來,作為終極的數字共同體的元宇宙與之前的作為生命共同體的人類世界,這二者之間的斷裂關系近乎一種“生離死別”。從生命向數字的轉化過程,也是舊人類死亡、新人類誕生的過程。顯然這個過程不可能是連續的,不是人類生命的下一個階段的進化(甚或突變),只能是否定性的,它徹底否定的是生命這個人類乃至萬物存在的基質和基礎。這樣一種否定性的轉化,直接讓人聯想到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第六章開篇所提及的“兩個相互對立”的“倫理實體”即家庭和國家的辯證運動過程,而二者之間的至關重要的環節正是死亡:“否定的本質于是表明自己是共同體的真正權力,是共同體賴以保存自身的力量。”正是經由死亡這個關鍵環節,每一個個體才得以真正從自然的生命共同體(家庭、家族、世系)的一員轉化和提升為倫理和政治共同體(民族、國家、政府)的一員。支配這兩個共同體的法則分別是“神的規律和人的規律”,而推動從家庭到國家轉化的根本動力恰恰是精神及其內在固有的返歸自身、認識和理解自身的持續而堅定的意志。
細讀黑格爾的這段文本會發現不同意味的死亡貫穿起這個轉化的過程:人作為自然存在即人作為對自身無所意識和反思的自然存在物,全然受自然法則的支配而“懵懵懂懂”但又俯首帖耳地走過整個從生到死的歷程。但人并非只是自然界中的“一個純粹的物”,當他進入家庭之后,仍然要受到“神圣”的自然法則的掌控,但卻已經開始自覺地“作為一個意識去行動”了。家庭與自然之間的最鮮明最直接的對立乃至對抗是死亡。家人會死去,一代代的人薪火相傳,前赴后繼,延續著生命的血脈,但我們對待家人之死的態度并不是將其視作一個單純的、普遍的自然物,相反我們會秉承傳統,按照傳承下來的儀式讓死者入土為安,而且從此不斷地對他們表達追思和緬懷。“家庭通過這種方式使死者成為共同體的一員,而共同體則牢牢地控制著個別質料的腐蝕力和各種低級生物,防止它們毫無忌憚地毀滅死者。”家庭已經開始從自然的共同體向倫理的共同體邁進,由此亦喚醒了每個家人的精神力量,他們不再只是盲目的自然存在,而是一步步成為覺醒的個體,有責任,有擔當。而實現這個覺醒的關鍵步驟恰恰是在家庭中才得以進行和發生的面向死者甚至“共死者同在”的葬儀。明白了家庭這個從自然向國家轉化、從神律向人律覺醒的中間環節的關鍵作用,隨后的另一種意義上的死亡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即已然成為民族和國家一員的公民主動地為人民赴死,為祖國捐軀,由此更為徹底地否定、超越了自身的自然存在,向著自由的精神境界躍升:“即從死亡上升到光天化日的現實性,上升到一個自覺的實存。”
黑格爾這一番透徹精辟的論證,恰好可以作為我們深刻理解元宇宙的前提。如果說元宇宙之前的人類歷史和世界的進化可以在黑格爾的意義上被簡化概括為從自然到家庭再到國家的精神覺醒的歷程,而其中每一次轉化的關鍵環節都是死亡,那么元宇宙所標志的恰恰就是這整個精神歷程的最終完結,以及下一個全新階段的真正起點,是從自然共同體,經歷精神共同體,最終進入數字共同體的關鍵“界檻”。既然如此,元宇宙作為轉化的界檻的作用理應同樣體現在死亡這個關鍵環節之中。甚至不妨說,元宇宙就是人類的第四次死亡。不理解這次死亡的深刻意味,就根本無法領悟元宇宙的真諦。那就讓我們從死亡這個要點深入元宇宙。
二、“共死者同在”:元宇宙的時間政治
死亡作為轉化和過渡的界檻必然帶有所有界檻都注定無法逃避的雙重性和含混性,即它始終同時既是連續又是斷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我們固然可以在黑格爾辯證法的意義上大而化之地談論否定之否定的揚棄,但其實更應該深入到這個含混的中間地帶,揭示出其中的種種復雜糾纏的關系。此種復雜性在黑格爾自己的文本中亦有鮮明的體現,尤其體現在《安提戈涅》這個持續引發聚訟紛爭的古老難題上。
概括說來,安提戈涅的最核心難題正如黑格爾所言,是家庭和國家這兩個倫理實體之間的沖突和矛盾的激化,只不過在索福克勒斯的原初腳本中,最終受到懲罰的是觸犯神律的克瑞昂,但若根據上述《精神現象學》的相關闡釋,我們顯然更應該理性地、清醒地站在克瑞昂這一邊,因為他畢竟代表了精神發展的必然性的趨勢和規律。然而問題并非如此簡單,誠如黑格爾隨后在《法哲學原理》中所清醒意識到的,克瑞昂即便確實代表了、體現了從神律到人律、從家庭到國家的轉化過程,但他自身卻對這個過程全無反思,毫無意識,只是盲目地、偏執地炫示國家的權威乃至暴力,進而突顯出國家和家庭之間的矛盾和對立。他根本沒有看清楚死者才是生者的前提,“安葬家人”的儀式才是通往“公民意識”的本質性環節。唯有經由死亡和葬儀這個否定性環節,才能實現從家庭向國家的肯定性轉化。誠如漢斯·魯因(Hans Ruin)的精辟概括:“人類不只是與生者共存,還與死者共在。”
但在魯因看來,黑格爾雖然有力地反駁了克瑞昂的盲目和自大,但他自己對于死者顯然還是缺乏“足夠”的尊重。他最終還是只將死亡視作精神發展運動“之中”的一個過渡環節,將死者及葬儀作為生者共同體“內部”的一個構成環節。但實際上,如魯因所敏銳指出的,“生死之間的‘幽靈(spectral)’地帶”本就是幽深曲折的,難以清晰化、簡化為單向度的精神運動的辯證規律。說到底,死者絕不是一個完全消極被動的存在,只能毫無抵抗、逆來順受地聽任生者對他們的安置和擺布,接受生者賦予他們的一切秩序和意義。恰恰相反,死者與生者理應是“相互承認(mutual commitment)”的。相互承認?這難道不是異想天開的臆斷嗎?死者即便有權力要求自己被承認,他也根本沒有任何能力去伸張和爭取這樣的主動地位吧?對于生者對他的不公正處置死者能起而抗爭嗎?死者能夠憤而“起身”捍衛自己的權力嗎?哈姆雷特的亡父確實糾纏著自己的兒子,一遍遍地催促他去“復仇(Revenge!)”,但最終做出決斷、了結一切的不還是那個活在世間的丹麥王子嗎?克瑞昂因為自己對死者的不敬而受到了懲罰,但最終安葬哥哥呂涅刻斯的不還是那個掙扎著活下去的安提戈涅嗎?即使我們不接受黑格爾式的絕對精神的運動,但仍然找不到足夠充分的理由去肯定死者的那種積極的、能動的作用,或者說得更徹底一些,去真正肯定死者自身的主體性地位。如果死者無法真正成為主體,那他又如何可能獲得本體論上的平等地位,進而與我們這些作為主體的生者共在呢?對此海德格爾說得很直白,“他人之死”充其量只是一個契機,它最終逼出的還是每個此在對于“向來我屬性”的領悟。一句話,能夠作為主體主動承擔責任的最終只是生者。
正因為如此,魯因的《共死者同在》一書雖然頗有篳路藍縷之功,但最終還是搖擺在生死之間的幽靈地帶難以做出決斷。他時而強調死者的那種(近乎列維納斯意義上的)絕對分離和超越的他者地位,但他的那些“關懷死者”進而與死者“共享”乃至“共建”同一個世界的諸多論述,其實最終還是意在如黑格爾那般“跨越界檻(across the threshold)”,進而“修復裂痕”(repair what is broken)而已,雖然他關注的不再是精神而是肉體,不再是精神的普遍運動而是葬禮儀式的具體細節。這也是為何他還是更偏愛將死者歸結為“幽靈”——雖然已死,但還是帶著怨念游蕩在塵世、糾纏著生者的殘存形態(survival)。但魯因所陷入的僵局并非只源于他自己的理論架構,也絕非他憑一己之力所能解決的。事實上,這或許是前元宇宙的人類世界的最根本的困境,或者更準確地說,這是難以超越的困境。通觀人類歷史,真正的“共死者同在”幾乎是難以實現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三個方面:首先,從事實層面來說,死亡永遠只是也只能是人類共同體“內部”發生的事情。死去的只是一個個人,逝去的只是一代代人,但人類的整體從未徹底瀕臨滅頂之災。簡言之,人類的總體從未如每一個個體那般有機會直面死亡這個終極大限。其次,從本體的層面上來解釋,這也是因為人類歷史無論怎樣充滿變故和曲折,但貫穿其中的根本力量仍然是生命(即便生命經過了諸多“超-”“后-”的變異),根本法則仍然是精神(無論精神經歷過怎樣的苦痛和挫折)。作為人類生存的本體,生命及其精神從未真正遭遇過徹底否定自身的他者和差異的力量。第三,從體驗的層次上來說,雖然世界各大宗教、各種文獻記載都曾對瀕死體驗甚至死后世界進行過種種或紀實或玄想的描繪,但真正對死亡有過切身體驗的人絕對是鳳毛麟角。上述三重限制幾乎是人類無法超越的有限性的終極邊界。既然如此,在人類世界之中,無論經由怎樣的途徑,無論是思辨還是踐行,幾乎都難以實現與死者的平等共在,遑論讓死者成為被承認的主體。在元宇宙誕生之前, “共死者同在” 充其量只能是一個美好的愿景,一句空洞的口號而已。
但元宇宙的誕生或降臨全然突破了這三重邊界。首先,它是全部人類從現實世界向虛擬世界的徹底的“大遷徙(migration)”,因而人類第一次面臨著整體滅絕的絕境。其次,它是從生命世界向數字宇宙的徹底轉變,因而人類的生命第一次遭遇到完全否定的力量。第三,今天的數字虛擬技術已經完全可以在體驗的層次上讓絕大多數人“真實”、真切地體驗到自己的瀕死的全過程。我們置身其中的這幾代人,幾乎無時無刻不在親身經歷著新的數字化身對舊的肉體生命的侵蝕、取代、改造乃至抹除。我們每個人都是瀕死者,而且我們每個人都心知肚明,或至少感同身受。也正是出于這三重逆轉,如今可以非常確鑿地肯定,“共死者同在”這個命題唯有在元宇宙之中才能真正實現。元宇宙之“元-”正在于它作為新舊人類轉換的生死交接的“間隙(interval)”。至此,我們亦得以對上文論述的元宇宙的時間政治的兩個基本特征進行重要的引申乃至修正:首先,元宇宙確實是人類世界“之后”的終極“超越”,這個超越也確實展現出極端的否定和斷裂的特征,但在這個間隙與鴻溝之處并非無物存在、無事發生。正相反,從事實、本體和體驗這三個層次來看,死亡就是在這個間隙所發生的最為重大的事件。在人類世和元宇宙的更迭之際、之處所發生的,正是人類所親歷的自身的死亡和生命的終結。正是因為如此,元宇宙的時間政治首先是死亡的政治(necropolitics)。
其次,由是觀之,元宇宙與加速主義、后人類等晚近思潮在時間性上的根本差異,就并非僅在于“預制未來”這一點了。或者更恰切地說,當元宇宙以預制的方式掌控過去和當下之時,斷然會在新舊人類轉換的間隙遭遇復雜而又棘手的抵抗。殘存的生命肯定不甘心束手就擒,一定會進行各種難以預制的頑抗。元宇宙的起點正是瀕死、趨死和赴死,但天底下還沒有什么比死亡更難以預測、預防和預制的。在這個死亡的間隙,元宇宙的預制注定不會一帆風順,也斷然不會所向披靡。在斷裂的深淵回響著死亡之聲,在空洞的循環之中交織著趨死之力。死亡這個終極含混的事件,驟然間擾亂了元宇宙那一派完美和諧的畫面。
死亡的這種含混莫辨的中間形態,早已有眾多哲學家給出過提示和闡釋。我們不妨還是回到《安提戈涅》這個老而彌新的謎團。晚近以來很多人都對《精神現象學》中的經典分析提出過尖銳質疑,比如朱迪斯·巴特勒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其實在神律和人律之間本不存在黑格爾所說的那種“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首先,從“語言體系”上來說,安提戈涅和克瑞昂就是“交叉聯系在一起難以區分”的;其次,更重要的是,安提戈涅的此種在象征體系之內的含混位置,并非僅僅涉及女性的身份和地位,完全可以且理應有一個更為普泛的追問,那正是“對于生死之間的這個獨特的位置,對于在生死的搖擺不定的邊界上發聲,我們應當怎樣理解呢?”對于夾在神律和人律之間痛苦掙扎的安提戈涅來說,這是一個根本的難題;而對于夾在瀕死的人類世界和新生的元宇宙之間的我們,這同樣是一個刻骨銘心的追問。死亡本不是一個瞬間發生的事件,也沒有一個明確劃分的邊界,更不是一個單向演變的過程。在這個獨特的位置和搖擺不定的邊界之處,有眾多錯綜復雜的力量交織對峙對抗,有不斷撕開又彌合的創口在一次次加深著我們對于生死的深切體驗。這個含混性才是思索元宇宙的時間政治的最為關鍵的要點。
對這個要點,幾乎沒有人說得比英年早逝的羅伯特·赫爾茨(Robert Hertz)更為凝練而透徹。在《死亡與右手》這本堪稱里程碑式的論著中,他從連續和斷裂、肯定和否定的交織糾纏的雙重性入手,深刻解析了死亡和葬儀的含混性,進而觸及“感染”之危險這個極具啟示性的主題。那就不妨以分離、整合、感染這三個主題對其文本進行大致概括。
首先,死亡作為“分離(separation)”當然是秉承了其恩師涂爾干的基本立場。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爾干明確指出:“宗教現象的真實特征仍然是:它們經常將已知和可知的整個宇宙一分為二,分為無所不包、相互排斥的兩大類別。”這也是為何以確定分離、劃定界限為要旨的“禁忌”會成為他的宗教社會學的核心主題。但如果真是如此,那我們想必會隨即引發出一個很自然的追問:還有什么比死亡更能夠突顯此種分離的現象能夠在“凡俗的與神圣的”這兩界之間劃定禁忌之邊界?如果說宗教確如涂爾干所說可以概括為禁忌、信仰和儀式的三位一體,那么死亡的禁忌與葬禮的儀式恰恰是體現、鞏固、維系核心信仰的最重要基礎。但令人費解的是,涂爾干全書對死亡和葬儀幾乎沒有論述,僅在接近尾聲的第五章蜻蜓點水般地提了一下“哀悼儀式”。赫爾茨的《死亡與右手》恰恰彌補了涂爾干的這個本不應該出現的重大疏漏。
正如涂爾干將禁忌區分為消極和積極、分離和接觸兩個方面,赫爾茨同樣也從分離和“整合”這密不可分的兩個方面來破解含混莫辨的死亡之謎。死亡當然首先是分離和排斥(exclusion)。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無論是出于何種自身或者社會的原因,當一個人死去時,他無疑就是從根本上離開了我們這些“生者”,進入“死者”的行列。他們不再是“這個”世界的一員,而是進入“那個”世界之中。我們與他們、生者與死者之間的維系也不再遵循世俗的法則,而是必須履行另一套儀式和程序。對于這個分離的終極禁忌,還必須進行兩個方面的深入的理解:一方面,它不是“瞬間完成的”,而總是體現、展開為一個長短不一的“持續過程(a lasting procedure)”,也就是說,在“死亡和最終的葬儀之間”總是存在著一段“過渡(intermediary)”或“間隙(interval)”的時間。而且,這在不同的文明和民族那里都是普遍的現象。這也說明死確實是分離之禁忌,但這個分離并非一個點,而總是拉伸為一個線段,或更準確地說是復雜力量交織滲透其中的“場域(field)”。最終,死者注定要徹底、完全地離開我們,但在這之前,他們還是要在“這個”世界之中與生者“共在”一段寶貴而又意味深長的時間。在這個時間段之中,我們令死者的遺體“安葬”(burial),令他們的靈魂“安息”(peace),并以此來給我們所有這些生者帶來“安慰”。由此看來,死亡并非僅僅是分離,它也是另一種“新的整合(a new integration)即一次新生”。死看似在新舊兩個世界之間制造了截然的分離和斷裂,但它同時亦以極為微妙和奧妙的方式在二者之間穿針引線。另一方面,分離也不是單邊和單向度的,并非僅僅是生者對于死者主動作出的安置與應對。正相反,誠如魯因所言,死者也同樣有他們的主動的“工作”要做。死者的此種主動作用亦展現出善惡分明的兩個方面。從善的角度看,與我們分離的死者進入的是一個漫長而又光榮的傳統,打開的是另一個神圣而又光輝的世界。他們的死既有意味,又有價值,他為我們這些生者帶來安慰、祈福乃至拯救。反過來從惡的方面看就截然不同,死者亦完全可能進入一個黑暗混沌的世界,并由此將那些邪惡的毀滅性力量帶到人間,在生者之間、在塵世之中進行可怕的散播和“感染”。正因為如此,生死之間的那個葬儀的時間遠非只是一派和諧溫暖的氛圍,相反它不啻為一個善惡交織、正邪對抗、明暗互滲的紛爭之地。親近死者,表達哀悼,本來就是一件充滿危險的事情。
三、《第二人生》:元宇宙中的死亡禁忌
赫爾茨的這一番鞭辟入里的闡釋對于我們深入理解元宇宙的時間政治具有深刻的啟示。作為人類的第四次死亡,元宇宙同樣展現出分離之禁忌、整合之儀式和感染之危險三個重要的方面。從分離的角度看,它劃定的是新舊兩個世界之間的巨大的、難以彌合的鴻溝。從整合的角度看,它又在技術、媒介和身體等基礎層次上推進、維系著從人類到后人類再到數字人類的過渡和轉化。而從感染的角度看,無論是將其視作禁忌還是過渡,否定還是肯定,元宇宙中的死亡和葬儀都絕非是一件簡單明晰的事件,而始終是交織著錯綜復雜力量之間的角逐和角斗。下面就讓我們帶著前文已經闡釋的理論要點,進入到元宇宙的具體細節之處,以人類學的方式來展現上述三個方面之間的分合異同。空談無益,下面不妨聚焦于《第二人生》這部劃時代的經典來進行深入思考。
選擇《第二人生》主要基于三個理由:首先,既然當下圍繞元宇宙展開的各種或嚴肅或戲謔的討論已然愈發空洞泛濫,那么回到其萌發之處,從最初的文本和作品之中去挖掘潛存的含義和可能性,就不失為一條有益的補救路徑。其次,元宇宙的源頭是多樣而復雜的,但如今大致能夠達成的一點共識就是,《雪崩》這部小說和《第二人生》這部游戲可以被視作兩個最為重要的發端。但是為何一定要選擇《第二人生》而非內涵更為豐富、意境更為恢宏的《雪崩》作為入口呢?這無非是因為《雪崩》至多只是初期的想象,但無論完美與否,《第二人生》才是元宇宙這個概念在橫空出世之后的第一次落地的實現形態。說得極端一些,與今天那些空穴來風的熱議相比,《第二人生》早在將近二十年前就已經在虛擬世界之中前無古人地第一次勾畫出了元宇宙的雛形。最后,從藝術性和思想性的角度看,《第二人生》雖無法與《雪崩》相提并論,但它至少有一個明顯高于后者的優勢,那就是它才是真正的集體的創造,是人與人之間的共在。《雪崩》說到底只是作家一個人的構想,即便怎樣栩栩如生,最終也還是紙上談兵。但《第二人生》顯然不同,它是鮮活的人生,而且是其中所有有著七情六欲的鮮活個體共同譜寫的交響詩篇。更重要的是,無論《雪崩》的文本后來怎樣一遍遍地被玩味和探討,但它的整體文本架構和敘事情節的主線是無法改動的。《第二人生》則相反,它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從第一個虛擬公民入住開始,就在不停地生長和變化,或者說,它的世界每時每刻都充滿著前所未知的實驗。這的確是一個游戲,但它本質上也是“另一場”活生生的人生,因此它也跟現實人生一樣,是可能性優先于現實性的。或許正是因為這一點,近年來涌現出不少對《第二人生》描繪的虛擬世界進行人類學考察的作品,下文重點參考的《在第二人生中成長》()就是其中的優秀代表。當然,關于《第二人生》實在有太多的主題可以展開,還是讓我們回歸死亡和葬儀這個本文聚焦的要點吧!
誠如涂爾干和赫爾茨所說,死亡首先涉及分離的禁忌。作為禁忌,死亡又展現出哪些特征呢?涂爾干的界定最為清晰全面。首先,它強調被分離和隔絕的兩界(神圣與凡俗、生與死)之間的“不相容”性,即各種儀式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恪守一條不容僭越和侵犯的邊界。其次,禁忌與褻瀆始終是一體之兩面,劃定邊界與僭越邊界也幾乎總是相生相伴,因此,一旦真的有人膽敢觸犯禁忌,那就必須從肉體和精神上施加雙重懲罰。肉體上會遭受各種“紊亂”,而精神上則更會遭到眾人的譴責和唾棄。第三,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確立神圣領域的至高地位及其對每個個體所施加的“絕對命令”。這三個要點在《第二人生》之中體現得同樣明顯,但又皆發生了極為微妙的轉變。從元宇宙的角度來看,《第二人生》同樣體現出“之后”和“超越”這兩個存在差異但又密切相關的根本維度。一方面,它是人類“之后”,因為它與人類之間肯定存在著千絲萬縷、剪不斷理還亂的傳承關系;而另一方面,它又是人類的“超越”,因此斷然會以一種全新的形態展現出從未有過的“新人”的面貌。死亡禁忌顯然首先凸顯出“超越”這個維度。《第二人生》不只是第一人生[所謂“真實人生(real life)”]的衍生、鏡像或倒影,正相反,它不僅有著自身的獨立性和完整性,而且展現出全面超越第一人生的無可比擬的優越性。因此“第二”更體現出“元-”的如下含義:名曰第二人生,但其實它才真正體現了人生的真義,它才是值得過的人生,它才是人生的真正起點。不妨借用《存在與時間》中的那個經典說法將第二人生稱作“本真的人生”,由此與作為“真實的人生”的第一人生形成反差和對照。本真意味著覺醒之后的人生是不再受到各種現實束縛的人生,由此真正回歸自身本質的人生。由此說來,將《第二人生》在海德格爾的意義上界定為“本真”似乎也并不為過。
然而,第二人生的本真性至少有一個重要特征不符合《存在與時間》中的基本界定,那就是對死亡的輕視和蔑視。它用以實現超越和籌劃的動力從來不是、根本不是所謂“向死而生”,而恰恰是將第二人生中的“生”與第一人生中的“死”徹底分離。之所以要進入第二人生去自由逍遙,正是為了從根本上跳出第一人生中的可朽性和有限性的牢籠,從而以更為徹底的方式去實現人生的可能性。如此看來,如果說在《第二人生》中死亡仍然是一種禁忌,那么它的信念和儀式都和之前的第一人生有著根本差異。在第一人生中,死亡的禁忌主要體現在生者對于死者的敬畏,前提是死后的世界是神秘莫測的,既可能是極樂的天國,亦可能是邪惡的地獄。但無論怎樣,人類始終是從生者的主體性視角出發去揣測死者。但《第二人生》則相反,玩家們已經在人類“之后”的世界了,已經進入永生而無死的境界了,因此,作為從元宇宙回望人類的“死者”,他們才是真正的主體,他們才是能動力量的主導。這些要點甚至已經作為基本信條明確寫進了《第二人生》的手冊之中。在McGraw-Hill Osborne Media公司出版的《如何在〈第二人生〉中做一切事情》()這部權威手冊之中,根本沒有任何關于死亡、哀悼、葬禮的操作指南,因而這本書的標題可以更為恰當地被改寫為“關于《第二人生》的一切,但除了死亡”。
之所以如此,正是因為在元宇宙中談論死亡是無意義的,體驗死亡是不可能的,甚至連思考死亡都是一件荒唐的事情。遍覽整部手冊,“死亡” 僅僅出現了很少的幾次[“葬禮(funeral)”甚至一次也沒出現過],但已經頗能展現上述特征了。第一處是開篇第一章第一段話:“一個全新的身體。不分男女。無病無痛,亦無死(No illness, pain, or death)。飛吧。這聽起來酷似《圣經》里對天堂的界定。”這里對《圣經》和天堂的直接指涉無疑凸顯了分離的鴻溝和隔離的邊界。這段話里反反復復出現的“新”“無”“飛”直白地將元宇宙的“超越性”展現在所有玩家面前:如今,我們所有人都已經是站在至高無上的頂峰上俯視陳舊過時的人類生活方式,這高下之間的分別自然也就讓人類身上揮之不去的各種有限性“頑疾”(生老病死)變成了無關緊要、無關痛癢的表面現象。死亡不再是觸動每一個生者的至深體驗,相反,它在被無限“推遠”的同時變得越來越若即若離,甚至若有若無。將人面臨的最深重的恐懼焦慮驅趕到一個安全的距離之外,這恰恰是禁忌儀式的一個功效。手冊中提及死亡的下一個“命題”是,“給所有新手的一個結論:千萬別擔心有刺兒頭(griefers)來推搡你,把你關進籠子,甚至‘殺死’你。在第二人生之中,沒什么徹頭徹尾的壞事(permanently bad)會發生在你身上,比如死亡”。你被推進溝里,還可以再爬出來。你受傷了,還可以吃藥補血。你生病了,還可以去找女巫施魔法來療治。說到底,哪怕你“真的”一命嗚呼了,那也沒什么大不了的,無非就是從“存盤點”再重新開始一遍而已。那么在第二人生中什么叫作“真正”死去?或者,元宇宙中的死亡到底意味著什么?無非就是AFK[暫時離開鍵盤(away from keyboard)]這個通行的術語。在這里死亡沒什么大不了的,就是游戲里面的一步操作而已。我暫時離開了,但我還可以再回來,我總可以再回來,更關鍵的是,我心心念念的總還是想再回來,因為那是一片無生無死、無病無災的完美樂土。一旦把死亡這個第一人生中的可怕惡魔遠遠地驅趕到安全距離之外,元宇宙就會變成一個自洽而圓滿的終極天堂。它是一個全新世界的起點,它是全新人類的搖籃,它才是我們所有人的最終歸宿。
然而,元宇宙天國中的生活看起來并非幸福完滿,因為誠如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一次次警示我們的,任何的分離都不可能是徹底的,任何的隔離都已經將僭越和褻瀆的可能性深深嵌進自己操作的內部。死亡或許正是元宇宙中最難以清除、根除的一種僭越體驗。因此,必然要動用各種極端的手法來懲戒“屢禁不止”的僭越行為。手冊中的第三個死亡命題就已然透露出這方面的隱隱不安和焦慮。“還有所謂的人為傷害(damage-enabled),也即你可能被迫遵守規則,由此也會非自愿地(involuntary)遭受‘死亡’體驗,比如先被射殺,然后被遣返回你的家。”死亡即使不再是每個人本己的可能性的極限,但仍然劃定了一個人為的邊界,那正是規則施加的邊界。當人為制造的死亡驟然間降臨在你身上的時候,它只是在提醒你,那個禁忌的邊界是不能觸犯的。你觸犯了,就要遭受懲罰,即使不能真正用“徹頭徹尾的壞事”來折磨你的肉身,但仍然可以在涂爾干的意義上從群體精神的角度對你進行詛咒和排斥。你不好好玩,不認真玩,不遵守規則地玩,就會被“強制去死”,被暫時剝奪玩的時間和權利,甚至被強制清零,抹除了你之前在第二人生中辛苦打拼得來的一切“績效”。這很可怕。這樣的死雖然發生在虛擬世界中,只是游戲中的一步操作,但它觸及每一個玩家的深刻度似乎不遜于第一人生中的真實死亡。
但即使虛擬之死可以達到無以復加的嚴苛,施加變本加厲的苦痛,但它同樣無法根除死亡式的僭越行為,只不過元宇宙中的僭越往往呈現出與第一人生中截然相反的情形。第一人生中的死亡是生者向著未來的終極邊界的投射和籌劃,而元宇宙中的死亡則正相反,它呈現出兩種形態:一是局部的、臨時的死亡,這并不嚴重,只是小打小鬧的AFK;二是近乎持久的、全局性的死亡,這很嚴重,因為你觸碰到規則的終極邊界和底線,你喪失了所有既有的身份和成就。這第二種死亡不妨稱為元宇宙中的“真實死亡”,它體現出外部性、強制性和必然性這三個根本特征。首先,它是從外部由規則施加的,而不是玩家主動承擔起來的。其次,它是強制性的,即沒有其他的可能性,甚至也不存在協商和斡旋的余地。你不能問“為什么要這么玩?我為什么要遵守規則?”你要做的是也只能是遵守規則而已。你要么好好玩下去,要么被強制清零,被迫去死。第三,由此它就是終極的必然性(涂爾干所謂“絕對命令”),它是元宇宙中的每一個玩家和居民無法掙脫和逃避的終極命運。它即使早已不是此在的向來我屬性,但仍然可以反過來被界定為玩家的向來“非自愿性”。當強制死亡的懲罰性禁忌出乎意外但又如期而至地降臨在玩家身上時,相信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會涌現出這樣一種真切深切的體驗:畢竟,我已經“被拋進”元宇宙之中了。手冊中關于死亡的第四個命題說得是如此觸目驚心,“第二人生會以各種方式融于真實生活之中。…… 雖然你不會在第二人生中真的面對死亡,但你非常有可能要直面一個稅吏(a tax man)”。這里的潛臺詞無非是,元宇宙確實是一個徹底超越了人類有限性的極樂天堂,但這個天堂是有規則的,它的規則是不容觸犯的,一旦觸犯就要遭受懲罰。你不再會死,但你必須納稅。你不納稅就不再是合法公民,你不是公民就沒有資格再生存在元宇宙之中。但你不在元宇宙中,又能到哪里去呢?第二人生早已全面入侵、吞噬了第一人生。如今,元宇宙已然搖身變成“元人生”,而你拖著肉身在呼吸和行走的那個物理宇宙早已蛻變為黯淡的背景和飄忽的倒影。
四、結語:語音(voice)——共情作為“感染力”
誠如赫爾茨所說,死亡這個可怕之物哪怕被封禁在重重禁忌之中,也仍然會爆發出難以徹底克服的感染力量。只不過,它不再像第一人生中那般或是來自外部的威脅(地獄、冥府),或是來自內心的焦慮(向死而生);相反,它早已被徹底內化于被規則嚴密包裹的至大無外的元宇宙內部,由此它早已被徹底剝奪了與每一個個體之間的活生生的體驗關系。但看似山窮水盡,仍有裂隙敞顯。死亡既然無法來自外部的沖擊,也無法在個體身上被真實地體驗到,那就只有一種可能了——在個體之間作為“共情(compassion)”被體驗到。我自己雖然不再有死,不再能死,不再體驗到死,但當我與你、我與他以極端的方式彼此面對時,卻時而會有最為強烈鮮明的死亡體驗涌現。這樣的共情體驗即使不再如通常所理解的死亡那般可怕,但從其極端的強度來看,它仍然足以取代日漸失勢的死亡而成為元宇宙內部的感染之力。
但為何一定要激發出種種觸犯禁忌的感染力呢?為何大家就不能太太平平地生活在被禁忌隔離和保護的安全領土之內呢?這不僅是因為僭越和感染的危險是始終存在的,而且還因為感染并非只是一種消極破壞的力量,而是具有一種根源性的能動和創生的力量。借用瑪麗·道格拉斯在《潔凈與危險》中的那句名言:“死亡的污染被當做積極的創造性角色來對待,從而有助于彌合形而上學的裂隙。”簡言之,一個真正有活力和創造力的社會形式和生存方式,必須有勇氣、有智慧從那些看似“污染”的禁忌之中獲取肯定性的靈感和動力。元宇宙同樣如此。如果我們仍然對它懷著應有的尊重和希望,那么如何從它的種種死亡禁忌之中激活時間政治的靈感或許是一條關鍵的道路。在《在第二人生中成長》和《一個虛擬世界中的生與死》()這兩部研究《第二人生》的代表作之中,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語音”這個僭越死亡禁忌的關鍵要素,頗值得反思。元宇宙中的個體以“化身”的形態生存(“living as avatar”),但化身遠非單純之物,它主要以文本(text)為依托,進而融匯了表情、性別、身份、種族等錯綜復雜的要素。這些要素之間時常也會發生失調和抵牾的狀況,但真正撕裂數字化身的完美面具、驟然間引入真實肉身的感染力的至為危險的要素恰恰是語音。語音所營造的那種人與人之間的不可思議的“親密性(intimacy)” 才是元宇宙那看似光滑無縫的機體內部的最為可怕的禁忌。不過多少令人遺憾的是,“禁止發聲”這個語音禁忌在上述著作之中都未成為一個要點。因此,我們有理由期待沿著涂爾干、赫爾茨和道格拉斯等人類學大師的禁忌理論的啟示,聚焦于語音對元宇宙進行更為細致的分析,更為透徹而有針對性地反思和批判。勞倫·貝蘭特(Laurent Berlant)曾不無嚴厲地指出,晚近以來所興起的“共情”理論潮流的一個最大癥結就是將共情簡化,還原為旁觀者個體的內心體驗,而未能真正發揮出它理應具有的在個體之間營造共鳴共振進而導向行動和變革的政治力量。語音會成為激活元宇宙的時間政治的關鍵要素嗎?我們期待著,憧憬著。在元宇宙中“發聲”,或許已經是一種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