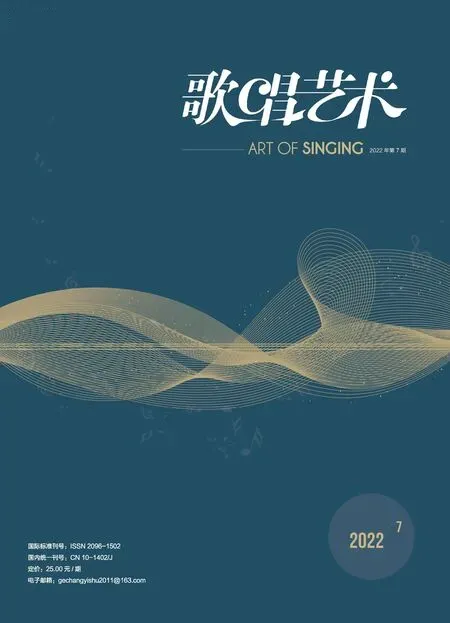源于原生態,信守信天游
——訪西安音樂學院聲樂系主任陳勇
趙世民
接到《歌唱藝術》的采訪任務,談談西安音樂學院聲樂系的建設,我和陳勇定好時間在西安音樂學院教學大樓前見面。因防疫要求,我不能擅自進樓,得陳勇和保安說明情況,領我上22層系主任辦公室。
陳勇問:“這次聊點啥?”
我說:“就六個字,今天、昨天、明天。”
陳勇說:“‘昨天’還用說?你可比我熟。我才當聲樂系主任12年,剛好一輪,可你……”還真讓陳勇說著了,我和西安音樂學院聲樂系的緣分可比中央音樂學院早。
輝煌的歷史,優秀的前任
1983年,西安音樂學院聲樂系的學生到西北政法學院演出,我作為西北政法學院的學生為他們服務,在舞臺一側拉大幕。那場演出有孟小師唱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有徐良唱的《駿馬奔馳保邊疆》,有王真唱的《大地早上好》(日本電影《狐貍的故事》的插曲)、《蘭花草》,有呂繼宏唱的《在那桃花盛開的地方》,等等。
或許王真看我拉大幕快,演出完,王真說:“大個兒,跟我們走吧。”我跟他們一塊回了音樂學院。那時,我身高1.88米,臂展1.98米,別人要七八下,我三下就能拉開大幕或閉上,樣子也比較憨。
王真帶我到了琴房樓北樓三層窗戶朝東的一間琴房,我看琴房的墻是有窟窿眼兒的厚紙殼,王真說那是隔音板。在放鋼琴的那面墻上有一個大胡子的頭像,也是憨憨地朝我們笑著。王真指著他說:“這是帕瓦羅蒂,當今世界最棒的男高音。”接著,王真用當時最新潮的雙卡錄音機給我放了首歌,說道:“這就是他唱的最有名的詠嘆調,歌劇《藝術家的生涯》里的《冰涼的小手》。”我一句(詞兒)不懂,但歌聲觸動了我。過一會兒,王真坐在鋼琴前,自彈自唱起來。我聽出來,唱的就是剛才錄音機里播放的帕瓦羅蒂唱的《冰涼的小手》。我聽著,他的聲音和大胡子的帕瓦羅蒂差不多。王真告訴我,“這叫意大利美聲!”
從此,我就喜歡上了“美聲”,喜歡上了意大利歌劇。我們差不多每周都要聚,不是看西安音樂學院的音樂會,就是聽王真“諞”(音“piǎn”,在陜西方言中有“侃”的意思)歌唱的一些事。
1984年,王真參加文化部主辦的國際比賽選拔賽,他第一輪、第二輪都脫穎而出,第三輪就是決賽,不管名次多少,都可以出國比賽,可王真卻棄賽回來了。我焦急地問:“這么好的機會,你怎么能放棄呢?”王真說:“我怎么也沒想到我能進第三輪,只準備了二輪的曲目。”
這期間,同在西安音樂學院聲樂系上學的徐良突然和我告別。他報名參加了“47軍”,說是下部隊演出時被部隊領導“感化”,說他定是名好兵。
我和徐良的緣分早在1975年。那時,我們都就讀于北京玉淵潭中學,我上初三,徐良上初二。有一天,他的班主任趙瑞云老師找我說徐良嗓子好,讓我幫幫他當廣播員。我用自己的校廣播組組長之便幫助徐良當了校廣播員,發揮他嗓子洪亮的特長。后來,在全校的文藝會演中,我指揮他們班唱了《長征組歌》,徐良一人擔任了《四渡赤水出奇兵》和《過雪山草地》兩首的領唱,我讓他模仿馬國光和賈世駿。看到徐良有這么大進步,趙老師多次感謝我,甚至請我到她家吃飯。在她家,我認識了她的三女兒—朱迅,也就是現在“央視”著名主持人,那時她才兩歲。1982年,徐良以男高音考上了西安音樂學院聲樂系,是他最早給我介紹了意大利“美聲”面罩唱法。他也時不時給我唱兩句高音,并問我:“聽著有沒有戴個頭盔的感覺?”
受王真、徐良等人的影響,我1985年退伍后來到了中央音樂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教授全校學生的必修課—馬克思主義哲學。
巧得很。1986年,王真、周江平(和慧的第一任聲樂教師)、魏晶、薛紅平、丁毅等西安音樂學院的青年教師到中央音樂學院進修,找的導師可都是大牌教授,如沈湘、郭淑珍、黎信昌等。我和王真他們幾乎每周都聚,聽他們上課,看他們匯報演出,并一起看各種音樂會。為了讓王真學習更安定,我甚至將音樂學院分我的東墻邊上四平(方)米的183號宿舍讓給他住,那里以前是臨時琴房。
那期間,我們收到了徐良的來信。信中說,他已隨部隊開赴老山前線,住在貓耳洞里,和普通戰士們一樣打仗,我們都很掛念他。結果,1987年的“中央電視臺春節聯歡晚會”,徐良一身軍裝,坐著輪椅,被人推上舞臺中央。他唱了首《血染的風采》,攝像還專給他的右腿拍了個特寫—只剩下空空的褲管。這是西安音樂學院聲樂系學生首次上“春晚”,并且是那屆“春晚”最大的亮點。原來,徐良在一次戰斗中受了重傷,不得已,從大腿根處截肢。他真是用他的鮮血和生命在唱《血染的風采》,引無數國人感動。
“王真們”也倍受鼓舞,歌唱技藝日日漸長。在一次“七一”晚會上,王真在人民大會堂獨唱《延安頌》,我們在電視上看直播,個個都感到無比自豪。接著,中央歌劇院、總政歌舞團等多家國家級文藝團體要調王真,但他還是回到西安音樂學院聲樂系做起了教師。
1990年,我陪沈湘夫婦到西安音樂學院聲樂系講學。在輔導王真唱《冰涼的小手》時,沈老師一激動,跟著王真一起唱起了High C。在回京的火車上,沈老師跟我說:“‘西安院’這幫年輕教師不得了,過不了幾年,他們就會走到前列。”
還真讓沈湘說中了。隨后幾年,西安音樂學院聲樂系教師安金玉奪得“央視青歌賽”美聲唱法專業組第一名,聲樂系培養的白萌、呂繼宏、和慧先后獲得該賽事專業組第二名,陳勇得了美聲唱法專業組第一名。這成績當時已經超過了中央音樂學院和上海音樂學院。這里還走出了在國際舞臺上闖蕩的中國歌唱家,如女高音歌唱家和慧,她是西安音樂學院聲樂系的重要教學成果,先后師從青年教師周江平和王真。

王真教授 (左) 與陳勇教授合影 (2022)
在海外奮斗的中國歌唱家中,和慧可以排在前列。這有四個標準。
標準一,世界頂級歌劇院,如紐約大都會歌劇院、斯卡拉歌劇院、維也納國家歌劇院、柏林國家歌劇院、科文特花園皇家歌劇院等,和慧在這些劇院演過經典歌劇《阿依達》《托斯卡》《蝴蝶夫人》《假面舞會》等劇主角的A組。標準二,和慧與世界頂級指揮家都合作過,如洛林·馬澤爾、祖賓·梅塔、穆蒂、奧倫等。標準三,與世界頂級男高音歌唱家,如多明戈、阿蘭尼亞、何塞·庫拉、里奇特拉等,和慧都同臺合作演出過歌劇。標準四,和慧演完威爾第的歌劇《阿依達》,被國外專家譽為“當今最好的阿依達”;演完普契尼的《蝴蝶夫人》,被贊為“當今最完美的巧巧桑”;演完普契尼的《托斯卡》,被譽為“可以和瑪麗亞·卡拉斯相媲美”。要不,“環球歌劇大獎”“奧斯歌劇大獎”,都頒給了畢業于西安音樂學院聲樂系的陜西安康人和慧。要知道,這是在和世界歌劇界一線明星的比拼中脫穎而出的。
這些成就,都是在王真當聲樂系主任時期獲得的。王真當了27年聲樂系主任,這無形中給繼任者陳勇帶來了巨大壓力。
源于原生態,信守信天游
陳勇說:“我當了12年聲樂系主任,除了鞏固以前的教學成果外,還要不斷創新。”
我問:“你在任時,最主要的創新是什么?”陳勇說:“我們聲樂系創辦了陜北民歌專業。”
2016年10月27日,我在國家大劇院小劇場看了“永遠的信天游—陜北民歌音樂會”,陳勇是這臺音樂會的策劃。看完音樂會,他跟我說:“西安音樂學院地處陜西,有那么厚重的音樂歷史傳統,又有那么豐富的民歌資源。我們一定要把握這個大勢。如何講好中國故事,對于我們這個陜北民歌專業,就是要講好陜北故事。這場音樂會,就算是對我們教學的一次檢閱。李興池教授為此次音樂會付出了巨大的勞動,他要根據全國各地的情況,調整編配曲目,從演出的前期聯系到落實,以及具體的演唱風格,他都費盡了心血。”
西安音樂學院聲樂系陜北民歌專業最突出的教學成果之一要數杜朋朋了。他參加過“中央電視臺春節聯歡晚會”,這是繼徐良、呂繼宏、丁毅等之后,又一個西安音樂學院聲樂系的學生在“春晚”唱主角。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文藝晚會”上,杜朋朋和王二妮演唱了《山丹丹開花紅艷艷》;在“信念永恒—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音樂會”中,杜朋朋再次領唱了這首陜北民歌。2021年,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多場重大演出活動中,杜朋朋也是主角。顯然,杜朋朋已經進入中國歌壇一線。前兩年,我和中國交響樂團策劃了一臺陜北民歌音樂會,也請了杜朋朋做主要演員。
國家大劇院那場音樂會,杜朋朋唱了《一對對鴛鴦水上漂》和《船工號子》。我感覺陜北味道很足,但山野風弱了點,“宮廷化”了。我琢磨陳勇跟我說過的話:“我們辦陜北民歌專業,要源于原生態,精于原生態。否則,原生態的歌手唱得好好的,我們系為什么還要專門培養?而且,從原生態的審美標準看,我們未必比得過土生土長的原生態。”
整場音樂會看完,見識了杜朋朋、雒勝軍等十五位學生的演唱,我突然悟透了“源于原生態,精于原生態”這句話。原生態歌手在山野里唱歌,由于空間遼闊,空氣、云霧會將歌手聲音中尖利的“毛刺”打磨掉,所以遠距離聽他們的歌聲,聲波傳到聽者的耳朵里是潤耳觸心的。而在劇場里還這樣唱,由于空間縮小,空氣來不及打磨那些“毛刺”,聲音幾乎直接傳到人的耳膜,聽者就會覺得沒有在山野里聽到的悅耳。

“永遠的信天游 ——陜北民歌音樂會”在國家大劇院演出 (2016)
我在陜北采風時親歷過這種現象。我們在山這頭,聽到對面山上一老農唱信天游,太悅耳了,那絕對是原生態的陜北民歌手。后來,我們找到他,在房間里,再給我們唱,我們讓他像在山野里那樣唱,結果就覺得他的聲音尖利得要刺穿耳膜一般。
陳勇說:“源于原生態,精于原生態,就是一條嗓子、兩種唱法。在山野唱,就回到原生態,保有粗糲和毛刺;在室內劇場唱,就更精致化,這也便于陜北民歌向全世界傳播。因為我們的民歌手到國外演出,都是在室內劇場、音樂廳,很少在山野里演唱。陜北民歌的味兒,關鍵是陜北方言與音樂水乳般交融。”這也可以說是源于原生態,信守信天游。
我說:“陜北方言,你們招的就是陜北人,沒問題;陜北音樂,他們入學前基本上都是原生態歌手,也沒問題。那把他們招進來后,怎么往‘精致化’培養呢?”
陳勇說:“一方面,我們聘請了陜北民歌傳承人來當導師。另一方面,他們也像普通的聲樂本科生一樣,視唱練耳、音樂史、音樂美學等專業基礎課都要上,要讓每個學生在世界音樂文化的大背景下感受和理解自己的陜北民歌。學院還聘請了喬建中教授來牽頭專門研究陜北音樂。喬老師之前是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所長,是地道的陜北榆林人,關于陜北民族音樂的論著等身,而且他還挖掘、整理了一大批陜北民歌。我們還邀請我們的前院長趙季平先生創作陜北風格的音樂作品,我們在‘全國青年歌手電視大獎賽’合唱比賽中奪得第二名的作品《陜北風情》,就是趙先生創作的。趙季平、韓蘭魁和我們的特聘教授李興池等根據陜北民歌創作的歌劇《米脂婆姨綏德漢》,雖說首演是王宏偉和雷佳,但我們也拿來演出,效果非常好。”
我問:“這些學員就來自陜北,是不是他們也能挖掘更多的陜北民歌?”
陳勇說:“我們的教學計劃有這一項設想。有一個階段的課程,就是讓學生回到家鄉,整理出鮮為人知的陜北民歌,考試就唱這些。杜朋朋也會作曲,自己采集來的陜北民歌素材,自己編創、演唱。”陳勇還希望將來與作曲家合作,能夠創作出新的以陜北民歌為素材的歌劇,前院長趙季平、前副院長韓蘭魁已經做出了榜樣。
其實,有的陜北民歌背后有著豐富的故事,如《蘭花花》《三十里鋪》《趕牲靈》。
比如,“趕牲靈”就是趕牲口,牲口就是家畜,是馬、騾子、驢等,怎么就變成了牲靈呢?原來這背后有一個凄美的愛情故事。
有個大戶人家,主人叫周塬,雇了個長工喜娃給他們家趕牲口。周塬有個小女兒叫小丹,喜娃經常給小丹講自己趕牲口走四方的奇聞逸事、風土人情。有時,走近地兒還帶著小丹,并護著讓她騎在牲口上。一來二去,小丹愛上了喜娃這個長工。周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地位如此懸殊,他怎么能同意呢?
于是,周塬托媒人為小丹說了很多家門當戶對的媒。小丹不是說這家的太胖了,就是說那家的太木了,反正非喜娃不嫁。周塬本想辭了喜娃,心想,女兒見不著他,慢慢就死心了。但又一想,這長工還會偷偷摸摸找回來的,帶著女兒私奔可怎么辦呀?周塬想了個毒計,借喜娃一次趕牲口出遠門,花錢勾結土匪把他劫了、殺掉。
那天,小丹送了喜娃一程又一程。路上,他們商量好,等喜娃這次回來,他倆就找個機會私奔。喜娃說,自己已看好口外有一個大牧場,水美草肥人稀,咱們就在那兒安家,放牧牛羊兼養自己的兒女。小丹問,要是你到口外看上別家的女兒怎么辦?喜娃發毒誓,那我就變成牲口天天讓你抽、隨你騎。喜娃邊說,邊用鞭梢抽著走在頭里的騾子。
喜娃剛出了西口,就被劫了。但劫匪沒有殺他,因為匪首是個女扮男裝的人,她看上了喜娃,想讓他做壓寨夫君。喜娃心里有小丹,哪里肯從?但為了能逃出匪窩,喜娃假意答應了女匪首。在女匪首和喜娃辦喜事當天,喜娃趁她喝多了酒,逃了。很不幸,眼看喜娃就要到家了,又被抓了壯丁,最后死在戰場上。

西安音樂學院合唱團參加“第十四屆全國青年歌手電視大獎賽”合唱組比賽 (2010)
小丹天天盼著喜娃回來帶著她私奔,終于有一天,只盼回了騾子。俗話講,老馬識途,但無言的騾子無法告訴她發生了什么。于是,小丹就天天趕著牲口去迎喜娃。時間長了,小丹魔怔了,就把那頭騾子當成了喜娃,口中還唱著:“走頭頭的那個騾子喲……”這首把騾子當情哥哥的民歌也慢慢傳唱開了,而忘了“牲口”化“牲靈”的本來面目。
《趕牲靈》要是能創作成歌劇,由陜北民歌專業的學生參演,那這個專業就更“火”了。
我問:“陳勇,你是正兒八經學‘美聲’出身,還去‘美聲’的發源地意大利留過學,怎么想到創辦陜北民歌專業呢?”
陳勇說:“那年‘青歌賽’,我們聲樂系合唱團唱了趙院長創編的《陜北風情》得了第二名。陜西省領導,還有學院領導,認為陜北民歌是我們的文化資源優勢,為了保護好這項非物質文化遺產,最好的方式就是培養更多這方面專業人才。尤其是我們西安(古長安)又是古代陸上絲綢之路的起點,要講好中國故事、講好陜西故事,最直接的當然就是創辦陜北民歌專業。經過兩三年的調研和籌備, 2012年我們招了第一屆陜北民歌專業學生。現在看來,在全國11所專業音樂學院,我們能和其他院校有所區別的,就是我們有陜北民歌這個特色專業。”
我問:“陜西民歌資源特別豐富,接下來是不是……”
陳勇說:“辦陜南民歌專業。陜西以秦嶺為界,秦嶺以北是黃河流域文化,秦嶺以南是長江流域文化。要不然賈平凹怎么會說出這樣的金句—‘秦嶺提攜著黃河長江兩域的文明’。陜南民歌和陜北民歌完全是兩回事,又和接壤的四川民歌、湖北民歌不一樣,特別好聽,只是演出和宣傳不夠。我們學院聲樂系、作曲系都有陜南籍的老師和學生。幾年前,我們也和陜南當地的院團合作,讓唱陜南民歌的演員到我們這兒進修。有時,我們會聯合作曲系到陜南當地學校聯合辦學,培養和提高陜南民歌的演唱水平。我也多次帶著專家團隊到陜南采風調研。預計,2023年,我們聲樂系將正式開辦陜南民歌專業。”
我說:“照你這思路,像隴東民歌、花兒,絲綢之路上的特色民歌,還不都得辦專業了?”陳勇笑了,說:“我們沒那么大野心,能辦好守住陜北民歌、陜南民歌專業就可以了。”
讓專業的歸專業,娛樂的歸娛樂
我問:“現在網絡發達,短視頻影響廣泛,幾乎是個人就能在網上開講授課。我看了些,大部分是誤人子弟,傳遞的是錯誤或有偏見的歌唱知識和技術。作為專業院校是不是也得弄些視頻,占領這個陣地?”
陳勇說:“這是占不過來的。很有可能,你剛發一聲,就被周圍的聲音淹沒。我想,就像偉人說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網絡大多是娛樂,我們還是要強調和樹立聲樂的專業性,起碼讓聲樂愛好者知道,要想專業地學習聲樂藝術是要上專業院校。通過每年報考學院聲樂系的人數來看,我們已連續多年超過2600人,這就足矣。”
我很贊同陳勇的說法。“我經常聽一些‘學院派’的專家和教授抱怨,說網絡媒體中的教學亂象得管一管了,不能是個人就能在網絡平臺發教學視頻,這樣就把正規的教學搞亂了。首先,你怎么管?你有什么權力管?網絡視頻人人都有權發布,這就是大眾娛樂,網絡自有它管理的規則。只要人家是個守法公民,發的有關聲樂視頻再業余、再錯誤,你也沒有權力封人的賬號呀。其次,專業的聲樂教學一定是‘一對一’的,系統的、循序漸進的,長達四五年,甚至十余年的工程。所以,將娛樂的歸娛樂,專業的歸專業。我們的專家、教授在專業的音樂院校,為自己的專業學生上好專業課就足矣,犯不著對網絡上的那些教學視頻義憤填膺。”
陳勇說:“為了加強我們專業院校的專業性,我和上海音樂學院、中央音樂學院等倡議過,院校聯合,搞一些專業交流、選拔、展演,等等。我們首先就在中央音樂學院搞了意大利歌曲、法國歌曲的比賽。2022年,為‘紀念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八十周年’,計劃11所院校聲樂系一起搞全國聲樂比賽。另外,全國11所院校的教師資源可以共享,請過來,派過去。比如,我們的陜北民歌專業就可以派出去,到全國各院校交流演出。前幾年,我們做得不錯,去過新疆藝術學院交流。”
我就在西安音樂學院學術演奏廳觀看過廖昌永率領的上海音樂學院聲樂系師生的演出,當晚廖昌永“裸唱”(無伴奏)《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我還在西安音樂學院排練廳,在中國音樂學院和西安音樂學院聲樂系師生的交流中,聽過馬秋華唱《天路》。我也在中央音樂學院聆聽過和慧跟該院聲樂系師生交流,并聆聽她唱的《為藝術,為愛情》和《晴朗的一天》。
其實,西安音樂學院聲樂系讓沈湘預言準了,也是派出青年教師去“中央”“上海”、去美國、意大利進修留學,請名校的名專家來開大師班交流的結果。這樣,西安音樂學院的聲樂教學才能異軍突起。
陳勇說:“我也參加過周小燕歌劇中心的活動,有長訓的,也有利用假期短訓的。他們會請一些國際頂級的專家前來講學,有管聲音的,有‘摳’語言的,有管音樂的。也會選拔年輕歌手出演角色,排一部歌劇。這就辦出了行業的標準,專業的方向。我們西安音樂學院聲樂系向周小燕先生學習,除了每年讓教師出去開音樂會、演歌劇之外,系里每年也要自己排一部歌劇。幾年下來,已排演了歌劇《江姐》《黨的女兒》《小二黑結婚》《米脂婆姨綏德漢》《白鹿原》《魔笛》《費加羅婚禮》《女人心》《唐璜》等。通過這些舞臺實踐,提高我們教師和學生的水平。”
陳勇說:“為了提高我們的專業性,我們對拔尖人才設立了‘雙導師制’。經過考核選出來的尖子學生,我們配備兩名主課導師。比如,這個學生專門唱德語作品,就由擅長德國作品的教師來教。下一個階段,學習唱意大利語作品,就跟擅長意大利作品的教師學。有的學民族演唱專業的,會放在‘美聲’專業教師班里學習一段時間。”
陳勇特別強調說:“語言是歌曲的靈魂。我們和器樂怎么區別?不就是把語言融入音樂嗎?如果沒有歌詞,僅有旋律,那歌唱藝術根本就不能獨立出來。而天下的語言又千差萬別,有極強的地域性,這就造就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歌唱風格的獨特性。所以,我們要求專業教師教出的學生語言風格一定要準確。這是一條重要的行業標準!唱意大利作品,意大利語就要地道,唱陜北民歌就要有濃濃的陜北方言味兒。”
我在陳勇的琴房觀摩過他給即將參加“吉利聲樂比賽”的學生上課,學生唱的是貝里尼的作品《憐憫我吧》。陳勇說:“你把歌詞唱準了,這歌詞就是‘劍’,一下就‘扎’進聽眾的心臟。沒唱準,那就成了‘盾’,阻擋歌曲的靈魂進入聽眾的心。你唱的意大利歌劇詠嘆調,詞唱不清,意大利味兒從何談起?”
想起2001年,我在清華大學舉辦意大利戲劇男高音費拉羅聲樂大師班上認識了陳勇。我見他上課,總是問題最多。大師有時想進度快點,陳勇就故意唱不準詞,好讓費拉羅糾正。這時,他就用錄音機將大師標準的意大利語發音全部錄下來,回去反復練習。大師班短短的20多天,陳勇進步最快,意大利歌劇味兒,他能唱得很地道,關鍵是以前老大難的高音也解決了。在匯報音樂會上,他完美地唱了有High C的歌劇詠嘆調《冰涼的小手》。陳勇當時跟我講:“費拉羅的確是大師。表面上,他不給你講唱高音的方法,但他‘摳’你的意大利語歌詞,只要唱準了詞,高音自然就出來了,神奇得很。”
大師班結束,我請陳勇到中央音樂學院我的音樂評論寫作課上與同學們交流,他唱了歌劇《托斯卡》中的詠嘆調《奇妙的和諧》等。他反復強調唱準歌詞的重要性:“我們不僅要唱準意大利語語音,還要知道每個字的意思,光知道整句的大概意思是不夠的。如,這首歌的最后一句詞‘sei tu’,有人唱得特‘狠’,像‘我要殺了你’。其實這句詞的意思是‘是你’,結合全曲理解就是‘我心里愛的是你’。知道了詞的意思,你唱得自然就溫柔了。”
作為聲樂系主任,陳勇對教師專業性的要求,他自己首先做到了。他當系主任這12年,在中央歌劇院版法語歌劇《霍夫曼的故事》中出演主角,在意大語歌劇《茶花女》《圖蘭朵》《采珠人》《羅密歐與朱麗葉》,在國家大劇院原創歌劇《山村女教師》《趙氏孤兒》《冰山上的來客》中都出演了男主角。這些角色可都是大劇院公開招聘的,而且陳勇還沒耽誤自己的教學和行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