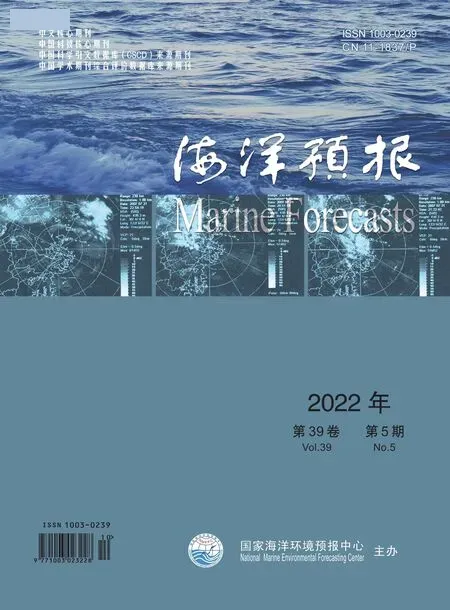基于現場調查的臺風“天鴿”(1713)和臺風“山竹”(1822)風暴潮災害影響和致災對比分析
賈寧,劉強,石先武,趙明利,劉珊,楊雅煜
(1.自然資源部海洋減災中心,北京 100194;2.自然資源部南海規劃與環境研究院,廣東 廣州 510310)
1 引言
廣東省珠海市位于珠江口西岸,南瀕南海,海島岸線長達690 km。珠江口是廣東沿海臺風風暴潮災害最嚴重的岸段之一[1-2],據統計,1953—2017年,影響珠海市的臺風共有166 個,年平均為2.6個,最多年份(1974 年)有 7 個,除 1956 年、1998 年和2005 年無臺風外,其余年份都至少有一個臺風登陸或影響珠海[3]。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和人口的日益密集,風暴潮造成的損失日趨嚴重。據統計,僅9316 號“貝姬”臺風風暴潮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就高達19 億元,風暴潮已成為制約珠海市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珠海市是珠江三角洲岸段珠江口(深圳—臺山)的一部分,而珠江口是一個喇叭口和河網區并存的復式河口,當強大的臺風把海水由喇叭口向內推進時,海水可向河網擴散,因此襲擊珠江口的臺風極易在珠海引發淹沒形成風暴潮災害[4]。
風暴潮災害現場調查具有直觀性、準確性和可信度高等特點,及時有效地開展風暴潮災害實地調查,對于了解風暴潮災害的成因、確定損失和影響、實施應對措施、查明薄弱環節和判斷防災減災措施的效果具有重要意義[5-7]。2017 年第13 號臺風“天鴿”和2018 年第22 號臺風“山竹”先后影響珠江口,兩個臺風路徑相當,強度相當,且均出現了破紀錄的高潮位[8]。自然資源部按照《海洋災害應急預案》(來源:http://gi.mnr.gov.cn/202004/t20200424_2509811.html),對兩個臺風引發的臺風風暴潮災害啟動了Ⅰ級應急響應,并派出調查組赴受災地區開展了現場調查。本文主要通過現場踏勘、走訪詢問和專題座談等方式,并利用實時動態載波相位差分(Real-Time Kinematic,RTK)等技術手段進行現場測量,科學識別了兩次臺風風暴潮災害對珠海市造成的影響,并對比分析了致災差異,以期為風暴潮預警報業務驗證以及各地方有針對性地開展海洋災害風險普查和防御工作提供參考。
2 方法
2.1 現場踏勘
自然資源部歷來高度重視海洋災害的現場踏勘工作。在近年工作的基礎上,自然資源部于2019年制定了《風暴潮、海浪災害現場調查技術規范》(HY/T 0275-2019)[9],對風暴潮和海浪災害的現場調查內容和技術要求進行了明確。本次現場踏勘按照標準的要求,重點開展了海水淹沒范圍、深度以及承災體受損情況的調查。在調查海水淹沒情況時,調查組根據現場實際情況選擇漂浮物聚集法和淹沒痕跡判定法對淹沒范圍和深度進行判定和測量。調查組廣泛尋找了可能受災害影響區域內被搬運至陸地的枯樹枝和海上垃圾等漂移物的聚集位置,并現場查看了沿海建筑物上殘留的淹沒痕跡,以此確定淹沒區域的邊緣位置。邊緣位置判定完成后,利用RTK 和手持定位系統等技術手段和設備對海水上溯邊緣位置的經度、緯度和高程進行確認,根據邊緣位置布設平面測網,當出現拐角或者周邊房屋、學校和養殖區等重要承災體分布密集時,則對平面測網進行加密布設,測點間距一般小于300 m。在確定的淹沒區域內,沿海岸垂直角度向縱深尋找殘留在商店和居民樓墻體、路燈、電線桿以及停靠在路邊汽車上的淹沒痕跡,通過測量淹沒痕跡線確定不同區域的淹沒深度。
調查組根據珠海承災體分布的實際情況,先后在漁港、重點養殖區和海岸防護工程等重要承災體的分布區域進行災害現場調查。在調查漁港受損情況時,調查組了解了漁港停泊的漁船數量、不同馬力漁船的受損情況以及漁港、碼頭等的受損情況。在調查重點養殖區的受損情況時,調查組重點了解了養殖類型、養殖物價格、養殖設備受損數量和養殖受損面積等。在調查海岸防護工程時,調查組主要了解了建造材質,并利用皮尺測量了防護設施的受損長度和寬度等。在實際踏勘中,技術人員從遠、近多角度對承災體進行照片記錄,單個特征點拍攝照片的數量不少于6 張,可以充分反映承災體的受損部位和受損程度等。
2.2 走訪詢問
在開展淹沒調查和承災體受損調查時,調查組深入受災群眾中,詳細詢問了災害的影響時間和影響程度。特別是在淹沒調查時,超過50%的淹沒痕跡點位均有災害見證人的驗證。同時,調查組與當地海洋減災主管部門進行了專題座談,對承災體受損和實際淹沒情況進行了進一步核實。
3 結果
3.1 自然過程對比
2017 年第 13 號臺風“天鴿”于 8 月 20 日 14 時(北京時,下同)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并于8月23 日12 時50 分左右在廣東省珠海市金灣區附近沿海登陸,登陸時中心附近最大風力為14級(45 m/s),中心最低氣壓為950 hPa。2018 年第22 號臺風“山竹”于9月7日20時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并于9 月16 日17 時前后在廣東省臺山市海宴鎮附近沿海登陸,登陸時中心附近最大風力為14級(45 m/s),中心最低氣壓為955 hPa。兩次過程的基本情況見表1。

表1 “天鴿”和“山竹”臺風基本情況Tab.1 Basic information of typhoons"Hato"and"Mangkhut"
從表1 可以看出,兩次臺風均在菲律賓以東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路徑為先穩定西行后轉為西北行[10],登陸點在珠江三角洲沿海地區,登陸強度為強臺風級別,中心最大風力基本一致。與臺風“天鴿”相比,臺風“山竹”登陸點更偏西、7 級風圈半徑更大、登陸時中心氣壓更高以及登陸地附近最大瞬時風力更小[11]。
從兩次臺風過程引發的風暴增水來看,在臺風“天鴿”影響期間,廣東汕頭—汕尾沿海出現了50~120 cm 的風暴增水,廣東惠州—珠海沿海出現了120~310 cm 的風暴增水,廣東江門—陽江沿海出現了60~110 cm 的風暴增水,廣東惠州、鹽田、珠海、赤灣、黃埔和橫門潮位站出現了達到當地紅色警戒潮位的高潮位,并破歷史最高潮位記錄。在臺風“山竹”影響期間,廣東汕頭—汕尾沿海出現了90~180 cm 的風暴增水,廣東惠州—江門沿海出現了150~340 cm 的風暴增水,廣東陽江—雷州半島東岸沿海出現了60~150 cm 的風暴增水,廣東惠州、鹽田、珠海、赤灣、黃埔、橫門和三灶潮位站出現了超過當地紅色警戒潮位的高潮位。從引發的增水來看,臺風“山竹”造成的最大增水高于臺風“天鴿”,且超過當地紅色警戒潮位的高潮位站點個數也多于臺風“天鴿”,說明臺風“山竹”的影響范圍更大。從對珠海市的影響來看,在臺風“天鴿”影響期間,珠海潮位站觀測到的最大增水和最高潮位均高于臺風“山竹”。
3.2 災害影響對比
3.2.1 海水淹沒
兩次臺風均引發了較大的風暴增水和高潮位。珠海海洋站(簡稱珠海站)位于珠海市香洲區,其觀測數據可有效反映研究區域內的增水和潮位情況。在臺風“天鴿”影響期間,珠海站觀測到了614 cm的高潮位,超過當地紅色警戒潮位147 cm;在臺風“山竹”影響期間,根據水痕跡線測得珠海站的高潮位為588 cm,超過當地紅色警戒潮位121 cm。較高的潮位造成珠海市城區出現了大范圍海水淹沒現象。兩次風暴潮災害影響期間,調查組先后前往香洲區、角門區和金灣區對淹沒情況進行實地調查和測量,鑒于兩次臺風過程影響區域相似,兩次調查測量區域基本一致,測量點位均超過120個。
經實地踏勘,“天鴿”臺風風暴潮災害導致的海水淹沒區域主要集中在香洲區情侶北路、中路和南路地區,南坪鎮的灣仔碼頭、橫琴鎮濕地公園和客運碼頭也出現了海水淹沒情況,金灣區和斗門區的海水淹沒情況并不明顯。淹沒類型以漫堤、漫灘和管涌淹沒為主(見表2),最大淹沒深度達200 cm。“山竹”臺風風暴潮災害導致的海水淹沒也主要集中在香洲區情侶北路、中路和南路地區,南坪鎮的灣仔碼頭、橫琴鎮碼頭及度假村也出現了海水淹沒現象。淹沒類型主要以漫堤、漫灘和管涌淹沒為主,最大淹沒深度為100 cm。從淹沒區域來看,兩次臺風風暴潮造成的淹沒區域基本一致,情侶路附近受海水淹沒嚴重。從淹沒深度來看,“天鴿”臺風風暴潮引發的淹沒深度普遍超過“山竹”臺風風暴潮。從淹沒范圍來看,“天鴿”臺風風暴潮造成的淹沒總面積大于“山竹”臺風風暴潮。

表2 調查區域內珠海市主要淹沒情況Tab.2 The main inundation situation in Zhuhai survey area
3.2.2 主要承災體受損
調查組查看了珠海市堤防設施、漁港、漁船和養殖區等的受災情況。經調查,兩次災害過程均對珠海市沿海道路及海堤護岸等造成一定損失,重點受災區域集中在情侶路香洲漁港—九州港沿線海堤護岸。兩次災害過程中珠海市海堤護岸受損情況見圖1。臺風“天鴿”導致珠海市情侶北路海堤護岸受損嚴重(見圖1a),較多海堤石料等被海水搬運至數米,而在臺風“山竹”期間,海堤護岸雖然也遭受了一定損毀,但未見較多石料堆積或被搬運至其他區域(見圖1b),因此從整體來看臺風“天鴿”對海堤護岸的影響程度更大。兩次災害過程對漁船的影響相對較輕,僅在臺風“天鴿”事件中發現部分船只被海水沖上岸導致擱淺,兩次災害過程中均未發現大范圍漁船傾覆事件,相關損失為船只停靠期間受風浪影響相互碰撞產生。兩次災害過程對海水養殖業的影響較為相似,受災主要體現在風浪導致的養殖設施受損和養殖物逃逸,以及臺風導致的部分養殖區停電,由于無法增氧,導致養殖物大量死亡。

圖1 兩次風暴潮過程造成珠海情侶路堤防設施受損嚴重Fig.1 The two storm surge processes caused serious damage to the guardrail of Qinglv Road in Zhuhai
“天鴿”和“山竹”臺風風暴潮襲擊珠海市造成的損失情況見表3。2017 年和2018 年廣東省發布的《廣東省海洋災害公報》顯示,“天鴿”臺風風暴潮災害造成的死亡(含失蹤)人數、損壞船只數量和直接經濟損失均高于“山竹”臺風風暴潮。“天鴿”臺風風暴潮導致珠海市2 人死亡(含失蹤),且為城市居住人員,為近年罕見。“天鴿”臺風風暴潮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更是達到臺風“山竹”的40倍。

表3 “天鴿”和“山竹”臺風風暴潮災害給珠海市造成損失情況Tab.3 Losses and damages caused by typhoon storm surge disasters of"Hato"and"Mangkhut"in Zhuhai
3.3 兩次風暴潮影響原因分析
3.3.1 淹沒差距分析
臺風“山竹”和臺風“天鴿”兩次過程的強度、路徑和登陸地等具有明顯相似性,但在珠海市造成的總淹沒面積卻差異明顯。原因如下:
(1)臺風路徑。從兩個臺風的移動路徑來看,臺風“天鴿”比臺風“山竹”的移動路徑偏北,更容易引起風暴增水,水體在三角洲河道堆積從而引發珠海市沿岸地區被海水淹沒。
(2)登陸時間。臺風“天鴿”登陸于農歷七月初二,恰好處于三角洲地區的天文大潮期,而臺風“山竹”登陸于農歷八月初七,處于三角洲地區的天文小潮期。風暴增水疊加較高的天文大潮,更容易形成高水位從而導致珠海市等地區出現淹沒情況[12]。
(3)瞬時風力。臺風“天鴿”結構更為緊密,體積更小,極大風范圍易集中在登陸點附近,造成短時間海水上漲較快,沖擊力更強,近岸浪導致護岸損壞較重,因此漫堤和潰堤淹沒較為嚴重。
3.3.2 損失差距分析
造成“天鴿”臺風風暴潮災害損失遠超過臺風“山竹”的原因主要有兩個。
(1)群眾防災意識。臺風“天鴿”是近50 a 來登陸珠海的最強臺風,引發了重大的風暴潮災害,海水大范圍淹沒珠海市區道路,多處沿海居民小區車庫進水。由于近年來珠海市未發生如此重大的風暴潮災害,沿海群眾對風暴潮災害的威力及可能造成的影響認識不足,兩名前往地下車庫的人員死亡。臺風“天鴿”災害發生后,當地政府采取了多種措施,進一步提高了群眾的防災減災意識和自救互救能力。在“山竹”臺風風暴潮災害影響期間,群眾對重特大風暴潮的認識和防災意識已經有所增強,因此采取了嚴密的防范措施,沿海居民區未出現車庫大量進水的現象,當地居民也未在臺風影響期間前往危險地區或開展危險活動,“山竹”臺風風暴潮災害未造成人口死亡。
(2)地方防御準備。臺風“天鴿”登陸前的預報路徑與實際路徑相差較大,且近海增強明顯[13-14],地方應對的經驗和準備時間不足。一方面,部分區域出現了停電現象,養殖戶無法使用增氧機,漁業養殖受損慘重;另一方面,由于防御準備不足,海岸防護設施未能有效加固,堤防系統薄弱環節(內部隱患)與外來作用(荷載)的共同作用導致海岸防護設施受損嚴重[11]。臺風“天鴿”災害發生后,當地政府深刻總結了災害的慘痛教訓,對香洲區情侶路、金灣區機場路和桂山島等重災區進行改造,增種了抗臺風植被,并對受損的防護設施進行了加固和重建,改造后的防護設施整體的抗風和抗潮能力顯著提升。綜上,雖然兩個臺風造成的海洋災害影響區域基本相同,但整體損失差距較大。
4 結論與討論
臺風“天鴿”和臺風“山竹”兩次臺風風暴潮過程給珠海市造成了嚴重的風暴潮災害。本文采用實地踏勘、現場測量和座談訪問等方式,獲取了兩次臺風風暴潮造成的淹沒和災害損失情況。通過對比發現,兩次臺風過程在基本路徑、登陸級別和登陸地點等方面具有較大的相似性,但臺風“天鴿”造成的風暴潮淹沒深度、淹沒范圍、人員死亡(含失蹤)數量和直接經濟損失均高于臺風“山竹”。鑒于兩次災害在珠海市形成的淹沒區域具有較高的重合度,因此仍需進一步加固珠海市區部分海岸防護設施,同時繼續加強海洋防災減災意識宣傳和海洋災害風險評估與區劃工作,進一步提升海洋災害應對能力。
本文全面分析了給珠海市帶來重大災害影響的兩次臺風風暴潮過程,但研究還存在許多可改進之處。一是對于淹沒范圍的測量主要基于現場走訪,可能存在對淹沒范圍了解不全面的情況;二是在承災體受損調查中,對海上養殖的受損情況關注較少,同時對于衛星遙感和無人機航拍等技術手段的應用還不夠;三是未對紅樹林、鹽沼和珊瑚礁等生態系統受風暴潮災害的影響情況進行調查,未來迫切需要建立一套針對生態系統的風暴潮災害現場調查技術方法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