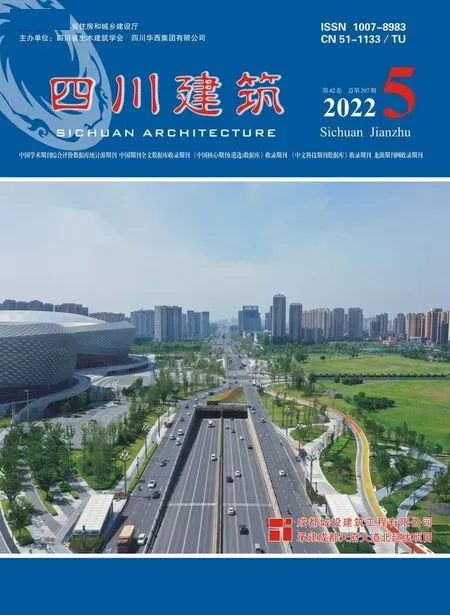人行懸索橋軟顫振特性風洞試驗研究
劉雪猛, 冉蕓誠, 李 強
(西南交通大學, 四川成都 610031)
近年來,越來越多景區開始建造玻璃景觀人行橋來吸引游客,橋面高程也在不斷提高,而人行橋主梁斷面一般為鈍體斷面,高風速下易發生破壞性較強的顫振現象,為確保人行橋的正常使用,有必要對其抗風性能的進行深入研究。
目前已有學者開展了人行景觀橋顫振性能的研究。2009年,許福友等[1]對宿遷黃河公園人行景觀橋在不同風場、不同攻角下進行了風致響應分析,試驗證實了其氣動穩定性。2012年,白樺等[2]對人行懸索橋抗風性能改善措施進行了研究,得出增設抗風纜和上中央穩定板都可提高其顫振性能的結論;2017年,何愷等[3]分析了跨度430 m的人行懸索橋的顫振性能,其結果表明:提高橋梁重量并增設抗風纜能很好地提升其顫振穩定性;2018年,魏志剛等[4]詳細分析了抗風纜不同錨固位置對人行懸索橋顫振的影響,結果表明:僅在跨中施加抗風纜就能顯著提高橋梁結構的固有頻率,從而提高顫振性能。綜上的這些研究和措施能有效抑制有明顯發散臨界點的“硬”顫振。
除了這些極具破壞的發散性“硬”顫振現象外,國內外學者在節段模型風洞試驗中發現,越來越多的鈍體橋梁斷面在達到起振風速后,并未表現出明顯的發散性顫振,而是呈現為在不同風速下均具有不同的穩態振幅,且振幅隨著風速的增加而緩慢增大[5-6]。這種表現出明顯非線性特征的顫振現象被學界稱為“非線性顫振”或“軟顫振”。Chen等[7-8]研究了軟顫振現象與顫振導數的關系;張朝貴[9]提出了一種非線性氣動力模型較好地解釋了軟顫振現象;朱樂東等[10]分析了4種典型橋梁斷面的軟顫振現象,并討論了影響軟顫振振幅的幾種因素;鄭史雄等[11]對π型斷面主梁軟顫振特性及抑振措施進行了研究;王騎等[12]研究了大跨橋梁顫振后狀態的氣動穩定性;董佳慧等[13]研究了邊箱鋼-混疊合梁的軟顫振特性,并給出了不同氣動措施對顫振性能的影響;伍波等[14]對雙層橋面桁架梁進行了風洞試驗研究,詳細分析了其軟顫振特性。目前鮮有針對人行懸索橋軟顫振的研究,而鈍體特性較為顯著的人行橋主梁斷面發生軟顫振現象的可能性較高,盡管軟顫振并不會導致橋梁斷面發生損毀,但其較大的自限幅振動對于游客的安全性和舒適性影響較大,因此需著重研究該類橋梁的軟顫振現象及特性。
本文以西藏·八宿·怒江72拐峽谷玻璃吊橋為研究對象,通過節段模型自由振動試驗,從軟顫振振幅大小、軟顫振頻率、彎扭耦合運動相位差、豎向振動參與度等方面對其原始設計斷面進行了顫振特性分析,對比了該人行橋斷面與其他形式斷面在軟顫振特性上的異同;分析了水平導流板對顫振特性的影響,得出不同攻角下不同工況的軟顫振臨界風速并進行初步分析。本文研究可為后續同類型橋梁的軟顫振性能的研究提供參考。
1 節段模型風洞試驗
1.1 工程概況
西藏·八宿·怒江72拐峽谷玻璃吊橋是位于西藏省的一座景觀人行橋,為提高主梁的抗風結構穩定性,在主梁下方兩側設置抗風纜。橋梁設計主跨為 152 m,橋面凈寬2 m,橋面鋪設超白鋼化夾膠玻璃。人行橋的橋面自重及橋面活載通過主索傳遞至兩側的錨碇,依靠兩側錨碇保持橋體的抗傾覆穩定性。人行橋主視圖如圖1所示,主梁標準橫斷面如圖2所示。
1.2 節段模型試驗參數
本文的風洞試驗研究在西南交通大學XNJD-2 直流式風洞開展,風洞試驗段截面高度為1.5 m,寬度為1.3 m,風速范圍1.0~20.0 m/s(表1)。
根據風洞斷面尺寸、阻塞率及試驗相關要求,制作了縮尺比1∶8的節段模型,模型長L=1.1 m,寬度B=0.375 m,高度H=0.21 m。附屬結構采用ABS塑料板制作并確保外形及透風率相似,模型由8根拉伸彈簧懸掛,并在模型兩端設置端板,保證流動的二維性,形成可豎向運動和繞模型扭心轉動的二自由度振動系統,如圖3所示。通過給定大振幅激勵,獲取自由衰減振動位移時程,由式(1)、式(2)可計算出該動力系統的頻率和阻尼比。具體試驗參數列于表1所示。扭彎頻率比實橋值與模型值之間的誤差小于4%,滿足試驗要求。由于顫振由扭轉模態主導,故以扭轉頻率計算實橋與模型的風速比,其值為2.66。

圖1 人行橋(單位:cm)

圖2 原始主梁橫斷面示意(單位:mm)

表1 節段模型試驗動力參數

圖3 彈簧懸掛節段模型
(1)
(2)
式中:f為頻率,ζ為阻尼比,yn、yn+m為相隔m個周期的2個波峰振幅值;tn、tn+m分別為2個波峰對應的時間。
2 原始斷面軟顫振現象
試驗測試了斷面在5種風攻角(0°、±3°、±5°)下的顫振性能,試驗來流為均勻流,對未加氣動措施的原始斷面進行節段模型顫振試驗。
圖4給出了不同攻角下人行橋豎向及扭轉振幅RMS(Root Mean Square)值隨風速變化的關系。由圖可以看出:隨著風速的增加,斷面并未有明顯的顫振發散臨界點,而是在達到起振風速后表現出振幅穩定的非線性顫振現象,即“軟顫振”。相同來流風速時,不同攻角下的軟顫振振幅大小差異明顯,振幅隨著攻角的增大(-5°~5°)而增大。

圖4 軟顫振振幅RMS值變化
由于軟顫振沒有明顯的發散臨界風速,此處參照橋梁抗風規范[15]中扭轉振幅RMS值0.5°時所對應的來流風速為“軟顫振臨界風速”。由圖4可知,不同風攻角下的軟顫振臨界風速存在明顯差異:隨著風攻角由-5°至 5°,軟顫振臨界風速逐漸降低, -5°風攻角下軟顫振臨界風速最大,為44.23 m/s,+5°風攻角下軟顫振臨界風速最小,為26.68 m/s;豎向振幅與扭轉振幅大小隨風速增長的變化趨勢較為類似,高風速下斷面呈現典型的彎扭耦合運動。
為便于觀察彎扭耦合運動過程中豎向和扭轉振幅的大小,此處以弧度表示扭轉無量綱振幅,豎向無量綱振幅定義為arctan(h/B),其中h為模型豎向振幅,B為模型寬度。以+5°風攻角實橋扭轉風速51.54 m/s為例,繪出扭轉和豎向無量綱位移響應時程曲線如圖5所示。由圖可知,扭轉無量綱振幅高于豎向無量綱振幅,但豎向振動也有較大的參與;并且位移響應幾乎同時達到峰值,可見兩者的運動相位差很小。

圖5 扭轉和豎向無量綱位移響應時程
為進一步分析人行橋的顫振特性,對不同攻角下各個風速的顫振時程數據進行快速傅里葉變換,從而獲得其頻域特性,圖6給出了軟顫振發生后,不同風攻角下軟顫振豎向、扭轉頻率隨風速的變化曲線,由圖可知:扭轉頻率與豎向頻率始終在數值上保持相同,這一特性與以往學者對于軟顫振頻率的研究結果一致;對于同一風速不同風攻角,軟顫振頻率則存在明顯差異,隨著風攻角由-5°至5°,軟顫振頻率由大變小;除-5°風攻角下頻率隨風速的增大而增大外,其余攻角下頻率均隨風速增大而減小,人行橋正攻角下的頻率變化規律與文獻[14]中的桁架梁一致,對于人行橋-5°攻角下頻率隨風速增大而增大這一現象還有待進一步做顫振機理的研究;模型系統的固有扭轉頻率為2.271 Hz,軟顫振頻率變化整體上圍繞在系統的固有扭轉頻率附近,其中正攻角下軟顫振頻率低于系統固有扭轉頻率,負攻角下軟顫振頻率高于系統固有扭轉頻率。

圖6 軟顫振頻率變化曲線
接下來詳細分析豎向運動與扭轉運動相位差大小、相位差隨風速的變化關系,對于彎扭耦合振動,豎彎運動方程與扭轉運動方程可寫為:
h=h0sin (ω1t+θ1)
(3)
α=α0sin (ω2t+θ2)
(4)
式中:h0、α0分別為豎向運動振幅、扭轉振動振幅;ω1、ω2分別為豎向振動圓頻率、扭轉振動圓頻率;θ1、θ2分別為豎向振動初始相位角、扭轉振動初始相位角,θ1-θ2即為相位差。
為清晰地看出相位差隨風速的變化規律,圖7給出不同攻角下相位差隨風速的變化曲線,由圖7可知:不同風攻角下相位差的變化規律存在明顯區別,3°、5°攻角下隨風速的增大相位差先由11.3°先減小為0°附近,而后開始增大到7°左右,兩者變化規律類似;0°攻角下隨風速的增大相位差由0.74°逐漸增大到7.69°;負攻角下的相位差明顯大于正攻角,其中-5°攻角下的相位差最大;-3°攻角下隨風速的增大相位差由27.9°減小為17.1°;-5°攻角下隨風速的增大相位差由44.13°減小為33.13°;人行橋軟顫振負攻角下存在明顯的相位差,為典型的彎扭耦合振動,正攻角下相位差相對較小,5°攻角、風速41.3 m/s時相位差幾乎為0°,此時的振動形態可認為偏心扭轉振動。

圖7 相位差隨風速變化曲線
為了較直觀地看出豎向振動參與程度隨風速增長的變化趨勢,用豎向振動無量綱振幅除以扭轉振動無量綱振幅,即振幅比來描述。振幅比越大表示豎向參與程度越高。圖8為不同攻角下振幅比隨風速的變化曲線,由圖可知:不同攻角下振幅比的整體變化趨勢是相同的,都隨風速的增大而增大;其中正攻角下的豎向振動參與度高于負攻角下的參與度,-5°下的振幅比明顯低于其他攻角。

圖8 振幅比隨風速變化關系
3 導流板對軟顫振的影響
參考傳統的線性顫振抑振措施,并考慮橋梁的美觀及氣動措施設置的便利性,采用斷面兩側增設水平導流板的方式(圖9),模型導流板寬度4.2 cm,寬度剛好與下橫梁齊平,具體措施如圖10所示。人行橋在不同攻角下扭轉振幅RMS值風速變化如圖11所示,由圖可知:安裝導流板后,與圖4(a)相比0°、3°、5°的3個攻角下的軟顫振起振風速增大,而-3°、-5°的2個攻角下的軟顫振起振風速減小,-5°攻角起振風速最小,只有23.76m/s;起振后0°、-3°、-5°的3個攻角下的扭轉振幅迅速增大,振幅增大到4°后增長速度逐漸緩慢;5°攻角下扭轉振幅始終保持在較低值。

圖9 水平導流板

圖10 軟顫振振幅RMS值變化圖
進而分析安裝導流板措施后對軟顫振頻率的影響,圖11給出了軟顫振發生后,不同風攻角下軟顫振豎向、扭轉頻率隨風速的變化曲線,由圖可知:從數值大小上看,軟顫振頻率整體小于系統固有扭轉頻率2.271 Hz;從變化趨勢上看,正攻角和零攻角下頻率隨風速增大而減小,負攻角下變化趨勢為先減小后增大,整體維持在較大值,其中-5°頻率大于-3°頻率。對比圖6可知導流板措施使負攻角下的頻率發生明顯改變,數值上整體降低并且變化趨勢也發生了改變;對正攻角的改變不顯著。

圖11 軟顫振頻率變化曲線
圖12為安裝導流板后相位差隨風速的變化曲線,與圖7相比,均是負攻角下的相位差明顯大于正攻角,其中-5°攻角下的最大;但導流板的安裝使其變化趨勢發生了改變:不同攻角下,相位差隨風速的增大均是增大趨勢,與原始斷面變化趨勢存在明顯差異。
從振幅比的變化關系圖13中可以看出:振幅比仍是隨著風速的增大而增大,但導流板的安裝使不同攻角的差異減弱,-5°攻角下的振幅比有了明顯的增大。
綜上所述,此導流板措施使人行懸索橋正攻角的軟顫振臨界風速大幅度提升,但降低了負攻角下的軟顫振臨界風速;降低了負攻角下的軟顫振頻率,使其低于了系統固有扭轉頻率;降低了負攻角下的相位差,并改變了其隨風速的變化規律;增大了負攻角下豎向振動參與度,尤其是-5°。

圖12 相位差隨風速變化曲線

圖13 振幅比隨風速變化關系
4 結論
利用節段模型風洞試驗,詳細分析了人行懸索橋的軟顫振特性及水平導流板的作用,主要結論:
(1)人行懸索橋呈現典型的軟顫振形態,即給定風速下,振動頻率單一且振幅穩定。
(2)不同風攻角下人行懸索橋軟顫振臨界風速差異性很大,-5°攻角時臨界風速44.23 m/s,+5°只有26.68 m/s。
(3)軟顫振發生時,豎向與扭轉振動頻率相同,隨風速的增加,顫振頻率減小(-5°攻角下數據點少,不明顯);負攻角下振動頻率大于模型固有扭轉頻率,正攻角下振動頻率小于模型固有扭轉頻率。
(4)負攻角相位差明顯大于正攻角,耦合振動形態顯著。
(5)對于人行懸索橋來說,水平導流板會大幅度增加正攻角下的顫振臨界風速,但會降低負攻角下的顫振臨界風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