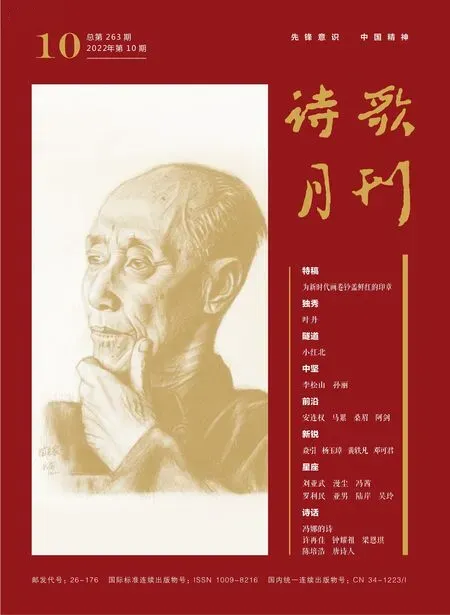從勞作中生發的自然之詩
鐘耀祖
對于作詩,馮娜似乎領悟到一種類似于古希臘人的詩學觀念——將作詩與制作器物等同視之。馮娜追憶起詩歌與勞動的古老羈絆,將詩人作詩與農夫勞作關聯起來,讓人隱隱瞥見留存于《詩經》《工作與時日》里那個詩人與農夫尚未截然分離、“勞者歌其事”的遠古時光。馮娜從小浸潤于云南麗江那秀麗淳樸的山水之中,對于鄉土的勞作也多有體驗,往往會在詩作中流露出一種對于自然與農事的細致感知,并由此生發出對于詩歌創造的領悟。
自然是作詩與勞作的共同對象,聯結著作詩與勞作。馮娜說“詩人本來就是自然之子”,作詩是詩人與自然交流的方式。詩人保持著與微小生靈和諧共棲的謙卑姿態,去接觸自然,書寫自然,進而更深入地領悟自然。而農夫與自然接觸的方式則是勞作,他們可以“抬頭看云預感江水的體溫”,可以“用一個寓言”指點“五百里外山林的成色”,能夠輕易地“辨認一只斑鳩躲在鴿群里”,而這一切都是“長年累月的勞作所得”——勞作讓農人的生活深深地植根于自然,讓農人可以深切感受自然的脈搏,這種農人與自然的親密關系讓向來鐘情于自然的詩人慨嘆:“我并不比一個農夫更適合做一個詩人”。
于是,“作詩—勞作”“詩人—農人”構成了馮娜詩歌中的兩組隱喻關系。“一個人終生只播種一種作物,算不算好農夫?”,這似乎是在問:一個人終生只寫一種詩,算不算好詩人?“他揀選的種粒也揀選著他”,也即是說:與其說是詩人在挑選詩歌,倒不如說是詩歌在非常嚴苛地挑選詩人;當詩人觀看農人削去枝葉,制作出“一個拙笨的容器”時,又怎不會想起薩福、狄金森她們取材于自然生命,質樸率真的作詩過程?
既然“詩人作詩如農夫勞作”,那么作詩的成果與勞作的果實也可建立聯系,“詩作—作物”乃至“詩作—植物”的隱喻關系便延伸而出:過度成熟的詩作便如熟透的果實,“果實帶給人安慰,讓人忘記事實上這是另一種衰老”,它們成為“一座正在朽掉的宮殿”,充滿了過度的“甜蜜”與做作。而詩人執著于“尚未熟透的山楂”,從已有的“酸澀”憧憬著“會有”的“甜蜜”,這種對于詩作“欲達高潮”的審美觀念,與萊辛“包孕性的頃刻”有共通之處。
這樣,馮娜從詩人與農人、作詩與勞作的古老淵源中重新發現詩歌與自然的密切聯系,生發出了以自然觀照人事的詩性思維——這是一種“我不能放棄”的“魔術”,是一種極具個性的“魔術”:以純粹本真的美為尺度,獨抒性靈,不必勉強自己學習那些“從來沒有學會過的技藝”,不流于陳套俗見。從這種自然的詩性思維出發,詩人以種種自然事物來象征人事,來解讀人事,來豐富對于人事的闡釋,遂產生了一些頗為新異的理解:“我”會從強悍的“母豹”來理解女人未被規訓的另一面;坦然地用危險而“迷人的蜃樓海市”來點綴人生“困頓的旅途”;借助大自然“廣大的沉默”來解救被塵世“聲音”所俘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