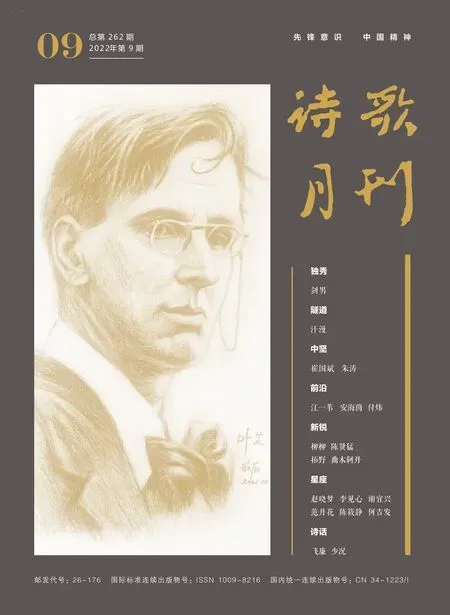付煒的詩
付煒
推窗見雪
重要的不是雪,而是純粹的消逝
在我眼前,猛然一閃
再也找不到相同的另一片
也許這就是我愛雪天的理由
我愛的——
是一種樸素里裹藏的絕望
是輝映著沉默的鏡子
是寂滅的安靜
是推窗的瞬間,宇宙仍然安好
我仍然有看雪的心情
而今而后
每天,那撲向空白的努力
又會折向自身。我為了摹繪
鏡子里陡直的光,使自己變得
如群山般沉緩。畢竟,我的天賦
在于坐在愛的人身旁找尋
平靜。在于癡迷宿命——
接受事物的教育和寫作的勞動
我要承認,我并非是一切的例外
最細微的鐘聲,也可以圈禁我
我缺乏一種無限,一種悲劇開始的
震悚感。我總是在意義叢林里
不懈走著,為了驗證夢的堅硬
與夜晚的斑駁。我不存在任何見解
別問我,時間到底脫落了什么
去觀察各式的眼睛,涌入的
細雪和塵土。穿過松弛的原野
撫摸一朵云掉落的碎屑
晚餐在靜穆里,呈現出罐頭般的
昏聵。我置身其中
感激詩的寬忍與慈悲
是的,我在說感激
父親卸下肩上的曠野
跟著父親返鄉,在日暮的小雨里
他一路無言,我一路恍惚
聽著遠處的暗雷。村莊越來越近
那隱匿在田野盡頭的光
裂隙一般,泄露出迢遞的消息
父親轉身看了看身后的我
仿佛關掉了世界的聲音。然后
我們繼續走著,枯草在我們鞋底昏厥
我感到父親的注視從未收回
又感到巨大的曠野即將湮沒他的背影……
到家了,我親眼目睹父親
在門前的水泥地上,簌簌
卸下了肩上所有的曠野與黑暗
對峙或消磨
我沉浸于冬日的邊緣,過濾
雪和六點鐘的天氣,我向外眺望
事物的暗影令人厭倦,樓下的車流
又開始擁堵。我翻開一本書
注視滿紙的煙云,也注視誰在我
眼前說的一個謊。令人驚心的并非是
哪個詞,而是書寫的無力與不可能性
畢竟我自身的容器時常有溢滿之感
那淙淙水聲,撞散了我的靜寂
令我削去錯覺和傷痛,將不息的
渦旋置于一個濃縮的夢境里
我攜帶決心與勇氣
潛泳在每個稍縱即逝的時辰
在故事的省略里耗盡最后一縷風
我與風疊合在一起,并用相同的
默契去模仿另一陣風。我感到
才能的虛假以及技藝的真實
感到每個人都如厚厚的帷幔
將恐懼遮蔽在空氣無法抵達之處
原諒我一生都在對峙,在消磨
我走向人群,卻不知道要說些什么
橋洞
停下片刻,讓影子歇一會兒
讓仁慈的傍晚再多一點寧靜
我的意圖無非是這么簡單
即便我知道,雪將在未知的風景里
擦亮一個瞬間
為此,我開始移動,以便身后的
黑暗更快合攏,我沒有回頭看
只是感到了一種熟諳的氣流
在我身上交匯,旋即碎裂
我依靠那猝然的經驗走向盡頭
盡頭只是一條路的初始。天還是
那么冷,奇跡還是沒有降臨
我走了很遠,回望橋洞
它咳出了許多疾馳的車輛
許多囂嘈而又興奮的烏鴉
在紛揚的雪夜,落在我眼前的
河面上,引起目光的一陣輕微騷動
星期六下午的灰燼——仿弗蘭克·奧哈拉
當全部的意義已終結,我掀開
一座薄暮的城市,讓孤單的鐵軌
運送我們的羞辱,讓一瓣兒玫瑰
贈予我們沉思與荒蕪。這世界
在窗簾后面,注視著我們
我們不必去想象它的模樣
不必去討一瓢水喝,不必還鄉
不必堆砌更多的陰影
我們羈留在自身的縫隙里,躲過
一場冷雨,和朋友圈無聊的詩
唯一的想法是,在雨后穿過夜幕下的
公園,不引人注意,也避開平庸的風
來到河邊,聽到浪的沉默
這就夠了。然后我們返回,撲滅一盞
臥室的燈,我知道你雙唇期待著什么
我們在黑暗里對話,說星期六下午
我們各自剝開的時間
我們享受它無用的溫柔,像云掠過樹梢
像椅子將我們挽留。巨大的平靜降臨在
附近的山崗,明天我們要去看一看
生長在那里的質樸的植物,是否
像你一樣噙著世間所有的光
清白,干凈,值得我抖落自身的灰燼
值得我將大海搬空
如此或如彼
群花欲悴。你潛伏在月光里
躲開一盞秋天的燈,靜觀枯葉
在風中節節潰退。你辨認出浩大的羞恥
藏在你往日的寫作中,難以消融
而長夜,僅僅是投身于詩的借口
妄圖從渺小的自我摘除掉一個狂歡的
年代。然后背過身
述說那早已傳頌的妙喻,無論你
與誰一起并肩走過漢語的巢穴
都將驚散那些詭譎的鳥群
你在焊定的天空下,想象潮水
和溺水的人,你聽見雨墜落的聲音
如此迷人,仿佛將要
沖毀那殘存于你身體里的忐忑
夜行列車
音樂從深壑里拯救出耳朵
黑暗因此而解凍。我懷著
觀潮的心情,潛入風景的輪廓
它們卻消逝在一片更大的輪廓里
城市,一座翻動不息的海
在盡頭,容納著我內心所有的潰敗
我無法想到,沿途,列車如誘餌
在驟冷的空氣里,留下
一道裂隙,誰耽溺其中
聆聽遠方的風暴,和漫游者
墨色的眼睛。穿過岑寂而擁擠的
迷宮之后,我寫下這首詩的第一行
細雨與余燼
在這灼熱的國度,言辭必須成為蔭涼。
——耶胡達·阿米亥
越來越安靜,在你熟諳的枝柯里
夏天久已渙散,空留下膨脹的浮光
在路過的少年身上煊赫著。你和
那些潤涼的象征物,絡繹在故園的
山麓下,舉頭望著嚴密的暮云
堆砌出史書里的啞然,人間
只聽得,潮音陣陣,群樹耳語
一個寬闊的夜晚即將展開
飄逸著鋒利的霧。真的很靜
雨的氣息令人想起失去,這失去
已經穿過了往事的重帷,直抵
一株野梨樹的咳嗽里
它驚落了滿地素雪,令你絕不
說出自己的沉默,絕不
用時間開鑿出空蕩的敵意
而一些事物正在燃燒,另一些
正在消亡,用塵埃般的耐心
緩慢地將一個故事吞噬,或許在早晨
或許在午夜,你將看見
灰燼映襯的臉龐籠罩著你的存在
還有雨,嚴肅地靜止于窗玻璃上
在夜風的呼吸中顯得岌岌可危
你不打算觸碰一滴雨內部的星辰
只任憑它在你眼里研磨出語詞的芬香
藏身之地
彼時我們在雨幕里談論塔可夫斯基
廣告屏不斷在我們眼睛里陷落
你說:務必要諳熟一個蘋果里
秘密的街道,還有北方樹林中
那些索居的羽毛,因為它們
與我們一樣,在詞語里沉眠
周遭是歡愉的霧,和不斷翻新的
人群,每一幀都飽蘸晦澀的遠景
仿佛涌動著季節的震顫。而我們
藏身其中,像兩枚核,落在傍晚的
徒勞里。只有偉大的漢語窺見過
我們的掌紋。只有鷹隼,在暗處
啄食過我們體內的版圖。但是
我們仍然能夠毫無破綻地絞殺閃電
將眾多驚悸的云朵
安放在我們虛構的峰巒之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