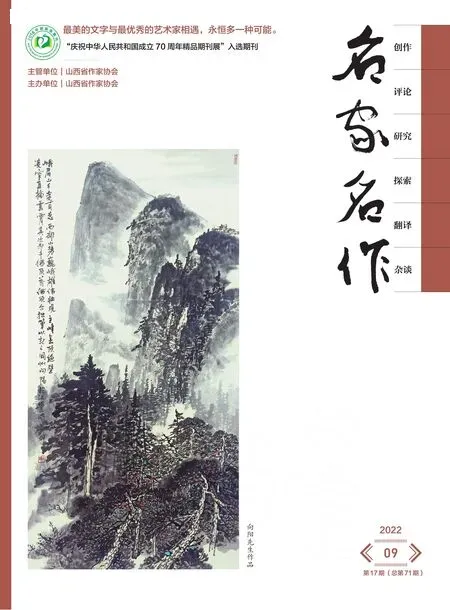凍土中的新芽—《一九八四》與《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女性角色比較
徐 寧
《一九八四》是喬治·奧威爾的代表性著作,書中虛構了一個在極權統治下充滿恐怖氛圍的大洋國社會,人與人之間關系支離破碎。故事中的女性形象被敘述者以一種男性中心主義立場建構。書中主要描繪的女性角色有三位,男主人公溫斯頓的情人裘莉亞、妻子凱瑟琳以及鄰居派遜斯太太。從她們的結局來看,女性在面對極權主義的侵害時不斷反抗卻仍被支配。尤其是裘莉亞的人物結局與命運更是讓人悲痛不已、感嘆萬分。米蘭·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通過一個個鮮活的人物抒發了輕與重、靈與肉、媚俗與政治的選擇,帶來許多有關生命價值的思考與啟發,闡述了作者心中的“存在”。正如昆德拉所說:“讓女人帶領我們,讓永恒的女性滲透到我們的心中。”作品對女性的心理和命運進行深入分析,解釋了在男權社會下女性生存的意義。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女主人公特蕾莎,她的形象也與現實緊密聯系,她的角色正展示了當時女性的困境,她的思想體現著女性在主體意識增長時所產生的矛盾與徘徊。她與《一九八四》中的裘莉亞看似毫無關聯,實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本文通過對《一九八四》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兩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形象的分析,理解不同背景下兩位作者對女性以及人類意識發展的審視與批判。
一、政治環境對女性的壓迫
喬治·奧威爾和米蘭·昆德拉都是因政治而顛沛流離,同時又將政治融入靈魂,不斷在社會歷史的邊緣徘徊的作家:喬治·奧威爾前半生流亡英國本島和歐洲大陸,后又遭到了共和軍的追殺,米蘭·昆德拉被迫移居法國。時代背景和政治因素與他們的個人生活經歷融合,滲透著他們的思想,滲透到他們的作品中,影響著角色的命運。《一九八四》中的大洋國社會雖為虛構,但奧威爾是將納粹德國、蘇俄與20世紀40年代的英國倫敦相結合進行創作。在《一九八四》中,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提出的全景敞視主義得到充分的體現與運用。全景敞視主義是一種間接懲罰的規訓方式,試圖通過規訓來維持社會秩序的運行。書中大部分人都遭受著物質、思想、行為等方面的壓迫,“大哥大”創造了一種全景敞視建筑,統治集團從語言、規訓、懲罰等多個方面控制群眾,從身體暴力到心靈思想,從外部的規訓監視再到內部的麻痹服從,監視者無處不在,群眾成為無意識的監督者和被監督者。而女性在此基礎上,又在性方面比男性受到了更多的束縛,統治者將性羞恥化,試圖將女性變成沒有思考能力的生育機器。極權社會中,統治者剝奪了女性的話語權,而女性自我思考的能力也隨之退化,自我馴化成被監視者。裘莉亞不同于其他放棄思考的女性,是具有反抗精神的一個人物。她最明顯的特點是外表順服、內心叛逆。裘莉亞作為一名外圍黨員,她的反抗方式就是在公共場合表現自己的合群和正直,以此來保障自身的安全。而在沒有監視的區域,她以打破規則為樂,渴望自由的生活。裘莉亞的故事軌跡體現了她所處的政治環境下女性的艱難境遇,也同樣是時代導致了她的悲劇。《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的時代背景是20世紀蘇聯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專制壓迫的氣息取代了民主改革風潮,同年八月又打著“主權有限論”的旗號攻占布拉格。特蕾莎在“布拉格之春”中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意義,不顧當局者的壓迫,充當愛國記者,拍下蘇軍慘無人道的行為。特蕾莎雖然勇敢堅強,擁有同理心和同情心,但個體的力量不足以抵抗殘酷的戰爭所帶來的生理和心理傷害,當統治者運用暴力的規訓方式時,特蕾莎不得不屈服,她的人生價值追尋也在政治高壓下喪失意義。時代的悲劇讓特蕾莎在實現自己理想的那一刻,走向了另一種“生命之重”。
二、男性凝視下的女性抗爭
凝視(Gaze)是一種帶著權力運作與欲望的,主體向對象投射注意力的目視方式。法國哲學家福柯曾說:“用不著武器,用不著肉體的暴力和物質的禁制,只要一個凝視,一個監督的凝視,每個人都會在這一凝視的重壓下變得卑微。”凝視的定義中并不含性別意識,但在男權社會中,男性占據權力主體地位,在各方各面對女性進行著凝視。長期的男權社會的意識形態中,女性一直是被動的客體,是男性目光的承受者。在男性居于主導地位的社會中,“男性凝視并非普遍的看。男人凝視,而女人就是被凝視被控制的對象,這是一種權力運用的方式”。菲勒斯中心主義的凝視充斥著《一九八四》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裘莉亞和特蕾莎在各自的故事中遭受相同的男性凝視,然而哪里有“凝視”,哪里就有“反凝視”,被凝視者一旦具有了主體意識,那么她們的主體性將不斷增強,她們的女性意識也在被凝視中覺醒與反抗,通過反抗等行動來爭取平等對話的權利,從“被凝視”逐漸轉為“反凝視”。在《一九八四》中,裘莉亞顯然是一個與極權社會抗爭的女性角色,她選擇的反抗方式是成為“真正的女人”,打破極權主義的性工具化和禁欲主義,還原性愛的愉悅。她從黑市購買巧克力、化妝品、高跟鞋,以享樂主義的方式表達對極權主義壓迫的不滿。她看穿了黨搞禁欲主義的原因,那就是防止男女之間產生統治者無法把控的盟約。她將目光放到溫斯頓身上,并想與之發生性關系,在這里男性凝視倒轉為裘莉亞為凝視主體,也就是“反凝視”。她選擇和很多黨員發生關系來打破規則,這種混亂的性行為在小說中壓抑的氛圍下具有了獨特的抗爭意義,她的性態度和性道德對男性凝視進行反凝視,在小說中的歷史社會環境中具有進步性。《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特蕾莎在童年時代遭受折磨,母親未曾讓她感受到溫暖,繼父不顧道德倫常偷窺她的身體,在酒吧做侍女時遭受許多男性顧客的凝視和挑逗。她無法忍受母親的粗陋和繼父的卑鄙,在與托馬斯相遇的一瞬間就下定決心要離開母親,逃離她所憎惡的地方,這就是她反抗的一種方式。她選擇托馬斯的行為雖然是一種依附,然而這種選擇也是對托馬斯的一種凝視。面對托馬斯多次的出軌和背叛,她雖然害怕,非常依附男人,但她心中并沒有失去對女性自主意識的探索,再次選擇離開托馬斯。特蕾莎不再自我壓抑,逃離到鄉村田園。這時在她的夢境中,托馬斯變為一只野兔,這意味著在特蕾莎的意識里,托馬斯不再是統治者,男性的精神和肉體對她的強大壓迫感已經被弱化,她逐漸完成自己女性主體的建構。這顯然是在男性凝視下的一種女性抗爭。
三、男權社會下的女性反抗限度
身處類似的社會背景下,兩部作品的女主人公都展現了相似卻又截然不同的悲劇宿命。但她們都具有一個相同點,她們的命運被男權體制的社會所操控。男性在父權制社會中掌握所有話語權。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到許多對女性的論述。“把男人定義為人,把女人定義為雌性。她是個雌性——用這個詞給她下定義就足夠了。”這種觀點將女性置于低級動物的位置,繁殖和生育成為女性唯一的存在價值。“圣托馬斯稱女人是一個‘附屬的’人,這是從男性的觀點出發,以某種方式暗示有性狀態的意外性或偶然性。”性別歧視在這個觀點下顯而易見:女性不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而只是依附于男人而存在的性別角色。女性并不與男性擁有同一平等位置,她們所處的地位是與男性“第一性”相對的“第二性”或者“他者”,她們無法擁有與男性平等的自主發展權。總而言之,女性的定義是由男性視角界定出來的。在波伏娃的觀點中,女性之所以是“女性”并非由先天身體結構造成,而是長期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勢力造成的。在父權社會中,女性的生存環境被壓縮,相較于男性,勞動力廉價,生活條件險惡,這使許多女性只能選擇放棄獨立,無法擺脫對男性的依附。
不論是《一九八四》中的裘莉亞還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的特蕾莎,都具有明顯的“他者”特征。在《一九八四》中,身處極權主義國度的女性成為去除女性自我的陰暗的中性人。極權社會污化性行為,將女性塑造為社會工具。裘莉亞雖然具有一定的反叛精神,但她的精神非常微薄。她的反抗是由生理本能所引發。溫斯頓對裘莉亞說,“你只是一個腰部以下的叛逆”,明確表達了以男性為主體的意識下,男性視角中的女性角色思想。裘莉亞用最能夠自我控制的身體話語,在感官上做出叛逆行為。但在脫離感官外的其他意識里,她就缺乏思想,更沒有擔當,也不相信黨的統治會被推翻。裘莉亞心中的解脫是成為真正的女人,即在男性眼中成為女性客體。正如《第二性》中所說的:“黑格爾認為,兩性必然是有差別的,一方是主動的,另一方是被動的,女性當然是屬于被動的一方。”在男權社會下,女性主動成為依附者。裘莉亞對于個人價值和個人理想的追求是麻木的。她和溫斯頓的關系看似是裘莉亞主動,但真正讓這段關系具有獨特的情感意義的卻是溫斯頓。裘莉亞作為一個“他者”在小說里存在,更證明極權社會中女性是“附屬品”。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進步,人們的觀念也在改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女性逐漸認識到女性的權利意識的重要性,并試圖去擺脫父權社會下男性中心主義的掌控。然而,女性的命運仍舊在男權社會的掌控下。特蕾莎雖然擁有較為進步的思想,具有一定的自我意識,但她與托馬斯的愛情是建立在父權主義基礎上的。這使女性在兩性關系中居于被支配的地位。特蕾莎從一開始就被托馬斯置于“他者”的地位。特蕾莎受成長環境和男權中心思想的影響,性格較為軟弱,習慣依附男人,并追求靈與肉的統一。托馬斯命令式地說“把衣服脫了”,就會令特蕾莎激動興奮,產生聽從于他和服從于他的想法。盡管她在之后選擇離開托馬斯,然而面對托馬斯的浪子回頭時,她又一次將自己置于“他者”的地位。從特蕾莎的夢境中也可看出,在她的意識里,托馬斯一直置于中心地位,男性擁有主導權,女性天生劣于男性,這也是特蕾莎女性主體意識薄弱的原因。她為了托馬斯放棄自己的生活,但將兩性關系建構在男權主義上必然不可能擁有幸福,她在堅守所謂的“生命之重”中丟失了把握女性自我命運的時機。
四、結語
喬治·奧威爾和米蘭·昆德拉這兩位背景、寫作技巧不同的作家在塑造書中的女性角色時有著很大的相似性,他們都從不同角度透視女性的悲劇,將女性放置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下,從政治環境、社會狀況以及人物自身的矛盾之中去詮釋女性悲劇的命運。裘莉亞和特蕾莎這兩位女性角色雖擁有不同的個性,但都具有一定的女性意識,并嘗試在男權社會下運用自己的方式進行反抗,但因為政治環境、社會環境等各種因素的影響,她們女性意識的覺醒也被限制在有限的范圍內,依舊沒能夠掌握女性自我命運,兩位角色的悲劇結局看似不同,但內核相同。文學作品源于生活,也能給讀者提供進一步的啟示和思考。當前,女性的社會地位隨著社會文明的進步而變化。然而,男尊女卑的思想還存在于一些國家和地區,社會中仍然存在歧視女性的行為。以作品為鑒,女性應認識到“女人不是生就的,而是逐漸形成的”,應將關注點放置于自身的主體性,而不是淪為“他者”或“第二性”,不斷解放個性,捍衛女性的尊嚴和合法權益,尋找自身幸福的落腳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