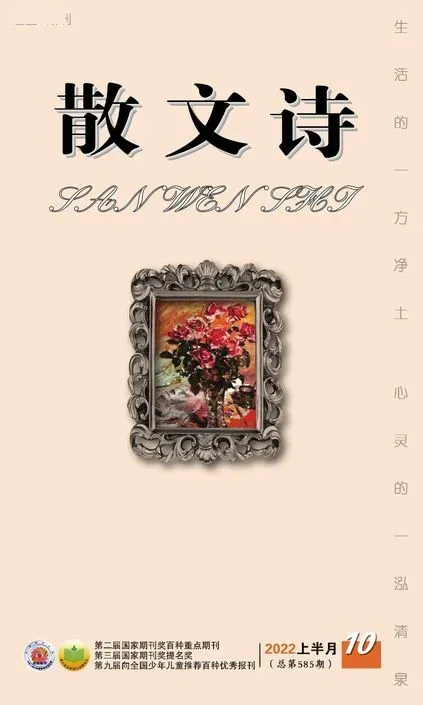茂名石化總公司風采
◎官演武
煉油樹
在這棵棵巨大的風景樹下成長,南方的城市,從蠻荒的年代走出油頁巖黑暗的隧道。
日夜飄散著新生活的情思,一張伸張的火舌舔向天空的臉頰——那是它向上飄動的鮮紅的花束。
城市聞著這些樹散發的異味,那樣親切地接受了這科學上被稱為污染的工業廢氣。
然而,這是油城的奶香,正如一只候鳥忠實于出生的季節,油城歌唱在它的蔭蔽之下,感謝它帶給出世的光明時刻。
煉油樹啊,有多少人為你牽腸掛肚,無論從哪個方向,在陸地,在海上,在空中,都關注著你四季的成長。
你流出的汁液,通過歲月忠實的言語,告訴了遼闊的大地。
告訴給南海之濱,在水一方——
這一方為我們無限愛戀的熱土,這南方廣闊、蒼翠的果園有無數的根,已深深地扎在我們的心頭。
鐵森林
迷失在城市的森林,迷失在鋼鐵里——
在這火樹銀花晝夜亢奮的綻放里。
飽吸科學雨水生長的樹木,縱橫而有序,直插云天,或伏地盤繞,用千枝萬葉構筑著企業之鳥的巢穴,歌唱在晨煙暮火里。
歌唱著城市不斷增長的年輪,鋼鐵之林結出利潤的果實,醉人的汁液,從這里,流向天空與大地的渴望,促使一切輪子和翅膀,加速了轉動和飛翔。
而這森林中的道路,潔凈而曲折。那些走過的植樹者,他們在樹下放飛思維之翼,掠過樹頂。
通過調度室的屏幕,感知整座森林變化的訊息。
感知整座城市的憂慮與幸福。
鐵的意志,鐵的紀律,鐵的向往,化作催生的雨水,滋潤著這些南方油城深厚的根——
這大地敏感的觸須,與祖國和人民緊緊聯系在一起。
廠區綠茵
勞動的情思,從緊迫節奏中傾落,沿路而生,圍鐵而長,在樓房前,在煉油塔下,盛開,綻放,伸張。
像綠色的音符撒播在工廠巨大的琴箱里,構成機械交響的和弦;像展示在太陽底下的斑斕衣裳,映襯著鋼鐵森林巨大的軀體。
像無聲的綠紗窗,像吸水器,使廠房每一時分都過濾在散發清芬的風里。
春在這里萌生嫩芽,夏在這里披上華裳;
秋在這里吹響葉笛,冬在這里留下吻痕。
這是生命的禮贊,洋溢著四季不凋的春意。勞動者的歌聲,留在這綠的唱片上。
工人潮
在時間的履帶上行進,街道是河,廠區是湖。
沖刷在崗位責任制里,在城市的大街上,那些身著統一顏色的身影,來去匆匆,像激流,像時針趕著時間。
這城市的潮汐,發出浩蕩之氣,沖刺在確定的進度里,推動企業之船,駛過城市的早晨與黃昏。
那些永不停止的機械,那煉塔上永不熄滅的火焰,知道這潮水的力量,是怎樣推動一座城市的轉動的。
被工人潮沖走的是過去;
被工人潮刷新的是未來。
海邊花園
大海的情懷,在岸邊開出四季爛漫的花樹。
海風在沙灘上吹醒港口的夢,將一座城市的路從陸地吹進蔚藍的航道,黎明最早朗誦大海的獻辭。
海浪在光芒中盛開花瓣,深海中的珊瑚樹要躍向岸邊,成為一株株洋杉,讓海水——這藍綠交錯的地氈,鋪開草坪延展的意境。
于是,來自大海與陸地的想象,化為了改天換地的日日夜夜。
在深挖坑中改換疏松的沙質,用黃泥鋪就海邊植物生長的溫床,跨越大海與國界,引進世界種苗,在昔日荒蕪地帶上,留下人類改造的景色。
木麻黃在生長。
椰子樹在風中挺起身軀。
南洋杉豎起一面面綠色旗幟。
木棉花點燃英雄的火把。
走進這座海邊的花園, 潔凈的道路與鮮艷的花草在一起, 陽光與明媚的笑臉在一起, 濤聲與油輪在一起, 磨菇般的油罐與海鷗的飛翔在一起。
走進石化港口這座人造花園, 像走進由咸澀到甜蜜的歷史,熱血與汗水, 意志與智慧, 孕育出美麗動人的人間童話。
單浮作業
駁接的命運注定要在深海中尋找位置。
在漂浮中尋找生命之根, 無數浪花的牙齒從身邊碎散。
在遠離岸邊的海中, 它像一個孤島, 最先接到太陽請柬, 最先走進太陽鋪就的紅氈里, 聽著遠航而來的油輪的笛聲, 心潮起伏, 像大海的呼吸, 像抖動的藍布, 激情在盡情地傾瀉。
通過那些海中的管道, 將油液注到一個企業強力跳動的心臟,傾訴著粵西一座城市的跨海心愿, 一代與海同在, 與港口花園同在的流暢心情, 要將世界的距離縮短在一條由陽光與月光鋪就的航道里。
要將大地上的壓力融化在海水, 通過這浮動的以大海為根的生命舞臺, 將海風吹成利潤的箭頭, 浪花舞蹈成榮譽的花瓣。
因為大海給它情懷, 25 萬噸的重載, 也顯得很輕很輕。
港 口
日夜地吞吐。
將每天的旭日吐出, 放飛汽笛與鷗鳥的翅膀, 水路鋪金灑銀。
吐出航空煤油、 汽油, 和南方油城豐沛的激情。
將每天的夕陽吞下, 放下海的帳篷, 將海水吹出星月之妙曲。
吞下原油, 石腦油, 和煉油企業裝置。 吞吐著東歐, 吞吐著沿海城市, 吞吐寬闊的水路, 吞吐日月星辰。
當每年一千多萬噸吞吐量成為記載, 港口便成為海濱城市的一塊巨大勛章, 我們看到——
集裝箱與大吊機在一起;
油罐與油輪在一起;
紅頭發與黃皮膚在一起;
陸地與大海在一起;
今天與未來在一起。
在港口, 沒有什么是凝固的, 海水, 一刻不停地將日子刷新洗亮。
遠 航
遠航, 是為了將岸更牢固地記在心里。
在早晨, 從岸的矚望中出發, 海浪從遠處奔來, 撲到岸上,濺起眷戀的淚花, 然后將不定的路放到了海的深處。
放到礁石之下, 暴風之中, 展開海的遼遠與雄麗。
而遠航人從不回避大海, 他也無法回避大海, 只能以海為道,行走在深淵與浪峰之間。
他吹笛, 歌唱和舞蹈, 全在海風與海水里。
在歌唱與舞蹈中深入大海, 枕海而眠; 他做夢, 苦澀而甘甜的夢, 泡浸在海水里。
唯有遠航, 才能將岸更牢固地記在心上。
遠航人要尋求深海中的珠貝, 要抵達彼岸, 在這個過程里完成偉大的使命, 在這個過程里, 他才能深深悟到岸的真實意義。
岸上, 有四季如春的花園, 有蘑菇般的油罐, 有無數期盼的眼睛, 和揮動的海濱城市的旗幟。
生日蠟燭——題茂名石化華粵公司
眼淚是情緒激動的夸張。
在所有祝愿的時刻, 有一種蠟燭置于豐美的蛋糕, 如人立于豐美的憨實和自然。
那就是無淚蠟燭。 正如一些實實在在的人, 在經歷一段慘淡而艱難的創業之后, 照亮享譽海內外的輝煌業績, 而今更成為某種象征, 點燃你的生日。
飄逝的就不再追憶, 亦無需慨嘆歲月如煙。
把那朵朵紅焰喻為最后的玫瑰也似為不妥。
蠟燭鐘情于生日是輝映, 若沉默的人鐘情于對土地的耕耘,當然無需靠哭泣來渲染豐富的內涵。
靜默地燃燒, 熱力地釋放, 美好地升華。
沒有淚啟引生命的開始。
沒有淚伴隨生命的運行。
沒有淚凝作生命的結局。
對那無淚燃燒的虔誠, 該有某種閃光的精神滲透你的情懷,使你懂得如何開墾未來。
燃燒的塑像
雕塑以凝固的姿態表現永恒。
而火焰, 是對永恒的否定。
這里的塑像與火之奇緣與生俱來, 火索是心靈的觸須, 表達對火的渴望。
只須一根火柴, 一點勇于融釋凝結的閃光, 便使這尊尊靜態生動起來。
一支支從心中升起的歡愉的紅焰, 在黑暗與寒冷的時刻, 在任何一個值得慶賀的日子里, 都燃燒成舒展的笑意。
所有想象與情感塑成的作品, 都在這靜默的微笑中, 化為飄逝的輕煙。
沒有流一滴惋惜的眷戀的淚。
而就在這美麗的自焚背景中, 那會飛翔的翅膀, 奔馳的蹄韻,深邃的眼神; 那溫柔與活潑, 慈祥與靜穆, 端莊與詭秘, 一切藝術的自然和自然中的藝術, 在靈妙的手指間脫穎而出, 以嶄新的姿態和眩目的色彩, 展開世界的斑斕。
蠟燭女人
光潔的蠟, 在廠房演變出四季的色彩。
熱爐里, 在壓塑板上, 在染色瓶中, 在嗡嗡的鼓風機前, 接受著一道道工序的造煉和描畫。
艱難的時日, 從漫長的礦道上走來, 絆落過有淚的少年, 如今, 卻有無淚的光明, 照耀著龐大的王國。
純樸的肉身, 活現出奔馳的馬匹, 展翅的雄鷹, 迎風的松塔,鮮麗的蘋果, 高潔的圣誕樹, 祝福著人世間一切美好的事物, 來到人間。
而我在斑斕的景色中, 看見她們——
蠟燭女人, 在寬大的車間, 像蜜蜂在采蜜, 像鋼琴師沉醉于琴譜上。
也像畫家俯身案桌前, 筆底下, 畫出無盡的情懷。
她們懷抱蠟燭, 以蠟鋪路, 眼神嚴肅而虔誠; 她們從眾姐妹的團結里, 看到自己高舉燭光, 走進了高樓廣廈之中。
看呵——
窗外, 縱橫塔罐的掩映中, 樹木蒼翠的大街上, 正馳過奔向世界的車輪。
檢 修
通過檢修來豐富建設的內涵, 與煉油塔和輸油管道同在, 作為一種對事業的修正, 從一個時代到另一個時代, 為那些身負重職的人們所延續。
檢修者站在建設的高處, 也站在城市的高處、 大地的高處,將企業的現狀與未來縱攬入懷。
目光卻從不為那些璀璨的燈火所迷惑。
心頭的喜悅, 只來自于一場對破裂與污損的事物的完美修復。
他們常常以身處大地的深度檢查被塵土侵蝕的靈魂, 在銹痕斑駁的背景里尋找著質變的根源。
檢修者, 身處于危險的境地, 身處于不由自己選擇的任何時刻。
在輸油的脈管面臨破裂的時刻; 在催化裝置處于松懈的時刻;在機械的螺絲從緊密的銜接中被磨損的時刻。
在爆炸隨時發生的時刻——檢修者, 沒有任何退路。
檢修者, 必須身懷絕技。
思維與行動, 都因科技賦予的精密顯得純樸而嚴謹, 能從最復雜的現象中, 探聽到機械心臟彈跳的律動, 用目光巡視, 用耳朵傾聽, 用心靈感知, 從一個個細節, 思考著廣大的聯系。
從時間的深度考勘生命存在的期限, 從散發塵埃的空間辨清事物演變的脈絡。
有許多新舊事物正在交替。 有許多運行程序需要更新。 有許多內在機制需要改變。 從齒輪到齒輪, 從管道到管道, 從塔到塔,從過去到未來——
檢修者, 深深知道: 他的職責, 來自于新時代的偉大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