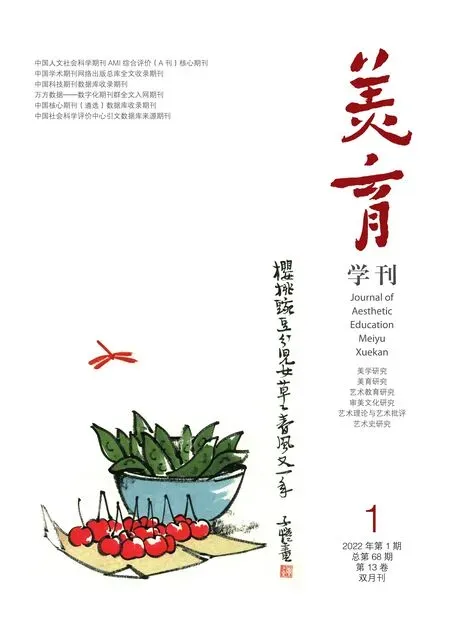美育的美學之緣與美學之助
宋生貴
(內蒙古藝術學院 美育研究中心,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筆者于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學習美學并逐步走上研究的學術之路,且在學習與研究美學的過程中,不自覺地向美育走近。之所以如此,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與教師職業有關,即教書育人的工作與美育的敏感度及興趣點密切相關;其二,理論性的思考與分析往往離不開生活與藝術中可感可及的實例;其三,涉及研究美學的目的。研究美學是為了什么?簡言之,首先是為了提升個人的鑒賞品位與人格境界。其中自然包含審美教育,即所謂“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上三方面的原因,決定了筆者在美學研究中往往很自然地聯系到美育,有時甚至是現實中的美育需求、美育問題成為推動美學研究的動因。正因如此,從一個向度看,美學研究可以推動美育的研究和實踐,從另一個向度看,則可以說美育研究和實踐也會推動美學研究。二者是可以互動互促的。
一
學習西方經典美學著作,須知悉眾多形而上的學術范疇,走進一個個邏輯嚴密的學術體系,得到各有特質的思辨性的學理啟迪(包括方法論方面)。縱觀西方美學史,從古希臘柏拉圖討論“美本身”(關于“本質論”的提問),到18世紀的狄德羅主張“美在于事物的關系”,再到19世紀的克羅齊討論“直覺—表現—鑒賞—美”之間的關系,再到之后諸家,可以說分門立派,各有其卓越建樹與貢獻。但共同之處卻貫穿其中,即對人的精神世界的關注。美學研究對人的精神世界的關注,可以有多個視角,也必然會涉及多個層面,但審美問題必在其中,我們習慣上籠統地稱作“客觀說”“主觀說”或“主客觀統一說”等就是如此。既然美學研究必然會關系到人的精神世界,關系到審美,那么其“美育”的作用自在其中。當然,其表現方式有的是明晰的,有的是隱含的;有的見于其表,有的含于論中;有的關乎大眾,有的限于“小我”。綜上所述,筆者有意表明的認識是,就西方美學史來看,在美學研究中有美育因素在。正因如此,1793年,德國美學家席勒的《美育書簡》問世,得到學界的廣泛關注,自有其學術發展的必然性。這標志著在美學學科中孕育已久的新概念——美育誕生。席勒指出美是“理性與感性的統一”,強調美育對人格完善的積極作用,對美育在美學中的地位及意義從學理層面予以肯定與闡釋。盡管有研究者曾指出,“席勒式”的美育主張,對藝術、美及審美活動寄予太多理想化的期望,甚至夸大了對人生與社會的作用,但其在美育學術發展史上的開創性與影響力則是顯而易見的。
“美育”的概念隨“美學”于20世紀初從西方傳到中國。“美育”與“美學”作為學術概念,是外來的、晚近的,但其實踐與理論則源遠流長、自成其史。傳統意義上的中國美學與西方美學有諸多不同,其中最突出的一點是,西方美學通常注重抽象的學術范疇的提出及闡釋,且依憑嚴密的邏輯關系而形成學術體系,于是有一本本大部頭著作出現。中國美學相對而言更重感性,在表述上講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而且言簡意賅,于是有語錄體的表述,以及文字簡短的詩論、文論、樂論、畫論、曲論、評點等。這方面的不同已成學界共識。此外,還有一點不同,是本文要特別指出的,即中國美學始終是突出美育的,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一部中國美學史,就是中國美育思想史。前面提到,縱觀西方美學史,可以見出美育的因素含蘊其中,而在中國美學史上,則明確體現的是美育的功能與目的。有學者指出:“因為中國古代的先賢談美、論藝術,大都是從教育的目的出發,以鑒賞的眼光,注重美和藝術的功能、作用,以便用于教育實踐,而不愿對美和藝術作純學術研究,一般都不去追問美和藝術的抽象本質,而是追求一種美的自由境界,或塑造一種超塵脫俗的高尚人格。中國古代美學思想也是深刻的,但它不表現在學理的邏輯建構上,而是表現在對藝術—審美經驗的體察與洞觀上。”這一特點啟示我們,從審美教育的角度探討中國美學,不僅會聽到研究結果的落地之聲,而且可以見出其現實意義。
二
關于中西方傳統美學比較中而見出的不同只是相對而言的。作為學科意義上的美學,其研究則完全可以同時在“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理論與實踐空間中進行。我們可以想象到這個“空間”之大,或許確實能夠由有限通向無限;我們也可以想象到,在此寬廣“空間”進行探求的意義——指向人的精神世界。這是多么重大、多么有意義的課題!
美育在美學學科結構中側重于體現美學成果的可實施性與現實有效性。這是在學科層次上的表述。如果從事實上的生成關系來看,美育實踐則是先于“美育”概念的,而且早期的美育實踐活動中鮮有美學理論的自覺應用。我們知道,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在席勒的《美育書簡》問世之前,都已然有悠久的美育實踐的歷史,并逐步形成各自的傳統。在西方,“全人教育”思想影響深遠,其源起可追溯到古希臘。所謂“全人教育”,其目標的關鍵點正是在“通識”與“博雅”教育實踐中,使受教育者成為身心和諧的“全人”,即人格健全的人。其實施內容與方法,針對人的知、情、意、行四個方面進行,并使之達到互通互融。在實踐中已經有了美育的存在。席勒在《美育書簡·第六封信》中指出:“希臘人的本性把藝術的一切魅力和智慧的全部尊嚴結合在一起”,“他們既有豐滿的形式,又有豐富的內容;既能從事哲學思考,又能創作藝術;既溫柔又充滿力量。在他們身上看到了想象的青年性和理性的成年性結合成的一種完美的人性。”在中國,美育同樣擁有深厚的歷史傳統,從先秦時期的“詩教”“樂教”即可見出其特點。孔子是中國歷史上備受推崇的偉大的教育家。他的理想的人才培養目標是“文質彬彬”“盡善盡美”的君子,他主要的施教內容是“六藝”,即禮、樂、射、御(馭)、書、數。如果寬泛一點看,在教育的涉及面上近乎“德、智、體、美、勞”兼備并舉(當然,不同時代在具體的教育內容及內涵上有所不同)。由此可見,孔子的教育目標、教育內容與方法,已具有了明確的培養健全人格的特點,并且尤其重視藝術及審美在教育中的地位與作用。孔子的教育思想影響深遠而廣泛,這已是中國古代教育史上不爭的事實。總之,在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始終是正向的、積極的追求,其中在教育方面,倡導并實踐“全人教育”,或曰注重培養健全人格與綜合素質,是正途與主流。當然,不同時代,不同國家與民族因文化意識、價值觀念以及生活環境、生存方式等諸多方面的不同,在具體的教育理念及表現與表達方式上會有差異。
教育發展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在健康而合規律的教育實踐過程中,“美育”無論是在其作為一個學術(教育)概念出現之前,還是之后,都體現出不可或缺的作用。因為無論是哪個時代,也無論什么樣的國度或民族,只有人的心靈世界得到應有的關注與滋養,人的情操得到陶冶,以及人的知、情、意、行四者得到平衡而和諧地發展,才有益于培養健全的人格。美育概念的出現,除了體現為認識上的自覺之外,還表明其存在的獨特性。而且正因為有這樣一個為人們取得共識的學術概念的出現,才會有共同的討論話題,并使相關問題的研究趨向系統與深入。
三
美育是美學與教育學、藝術學、心理學等交叉應用與實踐的學科,彼此間的互滲與融合生發于自然而然間。從實際應用方面看,更容易從美育與教育的結合中見出實效;從引發興趣與陶冶情操方面看,美育與藝術之間有天緣之合;從學科的歸屬方面看,美育與美學最為密切,或者說就是在同一學科結構之中。正因如此,可以說美育與美學之間既存在學理上的淵源關系,又具有互動互促乃至彼此推助并向前邁進、向外延展的可能。如果說美學的學科發展可能產生多方面、多領域的影響,那么,美育則是其一種走向應用而且最能見到實效的轉化與推動。
朱光潛曾以個人的經歷與體驗為例,講美學研究可以推助審美感受力及美感境界的提升。他說:“我自己還是一個‘未能免俗’的人,但是我時常領略到能免俗的趣味,這大半是在玩味一首詩、一幅畫或是一片自然風景的時候。我能領略到這種趣味,自信頗得力于美學的研究。”朱光潛推己及人,把自己的感受與收獲以書信的方式和讀者交流:“在這封信里我就想把這一點心得介紹給你。假若你看過之后,看到一首詩、一幅畫或是一片自然風景的時候,比較從前感覺到較濃厚的趣味,懂得什么樣的經驗才是美感的,然后再以美感的態度推到人生世相方面去,我的心愿就算達到了。”我們從朱光潛以上表述中,可以明晰地認識到一種相互關聯的助推關系,即美學研究可以啟發與提升美感及審美境界,“美感的態度”又可以使人由“一首詩、一幅畫”等個別審美對象進而“推到人生世相方面”的廣泛意義上。而這后一層目的的到達,事實上亦即美育的指向與效果。
美學研究對美育的影響及推助作用是多方面的,大而言之,包括學理視野、認知層次、學術范疇、理論資源,以及進入實施過程的方法論啟迪等。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卷八中說:“音樂應該學習,并不只是為著某一個目的,而是同時為著幾個目的,那就是(1)教育,(2)凈化,(3)精神享受,也就是緊張勞動后的安靜和休閑。由此可知,各種和諧的樂調雖然各有用處,但是特殊的目的宜用特殊的樂調。”從亞里士多德的具體論述中可知,上述學習音樂的三種“目的”中,“教育”側重于倫理與認知,“凈化”側重于情感的激發與影響,“精神享受”側重于心理放松與快適。如果將此三者整合而觀,則可以說其實是共同指向于人——人的精神世界。從對人的感化與教育的意義上看,此三者事實上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最終達成一個趨同性的目的,那就是實現對人的審美教育。亞里士多德是希臘美學思想的集大成者,被譽為“西方美學思想的奠基人”。他提出的一系列美學范疇以及形成的美學體系對后世影響巨大而深遠,其中包括對審美教育的影響,如上述“凈化”說、“精神享受”(或曰“精神快適”),還有“模仿”說等,都已成為其后歷代美育中的重要理論資源。
把視線轉向中國,討論美育的美學之助——從學理層面到付諸實踐,蔡元培是尤其值得推崇的范例。蔡元培是中國近現代卓越的思想家、教育家、美學家及美育實踐家,他于1907—1911年留學德國,在此期間,對西方美學進行了系統而深入的研究,同時考察了歐洲多個國家的傳統藝術與現代教育。他撰寫了一系列美學論文,把西方近現代美學研究成果介紹到了國內。1912年1月,蔡元培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總長,就任不久即發表《對于教育方針之意見》,明確將“美育”列為國民教育方針的宗旨之一。此后,把體、智、德、美并列為“四育”。1917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后,他進一步對倡導和推動學校美育有了全面的思考。在新文化運動背景之下,他態度鮮明地標舉“以美育代宗教”,強調“美育是一種重要的世界觀教育”。從1917年到1938年的二十余年間,蔡元培發表了《美學觀念》《以美育代宗教說》《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旨趣書》《在北京大學音樂研究會之演說詞》《文化運動不要忘了美育》《美學的進化》《美術與科學的關系》《美育實施的方法》《美育》《二十五年來中國之美育》《美育與人生》等一系列有關美育的文章與演講。他在一再強調美育的意義及其在學校教育中的地位的同時,具體提出了美育的實施方法,規劃出了全民美育的理想藍圖。蔡元培從美學到美育的探索與實踐所出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是中國美學史和教育史上一份彌足珍貴的遺產。
四
前文提到,美育在中國擁有悠久的歷史,從先秦時期的“詩教”“樂教”可見其特點。到近現代,蔡元培等有遠見卓識的教育家、美學家傾力倡導美育,并做出了不朽業績。如今,距蔡元培時代過去了約一百年,那么,現實中的美育狀況如何呢?
在筆者看來,如今“美育”對于多數人而言還是比較陌生的。更大范圍不說,僅就與學校教育有關的群體看,如學生、教師、家長,有多少人知曉何為美育?抑或美育何為?這里所說的“陌生”,并非意味著人們對美育這個概念全然不知,而是指對其內涵的了解,以及在實踐中的落實。如果這個判斷大致不謬,那么,如今進一步積極倡導美育并且切實提高認識,依然是很有必要的,而且應該是首先面對的。就學校教育而言,黨的教育方針中明確指出:“全面實施素質教育,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努力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在德智體美勞“五育”中,對于德、智、體、勞四者的所指及功用,人們——特別是教育者(教師)與受教育者(學生)及其家長,都是清楚或比較清楚的。但是,他們對其中的“美”即“美育”的認識與理解則未必清楚、到位。應該說,這在一定程度上與美育的特殊性有關。與其他“四育”相比較,美育的“特殊性”至少有三點:其一,美育不容易顯示出直接的功用;其二,美育不容易見出直接而顯在的成效性,因為美育屬于情感教育與趣味教育,主要作用于人的心靈世界與人格情操,是內在的、潛移默化的,故而有判斷與言說上的難度;其三,美育的實施方式與過程通常是開放的,與包括德、智、體、勞在內的其他方面交融互滲。這便使人們在認識與理解上相對而言似乎有了些難度,同時也容易有見仁見智的差異。譬如,曾經有一種觀點認為德育中包含了美育,因此無需專設美育。美育的這些“特殊性”,其實在一定程度上恰恰也體現了與美學相關聯的某些特點。
朱光潛曾在《談美感教育》一文中講到德、智、美“三育”之間的關系,以及在當時與之前(20世紀三四十年代)美育的實施情況。他說:“物有真善美三面,心有知情意三面,教育求在這三面同時發展,于是有智育、德育、美育三節目。智育叫人研究學問,求知識、尋真理;德育叫人培養良善品格,學做人處事的方法和真理;美育叫人創造藝術,欣賞藝術與自然,在人生世相中尋出豐富的興趣。三育對于人生本有同等的重要,但在流行的教育中,只有智育被人看重,德育于理論上的重要性也還沒有人否認,至于美育則在實施與理論方面都很少有人顧及。”從文章寫作的時間及背景看,朱光潛所講的是伴隨新文化運動而生的20世紀40年代及之前的中國現代教育中的情況。但在今天讀來,仍覺有一定的現實針對性。這便說明,美育雖然很重要,但是真正做到持續而有效實施其實不易。
進入21世紀以來,在新的生存與發展環境中,當代人面臨諸多新的課題。其中,從人自身的存在方面看,則需要正確認識并努力處理好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以及人自身“靈與肉”這四重關系。借用一個音樂名詞比喻,即如何調適與完成好這“四重奏”且達到“和諧”佳效,越來越重要。當然,這是一個很大的課題,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科學等眾多方面,其中,美育的作用不可或缺。在新的時代,通過大力倡導與推進美育研究與實踐,特別是在學校教育中“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讓受教育者得到全面發展,實現“立德樹人”的根本目標;在更大的社會范圍之內,提升審美世界觀,使人們以更寬廣的胸襟與高尚的境界,以審美的態度對待自然、社會、他人與自身,共享“和諧四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