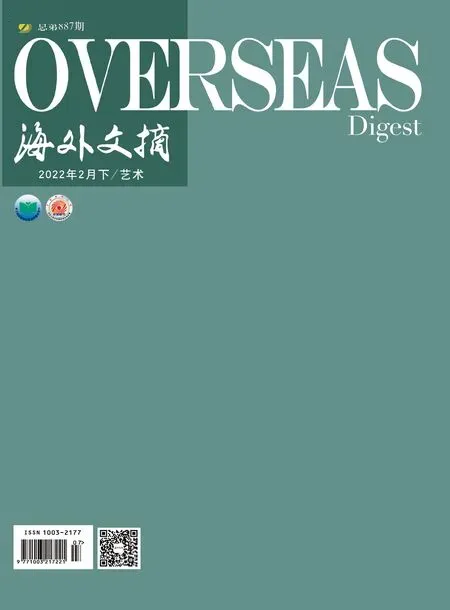教育題材影視劇的現實主義特征
——以電視劇《小舍得》為例
□李征/文
作為聚焦親子關系與教育理念的電視劇,《小舍得》用現實主義的關照視野串聯起豐沛的家庭生活群相,通過對社會熱點的精準透析和教育情境的寫實描摹,全景式地展現了代際沖突、階層差異、職場生態、夫妻關系等多元議題,將升學重壓之下中國家庭的情感矛盾與教育困境集納于熒屏之間,以深刻的藝術視角挖掘內涵深度,以溫暖的社會底色紓解大眾對于教育問題的集體焦慮,進一步拓展了教育題材影視劇的敘事場域,彰顯出現實主義品格特色。
近年來,隨著現實主義題材熱的回歸,以育齡家庭和代際關系為主軸的教育題材影視劇正以高頻的話題熱點、多元的創作類型和溫暖的現實基調切入教育的各個階段,成為現實主義題材創作的新亮點。從直擊高考陣痛的《小歡喜》《少年派》到聚焦海外留學生的《小別離》《陪讀媽媽》,再到以“幼升小”為視點的《學區房》《陪你一起長大》,教育題材影視劇精準契合了社會轉型期大眾對于教育議題的精神訴求,在富有戲劇沖突的影像符碼中透析當代中國家庭的教育現狀和現實困境。
作為檸萌教育“小”系列的第三部,《小舍得》延續了前作《小別離》和《小歡喜》的現實關照性,將創作視線投射于“小升初”的教育戰場,進一步窺探親子關系與教育理念相互羈絆的粘稠之地。全劇選取了三個育齡家庭作為敘事藍本,以六位性格、職業、理念各異的家長構筑交織的人物關系網,將代價關系、師生關系、青少年教育、職場生存等多元議題融于敘事情境,直面現實交困下家庭教育的錯位與偏差。透過家庭生活的橫截面,在與現實主義創作手法的交匯中,完成著對真實生活的鏡像傳達。
1 社會熱點話題的現實聚焦
電視劇“大眾文化”的傳播屬性與根植于戲劇沖突的藝術本體性,決定了現實主義創作必然以呈現影響大眾生活的“社會議題”為己任,而其影像逼真地反映現實的強大功能,也在奠定其與時代同步“在場”的類型意義。《小舍得》充分把握多元語境下紛繁復雜的社會現狀和情感矛盾,通過擷取“小升初”這一敘事場域,將“補習熱”“學區房”“教育內卷”等隱含在時代癥候下的社會熱點與教育問題深度結合,多維度審視中國家庭置身的教育困局,具有很強的現實觀照性。
1.1 與教育政策深層呼應的敘事文本
《小舍得》敏銳地把握教育領域的最新動態和時事新聞,通過虛構的故事情節,將近年來國家針對教育體制改革出臺的一系政策巧妙地縫合進電視劇的敘事文本中,以獨特的觀照視角觸摸教育問題背后復雜的深層肌理。如,班主任張雪兒在開家長會時,將成績單上都貼上了黃色貼紙,切合了教育部新規“中小學不得公開學生個人的考試成績名次”的時政要點;米桃一家作為外地務工人員,可以通過繳納一定年限的社保,讓子女享受就地入學的政策福利;而南儷原本為了孩子的升學大計重金購買的學區房,卻因學區房生源“不看戶籍看學籍”政策新規導致計劃落空;田雨嵐千方百計送子悠去課外輔導班,也因校外培訓機構的治理政策被迫按下了終止鍵……《小舍得》將政策新規、時政要點恰當地融入到了劇情的沖突構建和人物的性格塑造上,有效地強化了現實題材影視劇的政策引導功效,呈現出“與時代同頻”的審美旨趣和現實品格。
1.2 與社會熱點緊密結合的情節刻畫
教育題材影視劇在話題上具有高延展性,它透過家庭教育的多棱鏡,將代際沖突、職場風云、二胎婚育等家庭成員所在的社會關系網,如串珠般連接在一起,深度挖掘熱點事件帶動敘事情節發展。劇中田雨嵐為了專注于子悠的教育,不愿意生二胎,在她急需用錢之際,卻被公公婆婆以借款300萬為由強迫她生二胎;南儷苦戰多年終于坐上了代理市場總監的位置,卻在職場對弈中意外成為了公司明爭暗斗的犧牲品,也暗示著女性職場生態的舉步維艱。《小舍得》充分利用熱點事件呈現出家庭生活和社會關系的多重向度,在全劇的教育困局和倫理糾葛到達頂峰之際,一場與社會時事同步而行的新冠肺炎疫情,也成為了劇中人物關系轉變,情節刻畫的重要節點。全劇精準的抓住與時代并行的社會熱點,營造出真實的話語場域,有力地釋放了公眾對于社會議題的集體情緒。
2 中國式教育圖景的寫實描摹
近年來,教育題材影視劇的敘事時空已由表現師生關系和青春故事的校園空間,轉向探討父母教育理念與行為的家庭場域。家庭空間成了投射青少年成長問題的主要場域,因此以家庭視角為教育破題,是教育題材影視劇對教育生態變化的有力觀照。《小舍得》以“家”為故事基礎,以南家這一大家庭內部失衡的人物關系和情感矛盾為敘事沖突,以三組家庭的教育理念和心理狀態為敘述引擎,通過刻畫富有真實感的“典型環境”和“典型人物”,完成了對當代中國式家庭教育圖景的寫實傳達。
2.1 空間環境的真實營造
典型環境的營造是人物活動與故事建構的基礎。《小舍得》透過精致的細節刻畫,以真實的藝術加工深入挖掘空間造型背后的家庭肌理和生存狀貌。故事開篇,鏡頭就對準了劇中幾組風格各異的家庭居住環境和空間布局。作為大家長的南建龍家是典雅的弄堂小院,從古色古香的文房四寶到簡約雅致的器皿茶具,無一不凸顯著男主人的文人氣息和閑適風格;南儷母親家位于上海的老洋房內,花團錦簇的露天陽臺和素雅精致的沙發桌墊,都映襯出“長公主”的高雅品位和生活習性。而南儷和田雨嵐家則是典型的中產階級家裝風格,時尚的高層住宅,現代化的家居陳設呈現出不同風格的家庭氛圍和藝術氣息。此外,相比明亮開闊的都市洋房,深居于街角巷陌的米桃家的空間結構更令人印象深刻。在市場盡頭公廁旁的水果店,狹小的空間被一分為二,前面用作攤位營業,后面搭建的閣樓則是一家三口的蝸居之地,《小舍得》透過富有差異的空間塑造,勾勒出了市井生活的民生百態。
同時,空間物象作為生活場景的現實依托,已不再是單純的裝飾布景,而作為隱藏于文本中的隱性話語,成為貫穿人物心境的外在投影。以南建龍家為例,擺在南家正中位置的圓形餐桌成為了這個重組家庭矛盾爆發的主戰場。從空間布局來看,餐廳外的各個區域都用玻璃門作為隔斷,在視覺上形成開闊視野又起到遮擋功效,暗含南家人看似團聚實則疏離的家庭氛圍。田雨嵐家開放式的廚房布局和書房設計,也契合了她強烈的掌控欲,便于她在做飯時也能掌握子悠的一舉一動。而鏡頭中反復聚焦的榮譽柜及柜中空缺的位置,更是她高壓式教育的外化呈現。《小舍得》將人物的性格色彩和生活軌跡不著痕跡的滲透在空間造型和細節刻畫上,不斷拓展著影視作品的空間敘事和文化內涵。
2.2 典型人物的自我投射
《小舍得》立足于中國式家庭的教育困境,以精妙的套層結構圍繞一個大家庭中的兩個小家庭展開論述主線,透過典型化的個體敘事尋找共性的社會問題,從情感癥結透析子代教育矛盾產生的深層根基,演繹著現實家庭的生活百態。作為沒有血緣關系的姐妹,南儷和田雨嵐的教育理念互為鏡像。南儷奉行的是“快樂教育”理念,主張讓孩子擁有多彩的童年,即便歡歡的數學成績滑坡至倒數,依舊不急不緩。而田雨嵐則是“雞娃”式教育的典型代表,從吃穿用度到生活習性,從作業習題到校外輔導皆事無巨細。她希望兒子行走在那條她精心鋪就的康莊大道上,把以犧牲孩子娛樂為代價換來的榮譽當成了攀比的資本。于是,在田雨嵐的“高壓式教育”面前,原生家庭的情感傷痛和教育內卷的社會現實,使一向佛系的南儷也不得不卷入競爭的陀螺式循環,成為了填鴨式教育最忠實的擁躉。
《小舍得》以立體化的人物形象,直指兩個身處子代教育焦慮漩渦中的中產階層母親及其母愛異化所引發的悲情現狀。歡歡在南儷應試教育的管控下由童話中的公主變成了任母愛驅使的競爭機器,進而逃離出走。而子悠也在田雨嵐以分數為目標,以愛為名的控制下產生了精神幻覺。《小舍得》將情感內涵細膩的縫合進故事情節、人物臺詞和場景敘事中。當子悠當著全班同學及家長的面,哭喊著“我的媽媽愛的不是我,是那個學習成績好的小孩”時,作為母親的田雨嵐在崩潰大哭后依然假如若無其事地幫兒子打理著一切。這種因教育焦慮引發的母愛迷失之痛和子代隔閡,以強烈的情緒感染力直觀的作用于觀眾的感性認知,構成人物、敘事與觀眾情感的深度關聯,引發觀眾自我投射式的情感關照和身份認同。
3 溫暖現實主義的情感關照
現實主義題材電視劇在描摹社會現實的同時,也承擔著建構時代溫度的重大使命。《小舍得》以問題化的敘事為統領,通過對家庭私域生活的藝術觀照,以痛感現實主義的視角直擊當下教育資源爭奪的殘酷性和代際關系的矛盾與失衡。在多維教育觀念的碰撞下,最終選擇了回歸溫情的敘事理念,柔和代際矛盾與社會痛點,在彼此的和解中完成了父母與孩子的雙向成長,實現了教育題材影視劇對現實生活干預和引導的藝術探索,打造了現實主義精神高地。
3.1 代際關系的呈現與反思
鮑溫的家庭系統理論指出,潛伏于所有人類行為背后的驅動力均源于家庭生活中的暗涌流動,以及家庭成員之間為獲得距離感和整體感而同時進行的推拉作用。因此對于教育題材影視劇的藝術探討,并不是單純由某個社會熱點和教育觀念引發的話題討論,更多的是對于家庭成員背后潛藏的親子關系和行為機制的深度探究。
《小舍得》中的每一個人都是帶著“創傷性”經驗的主體。南儷的痛苦在于原生家庭帶來的情感痛點,父母的離婚和田雨嵐母女的突然闖入,打碎了她完美的生活。理性上,她并不認同田雨嵐用揠苗助長的方法培養出來的兒子,但感性上,她卻不能接受教育背景、社會地位皆不如她的田雨嵐能教出比她優秀的下一代,于是她錯誤地陷入了搶跑教育的誤區,始終圍困在攀比和失衡的心靈困局。相比南儷,田雨嵐更加陷入了原生家庭帶來的情感裂痕和性格缺陷。從小跟著單親母親長大,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直到高中母親與南建龍的結合,她才獲得了遺失已久的父愛。但親生與非親生的界限還是在她的心里扎下了深深的烙印,這種長久以來的敏感和自卑成為刻進她性格里的顯性符碼,于是培養一個成績優異的兒子變成了她揚眉吐氣的唯一希望。因而她與南儷的競爭與攀比,歸根到底還是困囿于性格中的自卑與不安。此外,在關注中產家庭的精神危機外,作為外來務工人員的米桃父母也在“咱們家跳出農門,可就指靠你了”的言語期許中,帶給了女兒無形的現實重壓和心理負擔。
除了對家庭關系的拆解和反思,《小舍得》通過對三個孩子的細膩關注,讓整部劇回到了對教育主體的深刻關切。劇中刻畫的夏歡歡、顏子悠、米桃是三個成長背景、性格特點各不相同的孩子。但相同的是,他們都在父母“唯分數論”的教育準則下,產生了由沉默到隱忍再到集體爆發的情感抵抗。無論是子悠站在講臺上哭訴母親的真實感言,還是歡歡因為受到打壓教育而對同學進行排擠孤立,抑或是米桃指責收入微薄的父母“為什么你們就這么沒用”,這些現象直指錯誤的教育理念對兒童內心所帶來的巨大傷害,折射出家庭、兒童、社會之間生態失衡的現實痛楚和深刻反思。
3.2 當代教育的凝視與思考
教育內卷,已經成為轉型時期中國社會的一個不爭的事實。《小舍得》在溫暖現實主義的基調下,通過三組育齡家庭在教育焦慮和倫理糾葛中呈現的集體性癥候,鋪陳出不同形態的家庭結構和教育方式,將教育話題的探討推向更深視角。全劇對不同層面的教育理念進行了細致梳理,涵蓋家庭層面的育兒沖突,教師執教理念上的分歧,學校與校外培訓機構的對立,以及不同家庭的階層差距等諸多問題,由此折射出了社會進程中代際沖突、城鄉差距、婚姻家庭等多元價值觀的相互角力。在現實主義的審美關照下,將目光投注于被家庭、學校、課外機構三方教育勢力合圍下的孩子的心靈時空,于凝視和思考中探尋著教育的精神實質。
“星光灑滿了所有的童年。”故事開篇在歡歡稚嫩的童聲中便點明了整部劇對孩童成長的美好希冀。《小舍得》在“舍”與“得”這樣一種悖論性命題中觸碰情感的傷痛,也傳遞出了發人深省的價值內涵。劇中的家長們在釀成苦果的邊緣終于幡然醒悟,在“舍”與“得”的抉擇中做出權衡,打破了“唯結果論”的教育死結,走出被教育焦慮裹挾的“囚徒困境”。三組家庭也在“對立—沖突—和解”中修復了各自的親子關系,重拾教育的初心。《小舍得》以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在龐雜繁蕪的現實困境中升起直抵時代重心的旗幟。希望通過一種溫情現實主義的情感力量,給觀眾帶來心靈上的撫慰和價值取向上的引領,并試圖提醒人們,摒除“唯分數論”的教育痼疾,尊重青少年的個體差異,守護孩子的身心成長,才能回歸教育的真正要義。
4 結語
在日趨多元的文化語境下,現實主義不僅是一種美學理想,更是一種樸素真摯的生活態度。秉持著現實主義品格創作出來的優秀作品,不僅能成為書寫時代變遷、社會發展的熒屏鏡鑒,也能通過寫實手法的視聽傳達,將觀眾帶入視聽影像建構的情感氛圍中,形成推動時代進步的精神力量。《小舍得》以現實主義的創作態度和洞察教育的人文底色,囊括了時代性話題和藝術訴求,以多樣化的個體敘事深入透析中國式家庭面臨的教育困境與倫理沖突,以互動的群體關系反映社會變革中多元價值理念的沖突和追求。通過對當下教育病癥的剖析和審視,呼吁全社會樹立正確的教育觀念,構建家庭、社會、學校三者之間和諧健康的教育生態鏈條,提升了教育題材影視劇的現實主義品格和價值內涵。■
引用
[1] 許婧.探析近年來我國電視劇對“家”的多元呈現[J].當代電視,2020(6):49.
[2] 王珍妮.現實主義手法對當代家庭題材電視劇的重構與表現:以《小歡喜》《小舍得》為例[J].視聽,2021(8):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