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可喜,亦可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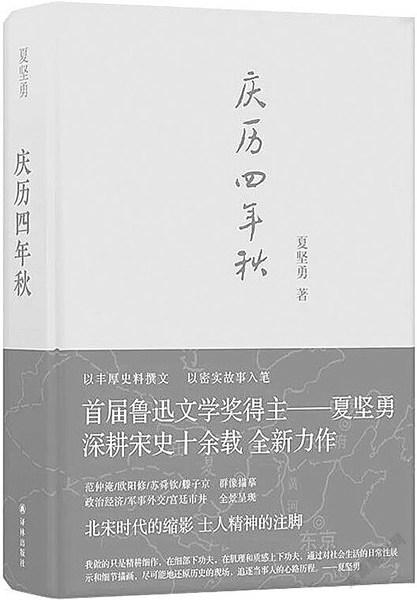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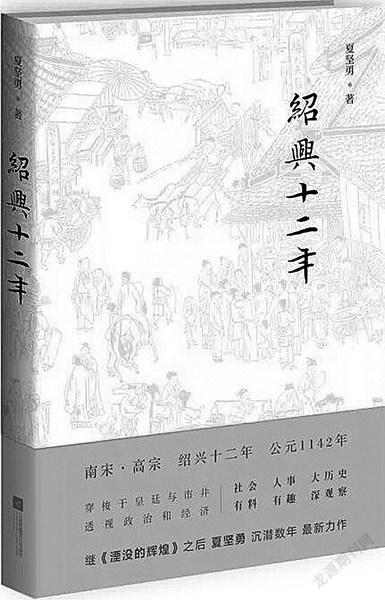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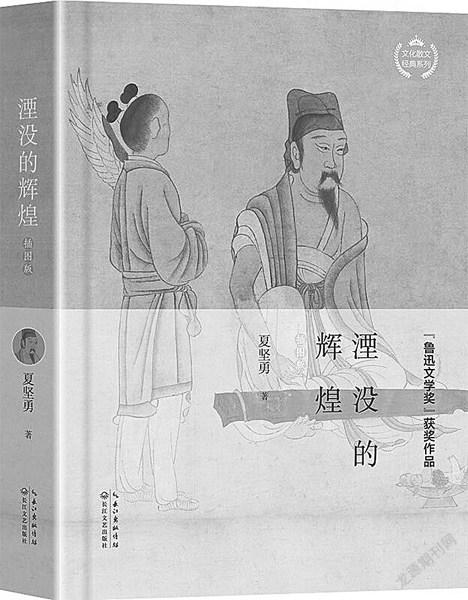
一、住進宋朝的身體
夏堅勇長久地浸淫于宋史。自《紹興十二年》以來,他的目光一直停留在宋朝,在宋朝的上空來回移動,在汴京和臨安之間左右徘徊。夏堅勇的宋史敘事是倒敘的,《紹興十二年》先去到臨安,《慶歷四年秋》從臨安回到汴京,《承天門之災》目光又稍稍前移,注目于宋仁宗之前的宋真宗:趙恒。
事實上,宋朝處于中國古代歷史的轉折點上,是一個值得敘寫,同時也有可能去深入敘寫的朝代。這從前人對于宋朝的評述中就可見一斑。陳寅恪認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后漸衰微,終必復振”①。嚴復曾在寫給熊純如的信中說:“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②對于這樣一個“造極之世”和“最宜究心”的朝代,作者的目光怎么會輕易離開呢?同時,宋史本身史料豐富,敘事詳盡,雖然錯訛很多,但仍不失為究人心世變的優質研究樣本。對于這樣一個可以在其間悠游馳騁的優質樣本,作為歷史散文作家的夏堅勇又怎么可能視而不見呢?怎么可能錯失一個可以“在自然、歷史和人生的大坐標上尋找新的審美視點,也尋找張揚個體靈魂和反思民族精神的全新領地”③的機會。
確定了寫作的“領地”,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寫。
夏堅勇對于什么是好文章有自己的認知。“散文是一個作家綜合實力的較量,這中間包括作家的生命體驗、人格精神、知識底蘊、藝術感覺和營造語境的文字功力。所謂‘綜合不應理解為工匠式的拼接和堆砌,而是一種詩性的重塑,有了這種重塑,散文才能在‘力和‘美兩方面皆鋒芒畢露,并走向各自的極致。”④這里所謂的“綜合”對于創作過小說、劇本等多種文學樣式的夏堅勇而言可謂駕輕就熟,他可以從容地調動多種敘事手段駕馭各種修辭融入他的歷史敘事中。“詩性的重塑”則是他的自我要求和藝術自覺。在其歷史散文作品中,他切實地將他對于好文章的認知兌現到他的寫作實踐中。
在夏堅勇關于宋史的歷史文化散文里下過兩場雪:一場下在《紹興十二年》的文末,另一場下在《承天門之災》開頭。這是兩場極具功能性的雪。
紹興十二年(1142年)的那場雪雖然下在文末,卻儼然是夏堅勇寫作《紹興十二年》的起點。開端從結尾處開始,在“紹興十二年的雪停了嗎?”⑤的發問所營造的氛圍中回溯《紹興十二年》中的人與事。
景德四年(1007年)的那場雪下在了《承天門之災》的開頭,這場雪下得很是生動而有興味:
景德四年冬天的第一場雪,比往年來得要晚些。
雖說姍姍來遲,卻并不是蓄謀已久的樣子,反倒顯得有點隨意,早晨還是很明朗的天色,到了小晌午說變臉就變臉。雪花剛飄下來的時候,似乎還有點試探的意思,但轉瞬間就紛紛揚揚地肆虐開來。攪得天地間一片混沌。大街上的人都顯得很狼狽,到處是抱頭鼠竄的身影。但畢竟是入冬后的第一場雪,氣氛終究還是歡樂的,即便是逃亡,也是歡天喜地的逃亡。慌亂者當然也有,例如在皇城前橫貫內城的東西大街上,那就真的是兵荒馬亂了。⑥
這場雪下在宋真宗景德四年,但分明像是下在了夏堅勇的眼前。在雪的“姍姍來遲”又“不是蓄謀已久”,“隨意”“變臉”又充滿“試探”,以及人們“抱頭鼠竄”的“慌亂”中,作為敘述者,夏堅勇仿佛站在歷史的現場,看著紛紛揚揚的雪和四處逃竄的人。有情緒的雪和活動著的人,讓筆下的寫作對象生動起來,這是夏堅勇敘述歷史的方式和歷史敘述的主要通道。他在敘述中首先將自己拋入歷史,住進宋朝的身體里旁觀歷史。此刻,他立定在景德四年開封的東西大街上,四處游走,表情嚴肅但并不慌亂。這還只是開始。他俯瞰京師,潛入王宮,跟隨真宗的東封、西祀的隊伍……以全知的視角關注歷史人物的言行,站在人物身邊感知他們的情緒和內心活動。甚至在文中以“現場紀要”(戲劇)的方式重現歷史現場。他在“現場紀要”的結尾處解釋說:“采用這種筆法并非故弄玄虛,而是為了保留歷史現場的直觀性和鮮活感,為后世立此存照。”⑦他充分調動和運用自己所有的敘述工具和手段重新回復歷史現場中的場景,實錄人物的行動和表情,任意指摘和品評人物,各種慨嘆更是層出不窮。從中可以看見敘述者所處的位置和張揚的敘事立場。
錢鍾書曾在《管錐編》中指出:“史家追敘真人實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理。蓋與小說、院本之臆造人物、虛構境地,不盡同而可相通。”⑧這里面有幾個層次:首先得是真人實事;其次是以事實為基礎,設身處地地體察、想象和揣度,使之符合人情義理;最后是非虛構與虛構之間既有區別又有相通之處。正如浦安迪在《中國敘事文學批評理論初探》中所說:“在中國敘事傳統中,無論歷史還是虛構,訴諸筆墨的便是真實的,要么忠于事實,要么忠于生活。”⑨忠于事實和忠于生活指向的都是一種所謂的歷史真實,一種有別于紙面記錄的——將歷史回歸到人的日常情感和行動——從紙面復活的實然的歷史。綜合運用非虛構與虛構的敘事手段,共同抵進歷史現場,重建失落的歷史真實。
同樣,夏堅勇的歷史敘事有別于歷史學家的敘事之處并不在于發掘歷史,發現歷史的隱秘,而是著意于理順歷史的經絡,深入歷史的細部,將自身對于生命情感的體察注入歷史的肌體中,填補歷史行進過程中的耗損,恢復歷史肌理的彈性,讓歷史盡可能生動起來。在作者筆下,歷史風云中注入了人間煙火,歷史不再冰冷,失溫的歷史重新恢復了體溫。
當然,夏堅勇這種綜合性的敘事方式并非獨創,在中國敘事史上亦有跡可循。他的歷史文化散文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中國史傳散文的傳統。產生于百家爭鳴中的戰國文章即雜糅了多種敘事手法,并不是單純的記錄歷史。“《戰國策》,既載史事,又雜縱橫,分析形勢,指陳利害,‘亦可喜,皆可觀最能代表戰國文風的特色。”⑩戰國文章又深刻影響了司馬遷,“《史記》一書綜合了戰國文章的許多特點,也可以說集戰國散文藝術之大成”11。魯迅所謂的“無韻之離騷”,即就《史記》的藝術表達和藝術成就而言。可以說,夏堅勇的歷史敘事方式可以追述到《戰國策》和《史記》的寫作路徑,只是他似乎走得更遠,也更加“任性”。如果說戰國文章是思想自由的產物,夏堅勇歷史敘事的成功則首先得益于其敘事方式的自由。對比夏堅勇的“任性”,歷史學家的歷史敘事就顯得有些“忸怩”。特別是在歷史學家將歷史作為一門科學看待之后,歷史學家首先將自己的歷史敘事套上嚴格的敘事枷鎖,然后不斷地試圖在其中突圍,引發各種歷史敘事轉向的努力,甚至放棄敘事,將事件的歷史過渡到結構的歷史,但同時又禁不住文學敘事的誘惑。在論及同樣是敘事的小說和歷史時,羅蘭·巴爾特認為“敘事并不一定是一種樣式法則……作為小說和歷史同時具有的這種敘事形式,一般來說仍然是一種歷史契機的選擇和表達”12。夏堅勇當然不會在意歷史學家們的敘事困境,也不會拘泥于虛構與非虛構之間的糾纏。他從自身的積累和認知出發,選擇符合自己的敘述方式,在歷史中狂飆突進,將歷史進程涵化入敘事進程,進入歷史學家們未曾抵達的地方。在歷史的觀念之外,重塑歷史本體。章學誠說:“古人文成法立,未嘗有定格也。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事,無定之中,有一定焉。”13文無定格中呈現出一種新的敘述的詩學和敘事正義。錢鍾書曾引用英國詩人亞歷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詩作《論批評》(An Essay on Critism),其中有這樣的論述:“規矩拘縛,不得盡才逞意,乃縱心放筆,及其至也,縱放即成規矩。”14夏堅勇在其“縱放”的敘述中為歷史散文的書寫探索或創立了新的“規矩”和法度。
二、不斷傾斜的身體
夏堅勇歷史敘事的方式是“任性”的,他的“任性”意在恢復歷史的人性溫度。有溫度的歷史易于感知,沿著生命情感的流動的路徑,歷史的理路也逐漸清晰起來,呈現出不同的歷史景觀。于是我們看見那個同樣顯得任性的主人公在歷史的路途中歪斜著的身影。
“一個任性的角色,可以變成行動的中心,統領整個敘事”15,宇文所安在《敘事的內驅力》一文中將這種類型的敘事稱為“中心敘事”。宋真宗在文中無疑就是這樣一個處于敘事中心的角色。他以太宗第三子的身份繼承大統的過程充滿戲劇性。由皇位繼承的邊緣人不期然站立到舞臺中央,“燭影斧聲”中長大的真宗身影踉蹌,內心惶恐。在登上皇位之后回憶往事時,仍然心有余悸,“當此時,朕亦自懼”16,心中無疑留下不小的陰影。
真宗朝處于宋朝的歷史過渡期,“澶淵之盟”則可以說是真宗朝的分水嶺。在訂立“澶淵之盟”的過程中,真宗的身影是遲疑的,御駕親征的車駕往北,他的身體始終側向南方。對于“澶淵之盟”態度前后的轉變則可以看出他身形搖擺,心無定見。“澶淵之盟”以及之后對于西夏的招撫消除了宋朝的外部威脅,宋朝獲得了長久和平發展的局面,與此同時,矛盾也轉向了內部。對于“澶淵之盟”的不同解釋,再次在真宗的內心投下陰影,直接引發了后來東封、西祀等神道設教的大戲的依次上演。
身形的踉蹌和搖擺都是宋真宗內心世界的陰影和變化在人間的顯影。
《傳習錄》中記錄了如下問答:
問:“身之主為心,心之靈明是知,知之發動是意,意之所著為物,是如此否?”
先生曰:“亦是。”17
身、心、知、意、物之間的聯動過程,生動詮釋了人類社會實踐的一般過程。宋真宗的行為當然也服從這個聯動過程,但“心之靈明”的缺失導致了他行動的走向發生了偏移。
“一國君臣如病狂然”18,《宋史》如此形容真宗朝“澶淵之盟”之后的時代,并對此感到驚奇。夏堅勇則將之視為一場災難。“病狂”是表征,“災難”則是就后果而言,是就同一個事件兩種不同的視角。前者描述表象,后者則看到了其內在的悲劇性。兩者相互聯結,就是人的病癥引發了災難,一場假天之名的人禍。歷史拋給了真宗機會,但他以一場鬧劇來回應。
說到底,這場綿延了整個王朝災難的始作俑者,是居于事件中心的“官家”——那個特地詢問過“官家”由來的——宋真宗。“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19皇帝始終居于王朝的中心位置,是聯結上天與天下的唯一樞紐,代天牧民。這是作為皇帝所應具備的倫理外觀。真宗十分看重“皇帝”至高無上的倫理外觀。“澶淵之盟”后,兩個皇帝的出現打破了皇帝唯一性的外觀。為了修補這一缺憾和維護皇權的正統及其權威,真宗執意于選擇引天命以自重,假天意以正名,無限擴張儀典的工具性,以虛擬的盛德裝飾虛假的冠冕。日益生長的碩大冠冕不相稱地覆蓋在他“瘦小”的身影之上,搖晃的是整個天下,傷害的是那些歷史中的失語者和失蹤者。在整個過程中真宗的身影偏離了位置,完全喪失了他作為皇帝所應具有的政治德性。“所謂政治德性就是某一政治角色的品質,在實踐意義上政治德性要求追求且只能追求該政治角色的內在利益,而這種內在利益只能通過政治實踐本身獲取。一言以蔽之,是其所應是,為其所應為。”20真宗偏離治理天下的軌道,在欺瞞天下的歧路上一直走到人生的終點。天下關懷停留在口頭上,“寧計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21。他始終行進在神化自身的途中,整個王朝則在他側滑的身影里負重前行。
在真宗傾斜的身影中,我們可以看見他如何精巧地周旋于王朝的關系網絡中,看見他的怕與愛、隱忍與執著。他持久地沉迷于神道設教之中,其內心的虛弱和孤獨躍然紙上。一個具有生命情感的人連同其內心的隱秘被從皇帝的名位和歷史的故紙堆中活生生地拖拽出來。在這里歷史不是觀念,不是理念,它回到人間,在人的身影晃動和情感流動中呈現出其本來的面目。“歷史知識的詩學回答政治或天真或野蠻之提問:要如何給予國王一個好的、科學的死亡?”22夏堅勇在其敘述中所要呈現的是一個皇帝如何生動又不那么體面地活著。當然也包括那些在歷史中曾經存活過的人,他們曾經如何活著。在這里,人跳脫過往歷史的言說結構在敘述中顯形。
三、在敘述的途中
真宗費盡心機假造天書,終以天書殉葬,所有任性的作為輕易地消弭于歷史的風煙之中。作者綜合各種敘事手段,將一系列看似離散性的事件析分成多個敘事單元,以細致的筆觸,生動完整地呈現了整個鬧劇的全過程。敘寫一場鬧劇,荒謬在敘寫真宗傾斜的身影的途中不斷顯現,荒謬背后的邏輯也在過程中被揭示出來。“當作為過程的實在變得清晰,一條意義的路線出現在歷史中。”23在作者精心而肆意的敘述過程中,意義自然生成,作者的反思也呈現在敘述的途中。
這場災難是一個時代的悲劇,但并不僅僅為一個時代所特有。作者在文末提及“某種精神基因”,除非基因編碼發生突變,不然無論善與惡,將始終留存在遺傳的鏈條之中,從過去指向未來。歷史始終在過去與未來之間,在過去與未來之間建立起一種連續不斷的連貫性。歷史慨嘆的聲響不僅來自后世,比如作者以《承天門之災》重述真宗的荒誕作為;也在歷史深處回蕩,比如趙壹曾在《刺世疾邪賦》中悲嘆:“勢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芻。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24跨越千年的時光,世界呈現出一樣的荒謬,似乎“某種精神基因”是我們揮之不去的宿命。令人沮喪的是,盡管我們可以清晰地認知到這種連貫性,但似乎很難克服這種沒有任何新意的歷史反復。歷史在重述中醒來,又于瞬間歸于沉寂,如此反復。夏堅勇行走在敘述的途中,他在當下以自己的方式重述歷史,言說過往,指向未來。歷史始終處在重述的途中,重點是我們將一直呼喚那種“亦可喜,亦可觀”的敘述。
【注釋】
①陳寅恪:《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載《金明館叢稿二編》,生活·新知·讀書三聯書店,2001,第277頁。
②嚴復:《與熊純如書》,載《嚴復集》第三冊,中華書局,1986,第668頁。
③④夏堅勇:《自序》,載《湮沒的輝煌》,東方出版中心,1997,第2-3、4頁。
⑤夏堅勇:《紹興十二年》,《鐘山》2014年第3期。
⑥⑦夏堅勇:《承天門之災》,《鐘山》2021年第6期。
⑧錢鍾書:《管錐編》第一冊,中華書局,1986,第166頁。
⑨浦安迪主編:《中國敘事:批評與理論》,吳文權譯,上海遠東出版社,2021,第381-382頁。
⑩112124劉盼遂、郭預衡主編:《中國歷代散文選》,北京出版社,1980,前言第3頁、前言第3頁、411、412頁。
12羅蘭·巴爾特:《寫作的零度》,李幼蒸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第28頁。
13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中華書局,1985,第508頁。
14錢鍾書:《管錐編》第三冊,中華書局,1986,第1193頁。
15宇文所安:《他山的石頭記——宇文所安自選集》,田曉菲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第83頁。
16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二,至道三年十一月甲子條,中華書局,2004。
17王守仁著、王曉昕譯注:《傳習錄譯注》,中華書局,2018,第118頁。
18脫脫等:《宋史·本紀第八·真宗三》,載《宋史》第一冊,中華書局,1985,第172頁。
19文瑩:《湘山野錄》,中華書局,1984,第45頁。
20亓同惠:《什么是政治德性》,《讀書》2019年第1期。
22雅克·朗西埃:《歷史之名:論知識的詩學》,魏德驥、楊淳嫻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第49頁。
23埃里克·沃格林:《天下時代》,葉穎譯,譯林出版社,2018,第276頁。
(李祥,《鐘山》雜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