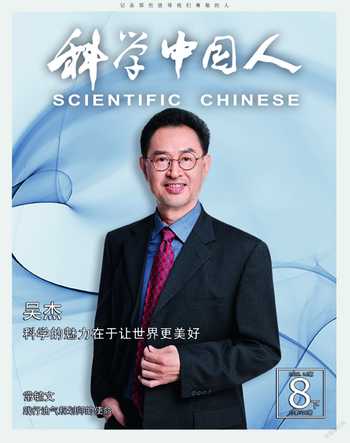情牽氣象 循夢而行
肖貞林
青藏多寬谷,高原多湖泊,青藏高原多故事。
大約6500萬年前,印度板塊與亞歐板塊出現了一次快速而劇烈的碰撞,可以說青藏高原及一系列的山脈就是這次碰撞的產物,這些由于大陸擠壓而抬高至不同高度的地面,在其后的數千萬年間各自展現著不同風貌,也由此孕育出了我國的大好河山,一條源遠流長、波瀾壯闊的黃河更承托著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燦爛文明。事實上,這片地勢高險的“不毛之地”,其實對我國有著不可磨滅的重要意義。因而,它的每一次氣候變化,每一次“呼吸”,都如一泓春水,一旦有風過,便會漣漪乍起,攪動著每一位氣象研究者的心,來自浙江大學地球科學學院的副教授田榮湘自然也不例外。
防災比救災重要
近年來,最牽動田榮湘心緒的氣候現象,當數2009—2014年間,禍及中國西南五省(自治區、直轄市)(即云南、貴州、廣西、四川及重慶)的一場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災,俗稱“西南大旱”。西南地區位于青藏高原的東南側,這便使田榮湘產生了探索青藏高原氣候變化與其周邊地區氣候相關性的想法。恰巧,在我國正式啟動第二次青藏高原科學考察期間,她隨即迎來了重大專項中的子項目“西風-季風變化背景下地氣相互作用過程在不同下墊面的長期變化趨勢”。在項目中,她和團隊聚焦被反氣旋控制的高原冬季,發現一旦反氣旋現象減弱,青藏高原東北部冷空氣也會隨之乏力,致使西南地區“陷落”進青藏高原南面暖空氣的控制之中,造成干旱現象。而對此成果,她直言:“探明其中機制只是項目的第一階段,如今第二階段的研究即將開啟,青藏高原的熱力動力變化對周邊地區氣候的重要影響仍然不可小覷。”
干旱如此,赤潮亦是如此。這種突發于海上的“紅色幽靈”一直被視為海洋污染的信號,它可導致海洋中的魚、蝦、蟹、貝類大量死亡,對水產資源破壞極大,嚴重時還會因沉積物的大量堆積而影響海港建設,為漁業、養殖業、旅游業均埋下了不小的危機。而令人感到遺憾的是,此種災害不可預防,因其形成機制極為復雜,目前學術界還未對其發生機制達成一致的認知,但目前可以明晰的是,要形成赤潮,必不可缺少鐵、錳、鋅、鈷、硅及維生素B1、B12、四氮雜茚、間二氮雜苯等成分。那么,這些營養元素又從何而來?
這個疑問曾一度盤桓在田榮湘心頭,揮之不去。為探索問題的答案,她親率團隊謹慎調查分析了此前15次大型赤潮事件,她發現氣溶膠,即懸浮于氣體介質中的固態或液態顆粒所組成的氣態分散系統,在“營養輸送”的過程中似乎有著非同尋常的相關性。“在2005—2006年間曾發生過15次面積大于500平方公里的赤潮事件,其中只有1件跳脫出了研究預設的規律。我們之前習慣于認為河流是輸送營養物質的首要載體,這似乎將我們的思路桎梏住了。但其實這并不代表其他介質就沒有輸送物質的可能,比如大氣。”有此設想,她第一時間找到了自然資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的專家進行討論與咨詢,但出乎她意料的是,這一設想并未在第一時間得到肯定與支持。但這并未使田榮湘感到氣餒,在博士導師翁煥新教授的指導與鼓勵下,她最終成功申報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大氣氣溶膠輸送鐵磷對引發東海赤潮的關鍵作用”。
此項目將東海列為主要研究對象。東海是世界著名的漁場,在我國的經濟和民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赤潮事件卻嚴重威脅著東海生態系統和區域經濟,這令田榮湘寢食難安。項目開展期間,她及團隊運用了前沿的大氣數值診斷模擬技術與生物地球化學研究方法,創新性地將天氣動力與環境科學兩個學科的思路加以結合,最終找到了大氣氣溶膠對鐵、磷的輸送、沉降與引發東海赤潮的關鍵作用。原來,大氣中的酸化作用可使氣溶膠中的鐵、磷元素從不溶態變成生物可利用的形態,其后隨著下沉氣流輸送到洋面,而此種空氣的下沉運動同時會帶來晴朗的天氣條件,這就為赤潮藻的生長提供了充足的光照,再結合東海洋流方向隨季風改變從而提供的水動力條件,就“順其自然”地促使了東海赤潮的發生。
此研究成果顯然為海洋赤潮災害的預報提出了一個有效的跨學科研究方法,同時為探索赤潮災害發生機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對降低赤潮災害的損失、保護海洋生態環境具有重要意義。“防災永遠比救災重要。”田榮湘說。
科研的傳承
不是只有舞者才會穿上紅舞鞋,從此曼妙旋轉,不知疲倦。在天氣動力及環境科學領域內默默耕耘、執教近三十載的田榮湘腳上,必定也有這樣一雙“紅舞鞋”。不然,她不會說出“我覺得科研是越干越有勁兒”的“豪言壯語”,更不會多次奔赴擁有極端環境的珠穆朗瑪峰及阿里地區,頂著高原反應開展科學實驗,終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科技部第二次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研究子專題、浙江省自然科學基金、“973”項目和其他各類科研項目11項,以及在國內外權威刊物上發表論文33篇的杰出成績。
回顧自己的科研道路,縱然已涉足其中數十載,但談起少時對科學的向往,田榮湘依舊心潮澎湃。兒時在媒體上看到眾多科學前輩的光輝事跡,使田榮湘在對科學的神秘燃起好奇的同時,也在她心中種下了一顆立志成為一名科學家的夢想種子。本科期間,推導大氣運動的方程組深深吸引著她的目光,不竭的進取之心最終將她推向了天氣動力學的懷抱。雖然方向已明,但彼時青澀稚嫩的田榮湘尚不能領會科研精神背后蘊含的真正含義是什么。
立足當下,田榮湘說:“我曾經在導師高由禧院士的身上切實感受到了堅守的力量、奉獻的大義。始終以國家需要為己任,時刻準備著奔赴科研一線,這是高先生用畢生經歷為我上的最生動的一課。”
20世紀80年代末,畢業于中國科學院蘭州高原大氣物理研究所天氣動力專業的田榮湘師從我國著名的高原氣象學家高由禧院士。彼時距離高院士自愿舍棄在首都中央氣象研究所工作的大好前途,為改變我國西北干旱面貌,帶領一家老小遷往尚未開發的甘肅貧瘠地區,已經過去了30余年。為增加河西走廊的供水,高院士曾在“融冰化雪、土炮消雹”中建立起了中國科學院蘭州地球物理所分所(蘭州高原大氣物理研究所的前身),而當田榮湘來到這里時,研究所已在高院士的主持下不斷完善和發展,他本人也在步履未停中漸漸走入了晚年。“但在我的記憶中,高先生仍然堅持身體力行地參與科研工作,并且始終告誡我們,科研要從需求出發,國家哪里需要,我們就隨時要做好奔赴哪里的思想準備。”
“直到現在,我還會時常把前輩的事跡講給我的學生們聽。”弦歌不輟,薪火相傳。曾經將一腔熱血傾注于三寸筆尖上書寫青春年華的有志青年,如今已成長為了一名可為后繼人才指引前路的“明燈”。
談起自己的學生,田榮湘眼中滿是驕傲與欣慰,“現在的年輕人,真的都很聰明”。即使在成長的道路上偶有叛逆,她也愿意作為學生身邊包容而和藹的“大家長”,悉心傾聽他們的煩惱,真誠給出自己的建議。“其實很多學生在逐夢路上都會因為迷茫而出現一些‘暫時的困惑’,這時候就尤其需要一些‘過來人’為他們指點迷津,不能任由那些負面情緒控制住他們,讓他們產生對知識的厭惡情緒或者是對學習的抵抗行為。”
春風化雨潤桃李,一束燭光照赤心。未來,田榮湘將繼續向著科學之光輝,循夢而行,無論是科研的“高原”還是育人的“珠峰”,她都會心懷希望,穩步攀登。
(責編:關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