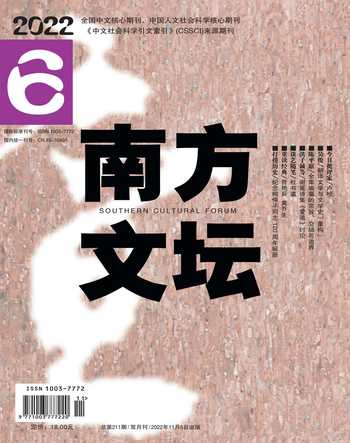盧楨印象
一個人來到一座陌生的城市,最先感受到的是絲絲縷縷的新奇——沒錯,穿行在陌生城市的街道,感受它的植物、建筑,它的口音、食物,它的風情、民俗,那種由生疏造就的錯位感會逐漸彌漫成一種美學判斷,進而這判斷又衍生出強烈的對比:這座城的樹比那座城的樹木品種更繁多,由于經緯度差異,花期更為漫長復瓣多于單瓣;這座城的食物也比那座城更斑駁,除了海鮮,更有名揚四海的包子、麻花和炸糕;而語言是更為特殊的比對,那座城的口音宛如平劇念白,這座城的方言則有種單口相聲般的幽默……然而時間久了便默念起那座城的好,那里有穿開襠褲一起長大的損友,有戀愛時常去的老電影院,還有孩子出生的產房……
在這座城,我的作息極為規律乏味:早餐、菜市場買菜、讀書、午餐、寫作、晚餐、散步、讀書……日復一日中,內心那種叫孤獨的東西開始叫囂。在那座城,時常跟一幫狐朋狗友胡吃海喝,那種墜入塵世的快感讓我對這世界抱以熱望敬畏,也讓我遲鈍的末梢神經變得敏銳,而在此城,世界鮮亮陌生如初誕,別說找朋友聊聊小說,連個喝酒的朋友都沒有。
有一天,楊慶祥忽然跟我說,天津有位叫盧楨的批評家,酒量不錯,你們有空了可以小酌。說實話我很驚訝,不曉得慶祥如何曉得我內心的想法,不過,身邊有個能說說話、喝喝酒的朋友于我而言是件多么美好奢侈的事。我很快加了盧楨的微信。過了段時間,我們欣欣然約好去吃涮羊肉。出發前我問,你喝白酒還是啤酒?他大大咧咧地說,都行。他回答得那么干脆,絲毫不拖泥帶水,不禁讓我刮目相看。大多數酒友回答起這樣的問題都會比較謹慎,一般如是回復:一、白的;二、啤的;三、啊,我酒量不好,喝茶就好。而盧楨如此坦誠的回答有兩種可能:一是他酒量委實不錯,葷素不濟,大概是酒中高手;二是他性格直爽,心思單純,根本沒想那么多。
那天中午我隨便點了幾瓶啤酒。由于初次見面,開始都有些意料中的拘謹。他看起來虎頭虎腦,目光明朗,像個在讀博士。閑聊中我才知曉,他既是一個六歲男孩的父親,也是一位高校教師。他說話的聲音是那種典型的播音腔,清亮,尾音又不經意間甩出本地方言獨有的語氣助詞。當他微笑著注視你講話時,你會感受到一種無端的信賴。那天我們委實沒喝多少酒,我們像相識多年的老友般講述著各自的人生經歷,講述著對于詩歌和文學的種種看法。我才知道,他上大學時就寫過一部長篇,博士畢業入職南開后專事詩歌研究,同時又閱讀了大量當代經典小說。當我們談起彼此的朋友時發現,竟然交集頗多。這種交集讓我們之間由于時光和空間造成的距離又拉近了一些。當我們在小酒館門口揮手告別時,我由衷地感謝起慶祥的美意。沒錯,他不光給我介紹了一位酒友,也給我介紹了一位可以談天說地的哥們。
慢慢就熟了起來。人和人的相識就是如此,有的見了一面便覺得話不投機,氣息也未契合,便不會有交集,身居同城卻老死不相往來;有的則一見如故交往頻密,不過隨著時間的流逝也漸行漸遠,怕也不是老杜所言的“交情老更親”;還有一種便是,縷縷續續的往來,清淡卻并沒有疏遠,松閑時小聚一番把酒言歡再各自分散,兩下歡愉。和盧楨的交往便是后者。有時寫小說到了傍晚,一時興起想小酌兩杯,便臨時約酒。除非夜間有課,盧楨總是欣然前往,更多時候,他帶著孩子奔走在前往輔導班的途中,手機里他氣喘吁吁地說,楚哥,等把孩子送回家,立馬就過去……他向來言而有信,喝酒也仍那般淡然,不搶酒,不拒酒,端端正正坐在那里,面帶微笑聽我講述小說創作的細碎感受與困惑。間或他會直接表達一下自己的觀點,但并不強迫我接納或認同。這時他身上那種豁達忠厚之氣便緩緩彌漫開去,讓我不得不挺直了腰身。沒錯,他身上的確有一種平普中正的氣質,這氣質除了與兒時的家教有關,怕更與他在南開大學的求學之路和導師教誨有關。
漸漸地,相聚次數多了些,朋友也多了些。他會帶同門的師弟來喝酒,師弟們的酒量都不錯,人也都亮堂實誠,到了最后,酒通常會被全部干掉,我也通常會醉掉。有幾次清晨醒來,望著窗外的陽光,實在想不起如何回的家,便打電話問他,他笑著說,是我們打車把你送回去的。他的聲音那么坦然,沒有善意的嘲諷,也沒有故作的愧疚,坦坦蕩蕩,仿佛我也是他的同學故友。這讓我內心涌蕩起小小的感慨。他倒是極少喝醉,通常情況下,他不會比我們少喝,或者說,他比我們喝得都多,可他總是酒桌上唯一保持清醒的那位。如此看來,他是天生的好酒量。酒量好,不張揚,也不虛與委蛇,當真是難得的好酒友了。我時常產生一種錯覺,他似乎就是我家隔壁那個眼瞅著長大的男孩,謙遜有禮,可這謙遜有禮并非出于禮儀或教養,更像是一種天生的親和力。有一次席間他去洗手間,不小心將一摞文件刮到地上,我幫他撿起來,原來是一份申報資料,順勢掃了兩眼:
盧楨,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入選天津市宣傳文化“五個一批”人才,天津市“131”人才,天津作協簽約作家。曾獲天津市第十屆“文藝新星”稱號,天津市教育系統“教工先鋒崗”先進個人稱號,全國微課程大賽一等獎,天津市青年教師教學基本功競賽一等獎,南開大學“青年崗位能手”……曾赴香港浸會大學、荷蘭萊頓大學、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做訪問學者,利用假期走訪80個國家,出版有暢銷書《旅行中的文學課》……
這時我才意識到,這個看上去樸素厚道、做事坦蕩的年輕人,這個時常跟我們默默喝酒、從不打通關也從不大聲喧嘩的小伙子,原來是位難得的學界才俊。跟他交往了近兩年,他從來沒有談起過自己在學術上的建樹,也從來沒有炫耀自己的師承,他只是大大方方坐在那里,安安靜靜地陪著我們喝酒,一點都不像個桃李滿天下的名校教授。或許正是他如此的性格,我們小小的酒局才不斷誕生吧?相逢意氣為君飲,系馬高樓垂柳邊,也許,會這樣一年一年喝下去吧?
前些日子,我準備離開這座城,回那座城小住。臨行前盧楨與師弟為我餞行,還拎著兩瓶極好的酒。我說,這么好的酒,留著,咱們喝二鍋頭就挺好。他笑著說,再好的酒,自己喝不如跟朋友一塊喝。
我覺得他說得挺對。他是位值得信賴的酒友。
(張楚,天津市作家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