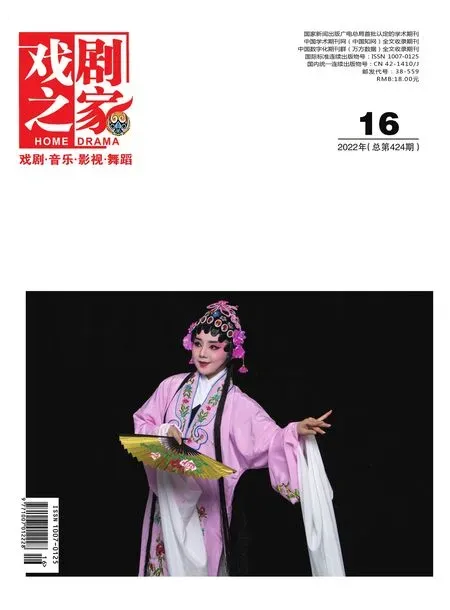從敘事走向奇觀
——查崔查勒姆·堯克爾電影作者風格分析
譚悅茗
(北京電影學院 北京 100091)
查崔查勒姆·堯克爾(1942 年11 月29 日—),泰國導演。1942 年出身于一個電影制作家庭,60 年代曾于美國接受電影教育。70 年代初開始電影導演創作至今,共導演作品32 部,拍攝類型豐富,包括社會問題劇、史詩片、青春片、科幻片等,技法上更偏向好萊塢式現代電影語言。其創作大致歷經兩個階段——20 世紀70、80 年代,堯克爾以拍攝“現實主義浪潮”的社會問題劇為主;進入泰國電影“新時期”,則投入的史詩片創作。
一、奮力抗爭的“異化”主題敘事
1970 年代的十年被稱為靈魂追尋的時代,青年一代開始研究自己的身份和周圍的社會。與其他地區的學生一樣,泰國學生使用流行文化作為媒介來表達自己的思想觀念和立場,電影就是他們的媒介武器之一。青年導演們也紛紛開始認識到泰國電影對現實社會的反映與呈現上的不足。一股要真實表現現實生活、揭露社會弊病與矛盾、揭示泰國國民精神狀態的“現實主義浪潮”在電影界興起,一大批反映泰國人當下生活與種種社會問題的電影不約而同地涌現。而堯克爾便是泰國現代社會評論電影的主要導演之一。堯克爾王子以自己的視角來觀察、理解社會表象,拍攝了一系列聚焦鄉村農民與城市底層貧民的命運、揭露都市犯罪、反映社會腐敗的影片,成為現實主義風潮的代表性導演。70 至80 年代,他拍攝了刻畫社會“黑暗面”的作品,包括描寫家庭危機的《可汗醫生》(Dr.Karn,1973)、批判司法缺陷的《公民:出租車司機》(Citizen:Taxi Driver,1977)、反映社會不公的《槍手》(Gunner,1983)等等。
在現實生活中長期失語的城市邊緣人,成為20 世紀70 年代至90 年代中期堯克爾電影中繞不開的“主流”人群。與傳統腐水電影(NamNao,英語為stinky water)對情節的重視不同,社會問題劇里的人物不再埋沒在情節中,而是凸顯出來,主角的精神世界成為主要描寫對象:貧困與失業狀態下,面臨生存的極端困境,個人的尊嚴被迫成為犧牲品——是維護公共利益卻繼續貧窮,還是為了自身利益而犯罪?影片將社會問題道德化,呈現出一代人的道德焦慮,并借此對社會體制的缺陷提出了“個人看法”,包括家庭、媒體、執法部門和司法體制的失德等等。堯克爾在客觀、甚至殘酷地呈現社會系統性困境的同時,也賦予平凡人以暗含的悲劇英雄屬性。《公民》、《公民2》、《宋斯瑞老師》(Somsri,1986)中的城市底層貧民,雖然身處不同的時代,但他們舉手投足間淳樸的秉性,真實、頑強的生命力,以及一種平和的定力,或多或少都滲透出濃濃的鄉土味道。面對普通人的經歷,堯克爾電影有著沉重的無力感,又具有深切的悲憫心。
堯克爾的代表作電影《公民》的靈感來源于堯克爾的街頭觀察,他在咖啡店看到一位出租車司機正愛惜地清洗著自己的汽車,這讓堯克爾意識到,這位司機的汽車實際上不是汽車,而是他的未來。故事講述了一名名叫杜蓬(Thongpoon)的出租車司機被都市所異化、吞噬的故事。杜蓬原是位于泰國東北部的烏隆他尼省(Udon Thani)的農民,他帶著兒子諾(Noi)來到曼谷定居,他用五年的積蓄買了一輛出租車,成為了一名穿梭于街頭的出租車司機。但不幸的是,他先是因為出租車被盜而失去了唯一的生活來源,接著又被攆出了棲身的貧民窟。他想找回自己的出租車,卻遇上了一個盜車團伙。走投無路的杜蓬憤怒地報復盜車團伙的頭目,最終因違法被關進了監獄。杜蓬這一角色鮮明地表現出堯克爾電影中“錯位公民”的形象。電影中,有不少鏡頭都表現出杜蓬身上困獸猶斗、身不由己的“異化”感。失去了棲身之所后,杜蓬一手牽著兒子,另一只手提著一個行李包離開了貧民窟。嚴酷的氣氛在他走出街巷之后變得更為強烈。當他走出窄巷斜坡,一排排單調而逼仄的房屋象征著都市對人的壓迫和異化,將他緊緊困在鏡頭的中間,正面鏡頭里,畫面中的杜蓬猶如籠中困獸,被嚴實地夾在銅墻鐵壁之間,觀眾的觀影情緒也在此時被調動,感受到了人物內心的壓抑與困頓。
這一時期,堯克爾所創作的社會問題劇的影像風格整體還是質樸寫實的。無論是人物造型、臺詞、場景或道具的設置,都力求對泰國現實生活做高度還原。為了增加現實題材的真實性,20 世紀70 年代,他是僅有的使用同期聲的泰國電影制片人之一。電影《公民》使用的是100%的拍攝過程中錄制的“真實的聲音”,而非后期錄音。同時在多數電影人使用唱片音樂時,堯克爾的作品都堅持使用原創音樂。因而他不僅在題材內容與視覺風格上有所突破,也是泰國電影產業化的有力推動者。但影片的視聽語言并沒有局限在寫實的層面,由于堯克爾對社會犯罪主題的關注,堯克爾對視聽語言的設計也借鑒了黑色電影、犯罪片的類型視覺風格,營造出一種粗糲現實中又帶有一定情緒性與寫意性的影片氣質。如他經常運用傾斜的構圖或暗黑的影調營造出不安與危險的氣氛,或是借助鏡頭的平移或縱深運動表現出人物細膩的情緒變化。
由于商業利潤的主導性因素,這一時期泰國電影市場主要還是拍攝能夠迎合觀眾口味、能給人們一時精神安慰或鶯歌燕舞類的影片,現實主義電影并不是當時泰國電影的主流。從80 年代中期開始,由于泰國政局逐漸穩定,民主政府也開創了經濟發展的新局面。受社會變化的影響,電影業也開始出現轉變:一是當時外國發行商不再抵制美國電影,好萊塢電影開始重新占領泰國市場,同時受到電視等新興媒體的沖擊,泰國本土電影數量不斷萎縮;二是隨著家庭電視的普及,泰國電影觀眾的主流群體正在發生更迭,都市市民群體,尤其是都市年輕人取代廣大農村觀眾,成為觀影主力軍。
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社會問題電影的生存能力受到了極大的影響:自80 年代起,制作量就持續下降,到1986 年幾乎完全停止。整個80 到90 年代,社會問題劇導演處于失語狀態,只有堯克爾仍在從事社會問題電影的制作,而他對這一類型的堅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特殊的皇室背景。但迫于市場壓力,堯克爾的創作方向也基于時代做出一定的調整:其一,城鄉二元對立被更寬泛的道德沖突所替代,社會文明與自然文明的關系成為新的題材;其二,日益嚴重的青少年犯罪問題成為新的靈感來源,促成了青少年電影與現實犯罪題材結合的第二波熱潮。
電影《馴象人》(The Elephant Keeper,1987)講述了馴象人布頌(Boonsong)在非法走私人與執法者的斗爭中,失去了心愛的大象,最終被迫離開家鄉的故事。影片中自然界的一切美好,都與都市所攜帶的“原罪式”的種種社會問題形成強烈的對比——影片中的大象蘊含著自然的靈性,馴象人身上也散發出淳樸與平和的生命定力,兩者相互包容的詩意圖景,曾經是田園牧歌最好的寫照,也是富有人文氣息的泰國文化的寫照,其內里蘊含的是一套根植于農業文明與佛教信仰、呼喚與自然平等和諧相處的生命邏輯。而在城市化與工業化的大規模侵擾之下,這樣的靈光與圖景正被迫走向消逝。堯克爾也借影片的結尾給出了自己的立場:布頌不得已帶著妻兒前往城市謀生,在路上,布頌仿佛又聽到了大象一聲又一聲的呼喚,布頌噙著淚水念著大象的名字,與它道別。即便現代化的進程不可逆轉,堯克爾還是在電影中對能與現代性異化相抗衡的自然之美做出了毫無保留的贊美。
1995 年,堯克爾王子著眼于泰國市場,拍攝了青少年犯罪問題電影《女兒》(Daughter,1995)來調整自己的創作風格。《女兒》是以偽紀錄片的形式拍攝,講述了一群吸毒成癖的少女的故事。影片以這些少女和她們的父母接受采訪作為貫穿線索,延展出四個家庭的悲劇圖景。這部電影取得了商業上的成功,并制作了續集《女兒2》(Daughter 2,1996)。堯克爾對墮落的青年女性群像的塑造準確而又觸目驚心,也讓觀眾對悲劇背后現實與家庭的原因有了更深入的體察。
二、史詩神話的“奇觀化”轉型
如果將電影分為奇觀和敘事兩個方面,那么堯克爾1999 年以前的作品大體上可以劃為敘事電影的范疇:影片依照敘事的要求來結構,展示情節、塑造人物、編寫對話是影片的核心。
新世紀的到來,經濟全球化浪潮已將人們卷入消費社會的潮流之中。消費社會帶來的“不僅僅是社會經濟結構形式的改變,也是一種整體性的文化轉變”。這種整體性的文化轉變預示著視覺文化的興起,彼時電影界也正在悄然興起一股追求視覺沖擊的“奇觀化”熱潮,全世界內的電影都呈現出這樣一種趨勢。九十年代起,針砭時弊的現實主義創作群體就逐漸走向失語,堯克爾也開始尋求自身的轉型。面對世紀末的經濟震蕩,堯克爾亦轉變姿態,拍攝了一系列以王室英雄作為主人公的史詩大片《暹羅皇后》(The Legend of Suriyothai,2001),以弘揚泰國民俗文化。此后他又拍攝了《泰王納黎萱》(The Legend of King Naresuan:Hostage of Hongsawadi,2006)、《泰王納黎萱2》(The Legend of Naresuan:Declaration in Independence,2007)等塑造皇室英雄的一系列作品,均取得相當的票房成績。
《素麗瑤泰》講述了泰國民族英雄——泰國皇后素麗瑤泰救國救民的英雄事跡,《泰王納瑞宣》系列則講述了泰國民族英雄——泰王納瑞宣帶領暹羅軍民多次抗擊緬甸入侵的故事。從《素麗瑤泰》到《泰王納瑞宣》系列,堯克爾的史詩電影幾乎記述了泰緬戰爭的歷史全過程,堪稱一組阿瑜陀耶王朝由建立到衰亡的影像編年史。對于史詩片而言,按照事情發生、發展和結局的時間順序來敘述故事有利于展現史詩片宏大敘事的優勢,但主題意識的膨脹,甚至是功利主義的隱喻或說教,必然會導致一定的藝術缺失。堯克爾的這一系列史詩片無一例外,都在試圖表現“民族—宗教—國王”立國三原則,反而遮蔽了歷史的本相與人物的個性,限制了歷史片的藝術表現。影片把國家的興亡歸結于主角的先知與大度,無疑使敘事顯得過分粗糙,簡化了歷史的復雜性,從而失去神話史詩題材應有的宏大敘事魅力。
隨著視覺文化的興起,堯克爾開始更加重視電影的商業性,并致力于提高影片的藝術水平和制作規模,可以說是在有意識地強化影片的商業特征。他遵循電影的商業操作原則,形成了具有泰國本土特色的類型片制作方式。首先,相對于其他類型,史詩片非常討巧,它的題材與主題賦予了史詩電影可“討好的商業元素”。史詩片中的神話敘事往往能契合一個國家群眾的民眾心理,能較強地調動國家的民族自豪感,因而相比起其他類型,史詩片更容易在國家范圍內打破類型影片的受眾限制,即使影片層面存在著這樣或者那樣的缺陷,觀眾也會更樂意花錢去觀看這種“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的大制作影片。在故事層面上,區別于過去現實主義創作,堯克爾的史詩電影強調民族英雄的傳奇經歷的塑造,以及唯美愛情支線的整合,以形成一種類似于好萊塢類型片的程式美學。同時,這類史詩片追求壯麗的視覺奇觀,在王室高預算的支持下,影片中大量運用數字動畫與特效技術,創造出了令人震撼的視聽效果。也正是因為這些新程式,使泰國電影在后來,尤其是在“新浪潮”運動進入第三階段之后越來越朝著類型多元化的方向取得了豐碩成果。
但值得注意的是,優質的奇觀電影往往建立在整個行業的高度工業化之上,而泰國在當時并不具備完善的民族電影工業體系,以至于高額的項目預算導致2012年堯克爾被中央破產法院裁定破產,并被置于絕對接管之下,這使他進行中的泰王納瑞宣續集也被迫終止。
三、結語
政治動蕩的20 世紀70 年代,堯克爾作為“現實主義”浪潮的代表人物,秉承著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關注泰國本土的現實問題,同時又融合了西方類型化的視聽語言銳意創新,透過社會問題的表面,描繪出“鄉村-都市”式沖突下的現實故事,最終觸及泰國傳統價值何去何從的主題核心。進入新世紀,視覺文化時代下現實主義創作逐漸走向失語,面對世紀末的經濟震蕩,堯克爾亦轉變姿態,拍攝了一系列以王室英雄作為主人公的史詩片,作品獲得泰國國內的高票房,重新呈現出對民族話語權強烈爭取的姿態。因此無論是堯克爾還是他影片的主題都涉及同一個問題:一個人如何適應自己所處的環境?正如他自己所說:“我拍電影的哲學是我不試圖改變世界,而是展現世界。”而隨著世界的改變,堯克爾也不斷轉變自己的立場,適應著時代的滾滾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