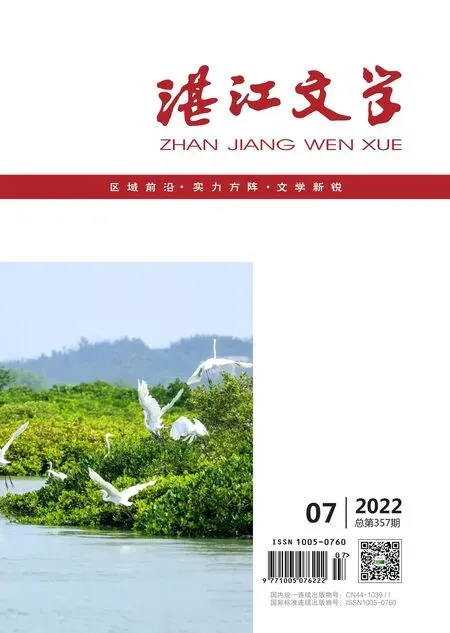一抹霞光染樟腳(外一篇)
◎ 林登豪
位于八閩大地的惠安、泉港、仙游交界的樟腳村,是閩地泉州市泉港區西北角一個偏僻的山村。樟腳村匯集著百余座色彩斑斕的古民居,曲曲折折的石板路上常常響起一陣又一陣尋幽探奇的足音。這個小山村搖身變成了“油畫村”“攝影村”,每年來這里采風的畫家、攝影師、驢友不計其數,福建省攝影家協會在此創建了攝影基地。
一座偏居山隅的小村落,緣何聲名鵲起——
2003年,土生土長的攝影家章先生拍攝的一張樟腳村的照片,在全國攝影大賽上榮獲大獎。之后在省內外的報刊雜志上發表,漸漸地令地處僻遠的小山村聲名遠播,吸引了無數的藝術家和驢友紛至沓來,與其親近和對話,成為啟發創作者藝術靈感的源泉。
古老的石頭房,古樸的民風,遠古的習俗,令樟腳村散發出濃郁的文化氣息。空閑時光來這里轉悠、轉悠,享受閑云野鶴般的悠閑,感受鄉村的寧靜與淳樸。哦!樟腳村,一座頗具特色的村莊,一幅悠遠寧靜的田園風光,給來訪者烙下新感覺。
從324國道泉港區段朝陽公路往里走六七公里,經過土型村,沿著蜿蜒盤旋的山路,到達了樟腳村,映入眼簾的是半山坡上一層層上下重疊、一幢幢首尾相連的“石頭厝”,儼然是一座古城堡偶現崢嶸;登高遠眺,疑似暗合奇門的石房陣。村子里全是石頭壘砌而成的古厝群,因村里有株700多年的大樟樹,人爬到樹上俯瞰,村子如在腳下一般,樟腳村也因而得名。
我放慢腳步,慢慢地游移著目光,生怕一不小心步入迷途,也怕驚動屋脊上那只在陽光下起舞的大蝴蝶,還不忍擾動倚著門前瞧著我的小狗及草叢里趴窩的母雞;更不忍心驚動:墻根曬著太陽瞇著雙眼養神的老人。村里長輩說,清代康熙年間,他們的先祖從外地遷徙至此;嘉慶年間,民居陸續興建。如今,古厝以磐石般的信念佇立了200多年。
在石階前,我與巧遇的曾姓老阿婆閑聊。她告訴我昔日為了建這些房子,先人在四周群山中覓到巨石掘出后,在山坡上挖一處大坑洞,用柴火燒了幾天幾夜,直把石頭煅軟切割后,肩挑背扛至山下,砌起石頭厝。古宅房間往往選擇在離地兩米左右的方位,門口的石梯從石墻里伸出的條石構成,或由片石從地上壘砌到門口,樓上住人,既防潮又可避免蚊子、老蛇干擾,樓下作儲藏間。比起土木結構的房子,它冬暖夏涼,清幽素雅。小鄉村背面幽幽的山坡上,是誰用卵石壘疊一層又一層的梯田,穿插中間的彎彎曲曲小徑闖進我的視線,夢幻出當年先民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歸的山水田園畫。
這些悠然的民居,墻上石塊相扶相嵌,上下布局講究,戶戶石階相連。一座座古民居大小不一,墻面的山石形狀各異,陽光輕輕一拍,色彩更鮮明,在時光的打磨下,溢出古色古香的情致,堪稱一絕。
古民居的墻石色彩依然油潤,被歲月沖刷得平滑光潔的石階,斑駁的門檻,或灰白或烏黑的梁木瓦片,銹跡斑斑的鐵鎖,爬滿墻角和屋頂的藤草……而今,平靜的古宅群中不時響起陌生人的腳步聲……犬吠聲常常從寂靜的石巷里傳出。
走進這一片全是石頭壘砌而成的古屋群里,歷史的厚重感彌漫在空氣中。墻上的石卵、石塊,都是鐵紅色的風化石。房子依山就勢而建筑,上下左右都不講究布局。不少人家,同座房子里從此房到彼房,還得上幾級石階。戶與戶之間,都有臺階相通。這里的房屋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窗戶少,并且都偏小,應該是為了防盜的。同一座房子里,卻一定要在前房與后房之間留下一道窄窄的露天巷道或小天井,為的是有利于通風和采光。
古民居中最為壯觀和堂皇的應數“瑞峰樓”。它位居山村的高處,有兩層樓房,統一用亂石塊砌成,整幢樓房三面壘石到頂,只在二樓正面墻上留三個小窗。大門由精雕的輝綠巖方塊石壘成拱形大門,門楣上嵌有“瑞峰”的匾額,落款為“清嘉慶四年乙未中秋”字樣。這座樓的底部墻寬一米,二層最窄處也有七十多厘米。樓內兩邊上下各有三個房間,后邊是小廳,中間是一個大天井。這種構造,與漳浦的土樓有點相似。可惜的是,一場大火過后,這座建筑精美的房子已經面目全非了。
穿行在卵石砌成的石巷里,兩邊的墻壁伸手可及。層層疊疊的石頭之屋錯落有致,狹窄的石巷經過雨水的沖刷,石梁上留下的印記,給石屋增添了幾多的滄桑。歷經時光的洗禮,石墻呈現出紅褐、灰白、藏青的色澤,在朝陽夕輝中,那么絢麗、繽紛,猶如童話般的空間。
樟腳古民居雖是簡陋,卻不簡單,粗獷卻不粗俗。不簡單的是它的顏色,不粗俗的是它的氣質。
我走到一個小岔口,一轉身,幾處青灰石的殘垣斷壁和老宅子出現在眼前,最東側的是陳平山故居,這幢兩層石頭屋里還住著一戶同族的宗親。斑駁的墻體和壘疊的石頭間,夾著快脫落的灰舊砂漿。二樓是陳平山的臥室,通向二樓的石階,已被塵土覆蓋,不再光滑如昔。
當年,陳平山就是沿著一層又一層的石階,堅定地走向革命征途。
陳平山,字震寰,1904年出生于樟腳村,1925年臘月,他從黃埔軍校第五期步科畢業,參加了廣州起義,不幸頭部負傷。1926年加入共青團,同年轉為中共黨員。1928年,黨組織派陳平山回福建漳、廈一帶從事地下工作;次年夏天,在晉江、南安、惠安等地準備舉行惠安暴動,任中共泉州特委軍委書記、福建省紅軍惠安總指揮部總指揮等職務。
1931年1月7日,陳平山接莆田特委的通知:迎接特委和紅軍教導隊進駐三坪地區開辟游擊根據地。他立即從仙游園莊趕回涂嶺,途經寨后村苦鳥籠灣時,遭遇當地軍閥收買的黃耐榮、陳密、蔡進水、蔡申生刺殺;他奮起拼殺,無奈人單力薄,身中數彈,壯烈犧牲,年僅26歲。
得知陳平山犧牲的消息后,黨組織和當地群眾深感痛惜和憤怒。次日,涂嶺區委負責人吳國珍、農民自衛軍陳俊臣等帶領武裝隊伍,在擁護革命的鄉親們主動協助下,一舉處決了兇手陳密、蔡進水、蔡申生(黃耐榮逃亡),為獻身革命事業的烈士討還血債。雖然陳平山血灑故土,卻為家鄉的窮人指明了一條光明的大道。
樟腳古民居的顏色五彩繽紛,一塊塊石頭在陽光下閃現各異的顏色,一堵堵墻壁呈現著鐵紅色、藏青色、淡黃色、紫褐色、灰白色、黑黛色……四堵墻一合圍,你就被視覺疲勞了,好像一下子什么顏色都沒有了。然而,再站遠一點,黑色屋頂宛若給石頭厝戴上一頂U字形的帽子,每幢房子的墻壁也呈現出不同的顏色。你看,山腳下靠路邊的房子,橘黃摻雜著栗色;旁邊以暗褐色為主色調,摻雜些許淡灰的房子。層層疊疊的古民居折射出迷人的色彩,幻變出一幅獨特的立體油畫。月光中的古民居,雨中的古民居又該如何?我也沒親眼見過,連攝影作品也未見過。
飄拂著神秘披風的樟腳古民居,它的品格是樸實堅韌的。這里的房屋鮮見梁和柱,難得一見的梁與柱也是由石塊壘成,然而,它的肢體卻柔中帶剛,別舉一格的滋味。仔細一看,每堵墻都由無規則的一塊塊石頭構成,大的攜著小的,小的墊著大的,它們中間并無太多的黏土,似乎每塊石頭之間還在透著風,每座房子還在喘著氣……但是,這些雜亂無章的石頭卻被墻之形狀給框住了,這些形狀有的是長方形,有的是三角形,還有的是梯形。
古民居的房屋最多砌到兩層,形狀不一的窗口鑲嵌在墻上,似一只只不甘寂寞的眼睛不停地凝視故土。在那陸續建成的房子里,歷經幾多的往事——有新婚燕爾的喜悅,有衰老病死的悲傷,有數代同堂的幸福,還有生兒育女的歡樂……櫛比鱗次的石厝,互相簇擁依偎著,竊竊私語不停。窄窄的巷道首尾相接,迂回的石階使石房連成一體。曲徑通幽處,墻體斑駁成圖案,墻角還吐出一撮撮、一片片毛茸茸的苔蘚,把一道絢麗濃厚的色彩涂抹得很寬、很倩、很養眼……仿佛人在桃花源中。
石墻的縫隙里泛出青綠的苔斑,使得巷道的空間陰仄而清幽。陽光只能打在高高的屋脊上,少許的光線漏在墻垣上,與幽暗的巷道對比,形成上下截然不同的空間。這里巷道連著巷道,岔道連著岔道,頗有迷宮中的神奇。
穿梭在奇妙的石厝中,雙腿疲乏了,便坐在村邊亭中的石椅上,泡一杯樟腳紅茶,趁熱呷上一口,一股獨特滋味的口感滑過舌尖,回甘清甜醇厚的韻味,香氣直透丹田。那種通透之情與君難說清。手端一杯紅茶,眼觀石壘古厝,坐看云起云散。
春節前后,一年一度的油菜花又盛開了。樟腳村20余畝的花海也迎來最旺盛的風采,田邊地角青連著青,綠疊著綠,綠還馱著黃,一片片,一壟壟,撐破了多少春江水。輕一些,再輕一些,別打擾了春之夢!田壟中金燦燦的油菜花與斑駁的古民居相映成趣,橙黃的花事開得如此多情,令踏青者過目之后心跳不已。正月十五的元宵節,扁擔燈全村相接,延綿數里,為山村幽雅的風景畫龍點睛,堪稱一奇,令人大飽眼福。
徘徊在大山懷抱中的石壘古民居,只覺得歷史就在我們足下……
千年湛藍抱銅山
漫步在銅山古城墻邊的大道上,一連串的疑問追尋來了:銅山就是銅山島嗎?銅山島就是東山縣嗎?
銅山地處閩粵之間,它猶如航空母艦,或漂泊于閩地,或漂泊于粵所,曾為一島兩屬。早在秦代,秦始皇平定百越,建南海郡,銅山劃入秦朝的版圖;到了東晉時代,建義安郡綏安縣,銅山也在其中;隋代之時,綏安并入龍溪縣,銅山又隨之并入該縣;到了唐代垂拱二年(686),銅山屬于漳州下屬的懷恩縣。唐開元二十九年(741),由于懷恩縣并入漳浦縣,銅山也就屬于漳浦縣了。到了明代嘉靖九年(1530),東北角的銅城,既是軍事重鎮,又是人口密集地區,就劃歸漳浦縣;其他的地方,因詔安建縣而劃歸詔安縣。
進入銅山北面的九仙山,銅山水寨闖進我的視線。歷史曾記載,銅山水寨是閩海五大水寨之一。明代初期,此山不但是軍事要塞,戚繼光、鄭成功曾屯兵設防;而且又是秀麗的風景區,如今已被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九仙山山勢險峻,曲徑縈紆,榕蔭蔽日,郁郁蒼蒼。半山腰碩大的古榕下,有長年不涸的“燕泉”,雖是匆匆路過,我的心扉綠意卻悄然綻放。不遠處又有幾棵大榕樹相為鄰,棵棵盤根錯節,長須垂掛,仿佛聽到它們輕盈的呼吸。
沿著明代開拓的“石磴云梯”登頂。此梯僅有數十級,蜿蜒在巖隙間,石階又陡又窄,勇往直前者,只好手援鐵欄桿,氣喘喘而上攀。回首一望,石壁上鐫刻“必喘”二字,果真道出此時登攀人的神態,大有畫龍點睛之效果。
視野豁然開闊,只見山頂有一天然石洞,取名“銅山石室”,為東山八景之一。該室由幾塊巨石合攏而成,室內清爽幽靜,閉目養神,思絮活躍,令人浮想聯翩——該有人在此隱居過吧?佇立石洞前,我極目遠眺:帆葉過后,浪花起伏,長堤一線,沙灘燦黃;大海中峰巒聳立,云霧飄浮,漁村散落,千舟待發。山下聳立九層的華福酒店,俏麗的高樓與悠遠的山峰竟秀,是誰與大自然共同創造了過去與未來?
一座聲名四播的山,難免留下不少名人的蹤跡。明嘉靖五年(1526),福建右參政蔡潮巡海留住銅山,在九仙山留下“宦海恩波”的摩崖石刻,這四個大字落筆端嚴,沉渾敦實。明萬歷三十年(1602),水師提督施德政率軍渡海到澎湖與倭寇激戰,勝利歸來之時,特在山上擺宴慶賀。席間,他揮毫寫下三百多字的《橫海歌》,并鐫刻石壁之上,歌詞滿溢壯士豪邁之氣,彌漫平倭戰績顯著的喜悅之情。明代武英殿大學士黃道周的《銅山室記》,暢敘此山:“壁立南向,下俯十仞,雖井泉未回,洞壑簡鮮,亦靈宰所直,宿真人之游邸也。十仞之下,舊環諸剎,鐘磬余鏗、浮于木末。左裂石竇,飛泉下滴,夏冬不枯……”稱贊九仙山可以與蘇州的虎丘山斗美。
明萬歷九年(1581),戚繼光派遣浙江義烏軍450人鎮守銅山,設把總一人,時稱“浙江營”,負責協調銅山至懸鐘、詔安、鳳山等地軍隊同心協力抗擊倭寇的入侵。明萬歷十年(1582),戚繼光特意來銅山巡察海防詳況。南明永歷年間,鄭成功曾把銅山作為屯兵,募兵,練兵,造船的軍事基地。山上尚有鄭成功練兵的水操臺。1982年在銅山石室內發現一塊《仙嶠記言》石碑,高171厘米,寬69厘米,碑文記載南明永歷六年(1652)鄭成功部將洪旭、張進、甘輝等43人捐銀修建觀音堂紀事。1661年,鄭成功收復臺灣時,銅山五百多名熱血的青壯年,隨其渡海作戰,出生入死。收復臺灣后,他們又為臺灣的安定與開發,作出不少的貢獻。屹立山巔,我凝視臺灣海峽,一股浩然之氣回旋胸膛,不知不覺地涌出文天祥的《正氣歌》: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
下山的半路上,居高臨下的我發現離古城墻不遠處有一巨型俊俏的巖石,一打聽,才知道它就是赫赫有名的東山風動石。
矗立在海崖上的奇石高四米多,寬有四米有余,重達200噸,似巨桃斜倚。《東山縣志》記載它“卓立于磐石之上,四面皆空,兩石相接,間不數寸,風至則動……”這奇石與臥地的磐石吻貼面只有二十幾厘米,每當海風勁飚,巨石搖晃欲墜。我站在巨石的側面,它峭立的方位僅是幾寸方圓的凸型且光滑的磐石,真令人驚奇,拍掌稱絕;我站在它的背面,只見它懸吊藍天白云間,天地雖寬闊無垠,唯恐它一不小心跌倒,自家性命難保;我轉了一圈站在它的正面,在巨石陪襯下,自己一米七的身高卻成為“侏儒”,腦海掀起沖擊波,浮躁靈魂有所沉淀……
明萬歷年間,督撫程朝京和詩人李楷,仰慕風動石的盛名,專程前往一賞。接待的官員在巨石下設一宴席,酒足之余,靈感勃發。李楷借景抒情:鬼斧何年巧弄丸,鑿得拳石寄層巒。翩翩陣陣隨風漾,輾轉輕輕信手摶。潮撼孤根危欲墜,雨余蒼蘇秀堪餐。五丁有意留奇跡,特為天南表大觀。程督撫應聲和之:文昌祠邊大石球,神仙蹴戲靈山頭。萬夫欲舉移不動,天風撼之動不休。五丁欲舉難為力,一卒微推不用餐。鬼神呵護誰能辟,動定機宜在此觀。吟唱音調剛落地,猛然一陣海風勁吹,巨石搖晃劇烈,似要墜落,滿座文武官員皆驚,人人自危,倉皇避之。這次衍生的有驚無險之舉,給后人留下“石下難設宴,吟唱不出三”的傳奇。
1918年2月13日,銅山發生7.3級大地震,接踵泥石流突然暴發,山石滾落,房舍倒塌,人員傷之,惟有風動石輕輕松松地點了幾個頭,依然屹立磐石上。
據傳:當年,侵華的日本鬼子動用軍艦的鋼索圍糸風動石。妄想將巨石拉倒,結果是猴子井中撈月一場空。著名女作家霍達的《奇石記》曾描述:凜凜然大節,中華民族,一山一水,皆有此無上尊嚴!據有關材料顯示,我國風動石屈指可數,惟有銅山風動石最險峻、最獵奇。科普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地理之最》,稱該石為“天下第一奇石”。
風動石宛若巨人,坐在海崖上,洞察銅山的是是非非,時光打了幾個盹,古城也感覺到地老天荒的分量。
在風動石幾十步開外,就是大名鼎鼎的關帝廟,由南面關帝廟入口處北望,有巨石如和尚躬身合十,是引人遁入空門嗎?
這天然巨石,高約四米,形狀猶如身披袈裟的僧人,虔誠地匍匐在地,俯首彎腰屈膝,合掌揖拜東門嶼上的文峰塔,巧成絕妙奇景——石僧拜塔。東門嶼的文峰塔,是巡海道蔡潮明嘉靖五年(1526)建成的,是用花崗石砌成八角七層的實心塔,為這一帶海域航行的標志。此石又被稱為“禮僧石”。銅山的晚清詩人、書畫家馬兆麟先生,曾做《五律·石僧拜塔》,詩曰:“怪石立山門,歸然道貌尊;折腰如合什,低首卻忘言。發禿寒花白,襯衣緇蘚皴,九年面壁者,應是汝前身。”
做為過客,也感覺到銅山的古樸中浸染了幾多的現代氣息。古城墻、九仙山、俏石頭使人沉醉視覺盛宴中,更令心海悸動和震撼,悄然于城垛邊,抬頭仰望,長空慢慢地延伸浮動的湛藍;低頭俯視,大海緩緩地深邃跌宕的湛藍;瞬間,連傳說與典故也湛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