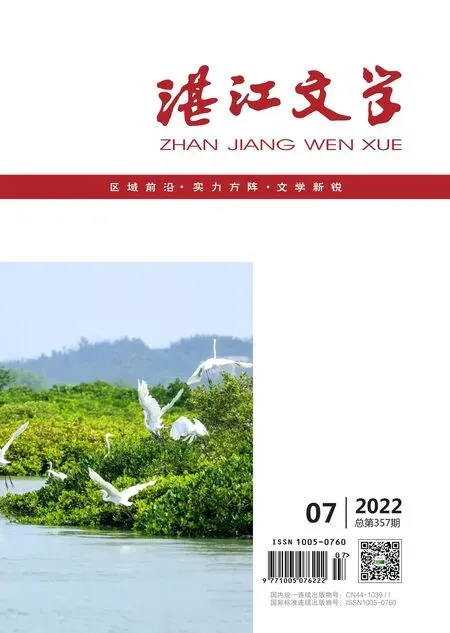鄉野記趣
◎ 張 波
老家的魚
老家村子,北面是淄河最大的支流,東面是一條小河,夏季豐水期,兩面臨水。有水就有魚,有魚就少不了漁事。
小時候,村北的河里,魚非常多。河里有水灣的地方,游魚成群。水深的地方,人們沒有漁具,拿魚兒沒辦法。水淺的地方,水流較急魚也不好逮。
這里常見的魚有白魚、鯰魚、鯽魚、泥鰍,還有一種“豆瓤子”,在溪流里跑得很快,肉質肥美。還有一種“沙里趴”——整天趴在水底的沙子上。“沙里趴”長不大,就一根主刺,肉也很細嫩。
沒有漁具,人們也有捉魚的辦法。“砸魚”是大人們常干的。我跟三叔下河砸過兩回魚。
三叔不知從誰家借來一雙高筒水靴,又找來一把大鐵錘。三叔抗著大鐵錘走在前面,膠靴發出“哐啷哐啷”的響聲,威風得很。我提著一只籃子,一溜小跑跟在后面。來到河邊,三叔下到水中,掄起鐵錘,向水流里大石塊砸下去,再用鐵錘把石塊勾翻過來。石頭下面若有魚,就被震暈,露出白花花的肚皮,在水里掙扎。三叔撈起魚扔到岸邊,我再把在卵石里亂蹦的魚兒揀到筐里。有時候三叔的錘要砸深水里沒露出水面的石頭,砰地一下,濺起大片水花,他自己也被濺得臉上身上全是水,扭頭看著我狼狽地笑起來。
這種原始的捉魚方法,也很見效。不用一個下午,我們就能砸半籃子魚。那時候生活困難,食用油匱乏,有了魚也不好做、不會做。滴點油在鍋里煎一下,就是菜。許多女性嫌腥,連碰也不碰。我和三叔“砸”了兩條半斤多的鯰魚,奶奶直接拿刀一剁,喂了雞。
雨水少的年份,河里水流就小了。有一年剛開春,河水眼看要斷流。村里男女老少像聽到號令,許多人都下河抓魚,滿河灘里都是人。那個周末下午我提著筐子拿著笊籬來到河邊的時候,其它魚早被人們捉光了,只剩下在溪流里亂跑的“沙里趴”和鉆進河底泥里的泥鰍。泥鰍滑得很,抓在手里,不等扔到岸上,它又哧溜逃脫掉進了水里。“沙里趴”行動很迅捷,你要把它趕到淺水里不能游了,才能捉住。
我想了一個辦法:在流水的河底扒一個坑,把笊籬放進去,上邊再蓋上一塊薄點的石頭。倉皇亂竄的魚兒躲進了我設的笊籬陷阱,就不再動了。過一會后,連笊籬加石塊一起從水里撈起來,到岸邊再揭開石塊,笊籬里滿是亂蹦的“沙里趴”。我過一會就起一次“網”,下幾“網”再換個地方,效率竟比大人們還高。那個下午,我捉了半籃子寸把長的“沙里趴”,可以說是滿載而歸。晚上,父親從生產隊放工回到家,看到我捉的魚,臉上樂開了花:“燙燙腌起來,過兩天刨地的時候吃!”
春耕季節,刨地是最累的活,也是最缺蔬菜的季節,大人們為天天啃咸菜而懊惱。煎個咸魚下飯,該是過年的待遇了。
有一段時間,隨著上游鄉鎮企業的興起,河里的魚越來越少,“豆瓤子”、白魚更是多年不見蹤跡。人們這時生活大大改善,不缺油吃,開始懷念河里有魚的日子。
這些年,在流域環境治理,水質得到巨大改善后,河里的魚又漸漸多起來了。夏天有洪水的日子,太河水庫里的魚常常順著河水溯流而上,人們經常能捉到幾斤重的大魚。家鄉村前的河里建起了多道攔河壩,幾斤重的白鰱會溯流到這里安家。
夏夜,人們坐在村東小河邊乘涼。月光灑滿山野,溪水銀光閃閃。突然,河里噗啦啦有東西亂蹦起來。“鯰魚上來了!”有人發一聲喊,乘涼的人都忙活起來。人們跑回家拿來手電、鐵锨,還有人拿著推磨的磨棍,到小河灘里捉起鯰魚來。棍砸,锨鏟,人們叫喊聲此起彼伏,手電光在河面上閃爍。幾斤重的鯰魚游到淺水里,這是大自然給人們送的厚禮啊!
這群鯰魚,讓村里的人們興奮了一個夏季,也播下了美好的期待。
趕山花令
驢駒嘴
春天,山上青草發芽的時候,藜藜嘴就長出來了。
藜藜嘴先長出兩片長長的略帶鋸齒形的灰綠色葉子,再露出一個小驢駒嘴樣的花蕾。幾天后,驢駒嘴張開了,藜藜嘴開出了蒲公英一樣的黃色花朵。
我們這里童謠這么唱:藜藜嘴,開黃花,閨女吃了長媽媽(乳房),小廝吃了長鴨鴨。小時候也不知道這說得是什么意思,反正知道它能吃。
藜藜嘴好吃!最好在它花蕾未綻開之前,把它從土里挖出來。它的花莖是淡褐色的,花蕾的頂端也是淡褐色,地下部分是長長的蔥白一樣的葉莖,水靈靈鮮嫩嫩。拂去泥土送進嘴里,葉子和花蕾清新爽口,白色的葉莖又脆又甜!
它那管狀的根部,把表皮剝去,也是能吃的,面面的,略帶點苦味,很有嚼勁。
小時候,春耕刨地的時候,大人從坡里挖幾棵藜藜嘴帶回來,那就是難得的美味了。沒有水果,主食就是窩頭煎餅,青菜很少見,魚肉更稀罕,這時候人們全靠弄點野菜和能吃的樹葉來補充維生素。那時節每天傍晚,父親從坡里回來,我都滿懷期望地跑過去看看他帶沒帶回藜藜嘴。稍大點,春天上坡拾柴火,看見它,便饑不擇食地挖出來填進嘴里,有時候還滿坡里去找。它是春天少見的能生吃、美味且壓餓的野菜,大人小孩都喜歡。
后來才知道,它學名叫鴉蔥,也叫雅蔥,各地還有土參、老鶴咀、老觀筆的叫法,中醫上用它清熱解毒,消腫散結。它的汁液能治瘊子,內蒙古的叉枝鴉蔥甚至用來治癌癥。用它煎茶、煎雞蛋,治妊娠嘔吐效果非常好。
再后來,讀蒲松齡《日用俗字》,看到“萵苣味如曲曲菜,驢駒嘴似蒲公英”,恍然大悟,鄉人說的藜藜嘴,是驢駒嘴的口誤!
賊蒜
賊蒜就是書上說的薤白、藠頭。
春分時節,山上的梯田里賊蒜很多。它細細的苗莖有的匍匐在地里,有的艱難地支楞在簌簌的春風里,像凌亂的綠色毛發。它的花太小了,及至暮春了才開,以至于你忽略了它,甚至懷疑它是不是還開花。它地表上的樣子很不起眼,挖下去,細細的莖牽著一個指甲蓋大的小白蒜頭。它的蒜頭不像大蒜那樣規規矩矩長在地表下,而是賊頭賊腦鉆得老深。
別看薤白樣子不濟,卻大有來頭,古人拿它入饌、入藥,也入詩。李商隱有“薤白羅朝饌,松黃暖夜杯”的詩句。白居易則云:“種薤二十畦,秋來欲堪刈。望黍作冬酒,留薤為春菜。荒村百物無,待此養衰瘵。”想來在溫暖的地方,它能長得比在我們這里肥壯。汪曾祺先生講北方人很少食薤,而南方多省份都吃。我想可能薤白產地不同,差異性很大。“桔生淮南則為桔,生于淮北則為枳”。我們這里的薤白,味道特別濃。
鄉人吃賊蒜不外乎兩種做法:一是烙菜煎餅,把賊蒜切碎了,放點鹽,攤煎餅時放進去,烙成煎餅卷。這種吃法,有的人喜歡,老遠就聞見了香味,有的人則嫌它味大,烀濃!另一種吃法就是炒雞蛋。
現在,你到太河、峨莊一帶,飯店里常有這樣一道菜:山蒜炒雞蛋!
東風菜
杏花落了,杏葉發出來,山坡上東風菜跟著就長出來了。東風菜的葉子形狀有點像杏葉,但沒有杏葉那么光滑。鄉親們管它叫杏茀子苗。它胖胖嫩嫩的葉苗往往幾株擠在一起,幾天就竄出一拃高,生機勃勃,有點神秘,仿佛是土壤里熱得不行,它要急著鉆出來涼快涼快。
這時候采的東風菜,一點塵土都不沾染。直接放進嘴里嚼,面面的,滑滑的,自有一種特殊的清香。拿它清炒、涼拌,都是好菜!聽村里人說,用它做渣豆腐非常好吃,但我至今沒嘗過。
東風菜嫩苗,人吃;夏初它開花了、老了,弄回家喂豬,豬也喜歡吃。
它還是一味中藥,能散風熱,清頭目,增強免疫功能、抗腫瘤。鮮東風菜搗爛敷傷口還能治蛇咬傷。
有一年春天,在外地,我們去爬一座山。我在山上見有東風菜,便采了一大把。同行的人們都不認識它。等在山下的飯店吃飯時,我讓人家用水焯了一下,直接用蒜泥涼拌,沒想到,大家風卷殘云,一會就把那盤東風菜吃光了。
山上東風菜并不是很多。不知道這種野菜能否種植。
山韭花
采山韭花要在農歷的七月份,中元節前后。這時候挎著筐到山上去,要到背陽的一面,在山頂下邊的陡坡上,野草叢中,星星點點,白色的山韭花就開成了一片。山韭花喜陰不喜陽,山前坡里很少見它。而找一個高點的山后坡,很快就能采一筐。
山韭花的味道比賊蒜濃得多。采上一筐,也不用洗,回家拿它和少許粗鹽粒上碾壓碎,壓成糊狀,再兌點涼開水攪勻,收在一個罐子里或壇子里。發酵一段時間后,山韭花醬就做成了。它的濃郁清香,是平地種的韭菜花沒有的。用它卷個剛攤出來的熱煎餅,香得真是沒法說!
鄉親們還都愛這一口:把摘回來的嫩眉豆和嫩豆角泡進韭花醬壇子里。到了冬天,把腌透的眉豆和豆角撈上兩根當咸菜,咬一口,脆脆的,豆角眉豆鮮鮮的豆香,和著韭花的醇香,在嘴里久久不散去。法國有名的腌酸黃瓜,只是酸脆,味道并不鮮;江南的腌菜,口感差了些;西南的泡菜,口感雖好,但蔬菜的原味已淡。家鄉人的山韭花醬泡菜,我認為是咸菜中的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