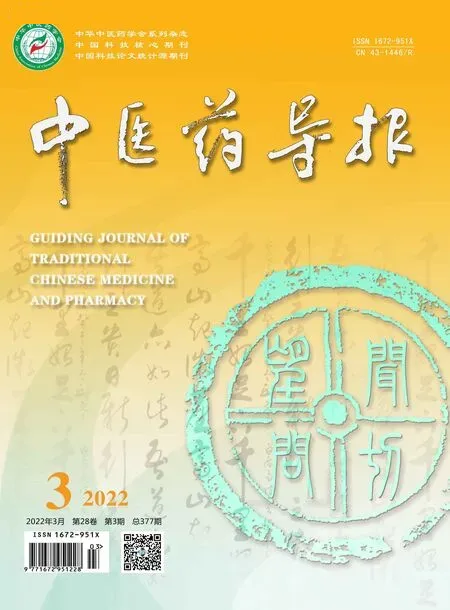吳旭“四辨一神”體系化論治兒童抽動障礙經驗*
王佳慧,鮑超,李建兵
(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江蘇 南京 210029)
抽動障礙(tic disorders,TD)是起病于兒童或青少年時期的一種神經精神障礙性疾病,臨床以不自主、反復、突發、快速、重復、無節律性的一個或多個部位運動抽動和(或)發聲抽動為主要特征。好發年齡5~10歲,男孩多于女孩[1]。目前,抽動障礙發病機制尚不明確,現代醫學根據臨床癥狀和病程長短的不同,將TD分為短暫性抽動障礙(TTD)、慢性抽動障礙(CTD)和Tourette綜合征(TS)3種類型,其中以Tourette綜合征最為復雜難治[2]。針灸治療本病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行業內缺乏治療本病的規范化、系統化的治療模式。
吳旭,教授,江蘇省名中醫,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獲得者,國家第四批名老中醫學術繼承人導師,師從邱茂良,系屬針灸大師承淡安所創“澄江針灸學派”。吳旭從事中醫針灸臨床、教學及科研工作五十余載,學貫中西,博采眾長,擅長運用針藥結合治療兒科神經系統疾病。吳旭教授團隊認為本病病機為“肝風內動,風盛筋急”“陰津虧虛,經筋失養”“神機失攝,經筋失約”[3]。筆者導師鮑超師從吳旭教授,故本文在前期基礎上進一步總結“肝風貫穿本病始終,肝血耗損為其終末”的病證特點,針對病程各階段關鍵環節,提出“四辨一神”精準化、體系化治療思路,并將吳旭教授臨床經驗整理如下。
1 “四辨一神”模式的內涵
針對兒童抽動障礙,吳旭教授發現傳統的辨證論治存在許多的不足,如忽視體質因素導致治療效果個體差異大,忽視病機病程演變導致對輕度抽動障礙療效好,中、重度抽動障礙療效差等。吳旭教授根據本病“肝風貫穿疾病始終,肝血耗損為其終末”的病機演變特點,創新提出“四辨一神”(即“辨體-辨病-辨證-辨經-調神”)論治模式。臨證中,以辨體為本,糾正偏頗體質,降低發病易罹性;以辨病為要,明確疾病診斷、病機、分期;以辨證為綱,結合辨病,靈活加減配穴,精準對應治療;以辨經為須,強調運用“肝主經筋、肝血養筋”指導原則,標本同治;以調神為護,強調調護小兒心神,貫穿治療始終,不同階段各有側重。“四辨一神”模式做到了綜合分析,動態觀察,個體化精準治療,有利于提高針灸臨床療效,降低其復發率。
2 “四辨一神”體系化論治兒童抽動障礙
2.1 辨體筑基 吳旭教授認為體質與本病具有相應性特征,TD患兒多有特殊的體質傾向。吳旭團隊運用王琦《7-14歲青少年體質量表》分析了100例TD患兒的體質,發現氣郁質占40%、特稟質占22%、陰虛質占20%、平和質占12%。同時,不同體質類型的TD患兒表現也不盡相同,如氣郁質患兒多情緒低落,精神緊張;特稟質患兒多稟承其父母,有TD家族史,且易過敏;陰虛質患兒多由于先天不足或后天失養,多形體瘦小,急躁易怒;氣虛質患兒多體虛易感,肺氣不足;痰濕質患兒多脾虛過食肥甘,形體肥胖。正是這些特殊的體質類型增加了其對TD的易罹性與難治性。
吳旭教授認為體質是可以被干預和調節的。體質的調衡,對疾病的發生、發展、轉歸和證候的形成與演變起著重要作用[4]。吳旭教授針對不同體質,強調個體化平衡體質,在選穴上具有特殊性,如氣郁質加肝俞、膻中、內關,特稟質加肺俞、大椎、足三里,陰虛質加腎俞、三陰交、太溪,氣虛質加脾俞、氣海、關元,痰濕質加三焦俞、陰陵泉、豐隆。在針刺操作時刺激量亦不同,體質弱,手法宜輕,體質強,可稍重。調節患兒體質,旨在筑基、平衡患兒健康基線,對本病的轉歸與康復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2.2 辨病結合辨證 吳旭教授認為本病總病機為肝風內動,且肝風內動貫穿本病全程,但存在明顯的階段性變化。西醫根據病程長短及發病程度將TD分為3種類型:短暫性抽動障礙(TTD)、慢性抽動障礙(CTD)和Tourette綜合征(TS)。吳旭教授創新性提出可以根據病程大致將本病病機演變分為3個階段,其中肝風內動在TD的3個階段都存在,血不養筋以第二、三階段為主,心神耗傷在第三階段尤為突出。吳旭教授認為疾病初期,外邪侵襲或情志失常引發肝風內動,病機以肝用失常、肝風內動為主,若失治誤治,則易損傷肝體,導致肝血不足,筋失濡養;后期體用均傷,神失內守,肝血虧虛,肝風更無制克。西醫的分類方法與吳旭教授分階段辨病的學術思想有相似之處,但局限于臨床癥狀和病程長短的不同,對發病機制無深入分析,亦無針對性治療。吳旭教授分側重、分病程、分階段論治,彌補了這一不足,對提高臨床療效有著借鑒意義。
吳旭教授強調辨病旨在從整體上把握疾病發生發展的全程規律,并針對這一特點,強調治療本病必須辨病結合辨證,詳別體用,分步論治。其中,用指功能層面,肝風;體指物質層面,肝血。肝主疏泄,主動,故在用為陽;肝藏血,血為陰,故在體為陰。
2.2.1 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病機以肝用失常為主。本病初期,風陽浮于淺表,尚未入里動血,傷及陰液,故癥狀較輕,僅表現為單一抽動癥狀,病程較短,往往不足1年。
吳旭教授立法潛陽息風,以恢復肝用,并自擬“調肝息風”針法。該針法以風池、合谷、太沖、肝俞為主穴[5]。風池屬足少陽膽經,為治風要穴。《素問·至真要大論篇》言:“諸風掉眩,皆屬于肝。”[6]肝膽相表里,瀉膽經風池可通調肝膽經氣,使肝陽得潛,無以化風。《針灸大全·八脈圖并治癥穴》曰:“小兒急驚風,手足搐,印堂、百會、太沖、合谷。”[7]合谷屬多氣多血之陽明經,太沖屬少氣多血之厥陰經,一陽一陰,一氣一血,一腑一臟,一降一升。兩穴配伍為四關穴,共奏平肝息風、調和陰陽之功。肝俞為肝臟經氣輸注匯聚之處,可調肝臟之虛實。《靈樞·本神》云:“肝藏血,血舍魂,肝氣虛則恐,實則怒”[8],說明肝臟與情志關系密切,故針刺肝俞可調肝經氣血,平肝亢,調理情志。
2.2.2 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病機以肝體不足為主。《溫病條辨·解兒難·俗傳兒科為純陽辨》曰:“小兒稚陽未充、稚陰未長者也。”[9]小兒生長發育尚未完善,為稚陰稚陽之體,若風陽日久不消,則易傷陰耗血,虛風內生,風氣擾動筋脈而發為抽動。稚陰未長,又耗傷陰血,則更易化火,熱極動風。此期患兒抽動癥狀較前復雜,伴隨癥狀較多,易反復發作,普遍病程較長。
吳旭教授立法瀉火養陰,以固護肝體,在取穴時,常配伍脾俞、腎俞、血海等穴,通過實脾益腎以補肝血。脾俞、腎俞為脾、腎經的背俞穴,陰病治陽,取脾俞、腎俞可補先后天之不足。《會元針灸學》記載:“血海者,是心生血、肝藏血、腎助血,腎之陰谷,肝之曲泉,脾之陰陵泉皆生潮之處,三陰并行,通血之要路。”[10]血海穴可補益肝血,舒筋緩急。在自擬經驗方的基礎上,亦可佐以補益肝血之品,如白芍、當歸、防己等。上述藥物均入肝經,可養血柔肝。針藥結合,效如桴鼓。
2.2.3 第三階段 第三階段病機主要為神失內守。《素問·湯液醪醴論篇》言:“形弊血盡而功不應者何?岐伯曰:神不使也。”[6]故可知臨床上針石湯藥已盡而抽動反復,病程遷延的根本原因是“神失內守”,耗傷心血,肝血更虧。臨床常見癥狀遷延難愈,反復發作的難治性多發性抽動癥患兒,此類患兒常表現出不同程度的心理缺陷和智力結構缺陷,并伴有較多的行為問題。
吳旭教授立法調神定志、身心同治,在前期針藥結合的基礎上,重視調神,結合綜合行為療法、家庭心理疏導等多種治療手段,綜合治療,以正其神。
綜合行為療法由醫師完成,基本流程:(1)回顧抽動事件,更新抽動等級表(5 min)。(2)回顧家庭作業以及進行相關的獎勵計分(5 min)。(3)進行“不方便”事件評估(5 min)。(4)進行功能評估(FBA),并提出相應的功能干預方案(15 min)。(5)進行習慣逆轉訓練(HRT)治療(20 min)。(6)放松訓練(5 min)。(7)布置家庭作業(5 min)。療程:每周治療1次,4周為1個療程,共觀察1個療程[11]。
家庭心理疏導由家長和老師完成,對患兒家長進行多發性抽動癥知識教育,提高家長對多發性抽動癥的認識,告誡家長不要過分注意患兒的抽動癥狀,更應避免采用打罵體罰的管教方式;家長與學校老師溝通,根據患兒興趣愛好,每天開展一些輕松愉快的文娛活動;父母不在孩子面前爭吵,創造家庭和睦、輕松的氣氛。
2.3 辨證簡明 抽動障礙證型繁雜不一,缺乏統一性。吳旭教授通過臨證總結,提出將本病患兒常見證型分為肝風內動、肝血不足兩種。將現代醫學TD的3種類型分別納入兩種證型,簡單明了,便于臨床應用。
2.3.1 肝風內動證 肝為風木之臟,體陰而用陽,肝的特點為喜條達而惡抑郁。小兒素有“真陰不足”、“肝常有余”的特點,真陰不足,則柔不濟剛,引動肝邪,化火生風,發為抽動。肝常有余,則剛燥之性顯露,肝陽上亢,亢則生風,故見不自主抽動。
吳旭教授治療以“調肝息風”針法為主,治以平肝息風、調和陰陽,輔以飲食、起居調護,重視家庭宣教,減少復發率。
2.3.2 肝血不足證 水谷精微所化生的營氣、津液、腎精共同化生為血液。《靈樞·決氣》曰:“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8]《諸病源候論·虛勞病諸侯下》提出:“腎藏精,精者,血之所成也。”[12]血液的生成與脾、腎關系密切。小兒具有“脾常不足”、“腎常虛”的特點,脾腎不足,則肝血無以化生,加之風陽傷陰耗血,抽動癥患兒中后期常表現為肝血不足證。
治療上,在“調肝息風”針法的基礎上,突出健脾益腎補肝血的穴位,中藥亦可加入滋陰養血之品,有利于減輕癥狀,避免加重,縮短療程,控制復發。
2.4 辨經佐調 經絡包括了十二經脈辨證、奇經八脈辨證和經別、經筋、皮部辨證3個方面[13]。吳旭教授首次提出在本病的第二、三階段必須辨經筋,并強調這是慢性抽動障礙(CTD)和Tourette綜合征(TS)兩類患兒取得療效的關鍵。
經筋與肝血關系密切[14],《風勞臌膈四大證治》曰:“筋必肝木,得血以養之,則和柔而不拘急”[15]。吳旭教授認為肝血充盈,則經筋活動靈活,在本病的第二、三階段,風熱熾盛,燔灼肝血,筋失濡養,發為不自主的抽動。
吳旭教授在臨證時發現,TD患兒在肝俞處多捫及條索狀結節。此處的條索狀結節即肝失調達,氣血運行不暢,血氣凝結而產生的筋結所致[16]。《雜病源流犀燭·筋骨皮肉毛發病源流》亦曰:“肝之經脈不調,氣血失節,往往有筋結之患,不論骸體間,累累若胡桃塊狀是也。”[17]故常取結節處針刺,手法上以刺筋為度,操作時快速刺入皮膚,減輕患兒疼痛,后逐漸深入,到達深筋膜層,在肌肉及結締組織豐厚部位,行補瀉手法以達到酸麻重脹的針感[18]。
吳旭教授認為《靈樞·經筋》[8]提出“以痛為腧”,不單純指阿是穴,更多是強調局部取穴對經筋病治療的重要性[19],并認為抽動部位附近的腧穴可調節局部經氣以緩筋,如眼部抽動取太陽、陽白,鼻部抽動取迎香,口角抽動取地倉、承漿,喉中發聲不能自制取廉泉,腹部抽動取天樞。故治以舒緩筋急,常取陽陵泉與抽動部分附近的腧穴,陽陵泉屬八會穴之筋會,主治與筋有關的疾病,與局部取穴相配合共同起到舒筋緩急、定痙止搐的作用。
吳旭教授強調經筋部與深筋膜相一致,針刺經筋部達筋膜層效果最佳。這一學術觀點不僅獨具特色,而且與現代針刺研究中認為針刺等物理刺激相當于通過筋膜支架上的刺激來調節細胞的生物代謝和活動[20]的說法相吻合。
2.5 調神養肝 TD患兒多精神活動過度活躍或精神緊張,故吳旭教授認為調神應貫穿治療始終,但每個階段側重不同。抽動障礙具有反復性、難治性的特點,分階段調神可增強療效,穩定病情,減少復發。
在本病的第一階段,病情較輕,病機以肝風內動為主。吳旭教授強調調神側重維護精神情志穩定。在針刺取穴上,常加百會、印堂等調神穴位。百會、印堂均為督脈腧穴,督脈入絡腦,且均位于頭部,可取其近治作用,健腦安神[21]。
在本病的第二、三階段,病情進一步加重,耗傷肝血,神失所守。吳旭教授認為神和血均由水谷精微所化生,同居于心、脈之中,同源互化,相互作用,因此,血虛時可以通過安神以代償補益[22]。在治療時,除針刺調神穴位外,可以輔助運用綜合行為療法、家庭心理疏導等多種治療手段,以期安神而少耗肝血,有利于疾病的轉歸。
3 典型驗案
3.1 驗案1 患兒,男,6歲,2021年1月11日初診。主訴:雙眼不自主上翻20余天。現病史:患兒20余天前開始出現雙眼不自主上翻,偶有擠眉,無其他動作,無喉中發聲,自行予眼藥水外用后無明顯改善,每日發作6~10次,間隔2~5 h,發作時間不固定,注意力尚可,納寐可,二便調,舌邊尖紅苔薄白,脈弦數。西醫診斷:抽動障礙(短暫性抽動障礙,TTD),YGTSS評分21分;中醫診斷:慢驚風(肝風內動證);體質辨識為氣郁質;治法:調肝息風。針灸取穴:百會、印堂、風池、合谷、太沖、肝俞、膻中、內關、陽白、太陽。操作方法:百會、印堂平刺0.5~1寸,平補平瀉;風池向鼻尖方向斜刺0.8~1.2寸,得氣后行平補平瀉法;膻中向下平刺0.5~1寸,得氣后行平補平瀉法;合谷、內關、太沖直刺0.5~0.8寸,合谷、內關得氣后行平補平瀉法,太沖行瀉法;太陽直刺0.3~0.5寸,平補平瀉,陽白向下平刺0.3~0.5寸,平補平瀉。肝俞附近尋到筋結點,針刺前必先點按肝俞3~5min,淺刺瀉法不留針,針刺完畢后配合肝俞拔罐。除背俞穴外留針30 min。療程:隔天治療1次,每周治療3次,4周為l個療程。
2診:2021年1月20日,雙眼上翻及擠眉基本消失,繼予鞏固治療。
3診:2021年2月15日,隨訪未復發,療效顯著。
6個月后電話隨訪,患兒家屬訴未見復發。
按語:患兒辨病為抽動障礙的第一階段,其主要病機為肝用失常,辨證為肝風內動證,結合其氣郁體質,選取風池、合谷、太沖、肝俞平肝陽、息肝風;加膻中、內關,膻中位于胸部,為八會穴之氣會,可理氣寬胸,疏肝解郁,平衡氣機;辨經發現患兒肝俞附近觸及條索狀結節,點按、針刺后并拔罐,使結節散去,則肝氣自疏,并結合其臨床表現,加太陽、陽白,兩穴均為局部取穴,疏通抽動部位經氣,以緩筋止搐,加調神穴位百會、印堂安神定志、清腦醒神。
3.2 驗案2 患兒,女,13歲,2020年11月23日初診。主訴:不自主聳肩伴搖頭1年半。現病史:患兒1年半前因升學壓力,出現不自主聳肩,搖頭,無喉中發聲,時輕時重,持續發作,間隔<1 h,上課注意力不集中,成績下滑,敏感,煩躁,挑食,夜寐差,盜汗多,大便干結,小便尚可,舌淡紅苔薄白,脈弦細。西醫診斷:抽動障礙(慢性抽動障礙,CTD),YGTSS評分35分;中醫診斷:慢驚風(肝血不足證);體質辨識為陰虛質;治法:瀉火養陰,固護肝體。針灸取穴:百會、印堂、風池、合谷、太沖、肝俞、脾俞、腎俞、血海、三陰交、太溪。操作方法:脾俞、腎俞取俯臥位,淺刺行捻轉補法,不留針;血海、三陰交、太溪直刺0.5~1寸,行補法。余操作方法同前。除背俞穴外留針30 min。療程:同前。自擬抽動障礙經驗方:天麻8 g,鉤藤8 g,醋鱉甲10 g,煅龍齒8 g,煅赭石10 g,炒白芍8 g,玄參8 g,麥冬8 g,甘草5 g,當歸8 g。7劑,1劑/d,水煎后分2次服。
2診:2020年12月14日,聳肩及搖頭發作程度減輕,頻率減少,每日僅發作1~2次。
3診:2021年2月22日,患者抽動癥狀基本消失,囑患兒注意生活調適。
6個月后電話隨訪,患兒家屬訴無抽動癥狀,無復發。
按語:患兒病程長,耗傷營血,辨病處于病程的第二階段,辨證屬肝血不足證,針灸取穴在“調肝息風”針法的基礎上,加脾俞、腎俞、血海健脾腎、益肝血;結合患兒的陰虛體質,輔以三陰交、太溪滋陰瀉火。辨經、調神方案同上一醫案,不多贅述。吳旭教授總結多年臨床經驗,自擬經驗方,取天麻、鉤藤鎮肝息風,鱉甲、玄參、麥冬滋補營陰,龍齒、赭石育陰潛陽,白芍、甘草柔肝舒筋,當歸補血養肝,諸藥共奏養血調肝舒筋之效。針藥結合治療有較好的療效,治療3個月后,癥狀已基本消失。
3.3 驗案3 患兒,男,8歲,2020年6月2日初診。主訴:不自主眨眼、扭頸伴喉中發聲5年余。現病史:患兒5年前開始出現不自主眨眼,未予重視,后發展為頻繁不自主眨眼、斜視、嘴動、扭頸、聳肩,喉中發聲不能自控,間歇時間<5 min。患兒平素注意力不集中,小動作較多,脾氣急躁,易怒,胃納可,喜冷飲,入睡困難,多夢,大便干,平素二三日一次,舌淡紅苔薄白,脈弦細。西醫診斷:抽動障礙(Tourette綜合征,TS),YGTSS評分72分;中醫診斷:慢驚風(肝血不足證);體質辨識為氣郁質,治法:調肝息風,養血舒筋,安神養心。針灸取穴:百會、印堂、風池、合谷、太沖、肝俞、脾俞、腎俞、血海、膻中、內關、太陽、頰車、廉泉。操作方法:頰車、廉泉直刺0.3~0.5寸,得氣后行平補平瀉。余操作方法同前。除背俞穴外留針30 min。療程:同前。因患兒畏苦,拒服中藥,未予中藥治療。予定期進行綜合行為療法和家庭心理疏導。
2診:2020年7月6日,患兒扭頸、聳肩,喉中發聲基本消失,仍有眨眼、斜視、嘴動,但癥狀明顯減輕。治療同前。
3診:2020年9月7日,患兒眨眼、斜視、嘴動、扭頸、聳肩,喉中發聲不能自控癥狀基本消失。
隨訪6個月未復發,療效顯著。
按語:患兒辨病為抽動障礙中最嚴重的Tourette綜合征,屬于本病的第三階段,辨證屬肝血不足證,治療以調肝息內風治其標,健脾補肝血治其本,定志安心神治其根。在第二階段“調肝息風”針法配伍補血穴位的基礎上,根據氣郁質體質,加膻中、內關;辨經根據發作部位,加太陽、頰車、廉泉,局部取穴以止抽舒筋。調神方面,在針刺治療前后,談心疏導,寧神定志,在針刺治療時凝神行氣,取調神穴位百會、印堂,并配合綜合行為療法和家庭心理疏導。
4 結語
兒童抽動障礙目前成為多發、疑難兒科疾病之一,給患兒、家長及社會帶來不良影響。吳旭教授緊扣本病“肝風貫穿疾病始終,肝血耗損為其終末”的病證特點,針對本疾病發展進程中的關鍵難點,創新性提出“四辨一神”體系化診療模式,通過辨體、辨病、辨證、辨經,分側重、分病程、分階段論治,將現代疾病診斷與中醫辨證有機結合,令醫者思路清晰,取法有度,不僅有利于提高臨床治療的精準性和有效性,而且為規范化運用針灸治療本病提供了創新性診療模式,也是針灸臨證中西醫結合的一個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