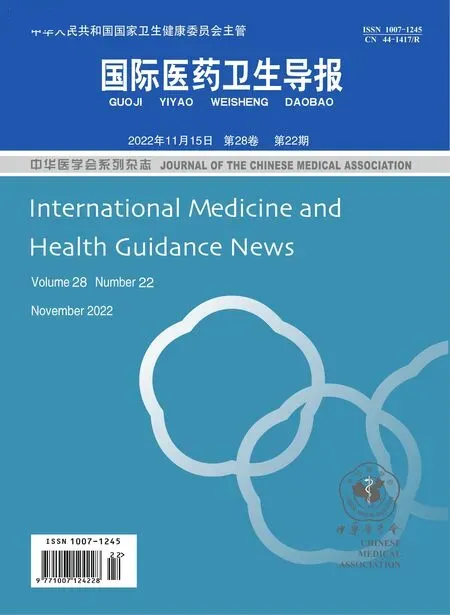孕晚期補充維生素D對母兒25羥維生素D水平及新生兒疾病的影響
張明 莊麗娟 馮驍 邱慧英 陳彩燕 魏曉帆 肖乃安
1 廈門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兒科,廈門 361004;2 廈門大學附屬中山醫院產科,廈門 361004;3廈門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醫務部,廈門 361003
維生素D 是一種脂溶性類固醇激素,除了可以促進鈣磷吸收,穩定血鈣、血磷的濃度以及促進骨骼礦化以外,還具有調節免疫功能、促進細胞增殖分化、抑制和殺死多種致病菌、維持上皮細胞完整性等方面的作用[1-3]。維生素D 缺乏嚴重影響母嬰健康。《中國居民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入量》中指出孕婦維生素D 推薦攝入量為每日400 IU,最高耐受量為每日2 000 IU,而孕晚期維生素D需要量更高。有研究顯示孕期每日維生素D 攝入量不足600 IU,血清25 羥維生素D[25(OH)D]水平不足達到50 nmol/L[4]。目前維生素D的重要性被廣泛關注,但全世界孕產婦和新生兒維生素D缺乏的現狀仍不容樂觀[5-6]。有報道顯示孕婦血清25(OH)D水平與新生兒維生素D 水平高度相關,但與新生兒體質量、頭圍、身長無明顯相關性[7];然而,亦有研究顯示孕婦血清25(OH)D 水平與新生兒體格發育指標呈正相關[8]。新生兒敗血癥和新生兒壞死性小腸結腸炎是新生兒期發病率較高的重癥疾病,嚴重影響新生兒健康。新生兒低水平的25(OH)D與其發生是否相關,尚存爭議[9-10]。孕期維生素D的補充劑量尚缺乏統一觀點,基于以上問題,本研究給予孕晚期孕婦加強補充維生素D≥600 IU至分娩前,觀察母兒維生素D水平變化,同時監測新生兒體格發育指標及新生兒期重癥疾病發生率,以了解孕晚期維生素D水平對母兒的影響。
對象與方法
1、研究對象
收集2019 年1 月至2021 年12 月在廈門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及廈門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及下屬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定期產檢并于兩院分娩的孕產婦及新生兒作為研究對象,隨機分為干預組和對照組,干預組316例,對照組337例;對孕晚期及新生兒期進行隨訪。納入標準:能在兩院及下屬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定期產檢并分娩的孕產婦及能隨訪的新生兒;排除標準:雙胎/多胎妊娠、胎兒畸形、遺傳代謝病以及產婦有甲狀腺及甲狀旁腺疾病等合并癥可能對試驗結果產生影響的病例。本研究已獲得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核批準。
2、研究方法
所有入組孕產婦在常規的孕期保健、分娩、新生兒隨訪的基礎上,對所有干預組及對照組孕產婦進行健康宣教及飲食指導,如增加戶外運動,增加日曬、增加含維生素D 豐富食物的攝入,對照組與干預組從孕期開始即通過補充含有維生素D 的復合型維生素補充維生素D,維生素D 劑量<600 IU;干預組從孕晚期(妊娠28 周)起,追加口服維生素D滴劑,使每日維生素D 補充量≥600 IU 至分娩前,維生素D滴劑[國藥控股星鯊制藥(廈門)有限公司,規格400 IU/粒];對照組未額外補充維生素D制劑,每日補充量<600 IU。
3、觀察指標
(1)孕產婦及新生兒25(OH)D 水平:所有入組孕產婦于干預前、待產時(分娩前5 d 內)檢測靜脈血25(OH)D 水平,分娩時留取新生兒臍血檢測25(OH)D 水平,采用化學發光法進行檢測。(2)維生素D 缺乏率:孕產婦及新生兒維生素D 缺乏及不足的標準按照《兒童微量營養素缺乏防治建議》確定,即兒童血清25(OH)D 水平15~20 μg/L(37.5~50.0 nmol/L)判定為不足,≤15 μg/L(≤37.5 nmol/L)為缺乏,成人以血清25(OH)D水平20~30 μg/L(50.0~75.0 nmol/L)為不足,<20 μg/L(<50.0 nmol/L)為缺乏[11]。(3)分娩方式及早產比例:統計新生兒早產的比例及分娩方式。(4)新生兒體格發育指標:測量新生兒出生體質量、身長及頭圍。(5)早發型敗血癥(early-onset sepsis,EOS)發生率:日齡≤3 d,EOS臨床診斷:有異常臨床表現并滿足下列條件中任何一項:①血液非特異性檢查≥2 項陽性;②腦脊液檢查為化膿性腦膜炎表現;③血中檢測出致病菌DNA。EOS確定診斷:有臨床表現,血培養或腦脊液(或其他無菌腔液)培養陽性。本研究統計EOS病例包括臨床診斷和確定診斷病例[12]。(6)新生兒壞死性小腸結腸炎的發生率:根據Bell分級住院期間納入≥Ⅱ期新生兒壞死性小腸結腸炎作為研究對象[13],統計發生率。
4、統計學分析
使用SPSS 23.0 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符合正態分布,以()表示,行獨立樣本t檢驗,計數資料以[例(%)]表示,行χ2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1、兩組孕產婦人口學特征比較
兩組孕產婦分娩年齡、產次、居住地、分娩季節等一般情況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

表1 兩組孕產婦人口學特征比較[例(%)]
2、兩組孕產婦及新生兒25(OH)D水平的比較
兩組孕產婦干預前血清25(OH)D水平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干預組孕產婦分娩前及新生兒臍血25(OH)D水平均高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2。
表2 兩組孕產婦及新生兒25(OH)D水平比較(μg/L,)

表2 兩組孕產婦及新生兒25(OH)D水平比較(μg/L,)
注:干預組自妊娠28 周至分娩每日補充維生素D≥600 IU,對照組每日補充維生素D <600 IU;25(OH)D為25羥維生素D
新生兒16.24±4.31 12.60±3.97 11.230<0.001組別干預組對照組t值P值例數316 337孕產婦干預前23.56±6.71 24.34±7.28 1.421>0.05分娩前27.91±7.56 24.65±6.83 5.788<0.001
3、兩組孕產婦及新生兒25(OH)D缺乏率比較
兩組孕產婦干預前25(OH)D 缺乏率及不足率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干預組孕產婦分娩前及新生兒25(OH)D 缺乏率及不足率均低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3。

表3 兩組孕產婦及新生兒25(OH)D缺乏率比較[例(%)]
4、兩組新生兒體格發育指標及新生兒疾病比較
干預組新生兒出生時頭圍、體質量及身長均大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兩組新生兒早產發生率及孕產婦剖宮產率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干預組新生兒EOS、新生兒壞死性小腸結腸炎的發生率均低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4。

表4 兩組新生兒體格發育指標及新生兒疾病比較
討 論
世界范圍內孕婦維生素D 缺乏問題普遍存在。有學者認為低水平25(OH)D 與孕婦及新生兒的多項不良妊娠結局有關。對孕產婦方面,孕期低水平25(OH)D 使孕產婦妊娠期糖尿病、子癇前期、產后抑郁的發病率增高[14]。對新生兒方面,低水平的25(OH)D 會導致胎兒生長受限,并增加佝僂病、感染性疾病和嬰兒期哮喘的發病率[15]。孕期補充維生素D 是否能對孕產婦和新生兒的不良結局有所改善,目前仍缺乏較為全面的研究。本研究從孕晚期開始加強補充維生素D,檢測孕產婦及新生兒25(OH)D水平、新生兒體格發育指標及新生兒期重癥疾病的發病率,并統計剖宮產率及早產率,以闡明孕產婦補充維生素D 對改善母兒妊娠結局的作用。
本研究顯示孕晚期每日補充維生素D≥600 IU 的孕產婦,其分娩前及新生兒血清25(OH)D 水平顯著高于對照組。對照組維生素D 補充劑量<600 IU 的孕產婦分娩前維生素D 的缺乏率達47.18%,分娩的新生兒維生素D 缺乏率達49.26%。本研究結果與報道的全世界范圍內孕婦維生素D 的缺乏率相一致[5-6]。而干預組孕晚期加強補充維生素D 使每日劑量≥600 IU 可使孕產婦及新生兒維生素D 缺乏率降至19.62%和17.09%,與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表明孕晚期每日補充維生素D≥600 IU 可以顯著改善孕產婦及新生兒維生素D的缺乏率。
孕婦提供的維生素D 是胎兒的主要來源,因此,學者認為孕婦補充維生素D 可以直接影響胎兒體內維生素D 的水平,進而促進宮內胎兒及產后新生兒體格發育[16]。本研究結果顯示,干預組新生兒體質量、身長及頭圍均顯著高于對照組,說明孕婦補充維生素D 對于新生兒體格發育有促進作用。本研究還顯示,干預組與對照組早產率以及剖宮產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有文獻報道,低水平的25(OH)D 使早產和剖宮產比率增加[17],與本試驗結果不同,可能是由于早產和剖宮產的影響因素眾多,單一的補充維生素D 對于早產和剖宮產比率不產生顯著影響。
新生兒敗血癥是新生兒期最常見的重癥感染性疾病之一,嚴重影響新生兒健康。新生兒壞死性小腸結腸炎是新生兒期常見的嚴重胃腸道疾病,多數認為感染是其最主要病因。本研究顯示孕晚期充足維生素D 可以降低新生兒敗血癥及新生兒壞死性小腸結腸炎的發生率。其機制可能與維生素D 的免疫調節和抗感染作用有關。維生素D 對T 細胞和B 細胞的增殖和抗體產生以及單核細胞和樹突狀細胞的免疫反應具有抑制作用[18]。維生素D 通過在上皮細胞、中性粒細胞和巨噬細胞中誘導抗菌肽表達而發揮抗細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作用;維生素D 亦可抑制腸道上皮細胞凋亡;抑制Th1 細胞介導炎癥因子釋放來減輕機體的炎性反應[3],進而增加機體抵御感染性疾病的能力、降低新生兒感染性疾病的發病率。
綜上結果顯示,孕晚期每日補充維生素D≥600 IU 可以提高孕產婦及新生兒血清25(OH)D 水平,降低孕產婦及新生兒維生素D 的缺乏率,促進新生兒體格發育,有效降低新生兒重癥、感染性疾病的發生率,為孕產婦合理補充維生素D提供理論依據,其具體作用機制還需進一步研究。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聲明張明:設計研究、實施研究、論文撰寫;莊麗娟、馮驍、邱慧英:實施研究、采集數據;陳彩燕、魏曉帆:數據整理、統計學分析;肖乃安:研究指導、論文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