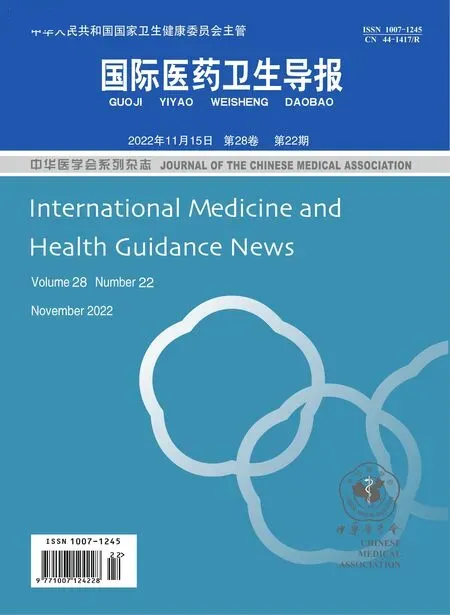泛發性濕疹伴發肝吸蟲感染1例
李嘉彥 羅育武
廣州市皮膚病防治所,廣州 510095
病例資料
患者,男,51 歲,廣州人。因“反復軀干四肢紅斑、丘疹伴瘙癢 3 年余,加重 1 個月”,診斷“泛發性濕疹”于 2022 年2月7日收入廣州市皮膚病防治所。患者3年前無明顯誘因出現軀干四肢紅斑、丘疹伴瘙癢,在醫院門診按“濕疹”予“穴位注射、抗過敏”治療后好轉,但仍有間斷皮疹復發。1 個月前無明顯誘因皮疹復發加重,腹部新發紅斑伴瘙癢,擴展至背部四肢,遂收入病房治療。患者平素體健,無發熱、咳嗽;無腹痛、腹瀉;無胸悶、氣促等不適,否認藥物或食物過敏史、過敏性鼻炎、哮喘病史,家族中無類似疾病史。患者自發病以來神志清楚,精神良好,飲食如常,大小便無異常,體質量無明顯變化。體格檢查:生命體征平穩,心肺腹查體未見異常。皮膚科查體:軀干四肢散在大小不等鮮紅或暗紅色斑或斑塊,部分融合,表面覆鱗屑或痂,淺抓痕,下腹部見粉紅色糜爛面,伴淡黃色滲出(圖1)。入院常規檢查:血嗜酸性粒細胞絕對值1.40×109/L,嗜酸性粒細胞百分比15.10%;血總免疫球蛋白E(IgE)2 556.0 IU/ml,大便常規:查見肝吸蟲卵(圖2);皮疹糜爛滲出液行細菌培養:金黃色葡萄球菌。肝纖維化5 項:血清透明質酸酶(HA)162.00 μg/L,輕度升高;尿常規、肝功能八項、乙肝兩對半、丙型肝炎RNA 定性測定、甲苯胺紅不加熱血清試驗、梅毒螺旋體明膠顆粒凝集試驗、艾滋病病毒未見明顯異常。血沉、超敏C 反應蛋白測定、心肌酶譜、風濕3 項、甲狀腺功能5項、抗核抗體(ANA)定量和敏篩變應原檢測均未見明顯異常。皮疹活檢病理診斷:(腰部)組織呈亞急性皮炎改變,符合濕疹診斷(圖3)。

圖1 濕疹患者入院時的臨床表現。A、B 為軀干上肢正背面位,C、D 為下肢正屈側位,可見散在大小不等鮮紅或暗紅色斑或斑塊,部分融合,表面覆鱗屑或痂;下腹部見粉紅色糜爛面,伴淡黃色滲出

圖2 大便常規檢查,光鏡下的肝吸蟲。A為10倍光鏡,B為40倍光鏡。光鏡下:肝吸蟲卵形似芝麻,淡黃褐色,一端較窄且有蓋,卵蓋周圍的卵殼增厚形成肩峰,另一端有小疣,卵甚小,大小為(27~35)μm×(12~20)μm

圖3 患者皮疹活檢的病理結果。光鏡所見:角化不全,漿痂形成,表皮增生,海綿水腫;真皮淺層血管周圍炎細胞浸潤;蘇木精-伊紅(HE)染色 ×200
治 療
使用注射用復方甘草酸苷(60 mg 靜脈滴注,每天1 次,成都菀東生物制藥股份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20080538,規格:甘草酸苷20 mg/甘氨酸200 mg/L-鹽酸半胱氨酸10 mg),甲潑尼龍片(24 mg,每天1 次,天津天藥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20020224,規格:4 mg),鹽酸氯環利嗪片(25 mg,每天2 次,焦作福瑞堂制藥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41025168,規格:25 mg)抗過敏治療,阿苯達唑片(0.4 g,每天1次,中美天津史克制藥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12020496,規格:0.2 g)抗寄生蟲。硼酸溶液濕敷糜爛處,糠酸莫米松乳膏抗炎止癢,維生素E 乳潤膚外用。經1 周治療,患者軀干四肢紅斑和斑塊基本消退,局部留色素沉著,下腹部糜爛面愈合。復查大便常規肝吸蟲蟲卵陰性。患者出院后隨訪3個月,未見濕疹癥狀反復,大便常規肝吸蟲卵亦是陰性。
討 論
濕疹是一種常見的變態反應性皮膚病,由于病因不明,皮疹易反復發作,并伴有瘙癢,給患者生活質量帶來嚴重影響。皮膚科臨床醫生在處理頑固復發性濕疹時,也比較棘手。目前臨床上斑貼試驗以及過敏原的檢查也常不能追查到患者的致病原因。本病例報道的泛發性濕疹伴肝吸蟲病,在常規的抗過敏治療和抗寄生蟲治療后,疾病痊愈并停止復發,提示肝吸蟲的感染可能是導致濕疹發作的原因。查閱文獻,既往有報道肝吸蟲導致的濕疹,常規抗過敏效果不理想,抗寄生蟲治療后皮膚癥狀消退的案例[1]。
在兩廣地區居民常有吃魚生的習慣,導致食源性的肝吸蟲感染在廣州不同地區人群的發病率達到7.3%,或更高[2-3]。因此,患者感染肝吸蟲后,其蟲體和代謝產物會被機體免疫系統的視為過敏原,而引發如濕疹等變態反應性皮膚病。由于濕疹、特應性皮炎等過敏性皮炎患者和寄生蟲感染患者都會出現血嗜酸性粒細胞和血IgE升高的情況,因此當出現這2 個指標升高的時候,皮膚科臨床醫生應高度重視排查寄生蟲的感染[4-5]。
治療上,阿苯達唑片作為廣譜的抗寄生蟲藥,對肝吸蟲有良好的效果,可作為首選藥吡喹酮的替代[6-7]。該案例患者口服阿苯達唑片1周的療法,效果顯著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