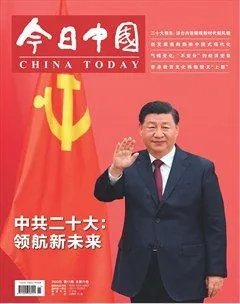跳出舒適區的創作才更舒適
文| 梭梭
不論是影視劇創作,亦或是其他藝術創作,跳出舒適區,突破舊有類型模式,則能夠打開一片新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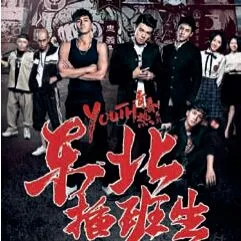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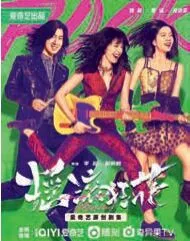
最近的影視劇爆款不少,比如悄然走紅的小成本網劇《東北插班生》,比如國內首部全景展現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最新成果的法治題材劇《底線》,以及顛覆三觀的母女故事《搖滾狂花》。這是三部截然不同的作品,題材類型相去甚遠,但挖掘它們受歡迎的根本原因,會發現其中最大的共同點,就是這幾部作品都是跳出創作舒適區,突破舊有類型模式,因而打出了一片新天地。
《東北插班生》雖然是小成本制作,但在豆瓣網上的評分卻高達7.7,秒殺不少大制作。大概是因為小成本網劇試錯成本低,膽子也就更大一些,跳出了一般青春校園劇的窠臼。劇中東北某高中的學生王虎因性格調皮、愛管閑事,被父親轉學到南方城市蓮花市一家國際學校。在南北地域文化差異帶來的極致反差里,展開了一系列爆笑校園故事。雖然沒有了常見的青春疼痛文學,但敢想敢干的主創讓東北方言、港臺腔、“泰式”中文聚在一起大雜燴,再加上南北方文化差異,自然而然地產生了一種獨特的喜劇效果,被觀眾戲稱為合格的“電子榨菜”,非常符合下飯劇的需求。
再說《底線》,可以說這是一個典型的成就類作品,旨在展現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最新成果。雖然是主旋律作品,但自從9月16日開播以來,收視率一直高歌猛進,不僅位列省級衛視收視率第一,同時網絡平臺的播放量累計接近30億,更有無數的熱搜話題,將這部劇推到更廣泛的人群面前,引發更大的社會關注,掀起了“追劇學法”、“圍觀庭審”的熱潮。
按理來說,這一類型的作品也是有一個標準打法的:主人公要高大上,故事不求好看但求彰顯成就。但《底線》的主創明顯不甘心制作一個工具作品,依然在創作上有著自己的藝術追求。他們在表達主題之外力求刻畫普通人的故事,打破固有印象,盡可能將司法工作者真實的工作狀態搬上熒幕,讓這部劇像是一部好看、耐看的職業劇,不僅能看到司法改革的成果,更能帶領觀眾進入并不熟悉的司法領域。劇集里有大量的戲份放在了展示法官判案的全流程上,比如以前幾乎很少見過的合議庭辯論,大量的庭前調解工作等等。
《搖滾狂花》的主題并不新鮮,就是講一對母女在分隔多年后重新生活在一起時所經歷的種種,從彼此得到不理解、排斥到認同。這個故事似乎依稀看得到去年周迅演的爆款劇《小敏家》的影子,只是那部劇里是一對母子的故事。《小敏家》里的周迅符合大眾對母親的認知,她對孩子全心全意地付出,甚至可以因此犧牲自己的感情生活。而到了《搖滾狂花》里,姚晨和莊達菲飾演的一對母女不走尋常路,彼此之間沒有那種無源的溫情,剛開始甚至排斥得厲害,女兒換鎖把母親拒之門外,而母親一轉身就用502膠水堵住了鎖眼兒;老媽把女兒的衣服都扔了,女兒在老媽臥室里縱火……當母親不像母親,女兒不像女兒時,要講好這樣一個雞飛狗跳的母女故事自然比傳統的母慈子孝類故事更艱難一些,但也因此變得更好看。對演員來說同樣如此,這樣的母女關系演起來可難多了,只是演好了就會很好看。可以說當創作者覺得不舒適的時候,觀眾就會覺得舒適。
但這種新并非天馬行空、空中樓閣,而是根植于生活、來源于生活。比如《東北插班生》中張文峰用一口港臺腔警告王虎時,王虎卻激動地跟家鄉的老同學視頻,直感嘆張文峰說話和偶像劇里的是一個味兒,把本來很兇的張文峰鬧懵了。這種對港臺腔的固有認識,也是很多人的共識,因此這種表達能讓觀眾與創作者之間達成一種彼此都懂的會心一笑,會讓觀眾覺得創作者是自己人,能夠同頻共振。
《底線》不僅完整真實地展現了法官如何工作的場景,還能隨著劇情的展開,看到鮮明的時代特征。比如全劇開篇的第一個案例,就是以當下正熱門的直播帶貨切入,將“流量至上”的商業環境中出現的勞資糾紛引入公眾視角。在一個個案件中,塑造了一個接地氣的法官群像,讓人覺得他們可親可敬。
古偶劇、校園劇、職業劇……類型劇都有著固有的模式,也都有著各自的舒適區,不愿跳出舒適區的創作者就會越陷越深,最后卻發現舒適區其實只是一片隱藏得很好的泥沼,而敢于跳出來的人則能夠打開一片新天地,引領行業風氣之先,反而能有機會更為舒適。這個道理不僅適用于影視劇創作,也適用于藝術創作的其他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