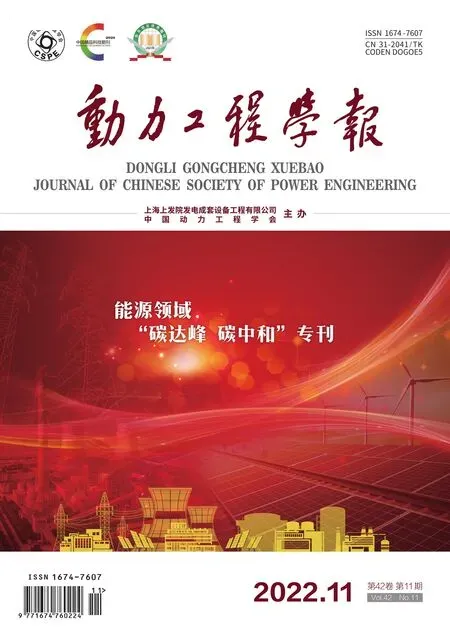風電調頻能力的潛力分析
唐 堅, 唐慶宏, 姚禹歌, 蘇劍濤, 路新江,肖逸雄, 吳玉新
(1.清華大學 能源與動力工程系 熱科學與動力工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084;2.龍源電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037;3.百度商業智能實驗室,北京 100193)
電力系統穩定包含電壓穩定、頻率穩定和功角穩定。隨著電源結構的不斷優化,應重新審視電力系統的穩定性和現代意義[1]。火電在我國電力系統中占據主導地位,但火電將化石能源轉換為電能[2-3],會對環境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國家“雙碳”目標提出后,燃煤機組向高效燃燒、清潔化方向發展[4-6],風電等新能源裝機容量也快速增長[7]。風能的儲藏量豐富、技術可開發程度高,因此風電的開發取得了較大發展,2021年風電新增裝機4 000萬kW。2021年發布的《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中指出要繼續推進風電協調快速發展。未來新能源電力將在電網中占據更大比例,充分挖掘新能源電力的調頻潛力對電網穩定及電網對新能源電力的吸納能力至關重要。
電力系統調頻是指當電力系統頻率相對額定頻率發生偏移時,電力系統中發電機組為平抑頻率波動,自動增減有功功率進行調節的過程[8]。大電網頻率波動主要有2種類型:一是小幅頻率波動,主要是正常運行過程中由于功率與負荷不匹配引起的波動;二是較大功率缺額引起的擾動,主要是由于聯絡線故障等原因引起的較大幅值頻率波動。
電力系統正常運行下的頻率波動以高頻次、低幅值為主,一般越過頻率死區時間不超過3 s,劉輝等[9]統計了華北電網頻率日越過調頻死區±0.033 Hz的次數為1 670次。可見,系統正常運行下的頻率波動需要機組頻繁動作參與調頻。在電力系統面臨較大功率缺額情況下,如“9·19”錦蘇直流閉鎖故障,系統產生3.55%功率缺額,在故障發生后12 s頻率下降至最低值49.56 Hz,造成較大頻率降幅,頻率的恢復過程也較長[10]。
考慮到風電自身出力波動性對電網的影響,風電裝機容量的增加將使系統暫態頻率特性惡化,削弱電網對突變事件的抗干擾能力。風機自身具有轉動動能較大及電控迅速的特點,如能挖掘風電的調頻優勢與潛力,則對提升電網吸納風電的能力,以及保證電網安全具有重要意義。因此,筆者首先分析火電與風電的調頻特點,從能量分析的角度提出了風機調頻潛力的評估方法,并在風電火電協同運行場景下分析風電參與電力系統的調頻能量值,挖掘風電調頻潛力。
1 風電與火電調頻特性分析
1.1 火電機組調頻特性分析
當電力系統出現頻率偏差時,火電機組調頻特性分析頻率偏差通過速度不等率換算成負荷偏差信號,經過電液轉換器和油動機組組成的電液伺服系統改變閥門開度,從而改變汽輪機進汽量,增減機組出力,從而平衡功率的供需關系,維持電網的頻率穩定。部分學者對電力系統火電機組調頻特性進行分析,并對機組一次調頻性能進行了優化[11-12]。由上述研究可知,火電機組調頻需要主蒸汽閥門及一系列機械結構動作和蒸汽做功過程,才能形成功率輸出,為電網提供調頻能量,這與電網頻率的快速響應需求是矛盾的。在特定情況下,如“9·19”錦蘇直流閉鎖事故,15 s內一次調頻正確響應的機組為59.6%,性能滿足要求的僅占12.5%,調頻能量釋放不足的現象進一步加劇[10,13]。為分析火電機組的調頻特性,基于文獻[14]的研究對600 MW超臨界機組調頻能力進行計算,其支撐電量(即調頻能量)的計算結果見表1。
由表1可知,機組提供30 s以內的支撐電量遠小于30 s之后的支撐電量,火電機組短時調頻能量貢獻小于長時間尺度調頻能量貢獻。原因在于火電機組頻率響應過程要經歷的蓄熱釋放、做功及形成功率輸出過程時間較長(>30 s)。但是,火電機組燃料投入可控,可為電網持續提供可控、足夠的調頻能量。因此,火電機組短時頻率響應能力較差(0~30 s),其優勢在于長時間尺度調頻能量的可持續性(>30 s)。

表1 600 MW機組調頻能力折合電量[14]Tab.1 Equivalent electric quantity of the 600 MW unit frequency regulation[14]
1.2 風電機組調頻特性分析
風電機組調頻能量主要來源于旋轉動能和減載預留2個途徑。
1.2.1 旋轉動能
雙饋風電機組的旋轉動能主要儲存在風輪、傳動軸、齒輪箱和雙饋電機轉子等組成的傳動鏈中。電力系統調頻過程通過控制風輪轉速來實現旋轉動能的吸收與釋放,為電力系統提供調頻能量。衡量風電機組旋轉動能的調頻能力主要以轉動慣量較大的風輪和電機轉子為主,可用等效轉動慣量表示:
JT=Jr+JgN2
(1)
式中:JT為等效轉動慣量;Jr為風輪轉動慣量;Jg為電機轉子轉動慣量;N為傳動比。
當風電機組滿足式(2)時,風電機組可參與調頻。
ω>ωlow
(2)
式中:ω為風電機組當前轉速;ωlow為機組能提供調頻動能的最低轉速。
假設風電機組運行在最大功率狀態的初始轉速為ω0(ω0>ωlow),調頻過程轉速變為ω1,則機組理論上可吸收和釋放的旋轉動能ΔEk可通過式(3)計算:
(3)
風電機組依靠調節風輪及轉子轉速突變來提供旋轉動能參與調頻,具有快速響應的特點,可以在毫秒級時間尺度下響應電力系統的頻率變化,為系統提供短暫的調頻能量。
1.2.2 減載預留
風電機組的減載控制方法有2種:一種是轉速控制,使風電機組的機械功率大于電磁功率,轉子超速運行,風電機組輸出功率降低;另一種方法是槳距角控制,通過增大槳距角而減少風力機捕獲的機械功率,使風電機組輸出功率降低,預留功率參與調頻。
全風速下某風電機組的典型理想減載運行曲線見圖1,MPPT曲線為最大風能捕獲模式,縱坐標為風力機輸出功率標幺值,ωN為風力機額定轉速。風電機組運行在最大功率跟蹤區時,優先采用轉子超速運行減載控制,由于槳距角動作屬于機械動作,頻繁動作將影響風機使用壽命,而且尾渦效應也會對機組的槳距控制產生負面影響[15]。當運行在高風速時,風電機組轉速已達到額定轉速,轉子無法超速運行預留功率,此時需增大槳距角以降低機組捕獲的機械功率。

圖1 風電機組的理想減載運行曲線Fig.1 Ideal load reduction operation curves of the wind turbine
1.2.3 風電調頻特性及潛力分析
截至2021年11月14日,我國風電并網裝機容量突破3億kW,充分發揮風電在電力系統中的調頻作用對電力系統穩定及電網吸納新能源電力具有重要意義[16]。部分學者對風電機組的頻率響應控制方式或協調策略進行了研究,通過優化控制模型使得風電機組更快響應頻率變化[17-19]。張梅等[20]和郭雁一夫等[21]通過開展風電一次調頻擾動試驗,證明了風電一次調頻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目前,丹麥、西班牙等風電強國已經將風電一次調頻技術列為普遍性要求[22],我國標準GB 38755—2019 《電力系統安全穩定導則》[23]也明確要求風電要具有一次調頻能力。
由于風電機組功率輸出波動性大,需要依靠穩定性強的控制系統來優化功率輸出,從而輸送優質電能[24-25]。風電機組參與電力系統調頻主要依靠電子元器件的動作控制執行風電功率的吸收和釋放,在時間尺度上可以快速響應電力系統頻率變化。因此,風電機組響應快速,具有參與快速調頻的潛力,但同時也存在調頻能量供給不持續的缺點。
目前,研究者們已開展了風電參與調頻的研究并得到應用,而對于風電參與調頻的潛力分析仍鮮有報道。考慮到風電參與調頻的能量釋放速率非常迅速,而風電調頻能量在短時間內(如30 s以內)的波動相對較小,因此風電的調頻潛力主要集中在30 s內的快速電量調整。在0~30 s內,理論上風機本身具備的旋轉動能或減載預留能量均可以通過電子原件動作迅速輸出,滿足電網的調頻要求。因此,可將風機所具備的機械轉動能量裕度(即風電調頻能量)作為評估風機調頻潛力的定量指標。下文從風電調頻能量的角度來定量分析風電及風電火電協同發電場景下的風電調頻潛力。
2 風電調頻能量分析
2.1 旋轉動能調頻能量分析
假設每臺風電機組的并網點處電網頻率變化已知,忽略風電機組個體調節差異。為定量說明風電場來源于旋轉動能的調頻能量,以某風電場134臺風電機組總場額定功率Pn場=201 MW運行一個月的運行數據為研究對象,總計443 554個采樣時刻。間隔10%風電場額定功率(即0.1Pn場)劃分功率區間,對風電場在不同功率區間運行時的調頻能量進行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各功率區間的樣本數均超過1 000,具有統計意義。由表2可知,風電場運行功率區間主要集中在40%Pn場以內,此時累計時間占比超過86%,風機運行臺數超過93%。

表2 風電場在不同功率下的調頻運行數據Tab.2 Frequency regulation data of wind farm under various power conditions
單臺風電機組來自旋轉動能的調頻能量可通過式(3)計算,根據風電機組風輪轉速變化2 r/min來計算風電機組釋放的旋轉動能,最終得到風電場所有風電機組旋轉動能提供的調頻能量隨功率的變化如圖2所示。

圖2 旋轉動能調頻能量隨風電場功率的變化Fig.2 Wind turbine rotating kinetic energy versus wind farm power
從表2和圖2可以看出,風電場一月運行時段中除3.16%的零功率運行時段無法提供調節電量之外,其余運行時段均可提供調頻能量,且通過旋轉動能提供調頻能量的份額隨風電場輸出功率的升高而增加,意味著風電機組出力越大,可提供的調頻能量也越大。風電場約有76.48%的時間段運行在0~0.3Pn場功率區間內,此時風電場最高可提供來自旋轉動能的調頻能量為513.70 MJ。分析表明,在實際運行中風電場具有為電網提供穩定、可靠、高效、充足的調頻能量的潛力。
2.2 減載預留調頻能量分析
風電機組減載預留調頻方式同樣可以實現快速響應,為電力系統提供調頻功率。如前所述,若單臺風電機組輸出功率P>0.1Pn=150 kW(Pn為風電機組額定功率,Pn=1.5 MW),則認為其具備調頻能力,計算某風電場134臺風電機組以減載預留功率調頻方式為電網提供調頻能量隨功率的變化關系如圖3所示。從圖3和表2可以看出,機組調頻能量及參與調頻風電機組臺數整體隨風電場輸出功率的增加而增加。風電場15 s支撐電量及30 s支撐電量都能為電力系統提供充足的0~30 s調頻能量,具有較大的調頻潛力。實際運行數據表明(見表2),在一個月運行時間內,風電場在減載預留調頻方式下有91.15%的時間可提供調頻功率,當風電場輸出功率在0.1Pn場以上時,約61.9%(83/134)的機組可提供0.1Pn調頻功率;當風電場輸出功率在0.3Pn場以上時,91.8%(123/134)以上的風電機組可提供0.1Pn調頻功率。

圖3 減載預留調頻能量及調頻功率的變化Fig.3 Frequency regulation energy reserved for load shedding versus wind farm power
分析結果表明,風電場具有提供0~30 s充足調頻能量的潛力,可以彌補電網0~30 s火電機組調頻能量釋放不及時的缺點,風電參與電力系統調頻具有響應快速、短時(0~30 s)能量充足的特點,可以作為優質調頻資源開發利用。
3 風電火電協同運行下系統調頻潛力
在調頻性能方面,風電機組具有響應快速的優點,但也具有調頻能量供給不持續的缺點;火電機組雖然響應時間較慢,但是燃料可調,調頻能量供給持續性好。風電機組調頻能量釋放具有毫秒級、秒級尺度,可以更有效地響應電力系統小幅頻率波動;同時,在大頻差事件過程中風電機組0~30 s調頻能量釋放可有效彌補火電機組在頻率陡然跌落過程中能量釋放不及時的缺點,能夠改善電網頻率跌落幅值。
學者們對風電火電協同參與電力系統調頻進行了大量的仿真和試驗研究。部分學者從風火負荷分配[26]、風電火電聯合控制策略[27]和風電火電協同一次調頻控制系統[28]等角度提出了提高風電火電協同調頻效果的模型,并通過數值仿真驗證了模型的有效性和風電火電協同參與調頻的優勢。以上研究表明風電火電協同調頻方法是有效的,但這些研究均從風電機組協調控制方法的角度出發對風電、火電協同參與調頻的控制策略進行了評估,并未考慮風電與火電二者調頻特性的異同。由前文可知,風電調頻的優勢在于0~30 s調頻快速性,火電機組調頻的優勢在于調頻持續性。因此,充分考慮風電調頻的快速性,充分發揮火電機組調頻的持續性,風電火電協同參與電力系統調頻是解決電網持續調頻能量供給的有效方法,可達到更好的電力系統調頻效果。為了證明風電火電協同調頻的優勢互補性,針對典型場景進行調頻能量計算,結果見表3。

表3 風電火電協同運行調頻能量Tab.3 Frequency regulation energy of wind-thermal operation
表3中,區域電網由風電、火電2種電源組成,總輸出功率為8 GW,火電裝機8.4 GW,總共14臺600 MW機組;風電裝機25 GW,總共16 667臺1.5 MW機組。此時,風電承擔58.8%的電量,火電承擔41.2%的電量。
從表3可知,火電機組0~30 s響應能力較弱,風電響應速度較快,同時受其功率波動影響,風電能量用于調節的時間不宜過長,因此選擇0~30 s過程分析該系統可用調節能量變化情況。
根據表3中的30 s支撐電量、旋轉動能和預留功率計算結果,風電火電協同運行時,風電機組可用于電力調節的能量隨風電供電率的增加、風電機組投運臺數的增加而快速增加。旋轉動能和減載預留方式均可提供大于火電機組的0~30 s調頻能量,證明風電具有較大的短時調頻潛力。考慮到減載預留運行的經濟性因素,風電機組來自于旋轉動能的調頻能量能夠滿足電力系統調頻能量需求。風電機組在供電率100%工況下運行時,風電負荷率為32%,意味著風電在不限電運行狀態下具有為電力系統提供0~30 s充足調頻能量的潛力。相比火電高比例運行,風電的加入可顯著提高電力系統短時,即30 s支撐電量(≤30 s)調節能量需求,再次證明風電具有較大的調頻潛力。
圖4給出了不同供電率下火電、風電機組調頻能量對比圖。由圖4可知,風電承擔負荷運行時,提供的調頻能量大于火電,能量隨著風電負荷率的增加而顯著增加。風電機組0~30 s調頻能量的釋放涵蓋了電力系統小幅頻率波動和大頻差事件調節時間尺度。在電力系統功率缺額引起的大頻差事件中,風電具有0~30 s調頻能量投入的潛力,可彌補火電機組0~30 s能量投入不及時的缺點,從而降低系統頻率下降幅度,提高電力系統穩定性。此外,火電機組30 s以上的持續調頻能量投入可滿足電力系統頻率恢復過程能量的持續需求,保證系統頻率恢復至正常值。因此,風電火電協同參與電力系統調頻具有較快的調節速度、更大的調節能力和更高的可靠性。

圖4 不同供電率下風電火電協同運行調頻能量Fig.4 Frequency regulation energy of wind-thermal power operation under different power supply rates
4 結 論
(1) 電力系統頻率波動包含由于功率負荷不匹配引起的小幅頻率波動和由于功率缺額引起的大頻差擾動。火電機組可通過改變燃料投入的方式持續提供調頻能量,而火電可用于快速調節的能量來源于其蓄熱,由于機組蓄熱的釋放至形成功率輸出過程的存在,導致能量釋放不及時,0~30 s調節能力略顯不足。
(2) 風電機組的調頻能量來自旋轉動能和減載預留,可實現毫秒級、秒級響應,響應速度快。風電機組0~30 s調頻能量的及時釋放可以快速響應電網小幅頻率波動和大頻差擾動,彌補大頻差事件中火電機組0~30 s能量釋放不及時的缺點,降低頻率下降幅度。但是,風電機組能量輸入不可控,無法持續提供調頻能量。
(3) 風電場一月運行時間內有96.84%的時間段可提供旋轉動能參與調頻,91.15%的時間段可通過減載預留參與調頻。風電調頻能量隨風電輸出功率的增加和可參于系統調節的風電機組臺數的增加而快速增加。風電機組具有為系統提供0~30 s充足調頻能量的潛力。
(4) 風電火電協同運行假定場景下,風電機組30 s支撐電量遠大于火電機組,具有釋放較大調頻能量的潛力。風電火電協同運行時,火電機組可持續為系統提供長時(>30 s)調頻能量,滿足頻率恢復過程的能量需求。風電火電協同運行可顯著提高0~30 s調頻能量的供給,縮短大頻差事件中頻率下降幅度,提高系統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