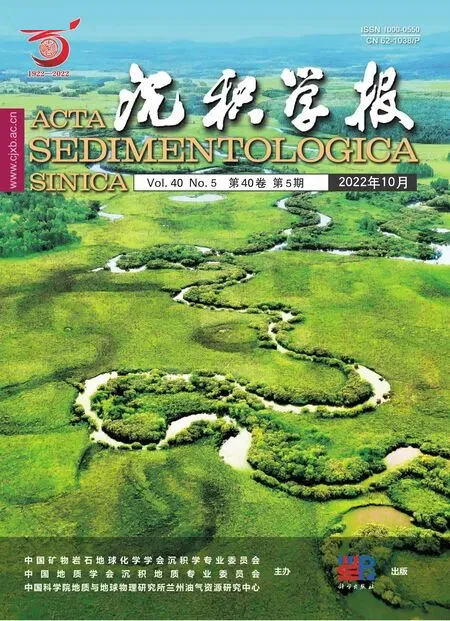基于風暴潮記錄研究紅樹林淤積速率時間變化
劉濤,褚冠宇,徐慧鵬
1.南寧師范大學北部灣環境演變與資源利用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南寧 530001
2.廣西大學海洋學院,南寧 530004
0 引言
紅樹林是生長在熱帶、亞熱帶海岸潮間帶,受周期性潮水浸淹,由紅樹植物為主體的常綠喬木或灌木組成的木本植物群落。紅樹林通常植株密集,故耗散潮水海嘯的水動能作用明顯,有助于防止海岸侵蝕并減少風暴潮和海嘯等自然災害造成的損失[1-4]。紅樹林也可以在沉積過程中埋藏封存大量有機碳,是海岸帶地區最重要的碳庫之一[5-8]。在全球氣候變化背景下,無論是評估紅樹林濕地的保持能力還是估算其碳埋藏速率和通量,長期沉積速率都是最重要的指標之一。當前一般以210Pb 測年法來測定這一指標,但是由于生物擾動、過剩210Pb 輸入通量不恒定等因素,210Pb 測年法在許多紅樹林濕地中并不適用,且依靠210Pb 定年法通常也難以獲取沉積速率的時間變化信息。因此,研究紅樹林長期沉積速率的時間變化信息,進而分析沉積速率對于氣候變化的響應特征,需要尋找其他研究方法。在一些受到熱帶氣旋影響的地區,強風暴潮事件可以將正常海況下難以起動的粗顆粒沉積物輸入紅樹林內,形成風暴滯留沉積層[9-10]。如果能確定這些風暴沉積層的形成時間,即可以將其作為時間標志,確定紅樹林長期沉積速率,分析沉積速率的年代際變化特征。此外,對紅樹林風暴沉積粒度特征的研究,還可用于分析紅樹林植株在風暴潮期間對于浪、流能量的耗散效率。本研究以廣西北海市的金海灣紅樹林為研究對象,結合210Pb 法以及當地風暴潮歷史記錄,確定了紅樹林沉積層中各風暴沉積層的年代,進而厘定了其長期沉積速率和各時段沉積速率,分析了林內沉積速率時空變化的原因。此外,基于風暴沉積粒度特征的研究,探討了紅樹林植株空間結構特征對于風暴潮期間波流耗散效率的影響。
1 研究區域與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對象為位于區域為廣西北海市南部的金海灣紅樹林(21°22′~21°30′N,109°12′~109°21′E)(圖1)。研究區屬北熱帶季風性濕潤氣候,年平均氣溫22.4 ℃,平均降水量1 667 mm,年平均濕度82%[11]。潮汐為全日潮,平均潮差2.36 m,最大潮差5.36 m。大冠沙沿岸海浪主要受季風制約,以風浪為主,最大波高主要出現在5—10月風暴潮季節。冬半年以偏北浪為主,各月平均波高0.3~0.5 m,最大波高為2 m;夏半年以偏南浪為主,各月平均波高0.2~0.3 m,最大波高為1.1 m。

圖1 研究區域的位置與地理環境Fig.1 Location and geological setting of study area
該區域海岸平直開闊,夏季海水鹽度為3.2‰~6.27‰,冬季海水鹽度為24.9‰~27.6‰[12]。紅樹林生長在寬闊沙坪的上部,沿海岸帶呈長條帶狀分布,東西長度約4 000 m,在離岸方向上長度不超過100~400 m,主要樹種為白骨壤(Avicennia marina),林內沉積物主要為泥質砂或者砂質泥。該地區林內土壤在部分岸段從內灘、中灘到外灘依次為淤泥質、泥沙質和沙質[13],一些岸段則是以沙質土壤為主[14],屬硬底型紅樹林基質。
為研究紅樹林濕地的沉積速率和沉積物粒度特征,本文展示了6 個沉積物柱狀樣的相關數據,于兩處橫切紅樹林帶斷面(圖2b)用泥炭鉆鉆探取樣,分別獲得DGS3,JHW1、JHW2、JHW3 和Z1、Z2 鉆孔。DGS3 的取樣時間為2014 年,取樣深度為50 cm;JHW1、JHW2和JHW3的取樣時間為2017年,取樣深度為50 cm,為DGS3 處向海前側等距采樣;Z1 和Z2的取樣時間為2019年5月,取樣深度40 cm。JHW斷面處的紅樹林年齡較老,植株高大(超過3~4 m),樹冠分布高度2~4 m,枝葉繁茂,封閉度高,但是植株間距較大,地面呼吸根十分密集(圖3a);Z 斷面處為2005 年以來擴張生長的紅樹林,樹齡不超過15 年,植株低矮密集(1~2 m)(圖3b),地表呼吸根短而稀疏。

圖2 不同年代紅樹林分布范圍及沉積柱取樣位置(a)2005年紅樹林;(b)2017年紅樹林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ngroves and position of sediment cores in (a) 2005 and (b) 2017

圖3 JHW1 和Z1 紅樹林群叢林分結構(a)JHW1處紅樹林植株高大稀疏,地面呼吸根密集;(b)Z1處的紅樹林植株低矮密集Fig.3 Stand structures of mangroves at JHW1 and Z1(a)old,tall mangrove plant at JHW1;(b)young,short mangroves(1-2 m)at Z1
沉積柱以間隔2 cm 進行分樣,進行粒度測定。其中砂質沉積物以篩析法測定,泥質沉積物以馬爾文公司生產的Mastersizer-3000激光粒度儀測定。測試前首先以濃度為15%的稀鹽酸浸泡樣品去除鈣質碎屑,后加入過氧化氫去除有機碎屑,再加入分散劑浸泡12 h 后方可進行粒度分析測定[15]。在獲取粒度頻率分布數據之后,以矩法計算粒度參數。另取DGS3與JHW1處樣品干燥并研磨過50目標準篩后,稱取約5 g樣品,裝入柱狀樣品管中壓實并用蠟密封管口,放置三周,使226Ra和210Pb處于永久衰變平衡體系。利用ORTEC 公司生產的高純鍺(HPGe)γ 能譜儀測定總210Pb 和補償210Pb 的比活度,兩者之差即為過剩210Pb 比活度(210Pbex)。210Pbex與時間的關系可以指數函數表示:

式中:C(h)為相應于時間t的深度h處的比活度,C(0)為表層沉積物的比活度,λ 為210Pb 的衰變常數(0.031 14 a-1)。
2 結果
2.1 基于沉積物過剩210Pb比活度計算的淤積速率
基于沉積物過剩210Pb 比活度計算了沉積柱JHW1 和DGS3 的長期平均淤積速率,在這兩個沉積柱中,過剩210Pb 比活度隨著深度呈明顯的指數下降趨勢,說明可用CF-CS 模式(Constant Flux,Constant rate of Supply)計算其平均淤積速率[16-17]。根據實測210Pbex數據和深度數據得到擬合曲線(圖4):

圖4 基于過剩210Pb 比活度計算的淤積速率(偏離趨勢線較遠的少數數據不采用)Fig.4 Accretion rate determined by excess210Pb radioactivity in sediment cores
JHW1:y=241.7e-0.051x,R2=0.91
DGS3:y=119.8e-0.020x,R2=0.92
為保證長期淤積速率準確性,JHW1中風暴沉積層數據(比活度≥200 Bq/kg)和DGS3中異常數據不采用。據(1)式計算結果表明,JHW1柱狀樣的14 cm及以下層位平均淤積速率為6.1 mm/a,DGS3 的平均淤積速率為15.6 mm/a。該紅樹林內側的淤積速率顯著高于前緣區,這也是處于波能較強岸線紅樹林淤積速率空間分布的普遍特點,林內淤積速率主要取決于波浪擾動強度,而非納潮量。前緣區由于波浪擾動作用較強,侵蝕事件頻發,其長期淤積速率偏低;而紅樹林內側區域波浪擾動作用微弱,沉積作用連續穩定,其長期淤積速率較高。類似的例子還有越南Ba Lat河口紅樹林,其前緣區在平靜天氣時的短期沉積通量是內側的數倍以上,而長期淤積速率卻低于內側[18]。
2.2 風暴沉積層年代判定
分析各沉積柱的平均粒徑深度剖面,可發現其中均存在數個顯著高于正常水平的峰值,考慮到該區域幾乎每年都要受到臺風影響,風暴潮頻發,這些粗顆粒沉積層應該是強風暴潮期間輸入紅樹林的滯留沉積物。研究當地風暴潮歷史記錄[19-22],可知近80年來當地共發生特大風暴潮5 次(最高潮位超過400 cm),分別發生于1934 年、1965 年、1986 年、2003年和2008 年(表1)。其中1934 年風暴潮較為久遠,臺風命名方式尚未完善,故引用文獻記載描述。

表1 廣西沿岸近80年來的5次強風暴潮(最高潮位>400 cm)Table 1 Information of huge storm surges since 1930s on Guangxi coast
JHW1 沉積柱從上往下依次對照風暴潮記錄進行定年,依據此定年結果(圖5,JHW1)得,1934 年至1986 年的平均淤積速率為5.4 mm/a,其中1965 年至1986 年的淤積速率為4.8 mm/a,1934 年至1965 年的淤積速率為5.8 mm/a,與過剩210Pb 法計算得到的JHW1中14 cm以下的長期淤積速率6.1 mm/a十分接近,表明風暴沉積層定年準確。其中1986年8609號臺風在當地引發了特大風暴潮,最大潮位高達593 cm,為有歷史記錄來的最高水位,可判定出JHW1沉積柱中深度26 cm處風暴沉積層的形成年代為1965 年,深度16 cm 處風暴沉積層的形成年代為1986 年,深度8 cm 處的風暴沉積層應形成于2003年,深度4 cm 處的風暴沉積層應形成于2008 年(圖5)。鑒于該紅樹林內的淤積速率自前緣區向內側增加趨勢,而1986年風暴潮為近60年以來強度最高,合理推測1986年的風暴沉積層在JHW2中位于22 cm深度處,在JHW3中位于34 cm深度處。考慮到1986年之后最大的風暴潮發生于2008年,可確定2008年風暴沉積層在JHW2中位于14~16 cm處,在JHW3中位于16 cm處。2003年的風暴潮強度在4次大風暴潮中相對較弱,在JHW2中,2003年風暴沉積層缺失,推測已經在2008 年風暴潮期間被侵蝕。在JHW3 中,2003年的風暴沉積層尚可識別,位于22 cm深度處。

圖5 沉積柱JHW1、JHW2、JHW3 平均粒徑深度的深度變化(陰影表示風暴沉積事件)Fig.5 Depth profile of grain size in cores JHW1、JHW2、JHW3 (shaded areas indicate storm-deposited events)
確定風暴沉積層的年代后,便可以其為時間標志計算各時段的淤積速率,結果如表2 所示。自1986 年至2017 年,JHW1 處的平均淤積速率為5.3 mm/a,JHW2處的平均淤積速率為7.1 mm/a;JHW3處的平均淤積速率為11.0 mm/a,與位于其向陸后側的DGS3 處淤積速率(15.6 mm/a)也具有可比性。值得注意的是,林內淤積速率有顯著的年代際差異(表2),1986—2008 年,JHW1 和JHW2 處的淤積速率均為5.7 mm/a,JHW3處的淤積速率為7.3 mm/a;而2008年以來,JHW1處的淤積速率僅為2.2 mm/a,JHW2處的淤積速率為10.0 mm/a,JHW3 處的淤積速率為14.0 mm/a。由此得出,2008 年以來該處紅樹林前緣區淤積速率大幅降低,而內側淤積速率則有顯著增加。其西側年輕紅樹林具有類似現象,自2008 年以來,Z 斷面前緣區(Z1 處)的淤積速率僅有2.0 mm/a,而內側(Z2處)高達22.0 mm/a(圖6)。

圖6 沉積柱Z1、Z2 平均粒徑剖面(陰影表示紅樹林沉積)Fig.6 Depth profile of grain sizes in core Z1 and Z2 (shaded areas indicate mangrove deposited layers)

表2 JHW斷面各處淤積速率(mm/a)Table 2 Changes in accretion rates in cores JHW1,JHW2 and JHW3 inferred from ages of storm deposit layers (mm/a)
2.3 風暴沉積的粒度特征及其反映的沉積動力信息
耗散波流能量,減輕風暴潮造成的災害,是紅樹林的一個重要功能。鑒于1986 年與2008 年的兩次風暴潮的強度相差不大,而該段時期內紅樹林的植株空間結構(樹冠分布高度與大小,植株密度等)肯定有所變化,為了探討紅樹林植株空間結構差異對于風暴潮期間波流耗散效率的影響,對比分析了1986 和2008 年紅樹林內風暴潮沉積的粒徑累積概率曲線特征。如圖7所示:1986年JHW1處風暴沉積的平均粒徑為110μm,而JHW2處和JHW3處的平均粒徑為220~250μm,前緣區風暴沉積的平均粒徑反而較內側偏細。紅樹林內側風暴沉積中含有滾動組分,粒徑范圍為1 000~3 000 μm,含量約10%,而前緣區風暴沉積中則沒有滾動組分,這反映當時前緣區紅樹林植株年輕稀疏,地表呼吸根密度極低,難以攔截由外至內輸入的滾動組分。在2008 年,JHW1 處風暴沉積平均粒徑為125μm,與1986 年相差不大;JHW2 處風暴沉積的平均粒徑則僅為80μm,較1986 年顯著減小,且粒徑概率累積曲線中已經沒有滾動組分。推測隨著紅樹林的不斷生長,地表呼吸根密度增加,紅樹林植株高度和樹冠都不斷增大,紅樹林對于風暴潮期間的波流能量耗散效率提高,粒徑大于1 000μm 的組分已經難以被輸入紅樹林內。而在Z斷面,紅樹林非常年輕,2008年風暴潮沉積的平均粒徑高達350~500μm,其中滾動組分的含量為20%~30%,躍移組分的含量為50%~60%。對比表明,在植株矮小的年輕紅樹林中,風暴潮期間波流能量耗散率要顯著低于植株高大的成熟紅樹林。

圖7 不同年代風暴沉積的粒徑累積概率曲線(a)1986年;(b)2008年Fig.7 Cumulative probability of storm deposits in (a) 1986 and (b) 2008
3 討論
3.1 紅樹林淤積速率的時空變化
在潮控型紅樹林或者河口型紅樹林中,輸入泥沙以懸浮顆粒為主,絮凝作用較強,前緣區通常因為由于納潮量大且能首先接受絮凝泥沙沉降,淤積速率通常顯著高于內側[23-27]。而浪控型紅樹林沉積物速率的空間變化特征與此相反,浪控紅樹林的淤積速率主要取決于波浪擾動作用的強弱,前緣區淤積速率通常顯著低于內側區域。金海灣紅樹林即是一處典型的浪控紅樹林,基于風暴沉積層定年,本項研究發現2008年之后金海灣紅樹林前緣區的淤積速率僅為約2.0 mm/a,而內側則高達10.0~20.0 mm/a,該處紅樹林淤積速率存在巨大的空間差異。在海平面上升速率較快的情形下,如果浪控紅樹林前緣區的高程和淤積速率都很低,則紅樹林前緣區會逐漸后退,林帶寬度會變小(紅樹林后側一般有海堤),會進一步導致林內淤積速率逐漸降低。有鑒于此,我們在評估海平面上升威脅下浪控紅樹林濕地的保持能力時,一定不能忽視對于紅樹林前緣區淤積速率的調查,也必須考慮林帶寬度變化導致的紅樹林內淤積速率改變(通常是降低),否則非常有可能高估此類紅樹林濕地的保持能力。
2008年以來,金海灣紅樹林前緣區(JHW1處)的淤積速率僅為2.0 mm/a 左右,較2008 年之前(5.7 mm/a)顯著下降,而紅樹林內部的淤積速率則較2008 年之前顯著上升,該處紅樹林淤積速率存在年代際變化。考慮到該處紅樹林淤積速率主要受波浪能量控制,極端氣候變化是影響波浪能量的主要原因之一。有研究表明當地自2009—2012年的風暴潮發生頻率為1.7 次/年,而1990—2009 年的風暴潮頻率僅為0.7 次/年[28]。風暴潮事件更加頻繁勢必導致前緣區侵蝕事件增加,長期淤積速率因而顯著下降。而在風暴潮事件中,林前光灘和紅樹林前緣區的沉積物通常會遭受侵蝕,并被潮流搬運輸入紅樹林內側沉積,風暴潮頻率的增加從而導致內側紅樹林淤積速率上升。由此,在評估此類紅樹林濕地保持能力時,也必須考慮紅樹林淤積速率對于氣候變化的響應,在不同的氣候情景下同一紅樹林濕地的保持能力可能會截然不同。
3.2 紅樹林植株空間結構對于風暴潮期間波流能量耗散效果的影響
紅樹林內不同位置、不同年代風暴沉積的粒度分析表明,植株高大,樹冠封閉度高的紅樹林對于強風暴潮期間波流能量的耗散程度要顯著高于年齡較小、植株密集低矮的紅樹林。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可能有兩點,第一,強風暴潮期間紅樹林內水深很大,低矮紅樹林的樹冠分布高度有限,無法耗散表層水體的波流能量,而通常表層水體的波流能量遠高于下層水體。植株高大的紅樹林樹冠體積大,分布高度高,可以大量耗散表層水體的波流能量(圖8)。第二,低矮紅樹林植株雖然密集,但是其枝干剛度小,易于搖晃,吸收波浪能量的效率遠不如枝干剛度大的老紅樹林。Masselet al.[29]的對于澳大利亞的Cocoa Creek 河口及日本的Natara 河口紅樹林內波浪特征的現場觀測,也得到了類似結果,即淹沒時水面高度與樹冠分布高度基本一致時,波浪能量耗散最大,而如果淹沒時水面高度低于或者顯著高于樹冠分布范圍,波浪耗散效果則大為降低。

圖8 JHW 斷面紅樹林樹冠高度與歷年風暴潮最高潮位Fig.8 Elevation of mangrove tree crown and the maximum tidal height of huge storm surges at JHW transect
4 結論
(1)以風暴沉積層作為時間標志,可以有效研究紅樹林內淤積速率的年代際變化特征。研究表明:1986—2008 年,金海灣紅樹林前緣區的淤積速率為5.7 mm/a,內側為7.3 mm/a;2008年以后,前緣區淤積速率降至2 mm/a,而內測淤積速率則增加至10~20 mm/a。2008 年之后當地風暴潮頻率增加可能是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
(2)紅樹林內不同位置、年代沉積柱中的風暴沉積層粒度特征分析表明,成熟紅樹林枝干剛度高且能夠有效耗散風暴潮高位表層水體波流能量。受此影響,植株高大、樹冠封閉度高的紅樹林對于強風暴潮期間波流能量的耗散程度要顯著高于年齡較小、植株低矮的紅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