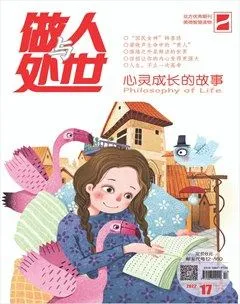“國民女神”韓喜球
張東亮

今年53歲的韓喜球,出生在臺州農村。年輕時參加高考,她報考了成都地質學院。研究生畢業后,韓喜球進入國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現自然資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工作。韓喜球埋頭學術,潛心研究深海多金屬結核。
2007年,中國“大洋一號”開始第19航次的考察,這次的任務,主要是在廣袤大洋中探礦,尋找海底“黑煙囪”。韓喜球說,“黑煙囪”是海底噴射出來的高溫熱液,在遭遇冰冷海水后,沉淀形成黑色金屬硫化物礦的一種現象,形似滾滾黑煙。那里就是“海底成礦工廠”。
在第2航段,憑著以往科考時積累的經驗,韓喜球敏銳地發現了西南印度洋脊上的首個海底“黑煙囪”,以及4個新的熱液活動區。根據內行人介紹,一個海洋地質學家,能找到一處“黑煙囪”,或者一個海底熱液礦化區,就是值得驕傲一輩子的事了。在第3航段中,韓喜球擔任首席科學家,承擔了整個航段的指揮任務。韓喜球這個名字,從此與“中國首位大洋科考女首席科學家”緊緊聯系在了一起。
韓喜球說,與太空探索、登月競爭、極地開發類似,深海一直是國際社會關注的另一處資源戰場。調查和開發海底礦產資源是國家戰略需求,“先來先得”是國際深海探礦的原則。深海探礦,顯然是一場時間與智慧的雙重較量。但是茫茫大海,去哪兒找礦,怎么找?這時,“探寶隊”隊長、首席科學家的判斷至關重要,韓喜球要為航次科學目標的實現負全責。科考船上的工作一般24小時不停歇,作業組4班輪換。作為首席科學家,沒人和她輪班,只要船上的馬達不停轉,韓喜球的工作就不分晝夜。
海上常年烈日當空,甲板被烤得有50℃的高溫。由于陽光曝曬,韓喜球每次出海,原本白皙的皮膚都會被曬傷,她戲稱自己變成了非洲人,過著“流血流汗,掉皮掉肉”的日子。但在韓喜球心中,豐富多彩的海底世界,如絲絹般華麗的洋面,給出海的日子增添了不少詩情畫意。在科考任務進展順利的間隙,她會抽出時間,觀星、賞月、填詞作賦,與強調困難相比,韓喜球更喜歡與大家分享大洋科考的快樂。她說:“海洋科考是一個探索未知的過程,你永遠不知道下一步會有什么樣的驚喜和發現,因此會有一種比較興奮的狀態。”
韓喜球說,海底蘊藏著豐富的礦產資源,比陸地上的礦產種類和數量還多。所以,海底寶藏的研究開發,已經關系到一個國家的資源戰略。而這些資源需要地質學家和海洋科學家,采用相應的深海技術把它們找出來。雖然這個過程復雜而艱辛,但每次取得新發現,都是非常有價值的。所以,她覺得接受大洋科考的挑戰,其樂無窮。
讓韓喜球至今難忘的是,在西南印度洋首次發現“玉皇山”礦床。那是2010年5月,西南印度洋“魔鬼西風帶”,“大洋一號”即將返航的前一天。當時,狂暴的海浪一度直撲到四層高的駕駛臺玻璃窗上,但是一想到已經發現顯著的熱液異常,而下次再回到這片海域不知道是什么時候,韓喜球決定再堅持一下,把多金屬硫化物礦找出來。她和團隊成員從午夜開始等待,凌晨風浪稍有平息的間隙,大家決定把電視抓斗放下海去做最后一搏。這時10 級狂風又呼嘯而來,科考船拖著兩三噸重物逆浪前行。韓喜球在駕駛臺指揮船舶前進的路徑,船長親自操船,科考隊和風浪整整搏斗了四個小時。直到她的對講機嘟嘟作響:“發現紅色熱液沉積物了!”“我們發現硫化物了,已經取到樣品!”
海上的顛簸與辛苦,換來的是豐厚回報。多年來,韓喜球負責主持了幾十項國家和省部級科研項目,在國際及國內一流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60多篇,在大洋多金屬結核、大陸邊緣冷泉碳酸鹽巖等方面均有突破性的調查研究成果。
2020年9月23日,一個三年級學生寫信問韓喜球:“韓阿姨,大海有多深呀?海洋里真的有寶藏嗎?”孩子對海底充滿了好奇與遐想。韓喜球告訴她:“海底像另一個陸地,同樣有溝壑、山丘和平原。太平洋里的馬里亞納海溝最深,達11034米,把整個喜馬拉雅山脈塞進去都露不了頭呢!海洋是一座巨大的寶庫,海底蘊藏著很多礦產資源,還有20多萬種海洋生物。”
入行三十年來,韓喜球踏遍6大洲20多個國家和地區。帶領團隊在海底多金屬結核、富鈷結殼、多金屬硫化物和天然氣水合物等資源的調查研究上,取得了重要成果。根據“先來先得”的國際規則,通過科考調查,為我國申請國際海底區域礦區提供了科學依據和技術支撐。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她為國家爭取到了萬里海底礦場。因為功績卓著,韓喜球先后獲得中國青年女科學家獎、全國三八紅旗手、全國先進工作者、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等眾多榮譽和稱號。
2022年農歷新年,韓喜球在辦公室門口貼上了一副對聯:登山觀錦繡,潛海探深幽。橫批:喜歡地球。前不久,韓喜球海底“尋寶”的事在網上出現后,她一下就火了,被網友親切地稱為“國民女神”。
韓喜球說:“全球經過科學家調查的海底,到目前只占5%,還有95%的海底沒有被探查過。人類對海洋的探索其實才剛剛開始。”
(責任編輯/劉大偉 張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