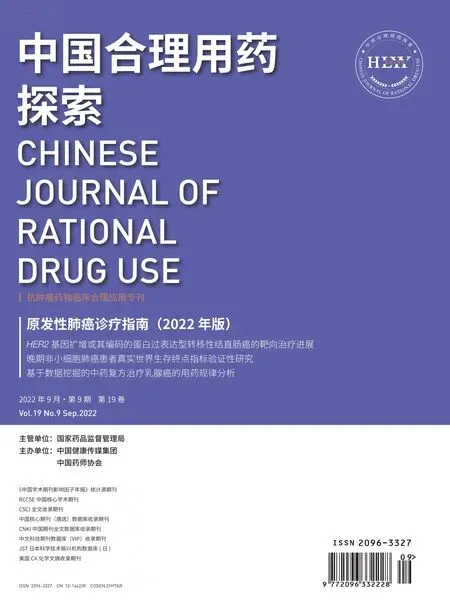1例達拉非尼聯合曲美替尼治療致反復發熱病例分析
黃碩涵,黃烽如,王萌萌,郭子寒
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藥劑科,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腫瘤學系,上海 200032
黑色素瘤是一種惡性程度較高、臨床預后較差的腫瘤,可發生于皮膚、肢端、黏膜、眼血管膜、軟腦膜等不同部位或組織。我國每年新發黑色素瘤患者約2萬人,且發病率和死亡率呈逐年上升趨勢[1]。BRAF V600突變是黑色素瘤最常見的基因突變類型,我國約1/4的黑色素瘤患者存在BRAF V600突變,且與攜帶野生型基因的患者相比,攜帶BRAF突變基因患者的腫瘤進展速度更快,臨床預后更差[2]。有研究證實,達拉非尼聯合曲美替尼雙靶治療可有效提高BRAF V600突變腫瘤患者的生存獲益[3]。
發熱綜合征是達拉非尼聯合曲美替尼雙靶治療常見的不良反應之一。臨床試驗數據顯示超過50%的黑色素瘤患者會出現與藥物相關的發熱,且發熱程度各異[4]。發熱綜合征通常發生在患者用藥初期(前3個月),29%的患者會經歷3次以上的發熱[5]。大多數患者對發熱綜合征可耐受,或經常規處理后體溫可降至正常水平;但若未及時進行適當干預,發熱可致患者脫水,易引發繼發性低血壓及多種并發癥,導致劑量中斷、減量以及永久停藥,進而影響臨床療效[6]。目前,臨床針對BRAF抑制劑聯合MEK抑制劑引起的發熱綜合征尚無統一的診治策略和防治措施,本研究擬通過分析1例達拉非尼聯合曲美替尼雙靶治療的晚期黑色素瘤患者反復發熱的病例,并對其進行合理干預,以期為達拉非尼聯合曲美替尼雙靶治療的發熱管理提供有效的建議,充分發揮臨床藥師在治療團隊中的積極作用。
1 臨床資料
患者,女性,年齡67歲,身高167cm,體重64kg。患者發現左足底黑斑8年,破潰后于外院行活檢檢查,病理結果提示肢端惡性黑色素瘤,Breslow厚度為2.2mm,未見潰瘍、脈管未見癌累及。2021年1月8日外院正電子發射型計算機斷層顯像(positr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PET-CT)結果提示左足底局灶增厚,左側腹股溝淋巴結代謝增高,轉移可能性大。2021年1月21日于本院行左足黑色素瘤廣切術、左側腹股溝前哨淋巴結活檢術,術后病理結果顯示:①左足底:肢端雀斑樣惡性黑色素瘤,范圍約0.5cm×0.3cm,伴潰瘍,Breslow厚度約2.2mm,Clark分級為Ⅳ級,未見明確神經及脈管侵犯,周圍真皮內見纖維組織增生、炎細胞浸潤、多核巨細胞反應,符合局切術后改變。②左腹股溝:淋巴結(1/2)見惡性黑色素瘤轉移(多灶,被膜下和實質內,最大灶直徑約0.19mm)。免疫組化結果為SOX10-Red(+)、HMB45-Red(+)、A103-Red(+)、PNL2-Red(+)、BRAF-Red(弱 +)。2021年 2月20日于本院行腹股溝淋巴結清掃術,術后病理結果顯示左腹股溝淋巴結(0/15)H&E切片未見肯定腫瘤轉移;周圍真皮及皮下纖維組織增生、炎細胞浸潤和組織細胞反應,符合術后改變。基因檢測結果顯示,BRAF基因第15外顯子呈突變型,CKIT基因第9、11、13、17外顯子和NRAS基因第2、3、4外顯子未見肯定突變。
2 藥物治療及發熱管理過程
患者于2021年4月7日開始進行達拉非尼聯合曲美替尼的術后雙靶輔助治療,具體用藥方案為:甲磺酸達拉非尼膠囊[Novartis Farmacutica SA,注冊證號H20190066,規格75mg(以C23H20F3N5O2S2計)]150mg/次,口服,q12h;曲美替尼片[GlaxoSmithKline Manufacturing S.p.A,注冊證號H20190069,規格2mg(按C26H23FIN5O4計)]2mg/次,口服,qd。患者于2021年8月4日上午服藥2h后出現發熱癥狀,體溫達38.0℃,臨床藥師建議患者暫時停藥并就醫,以明確發熱原因。當晚患者退熱,臨床藥師建議觀察,退熱超過24h后可恢復用藥。患者于2021年8月5日晚上再次出現發熱癥狀,體溫達39.0℃,并于2021年8月6日至當地醫院就診。實驗室檢查顯示C反應蛋白(C reactive protein,CRP)水平為24.65mg/L,白細胞及中性粒細胞計數無異常,外院診斷為非感染性發熱并給予布洛芬緩釋膠囊(上海信誼天平藥業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31022720,規格0.3g)和連花清瘟顆粒(北京以嶺藥業有限公司,國藥準字Z20100040,規格每袋裝6g)退熱,具體用藥劑量不詳。患者于2021年8月7日體溫恢復正常,隨后四肢出現大面積皮疹(3級),外院予甲潑尼龍片(天津金耀藥業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20020224,規格4mg)、依巴斯汀片(杭州仟源保靈藥業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20040503,規格10mg)、復方甘草酸苷片(樂普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20073723,規格每片含甘草酸苷25mg、甘氨酸25mg、蛋氨酸25mg)治療,具體用藥劑量不詳。2021年8月21日患者皮疹完全消退,以原劑量恢復達拉非尼聯合曲美替尼治療。患者于2021年8月29日晚上再次出現發熱癥狀,體溫達38.8℃,自行停藥,并服用布洛芬緩釋膠囊0.3g/次,bid,對癥處理后好轉。2021年8月30日外院早晨血常規、CT結果顯示無異常,晚上患者發熱至39.2℃,檢查結果顯示患者CRP水平為49mg/L且伴有白介素6(interleukin-6,IL-6)、降鈣素原升高,分別為55.67pg/ml、0.05ng/ml,尿液檢查結果提示患者有尿路感染,給予布洛芬緩釋膠囊0.3g,口服,St;注射用頭孢西丁鈉(揚子江藥業集團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20057973,規格按C16H17N3O7S2計1.0g)2g/次,q12h,ivgtt;乳酸左氧氟沙星氯化鈉注射液[浙江醫藥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藥廠,國藥準字H20053161,規格250ml∶乳酸左氧氟沙星0.5g(以C18H20FN3O4計算)與氯化鈉2.25g],500mg/次,qd,ivgtt。患者于2021年8月31日凌晨再次出現發熱癥狀,體溫達39.5℃,服用布洛芬緩釋膠囊后發熱癥狀消失。患者自述退燒藥效果欠佳,因此,臨床藥師建議口服10mg潑尼松片治療,同時外院醫生開具同類藥物地塞米松10mg(具體廠家信息不詳)靜脈滴注。患者于2021年9月7日退熱,開始恢復達拉非尼聯合曲美替尼雙靶治療,為防止再次出現發熱綜合征,臨床藥師建議患者每日早晚同服5mg潑尼松片。患者于2021年9月18日自行停用醋酸潑尼松片(天津信誼津津藥業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31020675,規格5mg)后,次日上午出現寒戰等不適癥狀,恢復服用醋酸潑尼松片后不適癥狀好轉。患者于2021年10月7日中午出現第3次發熱癥狀,體溫最高至39.4℃,立即停用達拉非尼和曲美替尼,口服布洛芬緩釋膠囊未見好轉,晚上體溫升至39.7℃,檢查結果提示CRP為29.24mg/L、白細胞及中性粒細胞計數無異常,外院予輸注注射用阿洛西林鈉(浙江金華康恩貝生物制藥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10960152,規格2.0g)8g/次,q12h,ivgtt和倍他米松磷酸鈉注射液(具體廠家信息不詳)4mg,qd,ivgtt,輸液結束后體溫降至37.6℃。次日早上患者體溫上升伴皮疹(2級)癥狀發生,至外院輸注注射用頭孢西丁鈉2g,q12h,ivgtt,注射用谷胱甘肽(上海復旦復華藥業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20060450,規格0.9g)2.7g,qd,ivgtt和注射用地塞米松磷酸鈉(具體廠家信息不詳)10mg,qd,ivgtt對癥處理,輸液結束后體溫降至37.0℃。2021年10月14日,考慮到患者此次體溫恢復時間已超過24h及臨床療效,臨床藥師建議患者恢復雙靶用藥,并每日早晚同服5mg醋酸潑尼松片預防發熱綜合征。患者于2021年11月11日體溫升至38.6℃,服用布洛芬緩釋膠囊后逐漸好轉;2021年11月12日中午體溫升至38.7℃,服用布洛芬緩釋膠囊0.3g,St后升至39.0℃,輸注頭孢類藥物(具體藥物不詳)和注射用地塞米松磷酸鈉(具體廠家信息不詳)10mg,qd,ivgtt進行治療;次日患者體溫恢復正常,繼續輸注頭孢類藥物(具體藥物不詳)、口服醋酸潑尼松片。患者后續用藥期間再未出現發熱綜合征,并于2021年12月21日完成了相應療程的術后達拉非尼聯合曲美替尼雙靶輔助治療。
3 分析與討論
發熱綜合征是達拉非尼聯合曲美替尼雙靶治療的常見不良反應,發生率達52%~71%,通常表現為發熱(≥38℃)或寒戰、畏寒、盜汗,伴有或不伴有流感樣癥狀。發熱多為1級(38℃~39℃)和2級(>39℃~40℃),3~4級(>40℃)發熱發生率較低[4]。此外,發熱綜合征也是改變患者治療策略過程中最常見的不良反應,包括劑量中斷(30%~32%)、劑量減少(13%~14%)和永久停藥(2%~3%)。研究表明,達拉非尼聯合曲美替尼引起第一次發熱的中位時間為19天(1~82天),中位持續時間9天,繼發(第2~4次)事件的中位時間為24~31天,繼發事件的中位持續時間為4~5天[6-7],且35%的患者在首次發熱時出現皮疹,81%的患者在發熱后開始出現皮疹。患者發熱期間可伴有CRP、IL-6水平升高,但中位中性粒細胞計數仍保持在正常范圍。此外,超過50%的患者經歷了反復發熱。本研究中,患者用藥近4個月后首次出現發熱癥狀,血液檢查結果顯示CRP升高、中性粒細胞計數保持在正常范圍內。因患者首次出現發熱癥狀的時間較晚,與文獻報道的首次發熱均發生在患者用藥的前3個月不符,因此臨床藥師一開始不能判斷患者發熱是否與達拉非尼聯合曲美替尼相關。但在后續的隨訪中,發現患者首次發熱后出現皮疹,停藥對癥治療后體溫可恢復正常,且再次恢復達拉非尼聯合曲美替尼治療后,患者反復、多次出現發熱,符合達拉非尼聯合曲美替尼治療相關發熱的特征和表現。
達拉非尼和曲美替尼聯合治療黑色素瘤所致發熱綜合征的發病機制尚不清楚。與達拉非尼單藥治療方案相比,接受聯合治療方案的患者發熱綜合征發生率增加,但接受曲美替尼單藥治療的患者未發生發熱癥狀[8-9],提示曲美替尼可能影響由達拉非尼驅動的發熱過程,推測是BRAF抑制劑刺激炎癥小體的活化、促進樹突細胞中IL-1β的生成,進而導致炎癥反應、引起發熱等癥狀[10]。發熱曾被認為是達拉非尼相關不良反應,在既往研究(COMBI-d,COMBI-v)和藥品說明書中都涉及達拉非尼的減藥或停藥[3,9]。多項臨床試驗(COMBI-APlus、COMBI-i)表明,“停用雙藥,原劑量恢復治療的發熱管理策略”較“僅中斷達拉非尼單藥,重啟時考慮減量或停藥”的發熱管理策略更優,且不影響療效[11]。基于上述研究,美國臨床腫瘤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ASCO)于2021年公布了最新發熱管理流程,提示患者一旦體溫超過38℃,應立即停用達拉非尼和曲美替尼,然后服用非甾體抗炎藥退熱;并鼓勵患者口服補液避免脫水,對于口服攝入困難或者并發癥風險高的患者可以靜脈補液;退熱緩解24h后可考慮原劑量恢復達拉非尼和曲美替尼雙靶治療;口服非甾體抗炎藥效果不佳者,可選用糖皮質激素(如潑尼松)進行退熱治療。
對于發熱綜合征,不常規推薦使用抗菌藥物治療,建議在明確感染或發生3~4級中性粒細胞缺乏的情況下使用抗菌藥物[12]。值得注意的是,達拉非尼聯合曲美替尼雙靶治療相關發熱綜合征可引起患者CRP升高,但中性粒細胞計數仍保持在正常范圍內[13]。
本研究中,患者服用達拉非尼和曲美替尼4個月左右開始出現發熱癥狀,初期臨床藥師建議暫停用藥,經服用布洛芬緩釋膠囊退熱緩解24h后恢復用藥,后又出現多次非感染性發熱癥狀,且為叢集性發熱,主要表現為30天內發熱-緩解過程超過3次[14],推測是由于患者自身和當地醫療機構對達拉非尼聯合曲美替尼雙靶治療引起的發熱綜合征認識不足并采取了不恰當的處理方式。該患者除明確尿路感染引起的發熱而使用抗菌藥物治療外,其余多次在僅CRP升高的情況下使用抗菌藥物是不合理的。患者初期出現發熱后使用布洛芬緩釋膠囊退熱效果較好,后續再次出現發熱后,服用布洛芬緩釋膠囊退熱效果欠佳,臨床藥師建議患者立即換用糖皮質激素。患者于外院輸注地塞米松注射液后,發熱逐漸緩解。
本研究中,患者經歷反復多次發熱后,擔心繼續服用達拉非尼和曲美替尼可能再次引起發熱。目前對于達拉非尼和曲美替尼致反復發熱的患者,尚無針對性的研究和成熟的預測手段。Lee等[15]的研究提示,非甾體抗炎藥以及減量用藥方案無法預防達拉非尼和曲美替尼所致的發熱綜合征,而皮質類固醇有一定的預防作用。鑒于目前國內尚無可替代的藥物聯用方案,為保證患者順利完成術后輔助治療,本院臨床藥師針對該患者的處理建議是使用類固醇激素進行預防和退熱處理,即每日口服10mg潑尼松。患者服用潑尼松后雖仍有用藥后出現發熱綜合征的現象,但發熱的嚴重程度降低,且因發熱的停藥時間較前縮短,最終患者順利完成相應療程的治療。在治療過程中,患者若能繼續耐受,建議繼續給予原劑量達拉非尼和曲美替尼雙靶治療;若患者不能耐受,可考慮梯度減量,即先減量達拉非尼,無改善時可再減量曲美替尼,也可考慮間歇給藥策略。
4 小結
達拉非尼和曲美替尼聯用是攜帶BRAF V600突變的黑色素瘤患者術后輔助治療(Ⅲ期)的首選方案,其相關發熱綜合征的管理也給臨床工作者帶來了巨大挑戰。本研究通過分析1例達拉非尼聯合曲美替尼雙靶治療引起的黑色素瘤術后患者反復發熱綜合征,探討了發熱綜合征的發生規律、潛在機制、相關定義以及相應的處理措施,為后續臨床藥師參與達拉非尼和曲美替尼聯合治療的藥學監護和服務提供了一定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