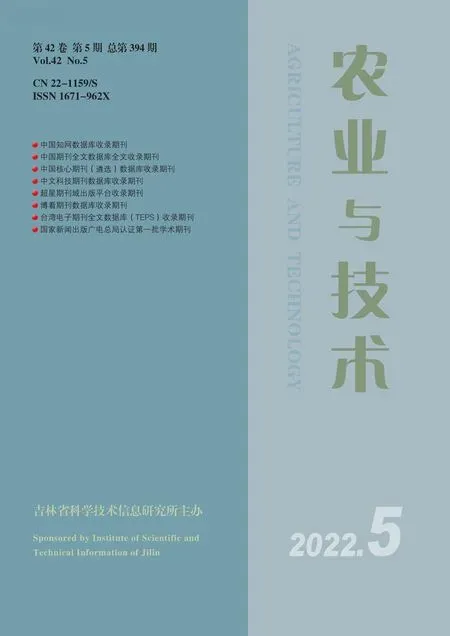土壤中鉛的危害遷移轉化及修復技術概述
王璐瑤李健鋒
(1.陜西省土地工程建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陜西 西安 710075;2.陜西地建土地工程技術研究院有限責任公司,陜西 西安 710075;3.自然資源部退化及未利用土地整治工程重點實驗室,陜西 西安 710075;4.陜西省土地整治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陜西 西安 710075)
鉛對人類和動物均有毒害作用,特別是幼兒。鉛及其化合物廣泛分布于環境中,且對人體有毒害作用,幾乎影響身體的每個系統,1995年,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皮膚和肌肉為僅有的2個不受鉛暴露傷害的系統。受污染的土壤、家庭灰塵、油漆碎片、礦山廢物和工業廢物等是人類接觸鉛的典型來源。由于異食癖的頻率、手到嘴的行為(如吮拇指、咬指甲和吃非食物物品)以及更高的腸道吸收和滯留率,兒童比成人更容易接觸鉛。吸收的鉛可能被運送到身體的所有器官和組織,如大腦、肝臟、腎臟或骨骼,然后傷害身體細胞,也可能通過多種途徑排出體外。鉛通過成土作用進入土壤環境,這與母質的起源、性質以及人為活動有關,其中,人為活動是土壤鉛污染的主要來源,包括工業、制造過程以及工業、生活廢物處理等。鉛在環境中的遷移主要取決于含鉛物質的形態,如果不考慮鉛的化學形態和礦物形態,就無法預估環境中鉛及其化合物的存在及其對生態系統和人類的潛在毒性[1]。因此,了解鉛的形態至關重要,不僅可以預測其遷移特性和生物可給性,還可以評估其對生物的潛在風險。本文針對含鉛化合物的特性、危害及遷移特性展開闡述,提出常用低成本、短周期鉛污染土壤修復方法,以期為重金屬污染土壤修復研究提供理論參考。
1 含鉛化合物的特性
鉛一般以溶解態或懸濁顆粒存在于水體中,但易溶性的鉛化合物很少,大部分鉛都會以固體形式沉淀,最終聚集在河流、湖泊、海洋的沉積物中。通常來說,土壤中的鉛是相對難溶的,溶解性的鉛含量僅占總Pb的1%~0.01%,并且遷移性較低,土壤中鉛的半衰期估計為740~5900a[2],因此,被鉛污染的土壤在數百年甚至數千年的時間里都保持著高鉛含量。另外,鉛化合物在酸性條件下更具遷移性,如礦物采選廢料或垃圾滲濾液。生物有效性是指土壤中物質或元素中可被生物體(如人類、動物或植物)吸收的部分。對于Pb而言,主要關注的是通過意外攝入土壤對人類的生物有效性,而植物有效性可用于描述可被植物吸收的土壤Pb。土壤中的Pb主要以3種方式存在,作為微溶礦物相的沉淀;吸附在粘土、Fe和Mn氧化物、堿土金屬碳酸鹽和硅酸鹽晶格上;通過與土壤有機質相互作用形成相對穩定的復合物[3]。鉛的遷移率取決于許多因素,土壤中鉛的形態、總含量、土壤的類型、土壤的pH值、土壤的水分含量以及降雨等引起的土壤水滲透。土壤、沉積物和礦物采選廢料中含鉛化合物的種類非常多,包括PbO、Pb(OH)、Pb3O4、PbO2、PbCO3、Pb2CO3Cl2、Pb3(CO3)2(OH)2、PbCO3·PbO、PbSO4、PbSO4·PbO、PbHPO4等。方鉛礦(PbS)是最常見的含鉛礦物,也是唯一一種富含Pb的礦物,含鉛量可達87%,方鉛礦可帶來可觀的經濟價值。在存在硫的還原體系中,最穩定的Pb固體形式是PbS。而在氧化環境中,如暴露于大氣或富氧水域,方鉛礦很容易轉化為其它常見形式的鉛,如角鐵礦(PbSO4)、白鉛礦(PbCO3)和火山鐵礦(Pb5(PO4)3X;X=Cl-,F-,OH-)將硫化鉛氧化成硫酸鉛。在各種復雜環境條件下,相比大多數鉛化合物,磷酸鹽狀態的鉛,尤其是火山灰巖是鉛最穩定的狀態[2-5,38,39]。一般而言,磷酸鉛鹽的穩定性大致為Pb5(PO4)3Cl>Pb5(PO4)3Br>Pb3(PO4)2>Pb5(PO4)3OH>Pb5(PO4)3F>Pb4O-(PO4)2>PbHPO4>Pb(H2PO4)2[4]。
2 土壤中鉛的危害
土壤不僅是農業的基礎,也是人類食品安全、飲水安全和生態環境安全的保障,自然或人為活動所排放的鉛進入土壤后不僅污染土壤,一定程度影響土壤質量、農作物土壤生態功能,種植在污染土壤中的植物在累積一定濃度的重金屬后,其代謝功能就會失調,使得作物產量低下造成作物的經濟損失,另外,還會通過食物鏈進一步危害人類健康。土壤中的鉛通常可經口、皮膚、呼吸道等途徑進入人體,其中,經口直接攝入是人體暴露于Pb的最主要途徑,特別是兒童因手口活動直接接觸造成的無意經口攝入。重金屬鉛具有神經毒素,嚴重影響兒童智力的發育,兒童血鉛含量與土壤的Pb含量密切相關,若長期暴露,兒童的智力及行為發育將受到影響。目前在我國關于重金屬污染土壤篩選、管控和人體健康風險評價標準是基于污染物總濃度,尚未其生物有效性,而土壤中鉛的總量僅可給出關于金屬富集的信息,不能說明該元素在上壤中的賦存狀態、遷移能力及對人體健康的影響[5]。
3 鉛的遷移轉化
除了固相控制土壤溶液和水體中的Pb2+活性外,吸附過程也會影響Pb2+的活性。某些水體中Pb2+活性的上限取決于沉淀的Pb固體的溶解度,然而,在實際測量中,大多數受試河水的鉛含量都遠遠低于其已知所含Pb固體的溶解度[6]。在平衡時,由于特定系統的陽離子交換能力,系統中溶解Pb的活性可能低于根據沉淀Pb固體物質的溶解度計算得出的活性。由于Pb或多或少不可逆地吸附在有機和無機表面上,因此在某些系統中,Pb的濃度可以通過吸附反應來控制。有學者建議可使用鐵氧化物、二氧化錳、磷灰石、粘土礦物、干浮游生物和泥炭蘚作為鉛的吸附劑。
4 鐵和錳氧化物對鉛的吸附
已有多項研究發現,新沉淀的Fe和Mn氧化物的表面是大多數溶解性金屬離子的高活性吸附位點,這些氧化物固定金屬離子的2個主要過程是特異性吸附和共沉淀。McKenzie[7]表明,9種合成的錳氧化物和3種合成的鐵氧化物對金屬離子的固定是由于強的特異性吸附,除針鐵礦外,這些氧化物對鉛的吸附均比鈷、銅、錳、鎳和鋅的吸附強,且Pb在這些氧化物表面上的吸附量會隨著pH值和表面積的增加而增加,而可以用電解質溶液置換的Pb吸附量通常很低(約10%)[8]。因此,吸附與共沉淀作用有利于保持土壤溶液和水中的低可溶性鉛水平。氧化物與金屬離子除了可以形成氧化物-金屬配合物外,還可以形成三元配合物,即氧化物表面-金屬-配體,配體可以是無機或有機配體。當磷酸鹽或硫酸鹽存在時,Fe和Al氧化物對對土壤中Zn2+的吸附增強,進一步證實了三元配合物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作用[9]。類似地,Al(OH)3在Ca2+和Cd2+等二價金屬離子存在下可增強對磷酸鹽的吸附,也表明金屬-磷酸鹽絡合物在氧化物上的吸附。
5 鉛污染土壤的修復
目前常用的污染土壤修復技術如異位固化穩定化、淋洗等,成本均較高且具有一定的破壞性,在去除鉛或降低鉛生物有效性方面往往是無效的,并且無法恢復土壤生產力。Cunningham等[10]對植物修復技術進行了研究,在植物吸收土壤Pb的過程中,Pb必須被植物根系吸收,轉移到植物頂部,通過植物收獲達到去除土壤中Pb的目的。然而,目前還有幾個問題需要解決,Pb在土壤中的低溶解度可能導致Pb無法被植物吸收;Pb從根部到頂部的轉移能力較弱;鉛可能對植物組織有毒害作用。許多研究人員建議通過使用有機螯合物來解決這3個潛在問題,但這也可能會導致其它問題,如鉛向下的遷移增強,進而污染地下水并通過地表和地下徑流導致Pb的擴散。此外,植物修復還可能危害以這些植物為食的食草動物,且修復時間較長,有研究通過分析在污染土壤上生長的植物的典型產量和大多數植物可收獲組織的鉛濃度,推測該項技術大約需要7~10a才能將土壤鉛濃度降低至300~1000mg·kg-1。除此之外,原位鈍化技術是目前可用于修復鉛污染場地的最經濟和最有吸引力的技術之一,該技術涉及土壤中鉛形態的轉化,難溶性絡合物的沉淀、相對穩定的有機絡合物的形成以及對有機和無機成分的吸附是鉛在土壤、沉積物和水中的溶解度的主要轉化途徑。因此,不溶性鉛化合物的沉淀和吸附將會降低攝入土壤中鉛的生物有效性。在應用土壤改良劑修復受鉛污染的土壤、礦山廢物等后,還需要植被輔助修復土壤以達到最優狀態,因此,原位鈍化方法可以使用化學或物理方法。目前常見的鈍化材料包括H3PO4、KH2PO4、重過磷酸鈣等含磷材料,含鐵氧化物、含錳氧化物等金屬氧化物材料,合成沸石、煤矸石、硅酸鋁副產品等礦物材料,有機肥、生物質等有機材料。
6 結語
重金屬鉛來源和用途廣、毒性大,可在土壤中以不同形態相互轉化,但土壤中鉛引起的生物效應和人體健康風險取決于其生物有效性而非總濃度。因此,在鉛污染土壤修復中應注重鉛物質形態的改變,盡可能將易溶易遷移狀態的鉛轉化為穩定態的鉛。以原位土壤重金屬鈍化技術為例,盡管總金屬濃度不會因添加鈍化劑而顯著降低,但該技術可有效降低重金屬污染物的流動性、生物可給性和毒性,因此也是目前常用的低成本、短周期的修復方法之一。而目前我國基于污染物總濃度的修復標準可能會導致不必要的過度修復,浪費人力物力,不利于污染控制的長期健康發展,這也是今后需要進一步改進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