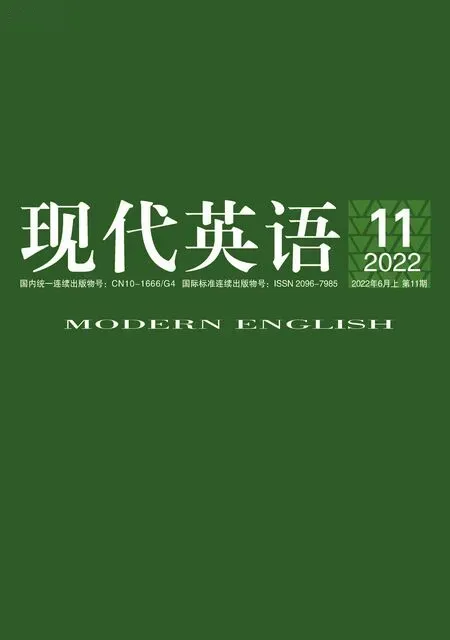許淵沖英譯詩中的“三位”思想及交際效果初探
李鑫 梁澤鴻
(桂林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廣西 桂林 541006)
一、引言
古詩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據著重要的歷史地位,承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中國向外傳播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使命愈發清晰,這也是提升文化自信,自強于世界民族之林和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必然要求。古詩是非常獨特的一種文化藝術形式,講求格律,依律行韻,要平仄,求對仗,用典故,語雙關,字里行間以含蓄為美,以意境為上[1],許淵沖教授將其“三位”翻譯思想融通于其譯作當中,利用不同的翻譯策略(“三化”),以求達到理想的翻譯層次(“三美”),從而在讀者端引發共鳴(“三之”)。溯源其“三位”翻譯思想,與儒、道兩家文化不無關系。此外,在賞析其古詩譯文時,可以發現其翻譯思想和交際翻譯理論存在異曲同工之處。文章將溯源許教授的“三位”翻譯思想,并從“三位”視角,以及交際翻譯視角,選取許教授輯錄在2006年出版《新編千家詩》[2]中的6首古詩英譯本進行賞析,探討其翻譯策略,以期為今后的翻譯實踐提供借鑒。
二、許淵沖“三位”思想和交際翻譯理論
(一)許淵沖“三位”翻譯思想及其溯源
許淵沖教授將其“三位”翻譯思想應用于古詩譯作當中,并提出諸多“三X”法則。比如,“三化”“三之”和“三美”等。“三化”是其翻譯思想的軸心,簡言之,在源文到目的語的轉換過程中,淺化法為具體到一般,旨在將深澀的原文譯成易于讀者理解的語言,可以使用的手段有一般化、抽象化等;等化為內容或者形式上的靈活對等,可以進行詞性轉換,也可以用“正說”“反說”或其他方法;深化為一般到具體,能使譯文深刻化,可用特殊化、具體化等方式[3]。淺化使人知之,等化使人好之,深化使人樂之[4]。這可以從儒家學說中找到其根源。《論語》中就提到了知之、好之與樂之三者間的關系,應用于文學翻譯,此三者就是從理解到喜歡,最后得到樂趣[5]。
“三美”的源頭活水則來自老子的矛盾論和優化論以及孔子的方法論。“意美”傳遞原詩神韻;“音美”講求押韻,有輕重平仄;“形美”則要求詩行整齊,或長短不齊如原詩。其中“意美”最重要,是根本,是目的;“音美”和“形美”為實現“意美”服務,是前提,是手段[1]。老子說的“道可道,非常道”應用于文學翻譯,不一定是“對等”,也可以是創新和優化;“名可名,非常名”則是說譯文或許比原文更貼近現實從而超越原文。孔子說的“不逾矩”遵循客觀規律,是求真;“從心所欲”則要求發揮主觀能動性、創造力,是求美。不過即便譯者發揮創造性,也不一定就譯得“美”。這在消極方面與老子的說法形成互補[5]。另一方面,藝術鑒賞存在審美差異性:同一作品,鑒賞者仁者見仁,各以其情而自得,是以譯無定本[6]。許淵沖教授深受儒、道思想的影響,使獨具中國特色的思維模式得以繼承和發揚;在魯迅、林語堂等人的影響下,又吸納了一定的美學思想;其使用的語言表達具有明顯的中國風格;嚴復、錢鐘書等人的譯論也令其深受啟發,衍生出許多經典的翻譯思想[3][7]。
(二)交際翻譯理論與“三位”思想的交疊
紐馬克繼奈達之后提出交際翻譯理論,就翻譯思想而言,二者都認為交流是翻譯的首要任務[8]。在詩歌翻譯中,也就是要更加注重傳達詩歌的神韻和信息,而非文字和形式。漢語民族與英語民族分屬于漢藏語系和印歐語系,二者在語言、思維和傳統習慣上都存在較大差異,所以譯者在交際翻譯理論下常打破原文局限,進行非忠實翻譯[9]。許淵沖教授的譯詩,尤其注重節奏音韻、詞形詞法、章句安排及修辭格的使用,以使譯詩音韻和諧,這樣原詩的文字趣味得以保留,既可反映原作所描之意境及其抒發之情感,又能令目的語讀者感同身受[10]。這實質上和交際翻譯重視傳達原文內容和準確度,又兼顧譯文讀者的可接受性,使其獲得與原文讀者同樣的交際效果是相一致的[11]。
三、許淵沖古詩英譯本賞析
(一)《春曉》
SPING MORNING
This morn of spring in bed I'm lying,
Not to awake till birds are crying.
After one night of winds and showers,
How many are the fallen flowers![2]5
此詩為唐代詩人孟浩然隱居在鹿門山(今湖北襄陽一帶)時所作。描繪的是一幅春曉圖,前兩句“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說的是詩人春早醒來,聽到周圍到處是鳥兒啼叫的聲音;后兩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說的是詩人回想起夜里風雨陣陣,看到那些被吹落打傷的花兒,頓覺惋惜。詩人因科考不中,還歸故里,此去經年,歲月蹉跎,最后一句“花落知多少”道出了對人生的嘆息。
譯文整體可視作等化。回譯之后可知譯詩非常好地再現了原詩意境。譯文還兼具形式美和韻律美。中國的古詩或對仗工整,或錯落有致。這首《春曉》是一首整齊的五言絕句。譯文每行為八個音節,句與句之間邏輯緊密,是為形美;一、二句的“lying”和“crying”,三、四句的“showers”和“flowers”均壓一個尾韻,且都是重音在前的雙音節詞,是為音美。
(二)《鳥鳴澗》
THE DALE OF SINGING BIRDS
Sweet laurel blooms fall unenjoyed;
Vague hills dissolve into night void.
The moonrise startles birds to sing;
Their twitters fill the dale with spring.[2]11
這首詩是唐代詩人王維描繪的山間夜景——人賦閑情,看桂花飄落;夜空寂靜,春山愈顯空靈;月亮升起,驚動山鳥,鳴叫于山澗,于動靜之中可以窺探出詩人悟禪的灑脫心境。“鳥鳴澗”譯為“The Dale of Singing Birds”精準對應原文詩題,既簡單明了,又具有深化含義,表明彼時、彼山澗是獨一無二的。譯詩四句均為主謂結構,層次分明,是形美;一、二句和三、四句分別壓尾韻,是音美。原文前兩句為“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但第一句不譯“花落”而譯“落花”,第二句不譯“山空”而譯“空山”,一是出于形式上的調整需要,二則將花和山擬人化;三、四兩句同樣也賦予了“月亮”和“山鳥”這些自然之物以人的特質,令譯文具有動感。月夜之下,山鳥歌唱,山谷空靈,溪水潺潺,是為意美。
(三)《相思》
LOVE SEEDS
The red beans grow in southern land.
How many load the spring trees!
Gather them till full is your hand!
They would revive fond memories.[2]15
這首詩也為王維所作。詩寄相思,全篇卻無一詞是相思。“紅豆”別名相思子(說法不一),在中國文化當中含有“相思”之意,但在西方文化中卻未必,直接譯為“Love Seeds”,為淺化。第一句“紅豆生南國”中的“南國”譯為“southern land”,也是淺化,“南國”二字,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南方,更有蘊含在“南國”二字背后的意象。直譯為“southern land”是恰如其分的,既不破壞詩文形式,又不煩瑣。第二句“春來發幾枝”中的“幾支”泛指多,譯文用“How many”與之對應,而“load”一詞可謂點睛之筆,表明春意盎然。第三句“愿君多采擷”中的“采擷”,譯文不用“pick”或“harvest”,而用“gather”,準確地把握了度。通篇來看,即便沒有解釋“紅豆”為“相思”,但讀者仍是能夠知覺的。
譯文的韻為一、三押,二、四押,構成音美。譯詩第三句正常語序應為“Gather them till your hand is full”,但出于押韻的目的,在語序和形式上做了調整,由此可知,“三美”有時也存在矛盾,當形美和音美無法兼顧時,譯者就要扮演一個“裁縫”的角色,有所取舍。
(四)《問劉十九》
AN INVITATION
My new brew gives green glow;
My red clay stove flames up.
At dusk it threatens snow.
Won't you come for a cup?[2]25
這首詩為唐代詩人白居易所作。風雪交加夜,詩人邀請朋友劉十九喝酒,同訴衷腸。詩的語言是樸素的,家常的。此詩重點在事不在人,所以題目直接淺化為“An Invitation”。第一句“綠蟻新醅酒”中的“綠蟻”是指新釀且未過濾的米酒上的綠沫,而非“綠色的螞蟻”。譯文則巧妙地譯為“green glow”。第二句“紅泥小火爐”,實則是省略句,完整的意思是說“我”可以用紅泥制的小火爐來暖酒。譯文并未補充說明,保持形式對等。但讀者并不會有理解障礙。第三句則用“threatens”來說明“天欲雪”,讓譯詩更加生動。最后一句“能飲一杯無”譯文也用疑問句來作為邀請,符合英文表達習慣,達到了應有的交際效果。再者,譯文一、三,二、四句押尾韻,也構成音美。
(五)《江雪》
SNOW ON THE RIVER
From hill to hill no bird in flight;
From path to path no man in sight.
A solitary fisherman afloat
Is fishing snow in lonely boat.[2]31
這首詩作者為唐代柳宗元。于詩人參與永貞革新運動失敗后,被貶永州期間所作。全詩語言簡練,意蘊深厚,表達了詩人不屈的精神與內心的孤寂。譯作語言簡練,以詩譯詩,以形譯形。原詩前兩句為“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其中“千山”對“萬徑”,“千”和“萬”是夸張的手法,泛指多,譯文則用“From hill to hill”和“From path to path”再現對仗;“鳥飛絕”和“人蹤滅”,譯文則用“no bird in flight”和“no man in sight”,對仗工整,兼顧了形美和音美。后兩句為“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第三句“孤舟”在譯文中對應“孤人”,以及第四句的“釣雪”,則是靈活對等;“afloat”與“boat”也壓了尾韻。譯文和原作一樣,都描繪出漁翁寒江獨釣之意象,傳達出一種萬籟俱寂的孤獨落寞之感。
(六)《秋夕》
AN AUTUMN NIGHT
Autumn has chilled the painted screen in candlelight;
A silken fan is used to catch flitting fireflies.
The steps seem steeped in water when cold grows the night;
She sits to watch two stars in love meet in the skies.[2]97
這是一首宮怨詩,為唐代詩人杜牧所作。詩題譯為“An Autumn Night”是為等化,說明這是宮女生活的常態。第一句為“銀燭秋光冷畫屏”,許教授譯“秋光”為“Autumn”,為淺化,既節省筆墨,又易于讀者理解。第三句為“天階夜色涼如水”,其中的“天階”可謂妙譯,“天階”其實就是瓊樓玉宇中的石階,譯文為“The steps seem steeped in water”,使之形象化、具體化。秋夜里,涼風習習,此時宮女孤身一人,只得拿輕羅小扇撲打流螢聊解苦悶,望著月色下的青石板,更增添了孤寂悲涼之感。此處譯文也采取了淺化的方式將這種情緒傳達給讀者,讓讀者能夠感同身受。最后一句“坐看牽牛織女星”中的“牽牛織女星”譯為“two stars in love”,也是淺化,含蓄表達了宮女的憧憬。從音韻上看,譯文每句結尾都押了/a?/音。所以此譯兼顧了形、音、意三美。
四、結語
通過對許淵沖教授這6首古詩英譯本的賞析,其“三位”翻譯思想可見一斑,許淵沖教授的譯作幾乎每首都運用了“三化”的翻譯策略,或等化,或淺化,或深化,然而,策略的選擇并不是盲目的,而是要根據源語與目的語之間的語言差異和文化差異,以及為了追求“三美”巧妙地采用不同的翻譯策略。這樣在讀者端才能引起良好的交際效果,令讀者知之,好之并樂之,從而更好地傳播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同樣地,譯詩的策略也可以根據實際需求靈活地運用到其他類型的文本翻譯上。在實際翻譯工作中,譯者應不斷學習,提升鑒賞能力,培養翻譯思維,擇優選擇適當的翻譯策略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