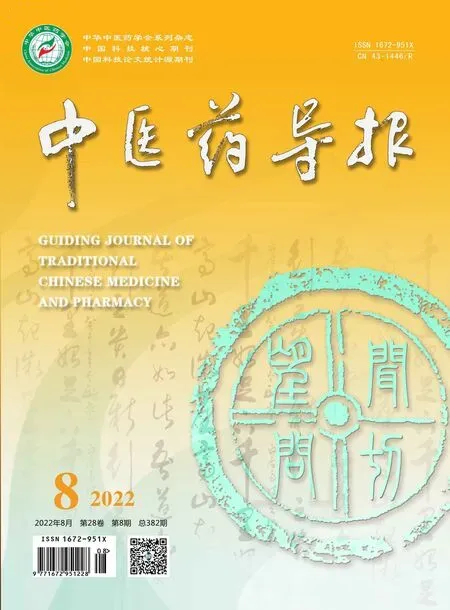陳士鐸《石室密錄》從腎論治用藥探析
朱 悅,許銀坤,林育純,張定華,鄢曉婷,吳翠敏,肖 赟,王一凡,李梓媛,符文彬,5
(1.廣州中醫藥大學針灸康復臨床醫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6;2.廣州中醫藥大學,廣東 廣州 510006;3.肇慶學院,廣東 肇慶 526061;4.江西中醫藥大學,江西 南昌 330004;5.廣東省中醫院,廣東 廣州 510120)
從腎論治作為中醫重要的辨治方法,在臨床中有極為廣泛的適用性與顯著療效。歷代醫家從腎論治的認識雖有各異,卻都重視對其觀點的闡述與臨證切用。《素問·上古天真論篇》中就提出“腎者主水,受五臟六腑之精以藏之”,強調從腎論治臟腑的重要性[1],并在《素問·藏氣法時論篇》中記載了“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致津液,通氣也”的相應用藥思路[2]。漢代張機在《傷寒論》中提出了少陰病脈證并加以從腎論治,如“少陰病,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者,附子湯主之”[3]。名醫傅山治產后失血嘔吐,從腎胃陰虧令虛火上炎加以辨治,倡導養血滋陰以斂陽,補腎養胃而止嘔的治療效果[4]。當今將從腎論治與現代疾病相關聯,如:劉如秀等[5]從腎論治心律失常,高月球等[6]從腎加以論治自身免疫性肝炎,薛冰潔等[7]以從腎論治角度對胚胎移植的成敗因素加以分析并總結經驗。
陳士鐸(以下簡稱“陳氏”),號大雅堂主人,明末清初時期著名的從腎論治醫學大家。陳氏性好游善學又訪師交友甚廣,故其文思立論多有新奇,辨治有據而方藥常隨證化裁,形成具有典型的陳氏從腎論治用藥風格[8]。陳氏著作《石室秘錄》對于從腎論治具體方法與用藥闡述頗為詳盡[9]。故通過對本書的研究,總結陳氏從腎論治的寶貴辨治經驗,以期為臨床施治與方藥研發提供必要的思路參考。
1 辨證特征
陳氏從腎辨證,注重從命門水火學說加以闡發腎水(真水)的重要性,并關注腎與異常水液(邪水)的聯系。此外,陳氏還善于從腎與各臟腑間生克關系加以辨治。
1.1 辨真水與邪水
1.1.1 命門真水 真水,又被陳氏稱為命門真水(腎水)。腎者主藏精,為人體封藏之本,其所含藏的先天之精,腎陰與腎陽,切合于歷代大多數醫家對于命門功能的見解[10]。如《靈樞·根結》最早記載:“太陽根于至陰,結于命門”[11]。李梃《醫學入門·臟腑賦》中言命門“以藏真精,男女陰陽攸分,相君火以系元氣,疾病生死是賴”[12]。張介賓《景岳全書·傳忠錄》云:“命門為元氣之根,為水火之宅。五臟之陰氣,非此不能滋;(五臟之陽氣,非此不能發。”[13]陳氏在《石室秘錄》中在總結前人對于命門觀點的基礎上,進一步主張命門與腎同為人體根本,其中寓含的腎陰即為命門真水(或言腎水、命門之水),腎陽則稱為命門真火(即腎火或先天之火),與真火相對應的火熱邪氣則稱為邪火。陳氏重視從真水(腎水)與真火、邪火的生克關系加以論述。如《石室秘錄·論命門》[9]論述為:(1)真火為無形之火,為無形真水所生,并居于真水之中。故維續真火,需滋養真水,使陰中求陽,以益火之源。(2)天下有形之邪火,為真水所克。故清除邪火,亦需注意對于真水的顧護充養,以壯水克火。由此可見,陳氏從真水生真火、克邪火的理論觀點,對于水火的生克關系加以界定厘清,更利于臨床對于水火理論的運用與發揮。
1.1.2 腎之邪水《素問·逆調論篇》言:“腎者水臟,主津液。”[1]可見腎主水,調節人體水液作用是腎臟發揮其功能的重要體現。而腎主司水液發生異常時,就會使水液無法正常代謝,變生邪水,如《素問·水熱穴論篇》云:“腎者……聚水而從其類也,上下溢于皮膚,故為胕腫。”[1]陳氏主張腎中邪水與真水是相互對立關系,應對腎中邪水加以祛除,則腎中真水得以顧護,腎火與心火方得生養。《石室秘錄·傷寒門》言:“蓋腎之真水,心藉之養,腎之邪水,心得之亡。”[9]《石室秘錄·陰治法》云:“腎中之火,必得水而后生。以水非邪水,乃真水也。邪水可以犯心而立死,真水可以救心而長延。”[9]可見陳氏對于真水功用關注的同時,對于邪水伴隨所產生致病危害也加以明確認識。故真水與邪水為腎主津液功能正向與反向體現,兩者在辨證中需一體看待,再加以明確甄別應對。
1.2 辨臟腑全生全克 陳氏將命門水火思想進一步延伸,提出腎與各臟腑間存在全生全克的關系。其一,臟腑賴腎水以全生[14]。陳氏認為因“無一臟不取資”腎水[9],故腎不單是生肝且對各臟腑都有生養的作用。《石室秘錄·論五行》言:“心得腎水,而神明始煥發也;脾得腎水,而精微始化導也……六腑亦無不得腎水,而后可以分布之。此腎之不全生,而無不生也。”[9]故陳氏在辨證各臟腑虛證時,多考慮腎水對于其的滋養影響并加以分析。其二,腎邪之火全克臟腑。腎火雖可溫熙五臟六腑,若其不能順利歸藏腎中則易變生邪火,對于各臟腑都會產生克伐的侵害。陳氏將此論述為:腎邪之火無一臟不焚燒危害,如心得腎邪之火而躁煩生;脾得之則津液干;肺得之而喘咳痰;六腑得之而燥渴多見[9]。由此可知,腎邪之火對于各臟腑的正常功能均有明顯克制作用,可使臟腑津液流失,繼而產生煩渴躁動、咳逆喘嗽等病癥。如上所述,陳氏從腎中水火對于各臟腑的全生或全克影響,加以分辨其與各臟腑生理功能與病理病癥關系。可見陳氏對于由腎辨理臟腑整體的機能與病變異常的獨到見解[15]。
2 治法特色
2.1 聯系水火互用,利水存精
2.1.1 水火相須互用,交通心腎 陳氏在論述陰陽時尤為重視腎陰與心陽,常以腎水與心火加以代指,且認為兩者相須為用[16]。如《石室秘錄·臟治法》云:“腎,水臟也;心,火臟也。視心腎二經為仇敵,似乎不宜牽連而一治之。不知心腎相克,其實相須。無心之火,則成死灰,無腎之水,則成冰炭,心必得腎水以滋養,腎必得心火而溫暖。”[9]陳氏認為對于腎水的顧護是水火相須為用的重點。如《石室秘錄·假治法》言:“上焦之熱,直至腎宮,腎宮不熱,則上焦清涼,火自歸舍,又何患喘與痰作祟哉。”[9]故陳氏在臨證中善用熟地黃、山茱萸補腎水以補心火。如《石室秘錄·抑治法》云:“不補腎宮之水則腎宮匱乏,水歸而房舍空虛,難以存活,仍然上泛,故必用補水以補火也。”[9]陳氏擬方多用純補腎水的熟地黃、山茱萸為配伍,佐以有“引下之絕品”的牛膝為使藥,溝通心腎水火,可令腎水有心火的溫熙,心火又有腎水的濡養,使水火相交以發揮兩者相須互用的功能。
陳氏重視交通心腎并主張“心腎不交,陰陽俱耗”則易外感邪氣或加情志憂愁抑郁,乃成大毒以致病。如《石室秘錄·偏治法》云:“陰寒直入腎宮,則必挾腎水上犯心君之火。君弱臣強,犯上自所不免。若不用大熱之藥,急救心君,則危亡頃刻。”[9]陳氏治療心腎水火不交為病時,善以肉桂溫陽御水,蓮子清熱等,以達御水救心,溫腎散寒之效。如《石室秘錄·本治法》中用肉桂補火以交通心腎,使“心氣下行,君火相得,自然上下同心,君臣合德矣”[9]。陳氏在《石室秘錄·閉治法》中言:“蓮肉尤能清心……使心腎相交,為關玉門之圣藥。”[9]由此可見,心腎同治、水火相交乃陳氏治法的重要特色。
2.1.2 利水存精 陳氏認為水濕類病理產物是腎精損耗的一個重要因素,通過利水祛濕可以更好地閉存腎精并促使疾病的轉歸。如陳氏在《石室秘錄·閉治法》中言:“車前利小便而不走氣,利其水則必存其精。”[9]《本草新編·車前子》載其在臨證中配伍諸藥(如配伍熟地黃補精血,配伍肉桂溫陽通氣等)可起到“用通于閉中,用瀉于補之內”達到“水竅開,而精竅閉,自然精神健旺”[17]。此外,腎精的充養又可促進人體水濕的排出。陳氏認為水濕所致的病癥乃陰精不足,而陰邪又乘虛犯之導致的。如在論治老人體虛水濕病癥時,陳氏常用六味丸補益腎水,以健脾胃之氣,去腎中邪水[9]。由上可知,水濕得利,可助腎精固存;腎精得充養,則水濕類病理產物易被祛除。利水與存精是對于腎主水與藏精功能的重要體現,兩者相互促進并共同維系著腎臟生理機能的常態運行[18]。
2.2 胃腎相關為用,從腎專治
2.2.1 胃為腎之關,胃腎相關為用“腎為胃之關”為《素問·水熱穴論篇》首先提出的觀點,但陳氏在總結前人經驗與自身臨床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胃為腎之關”更切合臨證實際[19]。陳氏持此觀點的理由有:(1)腎陰腎陽需賴胃以補養。腎與胃為人體先后天之本的關系,后天有濡養先天的作用。人體由口腔攝入飲食,通過的胃腐熟消糜后,再經各臟腑協作方能最終化生精微并供給于腎臟,充養貯藏為腎陰腎陽[20]。如陳氏在《辨證錄·虛損門》論述虛損病時強調:“胃為腎之關門,胃傷則關門必閉,雖有補精之藥,安能直入腎宮,是補腎必須補胃也。”[21]明代張介賓在論述玉女煎時也認為陽明胃熱氣火有余,熱邪耗傷胃陰也會進一步致使腎中陰精不足,當先清胃熱,再滋腎陰以達胃關得閉,腎陰得補,諸癥得愈。可見胃腑功能的正常與否會為影響腎臟得到充養的重要因素。(2)胃為腎中邪氣出路。如《辨證錄之遍身骨痛門》言:“風濕入于經絡則易去,風濕入于骨髓則難祛,以骨髓屬腎,腎可補而不可瀉,祛風濕則傷腎……雖腎不可瀉,而胃與大腸未嘗不可瀉也,瀉胃與大腸之風濕,而腎之風濕自去。”[21]陳氏在臨證治療腎經腰痛時,認為白術健脾胃,可使水濕邪氣不留存而免于侵犯腎經,故最利腰臍疼痛病癥。如《石室秘錄·順醫法》載陳氏在治療氣虛濕著腎中,善用白術利胃且能祛濕以護腎的功效,使大小便得脾胃之氣而能合,腎中邪氣得以隨二便排出[9]。由此可見,胃為腎中邪氣的排出的重要路徑,是維持腎臟功能正常運行的關鍵。綜上可知,“胃為腎之關”是以腎臟補養以胃的飲食攝入轉化為重要來源,又以胃為腎中邪氣出路的方式加以實現胃腑對腎臟的調控作用。胃腎間存在緊密的聯系,需相互關聯為臨床辨證運用。
2.2.2 從腎專治 從腎專治,在《石室秘錄·專治法》中論述為“專治一臟,單刀直入之謂也”[9]。在陳氏的臨證治療中體現有二:(1)寒中陰經,治腎當專直。人病直中陰經寒癥,此病勢侵襲如奔馬般峻猛,出現“舌黑眼閉,下身盡黑,上身盡青,大便出,小便自遺”[9]等癥。倘若多臟用藥則藥力分散則難以遏止病邪進一步入里,不如“只用一二大將,斬關直進”[9],從腎施治來得奏效迅捷。陳氏在《石室秘錄·霸治法》中論述此法為寒邪直入腎宮,死亡傾刻,不可用王道多方緩治,必由腎單刀直入,推蕩逐除邪氣,方能轉危急為安然。(2)純補腎陰,消弭虛火。陳氏在《石室秘錄·陰治法》中提出:“用純陰之品,一直充進腎宮,滋其匱乏,則倦怠之形,不上焰于口舌皮毛之際……自然陰長陽消,不治陽而自安也。”[9]陳氏純補腎陰,可以視為其對腎陰全生各臟腑,腎中邪火全克各臟腑理論的重要運用。如陳氏認為臍與齒俱是腎經循行所過的部位,而臍與齒出血皆是腎火外越的表現。其多用六味地黃湯并酌加有專能止竅之漏、補腎益骨功效的骨碎補,滋腎水以使虛火自息[22]。
3 方藥運用
3.1 君藥重用,長治久服 陳氏探討的從腎論治病癥多屬虛勞內傷,成非一日,則治亦非一日可以取效。故需對于治療主癥的君藥加以重劑量運用,以久服湯藥丸餌漸達病愈。陳氏又將此方藥總結為王治法,即以王道中正平和治之。君藥重用久服,藥力與日漸增,看似平常,用之有治本守正的妙處。如全生至寶丹中以山藥為君藥,用量達兩斤,其余用藥有“芡實一斤,薏苡仁一斤,黑芝麻八兩”等;《石室秘錄·完治法》[9]中用黃芪半斤為君藥,配合“杜仲一兩,防風五錢,茯苓五錢”等加入黃酒共煮溫服以治療腰痛足痛;治療陰癥癰疽的陰陽至圣丹中,金銀花一斤為君藥,輔藥有“生地黃八兩,當歸三兩,玄參五兩,麥冬三兩”;利腰丹中用“白術二兩,杜仲一兩”,酒煎服10劑等。其余方劑還有:定風去暈丹、養陽湯、斷夢止遺丹、斂汗湯、補氣消痰飲、黑鬢仙丹、安火至圣湯等[9]。以上諸方中君藥的用量都為最大且明顯超過于其他藥物,體現君藥在其中對于功效與作用的主導性。且臣藥、佐藥與使藥的藥味雖多,藥量卻依次遞減與君藥形成一定配伍比例,可見陳氏處方以藥量明確裁定君臣佐使,協調藥物的整體作用,值得臨床加以借鑒。此外,上述方劑用藥劑量整體偏重,又以久服固本,持續見效為特點。可見陳氏從腎論治病癥不拘泥治療常病所倡導的“一劑知,二劑已”的快速奏效,而以切合患者主癥酌君藥重用,久服以利長遠治療[23]。
3.2 善用對藥“偶治” 陳氏稱二味藥(對藥)兼而治之為“偶治”法[24]。偶治法既可以彌補單一藥物性味藥功效的不足,且可助發揮兩味藥的各自優勢,取長補短。陳氏以闡釋對藥偶治的方式將從腎論治理論加以發揮,主要體現在命門水火學說和臟腑生克變化。陳氏從腎論治常用的對藥偶治有人參-附子、玄參-麥冬、熟地黃-巴戟天、山藥-芡實等。陳氏用補氣藥人參、溫里藥附子二味治療中寒之證,陰寒迫陽氣外越。《石室秘錄·本治法》言,人參、附子二味相合則無經不入,補真火以“救心腎,而各臟亦無不救之”[9]。用人參以挽真火于絕續之頃刻,附子可直入心腎驅寒,兩藥偶治共奏補火救逆、益心溫腎以祛寒之效[25]。人參-附子藥對涉及到方劑如參術附桂湯、逐寒回陽湯、祛寒至圣丹、消冰散、救心蕩寒湯等。此外,陳氏還常用清熱藥玄參與補陰藥麥冬合用,退虛邪火熱,補腎中真水以滋肺陰,可用治如斑疹清虛熱以消斑,如方劑雙補至神丹、清肅至涼湯、安火至圣湯、消陰堅骨湯等;熟地黃配巴戟天以補腎益精,滋真水養真火,常用于陽痿、夢遺與早泄類男科病,可見于方劑益心止遺丸、引火升陰湯;補陰藥山藥配伍收澀藥芡實在治療虛勞、不孕不育、陰萎諸病癥中,以兩個不同藥類間的相互配伍以增大藥物間差異性,拓寬功效范圍,最終共同達到補腎健脾、祛濕固精的作用,涉及方劑有心腎同補丹、遺忘雙治丹[26]。
4 病案舉例
一患者為雙蛾病,喉門腫痛,痰如鋸不絕,茶水一滴都不能下咽,然而疼痛雖甚,至早上則癥狀有所減輕。病者“喉雖腫,舌不燥,痰雖多,卻不黃而成塊,此乃假熱之癥也。若以寒涼之藥急救之,下喉非不暫快,少頃而熱轉甚。人以為涼藥之少也,再加寒涼之品,服之更甚”[9]。陳氏以少商穴刺絡放血以急瀉熱邪。方用消火神丹:“附子一錢、熟地黃一兩、山茱萸四錢、麥冬三錢、五味子三錢、牛膝三錢、茯苓五錢”[9]。水煎服,藥下喉則其火勢熱癥立時消散,聲音恢復響亮。
按語:患者癥見喉嚨腫痛、痰多,甚至茶水不下,歸屬于中醫“喉痹”范疇。此病屬于臨床常見病種,內感外傷皆可引起,《素問·陰陽別論篇》云:“一陰一陽結,謂之喉痹。”[1]現代醫家普遍認為喉痹是由于外邪來犯,侵襲喉門,或臟腑受損,咽喉失養,或虛火上炎所致[27]。陳氏認為此患者因腎水枯竭,心火失腎水潤養,正虛則邪熱相火上越,蒸灼津液,凝練成痰,致使喉門窄小,郁而腫痛。方中以附子補心溫陽[28],以安君火。熟地黃、麥冬以補腎滋陰,配伍收澀山萸肉與五味子,補斂相合,壯腎水以消邪熱。再佐以牛膝引火下行,活血通絡消腫,茯苓益氣利水寧心,既可防補益滋膩斂邪,又可交通心腎。諸藥共用使腎水得充養,心火有腎水之潤,又有引導交通之使,心腎自安然而虛火無上泛,故喉腫熱勢自消,聲音恢復響亮。
5 結 語
陳氏在繼承前人經驗與自身臨證體會的基礎上,對從腎論治的相應辨證與治法用藥加以靈活變通運用[29]。形成陳氏所著《石室秘錄》中從腎辨證疾病,主張辨命門真水與腎之邪水,并將命門水火思想進一步延伸,提出腎與各臟腑間存在全生全克的關系。治法包含:水火相須互用,交通心腎,利水存精;胃為腎之關用,從腎專治。方藥運用以君藥重用且久服,善用對藥“偶治”為特點,涉及方劑有全生至寶丹、陰陽至圣丹、利腰丹、養陽湯等,常用藥對有人參-附子、玄參-麥冬、熟地黃-巴戟天、山藥-芡實等,值得臨床加以借鑒運用。通過對本書的研究,總結陳氏從腎論治的寶貴經驗,以期為臨床施治與方藥研發提供必要的思路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