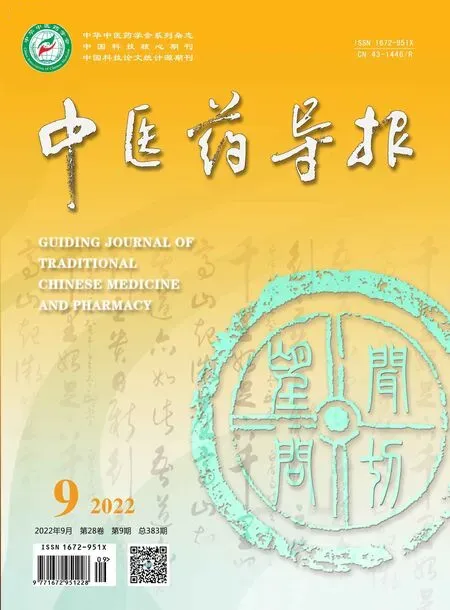得氣與針刺技術多元化
陳 卓,張 靜,李智涵,嚴 顏,賈 沄,姜 煜,范曉琳,張 義
(北京中醫藥大學針灸推拿學院,北京 100029)
得氣的概念最早出自《黃帝內經》,是中醫針刺技術的經典步驟。《靈樞·九針十二原》:“刺之要,氣至而有效”,《針經指南·標幽賦》:“氣速至而效速,氣遲至而不治”,通常認為得氣與療效密切相關。但現代研究[1]顯示,得氣與針刺療效之間是否有相關性尚存爭議。截至目前對于得氣的討論較多,但對于不追求得氣的刺法及其原因討論較少。因此本文分析在針刺治療中是否追求得氣的原因,并從得氣角度探討針刺技術的多元化發展。
1 得氣的概念
得氣是中醫針刺療法的經典概念。與得氣相關的概念還有氣至和針感,很多專家對現有文獻進行總結,認為三者之間既有聯系,也有區別[2]。《黃帝內經》中得氣的概念與《難經》及其之后古籍記載也有所不同[3],有廣義和狹義之分,氣至為廣義得氣,是治療的最終目的;狹義得氣是針灸治療的前提[4]。現代的得氣概念即狹義得氣,本文僅對狹義得氣概念加以分析。
得氣是指針刺入腧穴一定深度后,施以提插捻轉等行針手法,使針刺部位獲得經氣感應。得氣可以從兩方面判斷[5],一方面是患者自覺針刺部位有酸麻、重脹等感覺,即患者的針感;另一方面是醫師手下沉緊的感覺,即醫師的手下感,同時可出現針下肌肉跳動、循經皮膚變化等客觀現象。得氣是針刺過程中醫患雙方的同步感應,若針刺后得氣,則患者自覺針刺部位有酸麻重脹等感覺,同時醫師手下有沉緊感,甚至跳動感;若針刺后未得氣,則患者無任何特殊的感覺或反應,且醫師感覺針下空松、虛滑。
患者的酸麻重脹等主觀感覺主要由針具刺激神經感受器引起。而醫生的手下感主要是指針下沉緊、滯澀等阻力感,其來源包含兩方面,一是針刺誘導肌肉主動收縮產生的沉緊感[6-9],即穴位肌肉出現抽搐,如剪切波聲彈性成像技術觀察到針刺足三里得氣后肌張力明顯增加[10];二是單向捻轉產生肌筋膜纏繞,出現一定滯針阻力造成沉緊感,如任作田等指出搓法、捻法、飛法等單向捻轉手法是高效的催氣法[11-12],張縉在取氣手法上也獨推搓法[13],可用于不易得氣的患者或穴位,也可用于得氣感的維持,所以得氣的沉緊感應該包含單向捻轉造成的肌筋膜對針體的適度纏繞[14]。
2 得氣概念產生和發展的原因
2.1 得氣概念產生的原因 黃龍祥[15]認為“血氣”是古典針灸學的“元范疇”,是針灸學范疇體系的歷史和邏輯統一的起點。以此為出發點延伸出一系列學說和觀點,構成整個古典針灸學理論框架。《素問·六微旨大論篇》云:“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人體之氣有“升降出入”之氣機,這決定著人體的生理機能。《靈樞·九針十二原》開篇即點明“欲以微針通其經脈,調其血氣”。針刺手法可通過調節氣機,維持人體氣血正常運行,進而保證生命活動的正常運行。《素問·離合真邪論篇》中提到:“大氣皆出,故命曰瀉……大氣留止,故命曰補”,在得氣的基礎上,針刺補瀉的目的是調整氣的不協調關系,從而發揮治病作用[16]。在“血氣”理論體系下,部分傳統刺法的行為邏輯是“調氣”,如《靈樞·刺節真邪論》:“用針之類,在于調氣”;《類經》:“用針之道,以氣為主”,再如“從衛取氣”“從榮置氣”“搓以使氣”“氣調而止”等論述。在血氣理論的框架下,用于“調氣”的針法強調得氣是針刺的前提,這是得氣概念產生的原因。
2.2 得氣概念發展的原因 民國以前的文獻多從醫生手下感論述得氣,如《難經》描述得氣為“其氣之來,如動脈之狀”,《標幽賦》:“輕滑慢而未來,沉澀緊而已至”“氣之至也,如魚吞鉤餌之浮沉,氣未至也,如閑處幽堂之深邃”。民國以后更加重視患者主觀感覺,如《新針灸手冊》[17]:“隨詢有無疼痛、發麻、脹重等感覺,作為施術之提示”。《針灸秘笈綱要》[18]:“病者感酸重,針下覺沉緊,甚或如電氣之傳布”。之后得氣的概念也就發展為對醫者手下感和患者感覺兩方面的共同描述,如《針灸學簡編》[19]明確表示:“得氣的表現可以從兩方面得到證實,一是針下的感應,二是患者的感覺。”醫生手下感加上患者感覺就基本構成了現代對得氣的描述。
民國時期學者開始用神經科學解釋針灸現象,認為得氣與“刺激神經”密切相關,如《高等針灸學講義》[20]:“以上所言之‘氣’自今日言之,蓋指神經云”,也就是只有刺激神經才能得氣。而刺中神經與否,借由針刺引起的患者感覺進行判斷。此時針刺患者所引起的酸麻重脹等感覺被統一為刺激神經所引起的感覺,如龐中彥《簡明針灸手冊》[21]:“凡當針體進入肌肉組織后,要探得到感受器或神經干或神經纖維,若探得到時病人有觸電、脹痛、麻痹等感覺”。故而針刺患者神經、肌肉、血管等引起的酸麻重脹等感覺,成為了得氣的標志之一。在此基礎上,人們又將對神經的刺激分為興奮和抑制二者,用以解釋傳統的補瀉概念。如《針灸療法入門》[22]:“針灸術治療疾病的基本原則,系運用興奮和抑制兩種手法,借以激發和調整神經的機能,以達到治愈疾病的目的。”“神經刺激”除了用來解釋患者得氣感覺和補瀉以外,也用來解釋得氣的手下感。如《石學敏針灸學》[23]認為:“在整個神經系統功能完好的情況下,針刺穴位時興奮了某些感受器……還可反射性地引起一系列生理反應(如局部的肌肉收縮)……這種得氣的感應對機體的各種功能可以產生調整作用。”
3 不追求得氣的刺法及其原因
得氣是中醫針刺技術的經典步驟,古今針刺技術通常重視針刺得氣,但針刺技術是多元化的,并非所有刺法都要求得氣。“調氣”只是針刺理論之一,古典刺法中還有排膿、放血、解結等多類非“調氣”刺法,現代也有很多不追求得氣的新針法流派。不追求得氣的原因有兩類:一是主觀上不追求得氣,如“調氣”理論框架之外的刺法;二是客觀上無法得氣,如淺刺法不刺入肌層,難以引出肌肉收縮。因此,得氣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得氣概念屬于特定理論范式下的產物,具有特定的產生、發展的背景和過程,以及特定的使用范圍。
3.1 排膿放血刺法 《靈樞·壽夭剛柔》:“刺營者出血”;《靈樞·經脈》:“急取之,以瀉其邪而出其血”;《靈樞·九針十二原》:“凡用針者……宛陳則除之”;《靈樞·官針》:“絡刺者,刺小絡之血脈也……贊刺者,直入直出,數發針而淺之出血,是謂治癰腫也……豹文刺者,左右前后針之,中脈為故,以取經絡之血者”。中醫學認為“血為氣之母”,適度放血可治療邪熱熾盛的證候,放血刺法不建立在直接“調氣”的基礎之上,而是通過放血間接的“調氣”,因此不追求得氣。
《靈樞·官針》:“大瀉刺者,刺大膿以鈹針也”,《靈樞·四時氣》:“徒疒 水,先取環谷下三寸,以鈹針針之”,排膿和排出腹水的鈹針刺法直接去除有害的病理產物,也沒有得氣的要求。此外,火針刺法也常用于排膿,如李東垣《論針烙法》記載:“當用火針……燒令赤,于瘡頭近下烙之……要在膿水易出,不假按抑”,火針排膿法也沒有得氣的要求。排膿放水刺法在歷史上曾經長期存在,但現代一般屬于外科的診療范圍。
3.2 淺刺法 無論是在古典刺法還是現代刺法中,都有淺刺法。淺刺法刺入深度淺,如果不達到肌層,醫者不會有“如魚吞鉤”般的肌肉抽搐感。同時如果沒有適度單向捻轉也難以產生滯針阻力。《靈樞·官針》:“毛刺者,刺浮痹于皮膚也……浮刺者,傍入而浮之,以治肌急而寒者也……半刺者,淺內而疾發針,無針傷肉,如拔毛狀……直針刺者,引皮乃刺之”。《素問·刺要論篇》:“刺毫毛腠理無傷皮”。上述各種古典刺法刺至皮膚或腠理,并且不伴有單向捻轉動作,難以產生典型的得氣現象。
與之類似,現代浮針療法要求平刺進針,僅達到皮下淺筋膜層,為典型的淺刺法[24-25],該療法要求醫生手下松軟無阻力,不求得氣,不辨虛實,不行補瀉[26-27]。腕踝針療法要求在腕部和踝部沿皮平刺,不到肌層,不求得氣[28]。腹針療法針刺至皮下,患者可以沒有任何感覺,不刻意追求得氣。此外,現代的皮膚針、皮內針也不追求得氣。
3.3 解結刺法 經筋有“連綴百骸,維絡周身”“主束骨而利機關”的功能,經筋痹證以“支”“轉筋”“痛”為主。現代研究[29-32]認為,筋痹主要是因為經筋循行中的“結”“聚”等處應力集中,以及經筋病變部位的軟組織張力增高而產生。針對此類疾病,《靈樞·官針》中有多種針刺方法可用來“解結”,稱為解結刺法,如齊刺、傍針刺、揚刺等多針刺法等,關刺[33]、合谷刺等單針多向刺法,以及恢刺等撬撥刺法[34]。這些針刺方法均可松解高張力軟組織,屬于“調筋”刺法。
上述多針刺和多向刺法是否需要得氣是有爭議的,筆者認為得氣不是這些刺法的必要條件。這些刺法皆出自《黃帝內經》,使用的針具應該是《黃帝內經》時代流行的粗直徑針具,治療對象為筋痹、肌痹、寒痹、痛痹、留痹等痹證者,從適應證和操作技術來看,更類似于一種叫做“經皮針刺切開術”(percutaneous needle fasciotomy)的方法,該方法通常采用注射針頭反復穿刺軟組織損傷病灶,常用于治療掌腱膜攣縮[35-36]、肌腱炎[37]、腕管綜合征[38]等運動系統慢性損傷。
股四頭肌攣縮是全膝關節置換術的常見并發癥,有人使用18號注射針頭反復穿刺僵硬攣縮的股四頭肌,在攣縮帶內從遠端到近端每隔1 cm穿刺10~20針,通過每個皮膚針孔可進行4~5次股四頭肌穿刺,這種方法可有效延長股四頭肌長度,改善膝關節活動度[39]。傳統針灸學中也有類似刺法,典型的如明末時期著作《針灸經驗方·腳膝》記載:“手足筋攣蹇澀,以圓利針貫刺其筋四五處后,令人強扶病人病處,伸者屈之,屈者伸之,以差為度,神效”。
對于慢性肌腱炎,有人在實時超聲成像下,采用22號注射針頭對異常肌腱進行反復的穿刺切開術,對肌腱異常區域進行20~30次穿刺,如果發現鈣化灶,則反復穿刺破壞鈣化灶[37]。慢性肌腱炎就是典型的筋痹,壓痛明顯的病損區域是典型的阿是穴,在病損區域使用注射針頭反復穿刺是“以痛為腧”針刺,和《靈樞·官針》中齊刺、傍針刺、揚刺等多針刺法,以及關刺、合谷刺等單針多向刺法是一致的。如果拋開理論依據,單從操作技術來看,“經皮針刺切開術”與《靈樞·官針》中用于治療各種痹證的多針刺和多向刺是一致的。所以有理由認為2000年前的《黃帝內經》中已經存在“經皮針刺切開術”,這也是中西醫殊途同歸的現象。相對于注射針頭的反復穿刺,實心的針灸用具更具有優勢,因為空心的注射針頭容易將空氣帶入組織,不利于針孔恢復。因此認為解結刺法更類似經皮切開術,得氣不是解結刺法的必要條件。
4 針刺技術的多元化
《黃帝內經》時期的針灸學從理論到技術都體現著多元化特征,當時的針刺手法中很多是具體的外科技術[40-41]。有研究[41-42]認為,隨著金元以后儒醫的興起,形成了帶有儒家文化色彩的針灸理論,外科技術被賦予了更多的內科色彩。此時針灸理論逐漸偏向于對經絡氣血的調節,這種特點一直延續至清末。
民國以后人們開始從神經科學角度研究針灸學,這是針灸學現代研究的開端。隨著現代科學的加入,“刺激神經”成為針刺起效的主流解釋,并以此解釋針灸調節氣血的機理。此時針灸術與外科技術漸行漸遠,這也是后世一直強調得氣的原因。如《新針灸學論叢》[43]:“針法里面原先也包括外科手術、放血、刺經絡等三方面;用針灸術治病,不論是刺神經的針與出血針,或皮膚針、串線針、火針,也不論是無瘢痕灸或有瘢痕灸、化膿灸,它所以能治病,主要是由于激發和調整身體內部神經調節和管制的機能。”
以得氣為特征的調氣針法是現代針刺技術的主體,一般通過行針促進得氣,得氣后根據患者具體病情進行補瀉,所依據的理論有經絡、氣血等理論。而現代研究認為,針刺是一種非特異性刺激,通過穴位感受器將機械刺激信號轉化為神經電信號并上傳各級中樞,經各級中樞整合后通過神經-內分泌-免疫網絡作用于全身,針刺作用具有良性、雙向性、整體性、綜合性、功能性、早期性等特點。
根據現代針灸學的習慣性認識,人們通常從經絡氣血角度,或者刺激穴位、神經調節角度認識《黃帝內經》中的各種解結刺法,例如認為合谷刺的作用是加強刺激,恢刺需要先得氣等等,這種認識沒有突破金元以來形成的對針灸學的習慣性認識。理論認識的長期停滯對學科發展是不利的。黃龍祥認為決定工具、材料、技術的歸屬是理論,沒有完整的理論覆蓋,就不能擁有完整的技術專屬權,沒有有效的理論支撐,技術也走不遠。《靈樞·官針》中解結刺法在金元以后不常被提起,甚至出現認識上的爭議,其原因是因為解結刺法難以用經絡氣血理論解釋,“治不能循理,棄術于市”就是這個道理。
當代隨著科技和學術的不斷發展,干針、針刀、浮針等以解剖學為基礎的新針法不斷涌現,雖然在理論上基本獨立于針灸而存在[44],也不能完全用“刺激神經”概括機理,但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黃帝內經》時代針刺技術的多元化狀態。如果將這些不能用現有理論覆蓋的新針法納入針灸學體系,必然要求相契合的新理論的出現。
5 小結
綜上所述,得氣是中醫針刺療法的經典步驟,但不是必需步驟。得氣現象是客觀存在的,得氣的概念是特定理論框架下的產物。未來針灸學發展必然走向多元化,應持謹慎和開放的態度對待新的理論體系,以推動針灸理論革新與臨床進步[4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