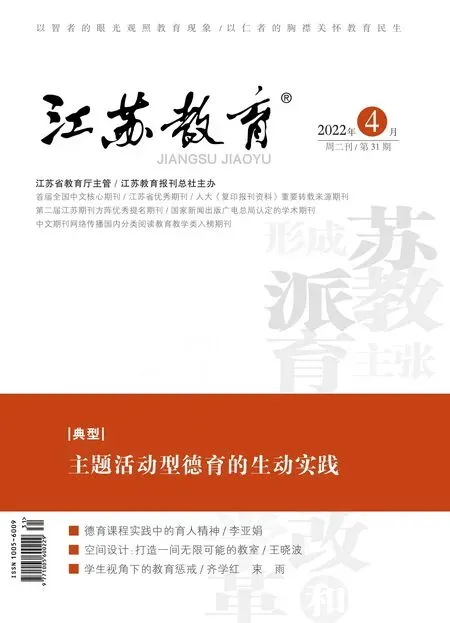學生視角下的教育懲戒*
齊學紅 束 雨
2020 年12 月23 日,教育部出臺《中小學教育懲戒規則(試行)》(以下簡稱《規則》),對教育懲戒的定義、適用情形、原則手段等做了規定,并于2021年3月1日開始實施。《規則》的出臺在中小學實踐領域以及社會各界引起了廣泛關注,一時間,“教育懲戒”成了一個熱詞。然而,大家更多的是從教育懲戒的主體——學校及教師角度出發,側重于教育政策法規尤其是校紀校規的制定與完善,很少有站在學生立場,從學生生命體驗角度出發的深度調查研究。
為此,我們課題組圍繞“學生群體對教育懲戒有效性的看法”這一核心議題,于2021年3月18日—27日,對江蘇、山東、北京、上海、河南五個省市共計582 名初高中學生進行了問卷調研,調研對象包括:初中生439 人,占總受訪人數的75.4%;高中生143 人,占總受訪人數的24.6%。調研對象主要集中在江蘇、山東兩大省份。問卷調查分析如下:
一、中學生對教育懲戒的了解程度
調查發現,作為教育懲戒這一教育實踐親歷者的中學生,對教育懲戒話題的了解程度并不算高。我們要求受調研學生以數字1—5 由低到高地表達他們對教育懲戒的了解程度,582位受調研學生對于教育懲戒了解程度的中位數以及眾數均為3,平均數為3.06。正如《規則》并非只是教師實施教育懲戒的指導手冊,同樣也是學生對照自身在學校中言行的標桿;教育懲戒并非只是關乎學校、教師對學生不良行為的“矯治”,同樣也關乎學生的“引以為戒”。但中學生對與自己息息相關的教育懲戒的了解顯然不夠充分。1993 年頒布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這一教育事業發展的綱領性文件中,明確將“依法治教”作為教育體制改革的重要舉措,標志著“依法治教”正式成為國家教育工作的指導方針,并在此后的政策文件中被屢屢提及。教育懲戒是依法治教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依法治教的必由之路,是教育健康發展的關鍵抉擇。學生只有對教育懲戒相關的法律法規、政策文本有足夠了解,才能在此基礎上對照《規則》,指導自身的學習實踐活動,并能以法律的武器維護自身合法、正當的權利,讓教育懲戒真正成為科學治教的重要組成部分。學校管理層、一線教師、學生,都需要對教育懲戒有正確的認識,因此面向全體中小學生開展《規則》的政策解讀尤為必要。
二、中學生對教育懲戒必要性和有效性的認識
與學生對教育懲戒了解不充分、不深入相對應的是,他們對教育懲戒必要性、有效性認識的正向態度。受調研學生對于教育懲戒必要性認識的中位數為1,眾數為3,平均數為1.29(-3表示非常不重要,3 表示非常重要),其中對教育懲戒必要性持負面態度(≤-1)的人數僅為54人,占樣本總量的9.3%;對教育懲戒必要性持中立態度(=0)的人數為115 人,占樣本總量的19.8%;對教育懲戒必要性持正向態度(≥1)的人數為413 人,占樣本總量的71%。受調研學生對于教育懲戒有效性認識的中位數為1,眾數為2,平均數為1.13(-3 表示非常不重要,3 表示非常重要),其中對教育懲戒有效性持負面態度(≤-1)的人數僅為63 人,占樣本總量的10.8%;對教育懲戒有效性持中立態度(=0)的人數為116 人,占樣本總量的19.9%;對教育懲戒有效性持正向態度(≥1)的人數為403 人,占樣本總量的69.3%。
調查數據顯示,中學生對于教育懲戒必要性與有效性的認識總體持正向態度,其中對教育懲戒的必要性所持的正向態度要略微優于有效性。研究表明,從學生視角出發,合法、合理、合規的教育懲戒在學校教育中是必不可少的。在現代社會,青少年的社會化進程是在學校這一專門場所中實現的,學校教育的一大功能便是幫助學生實現社會化,社會的規范、知識、技能透過這一模擬系統為學生所掌握。在真實的社會結構之中,人們普遍借助以法治為標志的懲罰系統治理社會,既然學校是對社會的模擬,那么教育懲戒在學校中的必要性也就無須質疑。學校教育負有社會化的職能,借助教育懲戒這一具有約束性的力量,讓學生逐漸學會適應一個制度化、結構化的教育世界,而制度本身就是具有強制性的,結構化中隱含著規訓甚至束縛。另一方面,學校教育最終要幫助學生學會適應成人社會,本質上要求學生作為個體去適應某種特定的社會結構,正如社會學家福柯指出的,要“把人引向正確的道路”,就必須借助“懲罰權”對個體實施規訓,使人適應社會結構。因此,教育懲戒就是一種幫助學生理解、認同與適應社會的手段,其必要性、有效性自然會受到學生的認可。
三、中學生對于教育懲戒目的的認識
在多選題“您覺得教育懲戒的目的是什么?”“教育懲戒的實施應達到哪些效果?”中,“培養并完善學生的是非觀”“起到警醒與威懾作用”“讓學生個人記住教訓”“盡可能規避更多的違規行為出現”這四個選項被選率很高。依據被選擇頻次的高低進行排列,“培養并完善學生的是非觀”被選470 次,被選率80.6%;“盡可能規避更多的違規行為出現”次之,被選411次,被選率75.6%;排在第三的是“起到警醒與威懾作用”,被選390次,被選率66.9%;“讓學生個人記住教訓”被選率在四個選項中排在最后,被選311次,被選率53.3%。從這一選擇結果可以看出,中學生對教育懲戒對于個人成長、班級管理效果的認同。
綜上所述,教育懲戒并非“為懲而懲”。換言之,教育懲戒是學校、教師教育引導學生的必要手段,具有管理性的功能,但又不同于純粹的行政管理權,其目標在于回歸教育的語境,最終實現“育人為本”的教育本質要求和價值訴求。也就是說,學校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將學生培養成人格健全的合格公民,使學生在走出校園、面向社會時,擁有成熟的、理性的人格。
從選擇情況可以看出,中學生對于教育懲戒目的有著清晰的、正確的認識。被選最多的選項是“培養并完善學生的是非觀”,這一目的指向的是學生的個體成長。自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以來,科學技術的進步引發了對“人”的思考,人性的光輝不再為神性所遮蔽,人的存在不再需要受到自然的直接宰制。在古典時期,人類自詡為萬物之靈長,認為自身便是一個完成了的存在。這一完成了的人并不滿足于在自然之中生存,而是矢志不移地做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穿透物之存在,解碼從自然到人類社會的一切現象。這個世界沒有秘密,至少沒有永遠無法為人類參透的秘密。隨著人類對于“人”的認識的不斷進步,后現代主義認為,人類是未完成的存在,身體的未完成性體現在人出生時器官的“未特定化”“非專門化”和本能的“欠缺”和“匱乏”。正是因為人類的未完成性,教育才得以發生,人類才存在著無限的可能性,人類才不只是在原地踏步,而能成為一種超越的存在。學生是非觀的培養與完善,正是在接受懲戒之后引以為戒,從而得以實現的未完成的人的超越。“盡可能規避更多的違規行為出現”這一選項是基于班級管理的考量,出于班級管理目的教育懲戒同樣是為學生個體成長服務的。“管理”并非是為“管”而“管”,教師通過“管理”,“盡可能規避更多的違規行為出現”,為學生營造一個更有利的學習生活氛圍與成長環境。可以說,違規行為出現頻率的降低是伴隨著學生個體成長必然帶來的結果,這是一個顯性的目的,其內核仍然是幫助學生完成個體的超越。
四、中學生對教育懲戒方式威懾力的評價
學生對教育懲戒方式威懾力度的平均排序結果顯示:排序最靠前的教育懲戒方式是“校級、年級處分”,為2.34 位;緊隨其后的是“停課停學”,平均排序2.46 位;“專門課程、場所的心理疏導與干預”“口頭或書面檢討”并列排在第三位,平均排序均為3.98 位;排在第五位的是“教師課后教導”,其平均排序為4.07位;排在最后的是“點名批評”,平均排序為4.17 位。從平均排序來看,教育懲戒方式的威懾力大小是:校級、年級處分>停課停學>專門課程、場所的心理疏導與干預(口頭或書面檢討)>教師課后教導>點名批評。
從結果分析來看,教育懲戒方式威懾力度大小的排序也基本符合《規則》中針對學生違紀行為程度輕重采取的不同程度教育懲戒行為的分類。《規則》第七條、第八條、第九條、第十條和第十一條分別規定了可以實施教育懲戒的情形,以及不同教育情形下可以實施的教育懲戒方式。首先,《規則》明確了教育懲戒適用的具體情形。其次,《規則》采取概括式表述,根據程度輕重將教育懲戒分為一般教育懲戒、較重教育懲戒和嚴重教育懲戒三類。在具體的懲戒方式上,根據學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學生違規行為的情節輕重,在第八條、第九條和第十條分層次制定了具體的懲戒方式。在《規則》中,“點名批評”“教師課后教導”“口頭或書面檢討”屬于一般教育懲戒,是可以針對學生越軌行為當場作出應對的輕微懲戒,因此其威懾力較小。“專門課程、場所的心理疏導與干預”以及“停課停學”是針對學生情節嚴重或影響惡劣的違紀違規行為的教育懲戒方式,屬于嚴重教育懲戒,因此這兩種方式的懲戒力度較大。“校級、年級處分”等其他教育懲戒方式則用于矯治違規違紀情節嚴重,或者經多次教育懲戒仍不改正的學生違規行為,因此威懾力度最大。
教育懲戒從實施的角度來看是一種懲罰性的手段。懲罰的功能本質上是防范性的,對痛苦的恐懼能夠防止被禁止的行為重復發生,進而達到引以為戒的效果。教育懲戒本身就帶有強制性和單向性,對于學生而言,教育懲戒這一教育手段具有威懾力也就不言而喻了。正是因為教育懲戒具有威懾力,懲戒機制才能流暢地運行。但正如前文所說,教育懲戒的目的是幫助學生成長,因此教育懲戒的威懾導致學生對懲戒、對權威帶有畏懼并非是一種目的。教育懲戒的威懾力可以制止越軌行為,幫助學生行為糾偏,但并非是對學生的越軌行為施以報復,讓學生感到害怕、痛苦。如果是以讓學生害怕、痛苦為目的進行懲罰,是教師在學校情境中至高無上權力的物質表現,是不連貫、不規范的,是凌駕于法律法規之上的,是為了在眾目睽睽之下制造強烈的恐怖效果,那么它不能稱為教育懲戒。
這一點也可以用于分析“教育懲戒方式的威懾力度越大,其教育效果越好”這一命題。針對上一題中威懾力度最大的教育懲戒方式,受調研學生被要求用1—10 來表達威懾力度最大的教育懲戒方式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解決問題,1 表示幾乎解決不了,10 表示幾乎都能解決,調研的平均數為5.68,眾數與中位數均為6。顯然,受調研學生并不認為威懾力度最大的教育懲戒方式就一定會有明顯的教育效果。教育懲戒是有威懾力的,最終會讓存在越軌行為的學生感受到害怕與痛苦,所以我們說懲罰伴隨著痛苦而來,但痛苦中并不存在某種神秘的德性,它僅僅只是懲戒的附帶反應,而非關鍵所在。愛彌爾·涂爾干指出,懲戒并非是為了使學生感受到害怕或痛苦,而是在遇到過失時確證過失所否認的規范。教育懲戒的威懾只能防止越軌行為的繼續危害,表現為一種對惡的后果的逃避,但并不能直接誘導學生得出一種對善的向往,所以威懾力只是一種手段,教育懲戒的最終目的應是要給學生重塑道德規范,使學生成為道德的個體。因此我們說,威懾力的大小并不與教育效果產生聯系,教育懲戒表現出的威懾力不是教育懲戒的目的,只是一種制止越軌行為、進而實現教育目的的手段。
五、教師對于懲戒方式的選取及學生的期待
在實施教育懲戒時,教師對于懲戒方式的選取存在兩種取向:一是以效果為導向,即根據不同的學生采取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教育懲戒手段來達到同樣的教育效果;二是以事件為導向,即針對同一類型的違紀違規行為,教師一視同仁地采取相同的教育懲戒。受調研學生中有215 人選擇了“以事件為導向”,占總數的36.9%;有360 人選擇了“以效果為導向”,占總數的61.9%;另外還有7 人選擇了其他,占總數的1.2%。這兩種取向很難分出孰優孰劣。“以效果為導向”是以保證教育懲戒的教育效果為前提的,因人因事、因時因勢采取不同程度或形式的教育懲戒手段,以期達到良好的教育效果。但是以效果為導向的教育懲戒,需要警惕教師依據學生的家庭、外貌、成績等因素對學生區別對待,美其名曰“以效果為導向”,這種教育懲戒手段的靈活性仍需要有定檔,在同一檔范圍內根據情況進行調整。而“以事件為導向”則更體現出違紀行為與教育懲戒之間聯系的必然性、確定性,體現出教育懲戒的剛性。學生視角下的教育懲戒應該是更具彈性的,體現出教育懲戒的人情味。教育公平并不是一個簡單的議題,公平也并非是絕對的平等,更不應打著公平的幌子行事實之不公平。公平體現在“起點公平”“過程公平”“結果公平”,因此,教師在實施教育懲戒的過程中,既要一視同仁,也要因材施教,在教育懲戒的彈性與剛性之間把握好平衡。
在“您認為針對初次出現違紀行為的學生,應采取怎樣力度的懲戒方式?”這一題中,我們要求受調研學生用1—5 來表示懲戒力度的輕重,1 表示程度相對較輕,5 表示程度相對較重。238 名受調研學生認為應當做到“程度相對較輕”,僅有25 名受調研學生認為應當做到“程度相對較重”。總體來看,受調研學生傾向于對初犯的學生采取較輕程度的懲戒。而針對屢次出現違紀行為的學生,除30 位受調研學生認為不應該加大力度實施懲戒之外,余下的552 人(占總樣本容量的94.8%)均認為應當加大懲戒力度。面對同樣的違紀違規行為,大多數學生認為應當根據是否初犯、是否屢教不改而采取不同力度的教育懲戒,體現的是中學生對于具有彈性的教育懲戒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