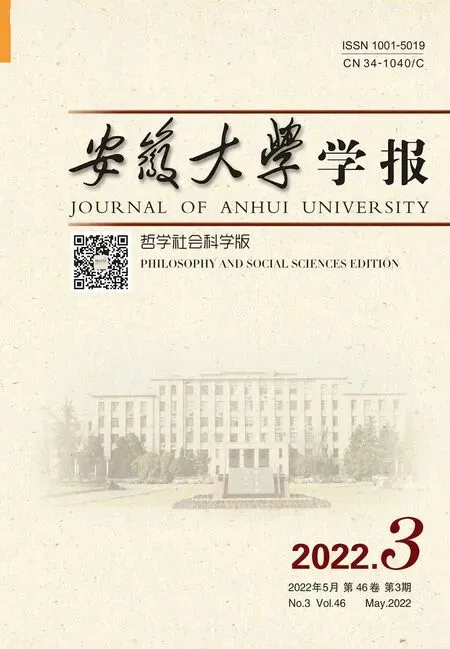被遺忘權作為新型權利之確證與實踐展開
阮晨欣
一、問題的提出
被遺忘權由歐盟法院于2014年通過“岡薩雷斯訴谷歌案”正式確立(1)參見蔡培如《被遺忘權制度的反思與再建構》,《清華法學》2019年第5期。。1998年在西班牙《先鋒報》的一篇聲明中,“岡薩雷斯”出現在為償還社會保障債務而舉行的房地產拍賣通知里。岡薩雷斯要求谷歌公司將其個人信息的全部內容刪除,《先鋒報》鏈接中也不得出現個人資料的相關內容。他認為這些債務多年來已經得到了充分解決,故這些個人信息不應再出現于網絡鏈接中。歐洲法院認為在權衡“有關資料的性質及其對資料當事人私生活的敏感性”與“公眾對資料之興趣”時,必須考慮公民個人信息之保護,進而達到“呼應社會趨勢,即個人掌握自己網絡生活的意愿”的效果(2)Eckart, Julia P., The Court Case Heard around the World——Google Spain SL v.Agencia Espanola de Proteccion de Datos——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and What It May Mean to the United States, Dartmouth Law Journal, vol.15, no.1, 2017, pp.42-43.。此外,2020年3月瑞典隱私數據保護局對未遵守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以下簡稱GDPR)的谷歌公司處以7500萬瑞典克朗(約合700萬歐元)的罰款,原因在于谷歌公司作為搜索引擎運營商執行用戶所提的“被遺忘權保護不力”(3)瑞典隱私數據保護局:《瑞典隱私保護局對谷歌處以行政罰款》(2020年3月30日)。https://www.imy.se/en/news/the-swedish-data-protection-authority-imposes-administrative-fine-on-google/,最后訪問日期:2021-03-20。。從實證角度看,被遺忘權的相關案例在國外已經不再是偶發事件,涉及該權利的案例數量逐漸增多。
2015年12月任甲玉案被稱為中國“被遺忘權第一案”,因為在該案判決書中首次出現了有關“被遺忘權”的認定問題(4)參見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2015)海民初字第17417號民事判決書、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5)一中民終字第09558號民事判決書。。被遺忘權的認定難點在于需要思考以下兩方面的平衡:一方面在互聯網中能夠輕易發現公民相關信息是言論自由和公眾知情權的體現;另一方面法律需要回應應該允許哪些信息可以從公眾視野中“消失”。目前,司法實踐仍不足以滿足公民對個人信息權的保護期待。面對當下個人信息安全受到侵犯的嚴峻態勢,無論是從保護個人信息權的完整性出發,還是基于對個人信息自由控制的社會心理需要之考慮,被遺忘權的確定和保護都有其必要性。早在2013年我國首個個人信息保護國家標準《信息安全技術公共及商用服務信息系統個人信息保護指南》(GB/Z 28828-2012)第5.5節規定了個人信息主體的刪除權利和行權范圍,在具有正當理由時個人數據可被刪除,且刪除的范圍涵蓋全部的個人數據。201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以下簡稱《網絡安全法》)第43條也涉及個人要求網絡運營者行使刪除行為的內容。202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隱私權和個人信息保護”章第1037條從法律上了表明對個人信息刪除等行為的保護。2021年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表決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以下簡稱《個人信息保護法》),在第四章規定了個人在信息處理活動中的權利。在法秩序統一原理下,被遺忘權是否屬于新型權利,應屬法律框架下的何種權利,仍需從新型權利溯源和正當化訴求論證等方面展開探討。
二、被遺忘權:一種有爭議的權利
被遺忘權是否作為一種新型權利,重點在于權利人是否享有個人信息自決權的全部內容。如果在維護個人信息的主動控制狀態時,公民個人不希望信息處理者對個人信息進行處理,并要求其刪除與抹去,那么該信息不應當允許被公眾隨意查詢。目前,在被遺忘權是否作為新型權利方面存在較大爭議。盡管較多國家立法都認為個人對其信息享有積極權利,強調個人對其信息的控制,具體表現為在發現其信息存在錯誤或不完善時,個人有權請求更正或者補充,以保證個人信息的真實性、完整性和準確性(5)參見王利明《法治:良法與善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67頁。,但對于“被遺忘權”這一術語的定義無法統一。國外有學者認為被遺忘權這一概念是以法律上的資格為基礎的,如信息被刪除的權利、社會遺忘和被遺忘權,且這種被遺忘的權利和允許個人遺忘的權利都可以放在遺忘的保護傘下(6)Karlsen, Meredith, Forget Me, Forget Me Not: A Right to be Forgotten in New Zealand’s Information Society, New Zealand Law Review, vol.2016, no.3, 2016, pp.507-508.。還有學者認為應將被遺忘權定義為一種確定權利,而這種權利的內涵是“忘記和被忘記的合法利益”(7)Bert-Jaap Koops, Forgetting Footprints, Shunning Shadows: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in Big Data Practice, A Journal of Law, Technology and Society, vol.8, no.3, 2011, pp.231-232.。它可能是一種需要保護的價值或利益,也可能是通過法律或其他監管機制以某種方式實現的政策目標。在被遺忘權的具體行為方式方面存在刪除、去索引、擦除、反對和遺忘等分歧。在行權方式方面,有學者提出參考美國《破產法》的方式實施“被遺忘權”的擬議程序。《破產法》為個人提供了恢復其金融聲譽的機會,正如被遺忘權為個人提供了修復其網絡聲譽的機會一樣。該擬議程序要求為互聯網服務提供商創建一個信息處理預設規則。同時,還有學者結合GDPR和美國《數字千年版權法》(DigitalMillenniumCopyrightAct)規定的對互聯網服務供應商的法定要求,認為應構建一個更細致的被遺忘權通知和刪除規則體系。
首先,被遺忘權應是一種獨立權利,并非否定說所認為的被遺忘權屬政策目標或道德規范(8)See Bert-Jaap Koops, Forgetting Footprints, Shunning Shadows: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in Big Data Practice, A Journal of Law, Technology and Society, vol.8, no.3, 2011, pp.231-236.。對于人的權利的保障應通過合法的具體的法規范確立,而不是以隨時可能發生變化的政策目標加以保護。法定權利通過把憑借自己普遍的、事先規定的規范化所創造的合法性的尊嚴賦予該項權利,既是順應信息社會中公民對個人信息安全感之需求,更是法治國用理性主義承載法規范對公民人權保障的明確規定。為此,《民法典》在人格權編設專章即第六章確認和保護隱私權和個人信息安全,具體表現為在隱私權一般性概念中離析出生活安寧權和私密信息權兩種特殊形態(9)參見汪習根《論民法典的人權精神:以人格權編為重點》,《法學家》2021年第2期。。從公民迫切需要掌握個人信息的完整性出發,公民意圖獲得被遺忘權來處理過去的、已公開的、負面的信息,以此維護公民形象和社會評價。而該項權利正是對人之尊嚴和人之自由進行權利化保護的體現。個人信息被遺忘權的權利化過程之所以能夠保護公民隱私和公民信息不受侵犯,在于它既是對公民物質利益的滿足,也是對公民尊嚴與自由價值的精神利益的保護。因此,被遺忘權的權利化過程是人權保護的自然選擇,是一種人應當享有的權利。
其次,被遺忘權作為個人信息權的一項子權利獨立存在,具有對抗信息控制技術所裹脅的牢籠逆境之作用。當今時代,信息大規模出現于網絡空間的現狀并不意味著所有信息都需要無限制普遍訪問。被遺忘權確立的必要性除了其具有維護人格尊嚴和自由在內的人權保障以及加強法規范規制以打破私力救濟與公權保障的不平衡性等因素之外,還在于個人信息基于大數據技術、人工智能、區塊鏈技術等科技發展,已經形成數據記憶模式,使得人們逐漸脫離“遺忘”這一人之本能,造成“人們有可能被信息控制技術所裹挾”之后果(10)梅夏英:《論被遺忘權的法理定位與保護范圍之限定》,《法律適用》2017年第16期。。我國有必要引入信息的遺忘機制,并進行本土化的創設,給予公民犯錯后重新做人的改造機會,對過去信息進行修訂和刪除。因此,越來越多的人申請對過去的信息行使被遺忘權,以此捍衛個人的自由權利,從而擺脫信息技術裹挾之后果。
最后,被遺忘權應是個人信息權的獨立子權利。這一新型權利,符合中國社會所存在的權利的各種新現象與新樣態,符合法律框架的相關規定,也符合法的正當性要求。被遺忘權作為一項新型權利存在,或者說作為一項獨立權利進入法系框架,存在合理性和現實基礎。否定說否定該權利作為公法獨立權利,認為該項權利勢必造成價值沖突和緊張,也會給互聯網企業帶來更多的成本負擔,還是應當回歸隱私權等具體人格權進行保護(11)參見楊樂、曹建峰《從歐盟“被遺忘權”看網絡治理規則的選擇》,《北京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4期。。這種援引“被遺忘權會踐踏言論自由”之觀點缺乏根據。該權的行使與言論自由之間并不沖突:行使刪除等行為時側重對個人信息的抹去,是一種“不說”的權利;而言論自由更多地強調信息流通與表達權的實現,是一種“說”的權利(12)參見薛麗《GDPR生效背景下我國被遺忘權確立研究》,《法學研究》2019年第2期。。被遺忘權基于法律規定的行使范圍,使人們“重新做人”與遺忘過去,最重要的是取得個人對公開言論的控制權。這是一個人對于過去所發生之事的一種修正。如果能夠滿足法律上的寬恕,那么公眾的言論表達將更加自由。在不影響他人合法權利的前提下,該權能夠滿足個體不欲公開的愿望。此外,被遺忘權是個人信息權完整性不可缺少的內容。被遺忘權能夠有效干預存在于網絡上已經過時、不合時宜、影響個體當前生活的信息。它通過向信息控制者提出請求權,進而實現被遺忘的效果。當然,在對個人信息實現控制時不可避免會產生與其他法益的沖突,這與個人信息權的行使范圍有關。例如《個人信息保護法》在個人信息處理規則中規定了六種不需取得個人同意進行信息處理的例外情形。從重視個人信息自主權的觀點來看,給予個人對過去可能會對其未來身份產生負面影響的信息的控制權是有價值的。
三、被遺忘權作為新型權利之確證
被遺忘權應是個人信息權的獨立子權利,具備隱私利益、財產利益以及其他人格特質。基于對個人信息自由控制的社會公眾心理之需要,確立被遺忘權能夠滿足公民對個人信息的控制自治和信息自由。本部分從法律體系框架和法秩序一體化視野出發,確證被遺忘權應是新型權利。
(一)被遺忘權之法正當性
1948年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19條界定了表達自由權的概念,認為這項權利包含有主動發表和信息傳播之自由的內容。尊嚴與自由是人類發展的動力,也是各國法律孜孜以求的公共利益所在(13)參見李先波、趙彩艷《大數據時代未成年人刑事信息被遺忘權保護困境及構建路徑》,《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如果被遺忘權得到救濟和實現,那么個人信息能夠通過刪除或斷開網絡鏈接等形式實現網絡消失,這是人之尊嚴與自由得到實現的具體體現。
1.一般人格利益:人之尊嚴與人格自由
被遺忘權與人之尊嚴與人格自由息息相關。它在法源上是“基本法價值私法化的工具”,在理念上追求尊嚴、自由等人格利益(14)高富平、王苑:《被遺忘權在我國移植的法律障礙——以任甲玉與百度公司被遺忘權案為例》,《法律適用》2017年第16期。。歐盟的一系列數據立法傾向于從一般人格權角度出發,維護人之尊嚴和人之信息權利,且并未明確區分隱私、信息等相關權利,而是作為一體化的基本人權加以規定。這些規定也符合歐盟立法維護人格尊嚴的基本價值追求。與歐盟的立法價值有所區別,美國相關立法則更側重于自由價值之實現(15)參見陳國軍《論大數據時代個人信息的私法保護與共享》,《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1期。。基于本土化移植考察,被遺忘權的法益不應認定為單一法益類型,因為該法益涉及一般人格權為基礎的人之尊嚴、人之自由等多種人格利益,并具有解釋、創造、補充等多種功能。在任甲玉案中,司法機關對當事人提出的被遺忘權訴求給出了回應,認為如果支持其訴訟,就應當證明該權利的合法性依據,最終駁回了任甲玉相關訴求。但是司法機關將任甲玉主張的被遺忘權視為一般人格權判決,并將該問題作為案件爭議焦點的做法意義深遠。基于此案,如果對被遺忘權的法益尋求保護,應盡量在本土法律化的框架中進行,且盡量避免“無效的負擔”(16)參見丁宇翔《被遺忘權的中國情境及司法展開——從國內首例“被遺忘權案”切入》,《法治研究》2018年第4期。。總之,基于一般人格權論述被遺忘權的法益,應當從理念上論證其具有人格尊嚴、人格自由等人格利益,并對公民的侵害行為進行法律框架內的正當性證成。確立被遺忘權的原因,來自公民想要刪除過去的信息、過去的記憶,進而不被他人所打擾和看見的心理。這一心理體現的是對過去網絡中所發生之事進行信息掩埋。無論是不愿被他人提及的負面形象,還是不愿被他人發現的擴大化的信息公開影響,都是對人格形象的一種侵犯。
2.個人隱私利益: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
被遺忘權的法益內涵與個人隱私利益具有關聯。1960年William Posser在論文中描述了隱私權在侵權法領域是如何創立的,以及將多少種不同的侵權行為列入其中(17)侵權行為包括非法侵入(intrusion)、公開披露私事(public disclosure of private facts)以及扭曲他人形象(placing a person in a false light)等。參見[美]路易斯·布蘭代斯、塞繆爾·沃倫等《隱私權》,官盛奎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03頁。。隱私權的核心在于不公開表達的自由,以及確定公開限度的權利,這表明隱私權具有消極自由的表現。英國古典主義哲學家通常認為的消極自由,指他人無法直接或間接、有意或無意地妨礙公民私人空間的權利(18)參見[英]以賽亞·柏林《自由論》(修訂版),胡傳勝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171頁。。它基于對公民私生活的尊重,給予公民自由生活的安全感和不被打擾的寧靜狀態。美國對于被遺忘權的相關規定,多源于對公民隱私權的保護,這種隱私權保護包含有公民處置個人信息的能動性自由。因此,有學者認為通過隱私權這一具體人格權,才能在技術迅速發展和網絡空間不斷擴大的背景下,“為網絡主體的人格自由構筑絕對性的權利堡壘”(19)陳璞:《論網絡法權構建中的主體性原則》,《中國法學》2018年第3期。。部分學者把被遺忘權劃為具體人格權的邏輯起點,力圖通過傳統的具體人格權對新現象進行剖析(20)參見雷閃閃、郭小安《關于被遺忘權法律性質的再思考》,《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不可否認,被遺忘權與隱私權密不可分,其核心法益也離不開對隱私信息的保護。從過去提出的信息性隱私權概念出發,這一“他人控制別人收集和公開有關自身信息”的權利,是從一種社會普遍心理訴求到公民個人權利保護的規范(21)張民安、林泰松:《隱私權的界定》,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491頁~497頁。。很顯然這一規范并非保護公民全部的私人行為,它受到一定的限制。這種基于隱私防御性權利的順利行使,有賴于整個社會群體的隱私規范以及他人不主動侵犯隱私空間才能實現。因此,被遺忘權具有消極自由的內涵。同時,被遺忘權也具有積極應對的一面,它對于個人信息的控制力使得這一權利凸顯了積極自由的內涵。
3.個人信息權之完整性:獨立子權利
被遺忘權能夠滿足公民對個人信息的控制自治和信息自由。個人信息權與被遺忘權關系緊密。作為新型權利,個人信息權具有獨特的法益內涵,我國正以此為基點構建日趨完善的個人信息保護體系(22)參見劉艷紅《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法益:個人法益及新型權利之確證——以〈個人信息保護法(草案)〉為視角之分析》,《中國刑事法雜志》2019年第5期。。被遺忘權歸屬于個人信息權之子權利進行保護,具有現實意義和實務操作性。作為一項獨立權利,被遺忘權不同于隱私權。首先,從權利的生成邏輯看待,隱私權來自公民對私人生活不受他人侵犯與打擾的一種安寧私密狀態的迫切需求。而被遺忘權則強調對個人信息的一種完整控制狀態。這種完整控制狀態與私密空間的安寧狀態側重點有所不同,它并不以信息是否具有隱秘性而進行區分,公開的信息同樣屬于個人信息權處理和控制的范圍。依據《民法典》第1032條、第1034條之規定,隱私權保護與個人信息權保護同屬人格權編的不同內容,二者具有不同的生成邏輯。個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在無法適用有關隱私權規定后,適用有關個人信息保護之規定。其次,從隱私權與被遺忘權的保護內容來看,隱私權中所涉“隱私”除了私密信息,還包括私密空間、私密活動。被遺忘權的對象則為個人信息,它以識別公民身份為標準。最后,從隱私權和被遺忘權的行使方式來看,隱私權強調對隱私信息的一種消極防御方式,即當事人不作為義務的行使,就是對隱私的一種保護。一旦當事人以作為行使公開他人隱私,則隱私失去了其專屬特征成為公開信息。被遺忘權則是主動行使的積極權利,在當事人發現其個人信息存在法定事由,例如已經超出雙方的約定、公開信息的目的已經實現、違反法律或行政法規之規定情形等,可以主動主張個人信息處理者刪除相關信息,以實現這類信息從互聯網層面消除的效果。總之,我國個人信息被遺忘權與隱私權屬于具有一定交叉的分立權利,不能將二者混同。我國法規范中并未明確提出“遺忘”,但被遺忘權的相關法律探索一直在進行中。我國具有豐富的個人信息刪除權立法經驗。因此,在本土化進程中認定個人信息被遺忘權與個人信息刪除權的廣義解釋重疊,具有法律適用和權利確定的雙重必要性。將“刪除處理”行為作為被遺忘權的重要行使手段,具有我國本土發展特色與對國外判例和規范的借鑒色彩。
(二)被遺忘權之法確證
法確證之概念源于刑法中正當防衛的正當化根據。對法確證原則或法確證利益的含義,有學者從法秩序規范有效性或法秩序統一性(23)參見魏超《法確證利益說之否定與法益懸置說之提倡——正當防衛正當化依據的重新劃定》,《比較法研究》2018年第3期。之概念理解,有學者從法預防性(24)參見歐陽本祺《論法確證原則的合理性及其功能》,《環球法律評論》2019年第4期。的角度理解。在此使用“法確證”之概念,是從法律體系框架和法秩序統一性出發,確證被遺忘權是新型權利,且其包含有獨特的法益內涵。被遺忘權的世界發展潮流給我國立法和司法實踐帶來很多經驗參考,但我國基于本土法律體系發展與實際國情的現實需求,并沒有對歐盟或者美國的被遺忘權立法進行照搬照抄,而是傾向于持謹慎態度,但目前的發展趨勢為逐漸對該項權利進行確定。
被遺忘權確立的法根基在于《憲法》《民法典》《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法律法規提出的對人權的保障和對網絡空間的保護。在法律法規層面,《憲法》第33條規定的“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表明人格尊嚴是一項基本人權值得保護,并為其他法律法規的制定與實施作出指引。第38條、第40條對人格尊嚴的保護規定是《個人信息保護法》制定的法源。針對個人信息保護的系列立法也表明我國對被遺忘權的重視。從我國立法實踐來看,被遺忘權保護的最初樣態為公民賬號注銷權的行使。公民通過行使賬號注銷行為得以抹去個人在互聯網中存在的記憶。以刪除行為作為脈絡找尋個人信息被遺忘權的法規范,具有科學性和合理性。一是有關個人信息刪除權的行使條件的規定。2012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的決定》第8條規定了要求網絡服務提供者刪除個人信息的情形,主要包括公民發現個人身份、個人隱私在內的個人信息被公開導致損害后果發生和來自商業性電子信息的侵擾兩方面。這與之后《網絡安全法》第43條對用戶啟動刪除權的行權范圍存在差異,后者范圍得到了擴大,且該權的啟動以個人申請單一方式進行。《個人信息保護法》第47條以列舉形式規定個人信息處理者應主動刪除個人信息的行為,包括處理目的的完成形態(已經實現、無法實現或目的不再必要)、服務停止或保存期限到期、公民個人撤回申請同意、違反法律法規行政法規或者違法約定以及其他情形。《個人信息保護法》所規定的刪除權通過個人信息處理者主動刪除和公民個人請求刪除兩種方式啟動。民法中對人格尊嚴的保護,體現在對一般人格權和具體人格權的保護中(25)參見王利明《人格權法中的人格尊嚴價值及其實現》,《清華法學》2013年第5期。。《民法典》第1037條列舉了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處理個人信息和違反約定處理個人信息兩種情形,可以通過申請請求處理者刪除。二是對有關特殊領域的個人信息刪除權的規定以及刪除處理具體行為的規定。《民法典》第1029條是對信用信息的刪除權。我國自古就有誠實守信的傳統,而被遺忘權建設可以參考本土存在的信用制度。該刪除權行使是通過異議方式對信用評價不當的個人信用信息進行刪除。三是對有關侵犯個人信息刪除權構成犯罪情形的規定。早在2000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于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第4條規定了構成犯罪的刪除情形,具體指非法截獲、篡改、刪除他人電子郵件或者其他數據資料,侵犯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之行為。我國刑法具體體現在第246條侮辱罪、誹謗罪,第252條侵犯通信自由罪,第253條之一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286條之一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等罪名中。此外,還包括相關司法解釋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相關問題的具體適用規定。
總之,在我國確立被遺忘權具有法正當性和法確證性。當然,如何規范個人信息處理者基于被遺忘權的相關責任與義務,如何刪除或是斷開網絡相關鏈接,仍然是法律治理中的難題(26)參見蕭郁溏《以比較法觀點規范網絡服務提供者于防制性隱私內容外流之責任與義務》,《政大法學評論》2018年9月總第154期。。賦予公民個人信息被遺忘權,能夠在網絡空間中劃分公共空間之公共利益與私人自決權之主動性的邊界,從而為保護公民信息權利提供更多方式。
四、被遺忘權作為新型權利之司法實踐展開
被遺忘權的確立,不僅可以滿足公民個人信息自決權完整性之實現,還是公民對網絡時代算法控制人類的一種反抗(27)參見姜野《算法的規訓與規訓的算法:人工智能時代算法的法律規制》,《河北法學》2018年第12期。。現代技術發展帶來的信息監獄,使得針對公民個體的數字記憶很難為人所忘卻。該權利正是基于此困境,賦予公民被遺忘的權利,使其對過去信息進行修正和彌補。公民刪除或隱去過去的信息,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逃離算法的監視,在不違背自己意愿的情況下給予或者不再給予信息的使用權,以此達到個人信息的安全。一方面,公民通過銷毀處理已不符合當下形象的個人信息,能夠使得負面信息隨著時間的推移獲得諒解和被社會忘記,進而樹立更為符合自己意愿的人格形象,從而實現人之尊嚴和人格自由;另一方面,公民能夠主動行使被遺忘權體現了法律對公民個人信息保護的關切態度。
(一)被遺忘權對個人負面形象的消減和更正
隱私權的保護遠遠無法滿足當今網絡社會對信息的保護需求,而被遺忘權的消極自由權利屬性,能夠以其防御性內容對個人隱私信息進行保護。在1931年著名的美國隱私案(Melvin v.Reid)中,當事人Melvin在判決結束7年且已經結婚6年后,發現在一部電影中包含她過去從事妓女隱私行業的故事。盡管她后來已經在社會中過著受人尊敬的生活,但這部電影所講述的經歷被其認為是對隱私權的可訴權利之侵犯。法院認為在出版物中包括Melvin的名字“無論以何種道德或倫理標準都是不正當的”,并認為這“是對她追求和獲得幸福這一不可剝奪的權利的直接侵犯”(28)George, Edward J.,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in the Digital Age: Using Bankruptcy and Copyright Law as a Blueprint for Implementing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in the U.S., Georgetown Law Journal, vol.106, no.3, 2018, pp.911-912.。這一判決肯定了沃倫和布蘭代斯所關注的第二種信息侵權行為,即私人事實的公開披露(29)Citron, Danielle Keats, Mainstreaming Privacy Torts,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98, no.6, 2010, pp.170-171.。這種侵權行為的認定邊界相當明確:它必須是公開行為而非私人披露行為,并且向公眾披露的事實必須是私人信息而非可以公開的信息。在該案中,這一行為加重了當事人的負面形象,侵犯了其人格尊嚴。
被遺忘權通過對已過時、不合時宜信息的刪除,或者僅基于公民主體主動請求刪除、斷開個人信息,能夠給予公民一個改變過去的機會,并消減個人的負面形象。這在一定程度上會鼓勵公民未來更多的表達,并使其處在一個安全可控的信息自決范圍內,創造言論自由發展的良好網絡環境。在任甲玉案中,法院認為被遺忘權在國外判決中已正式確立,并作為法規范存在于GDPR表達中,屬于歐盟所確立的概念;而我國盡管對該項權利有諸多探討,但法律法規中對這一權利類型并未有明文規定。本文不贊成法院認定的并無被遺忘權權利類型以及一般人格權權屬之說,但不可否認,該案的意義在于“賦予相關利益在具體的個案中享有實體法上的準權利地位,在程序法上承認并按照權利的規定給予適用權利保護方式和責任承擔方式保障的機會”(30)參見張建文《新興權利保護的合法利益說研究》,《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這仍然是被遺忘權被法律和司法實踐重視的體現。
被遺忘權對公民形象的更正具有范圍限制,尤其表現為信息控制力的限制。新技術為公眾提供了廣泛的發言機會,它們分散了對文化、信息生產和廣大受眾的控制(31)參見杰克·巴爾金《表達自由在數字時代的未來》,《蘇州大學學報(法學版)》2021年第1期。。首先,行使被遺忘權受到主體限制。普通公眾的個人信息傳播范圍有限,在較短時間內較少存在爆發式的傳播,造成的影響效果不會太大,由此產生的沖突風險多基于個人自身的發展或個人自身過去的負面評價。正如前文提到的任甲玉案件中,任甲玉過去的教育機構經歷雖然存在于互聯網搜索引擎中,但是第三方看到的人群多為招聘機構,一般普通人很少會去查其他人過去的經歷,損害的也是任甲玉個人的未來工作規劃和可能獲得的崗位。因此,普通公眾被遺忘權的沖突利益,更多傾向于個人利益價值本身。而公眾人物的被遺忘權則需要在合理基礎上進行必要的限縮。公眾人物過去的形象如果靠被遺忘權得以不斷隱藏和“洗白”,那么世間將永遠存在正面且完美的公眾人物,其所犯下的道德錯誤、法律錯誤也將被一并掩蓋。這顯然不符合利益平衡的標準。其次,信息發布目的使得行使被遺忘權受到限制。信息發布主體基于法律允許或公共利益的需要發布個人信息,如司法文書公開中存在未成年人主體、存在公民隱私等例外,以及數據脫敏后的公眾信息發布等,是個人利益更多的讓渡給公共利益的存在。
(二)被遺忘權以信息的控制程度衡量責任
《個人信息保護法》第51條規定個人信息處理者必須基于個人權益的影響、可能存在的安全風險采取必要措施,承擔相應義務,以滿足公民對個人信息的控制權利。在信息處理者做好相應措施履行信息處理義務后,網絡平臺經營者的合法利益也應當受到法律的保護。就保護個人信息的觀念而言,對信息的控制程度意味著要平衡信息處理者和公民之間的關系,并基于一定的價值衡量采取措施以期達到雙方的平衡。我國法律法規對于被遺忘權的權利保護形式和侵權結果承擔之適用,重點在于根據上述利益平衡確定權利行使的邊界。
在杭州蜜獾文化創意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標權糾紛案(32)參見范天嬌《平臺及時履行刪除義務不承擔侵權責任》,《法制日報》2020年4月22日,第6版。中,法院通過適用“通知—刪除”規則進而保護網絡平臺經營者合法利益。該案具體案情為該公司在北京某公司經營的手機App上,發現某酒吧未經其授權許可,使用注冊商標“一品脫”字樣,認為北京某公司未盡平臺審慎義務,造成其侵權后果。由此,該公司要求北京某公司承擔侵權責任并賠償損失。在這一侵害商標權糾紛案件中,法院通過分析該手機App的經營模式,認定涉案視頻系第三方用戶自行上傳,認為該互聯網平臺公司并未存在與侵權公司某酒吧共同侵權的主觀故意,也沒有進一步擴大對蜜獾公司的侵權影響,最終認為北京某公司不承擔侵權責任。這一案件中,基于信息的流通性和數據共享的平衡,在被告實施刪除義務后,并沒有新的損害結果的發生,平臺不承擔侵權責任。這一判決符合互聯網平臺發展需求,也保護了原告公司的商標權法益。這些都是合理保護理念的體現。
《民法典》《網絡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對個人信息安全進行了初步規定,但其規定的內容不夠細致,很多概念仍未厘清。由此法律需要進一步完善,從而依法進行法益衡量。與私法保護公民個人信息法益相對應,公共空間存在大量的隱私信息,公民個人信息無時無刻都處在透明狀態。但是,“公共空間大規模監控的運用,從客觀上提升了公安機關發現違法犯罪的能力,從而有助于抑制潛在不法者的主觀犯罪動機”。這種基于犯罪預防的公權力獲取公民個人信息行為,并沒有完全犧牲公民個人隱私和對財產進行侵害,可能只是“收集、存儲和使用了廣義上的個人信息”(33)劉艷紅:《公共空間運用大規模監控的法理邏輯及限度——基于個人信息有序共享之視角》,《法學論壇》2020年第2期。。在新冠疫情暴發之初,出現了大規模特定區域的手機號在內的個人信息泄露事件,這并不是堅持公共利益衡量、保證公眾知情權的體現。如果受侵害的權利主體可以提起基于被遺忘權的法益訴求,那么即便是過去主動公開的個人信息,也同樣可以要求信息控制者采取刪除、屏蔽個人信息的措施,并追究其侵犯公民信息權的刑事責任。
(三)被遺忘權對“刪帖”“洗白”行為的回應
有關“刪帖”“洗白”案例已逐漸引起公民與實務關注,并對公民個人信息保護的法律適用產生了困擾。行政法高度關注個人信息的收集和不法使用,而刑法側重打擊個人信息的不法流轉環節(34)參見李懷勝《公民個人信息保護的刑法擴展路徑及策略轉變》,《江淮論壇》2020年第3期。。以何某、付某等人自媒體“碰瓷”案為例,其利用相關報紙旗下微信公眾號在當地的影響力,選擇不同地產商發布“不實負面信息”,然后讓地產單位出資幫其刪帖,最終何某、付某等人被分別判處有期徒刑并處罰金(35)參見青島市黃島區人民法院(2019)魯0211刑初847號刑事判決書;參見李長安《自媒體“碰瓷兒”法紀不容》,《人民法院報》2019年11月17日,第2版。。在該案中,何某等人既是管理者又是經營者,發帖刪帖的權利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地產商則害怕自媒體聯合發布負面信息導致其自身利益受損。2013年9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通過的《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3〕21號)第7條認定有償為網絡信息提供刪除服務等行為,屬于非法經營罪的行為類型。而相關非法刪帖產業轉入地下成為黑灰產地帶,為法律治理增加了難度。2014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通過的《關于審理利用信息網絡侵害人身權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法釋〔2014〕11號)第14條進一步規定,相關支付報酬進行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服務的行為為違法行為。但刪帖的不良需求并未因為司法解釋的規定從此銷聲匿跡,反而更為突出,從過去的有償刪除個人信息行為,進一步擴大到“輿情監控”和“搜索監控”等領域。在“洗白”過程中,通過刪除帖子、割斷搜索引擎、搜索優化、雇傭“洗白”人員、運用黑客技術等手段,將網絡中的個人信息抹去,從而實現“正面形象”。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還存在行為人通過技術操作或金錢服務將對自己個人有利的信息在搜索引擎中提前,從而使自己和他人首先看到自己的正面信息的行為。
非法刪帖行為僅依靠非法經營罪這一罪名規制且僅針對刪帖群體是否合理值得商榷。這與被遺忘權的行使范圍密切相關。由此可以通過以下三種情形說明:第一種情形是公民主體通過找其他刪帖公司刪除對自己不利的他人言論或他人報道,這是對他人言論自由的侵犯,已超出個人權利的合法范圍。如果認為對自己不利的他人言論或他人報道涉及誹謗、侮辱,完全可以依據私法對公民人格權的保護進行起訴,并進而根據情節嚴重程度以侮辱、誹謗罪處理。但是,刪帖公司的所作所為侵害了憲法賦予公民言論自由的權利。他人(進行言論表達或僅僅只是跟風、低程度的表達)的自由和尊嚴受到侵犯往往得不到保障,也不利于良好的網絡生態的營造和積極性權利的伸張。第二種情形是公民主體對自身言論或信息的刪除,尤其是公眾人物或官方機構,刪帖公司的行為則侵害了公眾知情權。第三種情形是要求刪帖或“洗白”之主體已侵犯他人知情權或言論自由等權利,那么從廣義上說,公民主體和刪帖公司存在一體的行動方向和目標,對這一主體的統一處理讓人產生對網絡世界的不安全感。法律監管和處理沖突風險的難點表明,被遺忘權的正式確立已經刻不容緩了。
總之,從司法實踐來看,在我國確立被遺忘權十分必要。該權能夠保護“信息主體”的言論自由,并通過行使對個人信息所享有的支配并排除他人非法利用的權利,實現主動性的積極自由與私密性的消極自由。被遺忘權也是個人信息權完整性不可缺少的內容。此外,針對公民個體這一弱勢群體與占絕對強勢地位的互聯網平臺之間的利益博弈,被遺忘權的確立能夠一定程度上改變二者不平等地位。從一定程度上而言,“被遺忘權的設定與實施有助于將這一失衡的天平予以扶正”(36)參見趙銳《被遺忘權:理性評判與法律構造》,《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5期。。被遺忘權的提出,使得公民能夠更完整地行使個人信息權,對個人信息進行廣泛控制。在發現無法刪除過去個人信息的情形,公民能基于該法益提起請求權,維護個人的人格尊嚴,實現言論自由的更好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