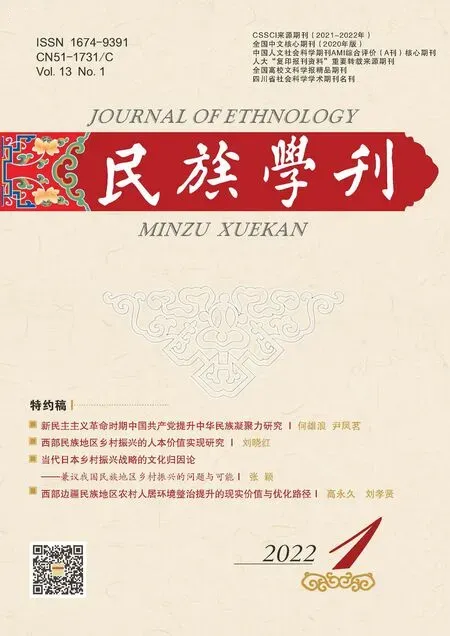外部勢力干預下的阿富汗族群沖突特點及影響
李 濤 袁曉姣
多數研究認為,阿富汗問題主要源于其國內的族群問題,而族群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勢力的干預造成的。各族群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直接決定和形塑阿富汗的政治結構及其與世界的關系。[1]69-70雖然族群本身在阿富汗并非政治因素,但自1992年以來,族群已成為外部勢力用于阿富汗政治和軍事動員的主要來源。[2]11-12
2021年10月12日,王毅外長在出席二十國集團阿富汗問題領導人特別峰會中指出:“阿富汗過去20年的經驗教訓再次說明,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發展道路、不同文明相互包容互鑒才是國與國相處的正道。將自身意識形態強加于人,動輒干涉別國內政,甚至訴諸軍事干預,只會帶來持續動蕩和貧困,造成嚴重人道災難。國際社會應尊重阿富汗主權、獨立、領土完整,支持落實‘阿人主導、阿人所有’的基本原則。”[3]從理性務實角度出發,支持阿富汗人民自主選擇符合國情的發展道路,最終組建廣泛包容的政治架構,尊重少數族群的基本權利,奉行與各國特別是鄰國的睦鄰友好外交政策才能有效促進阿富汗族際關系的和解。
一、外部勢力干預阿富汗族群沖突的背景
(一)特殊的地緣政治地位
阿富汗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地理上,阿富汗位于亞洲的中心地帶,地處戰略要沖,是連接南亞、東亞、中亞和西亞的樞紐。阿富汗北臨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東北與中國為鄰,東部和東南部與巴基斯坦接壤,西部與伊朗相鄰。地緣政治學家一再強調歐亞大陸核心區對世界霸權的戰略重要性,伊克巴爾(Mohammed Iqbal)稱阿富汗為“亞洲的心臟”。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歷史上不同時期的阿富汗都引起了外部勢力的注意。阿富汗曾是北方民族進出南亞次大陸的主要戰略通道。俄國進出印度次大陸,阿富汗是必經之地。自19世紀以來,世界主要霸權多次在阿富汗進行角逐。在19世紀,阿富汗成為英國和沙皇俄國之間的緩沖區。進入近現代以后,阿富汗是英國北上中亞、蘇聯南下印度洋的可選通道之一,后來也成為美國北上中亞地區的戰略通道。[4]
“杜蘭德線”(Durand Line)則使阿富汗周邊地緣政治局勢更加復雜化。1893年由英國殖民者劃定的“杜蘭德線”將普什圖族人一分為二,分別劃歸阿富汗和英屬印度。1947年南亞次大陸分裂時,阿富汗要求印度普什圖族“自決”的主張石沉大海。其結果是,阿富汗成為唯一反對巴基斯坦加入聯合國的國家,這也為未來30年間兩國緊張關系奠定了基調。[5]對巴基斯坦而言,夾在印度和阿富汗中間是噩夢般的場景,巴基斯坦迫切需要改變這一緊張局勢,蘇聯和美國的軍事介入則進一步加劇了該地區地緣政治緊張局勢。21世紀初,阿富汗作為毒品產地和跨國激進主義、恐怖主義力量的集散地,加上儲量豐富的戰略礦產資源,其戰略價值有增無減,大國政治的內容更豐富,策略也更多樣化。[6]
(二)民族特性中國家觀念薄弱
首先,族群的分散性和外部勢力的持續干預塑造了阿富汗分裂的社會與淡薄的國家觀念。阿富汗人至今尚未建構起“國族”,也未能形成具有“共同特質”的國族文化。[7]自20世紀后期以來,普什圖人、塔吉克人、哈扎拉人和烏茲別克人等因語言、宗教等方面存在的差異逐漸得到識別。但基于諸如“阿富汗北半部長期被視作波斯的組成部分”這樣的觀點和現象的存在,“國族”對阿富汗各族而言仍是一個比較陌生的術語。阿富汗的國家權力受限于社會的微觀層面,村莊、山谷、部族、部落以及宗教團體構成了分散的權力政治框架。[8]各個族群分布在興都庫什山脈及其被孤立的山谷,以及沙漠、河谷、草原的側翼。其中占統治地位的是普什圖人,同時還有講波斯語的塔吉克人和哈扎拉人,講突厥語的烏茲別克人和土庫曼人以及其他少數族群。這些民族在20世紀初成為由英國和沙皇俄國劃分的緩沖國居民。因此,阿富汗是作為典型的緩沖國家出現的。其不僅身處19世紀英帝國和俄羅斯帝國的對峙之中,還部分地被這種對峙所定義。當英國人在印度根深蒂固時,俄國人通過建立若干保護國擴張進入中亞,使得俄國人和英國人成為后來被稱為“大博弈”爭斗中的潛在對手。①但讓對峙變成真正意義上的戰爭對于英俄兩大勢力都沒有好處,在兩國之間存在一個緩沖國合乎雙方之需。這樣一來,阿富汗的國家疆界在19世紀末由此大體固定下來。[9]12-13
其次,以部落聯盟形式建立的王朝國家政府權威虛弱。在政治和行政意義上,阿富汗是以一個特點鮮明的王朝國家建國。在艾哈邁德沙·杜蘭尼(1747-1772)時期,阿富汗以部落聯盟形式建立了統一國家,此后君主制度存續了兩個世紀。在19世紀的大多數時間里,阿富汗國表現為前現代形式。[10]由于受英俄等帝國勢力的干預,阿富汗各族群部落未能實現獨立發展,而是依賴從外國政府獲得經濟和軍事資源。一個以部落為基礎的君主政體監督著一個軟弱的政府,強加給那些沒有融入共同經濟或民族的族群。[11]在地方層面,阿富汗仍保留了以部落制度為代表的地方自治制度。國家的合法性主要來源于傳統形式的代表和協商,特別是普什圖部落的領導,同時將遜尼派伊斯蘭教納入法律體系。然而,這種合法性是有條件的,國家必須嚴格限制對地方或私人事務的不必要干預。直至1978年4月發生共產主義政變后,阿富汗的王朝統治才結束。在這一時期,作為緩沖國的王朝統治者主要依賴外國保護鞏固和加強統治地位。
中央權威虛弱和社會分裂為外部勢力的干預提供機遇、抓手乃至代理人和盟友。外部勢力的干預同阿富汗族群沖突進程持續互動,相互塑造。外部勢力的干預并非阿富汗的主動選擇,外部勢力的介入加劇了阿富汗族群分裂。“阿富汗國從根本上說是一個軟弱的國家。一方面,它在這個國度的很多地方是一個無所不在的存在;另一方面,它在大多數時候又只是一個被動和遙遠的存在。”[9]14中央政權偶爾能夠集中權力來為其目標服務。但大多數時候,在國家和國民之間有一條深深的鴻溝。首都喀布爾的官員討厭被派到外省,而很多農村居民發現城市官僚對于農民的生活方式和調整其社會關系的正當傳統結構一無所知,[12]這樣的國家政權無助于管理和控制復雜的農村地區。因此,阿富汗政治、社會結構和文化的核心特點,即政府權威虛弱、社會四分五裂、極富反控制的獨立精神等民族特性中較為薄弱的國家理念,成為外部勢力干預阿富汗族群沖突的重要客觀原因。
(三)族群關系的跨國性
阿富汗國家歷史的演變及周邊地緣環境的復雜性塑造了其族群關系多樣性和跨國性。阿富汗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族裔眾多且構成復雜,其中主體民族為普什圖人,其次是塔吉克人、哈扎拉人、烏茲別克人以及其他少數民族。普什圖語和達里語是阿富汗的官方語言,此外還有烏茲別克語、土庫曼語、俾路支語等其他語言。在宗教信仰方面,阿富汗主要人口信仰穆斯林,其中多數為遜尼派,以哈扎拉人為主的少數人信仰什葉派,還有包括印度教徒、錫克教徒和少數基督徒等其他宗教信徒。同時,由于地處亞洲大陸的中心地帶,阿富汗人口較多的族群都屬于跨境族裔,具有跨境人口比例高、族裔成分多、分布范圍廣等特點。阿富汗各族群的分布在各個方向上都跨越了國家政治界線,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邊界兩側都有普什圖人,阿富汗塔吉克人、烏茲別克人以及土庫曼人都與相應的鄰國擁有跨境民族,哈扎拉人則與鄰國伊朗同屬于什葉派穆斯林。同時,來自更廣泛地區的強大文化影響,特別是來自古代波斯和中亞,以及阿拉伯次大陸的鄰近地區部落傳統與普什圖人具有許多相似之處。[13]阿富汗各族群與相應鄰國之間因民族、語言、宗教信仰等關系構成了族群間關系的跨國性特征。因此,盡管政治邊界將阿富汗與周邊鄰國劃分開來,但阿富汗的族群與周邊鄰國仍存在跨境民族間溝通與互動關系,深受周邊鄰國的影響。
二、外部勢力干預下的阿富汗族群沖突歷史脈絡
(一)族群矛盾形成階段(1893-1979年)
英國庇佑下的普什圖人政府推行民族等級制度埋下了阿富汗族群間矛盾隱患。自16世紀到18世紀,印度莫臥兒人、波斯薩法維人和烏茲別克沙伊布尼人共同占領了現在的阿富汗。18世紀由普什圖人建立的杜蘭尼王朝使阿富汗成為統一國家。19世紀后,阿富汗成為英國和沙皇俄國的爭斗場。在經歷了三次抗英戰爭后,阿富汗于1919年打敗英國,實現獨立。但1893年英國入侵阿富汗劃定“杜蘭德線”后,由英國庇護的普什圖家族統治阿富汗國家和社會,推行民族等級制度,埋下了普什圖主體民族內部以及主體民族與其他少數民族間矛盾隱患。普什圖人在國家治理過程中長期采用“排他性”部落統治模式,在國家所有領域和地區都享有特權,獲取了占有公職等大批公共產品的機會。[7]阿富汗人受到的不同待遇伴隨著族群成見的形成而出現。普什圖人被認為是“好戰的”,塔吉克人被認為是“節儉的”,烏茲別克人被稱為“野蠻的”,哈扎拉人被稱為“文盲”和“窮人”。[2]3-4普什圖人主要掌控國家政治權力和軍隊,塔吉克人在阿富汗政府公共服務部門和貿易部門占據主導地位,土庫曼人和烏茲別克人則主要從事農牧業,哈扎拉人位于社會最底層。以杜蘭尼家族為代表的普什圖人牢牢掌控阿富汗國家政權;塔吉克人善于經商,阿富汗各大城市的金融和貿易大多由塔吉克人掌握,構成了阿富汗城市富裕階層主體;烏茲別克人和土庫曼人以農業和畜牧業為生;因普什圖領導者的擴張主義政策和遜尼派對什葉派穆斯林的歧視,以游牧為生的哈扎拉人則被迫遷往城市,成為阿富汗社會的低收入者。
普什圖人作為阿富汗的一個多數族群,與其他部落和族群間關系一直存在爭議。最重要的是,多年來普什圖部落間的競爭間接壓制和擾亂了塔吉克人、烏茲別克人和哈扎拉人等其他族群的區域和社會環境。這些少數族群在后來阿富汗反塔利班行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1]76-77
(二)族群矛盾加劇階段(1979-1989)
蘇聯的入侵加劇了阿富汗國內族群分裂和外部勢力的干涉。蘇聯入侵阿富汗以后,由普什圖人主導的民族等級制度格局被打破,開始逐漸逆轉為對非普什圖人團體有利的政策。由蘇聯扶植的帕切姆派掌權后,增加了非普什圖人在軍隊和官僚機構中的代表性。[14]蘇聯的入侵將阿富汗從一個遙遠的前哨變成了冷戰對峙的關鍵場所。[9]17族群成為團結和分裂阿富汗反對派武裝組織的一個重要因素。在巴基斯坦,普什圖伊斯蘭主義者牢牢控制著抵抗運動的領導層,而伊朗則支持哈扎拉什葉派團體。[15]243-253對蘇聯的軍事抵抗來自阿富汗社會各界,但武裝抵抗人員逐漸被稱為“圣戰者”。阿富汗圣戰者的組成多種多樣,包括主要在巴基斯坦開展活動的政黨、阿富汗國內態度搖擺不定的指揮官以及支持他們的社群。②圣戰者反映了阿富汗社會各族群、教派以及經濟等方面的復雜性和意識形態的差異性。其中包括接近列寧主義的“伊斯蘭黨”、溫和的“伊斯蘭社會黨”以及受蘇菲教派和瓦哈比教派影響的一些較小黨派。這些黨派成為國際勢力干預阿富汗內政的突破口。[16]
在20世紀80年代,圣戰者的抵抗行動得到了美國和巴基斯坦的積極支持。美國的意圖是打擊蘇聯支持的阿富汗政府,并將圣戰者視為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相比之下,巴基斯坦的戰略利益則更為復雜。巴基斯坦與阿富汗的邊界爭議自1947年以來持續發酵,因此巴基斯坦無意于增強阿富汗世俗化民族主義者的地位,而是傾向于支持阿富汗激進的伊斯蘭主義者。③戈爾巴喬夫上臺后蘇聯開始撤軍。同時,蘇聯鼓勵其扶植的納吉布拉政府嘗試通過“民族和解”來擴大政權基礎。依靠蘇聯提供的物資,納吉布拉在1989年蘇聯撤軍后得以繼續維持統治。但其統治存續是靠使用蘇聯提供的資源收買阿富汗不同黨派關鍵人物的忠誠。這些資源一旦耗盡,各黨派立刻改換門庭,1992年4月,納吉布拉政權徹底崩潰。
蘇聯入侵阿富汗期間還導致了大量難民的出現。至1990年初,約620萬阿富汗難民生活在國外,其中多數分布在巴基斯坦和伊朗。④在巴基斯坦的大部分難民后來成為塔利班運動的滋生地。塔利班的崛起是數十年來普通阿富汗人日常生活遭到破壞所導致的結果。⑤塔利班的發展,也為阿富汗國內族際關系和族群沖突帶來更多不確定因素。
(三)族群沖突爆發階段(1989-2001年)
蘇聯撤軍后,在無政府狀態下,由外部勢力支持的阿富汗各族群間爆發了激烈的權力紛爭。其中,以俄羅斯、印度和中亞國家支持的北方聯盟與巴基斯坦、阿拉伯國家支持的伊斯蘭武裝聯盟間軍事沖突為主要代表。
蘇聯撤軍后,納吉布拉政權隨之垮臺。喀布爾被阿富汗圣戰者成員接掌,但同時面臨兩個難題:一是他們雖然接管了喀布爾首都地區,但卻沒有繼承到有效運行的國家機制。在此期間,政府軍隊分裂成民族和地區兩大陣營。二是圣戰者內部因權力分享方案出現了意見分歧。盡管大多數遜尼派穆斯林圣戰者領導人同意成立“領導委員會”,但卻遭到少數領導者的拒絕。[17]盡管此后為彌合分歧進行了數次嘗試,但圣戰者內部關系仍然持續高度緊張。這一時期,圣戰者內部的對峙導致了殘酷的武裝沖突,造成了嚴重破壞。各種政治組織控制著首都喀布爾不同區域:西部是什葉派“統一黨”的軍隊,北部是效忠于艾哈邁德·沙阿·馬蘇德(Ahmad Shah Massoud)的軍隊,巴拉希薩爾地區是追隨前共產黨指揮官阿卜杜勒·拉希德·杜斯塔姆(Abdul Rashid Dostum)的民兵,帕格曼地區則是阿卜杜勒·拉蘇爾·薩亞夫(Abdul Rasul Sayaf)的支持者。[18]1992年6月,“統一黨”與薩亞夫的軍隊率先爆發武裝沖突。緊接著,南面的伊斯蘭黨軍隊也參與進來。
塔利班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登上阿富汗的政治舞臺。塔利班先后攻占了坎大哈與赫拉特,又于1996年9月占領了喀布爾。[19]巴基斯坦的支持對于塔利班運動的崛起起到了關鍵作用。[20]塔利班的最初目的是結束阿富汗國內的無政府狀態。但在面對強大的非普什圖軍閥和民兵時,塔利班希望再次重建由普什圖人控制的中央集權國家。[15]243-253在塔利班執政期間,普什圖人內部也出現了分裂,阿富汗南部和東部的普什圖人高級指揮官與塔吉克領導人馬蘇德結盟。塔利班與馬蘇德展開了激烈的軍事斗爭。
(四)族群沖突深化階段(2001-2021)
9·11事件后,以美國為首的外部勢力對阿富汗族群沖突進入新干涉主義時期。美國出兵阿富汗之后,喀布爾落入反塔利班武裝手中,大部分塔利班領導人逃往巴基斯坦。此時,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繼續通過支持塔利班,并為普什圖人接管阿富汗提供資金。⑥另一方面,伊朗、俄羅斯、印度和部分中亞國家則繼續支持非普什圖人的北方聯盟。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則通過多數決議,支持通過阿富汗各方之間旨在建立基礎廣泛、多族裔和具有充分代表性的政府的政治談判推動和平進程。
美國扶持的過渡政府族群政治體系進一步加深了阿富汗各族群之間的分裂。美國支持的阿富汗新政治體系旨在平衡族群關系,防止沖突再次爆發,表面試圖讓新政治體系更具代表性、更開放、更公平地為所有阿富汗人提供競爭環境,實際卻仍建立由普什圖人主導的政府,且更突出了族群問題在阿富汗政治中的重要性,加劇了族際政治斗爭與隔閡。[1]79此外,中央集權制度也未能在國家層面實現有效治理。其中精英聯盟和庇護政治仍然為當權者服務,但在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方面收效甚微。政府關鍵職位的任命相當于政治利益的分配。美國扶持的阿富汗過渡政府新政治機構的設計繼承了阿富汗政府一貫的軟弱性。過渡政府在議會選舉中實行民族配額制度,加劇了極為脆弱的族群沖突局勢。[21]根據《波恩協定》,阿富汗過渡政府成立了多達29個政府部門,這奠定了各個族群構成的政治派別所控制的政府部門相互對峙的基調。[22]再者,美國2002年反對將國際安全協助部隊(ISAF)擴展到喀布爾之外,迫使卡爾扎伊政府將外省和地方的實權職位交到武裝分子手中,以獲取地方武裝勢力的暫時和解。這一決定導致合法的地方領導階層被邊緣化,特別是以普什圖部落結構為基礎的地方領導階層。從長期來看,這一決定使過渡政府在阿富汗民眾心中的形象受到極大破壞,導致了嚴重的裙帶關系和行政失當問題。⑦
此外,阿富汗2004年憲法確立了強大的總統制,其結果是在行政系統內部創造了一個超負荷的辦公室,導致一些關鍵問題除非引起總統注意否則就無人處理的尷尬局面。然而,美國推出的過渡政府領導人卻無法勝任掌舵者一職。卡爾扎伊總統是在20世紀80年代的阿富汗無政府政治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其政治理念并非關于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而是對保護國、關系網和盟友關系的維系。“隨著時間的推移,卡爾扎伊的優勢越來越無足輕重,其弱點卻日益凸顯。環繞在其周圍的自私自利、陰險狡詐的幕僚網絡使得這一問題更加惡化。”[23]同時,阿富汗政府還面臨持續不斷的塔利班叛亂。
三、外部勢力干預下的阿富汗族群沖突主要特點
(一)族群成為外部勢力干預阿富汗內政的主要工具
外部勢力將族群作為其干預阿富汗內政合法性的主要論據。一方面,無論英國、蘇聯還是美國都是將意識形態與外交政策相結合,將族群作為干預阿富汗內政的工具,最終都體現為對阿富汗的占領和改造。另一方面,阿富汗國內各政黨則以族群的名義尋求國際庇護和國內社會政治動員,以實現其政治要求和目標。民族意識形態的領土化成為以民族或族群名義使用暴力的重要條件之一。[24]尤其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族群在阿富汗軍事戰爭和政治言論中的地位有所提高,各類政黨試圖以族群的正當性和合法性來宣傳其政治主張。例如,巴基斯坦通過支持阿富汗普什圖人領導的伊斯蘭武裝勢力來應對普什圖民族主義的威脅。蘇聯入侵阿富汗以后,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支持為巴基斯坦提供了削弱普什圖民族主義的長期愿望。巴基斯坦通過支持阿富汗難民中的泛伊斯蘭主義,資助邊境地區的伊斯蘭政黨,由此導致了一種新的“普什圖伊斯蘭主義”,塔利班掌權期間,這一特征得到了進一步強化。以普什圖伊斯蘭主義為特點的塔利班打擊親印度、親俄羅斯和親伊朗的北方聯盟,反對阿富汗所有溫和派和進步派普什圖人團體和政治領導人。在此情況下,相互競爭的各政治派系加強了族群歸屬,為族群分裂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也將這種分裂擴大到普通民眾,加劇了族群的政治化。
(二)國際庇護為族群贊助政治提供了機會
外部勢力的干預增強了庇護政治在阿富汗族群政治中的作用,形成“國際庇護——中間人——贊助網絡”干預模式。歷史上,阿富汗曾長期屈服于部落權力、地方領導人和民族地區強大的“微觀社會”。[25]302-303因此,政府精英必須與外部勢力形成共同妥協、融合的復雜關系,從而確保中央政府權威和權力的合法性。美國入侵阿富汗以后,卡爾扎伊政府在美國支持下也采取類似舉措,對地方政治勢力以遷就政策取代武力鎮壓,并建立了一個復雜的關系網絡,一直延伸至村一級。[25]302-303這些關系網絡通過家族聯姻、伙伴關系和收受禮品等手段得到強化。卡爾扎伊政府試圖通過這一贊助關系網絡將各個族群、部落和派系組織領導人聯系起來,以獲取政治支持。然而,阿富汗族群政治派系由多種社會力量組成,其構成本身具有較大的模糊性。隨著各種外部勢力的介入,族際政治的贊助網絡和相互分裂也進一步加強。通過支持地方軍事指揮官作為關鍵的權力中間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強化了以族群和宗教團體名義運作的外部干預網絡。[15]6在阿富汗政治秩序中,族群政治由權力中間人領導的流動贊助網絡定義。通過從外部渠道獲取資源,利用族群、宗教派別和亞種族關系建立支持網絡。阿富汗一些政黨盡管公開承諾擁護新政府,但并未放棄與外部贊助勢力間的庇護關系。自2001年以來,在美國及其盟友等外部勢力的支持下,族群贊助網絡得到極大加強,反之又影響了族群聯盟的形成及其相互關系。選舉通過讓某些網絡承擔更大的政治角色,為贊助政治的繁榮提供了更大的機會,強化了以族群為基礎的身份政治標志。[25]316
(三)族群沖突隨外部干涉力量增加而加劇
蘇聯入侵阿富汗以前,阿富汗國內的族群矛盾尚未上升至沖突層面。主要表現為普什圖人和其他少數民族間矛盾,其中以普什圖人和哈扎拉人的矛盾最為嚴重,但并未上升至權力政治層面。阿富汗戰爭爆發之前,族群作為社會組織基礎的地位非常有限。盡管阿富汗國家已經將族群“歸屬”提升為政治的主要指導原則,但沖突仍局限于社會微觀層面,不存在利用族群來提出政治和經濟要求的政治運動。蘇聯入侵阿富汗以后,以美國為首的部分資本主義陣營國家也隨即介入阿富汗族群矛盾。在此階段,普什圖人與塔吉克人、土庫曼人以及烏茲別克人等少數族群聯盟矛盾進一步激化。加之國際伊斯蘭主義勢力的滲透,使得阿富汗族群矛盾趨于極端化。蘇聯撤軍后,已有的外部勢力繼續對阿富汗各個族群施加影響。在外部勢力的贊助下,無政府狀態下的阿富汗各族群爆發了激烈的權力紛爭。美國出兵阿富汗之后,阿富汗族群間隔閡與分裂進一步深化。在此期間,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安全部隊支持卡爾扎伊過渡政府,印度、俄羅斯和中亞國家與北方聯盟保持密切往來,同時印度追隨美國圍剿阿富汗塔利班,將其定性為“恐怖組織”,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等伊斯蘭主義勢力則成為塔利班的支撐動力。此外,聯合國也介入其中,試圖幫助阿富汗過渡政府建立代表廣泛族群的包容性政府和解進程。外部干涉力量的增加并沒有有效緩解阿富汗族群矛盾,反而導致阿富汗族群沖突更加復雜化,族群間政治分歧與隔閡也進一步加深。最為突出的表現是,美國主導下的前阿富汗政府,在總統之外還設立與其分權的“政府首席執行官”或“民族和解高級委員會主席”[26]。
(四)阿富汗族群沖突逐漸趨向伊斯蘭化
自蘇聯入侵阿富汗以來,在阿富汗國家政治中,伊斯蘭教的權威性得到了持續提升,其中部分原因是阿富汗伊斯蘭政黨從國際社會獲得了外部援助。但主要原因是阿富汗各族群間的權力紛爭與分化摧毀了其有限的民族凝聚力[27]12,傳統部落族群的權威逐漸被宗教權威取代。雖然阿富汗大部分民族都信仰伊斯蘭教,但1978年“四月革命”(又稱“Saur革命”)以及隨后的蘇聯入侵,成為阿富汗伊斯蘭主義族群動亂的起點。由蘇聯扶植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農村地區的改革遭到伊斯蘭教和部落機構的堅決抵抗。蘇聯的入侵改變了阿富汗內部族群紛爭的維度。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陣營支持阿富汗抵抗組織,其成員主要包括伊斯蘭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伊斯蘭主義者觀點激進,認為其斗爭主要是為建立一個符合伊斯蘭原則的國家和社會而斗爭。在國際伊斯蘭主義勢力的支持下,伊斯蘭教成為抵抗蘇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工具,一些代表普什圖人和塔吉克人的反對派領導者紛紛成立了“伊斯蘭黨”(Hizb-i-Islami)。[27]11-12國際支持者的政策更偏向以伊斯蘭教為導向的阿富汗政黨,這改變了阿富汗社會內部的權力動態,有利于伊斯蘭勢力,直接導致了傳統族群部落結構的削弱和激進伊斯蘭的崛起。[27]20同時,保守伊斯蘭教勢力的崛起對阿富汗普什圖的傳統部落結構也帶來挑戰。伊斯蘭政黨在阿富汗普什圖社區招募成員,建立宗教社會組織,創辦宗教學校,進一步鞏固了宗教力量,削弱了部落族群力量。阿富汗族群沖突逐漸演變為傳統部落勢力和伊斯蘭武裝力量之間的沖突。[27]23
四、外部勢力干預下阿富汗族群沖突的影響
(一)對阿富汗國內政局的影響
外部勢力支持下的族群沖突打破了阿富汗國內政治力量的平衡,導致民族和宗教極端主義勢力的崛起。內部紛爭和外部介入使阿富汗各族群間相對實力發生了巨大變化,阿富汗傳統社會結構也因此迅速改變。蘇聯入侵阿富汗以后,終結了普什圖人長期統治阿富汗的歷史。蘇聯支持的人民民主力量政府推行激進的政策,旨在迅速改變阿富汗社會,包括強制推行土地改革、廢除封建制度、建立識字階層以及禁止某些宗教習俗等舉措。[28]結果導致普什圖民族主義勢力和伊斯蘭主義勢力的崛起和激烈反抗。在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支持下,這些極端主義勢力逐漸強大,致使阿富汗各族群間關系更加對立和復雜,政治紛爭不斷。同時,在大國勢力干預下,族群沖突還進一步加深了族際政治紛爭與隔閡。美國支持下的共和國政府建立的族群政治體系進一步加劇了阿富汗各族群間對立與分裂。美國支持的卡爾扎伊政府和加尼政府表面上試圖讓新政治體系更具代表性、更開放、更公平地為所有阿富汗人提供競爭環境,以平衡族群關系,防止沖突再次爆發。但實際建立仍是由普什圖人主導的政府,且更突出了族群問題在阿富汗政治中的重要性,加劇了族際政治斗爭。[1]79
族群沖突導致阿富汗國家重建的政治基礎殘缺不全。在與各自“盟友”的關系不斷加強的同時,跨境族裔人口與阿富汗的關系正在逐步疏遠。各族有限的實力和對諸族共同利益的淡漠,為“民族黨”亮相提供了契機。事實上,它們除了自己,不愿也不能代表各族共同利益,提出的“建設和平穩定的伊斯蘭國家”等治國方略,也很可能淪為一紙空文。[7]
同時,族群紛爭的長期存在,還促使維系各族群經濟聯系的紐帶更加脆弱,引發新的社會問題。阿富汗沖突各方長期相持不下,使本就貧窮落后的國家幾乎到了無路可走的地步,喀布爾一直未擺脫難民城市的困境。農村人口的貧窮和饑餓情況尤甚,導致大量平民死亡和流離失所,引發了難民危機。自2001年美國出兵阿富汗以來,沖突直接導致超過5萬平民以及約5萬1千多名塔利班武裝人員死亡。⑧而難民的跨境流動也為阿富汗邊境地區以及周邊國家帶來了諸多安全問題。
(二)對周邊地區安全的影響
在英國作用下劃定的“杜蘭德線”導致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間普什圖民族永久的政治分離。這一舉動破壞了普什圖民族主義的概念,將普什圖人強行分離,同時也導致阿巴兩國普什圖人的矛盾和沖突。此后,阿巴兩國因普什圖尼斯坦問題引發持續性矛盾以及周邊政治局勢的動蕩。其中,阿富汗一些普什圖政黨支持巴基斯坦普什圖人自決。巴基斯坦也試圖通過支持圣戰組織培養阿富汗普什圖人激進伊斯蘭主義思想以對抗普什圖民族主義。[1]79在阿富汗境內同時發生的戰爭中,包括巴基斯坦在內的幾個部落在阿富汗境內及周邊地區分散和流離失所,導致多年來該地區人口結構發生巨大變化。
外部勢力干預下的阿富汗族群沖突也對南亞和中亞區域各國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1979年蘇聯對阿富汗的軍事干預引發了戰爭和混亂的循環,反過來又在阿富汗的地緣政治環境中造成了重大變化。蘇聯的干預受到許多相互關聯的力量的挑戰,其中包括阿富汗當地、周邊地區和國際力量。這些新力量的崛起以及使其得以運作的跨國職能聯系對整個區域產生變革性影響。[29]2001年美國對阿富汗的軍事干預再次引發了新一輪的阿富汗戰爭和周邊局勢的動蕩。國際宗教極端主義勢力借機涌入阿富汗及其周邊鄰國,并制造多起恐怖襲擊事件,嚴重威脅周邊國家的邊境安全與穩定,進一步增加了該地區的反恐壓力和挑戰。同時,阿富汗的族際權力紛爭引發的難民潮和跨境毒品走私等非傳統安全問題還外溢至周邊鄰國,對周邊國家和地區構成安全威脅。內外勢力交織下的內戰與權力斗爭導致阿富汗戰爭持續數年,大量民眾逃往周邊鄰國。截止到2019年,伊朗和巴基斯坦收容了約400萬阿富汗難民⑨,其中部分宗教極端主義者混入難民當中,組織和策劃恐襲活動,周邊鄰國和地區因此遭受直接影響。
除外部援助外,阿富汗國內各族群黨派主要依靠毒品生產和交易以獲取資金。近年來,阿富汗生產的毒品嚴重影響了巴基斯坦、伊朗、中國等周邊鄰國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安全。[30]在巴基斯坦尤甚,據聯合國毒品和犯罪控制辦公室估計,阿富汗生產的鴉片類毒品近45%進入到巴基斯坦。⑩
(三)對國際安全的影響
國際泛伊斯蘭主義勢力的滲透導致阿富汗族群沖突向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發展,并擴散至全球。“基地”組織將塔利班的信仰轉變為對任何不遵循其信仰的人的仇恨。[31]98與動員農村普什圖族人的塔利班不同,“基地”組織使用自上而下的方法馴服塔利班領導人,以實現其將阿富汗作為泛伊斯蘭議程基地的目標。“基地”組織的目標受眾并非平民,而是已經信奉伊斯蘭教的社會骨干。[32]“基地”組織成功培養了阿富汗塔利班領導人,這有助于確保其意識形態進一步滲透到阿富汗以及其他國家武裝勢力中,并重新定義了阿富汗基于宗教而非族群的信仰基礎。[31]99-100“基地”組織以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邊境部落地區為隱匿地,向中東、北非以及歐洲等地區擴散影響力,并制造各類恐襲活動,對人類文明價值帶來巨大危害。
五、塔利班掌權后阿富汗族群沖突的走向
(一)族際關系的和解面臨內外多重困境
首先,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將加劇阿富汗國內族群沖突與人道主義危機。外部環境的變化與族群沖突的延續可能導致阿富汗陷入人道主義危機。長期以來,阿富汗的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外部援助,國家預算大部分都來自國外。美軍撤離阿富汗以后,不僅切斷了對阿富汗的資金援助,而且凍結前阿富汗政府中央銀行的財產,并在難民大規模流動和安全威脅的情況下拒絕予以國際承認。在阿富汗族群沖突和權力紛爭仍未結束的情況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阿富汗實施經濟制裁將會導致普通阿富汗民眾遭受更深重的苦難。其次,西方國家面臨是否應該承認塔利班政權合法性的困境。阿富汗境內恐怖組織與宗教文明界線開始逐漸模糊化,二者之間的匯流導致國際反恐任務更為艱巨,而塔利班與國際伊斯蘭主義極端組織關系密切。隨著塔利班接管阿富汗政府這一既成事實的確立,塔利班政權能否代表阿富汗合法政府組成符合各族群共同利益的聯合政府,區域大國如何與阿富汗國內各族群黨派進行對話,如何通過外交渠道和次國家外交體系進行有效溝通,[33]塔利班的包容性與合法性程度等問題成為西方國家是否予以認可的新困境。
同時,內部權力紛爭和國族認同的缺失也導致族群和解前景堪憂。塔利班認為,喀布爾的政府應該屬于普什圖人,而不是“異教徒”外國人和非普什圖人。但塔利班不會尋求建立單一的普什圖民族國家,而是重建伊斯蘭酋長國。[34]塔利班政權同時也表示,國家領土的完整不一定帶來社會融合。然而,長期持續的族群沖突導致阿富汗各族離心離德的歷史文化陋習長期傳承,國族認同長期缺失。將本族利益置于國家利益之上,已成為阿富汗各族群共同面臨的問題。阿富汗各族群已習慣于權力紛爭,不愿為建立強有力的政府而努力。實際上,阿富汗各族群的政治目標存在較大差異。從毒品生產和交易中獲益諸多的普什圖人,擔心政府強大而使其丟掉“甜果”。一些烏茲別克人擔心政府強大會威脅其與境外“同胞”實現“共同建國的理想”。[7]阿富汗族群關系的和解進程仍充滿不確定性。在執政能力有限的前提下,能否構建基于各方共識層面的廣泛包容政治架構將是塔利班政權面臨的主要挑戰。對內而言,塔利班政權必須同其他少數族群代表就政治取向、文化傾向等問題進行和平談判。“如果塔利班建立包含阿富汗所有族群、伊斯蘭教在內所有政治傾向以及那些尋求推動伊斯蘭進步運動力量的聯合政府,阿富汗就有希望;假如產生的是一個相當保守的政府,但只要它是一個主權政府,那么阿富汗也能有一些希望;如果它只是一個塔利班政府,或是一個部分由伊斯蘭世界其他國家或外部力量控制的政府,那么阿富汗就沒有希望。”[35]此外,主權關切、安全利益、地緣政治動態、跨境關系以及連通性和貿易等內外因素也將共同塑造阿富汗族際關系的未來前景。[36]2-3實現阿富汗的短期穩定并確保穩定局勢的長期可持續性將是一項巨大挑戰。決定阿富汗族群關系的緊張局勢源于許多結構性因素,且根深蒂固。近期俄烏沖突也將為阿富汗及中亞地區帶來深遠的地緣政治影響和更多不確定性。在當前暴力、戰略對沖和相互不信任的環境下,這些問題不太可能得到解決。[36]2-3
(二)族群沖突難以擺脫國際干預
塔利班重新掌權后,阿富汗很有可能再次成為受外部力量支持的阿富汗不同勢力之間權力紛爭的場所,并在南亞、中亞和西亞引發外溢效應。?“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近期正在阿富汗重組,在阿富汗得到了恢復并獲得了新的發展空間。[37]阿富汗裔美國作家安薩利對此指出,“很難想象外部力量不會再次試圖干預阿富汗。塔利班最初的成立也與外部力量存在聯系,比如其部分成員來自巴基斯坦一些激進的伊斯蘭宗教黨派控制的難民營;在塔利班成員童年時期塑造了他們世界觀的宗教學校是由阿拉伯世界其他地方的激進分子建造和資助的。阿富汗依舊是那個上演全球大戲的舞臺,對很多人來說,這場大戲比這個貧窮國家本身更加重要。”[35]
此外,塔利班政府也將尋求保護其在阿富汗利益的地區或國家的支持。其中,巴基斯坦仍有可能成為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的最重要支持者。主要基于以下因素:一是許多塔利班成員與巴基斯坦宗教學校和神職人員保持聯系;二是巴基斯坦將繼續保留通過控制貿易和過境聯系對潛在塔利班政府施加影響的能力;三是巴基斯坦軍方與塔利班領導人關系密切,且這種影響可能會持續。[36]27-28一位前巴基斯坦駐阿富汗大使建議,如果阿富汗穩定局勢有所改善,更多塔利班成員可以將其家庭和企業遷出巴基斯坦,以獲得更大的獨立行動空間,提高其在阿富汗的合法性地位。[38]
(三)塔利班政權與什葉派穆斯林少數族群和解困難重重
由于信奉什葉派伊斯蘭教,阿富汗內戰時期哈扎拉人曾面臨塔利班政權的嚴厲鎮壓。同時,哈扎拉人還一直是國際圣戰組織在阿富汗的主要目標之一,而阿富汗塔利班與國際圣戰組織關系密切。作為一個高度意識形態化的運動,塔利班不太可能在任何根本立場上發生轉變,盡管其可能會出于戰術考慮而設法讓自己顯得不那么極端。?普什圖人和非普什圖人之間,特別是普什圖人和哈扎拉人之間,沒有古老的仇恨。但他們之間的沖突關系在1992年之前由于阿富汗普什圖人政府的驅逐政策而變化。隨著塔利班的重新掌權,許多哈扎拉人擔心塔利班對哈扎拉人的大規模迫害會再次上演。盡管塔利班承諾組建一個包容性的政府,其政治領導層對哈扎拉人采取了更為務實的態度,但由于歷史積怨和宗教派別沖突等問題,短期內塔利班與哈扎拉人關系的和解仍面臨諸多障礙。
(四)國際恐怖主義勢力的上揚將為阿富汗族群關系和解帶來不確定性
當前阿富汗境內仍存在一萬多名外籍暴恐分子和圣戰者,大多來自中東地區。其中巴基斯坦塔利班約6000人,“伊斯蘭國”約2000人,“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以及“伊斯蘭圣戰聯盟”均約數百人,美國的撤軍將進一步刺激這些恐怖主義勢力做大。[39]59-61“阿富汗周邊地區國家和世界主要大國主要關心的安全問題是防止阿富汗再次成為國際圣戰分子的避風港。”[40]對此,塔利班發言人蘇海爾·沙欣(Suhail Shaheen)表示,塔利班希望和平移交權力,并支持阿富汗建立伊斯蘭包容性政府。[41]但實際上,伊斯蘭主義仍然是塔利班的基本底色,它不會在這一意識形態定位上后退和妥協,這是塔利班將其政權名稱定位為“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的原因所在。[42]阿富汗塔利班與國際伊斯蘭主義極端組織哈卡尼網絡(HQN)和“基地”組織具有長期而緊密的聯系,最早可追溯至阿富汗反蘇聯圣戰時期。與美國和北約部隊作戰的共同經歷,以及包括異族通婚在內的家庭紐帶,則進一步加強了這一密切聯系。[43]阿富汗北方聯盟代表艾哈邁德·馬蘇德(Ahmad Massoud)對此公開表示,愿意與塔利班建立一個包容各方的政府,但不會接受極端主義和原教旨主義。[41]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的包容性政策改變了過去的伊斯蘭極端主義,但也面臨如何在內部統一共識,彌合強硬派和溫和派分歧的挑戰。在外部,則面臨與巴基斯坦塔利班和“基地”組織等極端組織切割,遏制“伊斯蘭國”挑釁和擴張的挑戰。[42]
六、結語
阿富汗族群沖突因外部勢力干預而起,在內外勢力共同作用下沖突進一步惡化。族群沖突是外部勢力干預阿富汗內政和軍事的突破口。一方面,在國際庇護下,阿富汗族群贊助政治得到迅速發展;另一方面,國際伊斯蘭主義勢力的介入促使阿富汗族群沖突趨向伊斯蘭化。在國際伊斯蘭主義極端思想影響下,阿富汗族群沖突開始向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發展,并向外擴散,為阿富汗境內以及周邊地區及全球安全形勢帶來巨大挑戰。美國撤軍以后,西方國家拒絕承認塔利班政權的合法性,并對阿富汗實施經濟制裁,導致阿富汗新一輪的人道主義危機和族際關系的惡化。塔利班重新掌權后,阿富汗族群沖突的和解仍將面臨內部權力紛爭和國族認同缺失、外部勢力干預和國際恐怖主義上揚等多重障礙。
對此,國際社會應就解決阿富汗族群沖突達成共識。單邊主義無法支撐阿富汗周邊區域安全,需要利益相關者參與共同協商,并通過文明間對話以減少沖突。[33]世界主要大國應將區域安全組織和多邊協商機制作為協調阿富汗族群沖突的平臺,其形式和功能需進一步法治化和常態化,保障安全承諾得以落實,不朝令夕改。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員和軍事專家戴維斯(Daniel Davis)指出,“試圖將美式政體強加于阿富汗人民,試圖在喀布爾重建一個有凝聚力的中央政府,試圖將美國式的解決方案套用在阿富汗問題上,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試圖依靠軍事力量通過代理人強行介入,必然會失敗。”[44]和平與主權是解決阿富汗族群沖突的兩個最關鍵因素。如果阿富汗人能掌握自己國家的主權,如果沒有任何外國力量對阿富汗的內政指手畫腳,如果整個國家能長期(最好是永遠)處于和平狀態,那么阿富汗將以自己的方式和步伐走向現代化。文化隨著時代變化是一種必然,但這種改變應由屬于這一文化本身的人們來決定,通過他們之間的對話和談判來產生。[35]
此外,阿富汗鄰國要各盡所能,凝聚共識,協調配合,支持阿富汗人民開創美好未來。[45]自2021年9月以來,阿富汗鄰國協調合作機制充分發揮鄰國優勢,為阿富汗局勢平穩過渡起到了建設性作用。在幾次阿富汗鄰國外長會議中,與會各國達成八項共識,其中包括通過接觸和對話,引導塔利班建立包容性政府,尊重和保護女性權利,奉行溫和穩健的內外政策;同時避免阿富汗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外溢,防止安全局勢進一步惡化。[37]未來,國際社會還應推動阿富汗建立多元包容的價值體系。以多元文明和多維視角來審視阿富汗族群沖突問題,將人本精神和人文關懷作為解決阿富汗族群沖突的核心價值原則。[33]同時,國際社會還應就共同打擊阿富汗及周邊地區國際恐怖主義勢力開展廣泛合作。重新接管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與“基地”組織關系難以切割,在長期“圣戰友誼”和用人需求等基礎上,若塔利班與其強行切割將可能導致塔利班內部出現分歧甚至分裂。阿富汗國內恐怖主義抬頭將產生“圣戰武裝割據”的示范效應,刺激圣戰者流竄到阿富汗周邊國家和地區進行遷徙圣戰。[39]在此背景下,主要利益相關國應在準確預判阿國內形勢的前提下,利用現有和新建的多邊機制,共同商討,合作應對阿富汗國際恐怖主義勢力。
注釋:
①關于英俄對峙的進一步討論,參見Karl E.Meyer and Shareen Blair Brysac Tournament of Shadows:The Great Game and the Rac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Basic Books,New York,1999。
②參見Olivier Roy Islam and Resistance in Afghanista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90年,第98-148頁;Abdulkader Sinno Organizations at War in Afghanistan and Beyond,Cornell University Press,Ithaca,2008年,第119-172頁。
③參見Mariam Abou Zahab and Olivier Roy Islamist Networks:The Afghan-Pakistan Connection,Hurst & Co.,London,2004年,第53-57頁;Rizwan Hussain Pakistan and the Emergence of Islamic Militancy in Afghanistan,Ashgate,Aldershot,2005年第93-133頁.
④參見Fiona Terry Condemned to Repeat?The Paradox of Humanitarian Acti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Ithaca,2002年,第55-82頁;Sarah Kenyon Lischer Dangerous Sanctuaries?Refugee Camps,Civil War,and the Dilemmas of Humanitarian Ai,Cornell University Press,Ithaca,2005年,第44-72頁。
⑤截止到2000年,在官方層面,沙特阿拉伯停止了對塔利班的官方支持,但私人層面的支持仍在繼續。
⑥參見William Maley Rescuing Afghanistan,Hurst & Co.,London,2006年第128頁;Antonio Giustozzi Koran,Kalashnikov and Laptop:The Neo-Taliban Insurgency in Afghanistan,Hurst & Co.,London,2007年,第16頁。
⑦“阿富汗戰爭:美國結束最持久軍事行動的四大相關問題”,BBC News中文網,2021年8月12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8171639。
⑧“伊朗向境內阿富汗難民兒童提供教育機會難民署呼吁提供更多國際支持”,聯合國新聞,2019年12月6日,https://news.un.org/zh/story/2019/12/1047011。
⑨參見UNODC(聯合國毒品與犯罪問題辦公室)《The Global Afghan Opium Trade:A Threat Assessment》,2011年,第28頁。
⑩ Bruce Riedel Armageddon in Islamabad,載The National Interest,2009年第102期,第9-18頁;Michael E.O’Hanlon and Hassina Sherjan《Toughing It Out in Afghanistan》,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Washington,DC,2010年,第4-8頁。
? 參見Thomas Ruttig How Tribal are the Taleban?Afghanistan’s Largest Insurgent Movement Between its Tribal Roots and Islamist Ideology,AAN Thematic Report 04/2010,The Afghanistan Analysts Network,Kabul,June 2010,網址:http://aan-afghanistan.com/uploads/20100624TR-HowTribalAretheTaleban-FINAL.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