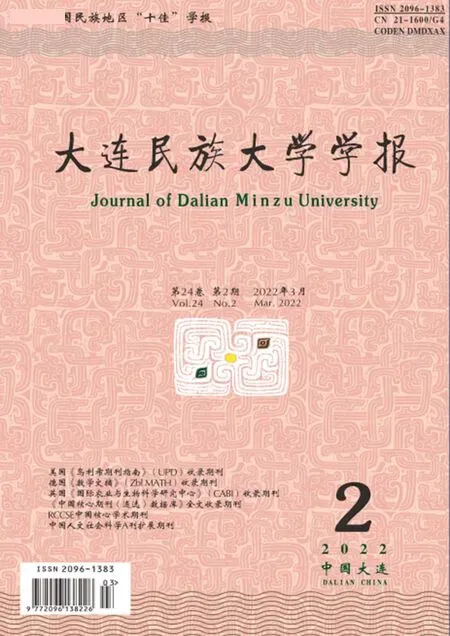雙雪濤小說的幽默敘事及對東北文化傳播的意義
鄭 玥,王 莉,紀秀明*
(1.大連外國語大學 漢學院,遼寧 大連116044;2.大連民族大學 學報編輯部,遼寧 大連116605)
小說語言不僅是敘事能力的體現,更是主體有意選擇后建構的切入世界的方式,涵蓋作家的創作意圖與價值判斷。黑格爾稱幽默能釋放出“精神的火花”[1],可視為作品精神核心的顯現。雙雪濤在訪談中也透露:“幽默不是調皮也不是雜耍,是一種本能,它是一種表達方式,在這個小說里我寫的一些看起來有點幽默的句子,它本身是有信息的,有我想說的東西在里面,而不是為了耍一個花活,來一個空翻,一個倒立”[2]。在雙雪濤的小說中,有大量幽默筆法佐證其觀點。幽默的敘事語言充分浸透著作家在東北的城市記憶,幽默打諢的語言背后是個體反抗孤獨的博弈和成長,是父子兩代人價值觀碰撞的隔閡和斥拒,更是對東北文化形象的解構與建構。透過幽默表象,探勘其實質是雙雪濤一代的新東北作家奪回文化闡釋權的敘事手段,為新東北文化補充了新視角,對推進新東北文化傳播大有裨益。
分析雙雪濤幽默敘事對東北文化傳播的意義,就要先厘清其幽默敘事語言與新東北文化形象建構的密切聯系。以小說虛構和現實真實的關系為例,雙雪濤在《我的師承》提到小說家的操守,他認為:“即使不用每次寫作時打上領帶,向書桌鞠躬,也應將時間放長,給自己一個幾十年的計劃每天做事不休……”[3]282。雙雪濤將小說寫作視為職業性的工作內容,一方面,作家的操守使其觀照現實,真實歷史背景和大量東北現實地標性建筑,常見于其大部分小說中,呈現出貼近現實的真實感;另一方面,帶有目的性的創作計劃和寫作意識,又人為地將文本和現實拉扯開,方便作者在距離中遙感歷史、折射現實,呈現擬態求其似的效果。這種寫作方式,使得雙雪濤的主體意識在小說情節的設置和小說敘述者評析的拿捏中尤為突出,在小說虛構性和現實真實性中突圍出來。為了彌合作家的主體選擇,其小說的語言敘事風格是勘破其小說思想內核的重要突破點。因此,本文結合小說中幽默語言的實例,擬從調侃式幽默、好壞顛倒式冷幽默和斥拒式幽默等方面,探究雙雪濤幽默敘事的獨特藝術魅力;同時挖掘其幽默敘事與新東北文化構建的內在關聯,分析雙雪濤幽默敘事對東北文化傳播的意義。
一、 調侃式幽默
也許對一個東北人來說,幽默感可能就像基因一樣,是刻在細胞里的樂觀。不似京圈的“純文學”血統,又或是上海的繁華現代,東北人身上總帶著一種“落地感”。他們得意地自夸,也坦誠地自嘲,用幽默的方式與這個世界打交道。雙雪濤用調侃的語氣建構出幽默氛圍,時常具有調節氣氛、舒緩敘事節奏等作用。
調侃式幽默是作者自我保護機制。當個體無法契合客觀主流的發展方向并與之產生沖突時,便會受到外來權力的擠壓與整改,此類“修正”行為會在對象的肉體或者精神上施加暴力。但是雙雪濤選用調侃式的幽默,以百毒不侵的姿態調侃暴力,作為個體與現實相處的潤滑劑。此類幽默敘事不僅展示出20世紀八九十年代東北特殊節點的歷史真實,插科打諢的調侃也流露出東北人天性樂觀的態度。首先是肉體暴力。從李斐(《平原上的摩西》)的自述中可以得知,幼年喪母是導致李斐的童年悲慘經歷的重要原因。父親是名工人,上班時間就將小李斐安置在托兒所。所里阿姨控制著小李斐的一切活動,包括上廁所的時點。孩子的玩鬧和無所顧忌便會招來嚴酷的管訓和一個接一個的巴掌。阿姨并不覺得行為不妥,反而義正詞嚴地宣告這些管教都是母親的職責。本是家庭缺失和教育不當導致的悲劇,但李斐意外認為“這讓我有些欣慰,沒什么大不了,晚上別的孩子有媽媽來接,我就會去想,你要倒霉了,回家也是這套”[2]15。童言無忌總讓人忍俊不禁,調侃暴力的幽默語言讓小說氛圍緩和下來,讓讀者啞然失笑的同時又覺心酸涌上心頭。幽默的甜緩釋了生活的澀,二者摻雜在一起展示八十年代東北城市生活的艱難現狀,寥寥數筆又將東北樂觀堅韌的脾性展示出來,共同構成了雙雪濤的調侃幽默機制。
再如《聾啞時代》中“我”遭受校園暴力的經歷。仗勢欺人的四年級大個子強搶“我”的電子表,倔脾氣讓瘦小的“我”在這場注定不公平的對抗中吃了苦頭。被對方一招打倒,手指被踩在地上咯咯作響,臨走時還受了迎頭一拳。這樣的暴力描寫是十分恐怖的,況且被害者“我”還是一個瘦弱的孩子。因放學比工廠下班早,挨完打后“我”仍需生火做家務。當油氈紙燒起來,不出意外的濃煙從爐坑里爭先涌出,“我”終于忍不住痛哭一場,“淚水沖壞了臉上完整的鞋印,因為我突然想起來,我已經六年級了”[4]。臉上完整的鞋印,和終于意識到自己被低年級打得毫無還手之力的事實,讓哭的行為變得又委屈又好笑。在雙雪濤的小說中,肉體暴力的承受者多為生活中的弱勢群體。他們的反抗被暴力壓制,遭受著種種無妄之災。但雙雪濤有意的調侃式幽默消解了暴力,肉體的暴力鉗制不住東北人思想的樂觀與堅韌。
除了肉體上的暴力外,言語欺虐也是雙雪濤小說中常見的暴力行為。《聾啞時代》多為初中時期的校園經歷,而老師則被作者有意放置在個性與自由的對立面,成為校園場域中權力的最高代言人。“我”創意的作文被語文孔老師掛上了零分的絞殺架,痛斥“這篇作文是她見過最長、最臭、最陰暗、最不知所云的作文”[3]29。英語老說“我”“扶不上墻”[3]29。雙雪濤三言兩語將東北特殊歷史時期下的社會隱痛描摹出來,但他無意做過多停留,繼而用幽默的筆法對抗和消解著傷人無形的暴力。面對老師語言上的尖酸嘲諷,“我”反而生氣的是“老子從小翻墻就不要人扶”[3]29。看似雞同鴨講的孩子氣般的應對,實際上是“自在的世界”與“自為的存在”的抗爭,用拒絕有效溝通的方式保護自我。
不論是遭受的肉體暴力,還是語言的精神凌虐,都通過調侃式的幽默語言化解暴力帶來的難堪與痛苦。幽默的調侃內化為東北人的喜劇因子,與東北二人轉和小品塑造的喜劇形象不謀而合;但東北“大下崗”背景下的大敘事和作者有意建構的自我保護機制,將東北人不以取樂為目的的幽默展示出來。在歷史的沉淀中,飽經風霜的幽默感滄桑倔強地在80年代以來加注在東北身上的刻板印象中突圍。以雙雪濤為代表的新生代東北作家,用幽默的文學態度,參與著新東北文化形象的構建與設想。
二、 好壞顛倒式冷幽默
如果說調侃式幽默是作者潛在的自我保護機制,那么好壞顛倒式的冷幽默則指向作者的審美傾向。此類幽默指的是在一定社會語境里人們的是非觀、價值觀和道德觀異化后產生的一種冷幽默,通常會引起人們對是非問題的反思[5]。在雙雪濤的作品中,好壞、美丑、乖巧與叛逆、正常與怪異的審美邏輯與常規相悖。異于主流的表象下,帶著理想卻悲情的浪漫主義色彩,潛藏著對人性的批判與理想,以及對新東北的展望與期待。
短篇小說集《獵人》的自序中,雙雪濤談及小說創作的心路歷程,以自剖式的書寫對自我進行精神層面的拷問。細讀自序不難發現,字里行間彌漫著精神孤獨的優越感與被消亡威脅的焦慮感。雙雪濤認為時間洪流勢不可當,現下鮮活的一切終將灰飛煙滅。直到與“我”有關的生活痕跡全部消弭的那刻起,才是其小說真正自由騰飛的起點。雙雪濤坦言“我腦中所規劃的未來也終有一天要成為遺跡,我寫下的小說將要獨自生活,成為自由的孤兒”[6]2。作者的毀滅意為重生的開端,每當作者預設到消亡來臨,精神便無由的震顫起來。雙雪濤對自己的野心與恐慌供認不諱,其言“正是我的膽怯使得他(特指‘我’的精神)驍勇而且貪婪”[5]2。直白宣告中帶著理直氣壯的態度,正視生命無奈的有限性與思想野性生長的無界限,讓原本附有消極含義的詞語轉向真摯坦誠的意味,呈現出理想卻悲情的浪漫主義色彩。
除了雙雪濤對創作本身內在性的思考,好壞顛倒式的冷幽默在小說人物形象設置中也可見一斑,最突出的就是無賴一類的人物描寫。“無賴”為貶義詞,意指不務正業、品行不端的人。在雙雪濤的小說中,對無賴的刻畫與主流釋義產生背離。小說《無賴》以20世紀90年代東北為故事背景,講述“我”家被迫拆遷后舉家投奔無賴老馬的故事。初識老馬,他被母親描述成酒鬼與慣偷的無賴形象。老馬總當著孩子的面,說些少兒不宜的話;嗜酒成性讓他看起來總是神志不清,像一顆隨時會爆炸的定時炸彈;偷盜前科更是他拿來酒后炫耀的“資本”,讓人瞠目結舌。但正是這位無賴,卻給予了“我”從未有過的溫暖。“我”費盡心機得來并修好的小臺燈,被工廠保衛科科長暴力奪走,“我”也被誤傷得鮮血直流。年幼的“我”執拗認為是老馬告狀,偏要他把臺燈要回來。孩子歇斯底里的強勢與對現實無力的弱勢形成對比,老馬安靜了半晌,決定替我拿回臺燈——竟是用自殘的方式。在酒瓶敲破腦袋之前,老馬又露出深醉時的微笑。他的微笑似乎宣告著精神的永恒勝利。文章結尾又下起了大雪,只不過這場雪更加瘋狂。工廠里的機器狂鳴震顫,路燈的吹響了午夜狂歡的號角。螺絲、軸承逃命式地飛濺,一切都跟著抖動起來。在這場無序的狂歡中,“我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安全感”[2]197。文章至此結束,而無賴深醉的微笑就像定格一般,停留在那個亮如白晝的雪夜。他的好色而大膽,是勘破世俗常規的不羈;他醉酒的不清醒,源于對現實清醒的認識;他偷盜的前科,是不偷就會餓死的生存法則下無奈之選。無賴粗俗卻溫柔,下流也可貴。不僅如此,小說《她》中,“我”期望成為“無賴”,認為“不要有無所謂的堅持,和百害而無一利的自尊”[3]195。綜觀雙雪濤的小說,異類人物比比皆是,除了無賴老馬,還有棋癡父親、瘋子安德烈(霍家麟)、戲癡呂東、飛行家李明奇等等。雙雪濤偏要打破審美的常規,將褒獎落實在真實的東北人性情之中。勘破人生的局限,才能更好扎根腳下,珍惜現在。也許正如《長眠》中那首朦朧詩,“讓我們就此長眠/并非異己/只是逆流//讓我們就此長眠/成為燭芯/成為地基/讓我們就此長眠/醒著/長眠//”[2]176長眠不是逃避現實,孤獨就是反抗孤獨的方式。
在雙雪濤的小說中,負面詞語帶有正面含義,而正面詞語逐漸喪失了人皆向往的魅力。《劇場》一文中,“我”買了一盆水仙花放在窗臺裝飾。這盆水仙花很漂亮,但“我”認為“水仙長得非常好,以至于我都覺得乏味,沒過多久我就又買了盆月季”[5]143。“好”本身是正面評價,但作者卻因為水仙太“好”,而感到乏味。再如《火星》中,高紅說“我的鳥死了,我懷疑是我媽過于喜愛他,而把他毒死了”[5]177。因為“好”而乏味,“太喜歡”所以厭煩。《聾啞時代》的學生群像中,“我”欣賞安娜的太妹性格,喜歡吳迪的狡黠與暴脾氣,討厭優秀學霸高杰和去個性變完美的昔日好友劉一達。這樣好壞顛倒的審美方式在作品中呈現出一種冷幽默,另一面真實。它不似前文調侃式幽默的興味,好壞顛倒式冷幽默透射出反諷和荒誕的鋒芒,從小人物的視角對東北大歷史事件進行獨特的思考,對人性的實時關注使小說散發出思辨的人文主義光芒。
三、 斥拒式幽默
除了調侃式幽默和好壞顛倒式冷幽默,斥拒式幽默指向人物關系的沖突,大多發生在父一代和子一代之間。此類幽默敘事為兩代人價值觀的碰撞,是不同時代下東北經驗的內部交流和碰撞。在雙雪濤的作品中,幽默敘事還牽扯到父子關系詰問上。即子一代對父一代旁觀者的分離姿態。小說中采用兩代人互看的視角,即父一代與子一代的相互審視,相互碰撞。小說中的子一代一般向著理想突圍,他們不能接受父一代的某些價值觀念,但血脈相承中的關愛又包圍著子一代,呈現出溫情又相互對峙的局面。也許,對于這批渴望邁入新生活的青年來講,一旦開始靠近父輩的思維習慣,便會陷入停滯不前的危險境地。只有采取旁觀者般的分離姿態,才能在心理和生活中獲得相對的穩定。
父一代的成長經歷伴隨著自五十年代起東北的壯大與輝煌。新中國成立之初對東北寄予厚望,資源優勢和經驗儲備讓東北成為當仁不讓的新中國工業基地的搖籃。回顧五六十年代的中國東北文化,長春電影制片廠制作了《白毛女》《上甘嶺》等一系列主流作品。工業的興盛、文化的成功將東北“共和國長子”的高大形象展現出來。以雙雪濤為代表的子一代新東北作家,他們在東北的生活經驗大致從八九十年代開始。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東北這個曾經輝煌無比的工業之子,首當其沖受到影響,出現了不可避免的退讓與隱痛。經濟策略的改革與發展影響著文學創作的內容和氛圍,在雙雪濤的作品中,生活窘迫的工人父母與野性生長的孩子碰撞起來。父一代的權威隨著經濟地位的下移逐漸弱化,子一代的叛逆成長和多元價值觀的引入使他們不愿接受父一代固化的思想觀念。
《聾啞時代》“我”的父母下崗,要去學校門口賣煮苞米,讓“我”感到巨大的恐懼。工人優渥地位的下墜,讓父一代產生生存恐慌,把孩子讀書賺錢當成救命稻草。年幼的“我”尚不能理解自己已經成為家庭的唯一希望,揉了揉眼睛說了句會努力學習的客套話,一家三口便抱頭痛哭。父母覺得兒子終于懂事了,而兒子只是被父母過度的期望壓得心驚膽戰和莫名其妙。無獨有偶,小說《跛人》中母親問兒子落榜后的退路,兒子直言去肯德基打工。“母親點頭了點頭說:不錯,有計劃就好。如果你落榜了,你知道我會怎么辦?我說:我不知道,你別太難過就行。她說:我會去死。”[2]137父母寄希望于兒子讀書上學改變命運,但時代的變化對子一代來說,終究是朦朧又模糊。父母苦苦支撐的艱辛、愛子之深與“我”的壓力感、羞恥和恐懼產生隔閡。嚴密厚重的愛并沒有喚起子一代的自我追問,反成為他無法承受的恐懼根源。
《光明堂》中,柳丁的姥爺死在礦上后不了了之,姥姥每想起姥爺去世的往事,便哭泣嘮叨。這種生活的苦難掩蓋在歷史的塵埃中,子一代柳丁當然無法理解姥姥敏感的情緒緣由,只覺得姥姥“哭起來沒完沒了,老淚縱橫,眼淚順著皺紋流到脖子后面去了”[6],形象十分可笑,柳丁躲避不及,甚至“聽得挺厭煩”。父一代切身經歷的苦難成為他們走不出的牢籠,而子一代并非事情的親歷者,一遍一遍地訴苦,以淚洗面并不能獲取他們的同情。雙雪濤用著十分大膽的語言刺激著讀者的神經,如果說調侃式的幽默敘事是作者試圖用滑稽的描寫,消解對抗現實生活中的種種暴力,那么斥拒式的幽默敘事則用更為冒犯式的敘事風格,將子一代與父一代的隔閡問題徹底暴露出來。這類幽默不僅是對父一代得過且過的混沌狀態的斥拒,也是對東北個體困境的關照和追問。
四、 幽默對東北文化傳播的意義
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使東北文化的發展和傳播面臨著巨大的挑戰。經濟重心的南移和文化市場日益增長的需求,讓東北文化的發展呈現力不從心的尷尬狀態。而雙雪濤的幽默敘事,有望助力新生代東北作家拿回文化闡釋權,在賡續傳統幽默風格和創新幽默內涵中,有望接替東北文化傳播的新一棒,促進東北文化傳播的良好態勢。
幽默不僅促進了東北文化的闡釋,也促進了東北文化傳播。文化自身特性是文化傳播的內在動力,雙雪濤以幽默作為闡釋東北文化的手段,繼承與發揮了東北文化本身的特性,有利于增強東北文化的傳播力。
首先,調侃式幽默是東北喜劇文化的縱向傳承。當人物受到現實世界的擠壓時,也能在生存的一隅縫隙中解除危機感。這種自我保護機制,承載著東北喜劇文化中的初心,即逆境生長的樂觀積極和為人處世的聰明智慧。除了人物性格上,調侃式幽默在敘事節奏和氛圍上也起到舒緩調節作用。正如雙雪濤所言:“這個小說本身的大環境還是沉重的,所謂的反諷和幽默的表達我覺得對這個小說是有益的。”[1]雙雪濤有意讓幽默的俏皮活躍作品氣氛,使閱讀氛圍與人物幽默性格相輔相成。比起其他現實主義文學中的嚴肅特質,雙雪濤在輕松的敘事氛圍中實現對東北文化的新闡釋,促進東北文化的傳播和接受。
其次,好壞顛倒式冷幽默意為對時代的橫向契合。20世紀80年代,文學的整體性松動,個人意識再次覺醒。好壞顛倒式冷幽默敘事意味著作家對東北人的關注點轉向平凡的普通人,以小人物的視角見證東北的興衰,在東北文化的輸出中增添對人性的內面性思考。對時代氛圍的把控和寫作風向的貼近,契合了東北文化傳播市場的需求。
再次,斥拒式幽默是兩代東北人的內部經驗的交流,經驗的碰撞展示出東北文化的內部磨合。東北工業文化成為斥拒式幽默的敘事根基,父一代東北工業興盛與子一代東北工業衰落的創作背景對照,在雙雪濤的小說中大批量出現。工廠、工人等東北工業文化的要素緊密充斥在小說的各個角落,而東北工業文化展示的新角度,勢必牽引出東北城市文化的脈絡,為東北文化傳播加入新內容。
總的來說,雙雪濤利用調侃式幽默、好壞顛倒式冷幽默和斥拒式幽默,從東北幽默特質、審美和價值觀三方面,重現藏在時代下的東北人事隱脈,對新東北文化本身進行豐富補充。結合實績來看,雙雪濤作為文壇新秀,2011年憑借處女作《翅鬼》初登文壇,獲第一屆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首獎。他的小說《刺殺小說家》由路陽執導改編成電影,已于2021年2月上映;《平原上的摩西》更名為《平原上的火焰》,預計在2022年上映;《我的朋友安德烈》于2021年出現在華策影業片單發布會。在海外介譯方面,雙雪濤的代表性小說集《平原上的摩西》,繼2021年4月在意大利輸出并出版后,英譯版也被亨利·霍爾特出版社收購,預計于2022年出版。文學作品影視化和譯介反映出大眾傳媒和文化傳播市場對作家作品的認可和需求,新一代東北作家帶著他們特有的敘事風格,正不斷接受市場的檢驗。我們有理由期待,新東北文化將在他們手上繼續傳播發展,碰撞出新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