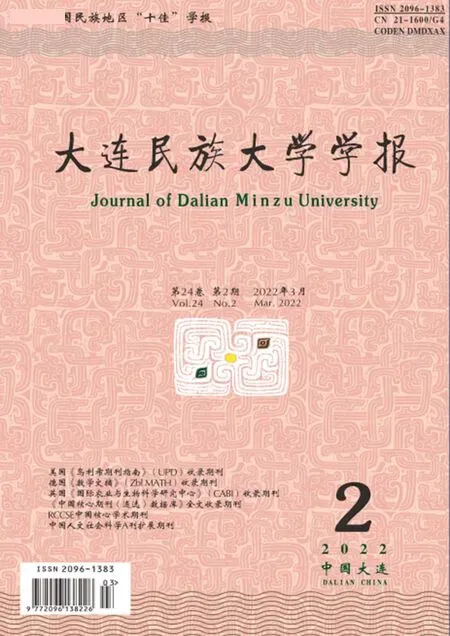派兼南北、學貫東西
——為黃淑娉教授90壽辰而作
周大鳴
(中山大學 移民與族群研究中心,廣東 廣州 510275)
2020年是黃淑娉教授90壽辰,筆者在2002年,黃先生從教50周年時舉辦過一個學術(shù)會議,轉(zhuǎn)眼已過去了18年[1]。筆者原本計劃舉辦一場學術(shù)會議,請學術(shù)界同行們聚一聚來共同慶賀。但是,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已經(jīng)延續(xù)了很久,現(xiàn)在看來疫情不知道什么時候結(jié)束,會議無法舉辦,加之何國強[2]與胡鴻保[3]也已選擇通過撰文的方式表達對黃先生的祝賀,鑒于防疫形勢如此,筆者也只能退而求其次,用短短文字來祝賀黃先生壽辰。
黃先生是1987年年底從中央民族大學調(diào)到中山大學的,那一年正是人類學系創(chuàng)系主任梁釗韜先生去世。我們理解梁釗韜先生當時調(diào)黃先生過來,應(yīng)該是希望她作為接班人擔起人類學系的擔子。彼時,人文學科正處于一個低潮期,不論是歷史、哲學或是人類學這樣的學科,都被當時的社會風氣認為是無用學科,鮮有人愿意修讀。當時整個中山大學里除了經(jīng)濟管理、計算機以外,其他的學科都不大熱。那時,大學發(fā)展也是低潮,大學教師的工資低、待遇差,流行“下海潮”,大量教師流失。即使是留在校內(nèi)的教師,也有不少忙著到外面“炒工”賺錢。因為經(jīng)費少、資源少,學科內(nèi)的競爭尤為激烈,內(nèi)部矛盾也凸顯出來。黃先生就是在那種情況下臨危受命的。
來到中山大學不久的黃先生,首先就得接受梁先生“托孤”的幾個學生,這種轉(zhuǎn)換師門一般導師是不愿意接受的,但黃先生毫無怨言。我記得當時的學生(其中有一位是胡鴻保)畢業(yè)之際似乎正是80年代末的那段特殊時期,請評委不方便,黃先生親自把學生帶到北京去答辯(當時帶著學生從廣州去北京只能坐火車,需要38小時,相當辛苦)。與此同時,人類學系也遭遇了一件危機事件——無人接任博士生導師。那個時候的博士生導師資格需要國務(wù)院學位委員會學科組批準,學校還沒有權(quán)限批準。黃先生頂著巨大壓力,不負眾望,順利獲得國務(wù)院學位委員會的批準,成為文化人類學專業(yè)的博士生導師。名正言順地成為中山大學人類學學科帶頭人,成為人類學“南派”的領(lǐng)頭羊!
筆者是1977年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本科生,畢業(yè)后留校任教,在職讀的碩士和博士,與黃先生相識早已超過30年。黃先生在中大一共招收了7位博士。我是黃先生招的第一屆博士,1994年考試,1995年春季入學,同學有何國強、覃德清(1995年秋季入學)。這兩位同學后來在學術(shù)上相當有造詣,何國強教授在藏學研究上獨樹一幟,可惜早早退休;覃德清教授是審美人類學的領(lǐng)軍人物,遺憾英年早逝。后來培養(yǎng)的幾位博士也成為學術(shù)界的頂梁柱,孫慶忠在中國農(nóng)大任教、黎熙元在中大任教,均為教授、博導。因此,黃先生一脈弟子、再傳弟子中有博士學位的應(yīng)該不下百人。
本文的題目沒有經(jīng)過黃先生同意,黃先生為人謙虛,若事先告訴她此事,她十有八九不會同意。但筆者自認為這一題目是對黃先生的評價恰如其分。首先,談“派兼南北”,人類學界早期有“南楊北吳”之說,人類學的“南派”和“北派”更因為張海洋的文章而廣泛流傳[4]。黃先生早年于燕京大學接受學術(shù)訓練,北派的代表人物大多是她的授業(yè)之師,如吳文藻、潘光旦、費孝通、林耀華等。1952年院校調(diào)整,上述幾位先生調(diào)到了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學院,楊成志——南派的代表人物也被調(diào)整到一起,黃先生畢業(yè)后也留在中央民族學院任教。可以說,黃先生受的學術(shù)訓練兼有南北兩派特征。其次,黃先生是地地道道的南方人,生在香港,祖籍臺山,17歲獨自北上到燕京大學求學,直到40年以后才回廣州工作,普通話講得好,一口廣州話也很地道,從語言上講,也是南北兼容。其三,其研究也是兼有南北,既跟楊成志先生到過中南、廣東、福建作調(diào)查,也與林耀華先生一起去過內(nèi)蒙、云南做調(diào)查;其研究成果既有理論研究,也有區(qū)域研究和個案研究。
再解“學貫中西”。黃先生受的學術(shù)訓練,中西結(jié)合,孫慶忠在《黃淑娉評傳》的第一章題目就是“中西合璧向?qū)W路”[5]。書中提到黃先生4歲開蒙,上香港英華女書院,更是中英文并舉,中文學的是《四書》,毛筆字臨摹書法大家,除中文課外,其余均為英文教學。抗戰(zhàn)爆發(fā)后,回臺山老家避難,入臺山一中上學。因時有日軍來犯,上學是斷斷續(xù)續(xù)的。筆者參觀臺山一中校史館時,黃先生被列入優(yōu)秀校友,特意在黃先生照片前留影。抗戰(zhàn)勝利后,黃先生入廣州培道女中,是教會中學。1947年以第一名成績考進燕京大學。燕京大學更是全英文教學的大學。所以黃先生有著很好的國學和西學的訓練。后來從事人類學、民族學的研究,很自然能夠把西方的人類學理論和方法融入中國的研究實踐中。黃先生早期的摩爾根與原始社會研究,后來的廣東族群研究,都可見其融匯中西學問的根底。
筆者1998年夏季博士畢業(yè),獲得了哈佛燕京的資助,去哈佛待了一年。1999年回來沒有半年,就接任人類學系系主任。在先生的支持下,人類學系進入了發(fā)展的全盛時期。2004年,中山大學體制改革,教師從長聘制改成聘任制,實行新的退休和醫(yī)療制度,為了享受舊的退休和醫(yī)療制度,一批老教授只好退休,先生也是那一年退的休。
一、學科建設(shè)
1.1952-1987年中央民族大學工作時期
關(guān)于黃先生的貢獻,可以從幾個方面談,一是學科建設(shè)。黃先生在中央民族大學工作36年,可以說一直是民族學、人類學園地里的“綠葉”。中央民族大學大師云集,黃先生長期做大師們的助手、副主任、副主編、副導師,毫無怨言。其行政職務(wù)也長期是副職,先是原始社會研究室副主任,后來又擔任民族研究室副主任。她參與了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的創(chuàng)建(1952年),組辦了民族學研究生班并擔任副班主任(1956年)。改革開放后,中央民族大學恢復招收民族學碩士和博士,黃先生也是協(xié)助林耀華先生指導學生。至今,莊孔韶、張海洋、王建民等都還尊黃先生為授業(yè)之師。
2.1988-2004年中山大學工作時期
1987年底回到廣州,來到中山大學人類學系工作,終于成為“紅花”,按照胡鴻保說的“萬綠叢中一點紅”。由于梁釗韜先生的辭世,黃先生逐步成為中山大學人類學學科的帶頭人。首先是不顧個人得失,接任人類學系主任;接著是突出重圍,獲得國務(wù)院學位辦批準成為文化人類學的博士生導師;第三是突破人類學只研究少數(shù)民族的怪圈,組織團隊對廣東漢族族群文化進行研究。在黃先生的領(lǐng)導下,人類學系重新走上正軌,為后來的發(fā)展打下了基礎(chǔ)。
二、學術(shù)貢獻
黃先生的學術(shù)貢獻,主要是這幾個方面,第一是民族識別;第二是原始社會史的研究;第三是文化人類學的理論方法研究;第四是族群研究;第五是世仆制度研究。
眾所周知,關(guān)于民族識別的研究是一個爭議特別大的話題,特別是在海外的一些學者,對于中國的民族識別一直持比較負面的評價。黃先生作為親身經(jīng)歷了民族識別工作的參與者,對于民族識別的相關(guān)問題有參與者自身的看法。黃先生1950年第一次到內(nèi)蒙古呼倫貝爾盟大草原調(diào)查,當時燕京、北大、清華幾所大學聯(lián)合舉行了一次大學實習,時間正值暑期。這是她首次田野調(diào)查和接觸異文化。大學畢業(yè)后,黃先生被留在了彼時的中央民族學院民族研究室工作,所以才有機會,跟隨老一輩民族學家、人類學家參與少數(shù)民族考察和調(diào)查。那時中央政府組織派遣民族學、人類學家對少數(shù)民族進行了多次調(diào)查,這些調(diào)查在后來被統(tǒng)一稱為少數(shù)民族社會歷史大調(diào)查。大概從1952年到1953年,黃先生隨同中南民族調(diào)查組,考察了中南的十幾個民族,包括苗族、畬族、侗族、瑤族、壯族等等。 1954年,她又跟隨林耀華先生參加了云南的彝族識別調(diào)查,這一次他們主要是調(diào)查彝族的分布的體系。這一調(diào)查對黃先生最大的收獲,便是將大小涼山,還有關(guān)于彝族主要分布的地域,整體考察了一遍。1955年黃先生又隨楊成志先生前往廣東的羅浮山、蓮花山,并且與施聯(lián)朱前往鳳凰山、福建省調(diào)查畬族。黃先生經(jīng)歷的這一系列的調(diào)查,使她感覺到關(guān)于民族識別的重要性,對于民族識別相關(guān)的批評,她進行了詳細的回應(yīng)。
首先黃先生認為民族識別從空間上、時間上、來源上,都有著它自身的多樣性,沒有唯一的標準可以判斷。民族識別的一個關(guān)鍵方面是民族語言。比如說苗族,原來主要是分布在湘西和黔南的地方,后來不斷遷徙,一直分布到全國7個省、240個縣,分布得極為分散,但是盡管呈現(xiàn)出如此分散的狀態(tài),卻依然保持了苗族的三大方言和相同的基本習俗。因此黃先生認為,苗族在一個分散的過程中,能夠長期保持自己的語言和文化習俗的大致穩(wěn)定,所以只用一個名稱是適當?shù)摹Ec此同時,有很多民族分得很散,但是可能在與當?shù)夭煌褡宓慕佑|中,這一民族沒有保持同一種語言,比如說畬族,鳳凰山的畬族,語言跟客家方言相近;增城、羅浮山區(qū)域的畬族,語言成分中有瑤族的因素,跟瑤族的語言比較相似。雖然畬族的分布在空間上很分散,語言上面也并沒有保持一致,但作為一個民族,保持住了對自身文化的認同(祖圖認同),因此命名為同一個民族也是適當?shù)摹|S先生這樣的回應(yīng),目的是告訴沒有經(jīng)歷過民族識別的學者們,當時進行民族識別的工作難度,識別的標準是多么難以把握。
民族識別的另一個關(guān)鍵問題是民族的認同,當時很多的地方將自己認同為一個民族,所以最初國務(wù)院收到了幾百個群體上報,自己認為自己是少數(shù)民族,民族識別的目的就是將它們好好地識別出來。這種識別既包括了從民族本身的一種認同,也包括了當時或多或少按照斯大林的關(guān)于民族概念的界定,從幾個方面去探討——是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經(jīng)濟生活、共同的語言,還有表現(xiàn)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zhì)。當然我們中國的學者在識別的時候并沒有完全按照這個定義,所以這也是說在民族識別的時候,還是有一定的靈活性。民族識別的工作,實際上為以后的民族工作打下了一個基礎(chǔ),開展了很多基本的歷史語言、文化習俗的調(diào)查,這些中國的材料過去并不掌握。所以后來黃先生在《中國社會科學》發(fā)文,重新談到對民族識別的認識,因為當時新中國剛剛解放,我們要清點自己的家底,知道自己有哪些民族的成分構(gòu)成,這當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6]。
黃先生學術(shù)貢獻的第二個方面是關(guān)于原始社會史的研究。由于50年代國家院系調(diào)整,把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作為一種資產(chǎn)階級的學科取消,唯一保留下來的只有原始社會史的研究,就是把原來做民族學做人類學的學者,轉(zhuǎn)到了一個研究室。那時的研究主要是論證,馬克思講的階級社會以前的那一段歷史時期,我們將它稱為原始社會史。過去在中山大學,梁釗韜先生就擔任過原始社會史研究室的主任。黃先生在中央民族學院時期,也是長期從事原始社會史的研究,在這方面她最重要的著作有幾本,一本是《原始社會史》,眾所周知摩爾根最著名的著作便是《古代社會》,接著恩格斯著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其主要的參考材料也是《古代社會》。馬克思專門在人類學筆記里面不吝對《古代社會》一書表達贊譽,所以黃先生她們的研究部,實際上承擔的是一個很重要的任務(wù)[7]。另外黃先生還參與編寫了一本《中國原始社會史話》,這是一本相對來說比較通俗的冊子,普及性的讀物(黃淑娉《中國歷代史話 5卷》(合訂本), 北京出版社 1992年版)。更有影響力的一本是她與林耀華先生合作主編的《原始社會史》(中華書局 1984年版)。這本書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是原始社會研究領(lǐng)域的必讀著作。《原始社會史》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把民族學、考古學的材料結(jié)合起來作原始社會時代研究。當時林耀華先生與黃先生為了撰寫該著作,特別參觀了中國的一些主要的早期原始社會史遺址與早期奴隸社會的遺址,花了幾個月時間做考古學的調(diào)研,同時也把中國一些少數(shù)民族的材料,特別對新中國建立前處于原始公社時期社會的少數(shù)民族的民族學材料進行了全面的考察,這方面的材料基本被兩位先生窮盡了。它是一本典型的民族學與考古學相結(jié)合,一本民族考古學的里程碑意義的著作。另外黃先生還發(fā)表了一系列的這一領(lǐng)域的論文,主要圍繞親屬制度研究[10]、《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1],以及關(guān)于血緣家庭和早期婚姻家庭存在的幾個問題[12]等等;同時還有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以原始公社作為主要制度的少數(shù)民族,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直過民族)的相關(guān)研究[13]。這些方面的研究,是黃先生改革開放之前的研究中最重要的一個部分,黃先生的貢獻是非常大的。
黃先生學術(shù)貢獻的第三個重要方面,是關(guān)于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的研究。因為黃先生與龔佩華先生合作的《人類學理論方法研究》(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 是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這本書當時獲得了國家人文社科二等獎,時至今日依然是研究生考試的必讀教材。可能很多人不了解黃先生其他的著作,但這本著作是絕大部分人類學民族學學者都了解的。因為考研究生的時候都要用到這本書。那個年代對國外的人類學教材、著作和理論翻譯得不少,但是我們自己編的著作相對來說比較少,黃先生用自己的一套學術(shù)體系,結(jié)合國外的一些教材,重新進行整理與實踐。所以這本著作有她獨特的思想,以及她自己的概括和歸納。黃先生將自己與其他中國學者們的很多研究成果融入到了其中。所以這本書不是一本描述性的教材,也不是一本照抄國外的教材,而是將中國社會與她自己的研究經(jīng)歷結(jié)合起來的一本書。這本書能夠延續(xù)那么長時間一再再版,說明它還是能夠經(jīng)得起歷史的考驗。這是關(guān)于理論的研究。書里的另一大亮點是關(guān)于各種流派的研究,過去最大的問題是國內(nèi)的學者對于原著的閱讀不夠充分。黃先生和龔佩華先生在編輯這本書之前,讀了大量的原著,后來兩人根據(jù)對原著的理解,重新進行概括和歸納,這是非常不容易的。這其實是學貫東西或者學兼東西的表現(xiàn),她能夠把西方的理論和方法,與她在中國的幾十年的民族學人類學研究、實踐相結(jié)合起來。這是一個關(guān)于研究方法的貢獻。
黃先生貢獻的第四個方面,是關(guān)于族群研究的,因為族群研究在當時是一個比較新的概念,實際上主要是在20世紀90年代的時候開始介紹進入中國,時至今日已經(jīng)成為了人類學民族學領(lǐng)域的流行概念。民族與族群這兩個概念,筆者認為最大的區(qū)別是,一個人群若要成為一個民族,有一個法律認定的程序作為前提——經(jīng)過民族識別,需要經(jīng)過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才能被承認是一個民族。族群相對來說,更多的是強調(diào)它的自我認同、強調(diào)與他群的差異性。所以族群實際上是一個學術(shù)概念,因此用族群來研究中國社會,筆者覺得可能相對來說比較方便,不涉及到一些學術(shù)之外的問題。所以黃先生就利用這個理論來研究漢人社會的不同的民系。研究民系,廣東當然是一個很好的典型,所以黃先生才致力于研究廣東的族群,這里面實際上就包括研究廣東的客家、廣府、潮汕等漢族民系以及其他的少數(shù)民族,而且這一個課題最重要的一點是彰顯了她的領(lǐng)導的能力[15]。該課題獲得了嶺南基金的資助,同時發(fā)動了不同學科的30余人參加。黃先生組織30余人調(diào)查研究,最后綜合在一起,花費了非常大的工夫。這一項目意味著黃先生的研究,從個人的研究發(fā)展到團隊的研究,從而為人類學民族學探索大平臺、大項目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寶貴的經(jīng)驗。所以通過這樣一個研究,不僅僅是獲得了研究成果本身,同時鍛煉了隊伍,加強了學科的建設(shè),為學科的發(fā)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礎(chǔ)。作為這一基礎(chǔ)的直接受益者,筆者接手中山大學人類學系主任以后,人類學能有很好的起步條件,與黃先生打下的基礎(chǔ)有很大的關(guān)系。在族群研究的方面,黃先生出版了兩本重要的書籍,一本是《廣東族群與區(qū)域文化研究》(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 ,一本是《廣東族群與區(qū)域文化研究調(diào)查報告集》(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 )。上述兩項成果都獲得了教育部人文學科二等獎。這基本上是彼時本學科能夠獲得的最高榮譽。如此足見黃先生在族群研究方面的突出貢獻。
黃先生學術(shù)貢獻的第五方面,筆者認為也是黃先生一生研究的總結(jié)。《廣東世仆制研究》(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在該書的序言里,黃先生回憶早年她和家人在臺山生活的時候,親身觀察到的家庭里面的“世仆”,或者叫做“家仆”,或者叫做“細仔”。根據(jù)黃先生日后的回憶,從那個時代她就很好奇,這樣一種制度,為什么還能夠在廣東這樣地方產(chǎn)生?為什么能夠保留?為什么能夠保存?針對這幾個問題,黃先生通過一生的人類學民族學研究經(jīng)驗,創(chuàng)作了這本書,筆者認為這是黃先生迄今為止最重要的一本著作。比較可惜的是,當時的評審者們沒有意識到這本書的重要性,當時只獲得了教育部人文社科的三等獎,筆者認為非常遺憾。這本書一方面告訴我們,一種制度,它延續(xù)的時間是非常漫長的,按照黃先生的結(jié)論,它是一種奴隸制的殘余。眾所周知,奴隸制至少從5000年以前就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一直延續(xù)到民國時期,也就是1949年以前,延續(xù)的時間如此之久,其中一定有它自身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奴隸制有著廣泛的空間分布,過去認為可能只有在一些少量的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保留這種奴隸制的殘余,比如說彝族,比如說還有一些其他的“直過民族”,實際上研究者們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注意到,在很發(fā)達的珠江三角洲,還保留著這樣的一種奴隸制殘余,而且還非常廣泛地存在。而且黃先生也回應(yīng)了陳翰笙早年對廣東調(diào)查的時候提出對世仆制度的一種解釋。因為當時陳翰笙他們也發(fā)現(xiàn)在廣東大量存在這種佃戶制,細仔制或者是世仆制度,但是他們當時沒有作出一個合理的解釋(參見陳翰笙《 廣東農(nóng)村生產(chǎn)關(guān)系與生產(chǎn)力》, 中山文化教育館, 1934年版)。所以黃先生通過她的研究,很好地回應(yīng)了這些問題,解釋了這樣一種制度,它的存在和延續(xù)的原因,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另一方面,筆者認為這本書是一個很好地將歷史文獻、實際的調(diào)查相結(jié)合的研究,也可以說是一個很好的歷史人類學的研究。為什么這么說?因為傳統(tǒng)修史,關(guān)于細仔制都是不入正史的,文獻里面的記載極少。所以黃先生通過到各個地方搜集各種各樣的檔案資料,把各種各樣的日記材料充分理解,然后對那些還健在的曾做過世仆的老人,進行調(diào)查、訪問,通過對他們這種經(jīng)歷的了解,來做深入的研究。所以這并不是一項僅僅只限于文獻的研究,而是通過實際調(diào)查,回到了臺山,黃先生自己的家鄉(xiāng),對自己家鄉(xiāng)的家族進行研究,了解世仆制度與宗族社會雙方在當時的社會生態(tài)環(huán)境相契合的一個過程。
要理解世仆制度,必須理解這種宗族社會,并且理解宗族社會以及相關(guān)的土地制度,才能理解世仆制。這是世仆制研究的第三個重要貢獻。因為大家知道廣東的宗族制度跟土地耕作制度是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過去陳翰笙在作調(diào)查的時候也發(fā)現(xiàn)了這個問題,所謂“太公田”,實際上是一種宗族土地所有制,宗族所擁有的土地在總土地面積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大。在番禺和新會等好幾個地方,都占到了50%以上,不是所謂地主所有或者富農(nóng)所有,而是一種宗族所有。而這種土地所有狀況,為少部分大家族的長期的佃戶制度或者世仆制度奠定了一個基礎(chǔ)。這一問題的發(fā)現(xiàn),為中國的制度研究作了一個貢獻,也可以說解釋了過去的土地所有制度的一種特殊性。所以筆者認為《廣東世仆制研究》這本書,實際上也充分顯示了黃先生的學術(shù)功底。因為這個研究非常不容易,材料十分難以獲得,那些參與調(diào)查的人員能夠全程堅持下來人也不多,要作這樣的訪談?wù){(diào)查很不容易。同時像這樣的調(diào)查,很多人也覺得不重要,因為這個過去可能被認為是下九流,或者是底層社會的人,而且是一種文化殘余,在這樣的情況下問題很容易被忽視掉。黃先生能夠從一個很小的地方入手,來解釋一個大的社會,來挖掘一個地方的一種特殊的制度。筆者覺得這是一個了不起的研究者才可以做好的。
三、結(jié) 語
黃淑娉先生是社會主義建設(shè)時期民族理論與民族工作實踐的開拓者,改革開放后人類學民族學大發(fā)展的傳火人,也是筆者最尊敬的導師。筆者受教于黃先生迄今二十余年,桃李之恩,難以言表。盡管僅以拙筆難以盡述黃先生之思想,唯獨欣喜的是依然時常可在康樂園內(nèi)見到黃先生硬朗的身影。本文謹以弟子之名向黃先生90壽辰致賀,絕學有繼,師道長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