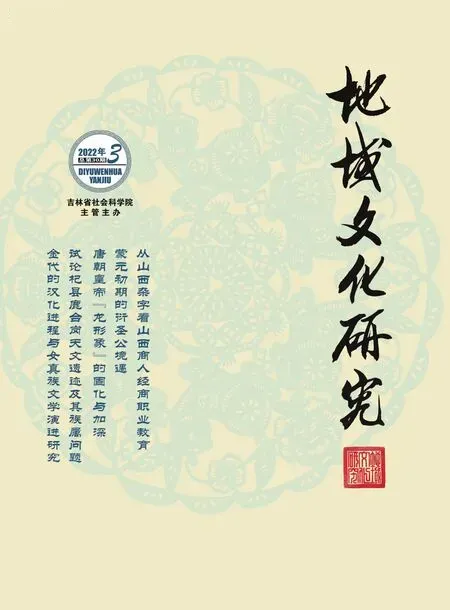金代的漢化進程與女真族文學演進研究
晏選軍 韓 旭
金代的漢化進程,與整個金王朝的歷史相始終。而金代女真族文學的發(fā)展,恰與這一進程隱然合拍。史學界對金代的漢化進程、文學研究界對金代女真族文學的狀況,均有不同程度的探討,為后來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參考。日本學者三上次男(Mikami Tsugio)的代表作《金代女真の研究》(Kindai Joshin no kenkyū)(Tōkyō,1937),盡管年代較早,但其提出的“女真文化復(fù)興運動”的觀點影響深遠。①Mikami Tsugio三上次男著,金啟孮譯:《金代女真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4-219頁。20世紀后期,陶晉生②Tao Jinsheng,The Jurchen in Twelfth-Century China: A Study of Sinicization(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6),68-83.和陳學霖(Chan Hok-lam)③Chen,Hok-lam,Legitimation in Imperial China: Discussions Under the Jurchen-Chin Dynasty 1115-1234(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5).的兩部專著幾乎同時完成,隨后赫伯特·弗蘭克(Herbert Franke)的重要著作也隨之問世。④Herbert Franke,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907-1368(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240-50.對女真族漢化研究的重要突破來自于金啟孮和劉浦江,兩位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女真文化復(fù)興運動”進行了討論。金啟孮系統(tǒng)地討論了金代女真文學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規(guī)律和特點,研究金代政策從漢化—女真化—再漢化的演變。⑤Jin,Qicong,"Jurchen Literature under the Chin." Chap.8 in China under Jurchen Rule: Essays on Chi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ed.Stephen H.West and Hoyt Cleveland Tillman(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5),216-37.劉浦江認為,金朝是一個典型的漢化的北方民族王朝,女真人接近漢族人的生活方式、猛安謀克的大批南遷、政治體制的一元化和海陵王確定漢文化本位的政策是導(dǎo)致女真人漢化的主要因素。①劉浦江:《女真的漢化道路與大金帝國的覆亡》,《松漠之間——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235-273頁。張晶和周惠泉發(fā)表了涉及這一主題的文章,他們將目光投向了女真文學。張晶通過對女真族詩人的詩歌作品進行分析,描述了女真族在文化心理上經(jīng)歷的深刻變遷過程。②張晶:《試論金代女真民族文化心理的變遷——兼議女真人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央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4期。周惠泉分析了金代的漢化進程與女真族文學的發(fā)展之間的互動關(guān)系,探究古代不同民族的文化沖突與文化融合的發(fā)展歷程。③周惠泉:《金代文學與女真族文學歷史發(fā)展新探》,《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王萬志等將視角回溯到金朝初期,展現(xiàn)了女真社會經(jīng)濟、政治、文化層面的嬗變與他族文化之間深刻的互動關(guān)系。④王萬志、程尼娜:《金初女真社會文化變遷研究》,《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4期。除了這些學者之外,還有一些研究議題同樣值得注意。朱莉婭·施耐德(Julia Schneider)評價了女真族各個皇帝統(tǒng)治時期的政策,研究表明,太宗、熙宗和海陵王的漢化運動的假設(shè)和世宗的“本土化運動”都不夠準確,他們利用漢族政治來確保自己的權(quán)力地位,調(diào)整了漢族制度的部分內(nèi)容以適應(yīng)他們的需要,而不能簡單歸納為贊成或反對同化漢族文化。⑤Schneider,Julia,"The Jin Revisited: New Assessment of Jurchen Emperors,"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41 (2011):344.該論文的價值不僅在于出色的介紹和廣泛的文獻回顧,還在于其獨到的研究框架,它是西方學者對女真族研究的代表性成果,這種研究范式會進一步推進西方學者的金代女真研究。
自金熙宗、海陵王采取了漢化措施后,金代女真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擋的漢化潮流。盡管世宗和章宗為了遏止這種趨勢,開展了所謂的女真文化復(fù)興運動,但都不可避免地被漢民族同化,他們的努力以失敗告終,后世甚至有“金以儒亡”的說法。⑥劉浦江:《女真的漢化道路與大金帝國的覆亡》,《松漠之間——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264-271頁。基于前人的充分研究,本文試圖從文學創(chuàng)作的角度來論述金代帝王在面對漢文化時復(fù)雜、糾結(jié)的心態(tài)。帝王們既想保留本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卻又受制于歷史發(fā)展的潮流而感到無能為力。從他們的詩文創(chuàng)作中可以明顯地感受到這種糾結(jié)的心態(tài)。本文擬就金代的漢化進程與女真族文學的發(fā)展歷程之間的互動關(guān)系,作一文史互證式的論述,以觀照金代文學走過的獨特歷程,思考古代不同民族間文化沖突融合的發(fā)展軌跡。
一、金代女真的漢化進程
以往學界評價海陵王是女真族漢化的主要推動者。其實,金朝統(tǒng)治者對漢文化的重視由來已久。⑦王萬志、程尼娜:《金初女真社會文化變遷研究》,《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4期。還在滅遼(907—1125)之前,金太祖阿骨打就下詔:“若克中京,所得禮樂儀仗圖書文籍,并先次津發(fā)赴闕。”⑧脫脫等:《金史》卷2《太祖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6頁。在對宋戰(zhàn)爭中,金兵每至一處,即大力搜求漢文書籍、文物、印版等。如天會四年(宋靖康元年,1126),“金人索監(jiān)書,藏經(jīng),蘇、黃文書,《資治通鑒》諸書,”“指名取索書籍甚多。”⑨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73,影印文淵閣四庫本。次年正月滅北宋后,金軍甚至還組織宋朝京師軍隊的降兵,“每日搬金帛禮樂器用、儀仗法物、秘閣書籍、國子監(jiān)經(jīng)史、道釋藏印版,未嘗休息,自旦至暮。”①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97引夏少曾《朝野僉言》。僅據(jù)《靖康要錄》、《三朝北盟會編》兩書記載,金兵克汴京前后兩三月間,就數(shù)次大規(guī)模取走宋國子監(jiān)、三館秘閣、太清樓等處所藏官書秘籍以及一部分私家藏書。另外,包括教坊樂工、影戲、小唱、傀儡戲、畫師等在內(nèi)的各色藝人,也都在金人的搜羅遣送之列。②見闕名:《靖康要錄》卷10、卷11,影印文淵閣四庫本;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77。
從宋朝的立場分析,這無疑是一場文化浩劫,難怪清代的四庫館臣會認為宋鼎南遷,“中原文獻,實并入于金”。③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190《全金詩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725頁。但是,從金朝的角度看,女真統(tǒng)治者極力搜求圖書文獻,這一行動本身就足以說明他們對中原典章文物的重視到了何等程度。各色藝人以及大量典籍文物的大規(guī)模北遷,為歷史上所罕見,客觀上也為金代文學的發(fā)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zhì)基礎(chǔ)。《金史》反復(fù)提及這些南遷典章文物對金朝制度建設(shè)和文化發(fā)展的重要性:“金人之入汴也,時宋承平日久,典章禮樂粲然備矣。金人既悉收其圖譜,載其車輅、法物、儀仗而北,時方事軍旅,未遑講也。既而,即會寧建宗社,庶事草創(chuàng)。皇統(tǒng)間(1141—1149),熙宗巡幸析津,始乘金輅,導(dǎo)儀衛(wèi),陳鼓吹,其觀聽赫然一新,而宗社朝會之禮亦次第舉行矣。”④脫脫等:《金史》卷28《禮志》,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691頁。“初,太宗取汴,得宋之儀章鐘磬樂篪,挈之以歸。皇統(tǒng)元年(1141),熙宗加尊號,始就用宋樂。”⑤脫脫等:《金史》卷39《樂志》,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882頁。“金初未有文字……太宗繼統(tǒng),乃行選舉之法,及伐宋,取汴經(jīng)籍圖,宋士多歸之。”⑥脫脫等:《金史》卷125《文藝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713頁。
海陵王(完顏亮,1149—1161年在位)是金朝歷史中推進女真族漢化進程的關(guān)鍵人物。海陵王遷都燕京(旋即改名中都)后,開始全面采用中原地區(qū)傳統(tǒng)漢制。為了加強對女真貴族及中原地區(qū)的控制,將一大批女真猛安、謀克戶遷往長城以南的中原河朔地區(qū),“不問疏近,并徙之南”。⑦脫脫等:《金史》卷8《世宗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85頁。并于正隆二年(1157)十月,“命會寧府毀舊宮殿、諸大族宅第及儲慶寺,仍夷其址而耕種之。”⑧脫脫等:《金史》卷5《海陵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08頁。會寧府(治今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阿城區(qū)南白城)即金舊都上京(貞元元年改稱北京),海陵王采取這樣的措施,目的就是要斷絕女真貴族恢復(fù)上京政治中心地位的念頭,事實上也基本達到了這個目的。如此一來,自然給女真族的漢化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契機。此舉具有的深遠歷史意義,大概只有北魏孝文帝拓跋宏(467—499)遷都洛陽可以與之相比埒。
其次,為了吸引更多士人參與到政權(quán)中,海陵王還改革了科舉制度。金代科舉主要承襲遼、宋兩朝之制,始于太宗天會元年(1123),設(shè)詞賦、經(jīng)義兩科。初期制度草創(chuàng),考試既不定期,亦無定式,是女真統(tǒng)治者在入主中原之初,為適應(yīng)中原漢地傳統(tǒng)政治體制而做出的相應(yīng)政策調(diào)整。⑨Tao,Jingshen."The Influence of Jurchen Rule on Chinese Political Institutions."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0,no.1 (1970): 121-30.科考中民族歧視現(xiàn)象突出,最明顯的表現(xiàn)就是“南北選”制度。“南北”都是相對于金朝統(tǒng)治區(qū)內(nèi)的漢人而言的,原遼朝所轄的漢人屬于“北人”,原北宋境內(nèi)的漢人則被稱為“南人”。“北人”與“南人”不僅所試科目有難易之別,單就錄取的名額看,也表現(xiàn)出明顯的傾向性。據(jù)《金史》卷五一《選舉志》所載,熙宗天眷二年(1139)的“南北選”取士,北選進士兩百人,南選進士一百五十人;皇統(tǒng)二年(1142),北選一百人,南選一百五十人。僅就錄取人數(shù)看,二者約略相當,但如果考慮到“南人”的應(yīng)試人數(shù)遠遠大于“北人”的因素,則其中揚此抑彼的意圖十分顯豁。并且,即使在“南北選”中中試,獲得仕進的機會,官職的遷轉(zhuǎn)也還有遲速之別。如貞元元年(1153)規(guī)定,北選進士釋褐授官后,歷兩任六十月,除下令;而南榜進士仕至同一官職則需三任九十月。①脫脫等:《金史》卷52《選舉志》,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160頁。此舉無疑激起了原北宋境內(nèi)知識分子的普遍不滿,加上女真貴族往往對應(yīng)試者采取脅迫甚至拘遣等強制手段,更加促使士人們心懷怨望,“由是士子之心失矣”②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7《太宗文烈皇帝》,《二十五別史》本,李西寧點校本,濟南:齊魯書社,2000年,第67頁。參考張博泉等:《金史論稿》第2卷第六編第三章《金代的科舉制度》,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第384-430頁。,這未免與女真統(tǒng)治者最初設(shè)科取士以籠絡(luò)人心的用意背道而馳了。直到貞元二年(1154),海陵王遷都燕京后,才取消“南北選”制度,統(tǒng)一在燕京舉行科考。海陵王對科舉較為重視,并本著“尊經(jīng)術(shù),崇儒雅之意”,增設(shè)殿試。③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35《天德科舉》,《二十五別史》本,李西寧點校本,濟南:齊魯書社,2000年,第271頁。正隆二年(1157),金朝科舉制度步入正軌,定期每三年一試,并在海陵王時期正式定下貢舉程式,科舉以律令的形式被固定下來。此后的世宗、章宗兩朝,金朝科舉達到了它的全盛期。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增設(shè)女真進士科,章宗明昌元年(1190),又恢復(fù)經(jīng)義進士,并創(chuàng)設(shè)制舉、宏詞科,科舉制度不斷得到新的發(fā)展,逐步完善起來,開科取士一直持續(xù)到金朝末期,金朝科舉制度的完善與金朝的漢化進程密切相關(guān)。
最后,海陵王本人也對中原文化十分喜愛與傾慕。史載海陵王“嗜習經(jīng)史,一閱終身不復(fù)忘。見江南衣冠文物、朝儀位著而慕之”④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13《海陵煬王》,《二十五別史》本,李西寧點校本,濟南:齊魯書社,2000年,第105-106頁。,即位前“頗知書,好為詩詞,語出輒倔強,慭憗有不為人下之意,境內(nèi)多傳之。……其居位時,好文辭,猶不輟”。⑤岳珂:《桯史》卷8“逆亮辭怪”條,吳企明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93-95頁。這些評價洵非虛語。從他的一首七律詩可見:
自古車書一混同,南人何事費車工。
提兵百萬臨江上,立馬吳山第一峰。⑥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14《海陵煬王》,《二十五別史》本,李西寧點校本,濟南:齊魯書社,2000年,第114頁。岳珂《桯史》卷八作:“萬里車書盍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劉祁《歸潛志》(崔文印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一亦引該詩尾聯(lián),則作:“屯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
字里行間流露出混一天下的勃勃雄心,掩抑不住,直欲破紙背而出。通過他存世不多的作品,一方面足以窺見其時兄弟民族在文學造詣上所達到的高度,同時也可以具體感受到游牧文化與中原農(nóng)耕文化相互融合,給中國文學帶來的某些新因子。
二、不可阻擋的漢化潮流:女真化運動的失敗
金世宗即位時,金朝政治形勢嚴峻,采石磯一役(1161)海陵王被弒與金軍的全線潰敗,充分暴露了素以勇悍著稱的女真軍事力量已到了衰弱疲懦不堪的地步。而頻頻發(fā)生的叛亂事件,更表明了統(tǒng)治區(qū)內(nèi)民眾的普遍不滿情緒。①可參看脫脫等《金史》卷6至卷8《世宗本紀》、趙翼《廿二史箚記》(嘉慶五年湛貽堂刊本)卷28“大定中亂民獨多”條。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女真族移居中原之后,狃習晏安,日趨奢侈腐化,部分喪失了尚武精神。遷居中原地區(qū)的大批女真軍事貴族,或由政府供養(yǎng),或靠租佃維持生計,自己并不從事耕作,許多人因驕奢懶惰,不事生產(chǎn)而陷入貧困不堪的境地。世宗時期已露出了這種苗頭,如世宗曾訓(xùn)斥留守上京的宗室當厲行節(jié)儉,說:“太平歲久,國無征徭,汝等皆奢縱,往往貧乏,朕甚憫之。”②脫脫等:《金史》卷8《世宗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89頁。章宗去世后,“宗室貴戚,素無威柄。重以宴安逸樂,升平日久,平居無事,口脂面藥,軟媚如婦人女子。一旦內(nèi)亂遽起,惶駭憂懼,莫知所為。”③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16《舒穆嚕氏神道碑》,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皇親國戚尚且如此,其他女真族人可以想見。
到了金后期:棄武習文醉心文墨者有之;游手好閑,甚至干脆無所事事者有之。久而久之,幾乎到了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地步,戰(zhàn)斗力喪失殆盡。至于采用漢姓、改著漢服、與中原漢人通婚等等,更是非常普遍的現(xiàn)象。④參看陳述:《契丹女真漢姓考》,載《東北集刊》第2期,1941年,第1-8頁;陶晉生:《女真史論》第六章相關(guān)部分,第106-108頁。而女真貴族生活上的腐化墮落又與享受特權(quán)、侵奪壓制百姓如影隨形,加速造成了當時社會危機的出現(xiàn)。不容否認,這一點同女真族南遷華北以后受中原文化的影響,沾染奢靡之習,以致逐漸改變了本民族原有的生活方式息息相關(guān)。女真族在長期的漢化進程中放棄了很大一部分的本土生活方式。⑤Jingshen,Tao."The Influence of Jurchen Rule on Chines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0,no.1 (1970): 121.世宗大定十八年(1178),張酢等上書切諫:“軍政不修幾三十年。闕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疲老之余,不堪戰(zhàn)陣。大定初已萬萬不如天會(太宗、熙宗年號,1123—1140)時,今沉溺宴安,消磨殆盡矣。”⑥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17《世宗圣明皇帝》,《二十五別史》本,李西寧點校本,濟南:齊魯書社,2000年,第133頁。軍備廢弛,一至于斯。鑒于此,世宗、章宗在擇善而從、大力推進漢化進程的同時,還通過多方努力,采取種種措施,極力保存和捍衛(wèi)本民族傳統(tǒng)文化習俗,使之不至失墜。但是,三上次男認為女真族退化的最重要原因?qū)嶋H上是他們將猛安謀克遷移到南方。⑦Mikami Tsugio三上次男著,金啟孮譯:《金代女真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4-219頁。因此,世宗的措施不可能成功,因為從一開始他們的目標方向就是錯誤的。⑧Schneider,Julia,"The Jin Revisited: New Assessment of Jurchen Emperors,"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41 (2011):350.
世宗的統(tǒng)治被認為是女真族統(tǒng)治的一個新階段,因為他被歷史評價為“女真族遺產(chǎn)的保護者”。⑨Schneider,Julia,"The Jin Revisited: New Assessment of Jurchen Emperors,"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41 (2011):383.世宗對女真“舊風”“舊俗”念念不忘,多次表示了復(fù)興本民族文化傳統(tǒng)的決心。他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復(fù)女真文化,如狩獵、球賽、射擊、服飾、語言和傳統(tǒng)生活方式。試圖通過發(fā)起女真“復(fù)興”或“本土運動”來抵制漢化。⑩Schneider,Julia,"The Jin Revisited: New Assessment of Jurchen Emperors,"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41 (2011):343.其中一項重要措施,就是開設(shè)女真進士科。
世宗即位之初,近侍有以罷科舉為言者,世宗問朝臣:“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臣屬以秦始皇為對,世宗于是顧左右侍臣說:“豈可使我為始皇乎?”于是罷其議不用。①脫脫等:《金史》卷83《張浩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864頁。看來他要吸取海陵王喪身辱國的教訓(xùn),一度想更張舊制,取消考試制度。不久,他就認識到這種想法并不明智。科舉取士在金朝實施有年,吸引籠絡(luò)了不少知識分子投身科場,獵取科第功名,既充實了官僚隊伍,又提升了參政官員的素質(zhì),對維持金朝統(tǒng)治起到的作用不容低估。至于他本人不欲為秦始皇所為,固然可備一說,根本原因恐怕還在此等考慮。但世宗確實又具有濃厚的民族本位思想,極力復(fù)興女真族固有的文化傳統(tǒng),金朝科舉考試全在傳統(tǒng)的儒家思想范圍之內(nèi),未免與他的初衷不合。這種矛盾心理促使他折中眾議,于大定十三年(1173)正式設(shè)立女真進士科,以發(fā)揚女真文化。
與普通進士相比,女真進士科專門為女真人與“諸色人”(包括契丹、奚人、渤海人)而設(shè),“漢人”與“南人”不得與試。所試分為策論、詩兩科,只舉行會試和殿試,免鄉(xiāng)、府試,以女真文字為程文,并且規(guī)定要加試弓箭、擊毬、騎射等,以期保持本民族的尚武精神。與普通進士相比,女真進士較易錄取,錄取后官職的遷轉(zhuǎn)也較快。創(chuàng)立女真進士科后,一批女真進士進入各級官僚機構(gòu),在金代中后期政壇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打破了女真貴族仕進全出軍功、世襲、門蔭三途的局面,一定程度上均衡了女真貴族與平民之間的勢力,客觀上有助于金政局的穩(wěn)定。
但歷史證明,女真進士科的設(shè)立是徒勞的。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即從文化的角度評價女真進士科的設(shè)立,似乎只能得出一個與金世宗的主觀愿望截然相反的結(jié)論。
其一,科舉取士制度并非女真族固有的東西,而是唐宋以來中原漢地政治經(jīng)驗累積產(chǎn)生的一種選舉制度。女真進士科的程序基本上遵循了宋朝的既定模式,提交的文本、提出的問題以及試卷使用的詞匯都來自中原漢地的經(jīng)典和歷史。②Wen,Xin."The Road to Literary Culture: Revisiting the Jurchen Language Examination System." T'oung Pao 101,no.1/3 (2015): 166.世宗移植這一制度,本身便是善于向中原傳統(tǒng)文化學習的表現(xiàn),是漢化加深的結(jié)果。
其二,女真進士科在初創(chuàng)階段,用意是經(jīng)由推廣女真文字來加強女真文化的建設(shè)。③參考陶晉生:《女真史論》第五章《世宗時代的改革運動》第二節(jié),臺北:食貨出版社,1981年,第84-88頁。世宗曾對宰相表示了女真文字創(chuàng)立未久、義理不如漢字深奧,用之于科舉恐招致后世議論的憂慮。宰相回答說:“漢文字恐初亦未必能如此,由歷代圣賢漸加修舉也。圣主天資明哲,令譯經(jīng)教天下,行之久亦可同漢人文章矣。”世宗于是命令援引“漢人進士例,譯作程文,俾漢官覽之。”④脫脫等:《金史》卷51《選舉志》,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141-1142頁。大有將女真文化發(fā)揚光大使之自成體系,以與中原傳統(tǒng)文化抗衡的意思。然而,科場雖然采用女真大字試策、女真小字試詩,但考試的內(nèi)容還是不出傳統(tǒng)儒家思想的范疇。世宗多次詔令頒行用女真文字翻譯的儒家經(jīng)典,其目的很明確:“正欲女直人知仁義道德所在耳”。⑤脫脫等:《金史》卷8《世宗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84-185頁。雖然用女真文字翻譯了一遍,但譯作傳達的仍然是儒家的倫理綱常理念。所以太子在聽到女真臣僚辯論伯夷叔齊是否行仁義之道時,才會大發(fā)感慨:“不以女直文字譯經(jīng)史,何以知此。主上立女直科舉,教以經(jīng)史,乃能得其淵奧如此哉。”⑥脫脫等:《金史》卷98《完顏匡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164頁。可見,在女真人中興科舉,除了就試時使用女真文字外,內(nèi)容上實與唐宋以來的科舉制度并無太多發(fā)明,儒家思想的主導(dǎo)地位基本沒有被動搖。
其三,從設(shè)科取士的長期效果來看,隨著科舉與教育的盛行,越是到金朝后期,儒家學說在女真族中越發(fā)深入人心。眾多女真貴族紛紛奔競于場屋之間,以登第入仕為榮,轉(zhuǎn)而視軍功、世襲等為異途。如女真進士出身的完顏伯嘉,就很看不起金末權(quán)臣朮虎高琪,徑稱“高琪武弁出身,固不足論。”①脫脫等:《金史》卷100《完顏伯嘉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211頁。一批女真軍功貴族也競相吟詩作賦,與文士往來密切,以文雅相尚,盡失女真勇武故態(tài)。女真尚武精神日趨衰微,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棄武習文一旦蔚然成風,無疑大大削減了世襲猛安謀克們的戰(zhàn)斗力。章宗時,太尉徒單克寧就堅決反對以猛安謀克習文辭、試進士:“承平日久,今之猛安謀克其材武已不及前輩,萬一有警,使誰御之?習辭藝,忘武備,于國弗便。”②脫脫等:《金史》卷92《徒單克寧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052頁。為了遏制女真族的蛻變勢頭,世宗、章宗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的補救措施,奈何漢化早已成大勢所趨,僅憑統(tǒng)治者個人的力量,形同堤潰而障之以手,根本無法遏制這一進程,何況他們自己也在自覺不自覺中沾染甚深。陶晉生甚至指出:“本土主義運動無法阻止當時的潮流,女真人成了中國傳統(tǒng)的‘臣服者’(prisoners),除了在其面前低頭,別無選擇。”③Tao,Jinsheng,"The Jurchen in Twelfth-Century China: A Study of Siniciza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hington Press,1977.83.至泰和七年(1207)十二月,章宗干脆“詔策論進士免試弓箭、擊毬”④脫脫等:《金史》卷12《章宗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82頁。。世宗當初設(shè)立女真進士科以維系本民族風俗的初衷,至是基本宣告失敗。事與愿違的還不止于此——女真人由于在思想文化上逐漸喪失了自己的民族特色,最終連政治上的優(yōu)勢地位也無法確保。
三、由盛至衰:民族融合下女真文學的發(fā)展
金世宗雖在這方面傾注了諸多努力,雖然其失敗命運最終不可避免。但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由于這批新造就的女真進士迅速崛起,為金朝文學輸入了新鮮血液。在進士科與女真進士科的帶動下,民族融合的趨勢進一步加強,多民族聯(lián)合政權(quán)下的文化水平得到較為顯著的提升。金朝后期文壇的全面繁榮,如果沒有這些欣羨景慕中原文化的兄弟民族人士的積極參與,將會因此失色不少。
劉祁總結(jié)金后期歷史時說:“南渡后,諸女真世襲猛安、謀克往往好文學,喜與士大夫游。如完顏斜烈兄弟、移剌廷玉溫甫總領(lǐng)、夾谷德固、朮虎士(疑‘士’為‘邃’誤。據(jù)同書卷三,朮虎邃字士玄)、烏林答肅孺輩,作詩多有可稱。德固勇悍,在軍中有聲,嘗送舍弟(按指劉郁)以詩,亦可喜。”⑤劉祁:《歸潛志》卷6,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63-64頁。金末重要文士多與崇尚儒雅的女真軍功貴族有著密切的交往,如元好問與完顏彝(陳和尚)、完顏鼎,劉祁、辛愿等與朮虎邃,王渥與完顏斜烈、完顏彝兄弟,王郁與朮虎邃、烏林答爽等,關(guān)系都在師友之間,彼此情誼深厚。世襲猛安移剌粘合(即移剌廷玉)“兄弟俱好文,幕府延致名士。初帥彭城,雷希顏(淵)在幕,楊叔能(宏道)、元裕之(好問)皆游其門,一時士望甚重。”⑥劉祁:《歸潛志》卷6,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63頁。世宗、章宗朝的女真軍事貴族孛朮魯孝忠,當時的文人如此描寫他風雅的一面:
卜居?xùn)|萊,問舍求田,得是勝地。重命增飾,以為修真養(yǎng)浩之所。日與羽流禪客、詩人逸士,抨棋酌酒,撫琴分茶。逍遙游宴于其中,高養(yǎng)天和,自適自得。雖漢之疏廣、晉之淵明,無以過也。①張金吾編:《金文最》卷38范懌《掖縣孛朮魯園亭碑》,光緒二十一年重刻本。
釋典文事,無不探討;緇流羽客,延納弗拒。文章末尾對孛朮魯孝忠的比附或許有些不倫不類,但還是很能說明問題。又如行壽泗元帥府事的完顏斜烈,“敬賢下士,有古賢將之風。初至商州,一日搜伏,于大竹林中得歐陽修子孫,問而知之,并其族屬鄉(xiāng)里三千余人皆縱遣之。”②脫脫等:《金史》卷123《完顏斜烈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683頁。事又見歐陽玄《圭齋文集》卷2《送振先宗丈歸祖庭》,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王沂《伊濱集》卷20《題歐陽興世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看來此君心儀歐陽修已久,故有此等舉措。
由于元明兩代對金朝文學評價普遍不高,除了元好問等寥寥數(shù)家受到一定關(guān)注外,文人學士往往無意于此。金源一代典籍文獻的缺失現(xiàn)象也十分嚴重,限制了我們認識的深入,這是令人遺憾的。不過,雖然這些女真軍事貴族留存的篇什很少,但管中窺豹,還是不難發(fā)現(xiàn)其藝術(shù)功力的深淺和藝術(shù)造詣的高下。如朮虎邃(1193后—1232),曾寄詩劉祁:
西湖風景昔同游,醉上蘭舟泛碧流。楊柳風生潮水闊,芙蕖煙盡野塘幽。花邊落日明金勒,云里清歌繞畫樓。今夜相思滿城月,梁臺楚水兩悠悠。③劉祁:《歸潛志》卷3,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5-26頁。
全詩情景融合無間,語淺意深,有余不盡,了不見粗豪習氣,實不失為一篇佳構(gòu)。
繼世宗之后即位的章宗完顏璟,對于中原文化的熱衷程度,在金代九位帝王中是最為突出的,并且造詣相當高。其父顯宗完顏允恭,自幼從儒者鄭松學習儒家文化,被世宗立為皇太子之后,“專心學問,與諸儒臣講議于承華殿。燕閑觀書,乙夜忘倦,翼日輒以疑字付儒臣校證。”④脫脫等:《金史》卷19《世紀補·顯宗》,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10頁。甚至因沉溺于中原文化而松懈了對本民族語言的學習,招致其父的訓(xùn)斥。劉祁也稱他“好文學,作詩善畫”⑤劉祁:《歸潛志》卷1,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頁。。章宗的母親徒單氏,也“好《詩》、《書》,尤喜《老》、《莊》,學純淡清懿,造次必于禮。”⑥脫脫等:《金史》卷64《后妃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525頁。成長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耳濡目染,沾丏中原文化甚深,自是情理中事。章宗工詩詞,他存世的數(shù)首詩歌,如《宮中》、《聚骨扇》、《翰林待制朱瀾侍夜飲》、《軟金杯詞》等等,雖乏遒健骨力而不失精致綺麗。⑦劉祁:《歸潛志》卷1,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頁。茲舉其《軟金杯詞》一詩:“風流紫府郎,痛飲烏紗岸。柔軟九回腸,冷怯玻璃盞。纖纖白玉蔥,分破黃金彈。借得洞庭春,飛上桃花面。”觀此可概其余。章宗還精擅音律,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二七引燕南芝庵《唱論》,將他與唐玄宗、后唐莊宗、南唐后主、宋徽宗四人并稱為“帝王知音者”。⑧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27“燕南芝庵先生唱論”條,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335-336頁。據(jù)《金史》卷三九《樂志》知,章宗對金廷雅樂多所厘定。《大金國志》卷二十記載,泰和二年(1202),章宗“詔大興府擇民間女子十三歲以上、有姿色黠慧者,選三百人進入禁中,教為酒令及敕習市肆歌勸酒。”顯然,章宗所喜好的并非僅限于雅樂,他對民間音樂有著同樣甚至更為濃郁的興趣。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南村輟耕錄》及鍾嗣成《錄鬼簿》又稱,董解元為金章宗時人,《董西廂》即出于章宗之世。①分見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27“雜劇曲名”條,第332頁;鐘嗣成:《錄鬼簿》卷上“前輩已死名公有樂府行于世者”條,《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2年,第103頁。看來,戲曲等音樂藝術(shù)樣式,在金章宗朝開始受到后世研究者的普遍關(guān)注,絕非偶然。
史載“章宗性好儒術(shù)。即位數(shù)年后,興建太學,儒風盛行。學士院選五六人充院官,談經(jīng)論道,吟哦自適。群臣中有詩文稍工者,必籍姓名,擢居要地,庶幾文物彬彬矣。”②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21《章宗皇帝》,《二十五別史》本,李西寧點校本,濟南:齊魯書社,2000年,第158頁。其實這只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他大力提倡學習使用女真語言文字;禁止女真人改漢姓和學“南人”裝束;限制女真軍事貴族每戶參加女真進士科的人數(shù),以保證足夠的兵源,等等,這些措施又顯系直接繼承乃祖維持女真?zhèn)鹘y(tǒng)文化習俗的立場。但與世宗時期相比,章宗完顏璟這一代人沾染中原文化更深,而本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喪失更甚。他自己是一個例子,他的堂兄弟完顏璹更是一個典型。
完顏璹(1172—1232),本名壽孫,世宗賜名為璹,字仲實,一字子瑜,自號樗軒居士,累封胙國公、密國公。完顏璹雖貴為王胄,但其立身處世、舉止談吐卻儼然似一介寒儒,無半點驕奢習氣。在今存金代女真文人的作品中,以他取得的文學成就最引人矚目,故元好問稱之為“百年以來,宗室中第一流人也。”③元好問編:《中州集》卷5“密國公”條,上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2年,第272頁。
完顏璹自小便接受儒家文化的教育,“少日學詩于朱巨觀(瀾),學書于任君謨(詢),遂有出藍之譽。文筆亦委曲能道所欲言”,加之與當時的名士大夫往來頻繁,“朝臣自閑閑公(趙秉文)、楊禮部(云翼)、雷御史(淵)而下,皆推重之。資雅重,薄于世味,好賢樂善,寒士有不能及者。……文士輩亦時至其門。家所藏法書名畫,幾與中秘等。客至,貧不能具酒肴,設(shè)蔬飯與之共食。焚香煮茗,盡出藏書商略之。談大定、明昌以來故事,或終日不聽客去。風流蘊藉,有承平時王孫故態(tài),使人樂之而不厭也。”④元好問編:《中州集》卷5“密國公”條,上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2年,第275頁。典型一位儒家士大夫的形象。他為自己的小像題詩:“枯木寒灰久亦神,應(yīng)緣來現(xiàn)胙公身。只因酷愛東坡老,人道前身趙德麟。”⑤元好問:《遺山先生文集》卷36《如庵詩文敘》,四部叢刊景明弘治本。趙令畤是宋宗室,與蘇軾友善,他的表字德麟就是由蘇軾改的。此詩尾聯(lián)既表明了作者對蘇軾的喜愛,又切合自己的皇族身份,若非熟諳中原文化并深造有得,斷不能道此。
完顏璹平生詩文甚多,晚年自選詩三百首、詞一百首,編成《如庵小稿》五卷,由趙秉文、元好問先后作序刊行。該集早已亡佚不存,今人從《中州集》、《歸潛志》等書中輯得詩詞五十余首。試觀以下所錄詩詞各一首:
四時唯覺漏聲長,幾度吟殘蠟燼釭。驚夢故人風動竹,催春羯鼓雨敲窗。新詩淡似鵝黃酒,歸思濃如鴨綠江。遙想翠云亭下水,滿陂青草鷺鷥雙。
——《思歸》
壯歲耽書,黃卷青燈,流連寸陰。到中年贏得,清貧更甚,蒼顏明鏡,白發(fā)輕簪。衲被蒙頭,草鞋著腳,風雨瀟瀟秋意深。凄涼否,瓶中匱粟,指下忘琴。一篇《梁父》高吟。看谷變陵遷古又今。便《離騷經(jīng)》了,《靈光賦》就,行歌《白雪》,愈少知音。試問先生,如何即是,布袖長垂不上襟。掀髯笑,一杯有味,萬事無心。
——《沁園春》①詩見元好問編:《中州集》卷5,上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2年,第275頁;詞見《中州集》附錄《中州樂府》,上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2年,第557頁。
七律語意淡泊,在蕭散曠逸中不乏清新韻致,第三聯(lián)對仗尤工整。詞作的筆調(diào)則在衰颯蒼勁與委婉蘊藉之間,就中似乎別有幽微心境,難以具體詮釋解說,《金史》記載了完顏璹在金朝覆亡前夕的一段話:“兵勢如此,不能支,止可以降。全完顏氏一族歸吾國中,使女直不滅則善矣,馀復(fù)何望。”②脫脫等:《金史》卷85《完顏璹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905頁。細玩此詞意蘊,或與此不無關(guān)系。完顏璹的作品雖散佚嚴重,但即使憑以上數(shù)作,稱他為女真文人中的佼佼不群者,亦當不為過。
金朝在世宗和章宗時期走向全盛。趙秉文評價說:“大定明昌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上方留意稽古禮文之士。”③莊仲方編:《金文雅》卷15趙秉文《張左丞神道碑銘》,光緒十七年江蘇書局重刊本。元好問回顧這段歷史時也說:“大定、明昌間,文治為盛。教養(yǎng)既久,人物輩出。”④元好問:《遺山先生文集》卷18《嘉議大夫陜西東路轉(zhuǎn)運使剛敏王公神道碑銘》。劉祁說世宗“善于守成,又躬自儉約以養(yǎng)育士庶,故大定三十年幾致太平。所用多淳樸謹厚之士,……偃息干戈,修崇學校,議者以為有漢文、景之風”;章宗“屬文為學,崇尚儒雅,故一時名士輩出。大臣執(zhí)政,多有文采學問可取。能吏直臣皆得顯用,政令修舉,文治爛然,金朝之盛極矣。”⑤劉祁:《歸潛志》卷12《辨亡》,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36頁。不難發(fā)現(xiàn),所謂大定、明昌之治,當時的文人之所以極盡美化之能事,著眼點正在其時儒家文治的全面展開——實質(zhì)上就是漢化的全面深入。與此相應(yīng),金代文學也逐漸走向成熟,日益展示出自己獨特的風貌。
至章宗末年,后戚、近侍和宦官擅權(quán),又崇尚浮華,大肆建宮設(shè)殿,社會矛盾開始激化,加上北方蒙古族勢力崛起構(gòu)成直接威脅,金朝敗跡已顯。此后,衛(wèi)紹王、宣宗、哀宗相繼嗣位,權(quán)臣紇石烈執(zhí)中、朮虎高琪等先后用事,政出多門,綱紀紊亂,金朝在內(nèi)外交困中一蹶不振,急劇走向衰亡。
頗有意味的是,據(jù)《金史·忠義傳》記載,金亡之際,“女直人無死事者,長公主言于哀宗曰:‘近來立功效命多諸色人,無事時則自家人爭強,有事則他人盡力,焉得不怨。’上默然。”⑥脫脫等:《金史》卷124,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705頁。哀宗的“默然”,既是對事實的默認,也透著幾分尷尬。考諸史籍,女真人殉國者確實不多,《歸潛志》卷五、卷六記載,只有裴滿阿虎帶(女真進士,御史大夫)、完顏仲平(女真進士,戶部尚書)、吾(烏)古孫仲端(女真進士,翰林學士承旨)、完顏仲德(女真進士,尚書右丞)、完顏彝(門蔭,忠孝軍總領(lǐng)、御侮中郎將)等寥寥數(shù)人。這些人多是女真進士科出身,沾染儒家傳統(tǒng)思想甚深,他們選擇殉國,很難說其中沒有漢文化的影響。完顏彝雖系蔭襲的女真軍功貴族,但也喜好文士,還一度從王渥學習程朱理學,實際上也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完顏仲德、烏古孫仲端等人,或有文獻記載能詩擅文,或有作品存世,隨著他們的殉國,金代的女真族文學也走向了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