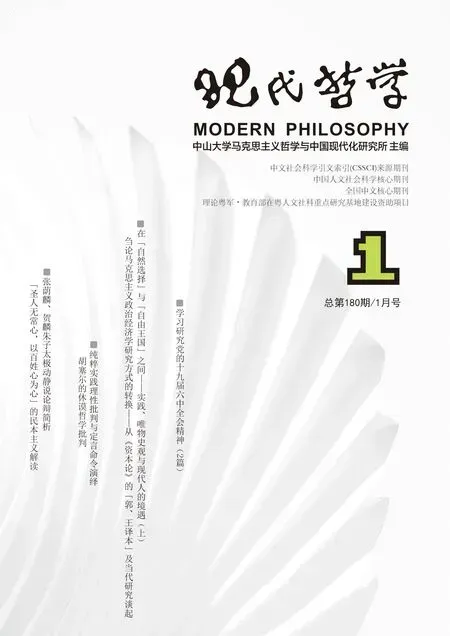馬克思機器理論與人工智能的相遇及反思
付天睿
人工智能是當今最炙手可熱的話題之一。憑借其高度先進的技術形態,人工智能被廣泛地認為已然超越了傳統的機器概念。然而,在其發展態勢尚不明確、社會影響尚不顯著(暫以歷史上兩次“工業革命”作為參照)的情況下,對其進行外在于技術的審視與反思是十分必要的。我們知道,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社會批判理論及其所揭示的資本邏輯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切中了當今時代的主題,而對機器的分析也是其中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馬克思的資本批判視野中的機器理論仍是我們分析人工智能與機器關系問題的關鍵視角。因此要探討人工智能以及人工智能與機器的關系,有必要從馬克思關于機器的理論出發。
一、馬克思機器概念的基本內涵
機器概念是馬克思進行政治經濟學分析和批判的重要環節和對象,正是由機器和機器體系所構成的現代工業直接激發了馬克思的批判理論的問題意識。根據當前對人工智能與機器進行性質判斷的問題框架,有必要從機器的結構和功能兩方面對馬克思的機器理論進行簡要梳理。
(一)結構:動力、傳動與工具的生產裝置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根據機器運行的結構與過程,將機器具體地分為動力機、傳動機和工具機三個部分。馬克思指出,動力機是機器的動力來源,比如瓦特所發明的蒸汽機;工具機則是區分或規定機器具體所能夠從事工作的核心部分,即傳統手工工場時人類手工技術的替代品;而傳動機負責以動力傳遞的方式將二者加以連接。機器的三種技能各司其職,不可或缺。在此基礎上,馬克思認為機器相對核心的部分是“動力機”和“工具機”,即為機器供能和真正能體現機器功能和業務的部分。為了克服自然力的有限性、低效率,就“必須有一種比人力強大的動力”(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2頁。,即機器的運行首先需要更高效能量的不斷供給。而把能量轉化為具體生產過程的部門則是“工具機”。“正是工具機的創造才使蒸汽機的革命成為必要。一旦人不再用工具作用于勞動對象,而只作為動力作用于工具機,人的肌肉充當動力的現象就成為偶然的了,人就可以被風、水、蒸汽等等代替了。當然,這種變更往往會使原來只以人為動力而設計的機構發生重大的技術變化。”(2)同上,第432頁。也就是說,在動力機的驅動和傳動機的輸送下,工具機不僅作為了機器特性的標識,也是機器不斷進化與完善的主要場所。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對于機器各個結構的界定不僅針對于作為個體的機器,同樣適用于由功能類似的個體機器的集合來分別擔任這三種結構的機器體系。
(二)功能:機器體系的構成和勞動與商品價值的變化
在總體性的理論視域中,機器的結構勢必要置于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之中進行考察,即在機器作為生產工具的生產過程中,機器的結構必然表現為具體的功能。
第一,機器的功能首先體現為分工的加劇。在馬克思看來,機器和機器體系的應用在社會生產中率先表現為對人的傳統勞動形式和勞動力地位的替代:“作為工業革命起點的機器,是用這樣一個機構代替只使用一個工具的工人。”(3)同上,第432頁。單個機器所能夠實現的僅僅是取代“使用單一工具的個人”,而只有不同類型機器的聯合才能真正實現生產規模的擴大,即機器體系才能夠作為機器在資本主義經濟運行中的具體形式。這里,馬克思將傳統手工工場的分工形式擴展到了機器體系中,只不過工人技術的差別變成了不同工具機之間的差別,以及工人其自身屬性或本質的區別變成了力學、電學及化學技術的區別。“機器是勞動工具的集合,但決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種勞動的組合……機器的采用加劇了社會內部的分工,簡化了作坊內部工人的職能,集結了資本,使人進一步被分割。”(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26-628頁。在這個意義上,機器不僅不是蒲魯東所認為的“分工的反題”,而是分工的強化與進化。
第二,機器能夠使商品的價值和屬性發生變化。既然在機器生產時代人類的勞動形式從直接的人力勞動轉變為對機器的操作,那么對所生產的商品的價值而言就無法以傳統的勞動時間來加以計算。首先,“機器”作為直接的生產資料,其自身的價值必然不同程度地體現在商品的價值中。馬克思指出機器進入全部的勞動過程,也憑借不同商品性質的差別而“部分地”進入了價值增殖過程。“機器本身包含的勞動越少,它加到產品上的價值也就越小……機器不是使產品變便宜,而是按照它自身的價值使產品變貴。”(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47-448、444頁。換言之,機器所帶來的勞動產品的增殖同生產機器本身所需要付出的勞動成正比。因而,在機器被作為新的生產工具使用于商品生產的過程中,商品的價值就成為兩種勞動的總和,即生產機器的勞動和操作機器的勞動。進一步,馬克思區分了“作為價值形成要素”和“作為產品形成要素”的機器,即商品價值中所蘊含的機器本身的價值和機器磨損的價值。對機器的生產越簡單,產品價值中對機器成本的計算越少。如果完全用機器來生產機器,那么商品生產中使用機器的成本就會遠遠降低到人力勞動生產商品時的成本。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即“生產機器所費的勞動要少于使用機器所代替的勞動”(6)同上,第451頁。。這二者的差值在馬克思看來恰恰導致資本家展開競爭,進一步改變了生產勞動的方式和結構。因此,雖然商品價值的勞動本質(勞動價值論)沒有因機器的使用而發生變化,但使得商品價值本身(或表現形式)產生變化得以體現為機器的又一功能特征。通過機器體系的應用,早先作為“物”的勞動資料與產品得以“轉化為一種與固定資本和資本一般相適合的存在”(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4頁。,因而無論是商品還是生產商品的勞動都在機器體系中資本化,商品的內在性質也在其價值發生改變的同時產生了變更。
第三,機器的應用能夠產生“剩余勞動”。基于機器對分工的加劇和機器生產中商品價值內涵的變革,馬克思揭示了機器在剩余價值的生產中形成的工人的“剩余勞動”。馬克思指出,“資本通過使用機器而產生的剩余價值,即剩余勞動”(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287頁。。由于機器體系大大提高了工業的生產效率,因而相對地縮減了工人的勞動時間和工人的人數。剩余勞動一方面體現在剩余勞動時間,另一方面也體現在“過剩的勞動人口”。在時間方面,雖然機器節約了一定的手工勞動時間,卻憑借因其自身而膨脹的生產規模而要求了更多的勞動時間。也就是說,雖然工人憑借從手工制作到機器操作而節省了一些工作時間,但同時操作機器對技術和體力要求的降低也威脅著傳統男性工人的地位。在行業和從業工人的雙重競爭下,工人們必須拿出比節省的更多的時間來投入新的機器操作中,否則將面臨失業或被婦女兒童替代的境地(馬克思也批判了資本對婦女兒童的不道德占有)。“這些人不得不聽命于資本強加給他們的規律……機器消滅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產生了經濟學上的悖論,即縮短勞動時間的最有力的手段,竟變為把工人及其家屬的全部生活時間轉化為受資本支配的增殖資本價值的勞動時間的最可靠手段。”(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69頁。所以,在馬克思看來,機器所造成的“剩余勞動”同樣是一種“追加勞動”“強化勞動”。
需要指出的是,機器功能的不同維度之間是內在連結的。在機器節約了傳統生產方式的勞動時間的同時,工人亦會憑借分工的深化和固化,從而被動地參與到不斷擴大的機器生產和對機器本身的生產過程中,最終實現資本的增殖。所以,馬克思所指出的機器的功能,實質上就是機器對整個資本主義生產秩序的功能,即對于工人剝削的加深以及對資本的強化。因此,機器的特征與性質在馬克思的理論體系中可以被認為分別體現于其結構與功能兩方面。而對于同作為在其時代新興的技術產物,人工智能在某種程度上同樣可以嘗試按照這一方式加以探討。
二、“人工智能”及其對傳統機器概念的外在超越
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人工智能成為當前社會形態中的全新現實。憑借著“智能”的加冕,人工智能與機器的關系自然面對著多種程度的轉換與革新。要考察這種全新關系的具體樣態,首先需厘定人工智能的基本意涵。
(一)人工智能概念及現狀
就目前而言,“人工智能”尚是一個相對模糊的概念。通俗來說,“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就是讓計算機完成人類心智(mind)能做的各種事情”(10)[英]博登:《AI:人工智能的本質與未來》,孫詩惠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3頁。。而作為一門學科,人工智能“作為計算機科學的一個分支,通常是指通過普通計算機程序來呈現人類智能的技術,以及這樣的智能系統能否實現,如何實現”(11)俞揚:《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三版網絡版“計算機科學與技術·人工智能”條目,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網站https://www.zgbk.com/ecph/words?SiteID=1&ID=216760&Type=bkzyb&SubID=81532,最后訪問日期2022年1月20日。。人工智能科學根植于傳統計算機科學,依賴于近年來發展迅猛的模式識別、深度學習和人工神經網絡等技術,大大提高了其產品的工作能力與效率,成為當前社會炙手可熱的前沿話題。就其智能化程度而言,人工智能可被分為“強人工智能”與“弱人工智能”兩類(12)See John Searle, “Minds, Brain and Program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vol.3(3),1980, pp.417-457.。在當前,人工智能普遍地應用在模式識別與搜索、機器翻譯、自動駕駛等多種領域,而所謂的強人工智能(即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則鮮有突破。除了2021年基于“悟道”人工智能模型的“華智冰”以學生身份入讀清華大學、2017年沙特阿拉伯向人工智能機器人“Sophia”授予公民身份,以及“AlphaGo”及其改進型在國際象棋領域的勝利記錄外,并沒有成規模的、看似具有功能意識和類人心智的人工智能個體進入人們的視野。因此,雖然人工智能時代在某種程度上已經來臨,但其在當前仍然處于萌芽階段。目前人工智能領域及其產品既在其核心技術屬性與發展方向上既有別于“機器”,同樣有足夠的理由仍然被認為是“機器”。
雖然當前人們普遍仍可以將人工智能看作機器,但顯然其已經與傳統意義上的機器有所區別。當代人工智能技術能夠通過人工神經網絡技術實現高精度、高速度的機器翻譯、深度學習能力,展現出同人類智能所高度類似的計算能力、記憶能力、決策能力甚至情感能力。如 “華智冰”不僅能夠處理信息、識別數據,還能夠作詩譜曲,進行情感和創造性活動。(13)See Zhu Hongyuan, et al. “XiaoIce Band: A Melody and Arrangement Generation Framework for Pop Music”, The 24th ACM SIGKD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CM, 2018; Zou Xu, et al. “Controllable Generation from Pre-trained Language Models via Inverse Prompting”, arXiv:2103, 10685v1[cs.CL], 2021.在這個意義上,以“機器”將其作簡單的屬加種差式的定義或歸類難免有失準確。換句話說,“人工智能”本身作為一種機器的同時亦與傳統的機器概念產生了某種張力,而這種張力的“支點”恰恰在于傳統機器并不具備的“智能”。
(二)人工智能對于傳統機器結構的消解
上文提到,馬克思認為機器同以往的生產工具最為顯著的區別在于“工具機”,即“功能”從勞動者的手轉向了機器機構。自機器誕生以后,其發展和改造主要也集中在“工具機”的部分,即豐富功能、提高效率。就人工智能而言,單一或某幾種功能已經不符合“通用性”的發展方向。因此,人工智能同傳統的機器概念的分歧首先體現在“工具機”概念的消解。
一方面,如果依然將人工智能的變革意義歸結于“工具機”,那么當前諸多人工智能產品在功能上更接近“某機”,如翻譯機、駕駛機等,而并非人們通常理解的“人工智能”。這樣看來,對于此類僅在“工具機”意義上有所革新的機器的“人工智能”的命名方式顯然不盡合理。雖然當前的人工智能應用現象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專門化的,但其與傳統的“工具機”具有本質的差別。傳統機器的設計制造更多地圍繞著其將要具備的功能,即其發明和制造過程就是對功能要求的滿足的過程,本質上是一種逆向的邏輯模式;而人工智能應用更多地是其核心技術的能力體現,是一種正向的過程,如基于人工神經網絡的模式識別技術既能夠制成人臉識別設備,也能夠進行詞匯和語句的分析。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憑借其“智能”的特征,本身已經能夠作為一定程度上的創造性“力量”對一系列生產活動進行推動。在馬克思看來,傳統的機器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減免了損耗在生產過程中的人力,但其運行仍然需要原初的“自然力”的動力支持。一方面,馬克思指出,諸如蒸汽機的機器發明的意義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其所能夠提供的新的機器動力,即有些機器是自身直接作為動力機而誕生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提到,機器特別是機器體系同以往生產形式最大的不同在于人類不再參與具體的生產過程,而只作為“站在機器旁邊”的機器使用者、管理者、監督者,人類對于商品的生產過程轉化為對機器的操作過程,同時商品本身的生產過程自然包括了對生產這種商品的機器的生產過程。就人工智能而言,人類的操作量與操作難度進一步降低。當前,人類不需要對“人工智能”進行直接驅動,反而可能需要依賴人工智能高度發達的算法和數據來進行能源或動力配置。“信息社會的動力機,如果作為一種隱喻的話,已經不再是蒸汽機、發電機等傳統能量裝置,而是個人電腦、云計算中心、智能手機等信息加工和處理裝置,物聯網和互聯網是信息社會生產工具系統的傳動機。”(14)陳自富:《強人工智能和超級智能:技術合理性及其批判》,《科學與文化》2016年第5期,第31頁。在這個意義上,人工智能憑借其發展的通用性實現了“工具機”與“動力機”“傳動機”“自動機”的連通,因而消解了以“工具機”判定機器自身性質的機器范式。
(三)人工智能對傳統機器功能的超越:從剩余勞動到剩余知識
在傳統大工業時代,機器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淘汰了手工工場的勞動力,卻沒有實現對人類知識或經驗的復制而對某一行業或領域內勞動者的替代。馬克思就此指出,機器“不斷地把工人逐出工廠,或者把新的補充人員的隊伍拒之門外”(1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23頁。。前文提到,按照馬克思對機器結構的劃分,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對動力機與工具機進行了整合。人工智能的應用不再單單增加勞動者的剩余勞動時間,更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以成為勞動者的方式而取代了勞動者。換句話說,人工智能不僅是人類科技線性發展的自然結果(即技術及技術的產品對以往由人來主要承擔的勞動活動的不斷取代),更是技術所期望的一種“非線性”的“質變”(雖然這種質變尚未真正完成),即對“人”的行為模式、思維方式進行模擬從而實現某種真正“智能”。以往機器能夠不同程度地實現對人類某種勞動形式的模擬和取代,而人工智能科學則在設計和一定程度的表征上體現為對“人”本身的直接模擬。人工神經網絡技術旨在通過電子元件模擬人類認知的根本形式——神經系統,而建立在人工神經網絡基礎上,基于大數據技術、貝葉斯概率統計學的機器學習技術則在一定程度上模擬了人的經驗能力和記憶能力。“深度學習發現多層知識表示,例如從像素到反差檢測器……到對象部分,以及到對象。”(16)[英]博登:《AI:人工智能的本質與未來》,第57頁。就這種定向而言,人工智能顯然已經在知識層面對傳統機器的范疇實現了超越。雖然當前人工智能技術尚未達到科幻作品式的與人類“不分彼此”,但在一些傳統行業中已經出現其對人類勞動者進行替代的情況,如自動駕駛技術已經趨于完善、自然語言識別及翻譯更加準確。在教育和醫療行業,基于對人類知識模仿的人工智能產品也在逐步推廣,“教育開始接受個人或基于互聯網的人工智能輔助……計算機心理治療師已經應運而生,費用比人類治療師低得多”(17)同上,第188頁。。近年來,因不斷戰勝人類冠軍棋手而備受關注的“深藍”“AlphaGo”等人工智能產品同樣基于深度學習技術,其根據不斷跟自己對弈的海量步驟和結果“記住”了棋局中每種情況出現后的較優方案,從而作出克敵制勝的選擇。這種運作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與人基于神經記憶的經驗思維類似。前蘇聯的冠軍棋手卡斯帕羅夫曾這樣評價“深藍”:“它經常放棄短期利益,表現出非常擬人的危險(human sense of danger)。”(18)尼克:《人工智能簡史》,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17年,第125頁。顯而易見,人工智能的“記憶”是遠超人類的,它所掌握的“知識”對人類而言成為一種剩余,這種對剩余知識的掌握恰恰就是人工智能對傳統機器的超越所在。
(四)人工智能對個體操作的超越:“一般智力”的對象化
無論就技術路向還是產品形態而言,人工智能都試圖在最大程度上接近生產過程中的真實客體和模擬主體,力圖構成一種主客體間的中介結構與主體間的交互機制。這種對基于主客二分的傳統認識關系和生產關系的改造形式將人類智能錨定并提取為獨立的對象,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同馬克思的“一般智力”理論產生了呼應,人工智能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作為了“一般智力”的物化形態。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指出,在資本的生產過程中,機器體系超越了勞動者個體生產的線性維度,成為對不同的技能、力量和單純的勞動量(勞動時間)的綜合,成為一種異在于工人的、根植于資本的“一般智力”;而人工智能憑借更高的技術形態進一步實現了在生產生活中對“人”抽離,以自動化的更高形式成為“一般智力”更加具體和完善的對象物。在人工智能的參與下,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已經不需要作為“生產過程的監督者和調節者”而“站在生產過程的旁邊”(1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96頁。,人工智能憑借其海量的數據存儲與處理能力、精準的環境和模式識別能力及高效的模仿學習能力,已然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完成如對生產過程的監督調節等本屬于人類的更多職能。“工人”的離崗再不會“使資本變成無用的東西”(20)同上,第293頁。,恰恰相反,在當前時代人類智力越少地干預作為“一般智力”的人工智能的分析和決策過程,反倒越能為資本的精準增殖提高效率。相比于傳統的機器體系,作為“固定資本”發展的全新階段,人工智能更接近馬克思語境下的“一般智力”的對象物,即在創造剩余知識的基礎上,人工智能能夠進一步運用這些人類難以掌握的知識和技能,從而以突破“工人監管機器”的傳統模式,進入“人工智能自決”的方式對機器概念進行超越。
所以,人工智能與傳統機器概念的差別分別體現于其結構和功能的革命性變化。然而,雖然人工智能對機器實現了某種超越,但由機器工業衍生、創造的人工智能技術和具體的人工智能產品在當前社會仍然有足夠的理由被認為并未完全超越傳統機器的概念,而更多的是一種空前強大、空前發達的機器。
三、機器與人工智能概念的內在統一
雖然人工智能可以被認為在多種角度對傳統的機器概念進行了超越,但這種“超越”顯然不是絕對的、內在的。要分析人工智能是否在總體上脫離了馬克思語境中的機器概念,勢必要進入馬克思學說的核心論域——政治經濟學批判。
(一)屬性的一致:人的機器化與機器的人化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使用“異化”概念來描述當前社會的勞動者失去自身本質屬性、逐漸淪為異己的工具的社會現象。在馬克思看來,在資本與資本家的剝削壓迫下,勞動者同自身本質的勞動愿望相背地進行生產勞動,使得在生產秩序中的人已然失去了勞動活動的自由,成為與機器無異的生產資料。“工人的結局也必然是勞動過度和早死,淪為機器,淪為資本的奴隸。”(2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21頁。片面化生產的總體過程取消了工人和機器的實質差別,因而在分工中勞動者必須與本是其體力之延伸的機器同臺競技。“分工不僅導致人的競爭,而且導致機器的競爭。因為工人被貶低為機器,所以機器就能作為競爭者與他相對抗。”(22)同上,第121頁。
而在“機器論片斷”中,馬克思通過“一般智力”對廣義的異化現象作了更加深入的表述。前文提到,人工智能作為一般智力的對象物,其完成了智力的對象化意味著使得本屬于工人的——機器的操作者的原始智能發生了物化,成為能夠被經驗的具體的物。在這個意義上,傳統的物化的邏輯才最終實現了自身的完成,即人的知識和能動性徹底地遷移到具體的、在現實中而不是在邏輯中異在于人的“物”之中。在人自身已然具備了“物”的屬性的同時,物也占有了原屬于人的“一般智力”,對這種異化的復歸或克服就成為一種神話,人和物的界限也就在技術和生產的進化中逐漸消弭。因此,人工智能作為以機器體系為特征的資本的生產力的進化,對資本主義社會在個體與群體、主體與客體層面的重構實際上就是異化的當代顯現。既然馬克思已經指出了機器“是人的手創造出來的人腦的器官”(2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98頁。,即機器和智力的同構性,那么在這種同構性更加牢固的現代社會和生產關系中人工智能對機器的超越顯然是失敗的。
雖然馬克思因對主客二分的傳統思維方式的拋棄而在之后的作品中逐漸放棄了對于異化表述的使用,然而異化所描述的人的“非人”化、機器化的社會現象卻從未停止,甚至伴隨著技術在當代的不斷突破而愈演愈烈。馬爾庫塞指出,“技術已經變成物化——處于最成熟和最有效形式中的物化——的重要工具”,“技術作為工具的領域,既可以加快人的衰弱,又可以增長人的力量。在現階段,人們對他自己的機械裝置或許比以前更加軟弱無力”(24)[美]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劉繼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年,第143、197頁。。無論是機器化的人的能動與創造性的喪失,還是機器本身成為“一般智力”的凝結,都意味著人與機器的關系漸趨模糊。在這個層面上,如果“人”都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機器”,那么由這些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創造力”的“人”所生產的,并以學習人、模仿人、創造人為特征的人工智能就更加失去了突破機器概念范疇的可能。既然在資本主義社會,尤其是現代工業社會中的人憑借分工逐步加深了機器化,那么機器化的人所創造的“人工智能”即便本身旨在超越“機器”,也一定是以“機器化的人”作為標志物、參考系的。因此,人的機器化的背景下所追求的機器的人化,必然導致了人工智能的機器化。這一過程并不只是科學的、技術的,同樣是人(類)學的、邏輯的。換言之,正是“人”這一馬克思論域中的核心概念,成為鏈接人工智能與機器的中間環節。
(二)地位的一致: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環節的機器與人工智能
正如馬克思將人理解為社會關系的總和,機器在其看來也應當被置于更加宏觀的社會圖景下來加以審視。馬克思在《雇傭勞動和資本》中指出,機器是作為資本的組成部分的生產資料(25)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36-738頁。。而在《資本論》有關手稿中,馬克思對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本質作了更為明確的說明。“勞動資料發展為機器體系,對資本來說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使傳統的繼承下來的勞動資料適合于資本要求的歷史性變革。”(2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86頁。所以說,機器是出現在資本主義原有生產方式中,又使這一生產方式發生革命變化的技術形式。馬克思并沒有將機器的出現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過程中某個創造性的事件,而是更傾向于將其解釋為生產力自然發展的過程和階段性的結果。雖然馬克思承認機器所能夠帶來的巨大變化,但我們同樣需要認識到這種變化是內在于“生產方式”的,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量”的變化。在“機器論片斷”中,雖然出現了“機器代替工人的技能和力量”“自動機由許多機械器官和智能器官組成”“它們是人的手創造出來的人腦的器官”等看似超前的表述,但這種表述內在、根植于對固定資本和資本一般的分析之中。據此,馬克思在總體上指出了機器對于維持、鞏固資本主義經濟和剝削制度的巨大作用:“受機器排擠的工人從工場被拋到勞動市場,增加了那里已可供資本主義剝削支配的勞動力的數量……機器的這種作用,在這里被說成是對工人階級的補償,其實正相反,是對工人的極端可怕的鞭笞。”(2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07頁。機器的引入并未解放勞動者,反而使勞動者“空閑”出來,被全新的資本和生產關系進一步剝削。“在他們(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引者加)看來,機器使用工人和工人使用機器是一回事。所以,誰要是揭露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的真相,誰就是根本不愿意有機器的應用,就是社會進步的敵人!”(28)同上,第508-509頁。在社會歷史的視域中,機器本身必然無法同其應用方式和效果相剝離,單純地討論機器及其技術顯然是非歷史的、形而上學的。因此,馬克思的機器理論是內化、服務于其勞動價值與剩余價值理論和唯物史觀的。“機器成了資本的形式,成了資本駕馭勞動的權力,成了資本鎮壓勞動追求獨立的一切要求的手段。在這里,機器就它本身的使命來說,也成了與勞動相敵對的資本形式。”(2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00頁。也就是說,如果機器的出現并沒有帶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實質變更,即沒有使得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制度發生變革,卻使之在某種程度上得以鞏固,那么機器只是資本主義經濟生產力的某種自然形式而已。
在《資本論》時期,馬克思盡管意識到技術的革新對于生產力的重大作用,但更多地將“技術”概念通過其具體表現——機器來加以分析。也就是說,技術在生產力發展中的作用是依賴于機器來體現的,即如果機器所服務于的根植于資本的生產模式沒有產生變革,那么“技術”的真正突破顯然在某種程度上也并未實現。就人工智能而言,雖然近年其在運行速度、識別精度上較以往有了顯著提高,但從生產關系總體上看,并未對馬克思時期就已然在某種程度上揭示的資本主義經濟及社會運行的內在模式產生較大程度的變革,分工、私有制、雇傭與剝削依然是勞動市場的基本規則與特征。雖然越來越多的“人工智能”被應用于生產生活的各種領域,然“996”等對勞動時間和工作量的嚴苛要求卻屢見不鮮、變本加厲,勞動者的嚴峻處境較馬克思所處的大機器工業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換言之,人工智能目前依然有足夠的理由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某種環節和結果。“機器對于它的社會用途漠不關心,只要這些用途仍然在其技術力所能及的范圍之內。”(30)[美]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第131頁。因此,就社會經濟層面的現象或結果而言,人工智能同樣未能擺脫機器的概念范疇。
在以技術本身來判斷人工智能同“機器”的關系,在難以學科技術內部的某種實質性突破來宣告人工智能已經徹底脫離了傳統機器的范疇的基礎上,依照馬克思語境中機器的政治經濟學位置,同樣難以通過顯著變化的生產關系來將二者劃清界限。也就是說,至少在當前階段,以技術本身來判斷人工智能依然屬于傳統“機器”范疇的論證方向是存在難度的。在這種情況下,正如在19世紀生產規模的擴大中,馬克思將剛剛大規模投入使用的機器理解為“工具的組合”一樣,以在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資本邏輯)或生產關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來判斷人工智能的機器屬性不失為一種有效的方法。一方面,既然人本身在資本的勞動關系中“異化”為“機器”(這一點得到近代以來還原主義、科學主義自然觀的側面支持),那么本身即由人所創造的人工智能更加難以成其例外。另一方面,與其說人工智能并沒有真正突破馬克思機器概念的界限,不如說技術不僅沒有突破當前社會形態的界限并在實質上與之同化,而這一界限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規律(即資本邏輯)本身。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既以唯物史觀的方式發現了人工智能同馬克思所提到的機器的內在統一,也憑借人工智能的具體問題再現了馬克思機器論的唯物史觀內核。對于人工智能與機器概念之統一性的揭示,實際上就是對資本邏輯在當前社會之固化、深化的揭示。人工智能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屬于機器的事實,實際上體現了當前技術的發展程度仍然未能從根本上變革生產方式、改變生產關系的事實。
四、人工智能反思與展望:以機器與人的關系為限
在唯物史觀的總體視域中,即便人工智能尚未脫離一般的機器概念,也作為一種全新的“智能的”對象形式在極大程度上重構了傳統的主客體、主體間和對象間關系。在資本邏輯與物象化的時代背景下,作為生產過程中的復雜客體、模擬主體與一般智力載體的人工智能進一步變更了以多者間的“區別”為前提的關系范式,從而在“前關系”或“元關系”的層面重提了機器與人的問題。因此,對這種全新的人機關系、人際關系的錨定和理解必然需要唯物史觀的再出場,即從生產關系的歷史維度和勞動本體的存在維度對人工智能問題進行總體審思。
(一)唯物史觀:人工智能的社會視角審視
在當前對于人工智能相關技術熱情高漲、對人工智能所蘊含的技術與文化前沿之象征趨之若鶩的現實中,往往缺乏將其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來加以整體審視的態度。而馬克思及其社會批判的思想進路恰恰是以此展開的。
針對彼時新興的大工業機器生產,馬克思從根本上指出了對機器問題實質的反思所應當注意的問題,即作為生產技術工具的機器與其所代表的生產關系的區分。“工人要學會把機器和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區別開來,從而學會把自己的攻擊從物質生產資料本身轉向物質生產資料的社會使用形式。”(3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93頁。馬克思及其理論雖然無法共享當今時代的問題意識,但馬克思在彼時所揭示的資本邏輯在今天仍然明效大驗。
前文指出,既然人工智能在當前西方社會中所具備的性質和所處的地位很大程度上體現、取決于當前主導性生產關系即資本的運行邏輯,那么唯物史觀對于人工智能的社會反思而言在很大程度上無法缺席。 “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看,人工智能是固定資本之最新物質存在形態,具有物質存在和社會存在雙重內涵。”(32)都超飛、袁健紅:《資本關系的重塑及其再生產:人工智能的社會內涵和歷史意義》,《江海學刊》2019年第6期,第125頁。在“人工智能”概念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局面下,從生產的角度對人工智能進行定義是有可能的。在這個意義上,人工智能尚未在工業生產方式的進化上產生顯著而深刻的影響,更多地是傳統工業生產方式下所誕生的“新產品”,因而其定義或命名方式就不免失之武斷。如果一種新興的技術現象并沒有對工業生產方式產生革命性的改變,那么其就更多的是“機器”,而非“智能”。隨著整個社會生產力與技術的不斷發展,我們必須認識到人工智能徹底擺脫傳統的機器概念是可能的。但是,這種“擺脫”同時始終離不開唯物史觀的審視與裁判。換言之,對于人工智能和其他新興的社會與技術現象的評價和定位,唯物史觀總能從社會的、歷史的視角出發對于技術和專業領域的評價進行相對客觀的補充。
(二)人工智能時代的“勞動本體”
在西方近代以來主客二元對立思維方式的影響下,當前人們并未做好將具備“智能”的某類全新存在物歸入除了“物”(客體)與“我”(主體)之外的第三類存在的準備。因此,人工“智能”所引發的張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轉換為傳統的“主體”與“客體”間的張力,并標明了主客體之間的一種界限模糊化、關系復雜化的可能趨勢。作為機器的人工智能模擬或具備與作為傳統的主體的人高度類似的主體性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人類“主體性”的危機,重新凸顯了勞動主體性問題的哲學思考。在這個意義上,人類是否還是單一的主體,抑或人工智能的“智能”可否在形而上學、認識論或心理學的層面上被認為可以與人類心靈加以等同或接近,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當前,相關研究的重點在于人工智能的智能程度,以及這種難以評估的智能水平所可能帶來的主體性和倫理危機。(33)參見涂良川、喬良:《人工智能“高階自動化”的主體可能性——兼論人工智能奇點論的存在論追問》,《現代哲學》2021年第6期,第32頁。在有關于人類自身思維形式的探索被看作“認識論”或“形而上學”而被現代哲學或科學在一定程度上束之高閣的今天,人們卻憑借對人工智能的思維模式的探索而在一定程度上將其重啟。既然人工智能以人類智能為藍本,那么“人工智能認識論”或心靈哲學也在很大程度上難以突破傳統形而上學的窠臼。
基于此,對人工智能的哲學思考的再一次視角變換就得以成為可能。為了能夠對人工智能社會現象作出準確的評估和判斷,在具體的技術細節之外,我們必須首先明確人工智能的第一本質,即人造屬性。即便人工智能的“意識”再次成為難以把握的思辨形式,即便這種極盡復雜的機器最終成為馬克思語境中的“一般智力”的物化形態,但就其歷史而言,人工智能始終必須是由人和人的勞動活動所生產的。
自然界沒有制造出任何機器……它們是人的產業勞動的產物,是轉化為人的意志駕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說在自然界實現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質。它們是人的手創造出來的人腦的器官;是對象化的知識力量。固定資本的發展表明,一般社會知識,已經在多么大的程度上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從而社會生活過程的條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這種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會生產力已經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僅以知識的形式,而且作為社會實踐的直接器官,作為實際生活過程的直接器官被生產出來。(3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97-198頁。
相比于簡單的機器,人工智能在一定意義上更接近于馬克思提到的“人類頭腦的器官”“物化的知識力量”,即“一般智力”的具體體現。人工智能產業的發展不僅僅是技術的進步,更是從知識形式到社會實踐的直接生產。因此,在人工智能時代,“勞動本體論”能夠獲得比以往工業社會中更加顯著的實踐意義。一方面,人工智能無論其基于何種知識、蘊含何種智能,甚至可能具備的任何類人的勞動實踐能力,但其在本質上都是人類勞動者勞動實踐的直接產物。在這個意義上,人工智能與人就已然形成了基于勞動的本體論次序。這種次序的形成為人工智能與機器的關系判定提供了全新視角,即在基于傳統機器定義進行論證缺乏效率時,可以憑借本體論的次序差別來對“機器”進行重新定義:人工智能在本質上是由人類勞動所生產的,那么人工智能就一定是“機器”。一旦人工智能有足夠的依據被認為是“機器”,那么其對于人類主體性的威脅就大大降低,生產勞動過程中的人類主體性維度反倒因此而得以凸顯。另一方面,這種基于勞動的本體論秩序同樣能夠在新時代的總體背景下為傳統主客二分問題提供全新的解釋路徑。在生產秩序和文化傳播中的人工智能,作為一種廣為接受和流行的公共知識,作為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的客觀互動機制與普遍公共知識媒介,標志著“智力”本身及對其的認知正從封閉的自我意識轉向開放的公共話語。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解決人工智能時代心靈哲學和認知科學所可能加劇的人自身的認同危機。
總之,對人工智能“勞動產品”第一本質的明確,不僅能夠為人工智能的發展和一系列可能出現的技術、倫理困境提供實在的邏輯起點(即判定其性質及與“機器”之關系),也能夠在缺乏確定性的意識哲學之外為人與人之間的“主體間性”關系及其內涵的個人“主體性”環節的社會存在論分析提供全新依據。作為生產過程中的復雜客體、模擬主體與一般智力載體,人工智能深刻重構了主客體之間、主體之間的中介系統。這標明了社會性主客體關系日趨交融化和復雜化趨勢,凸顯了勞動主體性與勞動主體間性的交互融合的發達現代社會結構,亟需唯物史觀在勞動主體論與社會存在論層面的新發展來予以回應。在當下以人工智能現象為代表的社會現實中,唯物史觀的全新批判形態也構成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發展的重要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