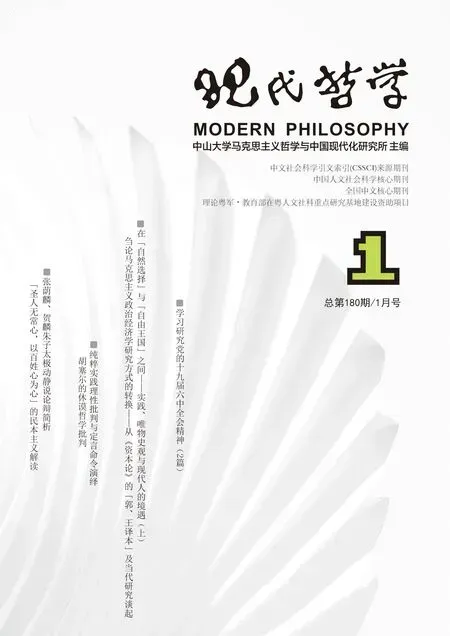馮契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新性探索
王向清 向 前
馮契(1915-1995)是我國當代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中國哲學史家。在哲學元理論研究領域,他撰著了《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邏輯思維的辯證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三本著作,建構了具有馬克思主義哲學屬性的“智慧”說哲學體系。在中國哲學史研究領域,他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撰著了《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兩部著作,對中國哲學史作了具有開創性的研究。在哲學研究中,他堅持“哲學是哲學史的總結,哲學史是哲學的展開”的史論結合原則,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作了創新性探索。
一、豐富與拓展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體系
馮契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豐富和拓展,主要體現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將狹義認識論拓展為廣義認識論。馮契認為站在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高度去回顧中外哲學史,便可發現中外哲學史考察的認識論問題主要有四個:其一,感覺能否給予客觀實在?其二,理論思維能否達到科學真理?其三,邏輯思維能否把握具體真理(首先是世界統一原理、宇宙發展法則)?其四,人能否獲得自由?(1)參見《馮契文集》第4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41-42頁。但近代西方哲學中以實證論為主的科學主義流派從狹義的角度來理解,在這一流派看來,前兩個問題指向形而下的對象世界,是認識論應當探討的有意義的問題;而后兩個問題涉及的是形而上領域,不屬于認識論探討的問題,對它們的探討也是無意義的。馮契不贊成對認識論作狹義理解的觀點,而主張作廣義的理解。廣義認識論主張一個完整的認識過程由“無知至知(知識)”和“知識至智慧”兩次飛躍構成。馮契對知識怎樣升華為智慧,也就是“轉識成智”進行了深入的考察。廣義認識論的創新主要體現為對“轉識成智”的考察,因而它又被命名為“智慧”說。“智慧”說對認識過程第一次飛躍的考察和流行認識論考察的內容基本一致,是可以用知識形態的概念、判斷、推理等名言世界所把握的形而下領域。而由“知識至智慧”的飛躍,考察的是認識論四個問題中的后兩個,涉及的是超驗的形上之域,難以為知識形態的名言世界所把握,主要憑借智慧去領悟、體悟,是以往的認識論沒有關注的領域。
在馮契看來,知識是可以用概念、命題、推理等名言世界來把握的理論系統,可以通過后天的學習來獲得、把握。而智慧著重關注的是形上之域,是關于宇宙人生根本原理的把握,是關于“性與天道”的學說。馮契以為,知識憑借飛躍能夠轉化為智慧。主體在認識世界、改造世界與認識自我、發展自我的實踐活動中,不但形成了以發現事實、條理等以求真為特征的知識形態的純科學;而且獲得了窮究會通的境界,達到物我兩忘、天人合一的哲學智慧。由知識到智慧的飛躍過程中,主體的精神狀態體現為連續性的中斷和頓然實現的感覺。知識側重分析和抽象,是對事物各個方面性質和屬性的把握;而智慧是關于天道、人道根本原理的把握,是具體的、綜合的。(2)參見王向清、張夢飛:《馮契的“轉識成智”學說及其理論意義》,《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2期。知識側重分析,知識相加不等于智慧,“把部分相加不等于整體,只有通過飛躍,才能頓然地全面、具體把握關于整體的認識”(3)《馮契文集》第1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419頁。。這就是說:知識通過飛躍才能轉化為智慧。在他看來,由知識到智慧的飛躍是通過理性的直覺、辯證的綜合、德性的自證而實現的。
第二,充實了認識論中“知覺”“意見”兩個范疇。無論在西方哲學史還是在中國哲學史上,“意見”都是認識論范疇,但在中西哲學史上都沒有揭示其含義、特點以及在認識過程中的作用。“知覺”既是西方哲學的范疇,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范疇,但它們同樣沒有揭示其含義、特點等。“智慧”說從實踐的觀點出發,在闡述人類認識由無知到知,由知識到智慧兩次飛躍時,繼續援用并充實了“知覺”“意見”范疇。
馮契認為感覺是客觀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而引起的認識活動,是意識和外部世界的直接聯系,感覺能夠給予客觀實在。那么,作為感覺綜合的知覺也能給予客觀實在,“知覺是指感覺和心靈對知識的把握”(4)馮契、徐孝通編:《外國哲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年,第523頁。。如果說感覺是認知主體對客觀世界表象的分析反映,那么知覺便是認知主體對客觀事物之表象與外部聯系的綜合反映。知覺將外部對象各種屬性進行綜合,把握整體、區別彼此、聯結異同,因而能“化所與為事實”(5)《馮契文集》第1卷,第138頁。。知覺具有客觀實在性,因其獨立于主體意識之外,且知覺本身亦是客觀世界的一部分,而被知覺對象亦具有客觀世界的時空綿延一致性;知覺具有整體性,因為知覺所綜合產生的內容是統一的整體;知覺具有時空性,知覺所綜合的客觀對象不但總是處于一定的時空關系中,而且認知主體與被知覺對象的關系也總是處于一定的時空關系中。因而知覺既能夠幫助認知主體進行自我認知,又能幫助認知主體感知客觀世界。
馮契所闡發的“意見”范疇的基本含義是指未經邏輯論證和實踐檢驗的是非界限不明的個人主觀性認識。意見有四個顯著特點:見蔽相雜的個別主體的主觀性認識,是非界限不明的個體認識,不同于偏見,依賴于客觀現實。馮契認為不同主體對同一問題產生不同意見的爭論是有其根源的。其一,不同主體不但要受所處時代的客觀條件的制約,而且受個人知識經驗、閱歷等主觀條件的制約;其二,不同主體在意見爭論的過程中還會受政治、倫理立場和認識過程復雜性的制約。不同意見的爭論在認識過程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通過不同意見的爭論達到一致的認識,在此基礎上通過實踐檢驗確定其真偽,以便把握真理。
第三,將“疑問”“觀點”這兩個普通概念提升為認識論范疇并進行論證,拓展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體系。“疑問”不是傳統認識論體系中所固有的范疇,以往的哲學家都沒有從認識論意義上關注。如前文所述,馮契對于“知覺”“意見”等范疇的展開、充實是以對“疑問”的把握來實現的。馮契認為,疑問就是由于人們意識到了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矛盾,進而提出的問題。這些矛盾具體體現為:新事實與舊概念之間的矛盾,假說與事實不一致的矛盾,各種觀點、學說之間的矛盾,真相與假象不一致的矛盾。疑問產生之時,具有兩大特征:認知主體在主觀情感上的疑難與驚詫、對于有知與無知的矛盾意識。“問題”是“疑問”的主體內容,“疑問”則是對“問題”內容的思維展開。疑問還能幫助認知主體關注有知與無知的認知矛盾、破除思維中形而上學的片面模式。認識起因于疑問,任何基于人類感性活動的認識活動、基于認識活動的實踐活動,都是在疑問產生后步步深入的。
馮契以為“觀點”就是指一貫的看法,貫穿在意見之中,對各種意見起統率作用。(6)參見《馮契文集》第1卷,第228頁。認知主體形成某種觀點時,將會以它作為看待事物的視角,并在對事物發表意見時秉持前后一致的態度。意見的分歧不一定是觀點的分歧,但對于重大問題意見的不一致往往彰顯了觀點的對立與斗爭。觀點從本質上而言是觀念結構,即是意念圖案與社會意識的結合,這種觀念結構也是對客觀世界的反映。馮契認為在“一致而百慮”的思維矛盾運動中,存在著實事求是的觀點與主觀片面偏激的觀點之間的對立與斗爭。這突出地反映在有知與無知的矛盾、正確與錯誤的對立及不同意見的爭論中。關于有知與無知的矛盾,認知主體應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將無知的羞愧情感化作努力求知的前進力量。關于正確與錯誤的對立,認知主體須知錯誤乃是日常生活中難免的。因而,認知主體要堅持“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原則,堅持自我批評的方式,在爭論之中發現自己的問題并勇于改正。對于不同意見之間的爭鳴,認知主體應當“從善如流”,不將主觀、片面、偏激的觀點作為至高無上的真理,而是要善于虛心接受他人的意見,這樣才能發展出較為全面的知識。
二、開拓性地建構了馬克思主義辯證邏輯體系
馮契曾提出過一個耐人深思的問題:明代以前,中國人在科學技術方面一直居于前列,那么中國古代科學家們是用什么思想方法指導科學研究的呢?在他看來,中國古代哲學雖然在形式邏輯研究方面不如歐洲哲學和印度哲學,但在辯證邏輯領域的研究卻居于世界領先地位。而中國古代辯證邏輯的發展一方面以古代科技思想的發達為基礎,另一方面又轉過來促進了古代科技的進步。他指出:“中國比較早地發展了辯證邏輯,也比較早地發展了辯證法的自然觀”(7)《馮契文集》第4卷,第48頁。。從某種意義說,中國古代較早發展起來的辯證邏輯為古代科學技術發展提供了思維方法的指導。基于思維科學是哲學理論重要來源的觀點,很有必要對我國古代的辯證邏輯進行挖掘、整理;而這種挖掘、整理既是總結我國古代自然科學成就的思維依據,又是為建構辯證邏輯理論體系服務的。為達到這雙重目的,馮契從史論結合的視角對辯證邏輯做了開拓性的探索。就“史”的層面而言,他撰著三卷本的《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撰寫《中國古代辯證邏輯的誕生》《論王夫之的辯證邏輯思想》《論中國古代的科學方法和邏輯范疇》等文,對我國古代的辯證邏輯思想做了較為系統和深入的考察。就“論”的層面而言,他撰著《邏輯思維的辯證法》一書,建構了獨特的辯證邏輯體系。
(一)對古代辯證邏輯成果的系統梳理
馮契在《中國哲學史研究》1981年第3期發表了《中國古代辯證邏輯的誕生》一文,對中國古代辯證邏輯誕生的根據、代表人物、基本觀點作了探討。他認為,人們在研究邏輯學之前,已經在運用邏輯了。人類的思維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因而思維形式及其規律也是“自在之物”。作為以理論思維的方式把握對象世界的哲學,在論證和辯論時,都要運用邏輯。從總體來看,人類的邏輯思維經歷了由自發到自覺、由較少自覺到較多自覺的歷史發展過程。形式邏輯和辯證邏輯作為人們正確思維的形式和規律的自覺掌握,也經歷了一個由簡單到豐富、由雛形到成熟的歷史發展過程。
馮契斷言,產生于殷周之際的原始陰陽說、八卦說和五行說已經有了樸素辯證法的萌芽。但只是到了春秋戰國之際,孔子、墨子、老子等諸子興起,展開“名實之辨”即關于名稱和對應對象的關系問題之爭,才觸及了邏輯學問題。墨子第一個提出“類、故、理”的邏輯范疇;《老子》第一個發現了辯證法的否定原理,并觸及辯證思維的論斷形式問題。戰國中期,百家爭鳴進入高潮,對邏輯問題的探討也大大向前:莊子對邏輯思維提出種種責難,以為有限的、抽象的、靜止的概念無法把握無限的、具體的、運動的對象;辯者惠施、公孫龍等圍繞名實關系展開的“堅白同異之辨”,進一步揭露了邏輯思維的內在矛盾;辯者的相對主義也是理論思維的必經環節,經過他們的揭露和責難,后期墨家才有可能在反思的基礎上建立古典的形式邏輯體系;到了戰國末期,荀子和《易傳》的作者等分別對“名實”之辨作了總結,提出了辯證邏輯的某些基本原理。
在馮契看來,荀子對辯證邏輯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提出了“制名”的目的是為了“辨同異”,揭示了辯證法是邏輯思維所固有的。二是概括了邏輯思維應遵循“符驗”“辯合”和“解蔽”的原則,強調主體應客觀地、全面地看問題。《易傳》對辯證邏輯的貢獻主要體現在提出了“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的觀念,初步涉及了思維的對立統一原理。《月令》《內經》對辯證邏輯的貢獻集中體現在探討了“比類”“取象”“度量”“順時”等方法,將辯證邏輯的比較法運用于具體科學。(8)參見《馮契文集》第8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59頁。馮契撰寫專文概括了明清之際王夫之對辯證邏輯做出的三大貢獻:一是對名(概念)、辭(判斷)、推(推理)三種思維形式作了辯證思考;二是對言、象、意、道的統一作了充分的闡釋;三是對分析和綜合的辯證關系作了充分論證。
(二)對馬克思主義辯證邏輯體系的獨特建構
首先,建構辯證邏輯體系的動因。
馮契著力建構獨特的辯證邏輯體系,其動因在于意識到了辯證邏輯在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進程中的重要作用。他確信:“從唯物辯證法這門科學來說,研究辯證邏輯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辯證法的生長點,至少是辯證法的生長點之一”(9)《馮契文集》第2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4頁。。
馮契指出,較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國的學術界片面強調哲學是意識形態和階級斗爭的工具,而忽視了它是科學。哲學作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概括和總結的科學,特點就在于以理論思維的方式把握世界。哲學要求總結、概括科學成就,開展嚴謹的邏輯論證,通過與對立的哲學體系的爭論來發展自己,并反過來推動科學的發展。在他看來,哲學概括科學成就和指導科學研究時,必須通過邏輯和方法論這個環節。作為邏輯學的兩大分支之一的形式邏輯在20世紀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而相對于形式邏輯的研究來說,辯證邏輯的研究卻停滯不前。因此,必須重視辯證邏輯的研究,推出新的成果為哲學概括科學的成就提供方法論環節,從而構成唯物辯證法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增長點。
其次,對辯證邏輯內容的開拓性探索。
第一,探討怎樣化理論為方法,闡明認識的辯證法如何通過邏輯思維的范疇,轉化為方法論的一般原理。(10)參見《馮契文集》第1卷,第50頁。邏輯思維是包含辯證法的,而對這種辯證法的認識有一個從自發到自覺的發展過程。馮契對邏輯思維從自發到自覺的過程進行了反思,并對達到自覺狀態的辯證思維的基本形式、基本規律和方法進行系統探討。反思的一大重要成果,便是提出了“化理論為方法”。“理論”主要指的是哲學理論,還包括其他各種理論;而“方法”則指哲學方法、邏輯方法與具體科學方法。“化理論為方法”就是要將哲學理論化為具有普遍意義的思想方法、將邏輯學理論化為邏輯學方法、將具體科學的理論化為具體的研究方法、思維方法。
第二,闡明了以“類”“故”“理”為骨架的邏輯范疇體系的主要范疇及其展開。在馮契看來,邏輯范疇具有辯證的本性與特點。邏輯范疇既是客觀世界的真實反映,又是人類探索外部世界與自我的階段性認識成果,因而其發展變化具有歷史性和辯證性特征。邏輯是認識的總結,考察范疇及其推移就不能不涉及認識的辯證運動。認識的辯證運動與范疇的辯證發展活動具有相同的特征,即二者都是由淺入深、由表及里、由外入內的過程。而以“類”“故”“理”為骨架的邏輯范疇體系的主要范疇,最生動地展現了邏輯思維的辯證運動,因而,馮契對之進行了深入考察。“類”范疇包括的次級范疇:同一和差異,個別、特殊和一般,整體和部分,質和量,類和關系。(11)參見《馮契文集》第2卷,第325頁。“故”“理”兩個范疇也都包括了幾對次級范疇,限于篇幅,這里從略。馮契建構的邏輯范疇體系蘊涵了這樣一個基本的觀點:通過“類”“故”“理”等范疇的展開及其辯證運動,邏輯思維能把握“性”與“天道”,也就能把握住具體真理。
第三,概括了辯證邏輯方法論所包含的五個環節。馮契不但將方法界定為“即以客觀現實之道,還治客觀現實之身”,而且把它作為方法論的基本命題。他認為辯證邏輯方法的原則主要是兩條:“一條是分析與綜合的結合,一條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12)同上,第407頁。。馮契在吸收列寧《哲學筆記》所揭示的馬克思《資本論》中兩種分析方法、毛澤東《論持久戰》所揭示的分析和綜合相結合包含的三個環節的基礎上,概括了辯證邏輯一般方法所包含的五個環節:從實際出發,保持觀察的客觀性;從分析和綜合相結合談具體和抽象;歸納和演繹相結合;邏輯方法與歷史方法的一致;理論和實踐的統一。這里有幾點值得指出:其一,馮契率先從列寧、毛澤東著作蘊涵的方法論原理的基礎上概括了辯證邏輯方法論的五個環節或步驟,為人們怎樣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方法的指導。其二,將“從實際出發,保持觀察的客觀性”作為方法的第一個和獨立環節,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立場。其三,第二個環節、第五個環節的創新性——就第二個環節而言,馮契的創新之處在于沒有將抽象與具體視為一種獨立的方法,而是通過分析與綜合的相結合談抽象與具體;就第五個環節而言,馮契不但將這一環節的闡述貫穿于方法的諸環節中,而且把假設和證明與理論和實際統一起來進行論述。
三、梳理與概括了中國古代的自然科學成就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誕生與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總結、概括19世紀西歐的科學技術新成果,尤其與細胞學說的創立、能量守恒與轉化定律的發現、生物進化論的拓展密不可分。恩格斯曾指出:“隨著自然科學領域中每一個劃時代的發現,唯物主義也必然要改變自己的形式”(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4頁。。但長期以來,我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卻忽略乃至缺失對自然科學成就的總結、概括。導致這種局面的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從事哲學研究的學者絕大部分不懂自然科學、沒有能力對當下的自然科學成就進行總結和概括;二是哲學工作者忽視了對中國古代自然科學成就的總結。馮契對這一局面深感憂慮,除了期望哲學工作者鉆研一點自然科學外,還特別注重對中國古代自然科學成就的總結、概括。如前所述,馮契意識到,辯證邏輯在我國古代的較早發展,促進了辯證自然觀的形成和自然科學的發展;形式邏輯雖然僅僅在先秦時期曾經有過短暫的輝煌,但也推動了自然科學的發展;自然科學方法、成就的取得都與運用邏輯學的類、故、理范疇相關。
(一)比類取象、比類運數方法的運用
在馮契看來,任何一門自然科學的發展都會采取“取象”和“運數”兩種方法。前者是定性研究的方法,后者是定量研究的方法。
比類取象是在考察宇宙萬物的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關系時,從考察對象中抽象、概括自身狀態、運動變化的性質“象”即概念或意義符號,然后“比類”即類推到與研究對象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事物身上去,也就是推斷與考察對象相同或相似的對象也會呈現這種狀態或具有這種性質。比類運數是運用數量關系去揭示研究對象的內在本質及其發展規律,并用這種數量關系類推到有相似屬性的對象上去。馮契認為,比類取象和比類運數遵循了墨家學派建構的古典形式邏輯體系“以類取,以類予”原則,也就是按事物間的屬種包含關系進行推導的原則。他指出,在科學發現中比類取象和比類運數不可分割,但在不同的科學中可以有所側重。在醫學、農學領域,科學家們側重于比類取象;而在天文、歷法、音律等領域中科學家們側重于比類運數。
第一,對比類取象方法運用的考察。如對《內經·素問》中比類取象方法的審察。在荀子以前,科學家們在運用墨家的“類”范疇從事科學研究時,總是按照屬種包含層次進行,主張“異類”不比。而《內經·素問》則突破了“異類不比”的類推原則,主張“別異比類”。所謂“別異比類”是一種考察表面類似但實質相異的情況,根據人體各部分之間的內在聯系形成的由此及彼的科學方法。《素問·五藏生成論》以為,各種脈象,醫生可用手指來度量、辨別;而五臟之象可由內臟功能反映在體表的現象來比類推測。馮契認為,《內經》的比類取象更接近于荀子主張的“類”范疇所包含的全面性的要求,體現了辯證邏輯的特征。“《內經》的比類取象的方法實際上要求從普遍聯系中比較各類事物的同和異,從而把握所考察對象的矛盾運動(陰陽消長的變化),以進行正確的推測。這是一種辯證邏輯比較法的運用。”(14)《馮契文集》第8卷,第215-216頁。正是比類取象診斷方法的運用,促進了中醫理論的發展。
第二,對比類運數方法運用的考察。馮契認為,天文、歷法、音律等自然科學研究中的比類則主要是通過度量、運數開展,也就是著重從數量關系去運用“類”范疇。在他看來,中國古代很早就懂得采用律管的長短來決定音律的清濁,因而可以從數量上的比例去規定音律的不同,逐漸形成了“三分損益法”,并用它來說明十二律。又如,一年可以分為四季,四季可以分為十二個月,因而也可以從數量上把握它們,也就是從日夜長短的變化、陰陽寒暑的消長去解釋氣候、季節的變化。《禮記·月令》更是認為十二律可以與十二月相適應,肯定音律和歷法體現了共同的數量關系,它們的“類”可以運數來確定。馮契以為,人們依據這種理論推斷,就會認為天體的運行、自然界萬物的生長、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都與音律和歷法一樣是陰陽對立因素的消長,在數量關系上有共同的秩序。這就是說,“邏輯思維可以從數量關系來刻畫它們。這種刻畫就類似于建立數學模型來解釋現象。所以比類運數的方法就是從數量關系來把握所考察對象的矛盾運動(陰陽消長的變化),形成正確的類概念以規范現象,進行預測”(15)同上,第216-217頁。。
(二)比類取象、比類運數方法的發展
《內經·素問》在運用比類取象的診斷方法時,基本上遵循了形式邏輯以類行之的類推原則;早期天文學、歷法學、音律學等在采用比類運數時也主要遵循了形式邏輯的類概念的要求。而隨著時代的前進,科技的發展,比類取象、比類運數也向前發展了。
第一,比類取象方法的發展。在馮契看來,南北朝后魏時期的賈思勰所著《齊民要術》推進了“比類取象”的定性科學研究方法,奠定了中國古典農學的基礎。這種推進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根據性、能(性質和功能)統一原理對農作物進行分類;二是按照農作物的性能即本質去培植、利用;三是在按照規律培植、利用農作物時,應因時因地制宜。馮契認為,《內經·素問》在運用比類取象這種定性方法診斷病情時,體現了“類”范疇所包含的全面性原理,有了辯證邏輯的特征;而《齊民要術》按照質性和功能結合的定性方法研究農作物的栽培、管理時,已經在嘗試運用邏輯學的“故”范疇,即探尋農作物分類、栽培、管理的根據、理由。(16)同上,第219頁。《齊民要術》中定性方法由“類”入“故”,推進了農業科學和農業生產的發展。
沈括對比類取象方法的推進在于重視運用矛盾分析方法開展科學研究。他綜合運用了形式邏輯方法與辯證邏輯方法,使得“比類取象”與“辯合符驗”兩種科學方法并行不悖。他在重視歸納和演繹相結合、個別與一般相結合的方法的同時,更重視運用矛盾分析法進行科學研究。他通過“陰陽相錯”“律呂相生”的表述方法研究音律,又通過“五運六氣”“濕亦能生金石”的理論來解釋銅的冶煉、鐘乳石、石筍的生成等現象,發明了“隙積術”和“會圓術”,直接體現了數學上的辯證思維。作為“堆垛術”早期形態的“隙積術”具有用連續模型來處理離散問題的理念,以實代虛,將“虛隙”化為實體來計算。而“會圓術”則發展了劉徽的割圓術中包含的以直弦代替曲弧的思想,體現了分與合的辯證統一。(17)參見《馮契文集》第6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90-92頁。馮契斷言,這些都是沈括靈活運用矛盾分析法進行科學研究的明證。
第二,比類運數方法的發展。在馮契看來,魏晉時期著名數學家劉徽在運用“比類運數”開展研究時,既像以往的科學家遵循了形式邏輯的規則、規律,又揭示了其中的辯證法因素。劉徽所著《〈九章算術〉注》中的辯證法因素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它用“得失相反”去理解正負的涵義,揭示了正和負的對立統一。其二,它首倡的計算圓周率的割圓術所用的極限方法也體現了對立面的統一,即直線和曲線、有限與無限的對立統一,包含了微積分思想的萌芽。其三,它關于幾何量的計算理論同樣體現了形與數、幾何學與代數學的對立統一,蘊涵了解析幾何的萌芽。馮契斷言,這是以《〈九章算術〉注》為代表的中國古典數學理論與歐幾里得幾何學的重大差別:前者不但遵守形式邏輯的規則、規律,更揭示數學理論中的辯證特點,而后者強調依據嚴密的公理系統推導,僅僅遵循形式邏輯的規則、規律。(18)參見《馮契文集》第8卷,第218頁。
(三)實驗手段的設計、運用
馮契認為,沈括在《夢溪筆談》中所總結、運用的科學方法達到了中國古代科學的最高峰。他不但十分重視實際情況的調查,而且很重視設計實驗手段,期望在人為控制的條件下獲得準確的事實和數據。他設計了聲音的共振實驗來驗證共振理論。實驗過程為,先把琴瑟的弦都調好,將聲音調成和諧,然后剪小紙人置于一根弦上,敲打這根弦的“應弦”,小紙人就跳動;而敲打其他弦時小紙人不跳動。這一簡單實驗驗證了“同聲相應”的共振原理。(19)參見《馮契文集》第6卷,第87頁。他還運用渾天儀數年如一日地觀察天象,設計了“分層筑堰”的實驗進行地勢測量,設計了凹面鏡成像實驗等等。這些實驗都力圖取得大量、真實的數據,以便從中概括規律性的知識,以指導工農業生產,體現了求真務實的精神。有學者指出沈括從事科學研究的方法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是“驗跡原理”。“跡”是事物的形跡、現象;“原”為動詞,即考察、辨析;“理”則是事物內在的本質和發展規律。因而“驗跡原理”就是通過對事物形跡和現象的檢驗,以便考察和把握事物內在的本質和發展規律。(20)參見周瀚光:《中國古代科學方法研究》,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1992年,第57-58頁。而要檢驗、驗證,除了觀察外,只能依靠設計實驗手段。馮契確信,沈括在科學研究中運用的“驗跡原理”方法的“原其理”,強調把握事物的內在本質和發展規律,實際上已涉及邏輯學的“理”范疇。
在馮契看來,近代實驗科學包含了兩個重要內容:一是運用實驗手段,在人為控制條件下進行觀察,掌握大量可靠的數據。二是用理論思維的方法提出假設,建立數學公式(模型)進行嚴密的推導、論證,再設計實驗進行驗證。(21)參見《馮契文集》第8卷,第225頁。馮契認為沈括將實驗手段運用于科學研究,由于沒有滿足近代實驗科學的第二條要求,因而不能稱為實驗科學,但已非常接近。
馮契認識到盡管我國古代的科學技術發展到明清之際時,在實驗手段、考據等方面已接近近代實驗科學和實證科學,但遺憾的是沒有能制訂出近代實驗科學方法。他分析了造成這種局面的兩點原因:一是明清之際的封建統治像巨石般壓在正處于萌芽狀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科技發展因素上,國家沒有為科學發展、工業生產提供必要的支持。二是當時在意識形態領域占統治地位的程朱理學反對人們面向自然,探求自然的奧秘,而是引導學人皓首窮經,空談心性義理,一味地從事“存天理、滅人欲”的道德修養。
馮契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新性探索還體現在建構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美學理論。限于篇幅,只能俟諸專文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