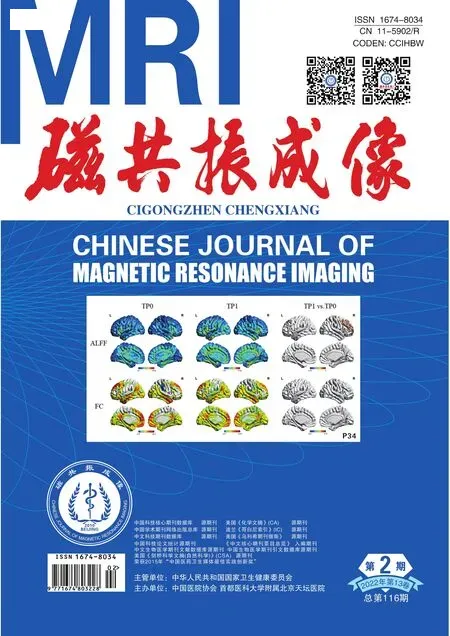心臟磁共振在肥厚型心肌病預后評估及危險分層中的應用進展
馮馨儀,張天悅,馮鈺玲,吳興強,李春平,李睿
作者單位:川北醫學院附屬醫院放射科,南充 637007
肥厚型心肌病(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HCM)是最常見的遺傳性原發型心肌病,可引發心率失常、心力衰竭和猝死等系列不良事件。盡管HCM 發生不良事件(如猝死)的概率很小,但卻是青年人(包括競技運動員)猝死的最常見原因。因此及時診斷并準確評估HCM 患者心臟受累程度,對疾病進行危險分層,識別需密切隨訪及強化治療的高危患者尤為重要。心臟磁共振(cardiovascular magnetic resonance,CMR)多參數、多模態成像,能從形態、結構、組織學改變、微觀結構異常等多個方面綜合評估患者心臟受累程度,從而為HCM患者的診斷、危險分層、治療及預后評估提供重要信息。現就CMR在HCM的危險分層及預后評估中的應用進展予以綜述。
1 常規CMR心功能參數與預后的相關性
1.1 左心室室壁厚度與預后
既往的研究發現,HCM室壁增厚程度是發生不良預后的危險因素[1];然而,大多數研究是基于超聲心動圖所測量所得的數據。隨后的研究發現,超聲心動圖可能會錯誤地將室上嵴包括在基底室間隔厚度的測量之中,因此可能會高估HCM 患者的心肌肥厚程度。CMR能更精確測量HCM患者左室壁厚度,并提供最可靠的HCM 表型特征和臨床診斷。Rowin等[2]對1766 名HCM 患者進行隨訪研究后發現左室壁重度肥厚(左室壁厚度≥30 mm)患者的猝死事件發生率高于左室壁輕度肥厚的患者(3.0%/年vs.0.8%/年,P<0.001)。在單純利用室壁厚度評估HCM 患者預后價值的同時,也應考慮左室肥厚背后的病理生理改變對患者預后的影響。
1.2 左心房形態、結構與預后
心房顫動是HCM患者最常見的持續性心律失常,主要與左房擴張和重構有關。房顫可導致患者心功能進行性下降、心力衰竭和全身血栓栓塞風險增加[3]。Maron等[4]發現房顫HCM患者的左房舒張末期容積(left atrial end-diastolic volume,LAEDV)顯著高于無房顫患者和正常對照組,且發生房顫患者的左房射血分數(left atrial ejection fraction,LAEF)百分比低于無房顫患者和對照組;經多變量分析確定LAEF (<38%)、LAEDV (≥118 mL)與房顫發生獨立相關。2014年歐洲心臟病學會指南(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 Guidelines,ESC)認為左房(left atrial,LA)直徑可作為判斷HCM患者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并將其納入HCM患者5年心源性猝死風險的計算公式之中,建議每6~12個月就應該對LA前后直徑>45 mm 的竇性心律患者進行48 小時動態心電圖監測(Ⅱa類)[1]。綜上可知左房的功能、大小和房顫與HCM患者預后密切相關,可用于指導臨床實踐中的風險評估。
1.3 心尖室壁瘤與預后
超聲心動圖是診斷心臟疾病最常用的手段,但由于在心臟三維成像和再現性方面存在局限,它通常難以顯示左心室心尖部位。心臟電影磁共振空間分辨率高,能多維度、多角度成像,在檢測左室心尖室壁瘤(left ventricular apical aneurysm,LVAA)方面明顯優于常規超聲心動圖;Yang等[5]對1332例心尖肥厚型HCM (apical 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ApHCM)患者進行了回顧性分析,發現超聲心動圖檢出LVAA 的漏診率為64.5%,且超聲心動圖未檢出的LVAA 多數為小動脈瘤(<20 mm);與無LVAA 的ApHCM 患者相比,伴有LVAA 的ApHCM 患者收縮期左室中部梗阻和心肌延遲強化(late gadolinium enhancement,LGE)的比例以及LGE的范圍均顯著升高(所有P<0.05);除此之外,伴有LVAA 的ApHCM 患者的無事件生存率顯著低于無LVAA的ApHCM患者。Rowin等[6]回顧性分析了2個中心共1940例HCM患者,其中93例伴有LVAA。經過4.4±3.2年以上的隨訪發現伴有LVAA的HCM患者的不良事件發生率是不伴LVAA的HCM患者的3倍(6.4%/年vs.2.0%/年)。
1.4 右心室形態改變與預后
雖然HCM 是最常見的遺傳性原發型心肌病,但其定義和大多數文獻都主要涉及左心室的改變,右心室(right ventricular,RV)的受累情況往往被忽視。既往有研究表明RV 受累與心源性猝死風險增加相關,且與室性心律失常獨立相關[7]。
在Maron等[8]利用CMR研究發現大部分HCM患者都存在RV形態學異常,且RV肥厚呈彌漫性,涉及整個或大部分RV壁,其研究還發現HCM 患者的RV 壁質量指數增加,最大RV 室壁厚度和左室(left ventricular,LV)室壁厚度顯著相關(r2=0.4,P<0.001)。?piewak 等[9]的 研 究 也 發 現RV 肥 厚 與HCM 患 者5 年心源性猝死(sudden cardiac death,SCD)風險之間呈正相關。由于迄今為止研究的RV 肥厚患者數量有限,以及未對使RV 肥厚患者SCD 風險增加的因素進行標準量化評估,RV 肥厚對HCM患者預后影響的相關因素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作為常規CMR參數,心臟形態學改變能為HCM患者提供一定預后信息,特別是在識別心尖室壁瘤方面,因CMR 不受氣體及掃描方向的影響,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但這些常規的CMR參數僅反映了局部的形態學改變,并不能對HCM 的潛在發病機制作出進一步解釋,因此對患者提供的預后價值相對有限。
2 功能改變與預后的相關性
2.1 心肌收縮功能與預后
左心室射血分數(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是目前臨床中最常用的心功能參數之一,其中LVEF<50%是HCM患者發生不良預后的高危因素[10]。但HCM患者心肌肥厚致使心室容量和舒張末期容積進行性下降,同時搏出量也減少,即使終末期患者LVEF 仍可處于正常范圍內,因此利用LVEF判斷HCM患者預后價值有限。
心肌收縮分數(myocardial contraction fraction,MCF)為左心室每搏量與左心室心肌體積之比,可以區分由于高血壓引起的左室心肌病理性肥大的正常受試者(MCF 減少)和左室心肌生理性肥大的運動員(MCF 增加),該指標亦是心血管死亡、心肌梗死、卒中以及控制心血管標準危險因素后新發心力衰竭的獨立預測因子[11]。在有關MCF 與HCM 患者預后的方面,既往的研究發現MCF下降可作為HCM患者不良心血管結局的獨立預測因素[11-12],但大部分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基于幾何假設的超聲心動圖計算所得的數據,其準確性和再現性較差,可使患者嚴重程度被低估,相比之下CMR 能提供更為準確的左室質量的定量評估。Arenja 等[13]納入了60 名HCM 患者,并將這些患者與100 名健康對照者的CMR 檢查結果進行了比較分析,最后發現左室肥厚患者的MCF 平均值顯著降低[(136.3%±24.4%) vs. (80%±20.3%);P<0.05]。
左室整體功能指數(left ventricular global function index,LVGFI)的計算公式為:(LV 每搏量/LV 總容積)×100,其中LV 總容積定義為LV 心腔平均容積[(LV 舒張末期容積+LV收縮末期容積體積)/2]和心肌體積之和。Desai等[14]在2008 年至2015 年間對681 名HCM 患者進行了觀察,對其最終結果研究后發現LVGFI 與LGE 范圍存在相關性,且LVGFI 減低與患者發生主要終點事件相關(P<0.01),除此之外Desai 等還發現LVGFI<37%的患者發生主要終點事件的比例明顯高于LVGFI≥37%的患者(14% vs. 8%)。在Huang 等[15]的研究中也發現LVGFI與LGE范圍呈顯著相關,且LVGFI有助于區分心臟淀粉樣變性和HCM。
目前,LVGFI 和MCF 作為評估左室功能的新參數,不僅可以確定心室肥厚時的心肌功能,還可以在LVEF 保留的條件下為患者預后提供一定信息,但由于基于CMR 的MCF 和LVGFI 對于預后意義的研究尚少,該論點需要更多試驗加以驗證。
2.2 左室流出道梗阻與預后
HCM 左心室的病理性肥厚可使左室流出道(left ventricular outflow tract,LVOT)變窄,變窄的LVOT在收縮期產生高速血流致使二尖瓣前葉前向運動(systolic anterior motion,SAM)進入LVOT,由于二尖瓣前葉與室間隔接觸,最終可誘發LVOT梗阻并導致患者猝死[16]。
心臟磁共振4D血流成像[4D flow MRI (3D phase-contrast MRI)]技術可以評估整個心血管的血流動力學改變,該技術可以將LVOT 三維血流模式可視化,并可量化合并收縮期高速血流的LVOT梗阻。van Ooij等[17]發現HCM患者的心肌細胞外體積分數(extracellular volume fraction,ECV)增加與收縮期LVOT 峰值壓力梯度升高存在顯著相關性(P<0.001)。2014 年ESC 指南認為LVOT 壓力梯度可作為HCM 患者的危險因素,并將其納入HCM 患者5 年心源性猝死風險的計算公式之中[1]。
基于CMR的心肌收縮分數及LVOT壓力梯度等功能學參數能辨別左室的生理性與病理性肥大,且可以識別射血分數保留的高危患者。根據CMR 的功能參數還能準確評估患者疾病的嚴重程度,但是在識別潛在高危患者的方面,還需進一步結合組織學相關檢查。
3 組織學異常與預后的相關性
3.1 CMR延遲強化成像
HCM 患者發生SCD 主要由心律失常導致,而結構異常的心肌則是心律失常的最主要病理學基礎。CMR 延遲強化成像可以在體檢測HCM 患者肥厚心肌中結構異常的替代性纖維化組織,且目前大量研究發現LGE 和心血管死亡率、心力衰竭死亡以及全因死亡密切相關,因此可通過LGE 對疾病進行危險分層[1]。
3.1.1 LGE陽性與預后
Kamp 等[18]的薈萃分析發現LGE 陽性與較高SCD 終點事件率以及全因死亡率有關,在HCM 患者中,LGE 是包括SCD、被終止的SCD 以及植入型心律轉復除顫器(implantable cardioverter-defibrillator,ICD)植入的強預測因子。Hen等[19]納入345 名HCM 患者后發現LGE 陽性[hazard ratio (HR):7.436;95%CI:1.001~55.228,P=0.050]是患者不良預后的獨立預測因子。
3.1.2 LGE的范圍與預后
盡管上述研究提示LGE 陽性可能是HCM 人群SCD 風險評估的標志物,但約半數以上HCM患者會發生心肌LGE,因此LGE的范圍(LGE 占左室百分比)及LGE 質量可能比單獨觀察LGE 陽性更能準確指導臨床實踐。
Chan 等[20]納入了1293 名HCM 患者,在對其他相關疾病變量進行調整后發現LGE 的范圍與SCD 事件風險增加相關,即LGE 范圍每增加10%,SCD 的風險隨之增加1.46 倍(P=0.002);即使在風險較低的患者中,左心室LGE質量百分比≥15%的患者的SCD 事件風險也增加了2 倍。Weng 等[21]的一項納入了2993名HCM患者的薈萃分析也顯示,在調整基線特征后LGE的范圍與患者發生SCD 的風險密切相關(校正后HR:1.36/10%LGE,P=0.005)。Greulich等[22]對220名HCM患者的長期預后研究中發現,LGE 范圍>5%的患者SCD 風險較高,而LGE 陰性或LGE范圍<5%的患者預后良好。在最新的一項研究中Liu等[23]發現,整體LGE范圍每增加10% (校正后HR:1.68,P<0.001)和局部LGE的范圍都與不良預后相關。
Raman等[24]在隨訪時間點前后對其研究所納入的HCM患者進行了兩次CMR檢查。在將兩次CMR檢查結果對比分析后發現LGE 質量從中位數4.98 g 增加到了6.30 g,26%的患者LGE 顯著進展(ΔLGE>4.75 g),LGE的顯著進展與左心室變薄、左室心腔大小增加和收縮功能降低相關,并使后續臨床事件的風險增加了5倍(HR:5.04,P=0.002)。在Dohy等[25]的研究中也發現心肌纖維化的質量與綜合終點事件密切相關(HR:1.005,P=0.51),且與心律失常終點事件相關(HR:1.02,P=0.07)。上述研究揭示了LGE的范圍是SCD事件風險的重要預測因素。
3.1.3 LGE的分布與預后
HCM 患者LGE 通常發生于右室插入點和室壁最肥厚部位。Barbosa等[26]對在其中心接受CMR檢查的HCM患者進行了回顧性分析,并對其LGE 的范圍和分布進行了評估,發現伴有室性心律失常的患者的LGE 范圍更大(7.40±5.3 vs. 3.52±3.0 節段,P=0.007);除此之外,Barbosa 等在分析LGE 的分布位置時,發現了一組致心律失常的節段,分別為心尖、基底下、基底前外側和室間隔中下段,且這組機械應力增加的心肌節段的LGE受累程度與室性心律失常的發生獨立顯著相關。
Li 等[27]在其研究中根據LGE 的位置將HCM 患者分為僅室間隔受累型和室間隔以外受累型,在隨訪結束后發現:室間隔以外受累型患者的心血管死亡率、全因死亡率、心臟移植和SCD 風險要顯著高于僅室間隔受累的患者。除室間隔受累位置外,LGE 分布于其他位置也與不良臨床預后相關,日本的一項前瞻性研究表明,右室插入點以外的LGE 是SCD、持續性室性心動過速和適當ICD干預的獨立預測因子[28]。
以上這些研究表明LGE 的陽性、范圍、質量及分布是獨立于室間隔肥厚等常規危險因素之外的重要預測因子,可為HCM患者的預后提供額外的信息。此外,除了上述常用LGE 指標之外,近年來新興的CMR 紋理分析技術,還能根據LGE 的紋理類型對同等量或位置分布相同的LGE 陽性患者再次細化,從而進行更精準的危險分層[29]。
3.2 T1-mapping、ECV與預后
盡管上述大量研究都表明LGE 是HCM 患者不良預后的獨立預測因子,但臨床中仍有半數LGE陰性的HCM患者無法利用LGE 對疾病進行危險分層。基于CMR 的T1-mapping 成像測量心肌的固有T1 值及ECV 值,可在LGE 之前發現心肌彌漫性間質纖維化。既往的研究發現,即使不存在血流動力學障礙、在LGE 序列中未能檢測出心肌局灶性損傷,T1-mapping 序列上T1延長和ECV也可提示HCM彌漫性心肌纖維化,并與左心室肥厚密切相關[30]。
Li 等[31]對263 例HCM 患者進行了前瞻性隨訪,在28.3±12.1 個月后發現,發生主要終點的患者LGE 范圍更廣、固有T1 值更高、ECV 值范圍更大;在多變量Cox 回歸分析中,ECV 值與主要和次要終點事件獨立相關,且ECV每增加3%,主要終點發生的風險增加1.37 倍(P<0.001)。在Avanesov 等[32]對HCM患者和對照者進行的研究中發現,整體ECV值是SCD風險的預測因子,且整體ECV 值作為單一參數對患者的預后具有出色的預測作用。
4 心肌應變與預后
心肌應變反映了心肌初始形狀的變形能力。位于心內膜與心外膜之間心肌的不同層面存在徑向增厚、圓周旋轉及縱向縮短三種運動方式,且心肌的應變在收縮末期達到峰值。當某位置心肌細胞結構出現異常時,異常心肌細胞的應變與其同節段心肌細胞到達峰值時間將出現差異[33],基于CMR的心肌特征追蹤成像技術(cardiovascular magnetic resonance feature tracking,CMR-FT)可以對心肌應變進行定量測量,且可先于LVEF 發現心室收縮功能障礙[34]。Hinojar 等[35]的研究發現HCM 患者的所有左室應變值均減低,發生主要和次要終點事件患者的所有收縮期左室應變參數均受損,且異常的整體縱向、周向和徑向收縮應變峰值與主要和次要終點事件顯著相關。Wabich 等[36]對其研究中的HCM 病患者進行了經胸超聲心動圖和CMR檢查,最后發現總體縱向應變是發生LGE的預測因子。Li等[37]也發現整體舒張期縱向應變峰值較低的患者發生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風險增大,在調整基線和CMR 變量后,整體舒張期縱向應變峰值仍然是最好的結果預測因子(HR:2.65,95%CI:2.21~11.44,P<0.05)。在Yang 等[38]的研究中還發現右室長軸應變是主要終點事件和次要終點事件的獨立預測因子。
5 不足與展望
目前CMR已經常規應用于臨床HCM患者的疾病診斷、危險分層及預后評估,但也存在掃描時間過長、部分心功能較差患者不能耐受、不能準確測量梗阻及高速血流等缺陷,限制了其應用。在常規CMR電影序列及LGE成像之外,包括T1-mapping、心肌應變等越來越多的特別是在組織學方面的CMR新指標、新參數可為HCM 的預后評估提供更多額外的預后信息。CMR 負荷灌注成像能準確、定量評估HCM 心肌微循環功能障礙,在闡明HCM 的發病機制的同時有望為危險分層提供新的影像學指標。在人工智能方面,Zhang等[39]利用“虛擬強化技術”無創性地獲得了與LGE 等效的“虛擬強化”圖像,且圖像質量高于LGE,這意味著隨著人工智能技術逐漸應用于心血管影像領域以及醫療機構數據共享的趨勢,結合人工智能的CMR 技術將對提高心血管疾病診療效率、精度、優化危險分層及指導臨床決策產生重大影響。Liu 等[23]發現,MYH7 和MYBPC3 基因突變陽性的HCM 患者,LGE 范圍更大,心血管影像與基因組學等多學科的迅速交叉融合,可以幫助我們從多個角度了解與評估疾病的嚴重程度。
綜上所述,CMR多序列、多參數成像,在HCM危險分層及預后評估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隨著CMR 新技術的不斷發展與成熟,CMR將在HCM的危險分層及預后評估方面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
作者利益沖突聲明:全體作者均聲明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