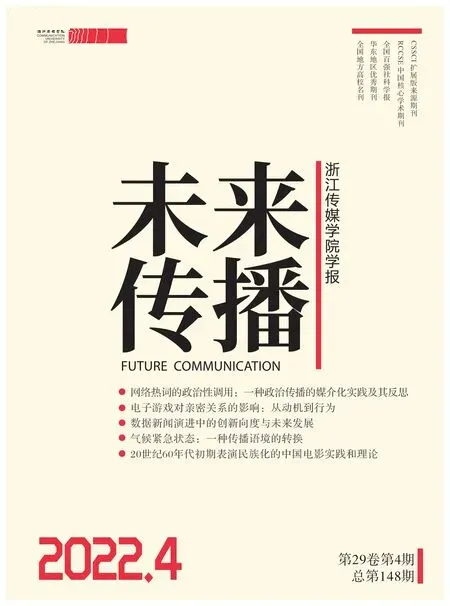20世紀(jì)60年代初期表演民族化的中國(guó)電影實(shí)踐和理論
厲震林
(上海戲劇學(xué)院電影學(xué)院,上海 201112)
自中國(guó)電影發(fā)端以來(lái),民族化一直是電影表演的重要話題以及追求旨趣。電影表演美學(xué)來(lái)源,初為自由吸納,中外“拿來(lái)”。20世紀(jì)30年代,中國(guó)電影漸次成熟,表演需要進(jìn)入美學(xué)階段,面臨著選擇和建設(shè),民族化開始成為問(wèn)題。其時(sh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傳入中國(guó),與現(xiàn)實(shí)政治結(jié)合,逐漸成為主流表演體系,但是,許多優(yōu)秀演員沒(méi)有完全照搬,而是融入民族表演的質(zhì)素,包括有意識(shí)和無(wú)意識(shí)的,中國(guó)文化的“融”特征再次顯現(xiàn)于表演的民族化范疇。1942年,鄭君里寫作《角色的誕生》一書,將斯坦尼體系與中國(guó)電影演員的經(jīng)驗(yàn)結(jié)合起來(lái),也不是硬搬體系,表演觀點(diǎn)包含了袁牧之、趙丹、金山、陶金、舒繡文、張瑞芳、唐叔明、陳凝秋、孫堅(jiān)白(石羽)、高仲實(shí)等演員的表演經(jīng)驗(yàn)以及對(duì)于這些經(jīng)驗(yàn)的學(xué)術(shù)述評(píng)。此有表演民族化的考量,是符合電影國(guó)情的,有表演美學(xué)的推動(dòng)作用。
20世紀(jì)50年代中期,陳荒煤對(duì)于電影民族化問(wèn)題,提出“應(yīng)該很好地來(lái)接受我們中國(guó)民族文化遺產(chǎn),從中國(guó)的戲曲、文學(xué)、繪畫、音樂(lè)、民間藝術(shù)中間吸收我們非常豐富的經(jīng)驗(yàn)和營(yíng)養(yǎng),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qū)﹄娪暗拿褡逍问絾?wèn)題作進(jìn)一步的探討。”[1]作為中國(guó)電影界的領(lǐng)導(dǎo)者和組織者,陳荒煤的言論是官方意志的一種表述,具有戰(zhàn)略性意義。1959年的獻(xiàn)禮片,若干重要影片的民族表演風(fēng)格已較濃郁,反映了中國(guó)人民的生活、心理以及習(xí)慣方式。
20世紀(jì)60年代初期,“民族化”又成為表演美學(xué)的凸顯問(wèn)題,它是基于中蘇關(guān)系破裂以后的國(guó)家自立及其民族自信需求,也是電影藝術(shù)在新中國(guó)深化發(fā)展所驅(qū)動(dòng)的,民族形式在電影,各個(gè)不同層面展開抒情敘事。此時(sh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為政治所累不被尊崇,長(zhǎng)期探索而成的民族表演方法,在表演實(shí)踐和理論中被廣泛重視,產(chǎn)生系列民族特色顯著的影片、表演以及理論,電影民族化漸臻理論化以及體系化。故而,在復(fù)雜艱難的國(guó)內(nèi)外政治和經(jīng)濟(jì)環(huán)境之中,電影表演的民族化問(wèn)題被重新提起,既有政治的訴求,也有藝術(shù)規(guī)律的使然。
一、整體的訴求
影片整體的民族化訴求,是若干導(dǎo)演和演員的美學(xué)理想,從劇本到表演再到影片,是民族意象的全局要求。1959年拍攝的《林則徐》,鄭君里在導(dǎo)演處理中已有民族形式呈現(xiàn)的成功實(shí)踐。林則徐、鄧廷楨在船艙暢敘離別之情,把酒告別之后,采用了李白的《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和王之渙的《登鸛雀樓》的美學(xué)意境,本來(lái)林則徐只是在江邊眺望鄧廷楨的遠(yuǎn)去船帆,后改為登山遠(yuǎn)眺,“林則徐沿著臺(tái)階,一口氣往上奔,奔”,“林則徐的渺小身影(因?yàn)閺倪h(yuǎn)處攝)沿著山脊往上奔,奔,他奔到古堡旁停步,眺望江上——”,“林則徐的渺小的身影又往上奔,奔,……奔上更高更高的山巔——”,“林則徐奔到西松白云間,眺望江上——”,“在曲折如帶的江上,白帆沒(méi)入彎處,漸漸不見——”,“林則徐悵望著,涌上眼淚。”[2]如此處理,古詩(shī)意境濃郁,兩人離情意味深長(zhǎng)。林則徐頂戴花翎被摘以后的一場(chǎng)戲,在表演處理上采用側(cè)寫方法,觀眾無(wú)法看見林則徐的面容,在氣氛的烘托之中,會(huì)有自由的想象。在此過(guò)程中,趙丹的表演始終是背影和側(cè)影,閉著眼睛沒(méi)有回答,此為情緒“靜”極,后與“滿街滿巷”民眾相見,乃為情緒“動(dòng)”極,一靜一動(dòng),有懸念有跌宕,余味無(wú)窮,深得中國(guó)美學(xué)神韻。趙丹在《林則徐》表演設(shè)計(jì)中的“六筆”,如同中國(guó)畫,表演“用筆”或飄逸、或平易、或潑、或爆、或舒,“這是我在表演風(fēng)格上力求做到民族化的一點(diǎn)嘗試”。[3]
同年拍攝的《林家鋪?zhàn)印芬灿姓w民族意象探索,江南地區(qū)特有的風(fēng)景風(fēng)俗、人情世故,謝添飾演主角的民族手法演繹,是中國(guó)氣派的美學(xué)格式。謝添表演重視角色外部性格體現(xiàn),但是,又很好地將設(shè)計(jì)痕跡消彌,有機(jī)地融入人物行為之中,在舉重若輕中呈現(xiàn)一種表演味道,故而林老板的角色氣質(zhì),是謝添專有的,其民族表演的味道儼然。
20世紀(jì)60年代初期,在此基礎(chǔ)之上,又出現(xiàn)了系列民族風(fēng)格典范影片以及表演。1961年,鄭君里在《林則徐》之后,又推出一部歌頌新人和新農(nóng)村的影片《枯木逢春》,是一部民族形式風(fēng)情萬(wàn)種的影片。影片開頭,是余紅仙演唱的毛澤東詩(shī)詞評(píng)彈《送瘟神》,采用橫移鏡頭方式,將濃郁詩(shī)情集中于一個(gè)鏡頭之中,又保持詩(shī)詞韻律的一氣呵成。詩(shī)詞的上半闋,是舊中國(guó)的悲慘情景;詩(shī)詞的下半闋,是新中國(guó)的歡快氣象。上述畫面內(nèi)容雖然變化多端,但是,在橫移鏡頭中卻交織在一起,故而也是統(tǒng)一的,如同古典繪畫的長(zhǎng)卷形式,在視點(diǎn)橫移中展現(xiàn)廣闊的內(nèi)容。在民族音樂(lè)“化用”中,民歌的畫外伴唱借鑒的是戲曲的“幫腔”以及“叫頭”唱法,諸如“走啊——”的“叫頭”高亢唱聲。
在藝術(shù)處理上,鄭君里提出“三破”的美學(xué)思想:破公式老套、破自然照相、破舞臺(tái)習(xí)氣。影片中,借用了戲曲《梁山泊與祝英臺(tái)》的“十八相送”和“回十八”的表演方法。冬哥和苦妹子闊別十年之后邂逅重逢,冬哥帶著苦妹子去見方媽媽,在原來(lái)話劇中是暗寫的,電影中則正面表現(xiàn),而且,要讓十年相思之情淋漓盡致地表現(xiàn)出來(lái),故而讓他們奔跑在廣闊的田園景色中,魚塘漁船點(diǎn)點(diǎn),“撒開百里羅紗帳,鎖住魚兒千萬(wàn)條”;稻浪滾滾,拖拉機(jī)在馳騁。“回十八”與此景色相同,拍攝角度也是一樣,金黃色的稻田、白茫茫的魚塘,長(zhǎng)堤楊柳依依、蓮池波平如鏡,但是,苦妹子心境迥異,身邊已經(jīng)沒(méi)有冬哥。用一種景同情異的方法,突出苦妹子渴望治好血吸蟲病的愿望。
《枯木逢春》在美學(xué)設(shè)計(jì)上是全局呈現(xiàn)民族風(fēng)格的,可以稱為民歌體的時(shí)代頌歌。1960年拍攝的《紅旗譜》,也是充滿民族情感和氣質(zhì)。朱老忠和朱老鞏飾演者崔嵬認(rèn)為:“演員在創(chuàng)造的角色身上,必須洋溢著農(nóng)民的氣質(zhì),民族氣派和民族感情,然后在特定環(huán)境中,使他的性格有所表現(xiàn)和發(fā)展。”[4]崔嵬的表演,在一些重大場(chǎng)面中氣勢(shì)磅礴,猶如大江大河奔騰,而與親人好友相處,卻是粗中有細(xì),如同涓涓細(xì)流,有著民族的表演氣質(zhì),是革命農(nóng)民的“這一個(gè)”,老舍稱贊他的表演“貞如翠竹明于雪,靜似蒼松矯若龍。”[4]值得一提的是,飾演惡霸地主馮蘭池的葛存壯,從青年演到老年,沒(méi)有將反面人物臉譜化,而是演出了這個(gè)北方地主的老謀深算,表面沉穩(wěn)而內(nèi)心陰險(xiǎn),是一個(gè)獨(dú)特的反面人物形象。
《李雙雙》是一幅北方農(nóng)村的生動(dòng)風(fēng)俗畫。張瑞芳在《扮演李雙雙的幾點(diǎn)體會(huì)》一文中寫道:“李準(zhǔn)要把《李雙雙》寫成一部反映農(nóng)村具有一定民族風(fēng)格的喜劇,從現(xiàn)有的文學(xué)劇本來(lái)看,應(yīng)該說(shuō),他已基本上達(dá)到了自己的愿望。”[5]其表演風(fēng)格設(shè)定為“性格的輕喜劇”,即性格矛盾的具有喜劇因素的表演方法。它實(shí)質(zhì)是介于正劇與喜劇之間,對(duì)演員的表演方寸拿捏很有要求,“越是外部戲劇性不強(qiáng)的戲越難演,越是不概念化的人物,尤其是工農(nóng)兵的新人,越容易演走了樣。這個(gè)平平常常的李雙雙,生活在平平常常的生活中,展開矛盾沖突的主要對(duì)象是自己又恨又愛(ài)的丈夫,我感到表演分寸是那么難以掌握,非重即輕,非多即少,平淡和動(dòng)人之間,似乎只差著一線的距離。”[5]張瑞芳采用一種“包圍法”,不是急于如何表演李雙雙,而是從外圍開始一步步地逼近角色,首先是與農(nóng)村社員交朋友同勞動(dòng),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捕捉角色影子;其次是深度閱讀李準(zhǔn)小說(shuō)以及其他作家的相關(guān)農(nóng)村題材小說(shuō),揣摩李準(zhǔn)作品的風(fēng)格,豐富對(duì)農(nóng)村環(huán)境和人物的想像;再次,反復(fù)研習(xí)劇本,使內(nèi)心視象在劇本的字里行間活躍起來(lái)。在此“功課”基礎(chǔ)上,初步確立人物的表演基調(diào)。它的表演方法不是演結(jié)果,而是重過(guò)程的,它是多性格側(cè)面綜合,其中呈現(xiàn)了民族特有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它不是黑白分明的,而是陰陽(yáng)互補(bǔ)。人物關(guān)系是又吵又好、又惱又愛(ài)的微妙關(guān)系,又有時(shí)代的清晰特色,琢磨角色在各種規(guī)定情況下不能不進(jìn)行斗爭(zhēng)的內(nèi)在原因,故而李雙雙的人物形象,是典型環(huán)境中的典型人物,是頗可考據(jù)的民族人物譜之一。
仲星火飾演的孫喜旺,也是影片整體民族風(fēng)格追求的人物譜之一。仲星火認(rèn)為,孫喜旺這個(gè)人物“既不能令人同情他,也不能使人討厭他”,[6]前者緣于他有小生產(chǎn)者的舊意識(shí),對(duì)新事物不太容易接受,后者則是他有我國(guó)勞動(dòng)人民的勤勞、淳樸和幽默,甚至是可愛(ài)的“赤子之心”,諸如老婆受到表?yè)P(yáng),喜孜孜地哼著梆子腔歸來(lái)報(bào)喜訊;在家煮面條,非要女兒說(shuō)好吃,父女倆為此爭(zhēng)執(zhí)了起來(lái)。“不同情”與“不討厭”之間的把握,是仲星火深入揣摩角色的中心,他需要在廣泛的生活體驗(yàn)和觀察中反復(fù)錘煉和塑形,逐漸確立人物的基調(diào)和色彩。仲星火設(shè)計(jì)若干精準(zhǔn)的動(dòng)作,而不僅僅是語(yǔ)言的魅力,蕩漾著濃郁的民族表演風(fēng)情。另外,仲星火的表演線條流暢,動(dòng)作和情感連接嚴(yán)絲合縫,沒(méi)有漏點(diǎn)和盲點(diǎn),無(wú)論是人物的言、笑、行、動(dòng),都顯得連貫和完整,即使是過(guò)場(chǎng)戲,也賦予人物性格的豐富性和飽滿性。仲星火表演的整體感和微細(xì)節(jié),包含了民族思維和民族美學(xué),“以小概大”以及“以大統(tǒng)小”,人物的性格和情感是飽滿的。他和張瑞芳共同飾演的北方農(nóng)村夫妻,是民族的人物和時(shí)代的畫像,逐漸成為中國(guó)社會(huì)的“公眾人物”,也使整部影片成為共和國(guó)歷史的文化記憶。
二、片段、局部和碎片
除了影片全局的民族意象,還有片段、局部和碎片的表演民族化特色。它雖然不是整體的訴求,卻在各自層面探索民族表演質(zhì)素,甚至在它的帶動(dòng)下擴(kuò)展至影片全域,使影片彌漫一股“國(guó)色天香”。
一是表演類型。《暴風(fēng)驟雨》的角色關(guān)系,是按照中國(guó)傳統(tǒng)美學(xué)方式設(shè)置的,如同戲曲舞臺(tái)的類型人物,善惡分明、黑白清晰,兩個(gè)階級(jí)陣營(yíng)對(duì)壘處于白熱化的狀態(tài)。于洋飾演的肖隊(duì)長(zhǎng)剛毅、深沉和真摯,李百萬(wàn)飾演的貧雇農(nóng)郭全海質(zhì)樸、自然和真實(shí),高保成飾演的雇農(nóng)趙玉林倔強(qiáng)、沉悶和忠誠(chéng),都可以在戲曲角色中確立它的“原型”。演員的外形、服飾、化妝和動(dòng)作設(shè)計(jì),是正反儼然的。《紅色娘子軍》的角色譜系也是如此,陳強(qiáng)飾演的南霸天形象是可以辨識(shí)的,只是他賦予了角色自身的心理邏輯以及由此呈現(xiàn)出來(lái)的反動(dòng)本質(zhì),是一個(gè)真實(shí)的惡霸地主形象。祝希娟飾演的吳瓊花,是一個(gè)成長(zhǎng)型的革命戰(zhàn)士,根正苗紅,形成“女性+成長(zhǎng)型+革命戰(zhàn)士”的角色類型,它需要符合以下的角色結(jié)構(gòu):苦大仇深、幫手指引、迭宕曲折、繼承接班。
上述角色類型,基本可以納入符號(hào)學(xué)家格雷瑪斯創(chuàng)建的“動(dòng)素模型”之中,在六種行動(dòng)素關(guān)系之中,主體/客體、發(fā)出者/接受者、敵手/幫手,這樣的角色及其關(guān)系基本是存在的,演員的表演也是需要按照這樣的“模型”關(guān)系實(shí)施。《暴風(fēng)驟雨》中于洋飾演的肖隊(duì)長(zhǎng)是一個(gè)英雄,他是成熟的主體,具有傳奇色彩、民間印記和純潔品質(zhì),具有一種卡里斯馬典型素質(zhì),有著中心價(jià)值資源的感召力和神圣性。祝希娟飾演的吳瓊花是成長(zhǎng)型的,她經(jīng)歷了兩個(gè)階段,從一個(gè)接受者,即英雄行為的受益者,成長(zhǎng)為一個(gè)發(fā)出者,即一支紅色娘子軍的領(lǐng)導(dǎo)者,也就是說(shuō)從客體變成了主體。她被置于一種力量結(jié)構(gòu)之中以及受其控制和規(guī)范,在與幫手、敵手以及中間人物的相互關(guān)系之中實(shí)現(xiàn)成長(zhǎng)轉(zhuǎn)換,從未完成體走向完成體。
在結(jié)構(gòu)主義力量之中,人物是被規(guī)約的,演員的表演也是被規(guī)約的。在一種類型表演之中,自由發(fā)揮的演繹空間不大,只能是一種局部或者碎片的改造和點(diǎn)綴,表演是可以類型辨識(shí)的,表情、外形、動(dòng)作、念白以及場(chǎng)景調(diào)度有著一種基本規(guī)范,它們可以從中國(guó)傳統(tǒng)藝術(shù)中發(fā)現(xiàn)角色的原型,甚至是一種互文的關(guān)系。青年男女正面人物的小生、花旦原型,花旦之中又可以細(xì)分之,中年女性的青衣原型,剛烈者、魯莽者的凈角原型,反面人物的丑角原型,雖然戲曲舞臺(tái)表演是細(xì)膩以及程式化的,電影表演與此形態(tài)不同,但是,得其神韻和味道,類型角色表演是古風(fēng)儼然的。
二是表演風(fēng)格。從類型到風(fēng)格,它是一個(gè)發(fā)展和提升。同樣一個(gè)類型角色,成熟或者杰出的演員會(huì)有不同的處理方法以及呈現(xiàn)出來(lái)的韻味。在類型電影表演的基礎(chǔ)之上,又豐潤(rùn)和拓展,形成個(gè)性表演特色。一些知名演員憑借豐富表演經(jīng)驗(yàn),以及對(duì)于傳統(tǒng)藝術(shù)的深邃理解,個(gè)人稟賦高超,在新中國(guó)形象創(chuàng)造中凝練或者深化個(gè)人的表演風(fēng)格,頗具表演符號(hào)意義。
謝添在《林家鋪?zhàn)印贰逗楹嘈l(wèi)隊(duì)》等影片的表演中,將復(fù)雜的人物性格,收拾得邏輯清晰,卻又有血有肉、渾然一體。其表演風(fēng)格舉重若輕、揮灑自如、從容不迫、意味濃郁,頗具民族化表演示范層級(jí)。他的表演哲學(xué),可以概括為“寧要真的假,不要假的真;要復(fù)雜的簡(jiǎn)單,不要簡(jiǎn)單的復(fù)雜;既是觀眾心目中所有,又是其他藝術(shù)作品中所無(wú)。”[7]這也體現(xiàn)在他導(dǎo)演的影片表演風(fēng)格中,他認(rèn)為喜劇表演的夸張,并非是過(guò)火的大或快,它的分寸依據(jù)是藝術(shù)的真實(shí)性、人物性格的可能性以及不同的形式風(fēng)格所要求的不同邏輯性,在許多情形下“靜止”“緩慢”“嚴(yán)肅”或“更嚴(yán)肅”等同樣可以構(gòu)成喜劇效果,甚至是更為高級(jí)的美學(xué)形態(tài)。這與謝添的表演風(fēng)格也是相通的,他總是在不動(dòng)聲色之中,從情節(jié)到人物到“味道”,層層遞進(jìn),角色形象至情至性。
在《甲午風(fēng)云》中,李默然的表演凝重深沉,張弛有度,具有一種強(qiáng)烈內(nèi)在的性格以及思想力量。他總結(jié)有“四個(gè)并用”的表演觀念:“演員處理臺(tái)詞要‘潺潺流水’與‘大江東去’并用;演員設(shè)計(jì)動(dòng)作要‘濃墨潑灑’與‘細(xì)描工筆’并用;演員把握和表現(xiàn)人物的情感、情緒要‘異峰突起’與‘綠茵小徑’并用;表演整體上要‘分寸準(zhǔn)確’與‘適度夸張’并用。”[8]在《甲午風(fēng)云》中的表演,已經(jīng)初具“四個(gè)并用”的端倪,他不著眼于一招一式的得失,而是注重整體綜合把握,濃淡相間而又張力充沛。
白楊創(chuàng)造的角色,具有東方女性的溫柔和害羞之美,以及勤勞和忍耐之韌,她的表演風(fēng)格優(yōu)美、自然、恬靜和鮮明。她在《團(tuán)結(jié)起來(lái)到明天》《祝福》《為了和平》《金玉姬》《春滿人間》《冬梅》等影片中的表演,盡管成就不一,但是,人物都是鮮明的,角色的情感和性格邏輯是嚴(yán)絲合縫的,她們因“有脈”故而是“活”的。她談及《祥林嫂》創(chuàng)作時(shí)稱道:“這個(gè)人物的‘脈’線直到現(xiàn)在想起來(lái)也都很清晰,就像有根脈絡(luò)分明的無(wú)形的線串在心頭,也正是這根‘脈’線才串起了角色的形象。”[9]這種尋找和確立“脈”線的方法,頗具民族藝術(shù)的創(chuàng)作方法,在中國(guó)古代文論中闡述詳全,成為角色的命脈。
項(xiàng)堃的表演嚴(yán)謹(jǐn)而又帥氣,這一階段的《紅日》《停戰(zhàn)之后》,仍然不在外形丑化反面人物,而是在靈魂上刻畫其反動(dòng)以及丑惡。《烈火中永生》中的表演稍微有點(diǎn)走形,較多呈現(xiàn)人物猙獰面目。外美內(nèi)丑,在戲曲舞臺(tái)上可以清晰地檢索到它的角色類型以及表演風(fēng)格。
三是表演修辭。在表演以及相關(guān)電影語(yǔ)匯中使用民族風(fēng)格表現(xiàn)手法,包括標(biāo)點(diǎn)符號(hào)式的表演細(xì)節(jié)、其他電影技術(shù)與表演的修辭結(jié)合。項(xiàng)堃每接到一個(gè)角色,對(duì)每一場(chǎng)戲都設(shè)計(jì)了幾種表演方法,作為一種預(yù)案與導(dǎo)演協(xié)商,或者供導(dǎo)演選擇。這里,他常常運(yùn)用一些民族特色的表演手段,諸如《停戰(zhàn)之后》中,為國(guó)民黨代表李國(guó)卿設(shè)計(jì)不少細(xì)節(jié)動(dòng)作,可以藝術(shù)地表現(xiàn)角色內(nèi)心世界,較為突出的是小扇子、小手帕,在不同的情景下會(huì)有獨(dú)特的使用以及相應(yīng)的動(dòng)作。小扇子、小手帕,在戲曲表演中也是常用之物,或表情達(dá)意,或描畫性格,或平添情趣。
為了呈現(xiàn)民族化表演情調(diào),其他電影語(yǔ)匯與之和諧配合。以攝影為例,《枯木逢春》是一種《清明上河圖》長(zhǎng)卷畫式的橫移鏡頭,它沒(méi)有采用好萊塢式的正反打鏡頭語(yǔ)言以及舞臺(tái)式的平鋪直敘,苦妹子從少年到成年的表演,是通過(guò)一個(gè)時(shí)空壓縮的橫移長(zhǎng)鏡頭完成的。《小兵張嘎》與演員表演的民族風(fēng)格相互映照,攝影對(duì)于情緒、意境和造型的營(yíng)造,達(dá)到一種“濃淡疊交而層層相應(yīng),繁簡(jiǎn)交錯(cuò)而輾轉(zhuǎn)相形”的效果,是一種“詩(shī)中有畫、畫中有詩(shī)”的“真、簡(jiǎn)、質(zhì)”的創(chuàng)作構(gòu)思。《早春二月》結(jié)尾的一場(chǎng)戲,披著白紗的陶嵐追趕肖澗秋,越過(guò)籬笆墻,鏡頭跟隨她的跑動(dòng),越搖越高,將人物融入江南景色之中,很好地襯托了演員表演的情緒以及敘事,呈現(xiàn)一種情景交融的藝術(shù)意境。《農(nóng)奴》明確提出向中國(guó)傳統(tǒng)版畫學(xué)習(xí),將表演成為版畫意韻構(gòu)成要素,“運(yùn)用一種有力的版畫式樣的濃重、低沉、粗獷的氣氛為攝影基調(diào),以此貫穿于全片,較為恰當(dāng)?shù)乇磉_(dá)出內(nèi)容和形式的統(tǒng)一效果。”[10]
三、必然與偶然
這一時(shí)期,民族化的電影表演思潮涌現(xiàn),是一種必然與偶然融合的文化現(xiàn)象。必然而言,中國(guó)電影表演自20世紀(jì)30年代初涉美學(xué)層級(jí),民族化即成為一個(gè)話題以及目標(biāo),貫穿于其歷史發(fā)展過(guò)程之中,時(shí)濃時(shí)淡,但是不曾停息。新中國(guó)電影表演發(fā)展已逾十年,文化情緒漸趨平和,民族化又逐成表演探索任務(wù)。偶然而論,中蘇關(guān)系失和波及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劇的中國(guó)地位問(wèn)題,與政治的交合使它無(wú)法繼續(xù)起一種指導(dǎo)作用,回歸民族化從偶然也就轉(zhuǎn)化成為一種必然,是政治的美學(xué)訴求。此為歷史與現(xiàn)實(shí)語(yǔ)境的宏觀闡述,若深化微觀角度分析,也有它的路線和脈絡(luò)。
首先,電影演員的“童年記憶”,許多與傳統(tǒng)藝術(shù)有關(guān),潛移默化以至迷戀至深。藍(lán)馬和石揮均有北京“天橋”觀摩經(jīng)歷,兩位小伙伴放學(xué)以后常去“天橋”游玩,諸種傳統(tǒng)技藝耳熟能詳,爛熟于心,回家以后能夠一一模仿。他們的“天橋”經(jīng)驗(yàn),從藝以后轉(zhuǎn)化成了戲劇電影表演的支點(diǎn)。從某種意義而言,“童年經(jīng)驗(yàn)”也是一種“幼學(xué)”和“童子功”,許多人也許沒(méi)有意識(shí)到它的顯著意義,其實(shí)它已經(jīng)在悄無(wú)聲息中規(guī)范了成年以后的基本審美甚至職業(yè)發(fā)展路線,它可能是補(bǔ)償性質(zhì)的,也可能是延伸功能的。如他們一般的優(yōu)秀演員,一以貫之將“童年經(jīng)驗(yàn)”“活學(xué)活用”,至20世紀(jì)60年代已是爐火純青,在電影表演中將童年所得化為自身藝術(shù)血肉,在呈現(xiàn)中了無(wú)痕跡,卻又是滿滿的民族表演神韻,意境和美感兼有。
其次,從藝之初所學(xué)的傳統(tǒng)藝術(shù)樣式,在轉(zhuǎn)行表演以后發(fā)揮它的美學(xué)基礎(chǔ)作用。趙丹就是一個(gè)重要的案例。他是學(xué)習(xí)繪畫出身,因?yàn)槊詰俦硌荻男校牵L畫訓(xùn)練以及實(shí)踐的美學(xué)原理,始終是他表演的靈感之一。他稱道:“繪畫對(duì)我是種無(wú)形的熏陶,它會(huì)帶來(lái)書卷氣、古典的美——心境、思想情操的高尚——自我感覺(jué)似乎也是畫中人了。”[11]前所涉及的《林則徐》,他是運(yùn)用中國(guó)寫意畫風(fēng)格表演的,是一種概括性較強(qiáng)的大落筆手法,共有六個(gè)筆觸。在《聶耳》中,表演是形似還是神似,他借鑒的是梅瞿山的畫法,大舍大取,不拘泥于形似,而是追求意境、精神和風(fēng)骨的神似。
最后,演員對(duì)于傳統(tǒng)藝術(shù)自覺(jué)或者不自覺(jué)的喜愛(ài)。上述的“童年經(jīng)驗(yàn)”和藝術(shù)履歷并非人人可有,它有著一定的偶然性質(zhì),但是,愛(ài)好傳統(tǒng)藝術(shù)卻是電影演員成長(zhǎng)的一種必然,許多演員自覺(jué)向戲曲、繪畫、書法等索取美學(xué)營(yíng)養(yǎng),將其納入電影表演的“主餐”之中,使“營(yíng)養(yǎng)”更加豐沛和科學(xué)。崔嵬一直非常愛(ài)好京劇以及地方戲曲,具有良好的修養(yǎng)、知識(shí)以及獨(dú)特的見解,并將之化為自身的表演韻味,他的表演總有一種中國(guó)風(fēng)格和氣派,在《宋景詩(shī)》《海魂》《紅旗譜》《老兵新傳》中,均有顯著的表現(xiàn),而且,它是渾然一體的,似乎沒(méi)有什么技巧,卻又充滿一種張力和節(jié)奏。正是傳統(tǒng)藝術(shù)的深深浸染,電影演員更為深入地體驗(yàn)表演美學(xué)的“豐與神”,才有濃郁的民族表演“神采、形采”,并在創(chuàng)造過(guò)程中大量借助它的技法。研習(xí)傳統(tǒng)藝術(shù),已經(jīng)成為許多電影演員的生活方式,并進(jìn)而啟悟他們的表演美學(xué)。
四、再探民族化表演理論
在民族化的探索與追求之中,從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到理論,最終達(dá)至民族表演體系建設(shè)。電影表演界從來(lái)未曾停止過(guò)對(duì)于民族表演理論的思考,只是呈現(xiàn)形態(tài)有異,或自成美學(xué)體系,或目標(biāo)大于實(shí)踐,或感悟靈性表述,或碎片式管見,卻是多從不同場(chǎng)域、方位和層級(jí)追尋民族表演體系。他們從表演實(shí)戰(zhàn)而來(lái),而非純粹的理論演繹,故而其理論有案例的支撐,又可以再回到實(shí)踐,在一種互動(dòng)關(guān)系之中,這些民族表演理論是充滿實(shí)踐精神的,也是具有美學(xué)智慧的。
1961年,白楊在《文匯報(bào)》發(fā)表《電影表演技藝漫筆》一文,是當(dāng)年全國(guó)故事片創(chuàng)作會(huì)議的大會(huì)發(fā)言稿,系統(tǒng)提出“三忌八訣”的表演體系。她雖然沒(méi)有提出民族表演體系概念,卻可以說(shuō)是它的通俗版,具有理論和實(shí)踐的雙重意義。所謂“三忌”,一忌“簡(jiǎn)單化”,技術(shù)手段不能單一,力避人物表現(xiàn)非常正確,卻不生動(dòng)、可愛(ài)、感人,“往往在一些概念、片面的認(rèn)識(shí)理解上下功夫,演員盡管用了很大的勁,演出來(lái)的戲是勁有余,而味不足,或者說(shuō)只有勁,沒(méi)有味,人物顯得單調(diào)平板”;[9](2-3)二忌“老套化”,總是按照一個(gè)固定的格式表演某一類型的角色,需要在千差萬(wàn)別中去下功夫,膽敢創(chuàng)新,根據(jù)不同人物和情景用心體會(huì),化身化形,繪影繪聲,才能別出心裁以及新穎地、有力地吸引觀眾;三忌“吃力化”,一個(gè)鏡頭里想功德圓滿,什么都想擠上去、裝進(jìn)去,結(jié)果演得非常吃力,觀眾看得非常吃力,“電影演員與觀眾之間,存在著表演與欣賞的合作關(guān)系,表演‘吃力化’,觀眾就有‘吃力感’,表演如有‘舉重若輕’恰切之妙,觀眾隨之也會(huì)得到美妙的欣賞愉悅。”[9](7-8)
“八訣”,則是包括品、熟、脈、穩(wěn)、神、趣、明、化。品,指人品和品質(zhì)。演員塑造角色性格,掌握人品乃是基礎(chǔ),否則人物身份和氣質(zhì)就會(huì)遜色,品是一項(xiàng)揣摩的基本功。熟,對(duì)角色的熟知,只有在精熟之下,所立的意才會(huì)造成刻畫人物的成功。脈,厘清角色的脈和整個(gè)影片的脈,表演才能脈絡(luò)分明,產(chǎn)生角色特有的姿態(tài)、聲調(diào)、節(jié)奏、動(dòng)向。穩(wěn),胸?zé)o浮念,一心專注其人其事,身入其境,要有一定之規(guī)。神,即是“像極了”,可以逼真到比真人更真、更美以及更有生命力,形神兼?zhèn)洌紊窈弦弧Hぃ屑纱舭澹毷侨ぶ掳蝗唬ぁ⒚钊ぁ⒆救ぁ⑸袢ぁ⒚廊つ酥裂ぁC鳎蟊硌菝魑鸵锥耙粌上虑〉胶锰幍膭?dòng)作,就能說(shuō)明不少內(nèi)容,看上去準(zhǔn)確、生動(dòng)、鮮明,即恰切而又有味道,既是‘寓意深遠(yuǎn)’而又‘明白如話’,這都是演員所要努力追求的。”[9](21-22)化,即將主題思想、人物關(guān)系、情節(jié)故事、藝術(shù)技巧同臻化境,身入化境,化得來(lái)、化得去,拿得起、放得下,放得開、收得住,意造其妙,出神入化。
上述“三忌八訣”,是白楊的經(jīng)驗(yàn)所得以及理論思考,較為系統(tǒng)地闡述了中國(guó)格式的表演美學(xué)體系,包含有豐沛的民族表演思想,它與戲曲表演有著文化血緣的關(guān)聯(lián),又有電影表演的特殊規(guī)律,是民族電影表演體系的初步成果。它是形而下和形而上的有機(jī)結(jié)合,它是應(yīng)用形態(tài)的,從實(shí)踐而來(lái)又可以指導(dǎo)和反饋于實(shí)踐;它是科學(xué)形態(tài)的,是高度概括的美學(xué)結(jié)論,是具有學(xué)術(shù)價(jià)值的。
趙丹是民族表演體系的倡導(dǎo)者和實(shí)踐者,其理論成果主要體現(xiàn)在《林則徐形象的創(chuàng)造》《聶耳形象的創(chuàng)造及其他》《魯迅形象塑造的初步探索》《爐邊夜話》等公開發(fā)表的系列論文之中。它們大多是創(chuàng)作談,對(duì)于一部影片的表演總結(jié)是系統(tǒng)而深刻的,其表演民族化的追求是自覺(jué)的,在實(shí)踐中的創(chuàng)作以及創(chuàng)新是有規(guī)有矩的,有問(wèn)題的出發(fā)點(diǎn)、目標(biāo)、方法以及步驟,它有著學(xué)術(shù)的嚴(yán)謹(jǐn)以及美學(xué)創(chuàng)新精神,是中國(guó)文論的表演演繹,并逐漸凝聚為中國(guó)民族表演美學(xué)。局限于創(chuàng)作談,缺乏宏觀分析場(chǎng)域,故而它是碎片化的,片片閃光卻尚未形成整體的理論光芒。趙丹的“中國(guó)民族的表演藝術(shù)體系”,其系統(tǒng)闡述是他1979年在上海戲劇學(xué)院的講課記錄,后以《趙丹自述》成書出版。它所涉及的內(nèi)容以及案例,主要是他“文革”前十七年的表演履歷以及美學(xué)體會(huì),其基本思考與20世紀(jì)60年代初期的表演創(chuàng)作密切相關(guān),故而它的理論成果,緣自于這一時(shí)期的思想雛形。其主要意旨如下:
其一,局限與無(wú)限的辯證關(guān)系。任何演員都有其局限,但局限是相對(duì)的,關(guān)鍵是克服局限并努力形成特點(diǎn),許多杰出的演員都有此經(jīng)歷,如周信芳、裘盛戎、程硯秋。“一個(gè)演員一生是否都能演各種各樣的角色,不見得。魏鶴齡,總理是夸他的,可也發(fā)現(xiàn)他演知識(shí)分子就不大像。假如我演農(nóng)民就很費(fèi)力,總是有局限的,否則是愚蠢的無(wú)效勞動(dòng)。所以我們要善于藏拙,又要會(huì)運(yùn)用自己力量,但要用得是地方,從頭到尾用力,那等于不用力。演技就在不瘟不火,能盡量擴(kuò)大無(wú)限,可塑性就強(qiáng)些。就如戲法人人會(huì)變,各有巧妙不同,優(yōu)點(diǎn)如不發(fā)展,還可能轉(zhuǎn)化為缺點(diǎn)。經(jīng)過(guò)努力缺點(diǎn)也可能轉(zhuǎn)化為優(yōu)點(diǎn),任何事物都可轉(zhuǎn)化,好當(dāng)中包含壞,壞當(dāng)中又包含好,這個(gè)辯證規(guī)律,生活如此,掌握技巧也是如此。”[11]
其二,個(gè)性與共性的辯證關(guān)系。個(gè)性包含著共性,沒(méi)有個(gè)性就沒(méi)有藝術(shù),而民族化是大眾化、生活深化以及現(xiàn)實(shí)主義創(chuàng)作方法深化的問(wèn)題。中國(guó)電影表演一直沒(méi)有跳出“話劇帶電”的窠臼,導(dǎo)演的手法是場(chǎng)景轉(zhuǎn)換,而非畫面閃現(xiàn),演員基本是舞臺(tái)表演的感覺(jué),還沒(méi)有形成電影表演的真正特性。“至于咱們的電影演員(當(dāng)然包括我自己在內(nèi)),至今也仍然沒(méi)有真正懂得電影與舞臺(tái)的表演技巧之區(qū)別究竟在哪兒,最多不過(guò)只懂得比舞臺(tái)稍微收斂點(diǎn)罷了”,“事實(shí)上,國(guó)外的許多卓有成就的電影演員,絕大多數(shù)都是來(lái)自舞臺(tái)的。話又要轉(zhuǎn)過(guò)頭來(lái)說(shuō)。這是因?yàn)閯e人的話劇歷史,早就有一個(gè)堅(jiān)實(shí)的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創(chuàng)作基礎(chǔ)。即:以體驗(yàn)為主導(dǎo)的,追求生活化,真實(shí)感,崇尚自然的表演藝術(shù)的傳統(tǒng)。從表演藝術(shù)的歷史淵源講,咱們的話劇表演早在20世紀(jì)30年代起就存在著一些虛假的、做作的、過(guò)火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沒(méi)有生命的雜質(zhì),還一直未能得到澄清。”[11](72)電影表演,與其他表演樣式存在共性,但自身的個(gè)性也是顯著的,它還需要彰顯民族化的氣質(zhì),是一種民族氣派的電影表演個(gè)性。
其三,體驗(yàn)與體現(xiàn)的辯證關(guān)系。它涉及“從自我出發(fā)”和“從角色出發(fā)”的關(guān)系問(wèn)題,兩者何者為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體驗(yàn)派”,它所針對(duì)的是當(dāng)時(shí)俄國(guó)舞臺(tái)上的形式主義風(fēng)潮,諸如展覽性的、虛假的、過(guò)火的、模擬的,它是從角色出發(fā)所致,它缺少一個(gè)“自我”過(guò)程,即體驗(yàn)的過(guò)程。這個(gè)“自我”是需要出發(fā)的,即再創(chuàng)造出角色,否則容易陷入自我擴(kuò)張、展示和展覽,需要“生活于角色,或叫做體驗(yàn)角色”,“同時(shí)通過(guò)自己的五官形體,生發(fā)出角色的形象來(lái)”,[12](74)它是“內(nèi)部技巧”與“外部技巧”的矛盾統(tǒng)一,是一種體驗(yàn)與體現(xiàn)的辯證關(guān)系以及演員與角色的關(guān)系。
體驗(yàn)與體現(xiàn)的關(guān)系,“體現(xiàn)的自身雖有其獨(dú)立的規(guī)律性,但一切高乘的體現(xiàn)則又必來(lái)自深刻的體驗(yàn)。所以說(shuō)體現(xiàn)的本身又包含著體驗(yàn)的成分!它們的關(guān)系是雞生蛋,蛋生雞。是相輔相成互為因果的關(guān)系。所以斯坦尼說(shuō)每一次的演出實(shí)踐,就是新的體驗(yàn)的開始。又說(shuō):不要去表現(xiàn),而要時(shí)刻在體驗(yàn)中——這就是事物的辯證法則。”[11](80-81)在中國(guó)電影演員中,趙丹是具有理論思考習(xí)慣的表演藝術(shù)家,在理論與實(shí)踐之間游刃有余,互有補(bǔ)益、共生共榮。他提出“中國(guó)民族的表演藝術(shù)體系”,雖然在理論上尚未形成完整體系,但是,他以自己的杰出表演作品,做了生動(dòng)的美學(xué)闡述以及形象注釋。
五、結(jié) 語(yǔ)
20世紀(jì)60年代初期,民族化成為電影表演的重要論題,是政治、歷史和美學(xué)“合力”作用的結(jié)果,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有效地推進(jìn)了中國(guó)電影民族表演體系建設(shè),從影片的整體、語(yǔ)匯至理論建設(shè),均有良好成績(jī),產(chǎn)生了系列的表演、影片和理論成果,是中國(guó)電影史以及表演史的珍貴遺存。它具有承上啟下的意義,是歷史的再度深化,又鋪墊了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lái)的表演民族化構(gòu)型。它既是重要的表演文獻(xiàn),又啟悟了美學(xué)原理,民族化是中國(guó)電影表演美學(xué)的底色,它并非閉環(huán)的,而是開放的,需要“融入”外來(lái)的藝術(shù)因子,在“融入”中使民族化更加具有現(xiàn)代感,盡管這個(gè)“融入”有成功也有失敗。電影表演民族化,已然形成深邃的美學(xué)文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