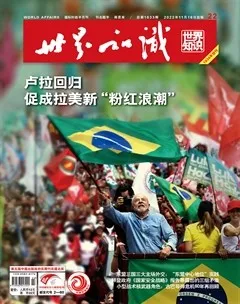“減產風波”暴露沙特美國盟友關系走弱
丁隆

2022年7月16日,美國總統拜登訪問沙特,并出席了在該國吉達舉行的由海灣合作委員會成員國及埃及、約旦、伊拉克領導人參加的“安全與發展”峰會。
2022年10月5日,以沙特阿拉伯為首的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與非歐佩克產油國(歐佩克+)第33次部長級會議決定,從2022年11月起,將原油總產量日均下調200萬桶。消息公布后,美國表示失望。在此之前,美國政府一直在向沙特等主要產油國政府施壓,阻止其減產原油。10月11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柯比表示,白宮正在重新評估美國與沙特的關系。“歐佩克+”產油國聯盟的大幅減產,引爆了沙特與美國之間積累已久的矛盾,此番互不相讓的陣勢在雙方數十年的盟友關系中實屬罕見。然而,沙美矛盾絕非“產量之爭”那么簡單。
追根溯源,當前沙美關系深陷危機是世界能源市場巨變所致。近年來,世界石油市場出現三個新趨勢。一是“頁巖油革命”后,美國實現能源獨立,并一躍成為世界主要石油出口國之一,對中東地區的石油依賴顯著下降。目前沙特約75%的原油銷往中國等亞洲市場。二是隨著頁巖油和替代能源搶奪市場份額,以沙特為首的歐佩克影響國際油價的能力顯著下降。歐佩克選擇擴大影響力,與俄羅斯等非歐佩克產油國合作維持國際油價。2016年,“歐佩克+”機制建立,它使沙特和俄羅斯的利益被深度綁定,即便2022年2月烏克蘭危機升級也無法撼動這一共同體。三是美國作為石油生產和消費大國,對國際油價漲跌態度矛盾。對美國而言,若國際油價過低會打擊其頁巖油產業,但油價過高又會推高其國內通貨膨脹率。因此,無論國際油價處于高位或低位,美國都會根據本國即時利益要求沙特增產或減產石油。這些混亂的信號讓沙特無所適從,雙方在油價方面形成利益沖突。同時,美國意圖左右沙特石油產量,也有將其視為影響中期選舉及制裁俄羅斯工具的因素,實際上已將油價政治化。這都提高了沙特利用石油反制美國的能力。
此番沙特做出減產決定固然是基于其對石油市場供求關系的判斷,但也難以讓人相信其中沒有政治考量。歷史上,沙特在石油產量方面配合美國的例子并不鮮見。此次宣布減產,倒像是在美國中期選舉前對拜登所領導的民主黨政府實施的“精準打擊”。因此,與其說當前沙美關系是忽然交惡,不如說是雙方積累已久的矛盾被激化。
令沙美關系雪上加霜的是雙方盟友關系中的安全支柱也開始動搖。能源獨立使中東地區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下降,并使其持續在該地區實施戰略收縮,明顯懈怠了對沙特等中東盟友的安全責任。自2009年奧巴馬政府上臺以來,美國歷屆政府持續從中東撤軍,現任拜登政府則將恢復伊朗核協議作為其中東政策的優先事項,并將對沙特構成切實安全威脅的也門胡塞武裝移出恐怖組織名單。因此,沙美“以石油換安全”的對價關系被顯著削弱。
長期以來,由于沙美兩國在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等方面“格格不入”,雙方擱置意識形態差異,在利益交換的基礎上建立盟友關系。美國保守派學者柯克帕特里克曾表示,中東現行制度符合美國利益,在中東推進“民主和人權”會使美國陷入被動。因此,美國的中東外交主要遵循“只談利益”的現實主義。但是,在2001年9.11事件發生后,美國推出“大中東倡議”,企圖用“美式民主”改造中東國家。然而,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深陷戰爭泥潭、伊斯蘭主義政黨打斷“民主化進程”上臺執政等現實,迫使其再次回歸“柯克帕特里克主義”。
但是,2021年拜登政府上臺后,顛覆了美國中東外交的“潛規則”,重拾“價值觀外交”。拜登政府借2018年沙特記者卡舒吉遇害事件向沙特施壓,甚至以干涉其王位繼承等重大而敏感的內政問題相威脅,這觸及了后者最敏感的神經。此外,沙特的民生水平一直在中東地區名列前茅。近年來,沙特還實施了女性賦權與外籍勞工權益保障等多項社會文化領域改革,美國卻對其取得的成績視而不見,一直揪著所謂“人權問題”不放。同時,美國在中東“人權話事人”的身份并不被地區國家認可,因其本身就是伊拉克、阿富汗等國人道主義危機的制造者。因此,拜登雖在烏克蘭危機升級后于2022年7月親赴沙特訪問,卻未能阻止沙美關系的繼續惡化。
近些年,隨著沙特年輕一代領導層陸續掌權,并在2016年推出“2030愿景”規劃,該國開啟歷史性的國家全面轉型。身為“80后”的沙特王儲默罕默德胸懷“大國夢”,立下宏志要將沙特打造成全球性大國。國族主義已成為沙特官方意識形態和主流敘事,這意味著沙特將不再一味追隨大國,而是要充分發揮本國能源稟賦,成為積極參與全球事務的大國。烏克蘭危機升級后,沙特石油資源的重要性再次凸顯,國際油價上漲使沙特擺脫了經濟困境。2022年沙特經濟增長率預計將超過8%,領跑全球。同時,沙特經濟總量也有望突破一萬億美元,成為中東與非洲地區首個邁進“萬億俱樂部”的經濟體,這給了沙特與美國叫板的底氣。同時,沙特的外交政策也逐漸體現出靈活性與務實性,因應美國的中東戰略調整,與伊朗、土耳其等“戰略敵手”緩和了關系。沙特在大國相爭中采取對沖戰略拓展外交空間,并不顧美國阻撓,積極與中國、俄羅斯等國發展伙伴關系,表現出強烈的戰略自主意識。美國顯然并未充分理解沙特正在經歷的“時代之變”,仍對沙特采取頤指氣使的傳統態度,便難免碰釘子。
“減產風波”揭開了沙美兩國矛盾的一角,暴露以沙美關系為代表的“美國—中東國家盟友體系”已顯著走弱。然而對沙美矛盾也不能過分夸大。“安全靠美國、經濟靠中國、能源靠俄羅斯”是沙特與大國關系的基本格局,也將在較長時期內被延續。在美國調整其中東政策和沙特國家轉型的背景下,兩國關系目前雖呈現出對抗多于合作的特征,但相互依賴性仍然存在。除石油與安全外,沙美合作還有新能源、科技、金融投資等多重維度。此外,五年前沙美關系的熱絡讓人記憶猶新。2017年,美國特朗普政府上臺后將出訪的第一站選在沙特,并出席“三合一”的阿拉伯伊斯蘭國家—美國峰會;2018年,沙特王儲默罕穆德也曾對美國進行為期21天的超長訪問。這些均顯示出沙美關系的特殊性。沙美關系與美國國內政治相關性較強,因此雙方關系仍存在被修復的可能,而沙特作為全球性能源大國,也將繼續在美國的中東乃至全球戰略中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