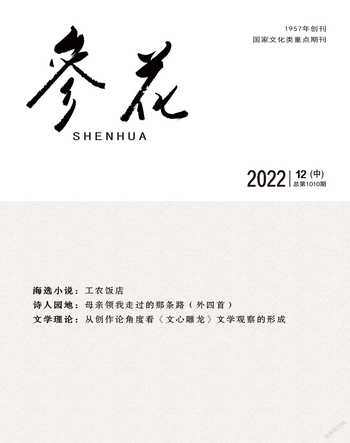凱特·肖邦《一小時的故事》中的象征意義解讀
一、引言
《一小時的故事》是十九世紀美國女作家凱特·肖邦的短篇小說。這部小說用簡短的字詞,生動描寫了一個體弱多病、受到丈夫壓迫的已婚女性在悲與喜交織的巨大打擊下,最終不幸死亡的悲劇。小說中的大部分故事情節發生在馬拉德夫人的房間里,凱特·肖邦在對與這個環境相關的一切所進行的描述中,有許多值得解讀的象征手法。小說中的象征意義大多與女主人公所處的空間有關,解讀小說中關于門、窗及被隔絕的空間的象征意義,是閱讀時需要去考究的一個方面,有利于挖掘作者寄托于這部作品的思想深意。
象征是人類文化中一種常用的信息傳遞方式,它通過采取類比于聯想的思維方式,以某些客觀存在或想象中的外在事物及其他可感知到的東西,來反映特定社會中人們的觀念意識、心理狀態、抽象概念和各種社會文化現象。通常而言,象征的本體意義和象征意義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但通過作家或藝術家對本體事物特征的突出描繪,會使讀者或藝術欣賞者產生一些由此及彼的聯想,從而領悟到創作者所要表達的含義。運用象征這種藝術手法,可使抽象的概念具體化、形象化,可使復雜深刻的事理淺顯化、單一化,還可以延伸所描寫事物的內蘊,創造一種藝術意境,引起人們豐富的聯想,同時,增強作品的表現力和藝術效果。在文學創作中,象征是一種十分常用的寫作手法,不同作家在寫作時會賦予不同事物以特別的象征意義,不僅能豐富作品的內涵,更能深刻展現賦予其中的意蘊。本文意在通過“象征”這一寫作手法來解讀凱特·肖邦的短篇小說《一小時的故事》。目的在于通過解讀這篇小說的象征意義,來領會凱特·肖邦蘊藉在這部小說中的深切思索和感悟。
二、《一小時的故事》的創作背景和梗概
《一小時的故事》是十九世紀美國著名女作家凱特·肖邦的短篇小說,也是其代表作之一。作者凱特·肖邦生活在十九世紀的美國,在那時,女性在許多方面的價值都被重新認可,女作家也逐漸得到了更好的發展。肖邦良好的家庭環境和教育使她在文學上能有所作為,較為美滿幸福的婚姻生活給予她作為獨立女性的思考空間,這也就為她日后寫下許多具有先進的女性意識的優秀作品打下了基礎。
短篇小說《一小時的故事》正是誕生于這樣的背景之中。這篇小說用簡短的字句,生動地寫了一個已婚女性“喪偶”的故事。主人公馬拉德夫人得知了丈夫的死訊,在突如其來的悲傷的傾軋之下,她感受到了人性和道義間的煎熬,并在其中嗅到了自由的氣息——丈夫的死意味著婚姻牢籠的崩塌。但在她不斷品味新生活,幻想未來的時候,她的丈夫又奇跡般地“死而復生”,回到了家里,馬拉德夫人最終“喜極而亡”。小說大部分情節的發生地點是在馬拉德夫人的房間里,她的情感轉換和想象也發生在這里。凱特·肖邦在對小說環境的描述中,巧妙地使用了象征的手法,其中便會包含作者的深刻思想。這也是本文要去探究這些象征意義的原因。
三、打開的“窗”
在《一小時的故事》中,馬拉德夫人在聽到自己的姐姐帶來的關于丈夫的死訊后,一下子就倒在了姐姐的懷里,放聲大哭了起來。而在自身悲傷情緒得到一定發泄和緩解以后,她馬上離開了姐姐身邊,“當哀傷的風暴逐漸減弱時,她獨自走向自己的房里,她不要人跟著她”。她獨自進入了房間,這就意味著這個房間是屬于她的空間,也承接了后續與這個房間息息相關的情節發展。在她進入房間后,小說最先描寫的是正對著她的一扇“打開的窗戶”和一把“舒適寬大的扶手椅”,凱特·肖邦在馬拉德夫人的房間里設置了一扇開著的窗戶,而窗戶旁邊放著舒適的椅子,其實就隱晦地暗示了對于馬拉德夫人而言,這扇窗戶是開放且令她感到舒心的,所以她才會在感到筋疲力盡之后,“一下癱坐在椅子里”。
因此,若以這扇開著的窗戶作為空間的界限,小說中此時的環境就被分割成了窗內與窗外這兩個不同的內外場景。窗內的環境,其實指的是馬拉德夫人獨自一人所處的房間。以窗戶作為劃分界限,窗戶內的環境——房間,是房屋的“零部件”,它是有限且是有邊際的,它的空間不是無限延伸的,而是被客觀條件所限制的。空間的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會使它的深層含義也帶有一定的拘束性。馬拉德夫人在收到丈夫的死訊后,短暫地失去了神志,而后便一個人走進了房間。人在受到巨大刺激時,做出的很多行為幾乎都是慌亂后下意識的行為,本質是為了排解自己的震驚并讓自己感到安心。馬拉德夫人會下意識地想要回到房間,從側面反映了房間帶給她的是正面的關懷,是一個會讓她覺得安心的地方。在夫妻共有的家中,一個能讓妻子擁有安全感的房間,其實正象征了一個作為妻子在這段關系中能讓自己感到安心的生存空間,馬拉德夫人也是如此。窗戶內的空間是安心的,但也是相對狹小拘束的,有邊際的安心感,永遠不是真的心安。窗戶內的房間正象征著馬拉德夫人這類女性在一段壓抑的婚姻中,艱難求得的極其有限的自我生存空間。
馬拉德夫人坐在打開的窗戶前,她看見了窗外的世界:“她可以看到,窗外露天場地上,樹木隨風搖曳,樹梢洋溢著初春的生機。空氣中充滿了春雨的芳香。樓下街道上,一個小販正在吆喝著招攬生意。遠處隱約傳來歌唱的旋律,屋下,數不清的麻雀正嘰嘰喳喳地歡叫。窗外的正西方,片片云朵融合交疊,偶爾間隙中露出一片片藍天”。此時她眼中的世界,也就是窗外的世界,是美麗的、生機勃勃的。她坐在椅子上仔細觀察,就好像從未見過如此的春景一般。春天象征著新生,是萬物的開始,小說里的春天也是如此。在英文版的原文中,更是巧妙地通過一個單詞展現了這種新生感:“當女主人公望向窗外‘the tops of trees that were all aquiver with the new spring life,此處‘aquiver有顫抖之意,將樹施以動作,這種微顫動作讓人聯想到了新生命的顫抖,帶著惶恐來到一個新的世界”。馬拉德夫人在這時驚慌地感受到了新生的來臨,這扇開著的窗戶,引導她看見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新世界,這個新世界充滿生機,這生機屬于世界上的一切,包括她。窗外不僅只是一個外面的世界,對于馬拉德夫人而言,更象征著一個與窗內的閉塞和妥協完全不同的生活。從窗戶向外,空間是延續的、廣闊的、無邊無際的,沒有顯性的圍欄,更沒有隱性的牢籠,這一切都象征著在失去丈夫后的馬拉德夫人的未來是自由且廣闊的。在馬拉德夫人面前打開的不僅是物理的窗戶,更是心里的窗戶,窗外美好的空間也象征著在遠離了被壓迫的婚姻關系之后,即將來到逐漸自我覺醒的馬拉德夫人身邊的自由生活。
窗戶分割了小說中馬拉德夫人所處的空間和她所看見的空間,并為這兩個不同的空間賦予了不同的描述。尤其著重描寫了窗外的美好景色,給予了這兩個空間對立性較強的象征意義,象征著馬拉德夫人在失去丈夫以后矛盾對立的情緒。“正如著名的評論家佩吉·斯蓋格絲認為肖邦筆下的女主人公往往過著‘雙重生活。‘打開的窗戶象征著她對相對家庭空間的外部空間的向往,是擺脫被緊鎖在家生活‘內在性的希望。”窗戶是馬拉德夫人雙重生活的聚焦處,是她與現實生活的交點,也是她同向往的生活的連接處。窗內的房間是馬拉德夫人在婚姻中尋到的“領地”,窗外的光景則是屬于她的自由生活。在這里,“打開的窗戶”不僅只是一扇窗戶,還是一個能夠擺脫房間內在閉塞性的出口。馬拉德夫人真切感知到了窗外的新生,并“透過那扇窗吮吸著仙丹靈藥”。這扇打開的窗戶,象征了馬拉德夫人能從壓抑的婚姻生活中脫離出去,是走向自由且有尊嚴的生活的一個機會,這個機會也是她自我意識覺醒的具象。物理意義上的打開的窗戶,象征的則是在心靈層面開啟的覺醒的窗。
四、緊閉的“門”
除了那扇打開的窗,在《一小時的故事》中,“門”也是一個重要的推動故事進程的道具。親人和朋友從門口進入,帶給了馬拉德夫人喪夫的噩耗。而在知道自己的丈夫“已經死亡”之后,馬拉德夫人獨自一人回到了房間,并關上了房間門,將自己與外界隔絕開來。而當她“舉手投足都宛如勝利的女神一般”地推開房間的門,準備走向新生活的時候,她的丈夫布倫特里·馬拉德打開了他家本該緊閉的房門,“死而復生”地出現在她的面前。
由此可以看出,在此,“門”這一事物是一個貫穿全文的重要存在,雖然其并非是一個被刻意描述的物件,但是卻在小說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也蘊含著深刻的象征意義。把“門”作為解讀小說象征意義的重要探究物,不僅是意在要去準確感知作者賦予在這扇門上的象征意義,也是要通過它來準確塑造女主人公馬拉德夫人這個人物的形象。以房間的門為標志,對于馬拉德夫人而言,門里門外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家庭是一個私密性與社會性的交界處,房屋的大門隔開了私人空間與社會集體空間,而屋內房間的門則劃分了更為隱私的小空間。房屋是帶有社會功能的,“客廳”一詞其實就體現了這一點,當大門打開之后,帶來的是親朋好友,是社會的集體融入需求。“在馬拉德夫婦家里,門外的空間連著客廳,是親朋好友聚集的社會活動場所,是主人公與外界進行交流的場所,在這里,人們的言語行為要符合社交禮儀,更要符合……”在小說中,窗內的空間是房間,門內的空間也是房間,窗內的世界象征的是馬拉德夫人在婚姻生活中屬于自我的狹小生存空間,門內的世界也是如此。馬拉德夫人在關上房門后待在房間里所做的一切糾結思考,就是她本人作為女性的獨立意識覺醒的過程。這樣的覺醒在當時的大環境下是難以做到的,但她卻在房間里完成了。這恰恰說明在緊閉的房門后,是象征隔開了傳統意識控制的,屬于女人的自由空間,是馬拉德夫人自我意識覺醒的溫床。
“門”作為一個重要的存在,不僅分割了現實層面的屋內與屋外,更在心理層面劃開了馬拉德夫人與壓迫她的大環境的連接。與門外的世界不同,緊閉的房門內部是馬拉德夫人尋求自我的“后花園”。當馬拉德夫人關上房門,把自己與外界隔絕開來時,她的姐妹“約瑟芬跪在緊閉的門前,雙唇對著鑰匙孔,哀求著想要進去。‘露易斯,開門啊!求你開門——你這樣會憋出病的”,而門內的馬拉德夫人則答道:“走開。我沒把自己弄出病”。由此可見,門外他人的想法與馬拉德夫人此時的心態是截然不同的,門外的一切都是如今感受到自由的她所要遠離的存在。但身在門外的約瑟芬,面對緊鎖的房門,仍然“雙唇對著鑰匙孔”,呼喊著讓馬拉德夫人打開門,這也象征著門外的一切是無孔不入、讓人難以逃脫的。而故事的最后,當馬拉德夫人已經打開房門,走向新生活的時候,她的丈夫“奇跡”般地平安歸來了,用鑰匙打開了自家的大門,瞬間,門外的一切都勢不可擋地涌向了馬拉德夫人,并最終沖垮了她。而這被外力推開的家門,平安歸來的丈夫亦象征了這壓抑的環境仍是一個讓她難以抗爭的存在。
小說中,緊閉的門存在于劇情各處,正是因為它的存在,讓女主人公得以獲得了短暫的安寧,也覺醒了自我的獨立意識。這扇緊閉的門隔絕的不僅是空間,更是一個女人在婚姻中所求得的雙重生活的兩面。“門”的存在,象征了女主人公馬拉德夫人與現實強烈的心理隔絕,是她被消解的自我開始不斷復蘇的一道分水嶺,也是幫助她完成覺醒的一扇渺小,但意義重大的“安全門”。
五、結語
在這部短篇小說中,“窗”和“門”在其中被賦予了豐富且深邃的象征意義。在這部由烏龍死訊所撐起的小說中,通過“打開的窗”和“緊閉的門”這兩件看似平常的事物,完成了對小說中場景的深層次構建,并讓這部小說有了更多值得去探究的細節。緊閉的門短暫隔絕了女主人公與門外的聯系,為她那矛盾復雜的自我意識的覺醒提供了一個與大環境相隔離的場所,也就是門內的場所——房間。而門內的環境——房間,同時,也是窗內的空間。房間里這扇打開的窗戶則有著與門相反的功能,打開的窗戶是馬拉德夫人與外界的一個相接口,但窗外的世界又與門外的世界不同,是美麗且充滿活力的,象征了馬拉德夫人即將得到的自由的新生活。這部小說寫的是馬拉德夫人作為一名女性所遭受到的帶著幽默色彩的悲劇故事,其中的一些細節在悲劇的浸染下,也散發出了深沉的味道。探究小說中的象征意義,是一個能更好了解這部作品,知曉作者用意,并追尋到那個時代的印記的好方法之一。
參考文獻:
[1][美]凱特·肖邦,等.著.六十分鐘[M].劉洋,等.譯.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8:22-24.
[2]張小波,徐李潔.批評話語視角解讀《一小時的故事》[J].懷化學院學報,2015,34(06):108-111.
[3]張麗.論肖邦《一小時的故事》的反諷藝術[J].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34(07):205-207.
[4]沈潔瑕.試以二元對立解讀《一小時的故事》[J].安徽水利水電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3,13(02):94-96.
(作者簡介:李洋,女,碩士研究生在讀,廣西師范大學,研究方向:英美文學)
(責任編輯 張云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