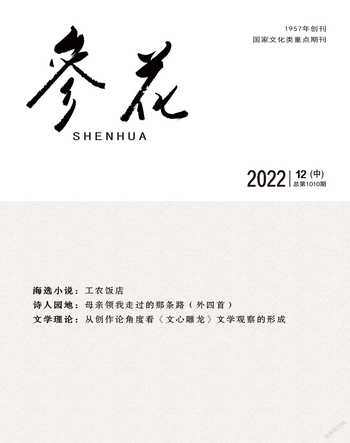論卞之琳“口語入詩”中的方言傾向
一、引言
語言與文學之間有著密切聯系,可以說,語言的構型影響著文學的生成與發展,最開始,現代詩歌便是以“文白之爭”進入人們視野的。作為“上承新月,中出現代,下啟九葉”的現代詩人卞之琳,他在現代詩歌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與作用,其最先以詩人身份亮相文壇,代表作《斷章》是家喻戶曉的名篇佳作。他詩藝精湛,有嚴格的詩學追求,一生創作的詩歌僅一百多首。卞之琳長于錘煉詩歌語言,強調“口語化”寫作,而這種“口語入詩”的背后,包含著容易讓人忽視的方言傾向,京白與吳語的調子,藏在其詩歌創作之中,主要體現為詩歌語言帶有北京、江浙地方音。因此,卞之琳筆下含有“方言”特質的詩歌,不同于一般方言詩,其詩歌語言直白,詩體精致,詩意細膩,這種方言特質的呈現與個人、詩史有緊密聯系。探究卞之琳以“方言”進入詩歌,可以發現在新詩發展過程中,現代詩人對詩歌語言的選擇。不過,“方言入詩”也帶來一些問題,讀者誤讀,方言去留,成為主張方言寫作的作家們面臨的難題。
二、卞之琳詩歌語言中的方言傾向
卞之琳主張“口語”入詩,他曾在詩集《雕蟲紀歷》自序中提到:“我寫新體詩,基本上用口語,但是我也常吸取文言詞匯、文言句法(前期有一個階段最多)……新時期也一度試引進個別方言,同時也常用大家也逐漸習慣了的歐化句法”。[1]“口語”“化古”“化歐”這三種詩歌主張,構成了卞之琳詩歌語言的主要特色。“化古”“化歐”主要指對中國古典文學與西方文學的創作方法與形式進行化用。那么,卞之琳所主張的“口語”又指什么?現代詩歌史上,“口語入詩”是一個十分復雜的詩學現象,閱讀卞之琳的詩歌,發現他的“口語入詩”可以理解為詩歌語言近似“白話”,并納入“方言”意識的詩歌主張。顏同林認為,“由于方言、土語一直受到排擠,卞之琳常用‘口語‘口語化來掩飾自己詩歌當中的‘方言‘土語化傾向”。[2]方言因素確實被卞之琳“口語化”寫作所掩飾了,但也正是由于卞之琳主張口語化寫作,他的詩歌才會表現出方言性,這種方言性主要體現為詩歌含有“京白之味”與“吳語之韻”。
首先,卞之琳詩歌語言的方言性體現為詩歌語言含有“京白之味”,特別是在其詩歌創作早期,“京白”尤為明顯。這種“京味”,主要從兩個方面呈現,其一,詩歌“京白之味”體現為人物常以“北京話”進行對話或獨白。卞之琳先從環境寫起,“集中寫北平街頭灰色景物,以及平凡人、小人物”,如《西長安街》《叫賣》《酸梅湯》《春城》等,都將視野集中在了北京城。按照卞之琳的話說,便是:“我更多借景抒情,借物抒情,借人抒情,借事抒情”。在環境與情感建構基礎上,卞之琳加入人物對話或獨白,例如“從遠處送來了一聲‘晚報”(《記錄》)、“什么,有人在院內/跑著:‘下雪了,真大”(《寒夜》)、“最后一杯了……啊喲,好涼”(《酸梅湯》)、“‘早啊,今天還想賣燒餅?‘賣不了什么也得走走”(《苦雨》),等等。這些詩句樸素卻富有靈氣,將人物生活情景與對話或獨白聯系在一起,完成了詩歌場面的構建。其二,詩歌中含有北京方言詞匯,常見兒化音。卞之琳在1930—1932年期間創作的詩歌,幾乎每一首都有“兒化音”的影子。如“腳蹄兒敲打著道兒——苦澀的調兒”(《傍晚》)、“小玩藝兒,好玩藝兒!……唉!又叫人哭一陣”(《叫賣》)、“快點兒走吧,快走”(《長途》),等等。當然,除“兒化音”外,也有其他含有京味的詞匯短語出現,例如“滑亮”“軋軋的”(《一個閑人》)、“你來要賬”(《過節》)、“矮叫花子”(《幾個人》),等等。這些方言詞匯與人物對話相互聯結,使詩歌飽含“京味”。
其次,卞之琳詩歌中的方言傾向還體現為詩歌語言蘊含吳語之韻。卞之琳在北京時期創作的詩歌,京味明顯,但其中后期創作的詩歌,特別是《裝飾集》與參加試點工作期間創作的詩歌,京味淡去,吳地方言逐漸進入讀者視野。卞之琳曾指出,他在后期詩歌創作中,“多數是試用一點江南民歌的調子,特別是《采菱》這一首,那卻又融會了一點舊詞的調子。這些詩都還試吸取了一些吳方言、吳農諺”。卞之琳巧用吳語進入詩歌,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利用“吳方言”詞匯與“吳農諺”,使詩歌帶有鮮明的吳地文化特色。例如在詩歌中加入吳方言詞匯,如《半島》中的“一脈”“來客”、《無題·四》中的“今朝”、《采桂花》中的“天收”、《搓稻繩》中的“息息”、《收稻》中的“小妮子”,等等。當然,個別詩歌的語言中還加入了“吳農諺”,例如《采菱》一詩描寫了在蘇州鄉下,人民集體采菱的場景,對集體協作、比拼摘菱的行為進行了贊美,利用農諺“采菱勿過九月九”,點明采菱的時間與農忙。
最后,部分詩歌吳語入韻。卞之琳以吳語方言音作為韻腳,王力在《現代詩律學》中論及現代詩歌格律時,指出卞之琳方言用韻,并認為“現代漢語詩人大約沒有故意用協音的。他們有時候押韻像是協音,其實只是方音的關系”。[3]卞之琳部分詩歌押吳韻,例如《望》中的“把它當作是一幅自然的地點;藍的一片是大洋,白云一朵朵”兩句。“朵”字,普通話讀“duo”,吳方言讀“tu”。諸如此類,還有《淘氣》中“足”與“腳”(方音押“o·”)等,都押吳韻。“京白”與“吳語”,是卞之琳“口語入詩”的兩種語言基石,是最為明顯的兩種方言傾向。
三、影響卞之琳“方言入詩”的原因
卞之琳方言入詩相較于其他方言詩人的詩歌,具有自身的獨特性,他對方言的運用是隱藏在詩歌的口語主張之中的。卞之琳的口語詩歌不似街頭詩、口號詩、打油詩,詩歌有自我的精致與詩意,不讓詩歌流于俗氣,是卞之琳一直堅持的詩學追求。他的這種詩歌語言傾向與個人、詩史有著緊密聯系。
其一,個人生長環境與詩歌主張,使詩歌不可避免地含有方言因素。卞之琳出生于江蘇,吳語是他的母語,這種語言影響了他一生。19歲后,他離開家鄉,到北京讀書,除吳方言外,他接觸到了第二種方言——北京話。雖然卞之琳在往后的人生中輾轉各地,但北京話對他的影響,不亞于母語方言吳語的影響。卞之琳也認為他操著一口南腔北調的語言,在1936年創作《尺八夜》時曾自嘲:“在北方,人家當然認我是說的南方話,回到南方,鄉下人又以為我說的北方話,簡直叫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地方人了”。吳語方言和北京地方音,構成了他詩歌創作的語言資源。加之卞之琳倡導“口語”寫詩,這種方言方音,進一步影響到他對詩歌語言的構型,口語表達中的方言因素,不可避免地進入了詩歌。
其二,從詩學背景看,卞之琳倡導口語入詩并涵蓋方言因素,與現代新詩發展有著密切聯系。晚清以降,“文白之爭”成為先進知識分子反抗傳統舊制的有力表現,而“方言”正是“文白之爭”的切入口。詩界革命時期,黃遵憲、梁啟超等人強調“我手寫我口”,黃遵憲主張“俗語”進入詩歌,大力收集“民歌俗謠”并進行模仿改作。到了新文化運動時期,白話文運動在“詩界革命”的基礎上,繼續對文言發難。張桃洲曾指出,以白話文運動為基礎的現代漢語有兩種對立,一是文言和白話的對立,二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歐化”白話和大眾語言的對立,這兩種對立都是關于現代漢語的資源問題,前者是討論現代漢語的語言基礎,后者就是在認可白話的基礎上,是否以一種更為淺白的白話(俗語、土語)作為現代漢語的未來方向。[4]“文白之爭”為“方言”進入文本提供了機會,白話文運動裹挾著“方言”進入文本為“方言入詩”助力。及至新月派時期,“方言入詩”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新月派詩人進行“土白入詩”的詩學試驗,常將抒情與敘事相結合,夾雜詩人家鄉的土白詞匯、句式,或是利用北京土話來進行表達。[5]聞一多、徐志摩、蹇先艾等人先后嘗試在詩歌中加入土白方言,并取得了不錯的效果。新詩生成時期的“文白之爭”,新月派的“土白入詩”,影響了卞之琳的詩歌創作。
四、卞之琳“方言入詩”下的困境與挑戰
卞之琳善于從日常生活中發現詩的內容,并在創作詩歌的過程中,進一步隱藏讓人難以琢磨的深刻內涵,他對方言的使用,并不是他建構詩歌語言的直接目的,而是主張“口語入詩”下的無意之舉。“方言俗語”巧妙地存在于卞之琳詩歌之中,與“口語”相互融合,詩歌語言簡單,詩意親切。回顧卞之琳創作詩歌的歷程,他的“方言入詩”折射出了新詩語言的生成問題,也流露出新詩語言建構過程中面臨的危機。
作為“母語的母語”,方言有民族性、地域性、民間性的特質,但方言進入詩歌,容易導致“讀者誤讀”。部分方言詩因語言限制的問題,受眾縮小,不是方言詩所處方言區的讀者,可能會在閱讀詩歌的過程中,難以理解詩意,方言詩歌似乎成了一部分人的詩歌了。從《雕蟲紀歷》看卞之琳各個時期的詩歌,不管是化用土語,還是利用方言押韻,卞之琳對詩歌語言的把握,可謂得心應手,整體上化用得十分巧妙。但部分詩歌的詩意是晦澀的,讓人琢磨不透。后來創作的詩歌,甚至被批為“難懂”,“卞之琳在《新觀察》上發表了……卻受到了批評。《文藝報》上幾位讀評論‘難懂……也被評為‘奇句充篇,難讀難講”。現在看卞之琳的詩歌,這些評價未免有失偏頗。詩歌語言的“口語性”似乎與詩歌“難讀”的詩意產生了分歧。那么在這個過程中,作為詩歌語言因素的“方言”,是否成了拉開詩歌與讀者距離的推手,進一步影響讀者閱讀,使讀者難以理解詩意,對詩歌產生誤讀?新詩發展過程中,各地域的詩人依據各自地域語言,介入詩歌,不同地域的讀者,是否因自己所屬方言語系與詩人方言區不一致,而難以理解詩人詩作的妙趣,值得深思。
另外,部分方言進入普通話行列與方言語音的消失,也是依靠方言寫作的詩人需要警惕的問題。卞之琳所用的北京語、吳語,為了更貼合大眾,其所采用的詞匯,一般是較流行的方言詞匯。例如北京語言中部分兒化音詞匯,吳語詞匯“垃圾”“老板”等。若不細看,很難發現卞之琳掩藏在“口語入詩”背后的“方言”“土語”。除了卞之琳所主張的是“口語入詩”,而不是“方言入詩”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普通話規則的改變與語音發音的變遷。現代漢語規則的改變,已經將這些常見的方言詞匯納入普通話,解決了語言的地域性問題,擴大了詩歌的受眾。現今看卞之琳詩歌,由于部分口語方音納入普通話,方言性變得十分淺淡,加上語音變遷,詩歌語言逐漸失去方言性。讀者幾乎不會對詩歌字詞的表面意思產生疑惑,但或許也不能順利地回到歷史現場,以當時的方言語音規則讀詩、品詩。并且,方言的語音性作用大于其文本性作用,如何將方言巧妙地實踐在書面文本之中,考驗詩人的創作能力。方言語音與書面語之間,有著不可調和的距離,這為方言書寫增加了難度。
隨著現代漢語語音規則的改變,方言在詩歌中產生的作用是否已經消失?方言是否還有進入詩歌的必要?方言與新詩之間的關系,是密切的,復雜的。“一方面,詩人對語言的提煉、純化,外部勢力強加于語言的‘雅正、‘規范化,使得新詩不斷地去方言化。另一方面,新詩因語言整體走向上的白話化、口語化傾向而與原生態方言保持著血緣關系。”[6]方言與新詩發展之間,存在語言沖突的同時,又在某些時段自動調和。正如卞之琳詩歌之中的方言因素,似乎隨著漢語規則的改變,逐漸隱藏起來,但是仍能夠感悟到作者主張“口語入詩”的良苦用心。
五、結語
方言在詩歌語言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雖然它不比通用語言受眾廣,但卻促使詩歌帶有地方色彩,是對傳統詩歌語言的反叛。卞之琳“方言入詩”的詩歌主張,使其詩歌語言更加自由,方言性、口語化,為卞之琳的詩歌帶來了生機。當然,“讀者誤讀”“方言消失”是卞之琳“方言入詩”遇到的困境與挑戰,也是現代詩歌發展過程中需要面對的問題,如何規避危險,提升詩歌品質,需要現今詩歌創作者慎重選擇。
參考文獻:
[1]卞之琳.雕蟲紀歷1930—1958(增訂版)[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2]顏同林.“化土”:在“化古”與“化歐”之間——以卞之琳為例[J].三峽論壇(三峽文學.理論版),2010(06):106-110+149.
[3]王力.現代詩律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4]張桃洲.語言與存在:探尋新詩之根[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5]顏同林.方言入詩的現代軌轍[M].廣州:花城出版社,2018.
[6]顏同林,譚琳妃.困惑與誘惑:方言入詩的兩難選擇[J].湖南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01):101-104.
(作者簡介:羅冬梅,女,碩士研究生在讀,西華師范大學,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
(責任編輯 葛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