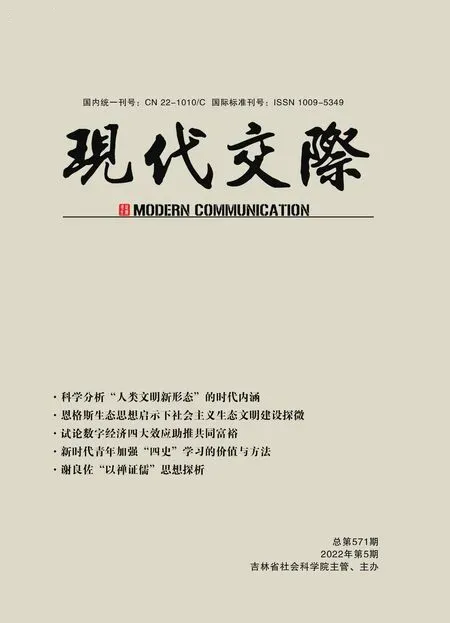謝良佐“以禪證儒”思想探析
□高雨潔 稂 荻
(中國計量大學 浙江 杭州 310000)
謝良佐,字顯道,人稱“上蔡先生”。“程門四先生”中,雖以楊時最為著名,然謝良佐對“二程”思想的發揮實則大于楊時,且對朱熹亦有所影響。他的思想從整體上看仍以“二程”為宗,堅守儒家本位而立論,但亦不可否認其受佛禪影響之深,因而世人多予其“入禪”之評價,如:朱熹曾謂謝良佐總在佛學中“探頭探腦”[1]568;南宋學者黃震亦認為其“以禪證儒”,“第因天資之高,必欲不用其心,遂為禪學所入。雖自謂得伊川一語之教,不入禪學,而終身常以禪之說證儒,未見其不入也”[2]918。由此,本文試圖從“以禪證儒”的角度出發,論述佛禪對謝良佐的哲學體系產生的影響。
在探討之前,我們有必要重申本文的基本立場,即謝良佐雖多被后人批評為“入禪”,實則仍是以“二程”學說為根基,從仁出發,對“天理”這一概念做出新的闡釋。《上蔡語錄》有謂:“所謂天理者,自然的道理,無毫發杜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乍見時其心怵惕,即所謂天理也;要譽于鄉黨朋友,內交于孺子父母兄弟,惡其聲而然,即人欲耳。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即滅卻一分天理;有一分天理,即勝得一分人欲。人欲才肆,天理滅矣。任私用意,杜撰做事,所謂人欲肆矣。”[2]918可見,謝良佐認為的天理有兩層含義:其一,天理是自然的、非人為的、不帶有任何功利目的的道理,常住而變動不得;其二,天理具有道德屬性。謝良佐指出,人們見孩童掉入井后自然而然產生的驚恐、不忍之心是天理的表現,即作為宇宙萬物所遵循的普遍理則的天理在人身上表現為自發的道德,是人人皆有之心。這是一種道德化和內在化的天理。這種內在于人心的天理亦為仁:“仁者,天之理,非杜撰。天理當然而已矣。”[2]922仁即天理,非后天人為,是本就如此的。在這兩層含義中,謝良佐更強調天理與人欲之間的對立,更重視天理的第二層含義,即其道德屬性。天理應當被理解為具有普遍性的、非人為的道德原則,而這種道德原則的本質就是儒家之仁。綜上,我們看出,謝良佐哲學體系之框架仍舊承襲“二程”,但他沒有止步于此,而是選擇借用禪宗的思維模式展開進一步論述。
一、儒之仁,佛之覺
在謝良佐看來,天理落實在人身上便體現為仁,人人皆具有天理、仁。因此,天理與仁同一,窮理實則為人受私欲污染、影響后的“有我”轉化、復歸于具有絕對道德的“真我”的過程,表現在人對自身之仁的體認上。而謝良佐在這一過程中提出“以覺言仁”,并以仁溝通心與天理,是后世所謂“終身常以禪之說證儒”之由來。
謝良佐將心與仁置于一處、“以覺言仁”的思想,在“二程”的著述中均能找到源頭。“二程”曾有“醫家以不認痛癢謂之不仁,人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為不仁”一說,以知覺(感知痛癢)比擬仁,指出于人而言,仁即是“覺”義理。謝良佐則發揮此說,《上蔡語錄》有謂:“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為仁,死者為不仁。今人身體麻痹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2]917可見,謝良佐試圖從兩方面論仁:其一,以心論仁,仁即是心,有生生之意;其二,以覺論仁,仁有知覺之用,可感通內外,若人之身體喪失知覺,則為不仁。就第一點來看,仁用以溝通心和天理,仁為萬物生生之性,生生之理,而仁與天理、心不二,則此三者皆具本體層面的意味。就第二點來看,“以覺論仁”容易使人將本體之仁與佛教之“覺”聯系在一起。謝良佐自己也聲稱:“仁是四肢不仁之仁,不仁是不識痛癢,仁是識痛癢。儒之仁,佛之覺。”[2]917“佛之覺”是何意?中國佛教多以遠離妄念、明見清凈本體為“覺”,指向的是對本體層面的清凈無染之性的認識,與“無明”相對。如《大乘起信論》中,“覺”“本覺”指向的便是眾生本來覺悟、本有清凈本體。而菏澤宗密更是直接將“覺”看作眾生皆有的清凈本心之用,以此用可以直接體悟清凈空虛之本心。謝良佐以“佛之覺”解仁,意味著仁也指向本體層面,即人們本有的內在道德本體,而不是經驗層面上認識主體向外的認知、體驗和感覺。關于這一點,謝良佐曾有謂,“知者,心有所覺也,非聞見之所及。只于聞見能擇而從之識之,與心知殊異,故曰知之次也”[2]920,“但存得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底心在,便是識痛癢”[2]920。顯然,這里的“知者”、知覺是內心道德本體覺悟和覺醒之后的狀態,而非“聞見所及”,非向外的認知和感覺。由此,謝良佐進一步指出,體悟到心之“本覺”,便是體悟誠敬之心,人才會發仁之情,行仁之事。
在此,謝良佐是要求人體悟宇宙萬物生生不已的本性及人心的道德本體之仁。不自覺體悟本心,則不可能達至仁的境界,體會天理,與理同一。“心有所知覺謂之仁。”若無知覺便無法識得本心之仁。這與禪宗的思維模式是接近的。禪宗所講“自心是佛”其實是建立在人的自覺(自我覺悟本心的清凈)之上。禪宗主張“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何以見性成佛?因為性本清凈、性自明覺,所以覺悟不應向外索求,而應反求自心,由此便覺悟成佛。禪宗的思維方式如下:人人皆有佛性且佛性本自清凈——明心見性——覺悟成佛。而謝良佐的思維方式如下:天理是宇宙萬物所遵循的普遍原則(在人的層面就是具有普遍性的仁)且天理或仁是具有道德屬性的當然之理——心有所“覺”,與理同一,達至仁之境界——自然而然地發仁之情、行仁之事。我們可以看到,謝良佐受到禪宗思維方式的影響,將仁如佛之本覺一樣,作為人們內在修養的超越境界和人們可以達到該境界的根據。這樣一來,仁,或者說天理,不僅是外在的道德約束和規范,而且成為內在的形上道德本體,那么強調對內心道德本體的覺悟則成為必然。然而,謝良佐本人并非完全流入佛禪。他指出,佛禪之“見性”有其弊端:“學佛者知此謂之見性,遂以為了,故終歸妄誕。圣門學者見此消息,必加功焉,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2]922儒家與佛禪雖然皆見此心,然佛禪見此心后不再有生意,不再起用,不再擴而充之,因此歸于妄誕。
二、對佛禪“作用是性”的批評
謝良佐曾就儒佛雙方的心性論評價道:“佛之論性,如儒之論心。佛之論心,如儒之論意。循天之理便是性,不可容些私意。纔有意,便不能與天為一。”[2]932我們認為,這可以看作對洪州馬祖道一系“作用是性”的批判。我們在上文中已經闡明謝良佐心性論的思維模式與佛禪相近,現在將通過對雙方“心”這一概念的分析,揭示其與禪宗,尤其是洪州宗的重要不同。
我們先考察洪州馬祖道一系的心性論。首先,洪州宗使用的“心”指向的是人的現實心、“平常心”。馬祖道一指出,“平常心”即“無造作,無是非,無取舍,無斷常,無凡無圣”之心,又是眾生日常現實之心,是“道”。“平常心”便是終極的境界:眾生只要隨順現實本心,不起任何執著和分別,如此一言一行皆是“道”的體現,也就達至佛的境界。可見,洪州宗將現實人心與本心、佛性聯系在一起,把兩者視為相通的。同時,洪州宗亦將此心作為萬法之本。黃檗希運曾有“此法即心,心外無法;此心即法,法外無心”之說,認為佛法乃至其他存在都是從心所生,以心為本,由此強調眾生現實心就是修行之根本:一切眾生當前的現實之心就是佛,眾生與佛無二。這樣一來,現實人心與佛性、清凈本心幾近等同,因此對于洪州宗來說,“心”不僅指向現實心,也指向心體,是佛性、清凈本心。
但是,將現實人心與佛性、真如本心等同,就難以保證后者的超越性,致使修行者容易淪入經驗層面,產生種種弊端。因此,洪州宗強調本體層面的佛性、真如本心,無法通過理性思維和語言文字把握,它是超越的,無分別的,修行者只能通過其顯現——“作用”進行體悟。洪州宗以“作用是性”為特征。“作用是性”意為將“作用”賦予與本體相同的地位,把它們看作本心、佛性之體現;另外,本心、佛性也必須通過“作用”才得以顯現。馬祖道一有“見色即見心”“見聞知覺即是本性”的說法,“作用”在此處即為“見聞知覺”。何為“見聞知覺”?宋延壽《宗鏡錄》卷十四有謂:“馬祖大師云:‘如若欲識心,秖今語言即是汝心。喚作此心作佛,亦是實相法身佛,亦名為道。”[3]492又《宗鏡錄》卷九十八有謂:“太原和尚云:夫欲發心入道,先須識自本心。若不識自本心,如狗逐塊,非師子王也。善知識,直指心者,即今語言是汝心。舉動施為,更是阿誰?除此之外,更無別心。”[3]942顯然,馬祖道一以語言、舉動施為(舉止動作)為本心、佛性。關于這一點,宗密解釋:“洪州意者,起心動念,彈指動目,所作所屬皆是佛性全體之用,更無別用。全體貪嗔癡、造善造惡、受苦受樂,皆是佛性。”[4]意為馬祖道一將一切動作皆作為本心、佛性之表現,因此無論是善是惡、受苦受樂,皆為佛性。由此我們得知,按馬祖道一的理解,“見聞知覺”應是各種官能、具體的行為,而這些都與本心、佛性等同。不僅如此,馬祖道一的“見聞知覺”也應包含“色”,即認識對象。這在其“見色即見心”的思想中有所體現。《宗鏡錄》卷一有謂:“洪州馬祖大師云:‘法無自性,三界唯心。經云:‘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心;色不自色,因心故色,故經云:‘見色即是見心。’”[3]418《宗鏡錄》卷十四又有:“今見聞覺知元是汝本性,亦名本心。更不離此心別有佛。”[3]492可見,馬祖道一的思維邏輯是:萬事萬物(色)不過是本心、佛性(心)之表現,并且心與色互相憑借,見色就是見心,見心即是體認佛性。因此,我們認為,作為認識對象的色也是“見聞知覺”,即“作用”。綜上,洪州宗將眾生現實人心與超越任何執著分別的佛性、真如本心等同,眾生與佛無二,而此心之作用——“見聞知覺”,即一切知覺活動和認識對象(色),是眾生自心、佛性之顯現。從這個角度看,眾生隨順現實人心,不執著不分別后表現出的“作用”就是佛性。(心=性,心之作用=心之顯現=性之顯現,作用=性)
反觀謝良佐,他將洪州宗所謂的“心”等同于儒之“意”,表明他將佛之“心”理解為認識主體的認識功能,如“心王”,而非本體層面的本心、佛性,它可以有“見聞覺知”,產生主體感覺意識。這樣一來,他認為洪州宗以“心”之“作用”為“性”之顯現,將主觀的見聞覺知與具有普遍客觀性的天理等同,是不合理的。“作用”只能是“心”而非“性”之顯現。而在謝良佐自己的哲學體系中,“心”與仁、天理同一,皆是“性”,是具有普遍性的、非人為的道德本體。可見,謝良佐認為佛之論“心”,從經驗層面切入,而他自己則從本體層面切入,二者有本質不同。綜上,謝良佐認為佛以“意”,即“作用”、見聞覺知為“心”,再以“心”為“性”,是相當不妥的,且“佛之論心”是從見聞知覺的角度進行論述,既然“心”有見聞知覺,它便有“私意”,是主觀的,不可以與具有普遍性的天理等同。在此,我們暫且忽略禪宗內部對“作用是性”觀點的批駁、更正,以及謝良佐的批評是否正確這兩個問題,謝良佐此語對宋明儒學家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此后儒學家辟佛大體延續他所創的這一思路,朱熹便認為知覺運動,即“作用”,為“心”,而“性”只能在理處講,是貫通知覺運動之理,將經驗層面的“作用”等同于本體層面的性,便是“流入自私耳”。不僅如此,直至明代羅欽順亦批評佛禪認“心”為“性”,將“心”“性”“作用”合一,這與謝良佐的辟佛思路并無不同。
三、境界與功夫上的異同
謝良佐認為佛禪見本心后不起用,導致其最終歸于妄誕,而儒家則在體悟天理后起用,因而具有生生之意。他又強調,儒家的起用絕非起做作之用,而是達至自然從容之境界,一切隨運自然。此“隨運自然”一說顯然是受佛禪的影響而提出的,但是對本體的不同詮釋致使雙方在境界和功夫論上多有差異。
1.“無著一事于胸中”、任運自然的境界
《上蔡學案》有謂:“余又問:‘堯、舜、湯、武做底事業,豈不是作用?’謝子曰:‘他做底事業,只是與天理合一,幾曾做作,橫在肚里!見他做出許多掀天動地蓋世底功業,如太空中一點云相似,他把做甚么!如子路愿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無憾,亦是有要做好事底心。顏子早是參彼己。孔子便不然,老者合當養底便安之,少者不能立底便懷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自然合做底道理,便是天之所為,更不作用。’”[2]935謝良佐認為,圣人的所作所為均是循理而為,自然而然與天理同,而非做作,“橫在肚里”。就上述材料來看,做作與自然而然相對,指帶有某種私人目的(如我想獲得好名聲)或執著于行仁本身(如我時刻告誡自己應該做好事)而行仁之事。而謝良佐強調的是無任何阻礙,自在超然的精神境界。達此精神境界的圣人只需循理而動,一言一行便自然而然流露出仁之質。倘若執著于發仁之情、行仁之事本身,便是“橫在肚里”,非圣人境界,此即所謂“不可著一事在胸中”。
謝良佐十分重視仁的自然流露和“不著一事”。就前者而言,顯然與洪州宗“觸類是道而任心”的思想有相近之處。“觸類是道”是洪州宗倡導的一種禪法,指修行者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住坐臥均是修行,是本心、佛性的自然流露。人們修禪,關鍵不在于苦修,而是要悟自心,任其本心行事,任運自在。與此類同,謝良佐的思維方式是人們若能體認天理、達至仁的境界,則一切行為皆是對天理、仁的自然順應,因而天理、仁亦通過日常行為自然而然流露,而非有意為之。這種境界是心不受任何外在制約的自然狀態,可謂:“獨對春風吟詠,肚里渾沒些能解,豈不快活!”就后者而言,“不著于事”之境界又與洪州宗講究的“莫于心上著一物”和“無心”有所聯系。大珠慧海曾提及“無心”:他既對本心持有高度的肯定,又強調“老僧無心可用,無道可修”[5]。大珠慧海認為,“無心”即對一切事物都不產生執著、分別,修行者“無心”,處于無思慮之清凈狀態,也就獲得了精神解脫;黃檗希運則更明確地提出“無心是道”,眾生獲得解脫必須先“無心”。關于“無心”,希運有謂:“此心即無心之心,離一切相,眾生諸佛更無差別”,“此法即心,心外無法;此心即法,法外無心。心自無心,亦無無心者”。[6]“無心”就是本心,無一切分別和思慮,不著一事。由此,希運認為“無心”便是“莫于心上著一物”。“莫于心上著一物”與謝良佐強調的“不可著一事在胸中”雖有相似之處,但也有所不同。希運在“莫于心上著一物”的基礎上反對知解,即理性思維、見解、語言文字等。他認為,知解是解脫的障礙,應該排除,除此之外,連除去障礙妄心的念頭都不應有,最終“行住坐臥,但學無心,亦無分別,亦無依倚,亦無住著”,“形如癡人,心如頑石”。而謝良佐的“不著于事”則明顯帶有防止學人落入虛無的特征,他一再說明:“‘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而言,則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2]924自然從容、“不著于事”之境與《孟子》中所謂“心勿忘,勿助長”一致。執著于事是為“助長”,固然不好,但若心“忘”,即以洪州宗“莫于心上著一物”為標準,則容易否定一切世間的感性與理性活動,最終失去人生的價值,墮入空無。
綜上,洪州宗所謂“莫于心上著一物”,強調在日常行為生活中“無心”,除卻一切知解、執著、分別和妄念,隨順本心體悟佛性,最終達至的必定為超越理性思維、分別執著的境界;而謝良佐的天理與心、仁聯系,是有內涵,可被把握的,它其實就是道德原則。謝良佐提出“與理同一”和“不著一事于胸中”,是將外在的道德規范內在化于人心之中。由此,人們無須做作,其所有行為均自然而然符合天理。在謝良佐看來,符合道德原則、“與理同一”是自然的,是人性的舒張,人們不需要執著于某件事是否道德,他們的任何行為都必然符合內在于人心的道德原則。
2.“敬”的功夫
正因謝良佐將“與理同一”作為“不著于事”的基礎,所以他在功夫修養論上又格外強調“敬”的作用,以保證人們時刻“與理同一”。“敬”在“二程”處是用以區別佛儒的重要概念,而謝良佐卻借助禪宗語言解釋“敬”。謝良佐有謂:“敬是常惺惺法,心齋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2]924其中,“心齋”被等同于“事事放下”,與“惺惺”相對。而“惺惺”一語源自于《禪宗永嘉集》中的“惺惺寂寂是,無記寂寂非”[7],指“常存他‘本來面目’耳”,在此處又有長期保持清醒之意,正如朱熹注:“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1]573謝良佐應是用“常惺惺”說明“敬”是使心始終保持“覺”,即覺悟、“與理同一”,而非昏昧的狀態。謝良佐以禪語“惺惺”釋“敬,是其“以禪證儒”的一大佐證。
進一步看,謝良佐強調保持“敬”,可以達到“事至應之,不與之往”的境界。這種境界是“覺”的體現,是“覺”在動態功夫中的體現:“或問呂與叔,問:‘常患思慮紛擾,程夫子答以心主于敬則自然不紛擾,何謂敬?’謝子曰:‘事至應之,不與之往,非敬乎?萬變而此常存,奚紛擾之有?’夫子曰:‘事思敬,正謂此耳。’”[2]921人處于世間,難免會有思慮紛擾,但只要心主于“敬”,紛擾自然也就不復存在。何謂“敬”?“事至應之,不與之往”,無論做何事,都時時刻刻保持與理同一、無有雜念,而非對事情本身起執著。世間變化多端,只有存“敬”于心,一言一行才可與天理相應,人們才可任運自然而不生紛擾,達至“無著于事”、自然從容的境界。
由此可見,洪州宗與謝良佐在境界和修養功夫上均有差異。洪州宗作為禪宗分支,仍以不執著為最高境界;而謝良佐認為佛禪論心未能上升到具有道德屬性的天理層面,僅僅無心而任心,最終取消了日常行為的倫理價值和意義(儒家倫理道德),這就是“歸于妄誕”。因此,謝良佐必須強調“敬”,使人們時時刻刻彰顯自己的內在道德本體——仁(天理),以此保證人們無須外在道德規范的約束,在隨順自然的情況下亦可使自己的行為符合天理(道德原則)。謝良佐一方面想要為人們卸下外在道德規范的重擔,另一方面又使道德追求上升為隨順自然的精神追求,促使人們由被動遵循外在的道德規范轉變為主動體悟自身的道德本體。
四、結語
綜上所述,謝良佐“以禪證儒”,其思想之獨特,主要體現在仁學心性論和圣人境界上。一方面,謝良佐吸收佛禪的心性論,貫通天理、仁和心,提高儒家之仁這一具有強烈道德屬性的范疇的地位,使其形上化、本體化,試圖以完善形上建構的方式緩解當時佛禪帶給儒家的沖擊;另一方面,謝良佐將外在的道德規范轉變為內在的道德本體,使人們對道德的追求上升至精神層面,同時強調這種精神追求應是自然從容、不做作的,以此取代佛禪而成為人們的精神寄托。“程門四先生”中,當屬謝良佐最具發越性,他辟佛和“以禪證儒”的思路對后世有著很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