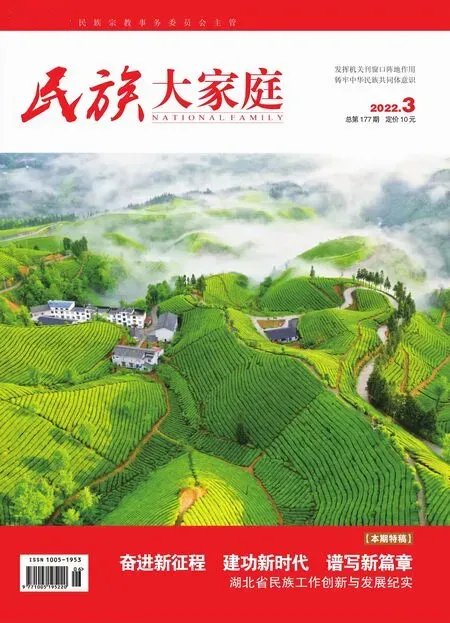道安大師佛教中國化的先驅者與奠基人
文/洪利民
道安法師是佛教中國化的開創(chuàng)者和奠基人。他一生致力于“佛教中國化”。道安的成就是全方位、系統(tǒng)性的:統(tǒng)一了僧姓;完善制定了《佛法憲章》《僧尼軌范》;首倡“凈土”信仰;創(chuàng)立六家七宗之首“本無宗”;撰寫、翻譯、注釋了大量佛學著作;編纂了中國第一部《眾經目錄》;開中國佛教史上佛經目錄學的先河等等,創(chuàng)造了佛教中國化的多項第一。梁啟超先生譽他為“中國佛教界第一建設者”。國學大師湯用彤先生稱:“東晉之初,能使佛教有獨立之建設,堅苦卓絕,真能發(fā)揮佛陀之精神,而不全藉清淡之浮華者,實在彌天釋道安。道安之在僧史,蓋幾可與特出高僧之數(shù)矣。”本文簡要梳理道安個人修學和僧團建設等幾方面的成就,以期對當前貫徹落實全國和全省宗教工作會議精神,進一步做好新時代宗教工作有所啟發(fā)。
勤學精進,學識淵博
道安,出生于西晉永嘉六年,俗姓衛(wèi),河北常山扶柳人,7 歲時開始學習儒家經書,12 歲出家為僧,20 歲受具足戒并外出游學。之后拜佛圖澄為師,道安曾因“形貌不稱”被人輕視,佛圖澄卻“與語終日”,還對看不起道安的人說:“此人遠識,非爾儔也。”后來,佛圖澄講法,要道安復述,道安挫銳解紛,答辯有力,眾人信服,時人流傳道:“漆道人(指膚色漆黑),驚四鄰。”
道安具有良好的佛學功底,還對儒家學說、文學和歷史深有研究。他一生重禪修、戒律,精研小乘教義和大乘般若學說,他以玄解佛,創(chuàng)立《本無宗》,創(chuàng)佛教義理、學術研究之先河。習鑿齒在《與謝安論釋道安書》贊嘆道安法師“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群書,略皆遍睹,陰陽算數(shù),亦皆能通,佛經妙義,故所游刃,作義乃似法蘭、法道,恨足下不同日而見”。其時長安人稱:“學不師安,義不中難”。豐厚的學養(yǎng)為道安大師接引徒眾、與社會上層人士、居士名流廣泛交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注譯經文,澤被后世
道安之前,“譯經之人,名字弗說”,很難知道哪部經是何人何時何地譯出來的。道安創(chuàng)撰《綜理眾經目錄》,為以后研究中國佛教的譯經史著,提供了第一部可信、可據(jù)的譯經史料書,即所謂《安錄》。道安在作總錄時,堅持“不見不錄”原則,凡入錄者,皆要過目,若僅據(jù)耳聞,則棄而不取。除嚴格審定收錄的經書外,道安還對經書翻譯的來龍去脈予以考訂,使《安錄》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惜已失傳。現(xiàn)存最古的經錄是南朝梁代僧佑所撰《出三藏記集》的第二部分經錄,就是在全部吸收《安錄》的基礎上加以擴充而成的。《安錄》不僅在中國佛教史上意義非凡,在中國目錄學史上也有重要地位。
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開始并不被國人所認識,只能依附于玄學等思想進行傳播,對佛經的翻譯、注釋不乏曲解之處。道安“窮覽經典,鉤深致遠”,用三分科判講解佛經一系列解經方法,對佛經進行注釋,“析疑甄解”“序致淵富,妙盡深旨”,使佛經“條貫既序”,講經者依之講經“文理會通,經義克明”。這既有利于佛教的廣泛傳播,又為以后佛經的注釋作出了范例,為深入研究佛經創(chuàng)造了條件。在長安(今西安)時,道安爭取執(zhí)政者和佛教界支持,組織人才翻譯經典。耗時七八年譯出佛典14 部183 卷,百余萬言。在長期實踐過程中,道安總結佛經翻譯的經驗,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譯方法性原則,受到后世的贊揚。
增進和合,厘定佛規(guī)
漢魏西晉時期,佛法初傳,漢地僧人落發(fā)出家,都從師姓,因而姓氏混雜。于是道安提出:“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他自己帶頭,將“竺道安”改為“釋道安”,他的弟子也改為釋姓,后來,道安在《增一阿含經》中稱:“四河入海,無得河名;四姓為沙門,皆為釋種”,證明其統(tǒng)一釋姓的合理性,從此佛門姓釋便成為中國佛教千年不變的永式。道安的改革,消弭了僧人因姓氏不同而突顯的身世、師門之別,更好地促進了僧團的自我認同,有利于團結,同時也體現(xiàn)了僧團在社會中的特色。
東晉時候,佛教得到了空前發(fā)展,寺院增加,僧人和信眾數(shù)量不斷增多,各種弊端也就隨之出現(xiàn),僧眾泛濫、魚龍混雜、管理混亂也引起統(tǒng)治階層的關注和不安。后趙武帝石虎就曾提出質疑:“又沙門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進,然后可為道士。今沙門甚眾,或有奸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偽。”表明僧團所應表現(xiàn)出的清靜莊嚴學修狀態(tài),所應具有的離世脫俗的精神風貌,已為王權和僧俗所認同、所期待。
對此,道安大師十分焦慮:“云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為護持僧團的清靜,以規(guī)約來規(guī)范僧眾,道安根據(jù)自己幾十年的出家生活經歷、修持心得以及對戒律精神的理解,結合當時實際制定出切實可行的《僧尼軌范》《佛法憲章》之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三例制定出來之后,“天下寺舍,遂則而從之”。“天下翕然奉行也”,道安通過對佛學和佛陀制戒意圖的深刻理解,厘定規(guī)制,使僧團進一步融入到了中國特有的環(huán)境、文化、思維當中,從而加快、加深了佛教中國化進程。
率先垂范,從嚴治教
道安法師初出家就“篤性精進,齋戒無缺”,其后師事佛圖澄,佛圖澄“酒不逾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無欲無求”的持戒修行讓道安景仰不已。他在《比丘大戒序》中寫道:“寧持戒而死,不犯戒而生。”可見其持戒之決心。
道安不僅自身嚴格持戒,對弟子們也嚴格要求。《高僧傳·釋法遇傳》中說到一個故事,法遇離開道安后,主持江陵長沙寺,寺中有一個僧人飲酒,法遇沒有將他驅遣出寺。道安用竹筒盛了一根荊杖送給法遇,法遇明白了道安的意思,自責說:“此由飲酒僧也。我訓領不勤,遠貽憂賜。”于是命維那師杖他三下,并寫信跟慧遠說:“吾人微暗短,不能率眾。和上雖隔在異域,猶遠垂憂念,吾罪深矣。”這事感動了許多人。道安的好友東晉名士習鑿齒在致謝安的書中贊嘆道安說:“師徒數(shù)百,齋講不倦,無變化伎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群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可見道安治教的風采。
荷蘭學者許理和對道安僧團的評價是“佛教首次獲得宮廷支持并首次由中國法師領導”,道安法師改變以往由印度或西域高僧主導的局面。早期追隨佛圖澄,代師宣法。后避戰(zhàn)亂,于恒山建寺立塔,接引天下學人,逐漸形成“道安僧團”,并有兩次分張徒眾。
第一次分徒在新野。時值荒年,寇賊縱橫,北方戰(zhàn)亂,他率弟子南下避走,走到新野,決定結合時局、各地風土人情和弟子的個性特點分遣徒眾,命法汰到南下傳法,并說:“彼多君子,好尚風流。”又命法和去四川,說那兒“山水可以休閑”。自己則率其余弟子到襄陽。
后來法汰到建康(今南京),忠實地執(zhí)行了道安“法依國主”的方針,并取得很大成就。法汰人在建康,但與道安保持著密切的通信聯(lián)系。他經常向道安通報建康的佛教情況,并常常寫信向道安請教。法和按照道安大師的安排,來到四川弘法,也取得不錯成績,“巴漢之士,慕德成群”。后來前秦苻堅攻破襄陽,道安被虜?shù)疥P中,法和便從四川趕到關中依止道安。
道安大師第二次在襄陽分張徒眾更是催生了中國凈土宗初祖——廬山東林寺開山祖師慧遠大師。
前秦大將符丕攻陷襄陽,襄陽即將陷落時,道安大師再一次分張徒眾。慧遠看著師父對即將分別的弟子一一叮嚀教誨,對自己卻無所交代,不覺跪在師父面前詢問教訓。道安大師勉勵他說:“如公者,豈復相憂?”由此可看出道安對慧遠是何等的信賴。此后慧遠駐錫廬山,以東林為道場,修身弘道,著書立說,創(chuàng)白蓮社,成為凈宗祖師。
世出世間,圓融無礙
妥善處理政教關系,是宗教在中國獲得以生存與發(fā)展的重要條件。道安首次提出“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的論斷成為千百年來中國佛教的重要原則。道安注重與當?shù)毓倭攀看蠓虻耐鶃恚鋵W問道德吸引了一大批官員和居士名流,“四方學士,競往師之”,“大富長者,并加贊助”,東晉的封疆大吏如桓朗子、朱序、楊弘忠、郤超等都非常敬重他。東晉皇帝還“遣使通問”,發(fā)布詔書,表彰道安弘揚佛教之功,并賜道安同“王公”一樣的“俸給”。前秦軍攻占襄陽俘獲道安、習鑿齒后,苻堅高興地說:“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別人問是誰,符堅說:“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并表示“安公道德可尊,朕以天下不易”。道安大師道德高風,千載以下,仍令人神往。
在與外界接觸交往過程中,道安法師雖倍受各方贊譽和支持,但始終保持了一個出家人的本色,不驕不躁,不卑不亢。如道安來到襄陽后,東晉名士郗超特意派人送來白米千斛,還寫了一封長長的信表示敬意。道安回了一封信,只有一句話:“損米千斛,彌覺有待之為煩。”寥寥數(shù)語道出了人在世間無法做到“無待而逍遙游”的事實,更道出了出家修行的宗旨,親切自然,意味深長。
宗教要長期生存發(fā)展,必須與所處的時代和社會相適應。2016 年和2021 年兩次全國宗教工作會議,都強調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佛教在中國的傳承發(fā)展,就是一部順應時代潮流的歷史。佛教作為外來宗教,在歷代祖師大德的不懈努力下,成為外來宗教中國化的成功典范,佛教文化也成為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宗教中國化不是完成時,永遠是進行時,需要回望來時的路,走穩(wěn)腳下的路,看清未來的路。當前,佛教界也面臨著一些影響健康傳承的因素,例如:有的商業(yè)資本千方百計試圖涉獵佛教領域,借教斂財;少數(shù)出家人法治意識不強,管理能力不夠,不善長處理各種社會關系,僧團內部之間不和睦,或跟社會上其他關系緊張;也有的學修懈怠,對弟子的培養(yǎng)和佛教長遠發(fā)展也缺乏思考和擔當;有的持戒不嚴,追名逐利,貪圖享樂,甚至違法違戒,引發(fā)社會詬病。這些現(xiàn)象雖不是主流,但也腐蝕著佛教肌體,影響其社會形象。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 年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指出,要支持引導宗教界加強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約束,全面從嚴治教,帶頭守法遵規(guī)、提升宗教修為。要加強宗教團體自身建設,完善領導班子成員的民主監(jiān)督制度。強調要培養(yǎng)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詣、品德上能服眾、關鍵時起作用的宗教界代表人士隊伍。這些要求是對上述佛教界與新時代不相適應的諸多現(xiàn)象,努力加強自身建設的對癥良藥。
回望歷史,道安法師是佛教中國化的第一位里程碑式人物,從他的事跡中,我們可以深切體會他在順應時代的思考和探索,并將有助于我們加深對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關于我國宗教堅持中國化方向的理解,有助于我們加強宗教工作黨政干部、宗教界代表人士、宗教學研究這三支隊伍,特別是宗教界代表人士隊伍建設。佛教界有識之士當從祖師大德身上汲取營養(yǎng)和力量,學修精進,嚴持戒律,恪守本份,不斷提升宗教修為,同時,要建章立制,加強管理,自重自律,整飭教風,努力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相適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