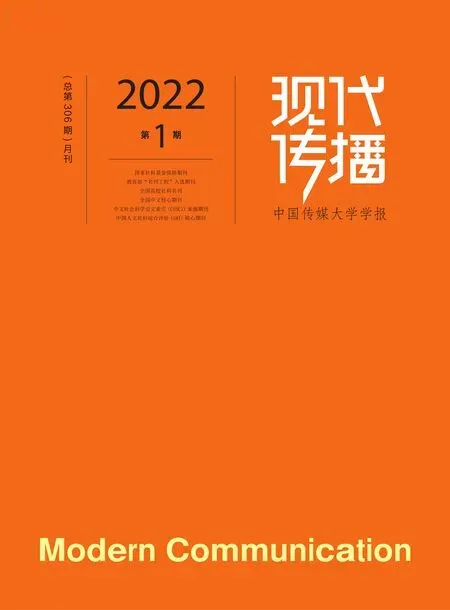無中介性:觸覺媒體的功能、研究及實踐*
梁德闊
一、觸覺媒體時代來臨
早在20世紀90年代,一些有識之士就認為“觸覺時代”(haptic age)到來了。電視出現不久,麥克盧漢(McLuhan)就預判觸覺媒體時代來臨。1964年,他發表了一個著名的宣言,指出電子媒體的新時代不是由視覺來定義,而是由觸覺來定義,因為電子媒體具備模仿觸感的能力,它能夠將信息廣泛地轉換成不同的感官模式。他把觸覺(haptic)理解為各種感官之間的一種綜合的、審美的相互作用,這在感官史的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義。①1999年,羅伯特·吉特(Robert Jütte)在德國報紙上發表宣言,指出“觸覺時代”到來。②日本物學研究會會長黑川雅之(Masayuki Kurokawa)稱,他們正在由視覺時代的20世紀向觸覺時代的21世紀轉變。③觸覺技術是計算機科學的一個新領域,旨在虛擬化觸覺,這種觸覺的人機接口技術發展很快,在此背景下“觸覺時代”反復被提出。霍華德·萊因戈爾德(Howard Rheingold)是一位技術愛好者,他指出機器的崛起必然會帶來身體的重新配置(the reconfigurations of the body),產生“觸覺寫實”(tactile realism),就像電腦圖形可以實現超級寫實主義那樣。④電腦科學家和觸覺學家巖田廣郎(Hiroo Iwata)將20世紀90年代定位為“觸覺界面的時代”。⑤實際上,自從觸覺界面第一次走出實驗室,進入大眾視野后,這種技術就處于一種不受人類意志控制的自我發展狀態,它總是決定性地、徹底地改變著媒介文化,而又無法預測其命運。
因為視覺中心主義長時間、大范圍地占據媒體研究的統治地位,觸覺媒體研究長期被忽視。媒體研究經常會動用一種充滿意識形態特征的、僅憑直覺的理論,該理論想當然地賦予觸覺模式一套基本的、不可改變的生理品質。與視覺感官相比,觸覺特性似乎更堅定地根植于身體的生理能力,不太容易接受批判性干預和詮釋。它是一種直接的、不容置疑的體驗。在數字媒體時代之前,觸感設備和觸覺媒體就已存在。由于對觸覺的歷史和文化生活缺乏正式的、全面的和經驗性的描述,媒體研究提出了觸覺在生理上的即時性和經驗性的概念,它存在于歷史和文化之外。媒體研究的及時性使學者們有機會接觸到越來越豐富的媒體生態,這其中就包含用戶的觸覺,于是學者們重新劃定技術、生物學和文化之間的界限。因此,觸覺媒體研究不僅是對觸覺和力反饋技術日益普及的反應,而且也是對傳統上以視覺和聽覺為主的感官偏好的反應。
觸覺媒體是對視覺中心主義的顛覆。視覺的“觀看”不僅在主體和客體之間筑起一道難以逾越的長城,還使人們與其生活的世界日益疏遠。這種疏遠一方面使人的自由意志如脫韁野馬般一意肆行,另一方面使生活世界徹底表象化地走向一種可自我復制、自我生產的“超真實”的“仿像”世界。這種視覺顛覆和觸覺回歸是從繪畫藝術開始的,印象主義畫家重視色彩的冷暖對比,就屬于觸覺而非視覺。印象派大師塞尚(Paul Cézanne)試圖消解繪畫中的唯視覺傾向,他通過色彩的空間化,旨在建立一種“雕像式”的印象主義。藝術如此,科技也不例外。喬布斯(Steve Jobs)認為“手是最好用的工具”,他推崇用觸覺把握世界,劃時代地發明使用了“觸摸屏”。
隨著觸覺技術在媒體中的廣泛應用,觸覺媒體時代悄然來臨。力反饋機制使觸摸屏能夠更加精確地“回應觸摸”(touch back),Immersion公司的觸摸廣告在傳統的視聽廣告中增加了觸覺技術。Good-enough的第二代虛擬現實(VR)吸引了更多資金流向虛擬環境中的觸覺技術研究,這是因為工程師們認識到“觸覺技術是我們與周圍環境互動方式的核心”⑥。特別是蘋果公司的智能手表(apple watch)和谷歌的“可以感知的游戲”(games you can feel)的上市,成為觸覺技術領域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這將會掀起觸覺技術在視頻、游戲、社交網絡及物聯網等領域的全面推廣和普及。
價格下降和技術發展促進了觸覺技術的推廣和應用。最早的觸覺技術是以推拉方式為主,被用在虛擬現實、機械人控制等領域,需要專業的軟件編程和昂貴的硬件支持,比如生產一個小球,軟硬件成本就高達一萬美元,現在Immersion公司能夠提供價格便宜的元器件(如馬達)和十分方便的軟件及工具,花費不到30美分就能獲得該公司的觸覺技術授權,在各種終端甚至智能穿戴產品上實現十分真實的振動感覺。與此同時,過去開發一項觸覺技術需要5個月時間,現在僅需要5秒鐘。SensAble公司研發的Phantom Premium是迄今為止在研究中使用最廣泛的觸覺設置,但這種觸覺設備的高價格(相比視覺顯示)限制了商業應用。Phantom Omni比Phantom Premium便宜一個數量級,在觸覺與機器人研究中廣受歡迎。2007年,Novint技術公司發布的Novint Falcon,是一個價格更便宜的三自由度觸覺裝置,反過來又比Phantom Omni便宜一個數量級。Novint Falcon的目標是針對娛樂應用,從高保真的研究設備到廉價的娛樂系統,在Novint公司有各種各樣的觸覺設備可以被購買。
與20世紀90年代相比,當下的觸覺媒體時代有哪些新變化呢?主要是媒介和傳播系統中的觸覺技術發生了轉變,這種變化是悄無聲息的,甚至沒有引起傳媒學者的注意。現在所處的觸覺時代是一種技術變革的余震,當觸屏手機、平板電腦和視頻游戲控制器進入日常生活時,媒介觸摸技術已經被馴化,而更先進的觸覺實例化技術已經在醫學模擬、設計工作室和機器人遠程手術上被使用。目前,雖然通過數字接口的存儲、傳輸和重建使觸摸轉向感覺的任務還沒有完全實現,但新觸覺技術流有望完成這項任務。觸覺引擎、觸感網絡、觸覺手套、觸摸魔杖,以及通過振動觸覺和電觸覺刺激系統來模擬觸覺現實的套裝,將會實現人的身體完全沉浸在模擬現實之中的效果。觸覺效果設計為用戶提供“足夠好”或“栩栩如生”的感官體驗,已經成為計算機編程中常規的和正式的分支學科,并附帶一套創建觸感幻覺的最佳實踐。現在觸摸可以通過應用程序編程界面操作,除此之外,軟件和硬件工程師還可以用其它手段來操縱觸摸。盡管這些應用程序偶然也會失敗,但不可否認,新技術已經改變了人們對觸覺的定位——通過觸覺技術,集體感覺器官(collective sensorium)已被無數次改變了。
二、觸覺及觸覺媒體的內涵
(一)觸覺涵義
Haptics(觸覺學)一詞源于古希臘的“haptikos”和“haptesthai”,前者指觸碰(touch),后者指抓住(lay hold of)。嚴格意義上說,觸覺指的是觸覺認知,也就是觸摸表面,源自拉丁語tangere,意為觸碰。廣義的觸覺是指運動感覺或者肌體運動的感覺,運動感覺源自拉丁語kinesis,意為運動和感覺。因此,觸覺信息可以分為接觸反饋和力反饋兩種,接觸反饋是通過皮膚與物體接觸所獲得的全部感覺,如壓覺、摸覺、刺痛覺、震動覺等;力反饋是人的肌肉、關節和韌帶等受到拉伸、壓縮和扭曲時而感知到的力量,如重量、沖力、運動等。觸覺學是在人為控制條件下體驗和產生觸摸感覺的科學和技術,與壓力、震動、疼痛和溫度等感覺轉化相關。它利用游戲桿、數碼手套等特殊的計算機輸入/輸出設備,使用戶在人機互動中獲得真實的觸覺感受。在神經科學和心理學的文獻中,觸覺學研究人類對于接觸的感知,特別是與運動(力/位置)和皮膚(接觸)感受器相關的觸覺。在機器人和虛擬現實的文獻中,觸覺學被廣泛地定義為機器人或人類與現實環境、遠程環境或模擬環境之間的真實的或模擬的接觸互動,或者上述場景的組合。
觸覺無需中介,接觸者和被接觸者以一種極其直接的方式聯系在一起,以至于兩者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是“零距離”的。觸覺不同于視覺、聽覺、嗅覺等,后者的實現和成立,要以一定的時空距離為前提,即以我與感覺對象一定程度的分離為前提。觸覺不需要物質中介,比如視覺有賴于光作為中介,聽覺有賴于空氣作為中介,而觸覺無須借助任何其他物及其性質就伸手可及、唾手可得。觸覺也不需要意識性、思維性的中介,用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話說,精神病人都能迅速用手觸摸到蚊子叮咬的地方,正常人更能“不假思索”地完成觸覺活動。他還解釋了“盲打”現象,這種現象之所以成為可能,就在于一旦我們把打字作為一種解決任務的身體意向的行為,那么打字的鍵盤就會成為自身身體的延伸。在他看來,觸覺是人類生命的“本能”活動,它被置于生命感受性的根本位置。
對觸覺學最重要的全面定義來自于胡塞爾(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在唯我論層面上,胡塞爾認為身體是“雙重的實在”(a double reality),它除了有物理主義的身體之外,還被構成“定位化感覺之載體”(bearer of localized sensation)“意志之器官”(organ of the will)及“定向之中心”(center of orientation)。胡塞爾將個人主觀經驗看作是理解客觀現象的源頭,人的身體及其觸覺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作為一個自由移動的存在實體,身體表達了自發性的功能,正是通過身體的自由活動,一個對象的世界、一個空間物質世界才最終被構成。身體還是所有方向取向的“零點”(zero point),周圍的世界以零點之身展現出不同的距離和方位。感官認知是不同的身體感覺系統的產物,身體感覺系統不停地對它接受到的和處理的信息進行平衡。有意識的聲覺、視覺、觸覺或者嗅覺經驗塑造了一個互動的預判系統,在認知過程中驗證預判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不同感覺存在的事實只有在“自我”從觸覺角度意識到某種感覺是不確切的或者是矛盾的時候才會有所發展,因為其它感覺以及它們提供的那種“相合的綜合”(Deckungssynthesis)或“聯想”,有助于保持認知過程的統一性和連貫性。⑦
(二)觸覺媒體涵義
對于“觸覺媒體”(haptic media),學界尚無明確而統一的定義。僅僅根據人的感官模式或者計算機的物理屬性來界定這個概念,是不明智之舉。帕里西(Parisi)和阿切爾(Archer)對此進行了廣泛的討論,他們認為觸覺媒體應當關注媒介客體(media objects)和主體身體(subjects’ bodies)之間的物理交匯點,須將觸覺作為觸覺媒體研究的中心而不是邊緣。⑧在一些案例研究中,作者解釋了各類觸覺媒體是做什么的,他們對觸覺媒體的定義是在觸覺媒體研究過程中零散地表達出來的,沒有概括性的界定。不過,他們均強調觸覺在媒介系統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持有一種內在的觸覺中心主義,把媒體與觸覺的互動看作是進一步實證研究和理論探索的理想場所。觸覺對媒體研究的重要性,并不僅僅是技術上的熱情,更確切地說,人類與媒體的觸覺對接是一種空間,在這個空間中,身體使用的規范模式被表達和被實施。觸覺媒體的概念提供了一種方法,該方法強調與媒介系統的觸感關系不斷變化的物質性,同時也引起人們對觸覺的文化地位和話語建構的關注。觸覺媒體概念的建設性取向,為媒體研究領域帶來了新的對象、實踐和歷史。通過觸覺重新思考媒體,可以開發出觸覺媒體所具有的潛在價值。
通過計算機虛擬技術,觸覺媒體和浸媒體(immersive media)都可以使用戶體驗到真實的感受。但觸覺媒體區別于“浸媒體”,它是觸覺學研究的分支,給用戶帶來的“真實感受”也不一樣。浸媒體是借助虛擬現實技術(VR)、增強現實技術(AR)和視頻直播等,給用戶帶來沉浸式、體驗式、交互式的體驗。浸媒體使用戶有身臨其境之感,參與到當下正在發生的新聞和事件中,從信息分享轉變為經驗分享。對技術公司而言,讓發送端的海量信息更加充裕地傳送到接收端是最好的解決方法。⑨浸媒體主要依靠人的視覺和聽覺獲取信息,而觸覺媒體依賴觸覺界面直接實現人機互動。觸覺界面試圖通過機械電子設備和計算機控制技術再現或強化操作或感知真實環境的觸覺體驗。它們包括一個觸覺裝置(具有傳感器和執行器的操作模擬器)和一臺控制計算機,控制計算機裝有能夠將相關人類操作輸入給觸覺信息顯示的軟件。為了提升人類操作者在模擬環境或遠程操作環境中的操作水平,觸覺技術尋求產生一種賦予性的感覺信號,使操作者感到真實環境觸摸可及。通過觸摸界面,人們不僅能看到屏幕上的物體,還能觸摸和操控它們。
三、觸覺媒體研究
(一)代表性成果
觸覺領域有兩個期刊:《Haptics-e》(www.haptics-e.org)和《IEEE Transactions on Haptics》。歐洲觸覺學與虛擬環境觸覺界面研討會(Eurohaptics and the Symposium on Haptics Interfaces for Virtual Environment and Teleoperator Systems)是研究觸覺的重要會議,每偶數年各自舉辦,奇數年聚集開會。IEEE的觸覺技術委員會網頁(www.worldhaptics.org)提供相關出版物和論壇的信息。很多關于觸覺研究的書籍,都是以上研討會文章的匯編。網站HapticStudies.org提供一個研究和討論觸覺媒體的博客,分享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新聞,還收集該領域的核心讀物清單,力圖建立觸覺媒體研究的文獻資料庫。
2017年第10期《新媒體與社會》(New Media & society)登載了一組關于觸覺媒體研究的論文,這是重要的代表性成果。杰拉德·戈金(Gerard Goggin)的《殘障和觸覺移動媒體》研究智能手機如何幫助盲人,為蘋果手機設計提供參考。智能手機替換電話導致從按鈕到觸摸屏的轉變,這給視障用戶帶來了導航挑戰,因為他們習慣了按鈕及其物理特性。戈金認為,在蘋果手機問世之前,手機是一種觸控媒體(touch media),對盲人用戶來說,“它所包含的是操縱電話鍵盤,讓屏幕閱讀器聽到信息,從而使用手機的功能。”戈金認為,蘋果手機是視覺障礙維護者和蘋果設計師之間的談判場所,因為它提供了“觸覺媒體和殘疾的政見切入點”。
在《移動媒體、家庭游戲和觸覺民族志》一文中,英格麗德·理查森(Ingrid Richardson)和拉麗莎·哈約思(Larissa Hjorth)認為,將移動媒體設備納入家庭的物理空間,通過建構娛樂和社會交往的新模式,移動媒體會改變家庭成員之間的社會關系。他們將自己的研究定位為民族志的“感官轉向”(sensory turn),發現用戶通過反復觸摸和操縱移動媒體而獲得物質享受(material things),進而他們研究了人與數字媒體建立觸覺親密關系的實用的和常規的習慣。該文是對如何積極建立新的身體聯系的一種經驗知識的探索,同時也是一種方法論,它鼓勵民族志學者關注用戶和設備的關系變化,因為移動媒體會改變其形態并具體化。
詹姆斯·霍奇斯(James Hodges)的《我該如何看待這件事?控制重建的Q*berts》,考察了視頻游戲Q*berts中的觸覺問題。自從20世紀80年代初Q*berts進入商場,該軟件彌補了控制臺和仿真器的不足之處,重新配置了人與游戲的身體交互模式。霍奇斯將游戲視為觸覺媒體的實例化,在保留軟件視聽方面不變的情況下,他思考如何通過改變與游戲文本的身體交互方式來從根本上改變游戲。他說,使用鍵盤而不是操縱桿來玩游戲Q*Bert的原始方式,“會造成觸覺穩定性的斷裂”,因為它需要使用不同的身體技巧來控制和駕馭游戲。隨著人們對保存和展示老游戲的問題越來越關注,霍奇斯建議,保護主義者們將受益于一種“游戲中的觸覺調諧方法”,這種方法對單純的代碼來說是不可簡化的。
黛博拉·盧普頓(Deborah Lupton)的《感覺你的數據:觸摸并理解個人數字數據》一文擴展了她關于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的工作,她通過3D打印的具象藝術(representational technique),探索了量化自我數據的具體化(materialization of quantified self data),其中,“數據身體化”(data physicalizations)鼓勵用戶與抽象的生物自我之間建立新的認知關系。盧普頓建議,“感受你的數據”的過程是作為一種顛覆性的物質平臺,針對數據可視化的典型實踐,而數據可視化則確定了自我技術進入的數量。由用戶的身體而生成的數據,通過3D打印機的過濾器,呈現出有形和物質的存在,顯然比屏幕上顯示的數據“更真實”。將數據的世界與原子的世界結合起來,數據身體化對傳統可視化實踐的視覺中心主義提出了挑戰,再次主張物質與虛擬的相互對立。
克里斯托弗·奧尼爾(Christopher O′Neill)在《觸覺媒體與觸摸的文化技巧:脈搏造影、光學體積描記術和蘋果手表》一文中,考察了從19世紀到21世紀脈沖診斷(pulse diagnostics)的變革實踐。奧尼爾把這種診斷方法視作插補在醫生和病人之間的一種文化技術。正如奧尼爾所主張的那樣,脈搏造影(測量和記錄脈搏的過程)逐漸被當作病人整體健康指標的一部分。恰當的和不恰當的脈沖診斷技術都會在社會協商過程被賦予權威性,醫生的“受過教育的手指”遇到了可以測量脈搏的新機械技術的挑戰。可穿戴數字健康追蹤器的出現,特別是它被放置在蘋果手表中,通過光學體積描記測量裝置與佩戴者的手腕接觸,進一步取代了醫生的權威。對奧尼爾來說,光學體積描記術是一種觸覺調解的形式,蘋果手表中的光感傳感器弱化了醫生的作用。光學體積描記術通過參與一種更普遍的醫學觸摸的去技術化和自動化,將醫療權威從訓練有素的人轉移到解譯演算法(interpretive algorithms)上。
瑞秋·普洛特尼克(Rachel Plotnick)的《力度、平面和沒有感情的觸摸:關于觸覺和按鈕的歷史思考》一文,考察了電動按鈕的去物質化(dematerialization),這是由移動通信觸摸屏界面來完成的;以及電動按鈕的再物質化(rematerialization),這是以可視觸摸屏圖標的形式、通過用戶手指與電容式屏幕之間的接觸而激活的。以19世紀末電動按鈕的最初使用為起點,普洛特尼克的歷史譜系學研究顯示,早期的按鈕是如何引發一場道德恐慌的,這是對自動化帶來的潛在的去技術化和非人性化效果的恐慌。這種擔憂預示著當代的爭論,這些爭論是關于我們的文化迅速擁抱觸摸屏界面的后果——聲稱物理按鈕的消失帶來有害的、情感的和認知的效應,這些聲稱反映了人類與機器的邊界之間正在進行的文化斗爭。將按鈕視為觸覺媒體,這無論是在媒體歷史編纂領域還是關于觸摸的媒體歷史檔案中,都暴露出一個更大的漏洞:幾乎沒有學者對媒體界面的物質性進行索引和分析。普洛特尼克的文章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一種模式,同時也展示了將觸摸作為專門研究對象的價值。
上述六篇文章展示了觸覺媒體研究的價值,反映了觸覺媒體研究的最新成果。每一篇文章都為觸覺媒體研究增加了一個層面,要么暗示其基礎,從而提出交叉學科,擴大21世紀新媒體研究的范圍;要么提供工具,重新設想媒體研究的過去。這種新的觸覺方向對媒體研究有利,更全面地將觸覺方向與各種方式結合起來,又通過這些方式將感官和媒體共同構建。
(二)跨學科研究
觸覺技術試圖提供在虛擬和遠程控制環境中進行人工操作的令人信服的感覺,這是一種相對較新的技術,同時也是發展最快的技術。這個領域不單將機器人學和控制理論作為根本基礎,還得益于人文科學領域,特別是神經科學和心理學。
人類神經系統的運動感覺功能和觸動感覺功能在觸覺學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前者是指在肌肉、韌帶和關節中感知運動和力量的內在感知功能;后者是指對皮膚變形的感知功能,觸覺是兩者的整合。運動覺的感受器位于肌肉、肌腱、關節和皮膚中,當這些感受器通過壓力覺察到位置的變化時,它們便把這種機械能轉化為神經能。神經能可以對變化的速度、骨頭的角度、肌肉的緊張度等信息進行編碼,然后這種信息被上傳到脊髓,最后傳遞到大腦,由小腦進行自動加工和協調。物體觸壓在皮膚上會引起皮膚的變形,從而產生觸動感覺。比如,溫度刺激作用于皮膚時會產生冷覺與熱覺,這是因為皮膚中有不同的感受器,它們能感覺到觸摸、痛、壓力和溫度等刺激。觸覺感受器末端有許多不同的球型小體,這些球狀細胞分布在皮膚的各層上,并對不同類型的觸壓刺激敏感。
在心理學方面,20世紀80年代,萊德曼(Lederman)和克拉茨基(Klatzky)定義了手的運動原型,并稱之為探索方法。他們發現八種探索方法及其最適用的物體屬性:橫向運動(紋理)、按壓(硬度)、靜接觸(溫度)、無支撐持有(重量)、封閉輪廓(全部形狀,體積)、輪廓跟蹤(精確的形狀,體積)、部分運動測試(部分運動)、功能測試(特定功能)。這些探索方法涉及與手掌表面的接觸、手腕的運動、各種自由度、皮膚的觸覺和溫度感覺,以及手的動感感覺。如果你要確定物體的重量,可以舉起它,通過上下移動手并產生來自皮膚、關節和肌肉的刺激方式;測量物體的一致性(比如軟硬、塑性或剛性程度),可以擠壓它或拉伸它,擠壓一個物體能夠知道它的軟硬程度,拉伸它能夠知道它的彈性。
心理物理學是研究如何設計觸覺設備的數據寶藏。它把刺激的物理特征和心理反應聯系起來,相比生理學和解剖學位于更高一級的水平。心理物理學的首要貢獻在于設計思路,觸覺研究者應用它回答了關于什么是觸覺裝備所必備的能力問題。這些感官能力必將轉化為設計需求。一些主流的心理物理學方法在觸覺學方面有著豐富的應用,其中包括通過限制和自適應自上而下的方法進行閾值測量。然而,閾值的感知并不是100%可靠的。感知精度往往取決于刺激強度,以及在命中率與誤報率之間的權衡,而權衡很大程度取決于在一個給定的時間間隔內所呈現的刺激的概率。
四、觸覺媒體的開發應用
(一)觸覺媒體應用
用觸覺替換視覺和聽覺,解決盲人和聾啞人的信息獲得問題,是觸覺媒體的最顯著功能之一。盲人要想閱讀計算機屏幕和獲取基于文本的信息,可以借助盲文顯示系統、盲文閱讀器和觸覺鼠標來實現愿望。通過給用戶指尖提供觸覺反饋,觸覺鼠標可以使盲人用戶在計算機屏幕上導航,識別圖形、圖片和文本等。英國格拉斯哥大學Brewster等人發明了Tacton,這種觸覺圖標是結構化的和抽象化的,可以用來替代視覺圖標和聽覺耳標傳達信息。1998年,斯坦福大學研制出Moose,它定義了帶有力反饋的Window窗口,在拖放邊框、滾動條時盲人能明顯感覺到這種裝置產生的作用力。Immersion公司生產的Logitech Wingman鼠標也與Window窗口一樣具有力反饋功能。這兩項觸覺技術適合盲人網頁瀏覽。Magnusson等人利用PHANTOM裝置和VRML語言建立了一個有力反饋的人機交互界面,幫助盲人感知3D表面。盲人和高度近視人士無法訪問數字化存儲的數值數據資料,一種較為常見的訪問方法是他們依賴數據的聲音反饋,但導航和訪問數據的方式通常是串行的和吃力的,這可以借助圖形圖像的力覺表達系統來完成。Fritz等人研究利用PHANTOM等三維反饋裝置表達復雜圖表和數學模型。日本筑波大學Iwata等人開發出Feelex,它是3D物體輪廓顯示系統,可以模擬與柔性物體表面接觸的效果。SmartTouch系統能夠將視覺圖像轉換成觸覺信息,并通過電刺激人的指尖顯示盲文。
模擬訓練動手醫療過程是推動觸覺虛擬環境研究的重要動力之一。從抽取血液樣本到外科手術,醫學侵入性治療診斷過程對病人而言有潛在的危險和痛苦。具有觸覺反饋功能的仿真器的目標是取代直接在病人身體上的輔導學習,醫生通過觸覺信息的介入去體會學習動手技能。仿真器在開發微創手術技巧方面已被證明高度有效,尤其是在早期訓練時提供觸覺反饋。對于觸覺模擬器訓練的預期益處包括:在訓練期間和之后降低病人危險;提升模擬非常條件或醫療緊急情況的能力;在培訓過程中收集物理數據,為學生提供具體、直接的反饋。模擬器設計方法、特殊醫療應用和培訓評價方法在過去二十年中得到廣泛的研究,然而,這種技術的成本仍然很高。此外,在模擬器技術中哪些技術得到改進,總是很明確的。
Immersion公司成立于1993年,專注于觸覺技術研發。Immersion公司生產的數據手套Cryber-Touch,可以為人手提供振動觸覺。CyberForce可以把力反饋信息傳遞給整只手和手臂。用手抓取物體時,Cyber-Grasp能為五個手指提供力反饋信息。由該公司生產的TouchSenser技術為手機、汽車、游戲、醫療等提供各種觸覺體驗。公司為生態鏈上的伙伴提供開發工具和軟件、觸覺效果庫等,將觸覺反饋應用推向所有領域,并在社交、游戲、視頻等生態鏈方面重點開發。蘋果手表的智能表情符號是在社交網絡中最常用的觸覺媒體。目前,微信、元宇宙、易信等社交網絡都在試用“表情符號”。Immersion公司在電影《國土安全》中使用了觸覺反饋技術,結果觀眾數量增加了5倍,并且愿意花費更多時間觀看。
觸覺技術雖然沒有在娛樂業以外廣為商業應用,但是它們正在被大量集成到實際應用中,一些新穎的創造性應用正在開發,包括輔助技術、汽車、設計、教育、娛樂、人際交互、制造/裝配、醫學模擬、微/納米技術、分子生物學、假肢、康復、科學可視化、空間技術、外科手術機器人。比如,在豪華汽車中駕駛,駕駛者經常會失去速度的感覺。出于安全考慮,設計師想出了一種可以制造震動的辦法,當車子達到某一速度時,這種觸感可以幫助駕駛者意識到他正在行駛的車速及其危險性。
(二)從按鈕到觸摸屏
“按鈕”(button)來自法語,意思是“突起”,用力可以將它從一個界面推向另一個界面。它既有發起的力,又有突出界面本身的力。當人們按下按鈕后,機器獨自在工作,這不是真正的觸摸,也沒有人的情感投入,用戶僅是一個旁觀者。用戶“脫離接觸”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用戶的活動似乎與觸覺、感覺或接觸沒有任何相似之處,他們根本沒有進行觸摸,而只是機械地為機器服務。其次,用戶按下按鈕后便立刻與其使用的技術疏遠開來,他們變得無所作為和情感缺乏,只是“代表”和管理,而不是互動。帕爾默(George Palmer)說:“我按下按鈕后,我的直接力量就終止了,與那個按鈕相連的電線會產生各種各樣的效果。但關于這種傳導的細節,我什么也不需要知道。……它的工作不是我的,而是它自己的。”鮑德里亞(Baudrillard)認為,按鈕、施壓等行為使人成為“全球化過程中的演員,人類不過是其中的角色,或僅僅是旁觀者”。塞爾多(De Certeau)也描繪了一個同樣慘淡的畫面:一位女士將她一整天的時間都耗費在按壓按鈕這件事情上,“(她)將自己的感情和力量釋放到一個按鈕的按壓之上,并在不控制中間步驟的情況下被動接收信息”。她已經“成為拙劣的旁觀者,看著機器在她面前發揮功能”。本杰明(Benjamin)在研究19世紀的技術時說,當打電話、拍照和開關按鈕時,“手的一個突然的移動”會導致一種心理上和生理上的中斷。哲學家傅拉瑟(Vilém Flusser)預言,在未來的世界里“手已經變得多余和萎縮”,只留下指尖進行著缺乏真正力量的“程序化的自由”(programmed freedom)。
在1999年末摩托羅拉公司發布A6166之前,人們從來沒想到過把觸摸屏和手機結合在一起,今天觸摸屏已成為智能手機的標配。觸摸屏是一種簡單、方便、自然的人機交互方式,現在廣泛應用于電子游戲、公共信息查詢、多媒體教學等。相比較機械按鈕,觸摸屏更加省力。只要你用手指在觸摸屏上輕柔地觸摸一下,就可以控制強大的引擎,毫無疑問,這會減少肌肉的力量。在操作過程中,控制與被控制同力量的大小沒有任何關系,不管被控制力增加多少,而控制力則保持不變。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標志,標志著意志力控制肌肉的力量。
平面美學吸引了藝術史學家和哲學家們的注意力,他們注意到了從深度到平面的普遍性轉變,認為這是一種設計價值。詹姆遜(Jameson)指出:“一種新的平面或無深度也許是所有后現代主義的最高形式特征,這是望文生義的、膚淺的理解。”一些藝術史家、建筑學家和媒體研究學者反對平面化的審美,認為這種審美鼓勵毫無深度的并且缺乏情感反應的互動。反對扁平化觸摸屏的人提出,這些觸摸使用戶在兩個水平上缺乏“感覺”——他們不能以看到或聽到的方式感知(觸摸)數字信息,也不能“真正地”或有情感深度地參與世界。班納什(Banash)解釋說,“深度的損失讓當代人幾乎無事可做,除了從一個表面滑動到下一個表面,人們無法定位自己與世界的關系”。用戶和設計師抱怨扁平化設計讓人感覺不到環境和控制的變化。他們將數字觸覺經驗描述為脫離實體的和不連續的,“我們的視覺器官和聽覺器官都沉浸在數字信息的海洋中,而我們的身體仍然被囚禁在物質世界中。……不幸的是,人們不能通過手和身體感覺到并確認這種數字信息的虛擬存在”。
觸摸屏缺少觸覺反饋,使用者只能依賴視覺和聲音來控制。你用力地還是柔和地敲擊鋼琴鍵盤,就會彈出不同強度的聲音,這是人類觸摸的效果。而當你點擊蘋果手機的觸摸屏時,卻什么也感覺不到。每一個按鈕都是一樣的,每一個動作也都是一樣的。因為觸摸屏是非接觸式界面,我們的手指只能在玻璃表面點擊和滑動,當然什么感覺都沒有。作為人們最重要的感覺之一的觸覺,在觸摸屏上沒有用武之地。用戶在觸摸屏上獲得的感受基本沒有區別,因為觸摸屏沒有產生任何物理變化,這使用戶很難找到圖標、超級鏈接、文字框或其它可選擇的用戶元素。這和我們已經習慣的方式大不相同。當我們按下一個真正的按鈕時,它的位置會變化,會有不同的聲音和觸感,讓我們知道它接受到了指令,而觸摸屏不會如此。沒有觸覺反饋,盲人使用者無法區分不同的點擊區,他們只能感覺到平滑的、冰冷的玻璃。這種適合殘疾人的需要引發對于控制面板開關和按鈕設計的需求重新興起。
近幾年,科學家試圖通過各種“觸覺”的干預措施來解決這一問題,如蘋果的“力度觸控”(Force Touch)(后改名為“3D觸覺”),旨在創造一種體驗,讓用戶在用觸摸屏時能感到“你正在按壓一個機械按鈕,事實上你只是把手指對準一個靜止的玻璃”。這種重新注入力量回歸觸覺的概念,不僅是一個技術創造方面的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和感官問題。科學家們還試圖將情感與觸感區分開來,以使觸感更可預測、更合理、更有效。帕里西(Parisi)指出:“觸感現代性(tactile modernity)”要在認識論上把感官加以分類,觸感體驗必須從非理性的和本能的沖動中分離出來,以便重新劃分觸感和設定“觸覺主體”。兩者的區分割斷了原始的、人的觸摸與科學的、機械的觸摸之間的聯系。區分觸摸的信息收集功能和它的情感表達功能,使人很容易想象到作為個體性的觸感和現代性的觸覺主體之間的沖突——觸摸動作是一種有序的、可預測的、可測量的操作,還是一種藝術的、親密的、情緒化的自我表達。
五、結語
學界雖沒有對“觸覺媒體”進行明確和統一的界定,但普遍認為“觸覺”是解釋觸覺媒體的關鍵,強調媒介客體和主體身體之間的物理交匯點。研究者更加關注觸覺媒體是做什么的,在案例研究中,他們往往持有觸覺中心主義。觸覺媒體的概念是建設性的,為研究者提供了一種方法論。觸覺媒體與浸媒體不同,觸覺技術使用戶感到真實環境觸手可及,而不是浸媒體的身臨其境感。
發表在《新媒體與社會》的六篇文章是觸覺媒體研究的最新成果,其得益于計算機科學、神經科學和心理學等。在實踐中,用觸覺替換視覺和聽覺,解決盲人和聾啞人的信息獲得問題,是觸覺媒體的最顯著功能。同時,按鈕不是真正的觸摸,也沒有人的感情投入,用戶僅是一個旁觀者。相比較機械按鈕,觸摸屏更加省力,是深度向平面的轉變。扁平化的觸摸屏缺少觸覺反饋,人們不能以聽到或看到的方式感知數字信息,也不能“真正地”或有感情地參與世界。科學家試圖通過各種觸覺干預加以解決,如蘋果的“3D觸覺”旨在創造一種體驗。科學家還試圖將情感和觸感區分開來,以化解作為個體性的觸感和現代性的觸覺主體之間的沖突。
注釋:
① McLuhan M.UnderstandingMedia:TheExtensionsofMan.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64.p.152.
② Robert Jütte.AHistoryoftheSense:FromAntiquitytoCyberspac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5.p.237.
③ [日]黑川雅之:《世紀設計提案:設計的未來考古學》,王超鷹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頁。
④ Rheingold.VirtualReality.New York:Touchstone.1991.p.139.
⑤ Iwata H.HistoryofHapticInterface.Grunwald(eds.).Human Haptic Perception:Basics and Applications.Basel:Birkhauser.2008.pp.355-361.
⑥ Abrash M.OculusConnect2Keynote.https://v.qq.com/x/page/e0198javxwp.html.2019.12.
⑦ [德]邁克爾·厄爾霍夫、蒂姆·馬歇爾:《設計辭典:設計術語透視》,張敏敏、沈實現、王今琪譯,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82-183頁。
⑧ D.Parisi,M.Paterson,J.E.Archer.HapticMediaStudies.New Media & Society,vol.19,no.10,2017.p.1517.
⑨ 侯麗:《“浸媒體”:傳播創新關鍵詞》,《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10月31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