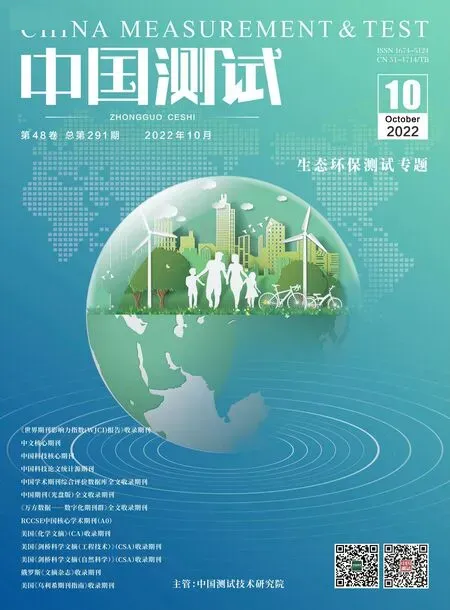高分子材料生物降解性檢測方法研究進展
黃開勝,趙 彥,張錫輝,丁琪琪,,徐董育
(1. 深圳市計量質量檢測研究院,廣東 深圳 518000; 2. 清華大學 深圳國際研究生院環境與生態研究院,北京 100084)
0 引 言
塑料因其良好的機械性能、可加工性、耐用且價格低廉等優點,被廣泛用于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作為全球最大的塑料生產國與消費國,我國塑料制品年產量逐年遞增,塑料表觀消費量于2019年突破1.26億噸[1]。由于分子量大且結構中含有大型取代基團,塑料很難被微生物通過脂肪酸氧化反應降解,導致塑料使用量的增加伴隨著固體廢物和塑料垃圾的快速累積,最終引起白色污染問題。據統計,全球海洋里現有將近5.25萬億噸的塑料碎片,其中92%為微型塑料。這些碎片可作為載體吸附大量污染物并富集在海洋動物的體內,最終通過食物鏈回到人類身上[2-3]。海洋中塑料微珠的發現加劇了人們對塑料污染的關注[4]。在2015年的聯合國環境大會上,微塑料污染與氣候變化、臭氧耗竭和海洋酸化并列為重大全球污染問題。全球現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提出了“限塑”和“禁塑”相關政策。我國國家發改委和生態環境部于2020年1月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見》,首次將塑料污染治理上升到國家層面。同年7月,國家發展改革委、生態環境部、工業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門聯合印發《關于扎實推進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為做好塑料污染治理工作,明確階段性任務部署。
值得注意的是,關于塑料垃圾的處理早有研究,不同國家地區采取的處理方式較為相似。首先,從源頭上減少對塑料制品的使用以降低廢棄物的產生量,其次提倡塑料制品重復使用和回收再利用,最后優化廢物的處理方式(如圖1[5-6]所示)。然而,由于塑料制品種類多且用途廣,尤其是塑料包裝、購物袋和餐具等一次性塑料制品,較難實現統一管理,常被任意遺棄或從垃圾循環處理系統中泄露到環境中去。因此,塑料廢棄物回收成本高且再利用價值低,目前僅有10%左右的塑料垃圾被循環再利用,大部分的塑料廢棄物依然是通過焚燒或填埋處理[7]。生物降解材料的出現為規避這類環境污染問題提供了一種有效手段。

圖1 塑料廢物處理策略
生物降解材料是指在自然界如土壤、沙土等條件下,或特定條件如堆肥、厭氧消化或水性培養液等條件下,能被微生物作用降解,并最終完全降解變成二氧化碳(CO2)或/和甲烷(CH4)、水(H2O)及其所含元素的礦化無機鹽以及新的生物質的材料。中國塑料加工工業協會秘書長馬占峰等人指出,政策導向為生物降解材料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塑料加工行業將繼續推進綠色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化建設目標,生物降解塑料及產品的需求將呈爆發式增長[1]。然而,目前生物降解材料產能過低,無法滿足市場需求。相比于傳統塑料,生物降解塑料的成本較高。這導致市面上的降解塑料材料魚目混珠,偽降解塑料制品層出不窮,真假難辨。因此,塑料制品的生物降解性檢測對于市場監管至關重要,本文羅列了一些常見的生物降解材料,并對現有的生物降解性檢測方法進行歸納整理,分析其優缺點,提出相應的改進意見。
1 常見生物降解材料
生物降解材料需要微生物能夠對其所有有機成分進行消化代謝。一般來講,生物降解涉及幾個關鍵步驟(如圖2[8]所示),分別是微生物在材料表面定植,微生物分泌胞外酶,胞外酶將聚合物降解為低分子量化合物,微生物消化代謝低分子量化合物使其轉化為自身生物質或以CO2的形式釋放。

圖2 聚合物生物降解過程的關鍵步驟
生物基頂尖研究機構nova-Institute最近發布的報告顯示,全球生物塑料產能增長迅猛,將從2018年的211萬噸左右增長到2023年的262萬噸[9]。天然多糖類聚合物如纖維素衍生物、熱塑性淀粉(TPS)及其混合物,憑借其價格低廉,來源廣泛易得的優勢,正在逐漸取代傳統塑料應用于柔性薄膜包裝領域[10-11]。聚乳酸(PLA)是目前學術界和工業界研究最為廣泛,產業化成熟度較高的一種生物降解材料,具有無毒無刺激、強度高、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可加工性等優點,有望替代聚苯乙烯(PS)和聚丙烯(PP)應用于包裝領域[12-13]。聚羥基脂肪酸酯(PHA)是一種天然高分子生物材料,可由多種微生物合成,具有優良的生物相容性、生物可降解性和塑料熱加工性能,可作為生物醫用材料和生物可降解包裝材料。據統計,PHA樹脂相關的國際專利數量僅次于PLA樹脂[14]。聚己二酸-對苯二甲酸丁二酯(PBAT)是己二酸丁二醇酯和對苯二甲酸丁二醇酯的共聚物,具有優良的延展性、耐熱性、抗沖擊性和斷裂伸長率等[15]。值得注意的是,PBAT的生物降解性一直備受爭議,直至2018年Michael等提出使用13C標記聚合物,并利用納米級二次離子質譜(NanoSIMS)跟蹤分析13C從可生物降解聚合物到二氧化碳和微生物生物量的整個轉化過程,明確證實PBAT的每個單體單元的碳均可被土壤微生物(包括絲狀真菌)利用來獲取能量并形成生物量[16]。PBAT是由BA鏈段(脂肪族鏈)和BT鏈段(芳香族鏈)聚合而成的半晶狀共聚酯。研究表明,相比于芳香族域(BT鏈段)和結晶區,脂肪族域(BA鏈段)和無定形區域更容易水解和生物降解[17]。聚丁二酸丁二醇酯(PBS)是由丁二酸和丁二醇經聚合而得的典型的可生物降解材料,用途極其廣泛,可用于包裝、餐具、化妝品瓶及藥品瓶、一次性醫療用品、農用薄膜、農藥及化肥緩釋材料、生物醫用高分子材料等領域。最新報告顯示,PHA的年產量約為25 320噸,占全球生物塑料產量的1.2%,PBAT和PBS的產量分別占比13.4%和4.3%[9]。聚己內酯(PCL)是由ε-己內酯單體在特定金屬催化劑的催化條件下開環聚合而成,可通過改變聚合反應條件來控制其分子量,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及生物降解性等,被廣泛應用于藥物載體、可降解塑料、納米纖維材料等領域。表1羅列了一些常見的生物降解材料及其特點和應用。

表1 常見生物降解材料
2 生物降解性檢測方法
目前,關于生物降解性檢測方法的研究有很多,大體可分為三類,即好氧微生物降解、厭氧微生物降解和其他檢測方法。
2.1 好氧微生物降解檢測方法
好氧微生物降解是指微生物以樣品中的有機物作為碳源,在有氧的條件下進行好氧代謝,經過一系列生化反應轉化為二氧化碳、水和生物質的過程。依據降解環境不同,好氧微生物降解檢測方法可分為土壤有氧環境、淡水有氧環境、海水有氧環境和堆肥環境。
2.1.1 土壤有氧環境
土壤有氧環境降解檢測方法是將薄膜狀或其他形狀的樣品埋置于土壤中,在一定溫度濕度條件下,樣品受熱、氧、水和微生物等因素作用而發生降解,通過定期測試樣品的力學性能變化、分子量變化以及質量損失等來評估其生物降解性能的測試方法。翁云宣等[27]將聚乳酸(PLA)和聚己二酸丁二酯-對苯二甲酸丁二酯(PBAT)按40∶60的比例混合并澆鑄成膜,對比研究PLA、PBAT和PBAT/PLA 薄膜樣品在土壤環境中的降解過程。通過使用SEM、DSC、TGA、IR和元素分析儀等手段對降解過程中的樣品進行分析,作者發現在PBAT、PLA和PBAT/PLA樣品的分子結構中,碳原子含量降低,氧原子含量增加。降解前后,PBAT/PLA共混物中各組分的熔點變化與各自單體聚合物的熔點變化基本一致,但共混體系中的PBAT和PLA的生物降解率與單一材料的生物降解率不同。在模擬農用地膜的使用環境下,Rudnik等[28]通過采用不同的暴露方法,對比研究了聚乳酸(PLA)和聚羥基烷酸酯(PHA)在土壤中的生物降解行為。結果表明,PHA比PLA更適合用作農業地膜的原材料。
土壤有氧環境下的檢測標準有ISO 11266、ISO 17556(即 GB/T 22047)和 ASTM 5988等。ISO 11266主要測定各種有機組分,ISO 17556(即GB/T 22047)主要測定材料的生物分解能力。在GB/T 22047中規定,在平穩階段或試驗周期(6個月)結束時,參比材料的生物分解百分率需超過60%,且兩個空白試驗燒瓶的生物需氧量(BOD值)或二氧化碳釋放量的相對偏差不超過20%,試樣結果方為有效。土壤有氧環境是模擬自然界土埋法而開展的生物降解性能檢測方法,具有很高的實際應用價值。然而,材料的降解效果與土壤性能指標(如土壤組分、微生物種類等)密切相關。由于受氣候、植被等因素的影響,各個地區很難采用統一的試驗土壤,導致土壤有氧環境的降解結果重現性較差[29-30]。而且,在降解過程中,很難完全收集塑料制品裂解產生的小碎片,因此,通過質量損失評估材料生物降解性存在缺陷。
2.1.2 淡水有氧環境
淡水有氧環境降解檢測方法是將實驗材料作為好氣微生物的唯一碳源,通過測定好氧微生物在水性系統中生長繁殖所消耗的氧氣量或釋放的二氧化碳量來評估材料的生物降解性能。生物分解率是生化需氧量(BOD)和理論需氧量(ThOD)的百分比或釋放的二氧化碳量和二氧化碳理論釋放量(ThCO2)的百分比。
淡水有氧環境下的檢測標準有ISO 14851(即GB/T 19276.1)、ISO 14852(即 GB/T 19276.2)、ASTM D5209、JIS K6951、ISO 9439、ISO 14593、OECD 301 A&F和EN 14047等。GB/T 19276.1和GB/T 19276.2是在好氧環境中進行測試,前者通過測定密閉呼吸計中的需氧量來評估材料的分解能力,后者通過測定釋放的二氧化碳亮來倒推材料的生物分解能力。在試驗周期(不超過6個月)結束時,空白燒瓶的BOD或二氧化碳釋放量不得超過經驗值的上限(這個值與接種物的數量相關)。由于降解反應在水介質中進行,微生物與試樣接觸均勻,所以此方法的重復性較好,可反映自然界淡水系統中材料的生物降解情況。適用于單一聚合物、水溶性聚合物、共聚物和含有添加劑的塑料材料等;但是,僅通過測定材料生物分解過程中的氣體釋放量來評估材料的生物降解率,無法觀察試樣本身的形態變化,水介質與試樣的吸附作用、試樣的形狀、試樣組分中含有的低分子物質或添加劑等都會對降解結果產生影響。
2.1.3 海水有氧環境
塑料垃圾對海洋環境的污染日益嚴重,每年有數百萬噸塑料垃圾在海洋中堆積,對生態系統、公眾健康和經濟造成多重危害。受潮汐、洋流和海洋褶皺影響,密度較大的生物降解材料可能下沉到亞海岸并到達海底表面。從海水表面至深海層,沉積物狀態從有氧到缺氧再到厭氧,呈現出急劇變化的氧梯度。在實驗室條件下,模擬海洋中不同海水沉沙區域棲息環境(如在海洋科學中被稱為亞濱海區的陽光可照射到的底棲帶),可通過測量塑料材料在接觸海洋沉積物時的CO2逸出量,來評價塑料材料的生物降解性能。依據國際標準ISO 19679(2016) 測定海岸帶海水-沉積物界面中非浮動塑料材料的好氧生物降解的試驗方法,Briassoulis等[31]在實驗室模擬條件下對4種塑料材料(包括LDPE、PHB、PBSeT和PBSe)進行生物降解性能評價并對該標準提出了改進意見。研究發現,在生物反應器中攪動海水表面可以提高海水-沉積物界面上氧氣的持續可用性(如圖3所示),從而在模擬真實的濱海環境的整個測試過程中保證好氧生物降解條件。

圖3 (a) 模擬海水降解反應器;(b) 用于攪動海水表面的磁力攪拌子
海水有氧環境下的檢測標準有ISO 18830、ISO 19679和ISO 22404。禁限塑令的實施起源于海水中塑料微珠的發現,因此,從根本上來看,在海水環境下評估塑料材料的生物降解性更具有實際意義。但是,海水本身的高鹽度使得其微生物濃度及豐富度較低,存在檢測周期長(一般為兩年)的問題,不適合作為市場監管的檢測方法。
2.1.4 堆肥環境
20世紀80年代以前,堆肥很少被用于處理固體廢物(歐洲為4%,美國更少)[32]。直到1994年,歐盟成員國發布的《包裝及包裝廢棄物指令》中明確規定堆肥法可作為處理包裝廢物的一種途徑。隨后,通過控制反應濕度、溫度、pH和停留時間等重要參數,使用堆肥法處理固體廢物的研究逐漸增多。在實驗室模擬測試條件下,細菌,真菌、霉菌和放線菌均可作為活性微生物用于降解實驗[6]。為了研究聚羥基脂肪酸酯(PHAs)的化學結構對其生物降解性的影響,翁云宣等[33]依據ISO 14855-1,對比研究了聚羥基丁酸酯 (PHB),PHBV(40%HV),PHBV(20%HV),PHBV(3%HV)和 P(3HB,4HB) (10 %mol 4HB)在受控堆肥條件下的生物降解行為。結果表明,PHAs的生物降解速率受其化學結構的影響,5種材料的生物降解速率由大到小依次為P(3HB,4HB) (40%mol 4HB),PHBV(40%mol HV),PHBV(20%mol HV),PHBV(3%mol HV),PHB。
工業殘留物、城市固體廢物和農業廢物中的木質纖維素累積量逐年遞增。木質纖維素材料的降解主要受到兩大技術瓶頸的阻礙,即木質纖維素的難降解性和缺乏高效的木質纖維素嗜熱分解微生物[34]。Wang等[35]通過利用原子力顯微鏡(AFM)、X射線光電子能譜(XPS)和13C核磁共振能譜(13C NMR)等技術,觀察了木質纖維素在堆肥條件下降解過程中的成分和結構變化。結果表明,降解后的木質纖維素總碳含量較初始含量降低了27.7%,總氮含量由1.1%增加到1.8%。水溶性碳、水溶性氮和水解酶活性在3~14 d之間波動較大,此為堆肥過程的活躍期。通過對XPS譜圖分析發現,可降解碳組分主要為C1(含C-H或C-C鍵),與初始量相比降低了25.5%。核磁共振結果(圖4)顯示,共振信號以氧烷基碳為主(76.6%~83.1%),烷基碳在8.1%~10.2%之間波動,進一步證實了木質纖維素的有效降解。

圖4 木質纖維素中在降解周期0、7、14和28天的13C NMR圖譜和RNMR-C/Ash值
堆肥環境下的檢測標準有ISO 14855(即GB/T 19277)、ASTM D5338、EN 14046、JIS K6953、ISO 14855和AS 5810等。ISO 14855是評價塑料制品生物降解性的最常用的堆肥方法。ISO 14855描述了一種標準的堆肥試驗,該試驗基于在好氧條件下通過測量CO2釋放量來評價材料的生物降解性能。在ISO 14855中,為了論證聚合物材料的生物降解指標和保證材料在180天內能達到最大降解程度,接種和測試參數都盡量設置到最優條件。然而,有研究表明,通過測定CO2釋放量來計算試樣材料的生物降解率的方法并不一定準確。CO2釋放量與聚合物分子量的減少、力學性能和化學結構的變化不直接相關,CO2的產生可能來源于添加劑,著色劑等其他物質,而非聚合物樹脂本身[32]。此外,由于堆肥中微生物的種類受其儲存條件(如溫度、濕度等)的影響,通過使用在不同時間和溫度下儲存的堆肥,Yang等人對比研究了不同時間和溫度下儲存的堆肥對纖維素、聚己內酯(PCL)和聚丁二酸丁酯(PBS)生物降解過程的影響[36]。結果發現,該實驗過程中纖維素的降解幾乎不受堆肥的貯藏時間和溫度影響,而PCL和PBS的生物降解性與貯藏條件密切相關。這表明纖維素可能并不總是適合作為評估樣品生物降解性能的參比樣本。
2.2 厭氧微生物降解檢測方法
厭氧微生物降解是指微生物在厭氧條件下,對樣品中的有機物進行厭氧消化代謝,轉化為甲烷、二氧化碳和生物質的過程。依據降解環境不同,厭氧微生物降解檢測方法可分為水性培養液厭氧環境、活性污泥厭氧環境和高固態厭氧環境。
2.2.1 水性培養液厭氧環境
水性培養液厭氧環境降解檢測方法是在水性培養液中以洗滌并稀釋后的消化污泥(含極少量無機碳且總干固體濃度在1~3 g/L)為厭氧菌源,通過測定樣品在密閉條件下厭氧消化降解為二氧化碳和甲烷的產生量來評估樣品生物降解性能的方法。
水性培養液厭氧環境下的檢測標準有ISO 14853(即GB/T 32106)。與淡水有氧環境一樣,由于降解反應在水介質中進行,微生物與試樣接觸均勻,所以此方法重復性較好。相比于有氧環境,厭氧環境具有檢測周期短、能耗低等優點,但厭氧菌在降解前需要進行孵化,并且對溫度和有害物質更加敏感,一旦失活,恢復周期較長。
2.2.2 活性污泥厭氧環境
活性污泥法是一種以活性污泥為接種物的生物處理技術,活性污泥法的降解效率與污泥數量和質量息息相關。Belone et al.設計了以十二烷基硫酸鈉和過氧化氫為原料的凈化污泥三步法,研究7種聚合物(LLDPE、HDPE、PP、PS、PET、PA66和SBR)在活性污泥厭氧消化過程中的質量、表面特征、力學性能、熱性能和官能團等方面的變化(圖5)[37]。結果表明,LLDPE、HDPE、PP、PS和PET在活性污泥處理過程中沒有明顯的降解。由于增塑劑和填料的水解氧化,PA66和SBR的完整性遭到破壞,抗拉強度均下降了約50%~60%。

圖5 HDPE, PA66和SBR降解前后的掃描電子顯微鏡圖譜
活性污泥厭氧環境下的檢測標準有ISO 13975(GB/T 38737)、ASTM D5210、ISO 11734和OCED 311等。其中,GB/T 38737是模擬活性污泥消化系統,接種物取自污泥污水消化池或牲畜糞便垃圾消化池等。通過測定試樣材料降解過程中的生物氣體(二氧化碳和甲烷)釋放量,來評估試樣材料的生物降解性。需要注意的是,污泥是一種難以管理的廢棄物,含有高濃度的有機物和病原微生物[38]。而且厭氧消化降解過程中會產生易燃和有毒氣體,如甲烷、硫化氫和氨氣等。目前,關于活性污泥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可生物降解材料(如PHA、PHB等)的生產方面[39-40]。
2.2.3 高固態厭氧環境
高固態厭氧消化降解是一種在固體含量很高的條件下進行厭氧發酵并產生沼氣的有機固體廢物處理方法。高固態厭氧消化降解過程一般分為三個階段,即液化階段、產酸階段和產甲烷階段,主要由產生揮發性脂肪酸的微生物(acidogens)和消耗揮發性脂肪酸產生甲烷的微生物(acetogens和methanogens)兩大功能類微生物參與[41]。相比于產甲烷微生物,產脂肪酸微生物的生長速度更快,導致脂肪酸無法及時被轉化為甲烷,體系pH值下降,進而抑制產甲烷微生物的繁殖,降低厭氧消化降解效率。因此,整個降解周期需定期添加堿液使體系pH值控制在適宜范圍內。
高固態厭氧環境下的檢測標準有ISO 15985(即GB/T 33797)和ASTM D5511等。其中,GB/T 33797方法是模擬最佳高固體含量(總干固體大于20%)厭氧消化環境,以厭氧消化處理后的家庭垃圾為接種物,通過測定試樣材料降解過程中的生物氣體(二氧化碳和甲烷)釋放量,來評估試樣材料的生物降解性。試驗周期一般為15天,如果生物分解現象依然明顯,可延長至生物分解平穩期。高固態厭氧消化降解具有效率高,出料量少和廢棄物資源化等優點。但是,由于其體系均一度和傳質效果較差的問題,物料在降解過程中的代謝產物易局部累積而對厭氧消化活性產生抑制作用。此外,影響固態厭氧消化過程的因素很多,如物料的負荷量、氨氮濃度、預處理方式(物理、化學和生物預處理)、消化工藝、總固體含量、微生物種類、多樣性和豐富度等[42]。代謝過程產生的揮發性脂肪酸(VFA)和氨氮濃度是抑制固體厭氧消化過程的主要內源性因素。
2.3 其他檢測方法
研究人員也會通過視覺觀察樣品在微生物環境中的形態變化,測定樣品酶解前后的質量損失、分子量分布、結晶度和機械性能等來評估樣品的生物降解性。
2.3.1 特定微生物侵蝕法
特定微生物侵蝕法就是以微生物對塑料的侵蝕程度作為評價塑料可生物降解性能的參考依據。該方法通過將試樣置于接種有特定微生物且無有機碳的固體瓊脂培養基中,在一定溫度濕度條件下培養4周以后,觀察試樣表面微生物生長狀況、試樣質量損失等性能變化來定性評價試樣的生物降解性能。假單胞菌是從土壤中分離出來的一種能夠降解各種類型塑料的生物降解微生物。Li Jiaojie等[7]利用從超級蠕蟲腸道中提取的假單胞菌對聚苯硫醚(PPS)進行降解研究(如圖6所示),提出了可用于比較和驗證不同類型塑料在10天這一短反應時間內的生物降解效率的篩選系統新思路。與之相關的標準有ISO 846—1997 塑料-微生物作用的評價。此方法操作簡單,重復性高,常用于快速評價材料的生物降解可能性,但無法給出材料的最終生物降解率。

圖6 特定微生物侵蝕法的操作過程示意圖
2.3.2 環境微生物試驗法
環境微生物試驗法是利用環境(如土壤、河水等)中的常見微生物,在實驗室條件下,將高分子材料試樣浸沒在含有環境微生物培養基中,通過測定材料質量損失、利用氣體吸收裝置收集材料在降解過程中釋放的各類氣體(如CO2、CH4等)、目測或顯微鏡觀察菌落生長情況等分析方法,來評估材料的生物降解性能[43]。環境微生物試驗法的降解機理有兩種,一種是微生物將酶釋放到周圍介質,酶與底物接觸發生降解反應;另一種是底物必須與微生物細胞緊密接觸,酶解反應發生在微生物細胞表面。此方法的數據重現性較好,但是降解周期與培養基的成分、培養條件等密切相關。
2.3.3 酶催化降解實驗
酶催化降解實驗是實驗室條件下常用的一種快速評價高分子材料生物降解性的方法。與非生物催化劑相比,酶具有一些顯著特點,即高效性、專一性、溫和性和可調控性。鑒于黑曲霉、皺紋假絲酵母、枯草芽孢桿菌和假單胞菌均已被證明對聚氨酯類具有生物降解活性,Natasha等[44]以牛血清白蛋白(BSA)為陰性對照,選用黑曲霉脂肪酶、皺紋假絲酵母脂肪酶、枯草芽孢桿菌酯酶和假單胞菌膽固醇酯酶4種商用酶對聚氨酯泡沫顆粒進行酶解處理,并用氣相色譜-質譜法和液相色譜-質譜法鑒定聚氨酯降解產物。結果顯示,聚氨酯泡沫顆粒在這4種酯酶的作用下均可降解,其中假單胞菌屬的膽固醇酯酶對聚氨酯泡沫顆粒的酶解效果最好,在24 h內產生的降解產物(二醇和二酸)量最高。
3 結束語
對高分子材料的生物降解性測試方法可歸納總結為兩種試驗方法,即篩選試驗(如酶解、水解試驗等)和模擬現實條件試驗(如土埋法、堆肥法等)。塑料材料的生物降解性能取決于塑料樹脂類型、尺寸大小、降解環境和降解時間等多個因素。其中,塑料樹脂類型直接決定該材料分子結構是否能被微生物消化降解。目前,評估生物降解材料的檢測方法標準很多,最常用的是GB/T 19277.1—2011《受控堆肥條件下材料最終需氧生物分解能力的測定采用測定釋放的二氧化碳的方法 第1部分:通用方法》。然而,此方法存在降解周期長、操作繁瑣、過程難控制、數據重復性差和檢測成本高昂等問題。現有的生物降解材料快速檢測方法,僅僅是通過化學分離和儀器分析的方法對材料各組分進行定性定量分析,并不能直接評估材料的生物降解性能。相比于純品材料,復合材料一般具有更優異的熱力學性能和穩定性。因此,可生物降解材料在單一體系和混合體系中的生物降解速率有所不同,研究復合材料的熱力學性能有利于更全面地對其降解性能進行分析。此外,前沿科學家們正致力于研究材料化學結構對其生物降解性的影響、開發可循環回收材料、通過基因工程手段研制用于降解傳統塑料的酶制劑等,旨在更加有效地解決塑料污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