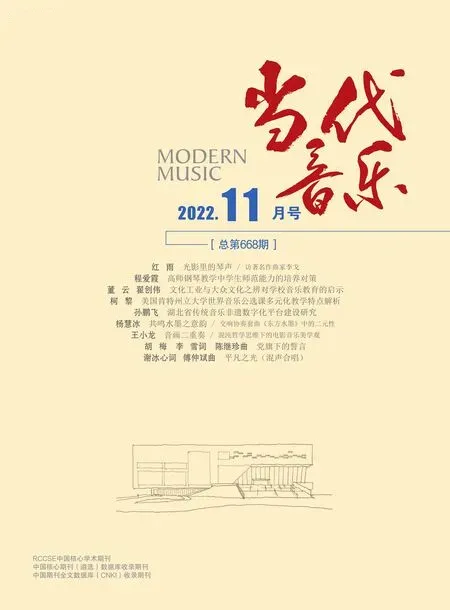節慶之聲 歲月回響
——節日文化下的三首《節日序曲》內涵闡釋與創作探究
李丹芃
節日文化是每個國家與民族文化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承載著民眾的情感和時空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新生的共和國迫切需要建立現代的、符合國家話語訴求的節日體系,一些具有特殊意義的時間成為國家節日體系建設的重要資源。[1]這些現代民族國家發展歷程中的產物,深深地嵌入當代中國人的觀念中,成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時刻。
“節日”作為一種文化活動,是藝術創作中經常出現的意象,放眼以節日為名的音樂作品,杰作甚多。“節日”題材實用性極強,易于藝術表達。“序曲”體裁短小靈活,創作和上演都十分便捷。這種體裁和題材的特性使得《節日序曲》的創作在各個歷史節點中不斷涌現,成為了音樂與社會、歷史連接的一座橋梁。本文將以朱踐耳、施萬春、杜鳴心的《節日序曲》為樣本,探析這三位成長于同時代的作曲家在面對同一命題時的創作目標與構思,聚焦于作品中如何塑造“節日”這一意象,以及其中所透露出的音樂與文化的相互關照。
一、節日內涵:主體解構與涵義重塑
(一)主體解構
本文所討論的三部《節日序曲》橫跨了20世紀60—90年代近30年的光陰。在這其間,“節日”這一字眼所能被應用的場景與指向的群體也發生著相應的改變。朱踐耳的《節日序曲》創作于1958年其在蘇聯跟隨巴拉薩年教授學習作曲之時,被作曲家視為他第一部獨立創作且成功的管弦樂作品:“以前我曾寫過幾部電影音樂,是片斷性的、不完整的樂隊作品,何況還是業余水平。故《節日序曲》才是我第一部專業性的管弦樂作品,也可說是第一部有成效的樂隊作品”[2]。雖然該作品是朱踐耳學生時代的習作之一,但作品完成時,正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十周年,為這部作品在國內的上演提供了良好的環境。1959年10月1日,由黃貽鈞執棒上海交響樂團在“上海慶祝國慶十周年音樂會”上進行了中國首演[3],自此之后,該作品也在類似場合中常有上演,這部作品由此形成了一種與“國家節日”的聯結。
時隔不久,1960年,施萬春的《節日序曲》完成了首演。從時間上看和朱踐耳的《節日序曲》是十分接近的。雖然這兩部作品都是創作于作曲家的學生時代,但與朱踐耳不同,施萬春的《節日序曲》[4]并不是學習過程中的一般習作,而是中央音樂學院專門為國慶十周年獻禮而特別打造的:“1959年我正上本科四年級,突然接到領導要我為新中國十周年大慶創作一部《節日序曲》的任務,我非常高興地接受了這個任務”[5]。由施萬春主筆,搭建框架,作鋼琴譜,就讀于本科三年級的魏作凡和民樂作曲系的徐志遠負責配器和民樂的部分,加之整個院校師生的通力合作,在極短的時間內便完成了《節日序曲》的創作任務。但由于創作時間的緣故,該作品并未趕上國慶十周年的活動,最終于1960年首演。由于反響極好,后面又在屢次上演中幾經修訂,最終形成了如今的版本。60余年來,這兩部作品經久不衰的持續上演,被改編成了各種版本以適用于不同場合,一方面證明了其內在的藝術價值,同時也難免與這兩部作品的社會屬性有關。
時間來到20世紀90年代,杜鳴心的《節日序曲》[6]不論從創作目的和應用場合來說,都與“國家節日”再無聯系。這是1990年應時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的于潤洋之邀,為中央音樂學院建院四十周年獻禮的一部委約作品,與前者相比,這部《節日序曲》不具有那么宏大的對象,而是專門為中央音樂學院這個“小集體”而作的,但杜鳴心在作品標題上則未多加限定,而是依舊直接使用了“節日”冠名。在這三部作品中,施萬春的《節日序曲》是為國慶專門創作的,自然具有著為國家獻禮的作品性質。朱踐耳的《節日序曲》雖然沒有以此為創作目的,但在作品創作完畢后的生命歷程中逐漸被賦予了這種涵義——在當時的社會語境下,“節日”未加限定,必然是“國家”的節日、“所有人”的節日。而20世紀90年代杜鳴心創作《節日序曲》時,已不再有這種思想桎梏,相比國慶,院慶只對極少數人具有重要意義,但依然可以被冠以“節日”之名:這與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的轉型密切相關——一系列亞文化群體、公民社會組織在改革的氛圍中得以活躍起來。從年初到年尾,各種屬性的節日交替上演。原本作為特殊事件的節日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習以為常的組成。歷史中的《節日序曲》創作,不僅是不同時期下對“節日”多樣解讀和主體解構的一個縮影,也是我國思想風潮、觀念變遷的一種體現和印證。
(二)涵義重塑
傳統意義上的節日一般具有較強的親和力,各個節日的儀式與行為也較為明確,大多是民眾自發性的。而現代的新生節日則更抽象,多以提升某群體的凝聚力為意義,官方行為則更多地參與其中。官方節日,尤其是政治性節日表達著紀念特殊事件的話語訴求,反映了對特定群體和人物的關照,體現著國家的價值取向,與其相關的文化事項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主流的選擇性和指向性,對身處其中的個體的意識形態亦有著重要的導向作用。
投射到具體的音樂創作之中,這三位作曲家的《節日序曲》,創作目的雖不盡相同但都在寫作過程中不約而同地聯想到了國家和人民,這與他們成長的年代與和個人生命歷程不無聯系。朱踐耳曾對自己的創作回憶道:“作品(《節日序曲》)中的主題,背景很熱鬧,好似天安門放禮花的熱情場景,這是我對五十年代初期剛剛解放不久的一片幸福的新景象、蓬勃向上的生活感受的表述。”[7]無獨有偶,施萬春的《節日序曲》也意在塑造出相似的形象:“呈示部主題表現普天同慶、歡騰熱烈的節日氣氛,表現中國人民意氣風發、斗志昂揚的精神面貌……呈示部副題用了一個上行的旋律動機,表現人們對祖國的熱愛,對美好未來的追求……盡管那個年代很困難,餓著肚子寫,但是激情四射,和當時中華民族擺脫欺凌、全國人民斗志昂揚的那種狀態很合拍。”[8]但與朱踐耳相比,施萬春的作品則明顯地更具民間風味,甚至有些鄉土氣息,一方面與具體的寫作有關,一方面也與作曲家在寫作時的形象構思有關:“北方的農村,涼爽的夏夜,寬敞的場院,男孩子們活潑嬉戲、玩耍追逐,女孩子歡聲笑語、載歌載舞的情景時時在腦海中浮現……”[9]。通過這兩位作曲家創作時的心路歷程,可以看到大的時代環境賦予人們的相同感受——新中國蓬勃的新氣象,人民幸福的新生活成為了他們共同的表達;與此同時,個體不同的經歷又使他們表達的話語產生了一定的差異——身處異鄉的朱踐耳,所聯想到的是“天安門”等最令人有民族自豪感的國家象征,其呈現出來的音樂風格也相對的沉穩莊重;身處于國內的施萬春,則著眼于實際與身邊之事,人民歡天喜地的祥和生活成為了他重點描繪的對象。
與朱踐耳和施萬春創作之時相比,杜鳴心《節日序曲》誕生的20世紀90年代,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境況已大有不同。雖然杜鳴心的《節日序曲》是為中央音樂學院院慶而作,但據杜鳴心描述,他在寫作過程不由自主地聯想到祖國的歷史。在談及創作過程中的所思所想時,杜鳴心回憶了許多過往的歲月,與前作重于表達剛解放時欣欣向榮的氛圍不同,杜鳴心在營造歡慶氛圍的同時,更希望能夠通過副部主題表現出在經歷“文革”、改革開放后的歷史厚重感,因此在整部作品中,副部主題的呈示和多次展開成為了筆墨最重之處。杜鳴心曾談到,雖無意于引導聽眾對于作品的理解,但他十分希望能夠營造出一種沉思性的,甚至帶有一絲憂傷的氛圍,展現出苦盡甘來的意味。雖然杜鳴心在形象構思上也是國家與人民,但所塑造的形象卻更中立低調,其意味也是更符合多層次的,與前二者的宏偉龐大或萬民歡慶大相徑庭。[10]可以看到,在1949年后的一段特定時期內,“節日”的首要涵義由“民俗”重塑至“國家”,已經深刻滲透到了一代人的心中及與之相關的藝術創作之中。
二、節日聲音:各具氣質的嘹亮號角
不論是在傳統民間文化還是現代政治文化中,慶典或節日中的文化內容,都是在一定的文化傳統下對具有象征意義的符號加以程式化表達。正如上文所述,三部作品產生的時代與三位作曲家的經歷使得他們的《節日序曲》皆具有了為“國家”為“人民”而做的屬性。在這些作品本身就具有的象征性之下,該追問的是如何使它們轉換為抽象的音樂語言。縱觀這三部作品,三位作曲家創作時,不約而同地使用了具有號角性質的音調,作為對這種象征的具體表達和塑造。
朱踐耳《節日序曲》的號角音調出現在引子處。整個引子部分就是在這一主題的不斷發展中形成的。引子共有28小節,可分為兩段,力圖表現出吹打樂的效果。小號開門見山地奏出穩步上行的號角主題,進行了這一主題的首次呈現。1—2小節是由分解的小三和弦組成的主要動機;3—4小節是對其的變化重復,增強了該音調的五聲性特點。
譜例1:朱踐耳《節日序曲》號角主題
除去引子外,這一號角主題也在作品的其他部位多有運用。如連接部中,引子動機與主部主題疊加、交織,不斷的模進、重復,共同構成了向副部主題連接部分,并總結了之前的音樂材料。展開部第一階段中,這一動機再次出現,長號不停的重復演奏,并進行變化和展開。爾后,朱踐耳又將這一主題穿插入主部主題的再現中,并采用復調的手法,使二者融合于一體,收獲了豐滿的音響效果。
在世界范圍內談及《節日序曲》,最為著名的作品大抵是肖斯塔科維奇之作。朱踐耳的這部作品即受到了許多肖氏《節日序曲》的影響:“我寫之前,參考過一些國外的《節日序日》,特別是肖斯塔科維奇那首。但我卻有中國的民族特點”[11]。在肖斯塔科維奇《節日序曲》引子處,也有一個號角性質的音調,在給人深刻鮮明的印象同時也是貫穿全曲的重要素材。雖然朱踐耳也使用了號角作為全曲最重要的形象,但整體的寫作手法采用了中國音樂中較為典型的單旋律,模仿中國的號角——嗩吶,用一種最直截了當的方式凸顯了中國風味,同時也區別于肖斯塔科維奇大三和弦構成的西方式號角:“小號的引子主題,有著嗩吶的氣派(若用嗩吶來吹,味道會更濃)。它是商調式的單旋律,并有模仿復調式的呼應,是中國式的線性思維,而非肖氏大三和弦的號角風格”[12]。
朱踐耳以線性思維的方式寫作,力圖區別于肖斯塔科維奇之作,但可以看到,其主題仍具有西方音樂中三和弦的性質。三十余年后,杜鳴心《節日序曲》中的號角雖然是和聲性的,但擺脫了分解和弦式的寫法,其民族化的特征體現于縱向的和聲方面。主題本身使用四五度交叉疊置的方式寫就,兩個外聲部形成了連續的平行七度,極富張力。
這一號角音調則作為呈示部的主部主題出現。首次呈示以銅管組為主體,所有低音樂器做強拍上的支撐,高音樂器演奏跑動性的織體,形成了一種“緊打慢唱”的效果。這一號角音調也作為整部作品中最為核心的概念,貫穿始終。在連接部結尾處,這一主題再次出現,交由單簧管、雙簧管、一二小提琴及中提琴演奏,英國管和一支小號對其進行模仿,形成了一唱一和的效果,并在下行模進中逐漸減少樂器數量,形成一種漸行漸遠的感覺。尾聲處,這一主題的時值擴張,不再是之前動力性極強,略帶有一絲不穩定的性格,而是變形成為更為穩重的四分音符再次出現,由小號與長號奏出。至此,除貝斯、大號外,所有樂器都以不同的方式對這一主題進行了呈示。
譜例2:杜鳴心《節日序曲》號角主題縮譜*

朱踐耳想要運用嗩吶來奏響號角,表現中國氣派的這一理想在施萬春的《節日序曲》之中得到了實現。施萬春直接選用了中國的號角——嗩吶吹奏曲牌《淘金令》作為全曲最重要的主題。在實際運用中,施萬春將《淘金令》原曲中加花的部分刪減,從而使主題旋律更為鮮明穩定。
譜例3:施萬春《節日序曲》主部主題中的《淘金令》曲牌

《淘金令》演變而來的主部主題由高音嗩吶與低音嗩吶共同吹奏,配以弦樂組模仿鑼鼓作為背景,民間打擊樂配以疏密相間的節奏,展現了普天同慶、歡騰熱烈的節日氣氛。在嗩吶對主題進行呈示后,交由弦樂組以加花變奏的方式進行重復,圓號與木管組作為背景襯托,進一步地加固了樂思。隨后的連接部以及各部分之間的連接也以模進和碎片化的方式使用了這一主題。在整個展開部的前半部分中,這一主題則通過不同樂器的交替演奏、在力度與奏法的對比與變化、不斷的離調轉調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尾聲處,主題以碎片化的方式再次出現,各樂器依次加入,形成樂隊漸強效果,在高潮中熱烈的結束了全曲。可以說,整部作品都是在以不同形式運用這一素材,并與不同材料進行呼應結合的過程中完成的。這一主題不僅是全曲最重要的形象,也是連接各部分,貫穿整部作品的靈魂。
三位作曲家在各自的創作中以不同的形式和手法表現了號角的元素,這一元素也是這三部作品中最為核心的概念。除去肖斯塔科維奇之作珠玉在前,難免受其影響外,這也與“號角”本身的特性有關:不論是西方的小號還是中國的嗩吶,都有著極富穿透力的嘹亮音色,很容易產生令人印象深刻的強烈效果,十分適合用來營造節日歡騰熱鬧的氛圍;再者,又與“號角”這一形象的文化意義有關:它既在軍隊、革命中有著重要的作用,又在中國民間的各種婚喪嫁娶等傳統儀式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無論從國家層面還是民間層面看,“號角”都是一個十分鮮明的代表性符號。因此,作曲家在面對節日題材時不約而同的運用了號角元素也就不足為奇了。
結 語
“國家是不可見的,它必被人格化方可見到,必被象征化方能被熱愛,必被想象方能被接受。”[13]《節日序曲》的發展軌跡不僅顯示了音樂在國家政治文化建設中的作用和民眾生活中的一種地位,亦反映出權威話語力量對文化建構理想的一種影響。本文的三首《節日序曲》,所表現的內容都與國家與人民有著一定的關聯,但同時各自持有迥異的氣質和多樣的民族元素。他們對時代、對生活的感悟成為了作品承載的重要內容,而作品本身也成為他們個人生涯中不同節點所思所想的一種體現。
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自由思想和個性張揚的關注成為新時代的特征。在這一背景下,一系列新興節日與傳統的民俗節日、政治節日共同構成了當代節日體系。節日的內容和形式日趨多元,傳統節日的內涵和儀式行為也在逐步更新。節日不會停息,圍繞著“節日”這一意象的音樂創作也將如影隨形,相信隨著節日外延和內涵的泛化,類似題材的音樂創作不論是在藝術構思還是具體手法上都將會有進一步的拓展和更加多元的表達。
注釋:
[1]張青仁.節日日常化與日常節日化:當代中國的節日生態——以2015年為案例[J].北京社會科學,2019(01):4—12.
[2]朱踐耳.朱踐耳創作回憶錄[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15:43.
[3]朱踐耳.朱踐耳管弦樂集 第1卷[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06:88.
[4]此處指初稿,該作品曾做過多次修訂。
[5]施萬春.樂由心生——淺談我的創作及創作理念[J].中國音樂,2017(04):7.
[6]本文的杜鳴心《節日序曲》指作曲家1990年所創作的作品。筆者所使用的樂譜為杜鳴心本人提供。據悉,杜鳴心在蘇聯留學期間亦創作過一首《節日序曲》,但目前已很難找到當年的樂譜和相關音響資料。
[7]朱踐耳、施萬春:兩部《節日序曲》誕生記[N].音樂周報,2009-10-31.
[8]劉紅慶,趙塔里木,謝嘉幸.驚日響鞭 施萬春音樂民族化探索之旅[M].濟南:齊魯書社,2014:53.
[9]同[7].
[10]以上文字來源于筆者2018年針對《節日序曲》的創作問題對杜鳴心進行的采訪。
[11]同[7].
[12]朱踐耳.朱踐耳創作回憶錄[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15:44.
[13]郭于華.儀式與社會變遷[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343.